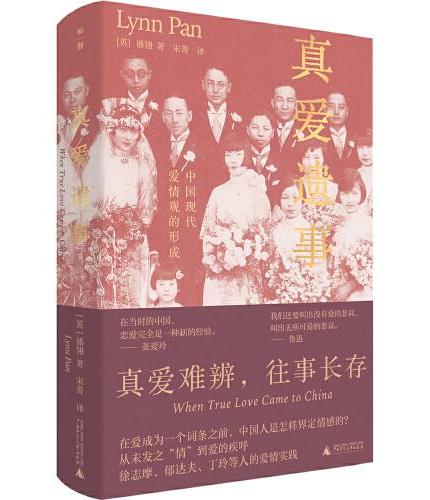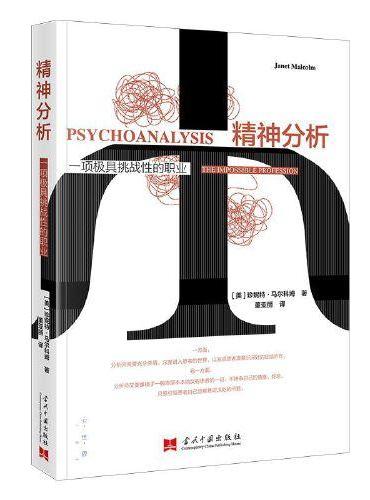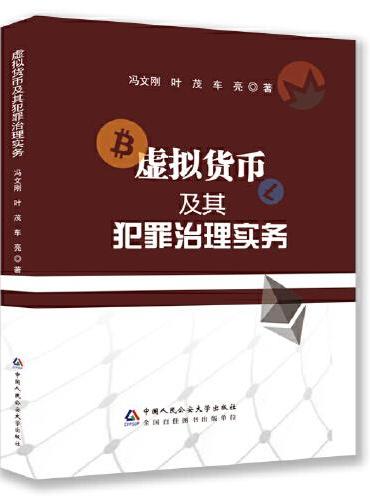新書推薦: 《
DK园艺的科学(100+个与园艺有关的真相,让你读懂你的植物,打造理想花园。)
》 售價:NT$
500.0
《
牛津呼吸护理指南(原书第2版) 国际经典护理学译著
》 售價:NT$
959.0
《
窥夜:全二册
》 售價:NT$
407.0
《
有底气(冯唐半生成事精华,写给所有人的底气心法,一个人内核越强,越有底气!)
》 售價:NT$
347.0
《
广州贸易:近代中国沿海贸易与对外交流(1700-1845)(一部了解清代对外贸易的经典著作!国际知名史学家深度解读鸦片战争的起源!)
》 售價:NT$
454.0
《
真爱遗事:中国现代爱情观的形成
》 售價:NT$
551.0
《
精神分析: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职业
》 售價:NT$
347.0
《
虚拟货币及其犯罪治理实务
》 售價:NT$
296.0
編輯推薦:
★《一天》作者大卫·尼克斯**作品:和爱人分手的方式有1000种,我都没有选择,我选择了第1001种
內容簡介:
《我们,一次旅行》是《一天》作者、英国浪漫喜剧大师大卫·尼克斯的最新作品,讲述了道格拉斯一家的故事。
關於作者:
大卫·尼克斯
目錄
目 录
內容試閱
1. 夜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