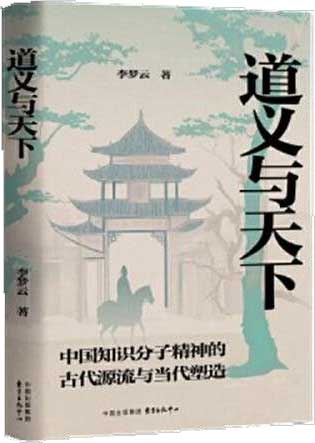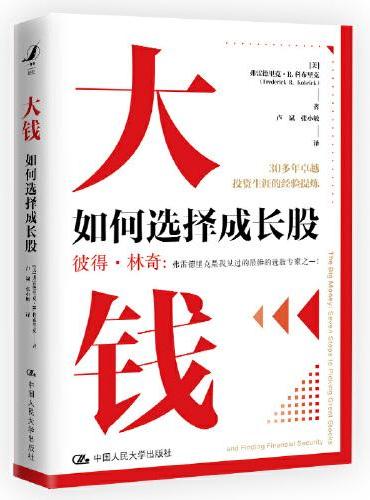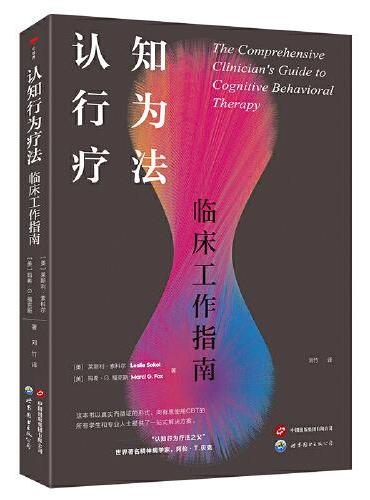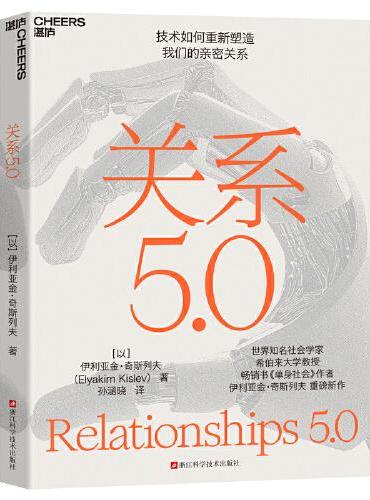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金钱的力量:财富流动、债务、与经济繁荣
》
售價:NT$
454.0

《
超越想象的ChatGPT教育:人工智能将如何彻底改变教育 (土耳其)卡罗琳·费尔·库班 穆罕默德·萨欣
》
售價:NT$
352.0

《
应对百年变局Ⅲ
》
售價:NT$
398.0

《
前端工程化——体系架构与基础建设(微课视频版)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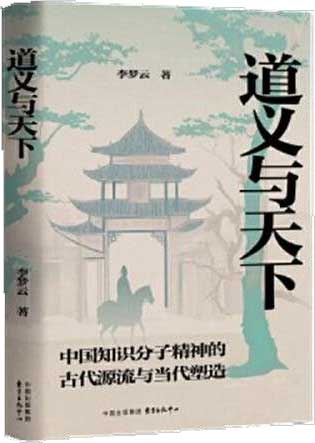
《
道义与天下: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古代源流与当代塑造
》
售價:NT$
4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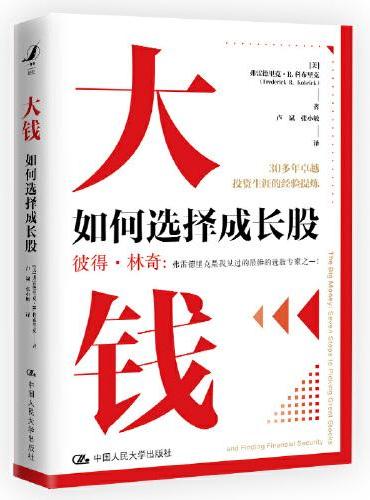
《
大钱:如何选择成长股
》
售價:NT$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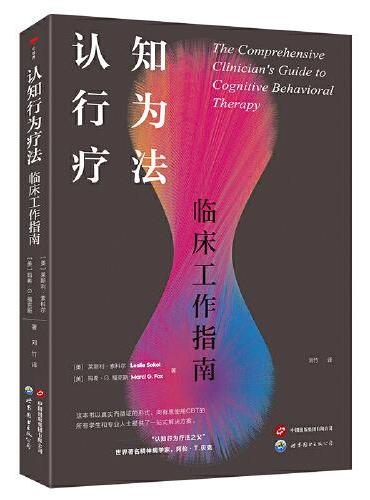
《
认知行为疗法:临床工作指南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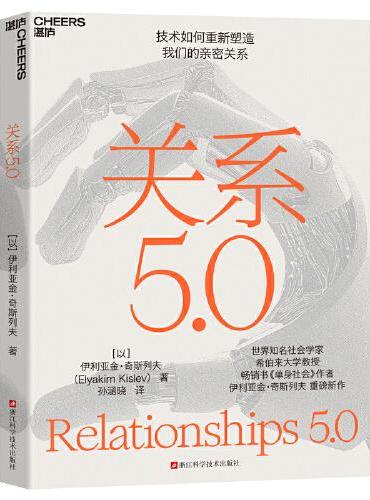
《
关系5.0
》
售價:NT$
612.0
|
| 編輯推薦: |
1944年的欧洲战场
亲历者经历血与火的洗礼
二战期间一位美国士兵在许特根森林战役与突出部战役中的英勇故事。
|
| 內容簡介: |
1944年11月,威廉?F.梅勒军士刚满二十岁。参加许特根森林战役后不久,他就被晋升为班长,因为步兵连的军官都已被杀害或者受伤。梅勒和他的士兵生活在冰冷的散兵坑里,仅凭步枪、几挺机关枪和手榴弹,以及日益减少的弹药抗击身经百战的德军士兵和他们的重型卡车和装甲坦克。
凭着坚定的勇气和决心,梅勒和第28步兵师的士兵们打完了美军有史以来*长的单线作战。然而,他们稍事喘息之后便立即被派去攻打阿登省凄冷的密林深处的德国人。梅勒和他的士兵们再次处于敌众我寡、装备落后的状态,但他们再次以顽强的精神加入到对希特勒的*后一战之中——即不久之后成为知名战役的突出部战役。素来喜欢自夸的德国国防军不得不倾尽全力对抗美国小兵。
这是一名士兵经历的真实故事。他凭借自己的风度和勇气不断适应环境,从一名普通的年轻步兵成长为军官。他以身作则,让他的士兵们懂得了如何在战争中生存下来。
|
| 關於作者: |
|
威廉·F.梅勒,二战老兵,1947年毕业于盖茨堡学院,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梅勒和他的妻子共同支撑家庭。他本人从商,事业成功,如今也已退休,居住在卡罗莱纳州北部,本书根据其亲身经历写成。
|
| 目錄:
|
引言
第一章:战役
第二章:姓名、军衔与序列号
第三章:棚车
第四章:第九战俘营B区,巴德奥布(Bad Orb)
第五章:第九战俘营,齐根海恩(Ziegenhain)
尾声
后记
|
| 內容試閱:
|
1944年12月16日,上午8:00
我一把抓住剩下的两名迫击炮队员,转身向前走去。“我想看看在雾里是否能够有所发现。跟我来。”我们在雾中慢慢地走着,异常小心。约翰的迫击炮正在热火朝天地开炮,炮壳纷纷落在我们前方右侧。我感觉不错。这是我**次听到不是向我们打来的迫击炮声。我以前从未进行过防守。黎明的到来使天色略亮,但在浓雾中的可视距离只有十英尺左右。我伸出手,可以触摸到浓雾。这种状况极度危险。我们经过比尔躺着的那个散兵坑。他们两人都看到了战友的尸体,但什么话都没有说。没必要说什么,尸体已经说明了一切。
我有些惊讶于自己的镇定;这种感觉不错。我似乎完全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迫击炮声已经停止。四周死一般地寂静,仿佛墓地。这如同对弈,彼此都在等待对手暴露自己。没有一丝动静。在这浓雾之中,远处究竟有什么呢?那些狗娘养的可能就在我们前方。我低头看着脚下的碎石路,雪已经开始溶化。我们有可能正在走入德军机关枪的射程之内;以前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们的来复枪挎在身体的一侧,里面装满了子弹,枪机已经打开。我们时刻准备摧毁雾中走出的一切。我走在前面,其余两人一左一右紧跟在后。我们离开那个倒霉的散兵坑,小心翼翼地走在碎石路上,没有弄出一丝声响。
我不想走得太远,我的机枪手不知道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的迫击炮再次开火,炮弹落在我们前方右侧。德军的枪声间歇地响起,好像正在向我们前方右侧移动。我想,那或许是一支巡逻队,正要离开。我不想在这里走得太远,被自己人击中。我们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死一般的寂静简直要将人逼疯。情况还允许我走多远呢?我不想在浓雾中迷路。我口干舌燥,神经紧张,期待有事情发生。
突然,我大惊失色,心脏剧烈跳动起来,因为我差点撞上两名德军。他们身着灰色制服,一个是上尉,一个是军医。他们就在我前面。我从未如此近距离地遇上两名全副武装的活生生的德军士兵。他们刚刚从雾中现身,正迎面向我走来。我抬高双手摇了摇。他们看见了,明白自己就站在我的枪口下。
军医举起了双手。上尉的右臂受了伤,他紧紧盯着我的眼睛,慢慢抬起左臂。我也盯着他。他想说:不要杀我,但他依旧沉默地注视着我。军医腰间别着一把卢格(Luger)手枪。我用举着枪的手指了指它,军医将枪交给了我。我取下上尉身上的瓦尔特(Walther)P38手枪,然后将两支枪全都别进腰间。这名上尉年纪尚轻,轮廓鲜明;军医年纪较大,面貌邋遢,头上戴着钢盔,臂上佩戴着红十字袖章。在这整个过程中,我的两名同伴始终举着来复枪指着两名德军,随时准备射击。
“打死他们。”一位士兵说。
我抬起手说:“我们不是杀人犯,不会打死他们。”
“这个军医携带武器,违反了《日内瓦公约》。我们可以打死他们。”
我转身面对他说:“你对《日内瓦公约》了解些什么?你要是打死他们,我就一枪打爆你的狗头。”我想起来了。他是从联邦监狱征召入伍的,是我排里**补充的人员之一。被征召入伍那天,他们三人还是同住一室的狱友。我对他们都感到头疼。
“你们两个带走军医。”
“怎么处置他?”
“带到谷仓里去,睁大眼睛,也许还有敌军。”
在我低头将来复枪指向路面时,德军上尉的眼睛一直看着我。他走在两名步兵身后,我走在他身后。他和我的体格相近,五英尺十英寸高,体重175磅,年龄也与我相仿,二十岁左右。我迫不及待想与他交谈。他一定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这些德军为什么在这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电话和无线电通讯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始终将来复枪抵在上尉的背上,边走边左右观察,谨防德国人随时出现。浓雾中有可能隐藏着一帮人,可以在几秒钟内就开枪将我们打死。我有些不安。这一切发生得太快,而且太容易。如果他们像我们一样把枪握在手中,也许我们就是举手投降的人。但是他们的枪没有握在手中,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此刻,我们处在炮位的半圆之内,已在自己的火线内。我惊讶自己为何如此镇定。德军肯定就在我们四周,但我们仅仅发现了两名。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新的伤亡人员。我不能再有任何伤亡。
我同两名曾是囚犯的士兵沿着碎石路一起慢慢走向农舍。经过散兵坑时,我指了指比尔的尸体。两名德军都明白发生了什么。
“告诉约翰在农舍里等我,你到迫击炮那边去。”我对大嘴巴士兵说。
“是。”他咕哝了一声。
我对另一个说:“你把军医带进谷仓,守着他。他如果想逃,就打死他;他如果逃脱了,我就打死你。我带这个上尉到农舍里去。”
我接着对他说:“我不想让军医和上尉待在一起。”
我们进入农舍后,我对无线电操作员斯利姆说:“你先把那东西放一会儿,看看能不能给这个德国人处理一下伤口。”
“我知道怎么做。”
我将军医的卢格枪交给约翰。“给你作个纪念吧。是你们的迫击炮弹壳让这个上尉受了轻伤。”
“我们发射了二十枚炮弹,只剩下几枚了。雾这么浓,也看不到结果。我们*好留住手头的,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好,无线电呼叫没有接通;我们好像孤立无援。我要出去看看那道山脊那边是什么。守着这个上尉,等我回来。外面怎么这样安静?”
我去了农舍左侧靠北的散兵坑。“我是梅勒。”
“我听到你来了。从今天早上起,我还没有看到一样东西,我的来复枪还没有开过火。发生什么事了?”
我告诉他刚刚发生的事情,然后要他到谷仓吃点煎饼,喝点咖啡。这些吃的是昨晚带进来充当早餐的。连里临近傍晚的时候用吉普车送来了这些食物。他们将热喷喷的食物装在巨型保温罐中送来,作为我们当天的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饭。我们的早饭可以吃到包括熏肉,煎饼,草莓酱和咖啡。
“我在这儿等你。”我说。“你吃完后,让迈克(Mike)和乔(Joe)过来。”一个人吃饭的时候,花费的时间就不会太长,因为没有同伴可以交谈。所有人就这样逐个被替换下来,飞快地填饱肚子。他吃完之后,返回了散兵坑。今早,我不需要召集他们开会。
我穿过谷仓时,负责看守德国军医的那个士兵守在他旁边。“我可就指望你在这儿守着他了。” 我说。他点头表示同意。我离开谷仓,穿过碎石路,朝右侧对着东南方向的散兵坑走去。在此刻的雾中,我的视线好了一点,因为黑暗的夜色已经褪去。我到达了散兵坑。
“迫击炮落满了这片区域。可是雾太大,看不清楚它们有没有造成损伤。”雷德报告说。
“都是我们的迫击炮,这点还不错。”
我告诉他我们俘获两名德军的最新消息。“太好了,也许我们可以用这两个德国佬交换一张离开这儿的门票。”可是,这些话是否能够真地实现,我们毫无把握。
1944年12月16日,上午10:00
“雷德,一直看着我。我要越过那个山脊,看看那边是否有情况。如果你看到有情况,就掩护我。我根本不知道那边是什么情况,这样做很危险,但是德军一定藏在某个地方。他们究竟都到哪儿去了呢?我们俘获的这两名德军迎面碰上我们,他们正去往某个地方。各处的无线电都没有回答,好像所有的人都从地球上掉下去了。
我手中握着M1卡宾枪,科尔特手枪挎在腰上。这两把枪都是从死亡的美国士兵身上征用来的。卡宾枪的子弹夹被固定到枪托上,科尔特枪的弹盒卡在我的皮带上,两枚手榴弹插在我的两个上衣口袋中,战刀插在右边的军靴里。
我前方五十码左右有座小山脊。在这清爽寒冷的空气中,松树如同许多的圣诞树,散发出宜人的气味。不知道我今年是否能够看到圣诞树。一丝微风搅动了雾霭。我可以看到五十码左右,这就好点了。光线变亮了许多,但天空的乌云仍然黑沉沉地压在头顶。白雪已经随着气温的升高而融化。温度肯定达到了华氏三十度左右。我必须谨防中枪,因为任何地方都可能有德军的狙击手,我们又没有军医。一眼望去,看不到任何东西。我心想:这里安静得像墓地。我走出树林,在一棵树下停住脚步。眼前的景象令我的所有感觉顿时凝固。我想吞口水,可嘴巴太干。我完全被震住了。我是怎样走到这里来的?我前面的雾并不浓,出现在我眼前的,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象。一座浅浅的山谷就在我脚下。这是一片绵延一英里左右的牧草地,一丝雾霭都没有。
从我所在的地方看过去,山谷大约三英里宽,里面挤满了德军。这不是战斗巡逻;这是一次侵略行动。构建一支军队需要的一切全部呈现在我的眼前:装甲步兵,兵员运输车,自驱炮,类似吉普的机动车,战防炮,以及数以万计的步兵。视线所及之处,全是士兵。他们成团地聚在一起,仿佛对空袭和炮轰毫无畏惧。这个规模看起来是一整个师的军队。(战后,我了解到,当时我看到的是国防军130装甲教导师。)令我感到庆幸的是,他们在山脊这边,而不是山脊背后。他们可能从我们身上碾过,根本听不到我们的尖叫声。他们肯定是从新木桥越过了乌日河,然后分散形成宽阔的阵线。之前,我曾反复要求过连长炸掉那座桥。可是,它依旧在那里,显然正在被德军使用,一定是我们的机关枪和迫击炮阻挡了他们,令他们无法沿路行军。由于浓雾遮住了我们的位置,他们肯定认为绕过我们要比同我们作战更迅速。他们太狡猾了。
接下来,他们会希望占据这条路的交叉口,而我们恰恰就据守在那里,迟早会惹祸上身。这座山谷中没有美军,I连总部远在山谷之外三英里处。我们被困住了。与连部和营部都无法通过无线电取得联系,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样的对峙不公平,我们或许会被迫离开自己的阵地,突围出去。
我慢慢走回布置机关枪的散兵坑。“我们的同伴比我们需要的多啊,就在山那边。看看就知道了。德国佬此刻正在战线这侧朝着我们的反方向走。”
科洛内尔爬出散兵坑活动腿脚。“你是说我们被包围了?”
“对。”
“该死的,我本来还想回家过圣诞呢。”
“我们必须先把这些德国佬从这里弄出去。”
我转身走回农舍。我的情绪开始低落。
1944年12月16日,上午11:00
斯利姆的任务完成得不错。“我把他的胳膊弄过了,给他包扎了绷带;吊腕带会让他更舒服一些。”斯利姆报告说。“伤口不大,那个德国军医已经处理过了。”
我对德国人点头示意,然后我们一前一后走进农舍的客厅。我们两个都坐到椅子上。他说他会说英语。“谢谢你给我吃的,还帮我处理伤口,而且没有打死军医和我。”我们在心里相互估量对方。“这里是你负责吗?”他问。我点了点头。他一定在想:这个头脑简单的小兵和他的士兵凭借微不足道的力量,怎么可能挡住我们的袭击?而我想的是,他要去哪里?在所有这一切中,他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他身着一件无懈可击的灰色军礼服,脚穿黑色军靴,头戴一顶作战军帽,肩上斜挎着一个双筒望远镜箱和一个漂亮的地图包。与他相比,我穿着一件破旧的野战夹克,肮脏不堪的旧裤子,破旧的战地靴,头顶钢盔。他的穿着似乎是为了参加游行,而我看似乎要去擦地板。
他与我年纪相仿,已经是一名上尉,脖子上佩戴着铁十字勋章,长夹克上则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奖章。这两枚奖章都非常重要。
他是一个相貌英俊的金发男子,很可能还是一名运动健将。德国的女孩子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的女孩子,都会认为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他的智商似乎也不错。我心中开始对他起了敬意。
“我想拯救你和你所有所有人的性命,以此报答你的善心。你在这里所做的工作值得褒奖。”他说话时,我解下了他身上的地图包。在这场对话中,我是持枪的一方,而他没有枪。他崭新的地图包是皮质的,泛着微光。我将它打开后,不由睁大了眼睛。**张地图绘制的是我们的阵地。机关枪所在的位置用红色标注,迫击炮是绿色,步枪手所在的散兵坑是黑色。农舍和谷仓按照比例绘制,甚至还包括干草堆。当他走出浓雾迎面碰上我时,他已经准确地知道自己的位置,以及我们具体的人数。这令我感到惊讶,但我微笑着说:“干得不错。”他点头作为答复。
“有三百个连行进在这条路上,每个连有三百名士兵。他们会拿下这块阵地。如果现在投降,你和你的手下的性命就可以保住。”他向我讲述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和苏联前线德军和苏军的伤亡情形。在他讲述时,我突然明白了德军如何获得了这张地图上显示的信息。
我笑了笑,然后说:“农舍。”他只是看着我,似乎默认了我的意思。唉,我真是太傻了!另一座农舍与谷仓就座落在通往德国的那条碎石路边上,就在我们阵地前方半英里处路的右侧,我们看得清清楚楚。这片地方四周全是开阔的草地,乌日河在路的正东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处。德军驻扎在河的另一侧的齐格弗里德战线内。好几次,我们几个人站在树林里,俯瞰那条河,欣赏那座新桥,倾听猎豹坦克充电的声音,观看德军排队吃饭的长龙。身处双方不会相互射杀的非战区内,感觉有些古怪。至少,在今天上午之前是这种感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