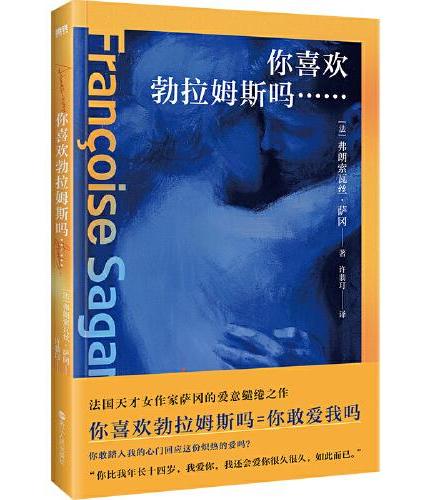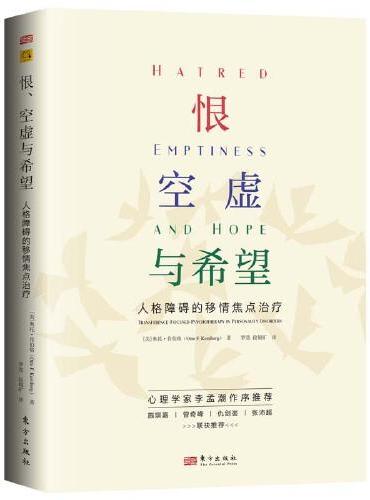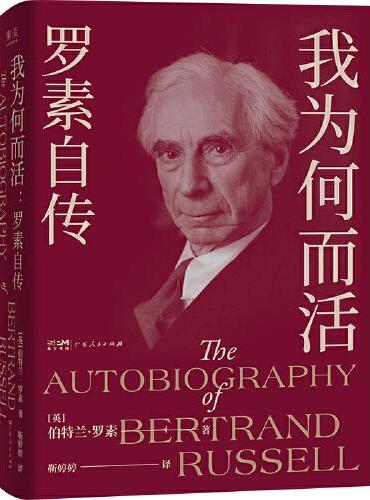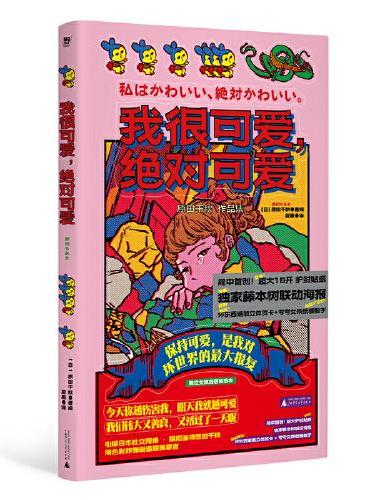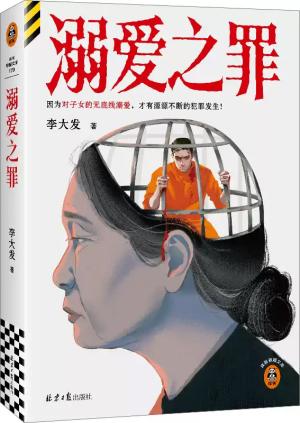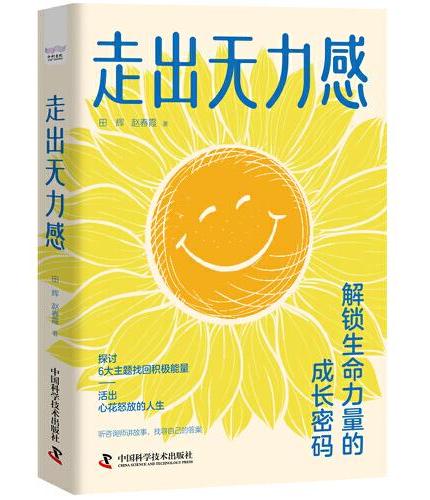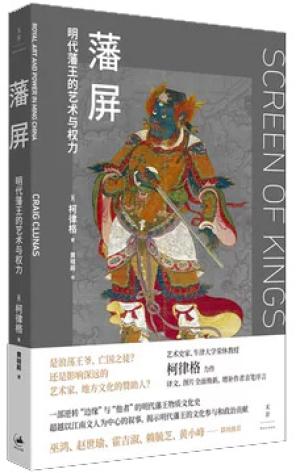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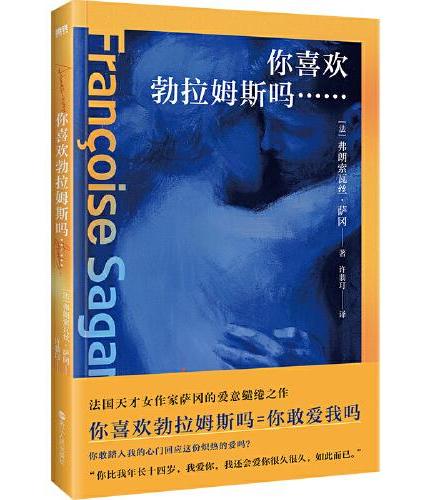
《
你喜欢勃拉姆斯吗……
》
售價:NT$
245.0

《
背影渐远犹低徊:清北民国大先生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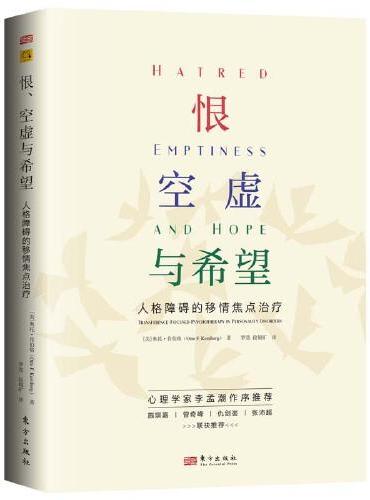
《
恨、空虚与希望:人格障碍的移情焦点治疗
》
售價:NT$
4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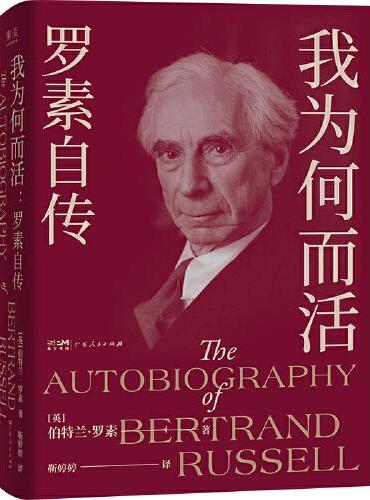
《
我为何而活:罗素自传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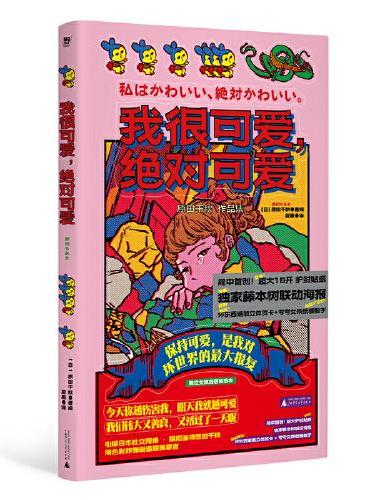
《
我很可爱,绝对可爱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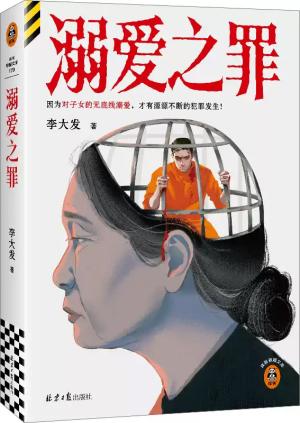
《
溺爱之罪
》
售價:NT$
25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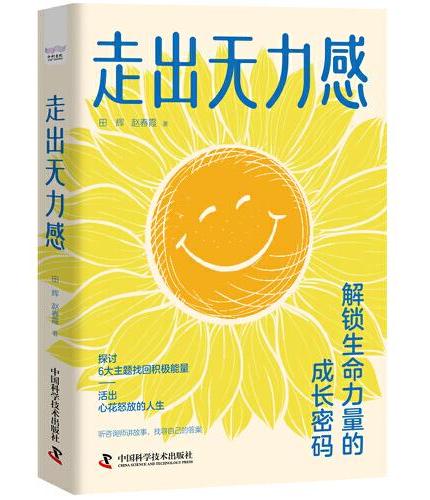
《
走出无力感 : 解锁生命力量的成长密码(跟随心理咨询师找回积极能量!)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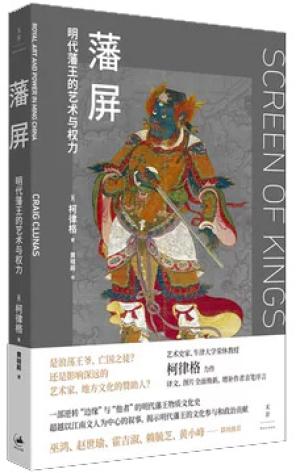
《
藩屏:明代藩王的艺术与权力(柯律格代表作,一部逆转“边缘”与“他者”的明代藩王物质文化史,填补研究空白)
》
售價:NT$
551.0
|
| 編輯推薦: |
这是一个关于名叫莫德的老人的故事。执着的莫德,可爱的莫德,坚强的莫德,勇敢的莫德,糊涂的莫德,悲伤的莫德……在她的身上,我们能看见自己父母的影子,或许还能看见自己将来老去时的点滴状态。不过莫德也稍有不同,她得了老年痴呆症,每一刻都会忘记自己上一刻做过的事情。
这是一个十分特别的故事,我们会被莫德的执念与孤勇深深打动,继而去审视我们的迷惘,我们的苦闷,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生活。我们是不是像她那样执着,那样坚持不懈?我们是怎么对待父母和老者的?我们的人生应该怎样度过?
莫德故事的创作者是英国年轻女作家艾玛?希莉,她的灵感来源于自己的祖母和外祖母,在她们的暮年时光,她一直陪伴着她们。她的文字真挚、细腻、睿智、幽默,甚至十分犀利。莫德的青春、莫德的暮年,在她的笔下,被展现地淋漓尽致。
这是一部荣获多项殊荣的作品,也是2015年英国各大畅销榜TOP1图书。
获奖情况如下:2014英国科斯塔奖年度小说处女作、2015贝蒂特拉斯克文学奖**小说、2015意大利萨勒诺文学奖**欧洲小说。
同时曾入围以下文学奖项:2014英国国家图书奖年度流行小说、2014年英国国家图书奖年度新人作家、2014
|
| 內容簡介: |
年逾八旬的莫德患有老年痴呆症。每一刻她都会忘记自己上一刻做过的事情。她纳闷地发现衣服兜里满是关于伊丽莎白的字条——
“伊丽莎白不见了。”
“她杳无音讯。”
“没有伊丽莎白的消息。”
“伊丽莎白在哪儿?”
“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
……
可古怪的是,警察、伊丽莎白“可恶”的儿子,甚至莫德自己的家人,都不肯帮她找回伊丽莎白:这些人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她?
莫德开始靠自己的力量一点点挖掘真相。她勇敢地冲破记忆的层层迷雾,执着地去寻找不见的那个人,而一切线索却指向了另一个始终悬而未决的失踪之谜……
|
| 關於作者: |
艾玛?希莉(Emma Healey
英国作家。艾玛四岁时写了**个短篇故事;八岁时渴望成为作家;到了十二岁,受到电影《独领风骚》之启发,决定长大后当一名律师。但十年之后,她重返写作之路。
艾玛大学主修书籍装帧艺术,并于2011年获得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她先后在两家图书馆、两间书店和两家画廊,以及两所大学工作。
《伊丽莎白不见了》是她的首部长篇小说,问世后收获多项殊荣,并成为2015年英国各大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图书。
|
| 目錄:
|
目 录
引子/1
伊丽莎白,你原来种过西葫芦吗?
空白记忆/3
这些空白的记忆让我不知所措。别说上周六了,昨天的事情我还记得吗?
碎裂的唱片/18
她从不倾听,倒是执意把我定义为永远活在过去的老古董。
口红/33
我得带好所有“装备”。假牙、助听器、眼镜,这些我一个也不能少。
远走高飞/50
如果一只侦探猎犬能助我一臂之力,我们就可以沿着她的气味一路追寻了。
教堂/74
一朵花脱落了,我用手将它攥住。这动作似曾相识。花是白色的,像是从婚礼上遗落的。
空欢喜/89
这是您第四次光临警察局了。警犬、法医、飞虎队,都在全力以赴进行调查。
怀念/105
很久之前,我和妈妈一起站在树下。当时的公园像是无边的大海,妈妈是一位在探测着水深的船长。
伤心花园/123
没有人在这儿等我,摆在窗前的椅子空荡荡的。原来我们常一起眺望窗外的飞鸟。
信/141
跟在某个人身后比自己形单影只要好,你可以知道应该怎么走台阶。
心碎的人/154
谈论她如同在谈论一只动物,是那种只有在神话中才会出现的鹰头狮或独角兽。
夜巴黎/167
他像是在寻找一些机关,以便将阀门打开,还原出物品背后的故事。
《香槟咏叹调》/182
面包切好了,看起来松软可口。我却看见上方有一句警示:不准再吃吐司。
我以为我要失去你/199
两只鸽子在树梢晃着脑袋,好似我和这个女人。我浑然不知,她是我的女儿。
秘密/216
那片指甲歇息在灰尘与彩线中,宛如一块儿破碎的贝壳,发着珍珠般的光泽。
猫/235
那个女人问我伊丽莎白的毛色,我一时错愕不已,但我想它应该是一只黑色的印度猫。
一瞬之光/261
每一则广告就代表一线希望,哪怕结果只是让我空欢喜一场。
伊丽莎白不见了/283
我没有纸条了,这让我六神无主。我像断了线的风筝在风中盘旋。
尘封旧案/299
我一旦开口,便会滔滔不绝。但是这些不是真的,也不可能是真的。
尾声/327
|
| 內容試閱:
|
碎裂的唱片
“伊丽莎白不见了,”我说,“我告诉过你吗?”我盯着海伦,但她却没看我。
“说过了。你打算吃什么?”
我端坐着,眼睛却朝菜单上方打量着,天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看着那些穿着黑白相间衣服的服务生,以及这里的大理石面桌子,不难判断这是一家餐馆,但是是哪家餐馆呢?我内心有些忐忑,我本应该知道的,这大概是一次宴请。但我知道今天不是我的生日,难道是帕特里克的忌日?只有海伦才会特意记下并且“纪念”这种日子。但看着外边街道上光秃秃的树木,我可以确定这不符合逻辑,帕特里克是在春天时过世的。
菜单上写着“橄榄烧烤”几个大字。菜单封面是皮质的,所以显得格外沉。尽管这个名字对我毫无意义,我还是用手指沿着这几个凹陷的大字顺次划过书脊的末端撞到了桌面,我干脆将它拉到腿上,然后大声地读着菜名:“胡桃南瓜汤、番茄芝士沙拉、蒜汁蘑菇、帕尔马火腿、蜜瓜——”
“好了,妈,谢谢了,”海伦说道,“我自己认得字。”
她不喜欢我把字念出声来,不是翻翻白眼,就是唉声叹气。有时候她甚至在我背后指手画脚,我曾在镜子中瞥见过她装出要掐我脖子的架势。“你要点什么吃的?”她问我,将菜单放低,视线却未从菜单上移开。
“腊肠馅西葫芦,”我继续读着,没办法停下来,“西葫芦近来又流行了么?我已经好些年没有在菜单上看见过了。”
在我小的时候,种植西葫芦的人还是很多的,那时候甚至有评选上品西葫芦的大赛。现在这种活动恐怕寥寥无几了。我就是因西葫芦而结缘伊丽莎白的。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家花园的围墙顶上镶了卵石,所以我便对她家的位置了如指掌。因为在六十多年前,正是在那座拥有卵石围墙的花园里,一些西葫芦被人连夜挖走了。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却很想到那个花园一探究竟,所以我便找了个机会去伊丽莎白家作客。
“你不喜欢腊肠,”海伦说着,“喝点汤怎么样?”
“我原来常和伊丽莎白一起喝汤。”我说,大脑却因一个念头而感到惴惴不安。“当年每天结束了乐施会的工作后,我们就聚在一起喝汤啃三明治,要不就是玩儿刊载在《回声报》上的填字游戏。但那都是很久之前的事儿了。”她还是杳无音讯。这让我无比费解。伊丽莎白从不外出,她一定遭遇了什么状况。
“妈妈?你必须点餐了。”
一个服务生正站在我桌子旁边,已经拿出了便笺。在我思量着他在这儿站了多久的时候,他径直弯下身子问我们想要什么。他的脸离我近得很没必要,我便侧着身子离他远点儿。“海伦,你听到过伊丽莎白的消息吗?”我说,“如果你听到什么,一定得告诉我呀。”
“会的,妈,你打算吃什么?”
“我是说,她不可能是出去度假了。”我合上菜单,想放下它,却找不到地方。桌子上到处都是碍手的东西,还闪闪发着光。伊丽莎白也有这些亮晶晶的玩意儿。它们摆放在她的桌子上,紧挨着布兰斯顿泡菜、色拉酱和很多装着麦提莎巧克力球的袋子。她那些袋子经常敞着口,巧克力球有时便会滚到地上,宛如一颗颗小巧玲珑的暗器。我常常担心伊丽莎白会因此滑一跤。“如果她摔倒了我也没法知道,”我说,“我怀疑他儿子根本不会劳心告诉我。”
服务生直起了身子,将菜单从我手中拿走。海伦冲着他微笑,点了我们两人的餐。我不知道她要了些什么。服务生点点头,边走边记,拐过了那堵饰有黑漆条纹的墙。桌子边儿上的盘子也是黑色的;我猜这肯定很流行。这家餐厅的风格就像一卷污迹斑斑的旧报纸,那种除了广告之外字迹全已模糊,***在冬季用来裹苹果的报纸。
“自己找点儿蛛丝马迹实在是困难重重,这是问题所在,”我说,意外地发现自己固守了话题,内心突然升腾起一阵兴奋,“家属均被通知,朋友则在不被告知之列,尤其是我这个年龄段的朋友。”
“这儿是原来那家小吃店,还记得吗,妈妈?”海伦打断了我。
我刚说了些什么?我想不起来。但一定是些供我参考的东西,一定。
“你想起来了吗?”
我大脑一片空白。
“你过去常在这儿和爸爸碰面,记得吗?”
我扫视了一下房间,靠着黑漆条纹墙面的桌子前坐着两个老妇人,她们凝视着平摆在她们中间桌上的某种东西。“伊丽莎白不见了。”我说。
“这儿还是小吃店的时候,你们在这里吃午餐。”
“她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小吃店,想起来了吗?哎,算了吧。”
海伦又叹了口气。她近来总是唉声连连。她从不倾听,也不把我的话当回事儿,倒是执意把我定义为永远活在过去的老古董。我很清楚她内心在想什么,她认为我精神恍惚。在她看来伊丽莎白一直好端端地待在家里,我即便是刚刚拜访过她也会转眼就忘。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是健忘,可我并不是失心疯,至少现在还不是。我对别人把我当疯子对待深恶痛绝。那些家伙在我搞错东西时故意投来“同情”的微笑,然后再给我“鼓励”的一拍,这一切都让我愤懑不平。尤其是当每个人对我的话都置若罔闻,而对海伦的言辞深信不疑时,我更加怒火中烧。我的心跳加速,牙关紧咬,我有在桌下踢一脚海伦的冲动,但我却踹到了桌腿。那些装着盐和醋的亮闪闪的调味瓶因此晃晃悠悠咯吱作响,一个酒杯也摇摇欲坠,海伦见状抓住了它。
“妈妈,”她说,“小心点儿,不然会打破东西的。”
我没有回答她,依然气得咬牙切齿。我简直要失声尖叫,但打破东西似乎是个不错的借口,这也是我现在*能泄愤的事儿。于是我拿起涂黄油的小刀,一把猛扎在桌边儿黑色的盘子上,瓷盘裂开了。我意识到海伦咒骂了些什么。一名工作人员立即飞奔过来,而我一直目不转睛盯着盘子看。盘子的中央微微裂开了,它看起来就像一张破碎的唱片,一张破碎的黑胶唱片。
我曾经在我家后花园发现过一些破碎的唱片。它们在菜地里,残破不堪,杂乱地堆叠在一起。每次我放学回家,妈妈便叫我去给爸爸打杂。爸爸会递给我一把挖红花菜豆沟的铁锹,然后消失在小棚子里。这些唱片的颜色与土壤几乎没有差别,要不是在挖土时听到咔嚓的响声,根本不会察觉到异样。没一会儿工夫,这些唱片碎片就被我的“园艺餐叉”捕了个正着。
当意识到它们是唱片的时候,我把这些碎片一一挖出来,扔在阳光照耀下的草坪上晒干。我想象不出这是谁的唱片。不过我家的房客道格拉斯倒是有一台唱机,我想到他原来似乎说过一次他的一些唱片坏掉了之类的话。无论如何,他是一个很本分的男孩儿,不像是随意丢弃垃圾的那种人。
“它们究竟是些什么玩意儿?”妈妈出来收晒干的衣服时,发现我跪在这些碎片上鼓捣,就不禁问道。
我把唱片上的土屑擦掉,开始将它们拼回原本的形状。我当然不会傻到认为这些碎片还可以放歌,只是想知道它们究竟是属于谁的。我用沾着泥土的手指拨弄着下垂的头发,脸上留下了点点污渍,妈妈一边用手将这些土渍拭去,一边说这肯定是邻居隔着篱笆墙扔进来的。
“隔壁每周都会迎来一个新房客。天知道现在那里住的又是什么鬼狐精怪,”妈妈说道,“我在园子里发现垃圾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她低头看了看这些劣质的黑胶唱片,“毁掉这些真是大快人心,一文不值的东西。莫德,把它们扔在红花菜豆沟里,好冲走它们。”
“好吧,”我说,“我只是想先把它们拼好。”
“为什么,你要为草坪设计踏脚石吗?”
“我可以吗?”
“别犯傻了。”
她笑着,腰后挎着收衣服的篮子,迈着优雅的步伐绕开这些碎片走进了厨房。我看着她走进去,她那红色的头发与房子的亮红瓷砖相比显得呆滞无光。
没一会儿我就拼好了这些碎片,在冬日和煦的阳光下,听着鸽子们彼此互动的“咕咕”声,这个工作很是让人惬意,仿佛是在拼一块儿七巧板,只不过拼完之后发现还缺东少西。但现在我能辨认出唱片的名字了:《弗吉尼亚》、《我们仨》以及《无人爱我》。
我跌坐在地上。这些唱片都是姐姐的*爱,她总是央求道格拉斯放给她听。如今,它们七零八落,与大黄和洋葱的碎渣沦为一伙。我搞不明白是谁又是出于什么原因会这么做。我将拼好的碎片再次搅乱,撒到了红花菜豆沟里。当我走回房子的时候,我看到道格拉斯在窗前伫立着,我猜他刚才一直在盯着我看,但刹那间一群鸟从树篱的暗处俯冲下来,我转过头去,正好瞥见一个女人的身影匆匆跑开。
“我必须在半小时内接到凯蒂。”海伦边说边披上了外套,尽管此时的我还没吃完手上的冰激凌。
冰激凌的口感冰冰凉凉,味道绝佳,但我却判断不出这是什么口味。不过从颜色来看,我想应该是草莓的。在走之前,我还需要去下厕所。我不知道女洗手间在什么位置,也不清楚自己原来是不是在这里用过餐。但这里的确勾起了我对一家小吃店的回忆,那时候我和帕特里克正在热恋,总是相约在小吃店见面。那家小吃店物美价廉,没有异域风情的餐点,也没有白色整洁的桌布,但菜却烹饪得色味俱佳,小店的装潢也是别具匠心。我常常在结束了交易所的工作后,在午餐时间奔赴这里,坐在一张靠窗的桌子前等待帕特里克。他的公司位于码头,是从事战后重建工作的,他常在码头那里搭电车来小吃店赴约。见我时他总会大步慢跑,面颊通红,头发甩来甩去,但他只要看见我就会咧嘴微笑。现在没有人像他那样冲我微笑了。
“你需要去洗手间吗,妈妈?”海伦已经把我的大衣递过来了。
“不,我觉得不用去了。”
“那么好吧,咱们直接出发。”
海伦今天对我颇有成见。显而易见,我是出了些状况,但那有伤大雅吗?我和服务生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我不想问海伦,以免自讨无趣。有一次,我对一个女士说她的牙齿让她看起来像一匹马,我记得海伦告诉我我说了这话,但我却不记得我说过。
“我们回家吗?”我换了个问题。
“是的,妈妈。”
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太阳就已经下山了,现在的天空颜色犹如墨水一般,但我还是能够透过车的挡风玻璃看到路标,我不知不觉地将那些字念了出来:“快车先行、平交路口、减速。”海伦的双手在方向盘上显得很苍白,她对我置之不理。我在座位上摇晃着,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膀胱就快要憋炸了。
“我们是在回家的路上吗?”
海伦叹了口气,这就意味着我刚才曾问过这个问题。当我们开上我家门前的街道时,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刻不容缓。“把我放在这儿。”我对海伦说,一只手已经抓上了门把手。
“着什么急,我们就要到了。”
我还是执意打开了车门,海伦猛地将车刹住。
“你知不知道你在拿生命开玩笑?”海伦说道。
我从车里钻出来,径直走到了路上。
“妈妈?”海伦叫着,但我顾不得回头了。
我快步走到门前,身体前倾,每隔几秒钟就得紧绷下肌肉。不知怎的,离家越近,膀胱就憋得越难受。刚才走路的时候我就解开了外套的扣子,急切地寻找着钥匙。在门前,我不断换着脚转移重心,发疯地将钥匙在锁孔里乱拧一气,可是门却迟迟打不开。
“天啊,不。”我喘着粗气。
*后,钥匙终于拧动了。我跌跌撞撞走进房里,将门砰的一声带上,手提包也被我重重摔在地上。我抓着扶手冲上楼梯,外套也被我抖掉了。但还是来不及了。解腰带的时候,我就憋不住了。我扯下裤子,却无暇顾及其他,穿着短裤就一屁股蹲坐到了马桶上。有那么一会儿,我让自己身体前倾,把头靠在手上,胳膊肘贴着膝盖,被尿浸湿的裤子就这样紧裹着我的脚踝。接下来,我用缓慢又笨拙的方式把鞋子蹬掉,把湿透的裤子从脚上拽了下来,一把扔到浴缸里。
房间里一片漆黑,但我现在又不能过去开灯,于是,我在黑暗中坐着,哭了起来。
凡事都得有理有据,得把所有的事情都记下来。伊丽莎白不见了,我不能袖手旁观,一定要让事情水落石出。但我现在依旧糊里糊涂,我甚至记不清上次见她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迄今为止我都掌握了什么线索。我给她打过电话但却没有接通,我想我应该再没见过她了。她没来过我这儿,我也没去过她那儿。接下来怎么办?我想我应该去她家转转,万一有什么蛛丝马迹呢?无论发现什么,我都要记在便条上,我现在得把笔放在包里。凡事都得有理有据,我把这点也记了下来。
离开门阶之前,我检查了三遍房门钥匙。我沿着路面慢吞吞地走着,阳光也无精打采地斜照在草坪上。唯独松树的清新味道让我感觉振奋,我大概好几天都没出门了,*近发生的事情让海伦忙得不可开交,但我的大脑现在一片空白,回忆过往只会让我头晕目眩。
我用麂皮粗呢大衣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大衣里边套着件针织套衫,里边还夹着一层羊毛裙,但我还是感到些许寒意。途经卡罗商店的时候,我在窗户前瞥见了自己弯腰驼背的样子,像极了温可太太,只是没有穿细高跟鞋而已。我边走边检查笔是否在包里,纸是不是装进了口袋。走了几步之后,我又不厌其烦地检查了一遍。毕竟*重要的事得靠它们来记录。正当我因不知道该记下什么而纠结的时候,沿途的道路给了我思路。首先得走完*后这座组装房屋,它被房主涂上了黄绿相间的油漆,很是令人作呕(伊丽莎白嘲笑过这房子的丑陋,她说如果她能发现一个陶瓷臻品的话,肯定得价值连城)。接下来要走过一家酒店的后方,那里的街道永远充斥着浑浊的脏水(伊丽莎白说那是人们早餐后倒掉的茶叶渣)。*后来到了美丽的金合欢树下,它的枝叶从满是蜗牛的前花园伸展开来(伊丽莎白每年都尝试插枝,但却总以失败告终)。
伊丽莎白的房子刷着白漆,窗户是双层玻璃的,窗帘则是网眼帘,这无疑在向外界宣布这是一户领养老金吃饭的人家。我当然不敢妄加评论,因为我家也同样安装着网眼帘。这栋房子是在战后建造的,这条街上几乎都是战后的新房子,但花园围墙却是老样子。房屋原来的主人将围墙顶上贴满了卵石,自此就再没有人改动过。伊丽莎白现在即便做梦也不会想到要将卵石挖除。在我还是小女孩儿的时候,我就特别好奇这一带的新房屋,尤其对这间有着卵石围墙的屋子念念不忘。
我按响了门铃。“铃声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回响。”我没来由地自言自语出这句话,但是无论房子是不是空的,铃声总是会在里面回荡不是吗?我等了片刻,将一只手探进门阶前一个满是泥土的桶里,这些桶里经常花草簇拥,但现在就连破土而出的嫩芽也不见半个。伊丽莎白今年肯定忘记种植球茎了,我把手迅速拿出来。我搞不清楚我的手在桶里干什么,难道我只是想摸一下球茎吗?或许我是在找别的东西?
我面朝着门,不知道自己已经等了多久。五分钟?十分钟?我看了下手表,但依然无济于事,时间总让我捉摸不定。我又按响了门铃,这次我特意在纸上记下了时间,然后看着秒针来来回回地画着圆圈。五分钟后,我记下来:伊丽莎白不见踪影。之后就离开了。或许正如别人所说,伊丽莎白去度假了。或许她现在和儿子住在一起,但我应该把这记下来的,我很确定,我有过类似的记录。那些记下的只字片语通常是我同别人展开话题的素材,也是给我自己的参考。譬如我可能会这样问海伦:“你知道吗,伊丽莎白去了法国南部。”或者干脆这样告诉卡拉:“伊丽莎白搬到她儿子那里了。”这种“新闻”对我而言价值不菲,因为海伦通常会知趣地多逗留半分钟和我聊聊。
所以我知道这次我也不会忘了记下来。伊丽莎白一定是不见了。但是目前我所掌握和证明的信息至多只能说明伊丽莎白现在不在家。
走到大门的时候,一个念头突然涌上来,不如我折回去从她家前窗望个究竟。我把鼻子贴在冷冰冰的窗玻璃上,将两只手拢在头顶,借着网眼帘的缝隙望了进去。网眼帘令漆黑的房间更加朦胧,但我却看见了空空的椅子和囊鼓鼓的靠垫。她的书在架子上堆得平平整整,那些马略尔卡陶器、花瓶还有汤碗则在灶台上排成了一条直线。我总是对伊丽莎白的“宝贝”大加嘲讽,因为那假树叶的纹理丑态毕露,那假鱼的鱼鳞更是令人不屑。但伊丽莎白却不以为然:“你不会想到的,这些物件中没准儿哪一个就是无价之宝。”她的视力不足以让她将那些“宝贝”看得真切,但她却能凭借触摸来感知,尤其是那些动物和昆虫的浮雕图案。她常用手勾勒出陶器上凸起部分的轮廓,那里的瓷釉犹如青蛙或者鳗鱼的皮肤一般光滑。她一生都在期待着发现点儿稀世珍宝。要不是寄希望于那点儿玩意没准儿真能带来金钱的利益,她的儿子早就不声不响地把它们扔进垃圾桶了。
我拿出一支笨重的钢笔,展开一张亮黄色的方形纸条,记下了这微不足道的发现:整洁的房间,伊丽莎白不在,没有开灯。我后退了几步,却不慎踏空在花坛中,一只脚陷在了土坑里。幸好我没有计划什么为非作歹的事儿。我小心翼翼地沿着花坛边缘走到房子侧面,想看看通过厨房的窗户能有什么发现。厨房这儿没有网眼帘,我很清楚地看到木质流理台上空无一物,水池也熠熠发亮。我立刻写道:厨房内没有外置的食物,没有面包,没有苹果,也没有碗碟。这些信息虽然不多,但多少得参考一下。
我穿过公园回家,大概是因为下过雨的缘故,空气清新怡人。地上的草有点结霜了,我喜欢听草被踩在脚下发出的嘎吱嘎吱声。距离室外演奏台不远的某个地方是一片下沉地带,那里宛如一个陨石坑,花草成群,还有可供休憩的长凳。说起来,海伦可没少出力,在那里参与种花种草的活动是她*早干过的大事之一,光是土她就来回搬运了几吨之多。那里可是避风向阳的绝佳去处,就连热带的花草也都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海伦很擅长让各种植物成活,她也一定知道什么地方***种植西葫芦,下次见她的时候我得记着专门问问。
七十多年来,我常常经过这个室外演奏台,因为这是我和姐姐去城里看电影的必经之路。战争期间,这里总是播放音乐,以激发人们的斗志。这儿总是不乏躺椅和身穿军装的男人,那种卡其色在明亮的草绿色映衬下非常醒目。姐姐苏姬经过这里时往往会放慢脚步,听听乐队的演奏,冲着士兵们微笑。她曾在圣廷苑舞厅跳过舞,所以也认识乐队的人。这时候我总会在她和大门之间急得跳脚,迫不及待想进城,想象着这次上映的是什么影片。真希望现在的我还能像原来那样欢呼雀跃,可我显然气血不足了。
下台阶离开公园时,我停下脚步回头望了望:天色已黑,一个人跪倒在草坪上,从演奏台那里还传来一个男孩呼喊的声音。他的喊声让我头皮发麻,不禁想加快脚步赶紧走到街上。在迈下第三个台阶的时候,一块儿亮晶晶的小石子把我绊倒了。我连忙去摸扶手,却抓了个空。我的指甲蹭在了砖墙上,手提包猛烈摇晃着,拖着我摔了下来。我的身体一侧重重砸了下去,胳膊的剧烈疼痛让我不由得咬紧牙关。鲜血从我的体内直喷出来,仿佛外界才是它们的归属。我发现自己目光呆滞,眼皮不由自主地张开,眼睛干涩难耐。
渐渐地,尽管仍心有余悸,但我又可以眨动眼睛了。因为体力不支,我爬不起来,于是索性翻了个身,休息了一分钟。这时我注意到生锈的扶手下方,一些看起来像沙土材质的漆面打着狐狸形状的烙印。我的掌缝间有些泥土,但我却想不起来是怎么弄上的。台阶的外沿划疼了我的后背。至少我终于摔跟头了,这些台阶一直是我的顾虑。还好没碰到脑袋,虽然我的半个身子和胳膊肘都未能幸免,明天就该瘀青了。我感觉这些瘀青在迅速蔓延,变成黑莓果汁的颜色。我还记得孩提时代自己身上总是青一块儿紫一块儿的,可那时候我居然能兴致勃勃地研究那些云一般的瘀青。我的屁股因为总撞上家具而伤痕累累,指甲也因缠进了轧布机而青得发紫。有一次,我的朋友奥德丽在东悬崖边上闲逛时摔倒了,为了拉住她,我的胸口重重撞到了围栏上,留下了一道黑色的印痕。还有一次,那个疯女人在我回家的路上狂追了我一路,也给我身上留下了点点印记。
那回是我被派去买东西,那个疯女人站在店内的柜台边上。当我开口告诉店主我要桃罐头和妈妈该分配到的食用油时,只见她像在和杂货店主嘟囔着什么。于是在店主称重并包装我买的东西时,我尽量躲她远一点儿,眼睛看着店里一处高高的角落。这里充斥着一种奇怪的八角味,我一度怀疑是这疯女人身上传来的,尽管窗台上那一桶桶的甘草也有可能释放这样的气味。我付完账,将货物揽到胸前,在路口等待电车通过,这时,突然感到自己肩上被重重一击。我吓得呼吸紧促,心怦怦直跳,几乎提到了嗓子眼。
是那个疯女人,她尾随我走出来,并用她的雨伞猛击我。她总是拿着一把墨黑色的破伞,伞面半开,犹如一只受伤的小鸟。她常站在路中央挥动那把破伞拦截行驶中的公交车,甚至还撩起她的裙子露出里边的短裤。别人都说她的疯癫和她死去的女儿有关,她的女儿早在战前就被公交车撞死了。人们谈起这事儿总是小声议论,或者开些彼此会意的玩笑,但如果你真想询问个一二时,他们总告诉你要保持安静,不要刺探,离她远点儿就是了,好像那个疯女人有巫术一样。
电车尾部终于慢慢驶离了路口,我又挨了一下猛击。我撒腿就穿过了路口,但她却不罢休。在我跑到我家那条街的时候,她依然穷追不舍,慌乱中我买的那些桃罐头全掉在了地上,那疯女人还在喊着一些我听不明白的话。我跑到我家厨房门前,大声喊着妈妈。她匆匆赶出来,那疯女人见状离开了,并拿走了那些桃罐头。
“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要看她,不要跟她说话,保持距离,”进屋时妈妈又嘱咐了一番。
我告诉妈妈,我什么都没做,但她还是狂追我。
“这样啊,我从没见她在杂货店里出现过。或者我们该叫来警察管管,但那疯女人的确让人可怜。我想她只是不喜欢看到这一带的年轻女孩儿吧,”妈妈说罢,就从窗户往外看去,生怕那疯女人还在附近。“因为她的女儿被公交车撞死了。”
我是年轻女孩儿就得遭这份罪?但我不禁猜想,她或许只是饥肠辘辘,想从我这儿拿点儿吃的而已。肩上的瘀青好几周都没下去,在我苍白的皮肤上黑得异常显眼,和那疯女人的雨伞一个颜色,就像那把伞把一块碎片掉到了我的肩上,宛如从受伤翅膀上掉下的一根羽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