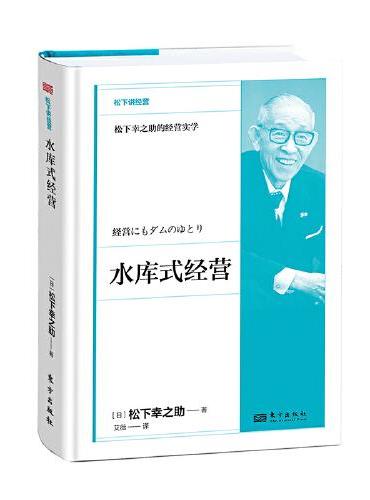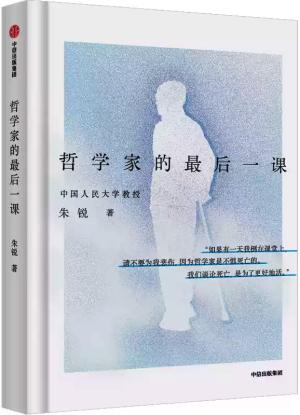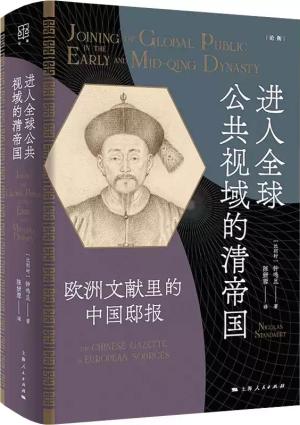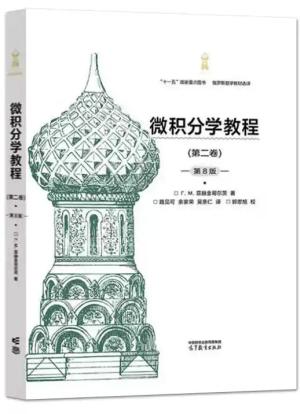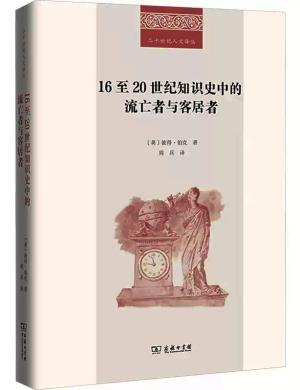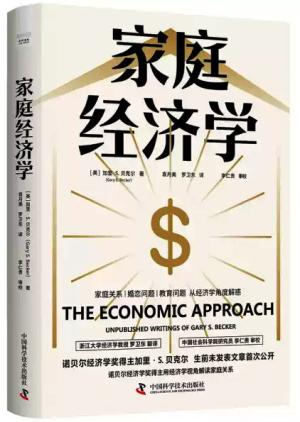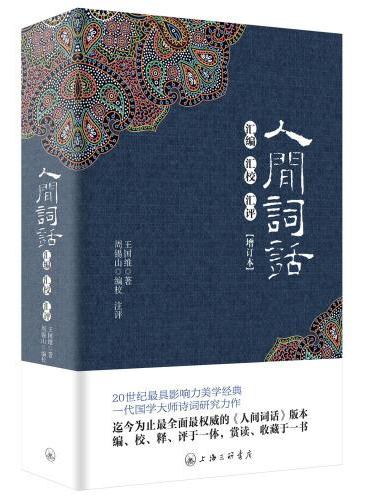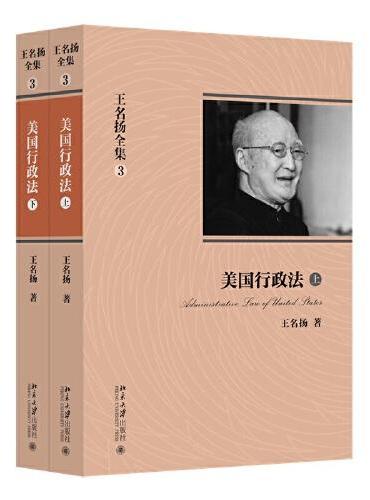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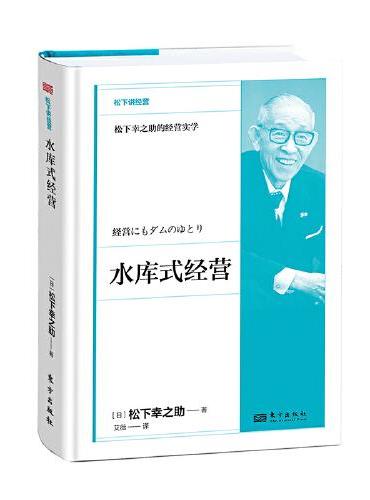
《
水库式经营
》
售價:NT$
2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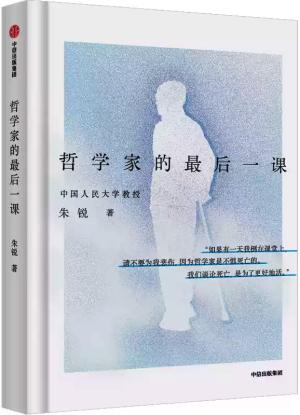
《
哲学家的最后一课
》
售價:NT$
2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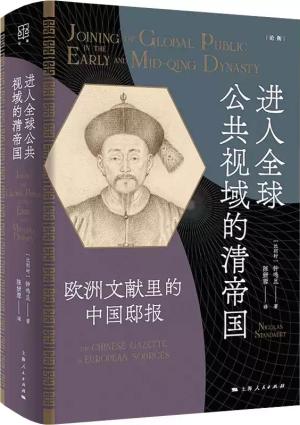
《
进入全球公共视域的清帝国:欧洲文献里的中国邸报
》
售價:NT$
6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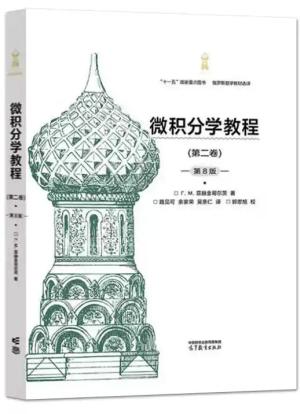
《
微积分学教程(第二卷)(第8版)
》
售價:NT$
5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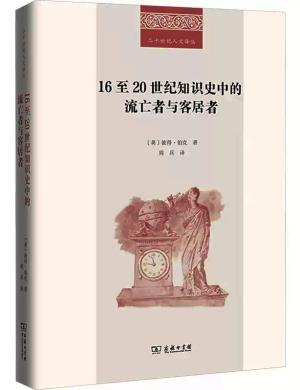
《
16至20世纪知识史中的流亡者与客居者
》
售價:NT$
48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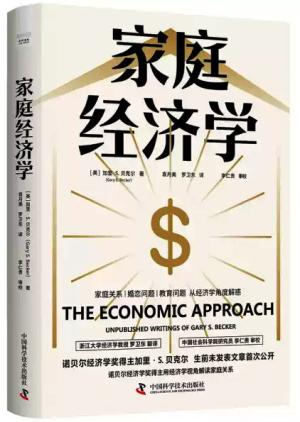
《
家庭经济学:用经济学视角解读家庭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S. 贝克尔全新力作)
》
售價:NT$
3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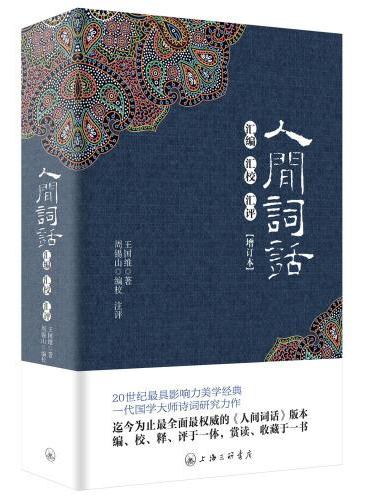
《
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新)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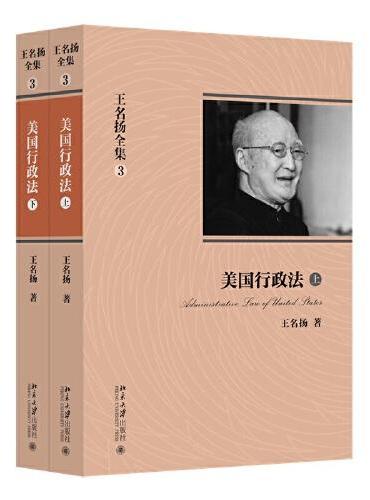
《
王名扬全集:美国行政法(上下) 王名扬老先生行政法三部曲之一
》
售價:NT$
806.0
|
| 編輯推薦: |
酒对于文人似乎总有一种特别的意义,然而即便他们有独特的饮酒“技巧”,喝酒吃菜、醉酒失态也和“常人”无异。
——来自六〇后余斌的讲述,喝酒背后的故事,更有一段过往时光的生活记忆。
|
| 內容簡介: |
“文人状写的‘酒病’,大率如此,路径是避实就虚,不说生理说心绪,撇开身体不适,升华出婉约的诗意。我是俗人,酒病既来,从来没带出什么愁绪,体味到的都是生理上的难受,——除了难受,还是难受。”
本书为余斌个人随笔集一种(共三种),无论是下酒菜的名堂,还是酒的趣闻,是关于喝酒的学问,还是醉酒的体验,余斌皆以调侃的笔调写来,但又真诚得近乎可爱。
|
| 關於作者: |
作者:余斌
六〇后,南京人,现供职于南京大学文学院。著有《张爱玲传》《事迹与心迹》《字里行间》《提前怀旧》等。
|
| 目錄:
|
第一辑 何物下酒
花生米
豆
蜂蛹
鸭四件
海蜇
凤尾鱼
烧鸡
奶酪
第二辑 且来把盏
烈酒
红酒的身价
喝啤酒,到比利时
温酒
酒瓶
分酒器的来历
世界杯啤酒方便面
第三辑 一醉方休
我把我灌醉
醉卧地板君莫笑
酒气
酒病
微醺
酒名
醉,还是没醉?这是一个问题(代后记)
|
| 內容試閱:
|
花生米
我家里没有喝酒的传统,祖父不喝,父亲也不喝。家里的饭桌上是见不到酒的,过年的时候也没有。
尽管如此,追认起来,也许我后来对酒的向往之诚,在幼时已经开始酝酿,只不过缺少自觉而已。中学毕业之前,没沾过酒,只是看过人喝酒。有两个酒人,喝酒时的表情应该给我留下过印象。一个是小黑子他爸,原本就是高喉大嗓,喝了酒更是声高,对他的拍桌子和骂骂咧咧,我有时看作豪气,有时视为粗鲁。
另一位住得离我们院子不远,常从他家门前经过,天好的时候,就看他坐在矮桌边喝酒,有时在门前的空地,有时在屋子里面,门敞着,像乡下的堂屋,另一扇门通向院内,越过他的头顶可以看到一畦绿菜。独门独户,偌大一个院子,土坯的房,土坯的墙,其实围着的,就是一个菜园子。记不得他是拉板车的还是什么别的职业,反正是干体力活的。
他们家抛头露面因此知之者众的,是他老婆,住那一片的人都叫她“陶妈妈”。她是居民小组长,常要挨家挨户地通知些事项,下达些任务—比如该交战备砖了之类。我偶或也被大人差去复命什么的,于是过其门而外,又有登堂入室的机会。
倘在傍晚吃饭的时候,老头子多半就正在喝酒。挺安静的喝法,一声不吭,慢条斯理,鼻子红红的,仿佛也有几分陶然。陶妈妈也喝,听说她“解放前”做过妓女,这个“解放后”已然消失了的行当很有几分神秘,引人遐想,当然如我之辈,也想不出什么名堂。只是有次陶妈妈来通知什么事,满口的酒气,还抽着烟,过后老阿姨和母亲说话间,似乎就把她的又抽烟又喝酒与那古老的行当联系起来。见我在一边,母亲很快就截住老阿姨的话头,陶妈妈的身份(尽管已是过去时)因此也就更显神秘。
可陶妈妈看上去与想象中妓女的艳冶、风骚一点不沾边,巴巴头(妇女梳的圆形发髻),长年一件不蓝不灰看上去脏而旧的大襟子衣裳,有点焦眉烂眼的,再就是一口被烟熏得焦黄,因稀疏而更显大的牙。她可能不像她老头子,天天喝,但也在一边坐着,抽烟。屋子里有张八仙桌,但喝酒都是在那张看上去快散架的小桌上,几只粗陋的碗碟,当然还有粗瓷的小酒杯。我去时陶妈妈除了惯常“啊吃过了?”的发问之外,有时还会让吃花生米,这让我注意到桌上有只阔口的玻璃瓶,里面装着油氽的花生,有个小碟,里面也是花生,显然就从瓶中来。后来我在其他人家看到过喝酒的人也有同样的花生储备,知道是怕花生回潮发软不好吃采取的措施,每次倒出一些便赶紧盖上盖,而瓶里面的总是较倒出的更诱人。意识中酒与花生的关系就此绑定。
既然不知酒味,闻不出酒香,喝酒人的神情虽非负面也还不能领略其妙,陶妈妈的喝酒又让人对喝酒是不是“好事”产生疑问,而玻璃瓶中的花生米却是印象颇深,我就只能假定,我对酒的向往朝童年记忆追溯下去,没准是从下酒物开始的,确切地说,是从花生米开始的。
花生在我们家算不得稀罕物儿。父母都是泰兴人,泰兴是沙土地,适宜长花生,不管哪边的亲戚进城,山芋、元麦粉之外,捎些花生,属题中应有。我不反对花生,问题是大多数时候,带来的都是连着壳的,而我被支派干家务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剥花生。这不免影响到我对家里花生的态度,虽然并不反对吃。
很长时间里,我很固执地认定家里的花生很糟糕,参照系即是陶妈妈家玻璃瓶中的。这与我们家的制作过程有关,与老家的花生品种无涉。店里卖的花生在分类上大体归在炒货。过去所谓“炒”货不像现在的往往用上了现代化设备,是地地道道的“炒”:炉上支径可三尺的大铁锅,锅中滚烫的铁砂和着花生、瓜子之类,大师傅站一旁手执铁锹也似的大锅铲,一下一下地翻炒。栗子上市的时节到处在卖糖炒栗子,有更多的店家门口支起锅来,当街作业,现炒现卖,铲子翻动一下,便有一阵香甜气味飘散开来,相当诱人。这样炒的花生,都是连着壳的。过年时自己家里也炒,不知道哪里弄来的铁砂—没这玩意儿,就容易给炒焦了。
连壳炒的花生,吃起来又要剥壳又要去皮,我有点感冒。去了壳(无油)干炒的我更能接受,省事之外,还因炒制时味道更能进去。路边小店里就有卖,通常是店家用纸包作三角形,偶或可见路人打开了且食且行。家里待客,这也是常见的品种,与瓜子并举,为炒货的大宗。印象深的有两种,一种颗粒较大,椒盐味的,皮色泛白,另一种是染了色的,近鲜红或紫红,用的是小粒的花生。前者是香里带咸,后者应该不是落选的残次品,而是另一花生品种,密实而有一种紧凑的甜香。
这些都不是专供下酒之用,其踪影在诸多并非吃喝之地的公共场所也不难一见:长途车、轮船、火车、电影院……往往人群散去之后,地上狼藉一片,花生壳、花生衣与瓜子壳同在,相当之壮观。
陶妈妈家玻璃罐里的属另一系列,是油炸的,我据以鄙视家中对应物的是这个。说到底,是因为油。不管干炒油炒,有一点是一样的:得一刻不停地翻来炒去。我不耐剥花生,却对掌勺发生兴趣,曾经主动请缨,结果炒到手酸。饶是如此,炒出的花生还是不像样子,暗红的衣子上总会黑上一点,吃起来好像同一粒上也是焦苦与生涩相伴。后来知道了,陶妈妈家的花生米粒粒匀整亮红的色泽,吃起来又那么香脆,实因那是从卤菜店买来的油炸的,—家里那点油,哪里经得起炸?偏偏我们家老阿姨还把着油这道关,炒花生时来得个(特别)吝惜,理由很充分:花生本身就是出油的,哪要放许多油?
油炸的花生米通常是连皮吃,手不碰,用筷子。下饭不行,最宜下酒。我对店里卖的东东有点迷信—家里做的与店里卖的,仿佛是专业与业余之分,区区花生米亦当作如是观。买来的自然要贵点,但我不解何以陶妈妈他们都买得起,大人就偏不肯买,非要在家里土法上马。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油炸花生米无须多少专业技术,自己也办得,只要有足够的油。
彼时在大学同学影响下,我已然开始向酒靠拢。某晚八九点钟,俩哥们突然闯到家里来聊天,因在酒的见习期中,就像学某样本事,要领在将得未得之际,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兴奋,便提议,我们喝酒吧。都说好。于是找出一瓶洋河大曲来,搜遍碗橱,除一点剩下的炒藕片,什么也没有,拿什么下酒呢?有一位发现了一碗剥好的花生米,嚷,有这个就行,比什么都好!且自告奋勇,说他炒花生米最是拿手。他说的炒其实是炸,看到他倒了半锅油下去,能将花生米都淹没,我忽地心头发紧,想想老阿姨的惜油如金,深觉奢侈得过分,只因要竭力显得大方,才忍着没让他住手。
待出了锅,果然有陶妈妈家花生米的样子,等不及抓几个尝尝,却是软的。那哥们拦着道,别急,待凉了才脆。便等着,一边就喝起来。待凉透了,已是酒过三巡,有说不出的期盼。拿盐撒上拌一拌,脆,且有说不出的香,单就着花生米,紧拉慢唱,我们把一瓶酒都喝了。
这是一九七九年的事,其时不论饭馆里还是家中,最常见的下酒菜似乎就是一碟香肠、一碟花生米。在学校宿舍、食堂,这样喝过好多回了,却好像是这一回,特别觉出花生米下酒的妙处,—别无他物,又有等待的工夫,脱颖而出,良有以也。
自那以后,凡喝酒,似乎就非花生不办了。也不一定非得油炸,盐水煮了味道亦佳,尤其在夏天,油炸的吃多了,口干舌燥,煮花生最是相宜。可以煮得烂些,也可以不那么烂,后者有咬嚼,我则更喜煮烂的棉软,与油炸的恰成对照。若说油炸花生米的香是外向型,盐水花生的香便是不显山不露水的那一种。盐水煮过之后浇上麻油,再来点醋,则香而爽,多吃不腻。
餐馆里的花样更多,什么话梅花生、蜜汁花生都来了,无非是煮了的花生经各种法子的腌制、浸泡,卤菜店里常见的则是与些少芹菜拌在一处。各有各的味,只是花生的本味隐而不彰。印象深的倒是一种唤作“醋泡生仁”的,是将花生皮也去了,生的搁醋里。小时没东西吃,有时也吃生的,是不得已,现在却发现,生吃与熟吃几为两物,生的却也有一种奇特的生香,涩里带一点甜。
大约现在人饮食里油水太多了,尽管卤菜店里没缺过油炸花生,印象中有一度似乎还是见得少了。待“酒鬼花生”出现,油炸一道,才有卷土重来的意思。似乎是从四川走向全国的,大概也借着川菜四面出击的势头。刚出现时有股新鲜劲,到处卖,以麻辣相号召,油黄的花生米中混着鲜红的辣椒屑,以这卖相,有店家玩谐音的噱头,号为“黄飞红”。一时之间,“黄飞红”一路的风头强劲,非麻辣味的被挤到了边缘。但外地人对麻辣的承受力毕竟有限,喧嚣过去,还是回到常态,店里卖的,大多是同样制法却不“飞红”的那一种了。而原先五花八门的名号也定于一尊,就叫“酒鬼花生”。
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一个牌子,后来发现乃是一种做法,有无数的生产厂家,凡这么做的,都以“酒鬼”为号。应该视为油炸花生米推陈出新的升级版吧?都是选特别的花生品种(老家的花生身材短胖,它却是长粒的,颇感清癯);去了皮再炸,炸出来多裂为两瓣,油更透得进去,照我们老阿姨的说法,本身又出油,里外相对出,特别硬挺香脆,味道格外饱满。
名为“酒鬼”,好这一口的却远出于酒徒之外,火车上常可看到乘务员推了小车来来去去地卖,而不分男女老幼,都将来做零食。命名者的思路大约是,“酒鬼”吃花生最讲究,代表着对花生米的最高要求,酒鬼专属花生米,就好比“手机中的战斗机”,再无花生米能出其右了。我虽这段时间对“酒鬼”情有独钟,倒也并不觉得它秀出群伦,至少盐水花生亦我所好。
将花生与酒并置却是深获我心。有位朋友与一位高人一起喝过酒,向我描述奇遇,说高人任什么下酒菜都不要,还特别强调一句,“连花生米都没有”。不知是钦羡还是不解。言下之意,花生米代表着下酒物的底线,若没有,则真正是干喝了。
底线往往是最基本因而也最少不得的,历数下酒之物而将花生米列为第一,其理在此。
豆
南方人称剥了壳的花生仁为“花生米”,北方人则称“花生豆”。称“米”称“豆”都是指其粒状,从定性的角度说,既不是“米”也不是“豆”。我不知现在通行的分类是不是从西人那里来,反正“豆类”(bean)与“坚果”(nut)泾渭分明,花生既为“豌豆形的坚果”(peanut),当然去“豆”甚远。
二者大概是软硬有别吧,但常作下酒物是一样的—豆子下酒,亦自不差。
名气最大的是茴香豆。因鲁迅的名篇《孔乙己》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的缘故,茴香豆在很多人最早知道的下酒菜中,当排在头名:一众酒客花一文钱买一碟茴香豆,就将来下酒,功能单一,并不兼以下饭。事实上鲁迅提到的下酒菜还有一样盐煮笋,与茴香豆同价,奈何孔乙己独沽一味,“茴”字又有“四种写法”,盐煮笋默默无闻,也在情理之中。
从知道茴香豆到以之下酒,就我而言,中间隔了好多年。不仅没吃过,也没见过,见识过的只能算是它的近亲:茴香豆是用陈蚕豆浸泡后再加茴香等佐料煮制而成,上海城隍庙有种零食叫作“五香桂皮豆”的(南京也有的卖),约略近之。“茴香”、“桂皮”均是提示味道的类型,并不涉及用何种豆子,但在江浙一带,仿佛约定俗成,一定是蚕豆。只是多用桂皮或多用茴香的差异之外,还有软硬之别:茴香豆带少许的卤,从皮到豆瓣皆软糯,盛以碗碟,五香桂皮豆则无汁干硬,近于炒货,与瓜子同科。茴香豆用以下酒,五香桂皮豆也可以,通常却是当零食,小孩、女子经常一包在手,边走边吃。下酒物与零食并非隔着楚河汉界,有不少食物乃是亦此亦彼,然可充下酒物的未必就可作零食,零食也不是皆宜于佐酒,有一端,就是下酒物得坐食。
小时吃五香桂皮豆,是当作宝物的。平日没东西吃,舍不得一下吃掉,贪那表皮上的味道,常会在嘴里含一阵,这玩意真有咬嚼,不脆,是干硬。茴香豆的软糯却是上大学读本科时去绍兴才领略到的。小馆子里都有卖,咸亨酒店里自然更不可少。绍兴人爱喝黄酒,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是按老例,论碗卖,一碗大概有半斤,孔乙己花四文钱买上这么一碗,再一文钱买碟茴香豆。—早不是这价了,不过当时仍很便宜,记得我落脚的县招待所里,散装的加饭酒是四角八分一斤。茴香豆与酒的搭配也仍未过时,招待所食堂里常有人如此这般,喝得有滋有味。
不同的酒,下酒之物的搭配或者也应有个讲究的。可能是因孔乙己的暗示,我总觉茴香豆要配黄酒最是相宜,黄酒后劲大,喝起来则一点不生猛,茴香豆的味道有点蔫,亦复相通。喝白酒就另当别论。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茴香豆虽是众所周知,却始终是一种地方性的下酒物,限于普遍好喝黄酒的浙东一带,别地不大见到。现而今咸亨酒店开到各大城市,南京已有两家了,茴香豆极寻常而仍被当作招牌菜,但似只能算作咸亨的一个节目,号召力限于店内的食客,出了咸亨,在偌大南京,便仿佛不存在。
当然,茴香豆不能代表全体豆类,南京人的下酒物中,各种做法的豆子正多。比如笋豆和兰花豆。笋豆顾名思义,是笋干与发开了的黄豆加了酱油、桂皮、茴香等味长时间地烧煮,带了卤出锅,笋与豆均不软不硬有咬劲,重重的酱油五香味。兰花豆的“兰花”则不知所云,是老蚕豆瓣下油锅炸,炸到酥透,仿佛半透明且翻翘起来—其名即是因豆瓣翻翘似花瓣也未可知,反正与中国食物、菜肴命名上避实就虚的路数是一样的,属“美其名曰”,但吃是好吃的。笋豆南京人也用来下稀饭,兰花豆则大体上就是下酒了。一香酥嘎嘣脆,一韧而耐咀嚼,代表了下酒物口感上的两大方向。我更喜欢兰花豆,去了壳的豆瓣油炸起来有一种撇除了杂质的纯粹的酥香,与花生米质地不同,放到嘴里一嚼,是一种“粉身碎骨”的酥脆。可惜也甭去评什么高下了:笋豆与兰花豆同命,不知从何时起,都已经从卖卤菜的地方消失了。令人怅惘。
黄豆也有油炸了下酒的,因是连皮一起炸,口感自与兰花豆不同,却有一优点:因粒小而经吃。隔壁院子里有个好酒的老头,秋夏天气常坐在院内,气定神闲,自斟自饮。也不用桌子,一只明清式样的破凳子当小几,上面立着其时南京平民中很流行的块把钱一瓶的“泗洪特酿”,再就是一碟黄豆,一只一两的小酒杯,别无他物。他坐旁边矮凳上,膝上摊一本书看着,不紧不慢地喝,隔一阵夹几粒黄豆到嘴中,有时眼睛并不从书上移开,却似训练有素,手感极好,总能抄底撮起几粒。途中从筷子间掉落的情形亦偶或有之,几上的要捡起吃,地下的要追回,一时狼狈。但他好像习惯于盲吃。
若不是油炸的—有一种卤的直煮到汁全部收干,表皮起绉,较笋豆更干硬而耐咬嚼—便要从容得多:油炸的手抓了弄一手的油,这却可以抓一把在手。喝口酒,扔几粒入口,很是笃定。我到他们院里去或从外面经过,常看见这一幕,不管炸的卤的,一顿下来,总要喝上一两个钟头。看人喝酒令我油然而生钦羡之意的,这老头肯定是一位,而黄豆无疑最能满足此种马拉松式的单干喝法。
可能是呼应对咬嚼的要求,下酒物中的豆子大多都是陈豆。与新鲜的豆子不同,虽是要以水来发开,却是淀粉味道重,没了那份水灵的嫩。新鲜豆子太嫩,炸不得,也经不起千锤百炼式的煮,但也并非不可用来下酒,只是这时要吃的是个新鲜劲了,故多是刚上市之时。江南一带的人喜时鲜,毛豆、蚕豆、豌豆上市时最是趋之若鹜。若豌豆,初时豆实尚在发育不全的阶段,淀粉少而水分多,吃起来与要将豆荚涨破的盛年豌豆几为两物,尤有一种清甜。蚕豆亦如此,固然也可剥出豆瓣来吃,然豆实不丰,内容无多,皮与肉也分不甚清,还是整粒带皮的好—事实上鲜味相当部分即出在那嫩时很厚的壳上。烧时要留新鲜本味在舌尖,油炒、水煮,盐而外无需其他味道。
不过以下酒而论,最常见的似乎还是毛豆。都是连壳煮,除了盐什么也不放,最实在的叫法,“盐水毛豆”,干干净净地地道道的本味。多年前我在苏州跟人在乡下喝过一顿酒,其他吃了什么都忘了,只记得各人面前堆了一堆毛豆壳,齐眉毛高。
还有一种,说新也新,说陈也陈,—我说的是发芽豆,芽是新芽,豆是老豆。发芽豆是老蚕豆温水里泡软之后搁在温度高的地方淋上水令其长出一点芽。但还是豆,不是豆芽,如果以黄豆芽绿豆芽为参照的话。豆芽的豆已成为芽的附庸,发芽豆则还是维持着豆的形态,那刚露尖尖角的一点好比多长出的一颗虎牙—都是才长出一点点就弄来吃了。我曾好奇地问过不止一人,如果像黄豆芽、绿豆芽一样令其生长下去,以蚕豆的体量,所得会不会是比豆芽粗大得多的芽,蘑菇柄似的,附带的一问是,怎么没见用蚕豆做豆芽?许是问得不是地方,没有人能回答我。
发芽豆妙就妙在不芽不豆,亦芽亦豆,方死方生之际,有豆的口感,又有芽的清甜味儿。大概有多种做法吧?至少我就见过和腌菜在一处炒,早上下泡饭。但我觉得盐水煮了最好,本色示人,保留了特有的一种鲜甜,不是嫩豆子那种清新的甜,不是老豆的面甜,也不是发酵带出的甜,只能归之于萌而未发的状态吧。
下酒嘛似乎还是黄酒为好。事实上,凡烧煮的豆,我都以为和黄酒更搭得上。
据说南京人过去也吃发芽豆,我却没见过,是在上海才知道有发芽豆一说。上海的菜场里就有现成的卖,可知上海人好这一口的人还不在少数。因下过泡饭也下过酒,对那特别的味道很是倾倒,回南京后偶进菜场还特别留意过,却见不着,很觉遗憾。
蜂蛹
下酒之物,各有所好,往往带有地域色彩,像花生米那样具有普遍性,地不分南北而都不吝称颂的,恐怕数不出几样。当然也就有有些人视为极品,另一些人不屑一顾甚或避之唯恐不及的,如蚂蚱之类,却也不多。
有个在云南插过队的朋友,最喜将当年在乡下的经历说得神乎其神,酒酣耳热之际渲染喝酒的种种,更是眉飞色舞。他说什么都拿来下酒,最过瘾的蚂蚱,一捉能捉上好几斤,开水烫一烫,掐了翅膀去了腿,扔锅里烤到焦黄,待水分尽失,椒盐一拌就开吃,香啊。又说有时更省事,围了油灯喝酒,也不拾掇,筷子夹了就在油灯上烤,腿啦翅膀啦燎得噼啪作响,现烤现吃,烤一个吃一个,再喝口酒,简直赛过神仙啊。却又补充道,最香还当数油炸的,麻油拌拌也不差,可怜那时没有油吃啊。
在场的都没下过乡,更没去过云南,听得啧啧称奇。后来才知道,不足为奇,传说的“云南十八怪”里就有“蚂蚱当作下酒菜”一说。只是外人听来,还是觉得不可思议,就像我们虽有悠久丰富的食虫传统,听说某地又或某餐馆拿昆虫当菜,虽不至当作天方夜谭,却仍不免莫名惊诧,仿佛有此一举,去文明远矣。
有一不喝酒的老同学,大概是认定人同此心,情同此理,听一帮熟人中的酒徒在网上聊酒经聊得欢,说下酒物越说越奇,有意要恶心诸人一把,便贴图一张,其上是一各类油炸昆虫的拼盘,从竹虫到椰子虫到蜂蛹到蝎子,不一而足。调侃之意,不言自明:想来点稀奇的?好,就来,看吃得消吃不消!
不知其他人如何,我反正是没被吓倒。并非在吃上面多么无畏,实因此前已见识过。云南人在异地做餐饮,过桥米线一类的小吃不算,大些的馆子,都会打两张牌,菌类之外还有一样,就是昆虫做的菜。在南京也是如此。早先“水木秦淮”一带有家“鲜菌阁”,火锅是主打,各种奇奇怪怪的菌菇往锅里涮(到最后那锅汤鲜到无可再鲜),也有冷盘、炒菜,无什特别,称得上独树一帜的,就是虫。五台山体育场那儿的一家唤作“云南味道”,规模大一些,也更能满足吃上面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
当然,少不了虫—在菜单上自成一个系列。别地的人当然也有吃虫的,却绝无这样的花样百出,大张旗鼓。南京人在吃上大体偏于保守,我不相信有多少食客对虫情有独钟,但到这儿来都有奇与怪的诉求,聊备一格,当然要点。座中若有女士,看着菜单上这虫那虫,大都花容失色,待择一二点上来,肯于一试的,无不战战兢兢,筷子不像是奔向美味,倒似在接近恐怖分子。
菜单上的虫有贵有贱,不晓得论价的依据。做法倒是简单,大体上就是油炸。我想除非是囫囵着吃,否则油炸相对而言也许是最能祛除惊悚心理的一法—虽不能令其彻底“陌生化”,炸得酥透了于吃时防止不必要的联想,总是更为有益。但若是个大的虫,就未必能臻于酥透的境界。有次要了一种椰虫(命名的一个依据是虫的寄生之地,如长在竹子上的虫便叫竹虫,以此类推,椰虫应是长在椰树上),炸出来还有小手指指头粗细,外面是焦脆的一层壳,里面则不仅是软,竟有几分呈灰白的粥样,端的让人举筷为艰。即使不说其他,下酒总称不上妙品。
其时正喝着酒,于是想起那年在云南的喝烈酒,吃蜂蛹。一九九二年与夫人去云南旅游,其中的一站以走亲戚为主,是到靠近越南那边的砚山县她大舅家。砚山小地方,没什么地方可游,整天窝在家里喝酒。大舅精瘦精瘦,却是精力旺盛,退休了,以搓麻、喝酒为主要生活内容。隔三岔五搓麻到夜里一两点钟回来,回来了且不睡觉,若有尚未上床的人,便拉着道:“喝酒!喝酒!”我做客的那段时间,这主要就是二表哥和我。二表哥是县多种经营办公室的头儿,家里的各种药酒也经营得不错。开喝之前大舅总要领我到放酒的地方,问喝什么。眼前是一溜装化学试剂那样的有玻璃塞子的大玻璃瓶,这个里面泡着乌龟,那口里泡着牛鞭,再一个泡着三七,还有好多叫不出名目的。我对一切的泡制的酒皆说不上什么期待,以为破坏酒的香,只是出于礼貌赞叹一番。若说此时有所期待的话,我希望的是端上来的下酒物里有蜂蛹。
这愿景多半不会落空,因蜂蛹二表哥显然也是多有“经营”的。大舅是当老爷当惯了的,回来嚷几声拿了酒来便坐等开喝,二表哥若是没睡(多半也是从外面刚回),便整顿一两样下酒的,否则大舅妈或某位表嫂会从床上爬起来侍候。砚山还是烧灶,生火挥锅铲,动静似比用炉子来得大,大舅又还会不时大声地下指令(无非“多些油”、“别忘了放盐”之类),虽只是一两样,大半夜万籁俱寂中,就有一种大操大办的声势。
有时有上一顿剩下的,也会将就。蜂蛹都是装进密封的罐子里,怕受潮变软。当然,哪里有现炒现炸的可口?多半是炸,也可以说是炕,关键是要令其水分尽出。坐在院里,一阵阵的香气就夹在柴草的气味中飘过来,待端到桌上,更是扑鼻的香。
小时在外面淘,逮着什么都吃,蚕蛹、蝉蛹、蚂蚱什么的,似乎都吃过,但都印象不深,除了只能是“尝鼎一脔”偶尔偷食(背着大人),食不得法(都是一帮很小的小孩自己瞎折腾,半生不熟的几率很高)之外,更因意不在吃,重在折腾,很大程度上应定义为玩耍。还有一条,一边喝酒一边吃与干吃是不一样的。下酒菜固然是佐酒的,然若是合适,喝酒的那一份悠然更能令其“境界全出”,真所谓“相得益彰”。蜂蛹作下酒物,便是如此。
蛹是幼虫,身上没成虫那么多水分,全身更是一体的状态,密实得很,没发展出种种器官,上上下下都是“肉”。酥酥的吃到嘴里,另有一种咬嚼。那香是蛋白质的香吧?辨一辨,似既非动物也非植物,不是肉的香,也无豆类的淀粉味。昆虫未长成之前,比如尚未羽化的蜂蛹,还不会动,就不应算“动”物吧?夫人有时候看电视打游戏到这时也还没睡,不喝酒,却屡被大舅招到桌上吃两口垫垫肚子,有次就与她辨析这问题,学理科的,容不得我旁门左道的想象,便有争执。大舅喝口酒拣粒蜂蛹扔嘴里,哈哈笑着道:“争啥子吗?蜂儿好吃不好吃?好吃?那就多吃。喝酒!喝酒!”
便吃。便喝。
鸭四件
“鸭四件”其实是两样,鸭翅与鸭爪而已,以单只鸭计,则上上下下,共得四件。四川人有个更富动感的命名,叫“飞飞跳跳”,翅所以飞,爪所以跳,虽说鸭子其实是不大跳的。
鸭四件很能满足下酒菜的要求。其一,经吃。一盘菜,若三口两口风卷残云吃个精光,那肯定不宜于酒。南京有些人将那种很能下饭、量大而风格偏于粗豪的菜肴称作“满口菜”,言下其实有对中看不中吃走精致一路的菜品的不屑(讥之“不够塞牙缝”)。此处所谓“经吃”却不是指这个:“满口”是量大、实惠,“经吃”则偏于强调耐咀嚼,“可持续发展”地下酒。
是否可充下酒之物,从无明文规定,极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凡上得餐桌的,无不可以拿来下酒。只是大概其的(大致),喝酒的不喝酒的,都有个关于宜与不宜的共识。倘要排个座次,列举出来的,应该和餐馆里上菜的顺序差不多,冷菜—热炒—烧菜,而头几位的十有八九是凉菜:下饭可以无须凉菜,喝酒则似乎非有凉菜不可。若同类东西有冷热之别的不同做法,喝酒的人肯定先取卤、拌、炸的那些,比如,宁取酱鸭、烤鸭、盐水鸭而不取香酥鸭,宁取熏鱼、油炸小黄鱼而不要大汤黄鱼,宁取凉拌香干而不取蟹黄豆腐……不是拒绝属热菜的那些,是得有凉菜打底。烧菜类连汤带水,更宜下饭,炒菜烈火烹油地上来,却也凉得快,凉了就口味大减,且重新加温也不是办法,而喝酒紧拉慢唱,总得有半个钟头的工夫,速战速决殊少悠然之趣。
那么何必鸭四件?单说与之本为一体的,鸭子的主体部分,不论为酱鸭、为烤鸭(南京连皮带肉吃的那种,北京烤鸭的吃法则殊不合下酒的要求)、为咸水鸭,何尝不是下酒的佳品?若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式的豪饮,属但求一醉与唯求一饱的合流,自然要得,且斩成一片片的鸭子使筷夹来吃恐怕还嫌斯文,徒手撕下腿来大嚼,方才过瘾。但若是想由渐进而达于陶渊明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式的陶然,满是肉的部位就嫌其太实,饮酒不可空肚,却也不可是饱腹的状态,肚子早早就填得满满,则酒便难得持续发展的空间。畜类边边角角、筋头巴脑的所在,与循序渐进式的饮酒,最能相契。所谓筋头巴脑者,实不止于鸭四件,举凡鸭舌鸭脖、鸭肫鸭心,均可入列,只是吃鸭四件似更普遍,可充代表。
说是鸭四件,现在的趋势似乎是鸭爪潜踪,翅膀横行,原是一起卖的,如今卤菜店里更常见的是翅膀。那么且说这个。
鸭翅看上去的确比较“横”,拐子杵在那里大钳子似的。其实却没多少肉,比鸡翅不如。有了鸡场大批量饲养的肉鸡之后,鸡翅已是和鸡的其他部分一样肥大多肉起来,渐渐也都按洋人的法子分解,可以有整根的,多数是“把汝裁为三截”,分为了翅尖、翅中、翅根。翅尖而外,皆多肉,头一回在洋快餐店里见到翅根,还以为是小个子鸡的腿。比起来,鸭翅枉自张牙舞爪地空有大骨架,却有点骨瘦如柴的味道,与肥硕的臀部整个不相称。但在别处的劣势,喝酒时却转为优势—又不是图它的肉。
倘说鸡翅丰若有余,那鸭翅简直就是皮包骨,肉多处也不过是骨头间的丝丝缕缕,加上关节处的脆骨,吃的过程以啃为主,辅之于嚼,几乎没有吃肉的感觉,肉的消息端在有无之间。咀嚼之外,作为载体,所载更在味道。鸭肫鸭心,也能提供咀嚼之妙,却仍伤于太实,易演为另一意义上的吃肉,内脏胆固醇高,在群起讲究健康之道的今日,尤其不宜提倡。鸭四件就绝无这样的弊端。吃时的稍有难度(须动手)还更令喝酒添几分从容,慢节奏里,酒与下酒物,才能“津津有味”。
说到味,已涉于下酒物要求的第二项,便是不咸。据说有人可以用甜食下酒,大多数喝酒的人恐怕还是视为旁门左道。“下酒物”常被归为“下酒菜”,“菜”为咸味,至少对中国人,不言而喻。然下酒菜不同于下饭菜,下饭菜不妨咸一点,下酒菜则不宜太咸。盖“吃”贯穿于“喝”的全过程,此时的“吃”大多又以“菜”为限,不及于“饭”,若下酒的如同下饭的那般咸法,那还不齁死?
鸭四件是可当零食吃的,零食的定义之一是可以空口吃,据说成都街头拿在手里啃的淑女,不在少数,这也就见得不会怎么咸了。以我所见,鸭四件多半是卤,鸡翅有烤的有炸的,鸭翅大概是过于皮包骨了,烤与炸两皆不宜。此外较常见的是和黄豆一起红烧,也不咸。
当然话不可说绝,自川菜四处攻城略地以来,各地方的人似也在向着重口味一路高歌猛进,下酒菜跟着水涨船高,南京一地旧有的下酒物固然还是维持着一向的清淡,新进的有些品种可就大悖有味而不咸的原则。好在人的口味是有“常”又有“变”的,像其他事情一样,“吃”上面越轨的冲动有时在明知不合常规的情况下也仍然不可遏止。且说一样与鸭四件沾亲带故的吧,我说的是鸭脖—不论作为零食还是下酒物,此物都称得上迅速崛起的新秀。
鸭脖子南京人并不陌生—南京号为“鸭都”,鸭身上的一切南京人皆不会放过。只是过去并不像鸭四件那样可以自立门户,通常都是以整只烤鸭、盐水鸭的边角料出现,卤菜店的规矩,买半只鸭则搭鸭脖或鸭头,半只鸭还可再析为前脯后脯,前脯什么都不搭,后脯通常搭一截鸭脖。鸭头早有单卖的了,一些酒店里甚且号为“金陵鸭头”,鸭脖却始终是附庸地位。按说鸭头鸭脖很合于下酒物筋头巴脑的要求(尤其是鸭脖),问题是整只地卤制,要让鸭身上肉厚处也入味,结果必是这些部位偏于咸,不像鸭四件,自成一体,味的浓淡上可另有尺度。
想不到在鸭脖上做出了文章的是吃鸭之风远不如南京之盛的武汉人。曾几何时,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都见卖鸭脖的了,论根卖,十元钱三根。好多连锁店,并非只卖鸭脖,也卖其他的零嘴,却都以鸭脖相号召,足见已是深入人心。而在吃鸭脖上面,我比大多数南京人领先了一步。
到武汉出差,其时“精武鸭脖”尚未走向全国,却已是风靡武汉三镇,打道回府之前,同行的人齐赴号称正宗精武鸭脖店所在的精武路,左近一带,数不清的店家,沿路一溜不锈钢桶,里面盛着卤汁,麻辣之气,扑面而来,无数的鸭脖堆在案上,让人遐想那些鸭子的去向。我们各人买了许多上火车,原是准备当土特产尽数带回的,火车开动后聚在一起喝酒,就想,何不拿些来作下酒菜?
也不知是否因有“正宗”的暗示,觉得较之后来在南京所食,特别肥大,仿佛武汉的鸭子一概甲状腺肿大。下酒无须肉多,但毕竟是鸭脖,拢共骨头缝里那点肉,还是活肉,且以那么重的味道,没点肉也架不住—真是辣,真是麻,也真是咸。或者是因为在车上,不安定的环境,喝酒也相应地是豪放的喝法,倒也不嫌味重。不仅不嫌,而且上瘾。吃得大汗淋漓,甚且汗珠子吧嗒吧嗒朝下掉,嘴里丝丝响着不胜唏嘘地,还是刹不住车地要吃。倘要练酒量,绝对要得—单是要压下那刺激性的重味,你也会不住地喝酒。那晚上一直喝到天亮,两大包鸭脖吃下去,啤酒喝完了继之以白酒。
当然是痛快,不过那是“非常道”,此外也因大体上喝的是啤酒,似乎大口灌啤酒才压得住,倒像是以酒来下鸭脖了。所以倘回归喝白酒的主流,还当鸭四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