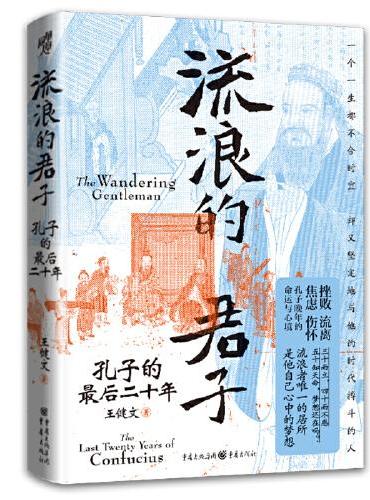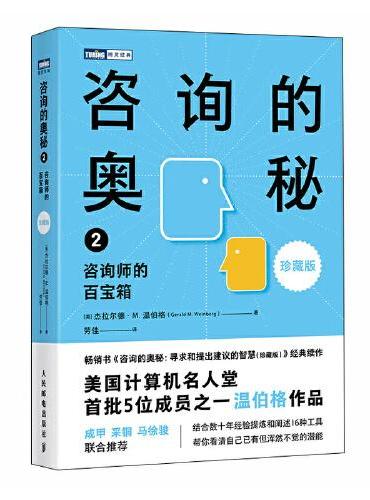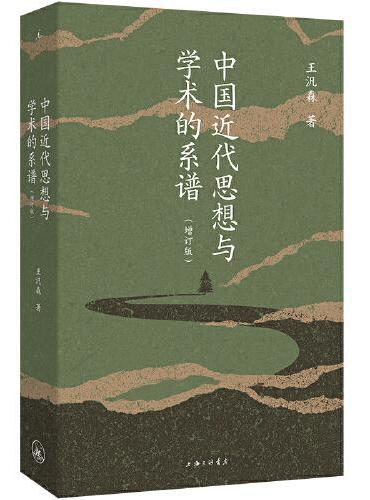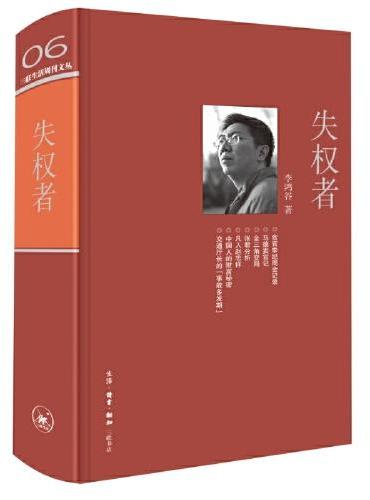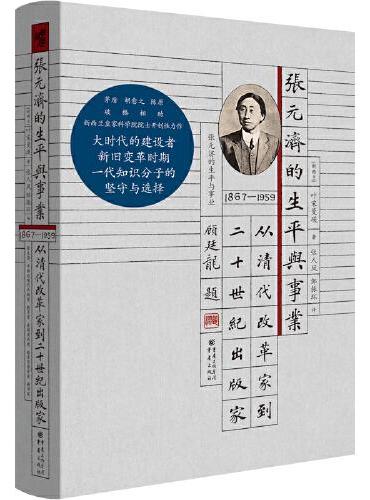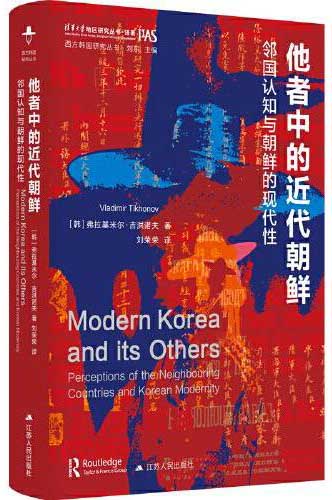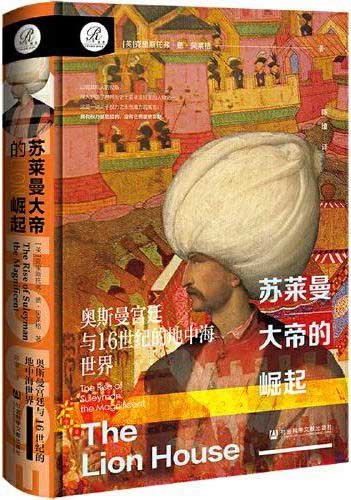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 王健文
》 售價:NT$
254.0
《
咨询的奥秘2:咨询师的百宝箱(珍藏版)
》 售價:NT$
356.0
《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
》 售價:NT$
500.0
《
失权者(三联生活周刊文丛)
》 售價:NT$
352.0
《
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
》 售價:NT$
398.0
《
他者中的近代朝鲜(西方韩国研究丛书)
》 售價:NT$
398.0
《
索恩丛书·苏莱曼大帝的崛起:奥斯曼宫廷与16世纪的地中海世界
》 售價:NT$
403.0
《
攀龙附凤: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增订本)宋代将门百年兴衰史
》 售價:NT$
454.0
編輯推薦:
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作品文艺气质的末日科幻
內容簡介:
《第十一站:写给这世界的一封情书》讲述了:雪夜,一位男演员猝死在话剧《李尔王》的舞台上。数小时后,人类文明因为一场流行瘟疫而分崩离析。
關於作者:
加埃米莉·圣约翰·曼德尔Emily St. John Mandel
目錄
第一部剧院
內容試閱
第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