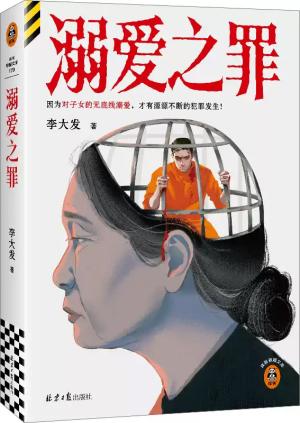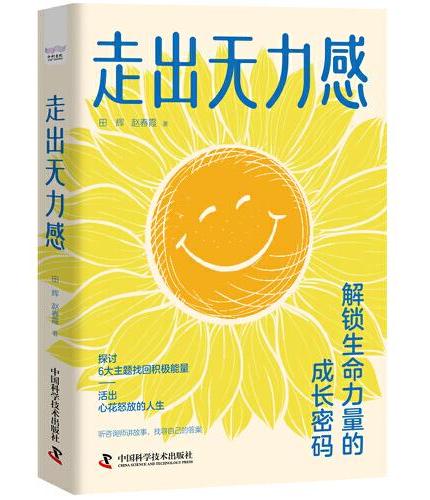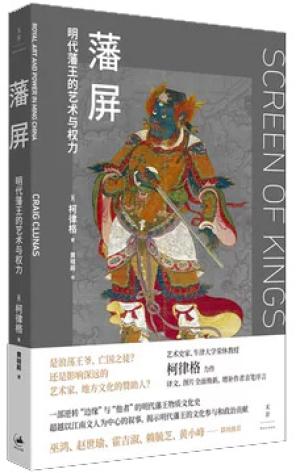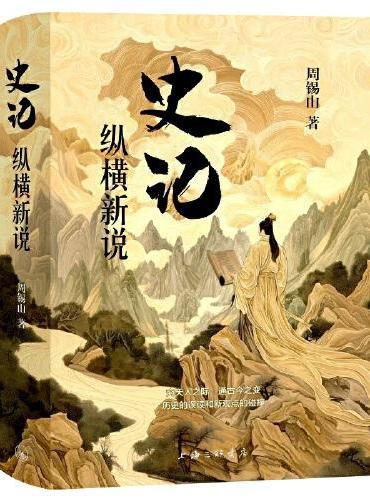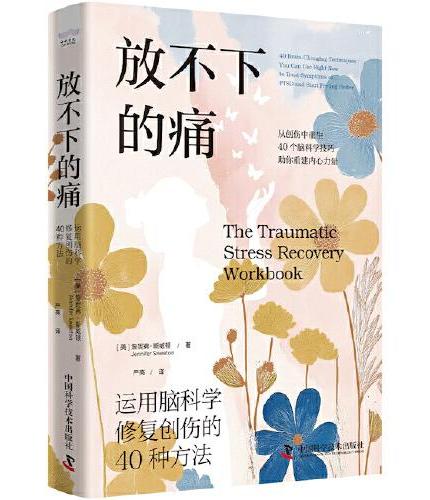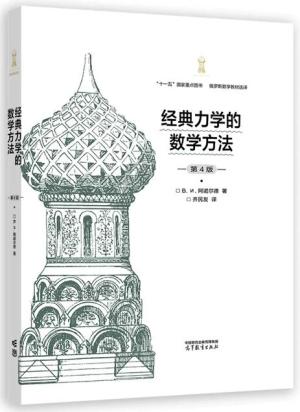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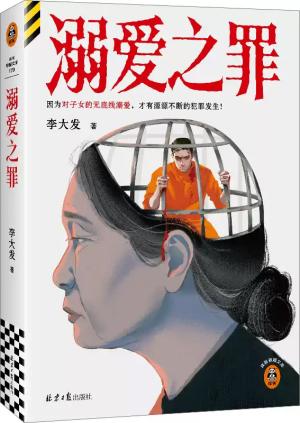
《
溺爱之罪
》
售價:NT$
25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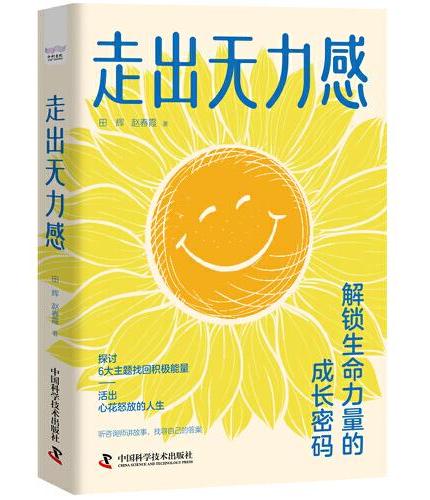
《
走出无力感 : 解锁生命力量的成长密码(跟随心理咨询师找回积极能量!)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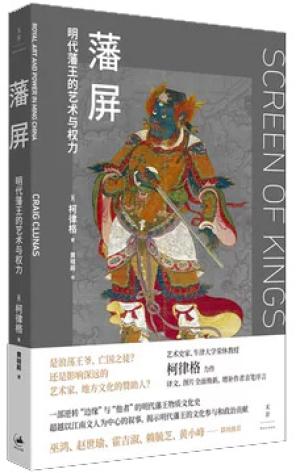
《
藩屏:明代藩王的艺术与权力(柯律格代表作,一部逆转“边缘”与“他者”的明代藩王物质文化史,填补研究空白)
》
售價:NT$
5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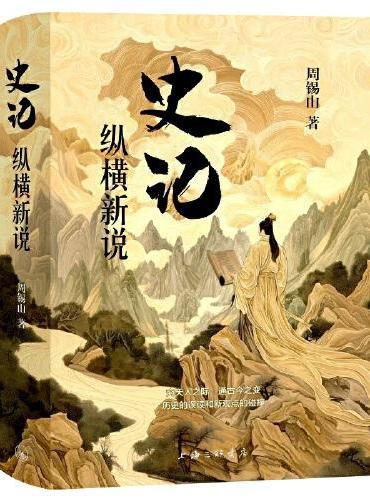
《
《史记》纵横新说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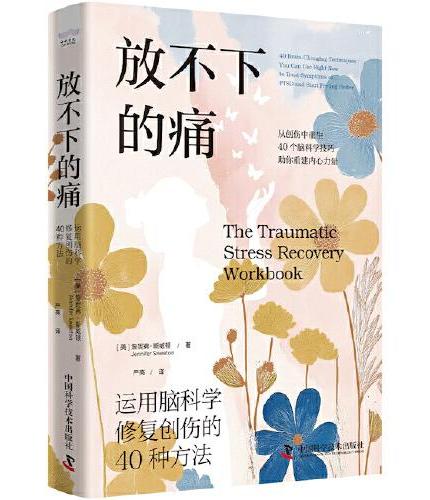
《
放不下的痛:运用脑科学修复创伤的40种方法(神经科学专家带你深入了解创伤背后的脑机制,开启全面康复之旅!)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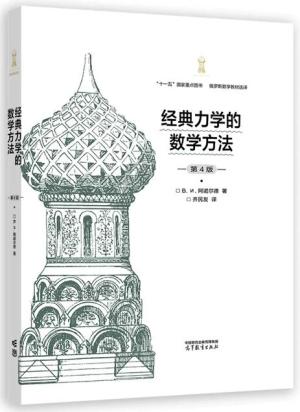
《
经典力学的数学方法(第4版)
》
售價:NT$
403.0

《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跟随历史的足迹 见证一个民族的觉醒与抗争
》
售價:NT$
305.0

《
功名诀:左宗棠镜像
》
售價:NT$
908.0
|
| 編輯推薦: |
1,奥登文学地位卓著,作品由译文社独家推出。
2,填补多年学术译介空白。
3,同一文集中的《奥登诗选》曾在2014年终图书评选屡获殊荣,销售很好,多次加印,为这本评论随笔集的市场推广,打下很好基础。
|
| 內容簡介: |
|
奥登是二十世纪改变了整个英语文学世界的人物,他的成就不仅仅是在诗歌、戏剧和评论领域留下了不朽巨著,而且其文字中所蕴涵的独特的现代性在当代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为文学各个领域的作家带来的深远启迪,是难以统计、不可磨灭的。《序跋集》是出版于奥登晚年的随笔集,在其文字生涯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序跋集》中所收录的随笔,写作时间横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内容涉及文学、神学、哲学、艺术甚至日常家居,材料翔实严谨,文笔纵横捭阖,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同时又巧妙地将个人经历融入给他人写的书评,许多段落犹如奥登的浓缩版自传。作为奥登最后一部随笔集,整部作品从人类的内在生活延续到外在生活,最后以人类成员之一的“我”加以整合,暗含了奥登的二元性思维模式和对人类双重属性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他对自己长期以来的思维模式的总结性陈词。
|
| 關於作者: |
|
W.H.奥登(1907—1973),英国著名诗人、评论家(由于其出生于英国,后来成为美国公民,所以也有人将其列为美国作家),举世公认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其作品数量巨大,主题多样,技巧高超,身后亦备受推崇,其独特风格对后辈作家影响深远。
|
| 內容試閱:
|
G先生
这本集子编译得很出色,碰巧作者又说是献给我的,我可不会因为得了这样的褒奖就不去把它吹捧一番了。
许多作家、曲作者和画家生前就举世闻名,可是在生前,甚至在人生的最后二十五年,自己本人就成为闻名国际的旅游景点的,我能想到的就只有歌德。每个去欧洲旅游的人,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是德国人、法国人、俄国人、英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免在自己的旅行日程上写下“拜访”歌德这一项,这与“观览”弗洛伦萨和威尼斯是同样的性质。
如果说大多数人拜访他就因为他是那一本书的作者,也就是他年轻时写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这显得更加古怪。即使在德国国内,他晚年的作品也只有那几本大获成功,比如《赫尔曼与窦绿苔》,还有《浮士德》第一部分,而他的一些最优秀的作品,比如《罗马哀歌》和《东西合集》,却无人问津,更别提受人欢迎了。《浮士德》的第二部分出版时歌德已经过世,有书评家曾这么说过:“歌德从我们眼前消失时,这本书出现在我们眼前,同样的,即使歌德的精神才华消失了,这本书的精神内容仍不会消失。”
歌德如何从不甚了解他的人群中得到这样的名誉,他又为何会有这样的名声?人们将他看作圣哲,像一个公共的神谕传达者,这一点对我来说至今仍是关于他的谜团之一。歌德的个性中有令人惊讶的一面,并不是说有人拜访他时他摆出一副冷若冰霜的面孔,人们满心期望能从他那儿得到一些金玉良言,可往往除了一句“哼!”或者“你真这么认为吗?”之外,一无所获,我指的是歌德居然会同意和他们见面。不时有愚蠢的访客上门,偶尔也有特别逗人的,譬如那个英国人,把德语的“那个呜咽的孩子”读成“那个十八岁的孩子”,还告诉歌德他吃了一惊,因为“民谣《魔王》里那位父亲被刻画得对孩子如此体贴入微,而毕竟他很有福气,有那么一大家子人”;但是多少都是平庸之辈,无聊至极啊!
年复一年,究竟歌德怎么才能忍受下来?也许《交谈与会面》里的一段话能说明部分问题,路加和匹克先生在序言里引用了歌德自己的话:
独处时我会想象把一个熟人叫到跟前。我会请他坐下,和他讨论那时候我脑子里想的话题。他偶尔也会回应,用他惯常的方式表示同意或反对……奇怪的是,我这么召唤来的人都不是我的好朋友,而是些很久没见的人,有一些甚至还住在地球另一边,我和他们也只是打过照面而已。但是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不是写作的人,他们善于接受他人,乐于倾听,总是兴趣盎然,不带偏见,接受他们能理解的事物。虽然偶尔我也会召唤一些天生爱反驳的家伙,来做一些辩证练习。
从这番坦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交谈对于歌德的意义,那不过是独白而已。他是和想象中的对象交谈,同样他也可以和实际的人对话。给他一瓶红酒,几个认真的听众,他也可以高谈阔论一番自己的想法,但那不是为了和听者交流,只是为了自己抒发一番。当然,和实际的听众交谈不无风险,因为他们总是会提些问题,或表示几声反对,独白式的演说则大可不必理会这些,可是实际上,看起来歌德只要一开口就很少被打断。所以有一次有人不但直截了当反驳了歌德,他还心怀感激承认了错误,当然他费了一番力气才有这样的态度,读到这样的事还真是头一遭:
……有一次,大伙在魏玛大公家用晚膳,歌德就火炮的学问发表长篇大论,尤其是炮兵连如何排兵布阵才最有效云云……我说:“我亲爱的议员先生!恕我冒昧,我们博美拉尼亚人都比较直接,我冒昧插一句嘴可以吗?在我们国家有句老话:各守各业,各安各职!您谈些戏剧文学,还有其他艺术方面的学问知识,我们自然洗耳恭听……但您开始聊火炮时可以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更不要说教我们军官如何使枪唤炮;请您原谅,但我不得不说这方面您确实完全是门外汉。”……歌德听了我这番话一开始脸色绯红,可能是生气了,也有可能是感到尴尬,不得而知……但是很快他就平复了心情,笑着说:“好吧,你们博美拉尼亚人都是绅士,你们是直接爽快,我刚刚听得可够清楚的,您那个也许不是直接,而是粗鲁吧。但是我们还是别吵来吵去的,我亲爱的上尉!您刚刚彻彻底底给我上了一课,下次您在场时我再也不提火炮的事情啦,也不会教军官们他们的份内事。”这么说着,他还非常诚挚地与我握了握手,我们后来一直是最要好的朋友;真的,对我来说,歌德现在比以前更需要我的陪伴啦。
(摘自《一个普鲁士炮兵军官》)
两个自说自话的人碰面会有什么遭遇?见到斯达尔夫人 后,歌德这么对他的朋友说:
“这一个小时过得很有意思。我插不上嘴;她很能说,可是有点罗嗦,是很罗嗦。”——与此同时,一群女士想知道我们的阿波罗大神给这位访客留下怎样的印象。她也承认说她说不上话。“可是,”(据说她边说还边叹了口气)“有人这么健谈,多听听也是美事一桩。”
(摘自《阿马利亚冯哈尔维格 》)
歌德喜欢交谈,却不会像西德尼史密斯 或者奥斯卡王尔德那样能说些诙谐的箴言警句。他曾说过:“想想肩上承担的对自己对他人的巨大责任,还敢有什么幽默感。但是,”他接着说:“我无意非难那些幽默作家。人到底需要良知么?谁这么说来着?”此外,也有清晰的证据表明歌德一旦认真起来,也可以逗乐其他人。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卢登就记得歌德讲过的一桩趣事,是关于一个古怪的奥地利老将军:他的讲述不可能比歌德当时讲得更生动,可是我们也被他逗得乐不可支。
歌德与约翰逊博士一样,说话从不言简意赅。不管是记载下来的言论,还是他的书面作品,你都无法找到一句这样过目难忘的句子——“周日应该不同于其他日子:人们可以散步,但不能向鸟扔石块。”(这是说他的无韵文作品。他的许多诗歌里有的是警句名言。)
可以说歌德和亨利詹姆士很像——詹姆士也很严肃,晚年时也口授他人完成自己的文学作品——他们说话非常咬文嚼字,只需这样补述:“(他们)说一口漂亮的书面语。”也就是说,歌德的口头表达已经具备了我们寻常在书本上读到的书面表达的一些特质。他思考的单位不是句子,而是段落,他能毫不迟疑吐出几个句子,每句都符合完美的句法,互相之间合乎逻辑。歌德是历史上少数几个人们认为演讲时就能当场录音的人,他们的语言用不着通过第三方回忆来再现。
当然,我们手头的材料无法涵括他所有的言谈。席勒是歌德生命里唯一一个智力相当的好友,虽然我们能读到他们的书信往来,但是却无法知道他们私底下相互都谈些什么。歌德与他妻子克里斯蒂亚娜私下如何聊天我们也不得而知。我们手头大多数都是些与歌德不怎么相称的人写的东西,无论他们和歌德私交多好,歌德和他们谈话时必定会自命不凡。如果就某些话题歌德要和他们吐露心声,那么他们一定会震惊不已,议论他脑子有问题。
歌德死后出版的诗作中,有一些对性欲和宗教主题的处理直截了当,令人吃惊,(顺便推销一下:在企鹅丛书的《歌德诗选》中可以找到一些,选编者也是大卫路加。)我们知道歌德有时候说话也用同样的调调。那些听他这么聊过性和宗教的人都不会把这次交谈和人分享,因为他们确实感到震惊,更加可能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自己有教养,仍然能区分公共演说和只能私下聊聊的话题,而如今人们把这一点全忘得差不多了。《交谈与会面》里有一段小故事,描述了歌德如何一开始就要惊世骇俗。讲法语的瑞士人索雷对歌德说,如果他生在英国,他应该是个自由党人。
“你把我看成什么了?”歌德跟他顶嘴,带着他的魔鬼梅菲斯特那种似是而非的嘲讽口吻,以此把谈话带到新的方向上。无疑他不想谈政治,因为他不喜欢政治。“如果我出生在英国——哦感谢上帝我不是英国人!——我应该会是个坐拥百万家产的公爵,或者年收入三万英镑的主教!”
“太好了!”我回答说,“但是假设你没那么走运?这世上厄运可多的是。”
“我亲爱的朋友,”歌德答道,“我们并非每个人生来就会走运。你真的认为我会干那种自找苦吃的蠢事?……我本应在诗歌散文里长篇累牍夸下海口,谎称自己确实有三万一年的收入。人只有谋得高位才不会被欺,而一旦名声大振了也不能忘了周围那群乌合之众不过是一群傻瓜白痴。如果不能把他人的辱骂变为自己的优势,那你也只会沦为那群人中的一个。那些辱骂正是拜他们的愚蠢所赐,我们自己不去利用,他们就会坐收渔利。”
路加先生和匹克先生很妥善地处理各方材料,比如里默尔和艾克曼 编撰的歌德作品集——在序言中见到他们有勇气顶着目前对《交谈》一书大加责难的风气,坚持对此书给予支持,我很高兴——他们还挖掘了很多大多数读者不熟悉的内容。
我自己对亚历山大斯特罗加诺夫伯爵日记的节选内容特别感兴趣。斯特罗加诺夫心里早就看歌德不顺眼,因为他厌恶文学爱好者的圈子,本人也不怎么爱读歌德的作品,可是到头来他却完全折服于歌德的魅力。
另外,我听说歌德讨厌戴眼镜的人,可是我以前从来不知道原因。
我总觉得戴着眼镜的陌生人会把我当成仔细端详的对象,他们凝视的眼神就是他们的武器,穿过我层层最最隐蔽的思想,在我一张老脸上四处搜寻最最细小的皱纹。可是想要通过这种方法了解我无异于破坏我们之间那种原本公正平等的关系,因为他们正在阻止我反过来了解他们。
如果歌德那个年代有太阳眼镜的话他的日子该多难过啊?
歌德不喜欢狗,这一点众所周知,也无伤大雅,不过这倒让我们惊讶于一个人兴趣如此之广的同时,还看到一个对他来说相对冷门的领域。歌德热衷于研究人类、天气、石头、蔬菜,不过在动物的领域,虽然他有过重要的解剖学发现,却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他给里默尔的理由听起来非常古怪:动物不会说话。
他唯一对动物感兴趣的一点是动物在组织结构上或多或少与人类相近,人是造物中最终无可争辩的统治者,而动物则是暂时的先行者。他不轻视动物,事实上他甚至会研究它们,但大多数时候他还是会怜悯它们,因为它们无法清晰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感觉,只不过是不见天日、受到压抑的生物罢了。
歌德曾说过他生命中唯一真正幸福的时光是在罗马的那几个月。他可能有点夸张,但是要说在意大利的日子是他成年后唯一真正自由的一段时光,倒并不假。那时他没有义务做任何事、见任何人,除非是他自己的选择。在魏玛,无论是身为公务员,还是剧院经理,或是社交名流,他都有诸多令人厌烦的义务要完成。
我真正的快乐来自诗意的冥想与创作。但是世俗的职务总是来打扰、限制并妨碍那样的生活。如果我可以多一些置身事外,不去理会那么多公共事务,过一种更隐士的生活,那么我会更快乐,也可以做更多作家该做的事。
然而他的世俗职务却都是他自己的选择,如果他决定退隐,过更加隐士的生活,没有人会阻止他。
我自己的感觉是歌德也许受忧郁症的困扰更多,他不愿向别人承认这一点,在他的谈话和作品中都没有提及,因为有忧郁症他才害怕独处。另外,因为他讨厌政党政治里的盲从现象,所以他也用自己的一套方法说服自己写作需要“根据一定的政治观点”,说服自己纯粹的文学生涯对人来说不够完满,用古希腊人的想法来说,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政治动物”,都有自己的社会责任,他无法违背本性而忽视那些责任。
歌德是个特别复杂的人,至少许多英国人美国人对他是既爱又狠。有时候人们觉得他傲慢自大,是个令人讨厌的老家伙,有时又觉得他满嘴谎言,是个虚伪的老人家,就像拜伦说的,“一只不愿离开洞穴的老狐狸,在洞中喋喋不休大道理说得好听。”可是,虽然人们会抱怨,最终却不得不承认他是个优秀的诗人,也是个伟大的人物。而且,当我读到下面这段逸事时:
歌德突然从马车里出来,开始端详一颗石头,我听到他说:“好啊,太好了!你怎么到这儿的?”——这个问题他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我不由得大叫一声,不是“伟大的G先生!”,而是“亲爱的G先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