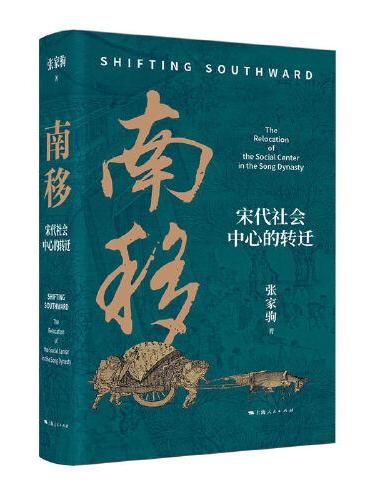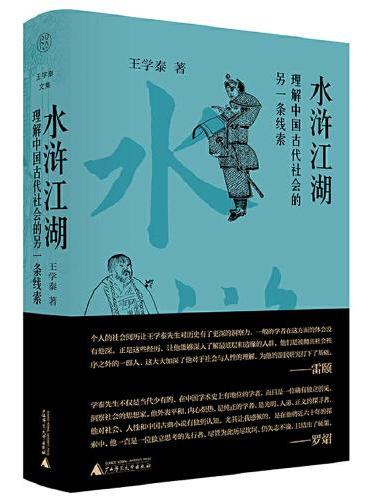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女人们的谈话(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最佳改编剧本奖 原著!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简直是《使女的故事》现实版!”)
》
售價:NT$
286.0

《
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境管控的全球化(共域世界史)
》
售價:NT$
653.0

《
一周一堂经济学课: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
售價:NT$
500.0

《
慢性胃炎的中医研究 胃
》
售價:NT$
30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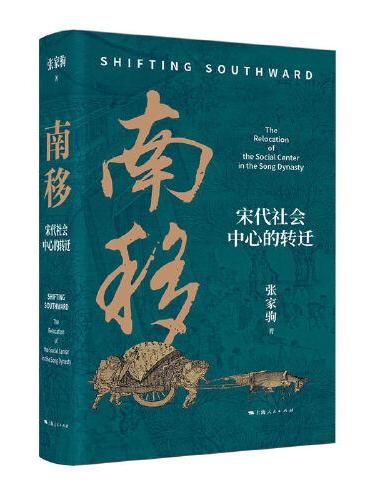
《
南移:宋代社会中心的转迁
》
售價:NT$
75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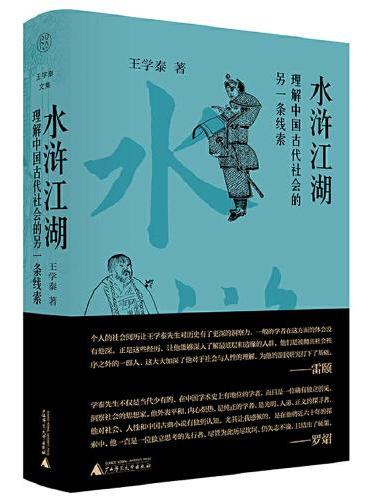
《
纯粹·水浒江湖: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另一条线索
》
售價:NT$
469.0

《
肌骨复健实践指南:运动损伤与慢性疼痛
》
售價:NT$
1367.0

《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MySQL版)
》
售價:NT$
301.0
|
| 編輯推薦: |
1,著名学者徐贲专文导读,“见证冷战历史的家庭故事”,以及在遍布秘密警察、告密网的国度里,卡在两个世界中间的人们生活与命运的另一个典型样本。
2,一切从一份意外收到的匈牙利秘密警察档案袋开始。这是一个监视、告密、出卖、背叛、审判、囚禁、信仰、坚守、勇气、释放、抗争、逃亡,而后刻意隐藏、遗忘的故事。
3,面对不堪回首的历史,该“让睡着的狗继续躺着”,还是要“打开潘多拉魔盒”?遮蔽几十年的秘密警察幽灵档案一朝揭开,呈现出一个守住*后的道德底线——不出卖、不背叛、不当告密者的真实案例。《布达佩斯往事》,是一个重新“发现”自己父母的历史的过程,更是那个阴暗、恐怖国家沉重如山的历史。
4,秘密警察监视、迫害作者的父母,但她既怨恨、谴责,却又真心感谢秘密警察,因为是他们所记录的巨细靡遗的档案让她看见了父母刻意隐藏的历史。有时候,真实的历史,比故事、小说更为诡异、荒诞,也更感人。
5,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联袂主编——理想国译丛(MIRROR)系列之一(014)——保持开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
| 內容簡介: |
本书通过冷战时期匈牙利秘密警察长达20年的档案,所揭开的一部隐藏了几十年的家庭历史和时代侧记。
冷战时期,苏联集团中的匈牙利,秘密警察通过庞大的告密网,试图全面渗透控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作者的父母原是匈牙利著名记者,他们的报道是西方了解匈牙利的重要信息来源。因此他们被视为“人民的敌人”,长期受秘密警察的监控,终因叛国和间谍罪而先后入狱。一家移居美国后,匈牙利政府却又异想天开地试图招募他们当间谍,而美国也对他们进行了几年的监控。书中不只还原了马顿夫妇被告密者包围的经历和遭遇,他们的抗争、坚守、脆弱和勇气,也展现了他们情感和内心的矛盾——夫妻之间相互的感情背叛与灾难中的支撑,父母子女之间的爱与亲情,人性的坚强与软弱,从而使得这本书更为丰富、复杂,具有血肉。
|
| 關於作者: |
卡蒂·马顿(Kati Marton),美籍匈牙利人,幼年随她的父母移居美国,获匈牙利政府最高文职奖。著有六部作品,包括《纽约时报》畅销书《隐藏的权力:塑造我们历史的总统婚姻》《大逃亡》等。
毛俊杰,1952年生于上海,1978年入复旦分校中文系,1981年后定居纽约,译作有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奥兰多·费吉斯《耳语者》、杰克·凯鲁亚克《吉拉德的幻象》等。
|
| 目錄:
|
导读:见证冷战历史的家庭故事/徐贲
中文版自序:送给我的中国读者
引言
第一章 从热战到冷战
第二章 幸福的童年
第三章 妈妈和爸爸
第四章 美国人
第五章 罪上加罪
第六章 缓刑
第七章 童年的终止
第八章 囚犯
第九章 我们仨
第十章 可怕的夏天
第十一章 父亲的屈服
第十二章 我们的新家庭
第十三章 父母的审判
第十四章 大洋彼岸
第十五章 重聚
第十六章 革命
第十七章 美国
第十八章 “花”
第十九章 往返布达佩斯
第二十章 又一惊奇
尾声
致谢
译名对照表
|
| 內容試閱:
|
【导读:见证冷战历史的家庭故事 /徐贲】
匈牙利裔美国记者卡蒂·马顿(Kati
Marton)在《布达佩斯往事》里讲述了父母和她自己童年时在苏联时代匈牙利的生活故事,许多关于她父母的往事都是从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里抽取出来的。罗马尼亚前政治犯齐尔伯(Herbert Zilber)说:“社会主义的第一事业就是建立档案。……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人和事只存在于他们的档案里。我们的存在掌控在掌握档案者手里,也是由那些设立档案者们所编造的,一个真人不过是他档案的镜影罢了。”档案是权力统治的工具,是权力为一个人建立和保留的“客观记录”,但它的素材却是由那些受人性卑劣因素和龌龊动机——嫉妒、恐惧、谄媚、背叛、出卖——所支配的“告密者”偷偷提供的。因此,档案里的“那个人”——苏联文化史专家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称之为“档案人”(file-self)——是一个幽灵般的阴暗存在。
档案人是一个被简略化和符号化了的概念,卡蒂的父母也是这样,她说:“我发现,不停地阅读这数千页的秘密警察记录,给我心灵带来极大压抑。……秘密警察的记录都是如此——全然超脱于血肉之躯之外。活人被压缩成简易符号”。她在档案里看到的父母是被意识形态压缩简略的罪人,“秘密警察关于他们的每一份文件,都是以‘高级资产阶级出身’起头”。留在档案里的正式裁决是“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又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忠实信徒,虽然公开从事自己的职业,但其报道对我们的国家利益不是嘲弄,就是充满敌意”。
然而,在政治意识形态定性的“人民之敌”后面,却有着不少日常生活的细节,包括秘密警察以什么手段、通过什么人获取了这些生活细节。这些偶然保留下来的细节成为卡蒂了解她父母的珍贵历史材料,也为她的家庭故事提供了具体的历史背景。卡蒂父亲晚年时,新匈牙利政府向他颁发匈牙利的最高文职奖,外交部长带给他的特殊礼物就是前匈牙利秘密警察关于他的一大袋档案资料,他却“从没打开那个档案袋”。卡蒂说:“对他而言,历史真是重荷如山——至少他自己的历史如此;对我而言,却是探索的出发点。”在《布达佩斯往事》中,我们读到的不仅是她从父母幽灵档案记录中探索到的一些真相,而且更是那个阴暗、恐怖国家沉重如山的历史。
一、恐怖与暴力
孟德斯鸠是最早把恐怖确定为一种政治体制标志的。他把不同的政府区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共和制、君主制和独裁专制,并且指出,每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形态都必须具备某种对维持它的体制不可缺少的精神因素(ethos)或文化倾向,维持君主政治是“荣誉”,维持共和政治是“德行”,而维持专制独裁则是“恐怖”,用人民的恐惧来统治他们。恐惧是人在生存安全感受到威胁时的基本反应,对人的伤害可以是肉体的、心理的、精神的或者象征意义的。
在政治权力有所公开制约,暴力行为受到法律约束,宽容和多元文化成为普遍伦理规范的社会中,恐惧会在很大程度上被疏导为一种个人的心理感觉或者超越性的经验(如对神、上苍、大自然、死亡的恐惧)。在这样的社会中,尽管有时会出现集体性的惊恐,恐惧不会长久成为公众生活的基本心态。然而,在实行秘密警察恐怖统治的国家,如纳粹时期的德国、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当然会有程度的差别),普遍的无安全感、朝不保夕、惊恐猜疑及担惊受怕便成为普遍的公众生活状态。恐惧因此也就成为这些国家人民梦魇般的创伤性心理特征。这一意义上的恐惧已经不再是个人情绪的变动或者甚至那种埋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关于存在的超越体验(对死亡的恐惧),而是一种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形成和长久维持的、具有特殊政治内容的心理机制。这是一种由政治制度制造和维持的结构性恐惧,一种必须从暴力统治的政治压迫关系来理解的社会心理。
1950年代初,卡蒂的父母活跃于布达佩斯的新闻界,他们分别是两家美国通讯社的记者。这时候,匈牙利人已经生活在拉科西政权的恐惧之中,记者们战战兢兢、噤若寒蝉,不敢越官方宣传规定的雷池一步。匈牙利的新闻自由迅速消失,还能够真实报道匈牙利现实情况的只剩下为外国通讯社供稿的记者,“1948年,匈牙利有六十五名正式的外国记者;由于逮捕、逃离、恐吓,到1953年仅剩三名。其中两人,就是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剩下的第三人还是秘密警察的告密者”。
这两位马顿便是卡蒂的父母。他们穿着讲究,生活优渥,一副“高等匈牙利人”的派头。那时候全匈牙利一共才有两千辆私家车,而马顿家却开一辆白色敞篷的斯图贝克美国车,就像“是在乘坐一枚火箭”。这是不是太招摇显眼,太危险了?“随着档案吐出的一个又一个秘密,我被另一种困惑攫住:父母为何要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冷战期间,大多数匈牙利人特意穿街过巷、绕道而行,为的是避免让人看到自己在跟美国人打招呼,而我父母最好的朋友都是美国外交官和新闻人。我认识的每一个匈牙利成年人都学会了窃窃耳语,而我父母却在响亮地发表意见”。
其实,马顿夫妇这么做,不是因为没有恐惧,而恰恰是因为感到恐惧。招摇显眼、公开与美国人来往不过是他们自我保护的策略。几年后,卡蒂的母亲被捕,秘密警察逼她承认是美国间谍的时候,她说,间谍只能悄悄地做,我们到美国使馆去,每次都是公开的,有这么当间谍的吗?当然,罪名是早就做实了的,这样的辩护就像马顿夫妇早先的故意招摇一样,是不能为他们免除牢狱之灾的。
马顿夫妇不过是美苏冷战中的一枚棋子,他们越是在美国人那里吃得开,匈牙利当局迫害他们就越是有所顾忌,需要三思而行。但是,他们越是与美国人来往甚密,官方也就越是怀疑他们是为美国服务的间谍。马顿夫妇对此心知肚明,匈牙利当局也知道他们心知肚明,彼此不捅破这层窗户纸,是因为双方都在玩一场特殊规则的游戏。而且,也正是因为马顿夫妇与美国人的特殊关系,匈牙利当局认为他们可能有利用价值,给予他们特别的待遇,也许可以交换他们的某种合作。卡蒂在秘密档案里发现,秘密警察曾经把她父母当作“告密者招募”的对象。这是典型的冷战渗透。
匈牙利人充满恐惧,这不仅是因为国家镇压的暴力手段,更是因为他们明白,神通广大的秘密警察在他们周围布下了一张由无数告密者构织而成的大网。这是匈牙利执行苏联化的结果,它依靠的是制度化的恐怖。作为恐怖统治的主要执行者,匈牙利秘密警察“直接汇报于斯大林的特务机关——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后来的克格勃。它于1946年9月成立……下设十七个科,发挥各自的特别功能。大家都知道,苏联红军是它的后台。事实上,它是匈牙利共产党内的苏维埃党派”。卡蒂心有余悸地回忆,“我在长大过程中渐渐认清,其[秘密警察]主要特征是残忍,普通的政治和外交行为都对之束手无策。它的第一科试图通过庞大的告密网,来渗透控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招募告密者靠的是恐吓:秘密警察会在深更半夜把对象从床上带走;他只要甘愿充当告密者,就可获释。我现在知道,这个告密网包括我家的大部分亲友;有些比较特殊且敏感的告密者——比如我家的保姆,因此而获得优厚报酬”。
苏联式的秘密警察是从俄国革命后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发展而来的,但是,“契卡”的创始人,素以正直、清廉著称的捷尔任斯基似乎早就察觉到,秘密警察是一个需要恶棍,也生产恶棍的体制。他说,为契卡工作的只有两种人,“圣人和恶棍,不过现在圣人已经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恶棍了”,“契卡的工作吸引的是一些腐败或根本就是罪犯的家伙……不管一个人看上去多么正直,心地如何纯净……只要在契卡工作,就会现出原形”。苏联将军,曾在叶利钦总统任期内担任俄罗斯总统特别助理的德米特里·沃尔科戈洛夫(Dmitri Volkogonov)说,1930年代中期苏联政治警察(NKVD)军官里只有两种类型的人,“冷酷无情的犬儒和丧失了良心的虐待狂”。苏联间谍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lov)回忆道,他负责招募新手时,他的上司克格勃高官帕维尔·苏朵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给他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运或天性受过伤的人——那些性格丑陋、有自卑情结、嗜权、有影响欲但又屡遭挫折和不顺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虽不至于受冻饿之苦,但却因贫困而感到羞辱的人……这样的人会因为从属于一个影响大、有权力的组织而获得优越感……他们会在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自己很重要的甜头,因而死心塌地地与权力结为一体”。
秘密警察统治使得整个国家的人民陷入一种近于歇斯底里的焦虑、捕风捉影的猜疑和非理性的恐惧之中,对他们有长久的道德摧残(demoralizing)作用。秘密的暴力比公开的暴力更令人恐怖,它会使人失去思考能力、道德意识和抵抗意志,因此退化到最低等原始的动物保命本能中去。为了保命求生、避免肉体折磨,人会变得全无廉耻、奴性十足、无所不为。秘密统治对政府权力的正当行使和合道德性同样有着严重的腐蚀作用。美国伦理学家希瑟拉·博克(Sissela Bok)在《秘密》一书里说,行政统治运用秘密手段,这会增加官员,“尤其是在那些自以为有使命感,因此罔顾常规道德考量的官员,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一旦国家发展出秘密警察力量或实行全面审查,滥用权力的危险就会增高。秘密本身就会变成目的,行使秘密权力的人也会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秘密政治迫害的卑劣和败坏,及其对全体国民的良心摧残,正是苏联式统治给所有前东欧国家和其他类似国家带来的一大祸害和道德灾难。
二、无处不在的“告密者”
希瑟拉·博克在《秘密》一书里还说:“权力来自对秘密和公开的控制力:它影响着人们思考什么,并影响他们选择做什么;而反过来,越有权力,也就越能控制什么是秘密,什么可以公开。”匈牙利这种统治是一种对“秘密”和“公开”拥有绝对控制的权力。它可以强行规定什么是不能对外国人泄漏的“国家机密”,也可以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利用告密者和强制“交心”、“坦白”、“认罪”来强迫人们公开自己所有的隐私。卡蒂的父亲以间谍罪被逮捕,是因为他向美国人传递了一份匈牙利的国家预算,这种在民主国家里公民知情权之内的信息足以在一个极权国家成为“非法获得”和“出卖国家”的重罪证据。
……
三、极权统治下的“勇敢”和“人性”
卡蒂是一个在极权统治下长大的孩子。她说,“我们是政治化了的孩子”,“在这种国家长大的孩子很早就懂得,与国家权力相比,她,甚至她的父母,都是微不足道的。不管父母多卓越、多机智、多有魅力——我父母就是如此——到头来只是掌中的玩物”。卡蒂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决定阅读她父母的档案的。既然每个人都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背弃自我、丧失良心,那么,自己的父母也是如此,又会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匈牙利秘密警察档案部门的主管库特鲁茨·卡塔琳博士向准备前去阅读档案的卡蒂几乎带有温情地建议,“这次,你如果能单独来,会更好”。这让卡蒂觉得不安,她彻夜未眠。她会在档案里看到自己怎样的父母呢?她担心、忧虑和害怕,是有理由的,“前不久,一位备受推崇的匈牙利作家获得他父亲的档案,旋即发现一连串令人惊叹的阴谋和背叛,有的甚至来自家人”。卡蒂申请要看父母的秘密档案,秘密警察的首席历史学家提醒她,这是在冒“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风险。卡蒂也知道,一旦打开父母的档案,也许就会看到他们“某种妥协或叛变的证据,从而永远打碎父母的形象”,“这风险是实实在在的。从君特·格拉斯到米兰·昆德拉,盖世太保和克格勃的秘密档案已陆续披露出长达半个世纪的背叛。我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不愿直面过去;他们对我说:让睡着的狗躺着吧,不要自找麻烦”。
……
【中文版自序:送给我的中国读者】
我的回忆录译成中文,在一个引起我独特共鸣的国家中与读者见面,这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73年秋天。其时,我刚刚大学毕业,来华拍摄费城交响乐团访华纪录片,那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美中之间第一次重大的文化交流。这次历史性的访问,让有幸躬逢其盛的我们大开眼界,认知大为改观。当然,那时的中国是个完全不同的国度,美中人民的相互隔绝已有二十多年。我观察(并拍摄)到,在共通的音乐语言面前,我们之间的差异——语言、文化、政治和地理——几天之内就涣然冰释了。美国的音乐家和三名新闻人,中国东道主,以及每晚来聆听贝多芬、莫扎特和海顿的美妙乐声的数百名中国观众,即使没有言语往来,也已获得了大量沟通。很简单,在被迫的多年隔绝之后,双方都燃起了重新交往的热望。这一次旅行从来没有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也彻底改变了我的职业轨迹。我当即就下定决心,当一名驻外记者:从摄像机的背后,来观看尽可能多的世界;在人类大家庭的遥远成员中,交上尽可能多的朋友。我还承诺有朝一日会回来,对中国作进一步的探索。
我在1999年兑现了这一承诺,陪伴丈夫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对中国作正式访问。理查德在自己外交生涯的初期就有改善美中关系的激情,从1970年代起,又在华盛顿和北京的和解中发挥关键作用。与我丈夫一起走进中国的外交部大楼,是另一次难以忘怀的经历。许多高级官员从办公室里涌出,口中高叫“迪克!”(他的昵称),与他拥抱相贺,像大学同学重聚时一样。在过去三十年中,这些人与我丈夫一起,努力克服历史和政治上的分歧,使美中人民走得更近。这一次,他们又有机会在一起并肩工作,为此而感到兴奋。理查德一直对外交事务情有独钟——在特定时间内与一名对手折冲樽俎——尤其是美中外交,他对中国怀有深深的依恋。
我眼前的一大喜悦是,随着我的回忆录在中国出版,我似乎又重新回到中国。这虽是我自己的故事,但也是经历过冷战特定时期的数十万人的普遍遭遇,前车之鉴,值得铭记。
我的童年结束于六岁,其时,匈牙利秘密警察将我父母从我身边夺走(这是孩子的直观感受)。那是1950年代,冷战冻结了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个人和家庭——父母和我——都变得微不足道。我将近两年看不到父亲,整整一年看不到母亲——非常漫长的一年。他们被指控和定罪为美国间谍,关在看守最严密的监狱中,无法看到彼此和他们的女儿。他们的真正“罪行”,其实不是偷窃情报,而是做了尽职的好记者——诚实无畏地报道日常发生的真实事件。当时有太多的坏消息——政治和经济上的肆意迫害——父母被认作危险分子,即国家的敌人。然而,他们是骄傲的匈牙利人,热爱自己的祖国,从来没有想去他国避难。(父亲认为,以匈牙利语来上演莎士比亚戏剧,会更精彩!)他们还坚信,如果害怕人民的不同意见,如果视异议为犯罪行为,如果将不赞同高官的人打入监狱,一个国家就不能自称是伟大的。
《布达佩斯往事》涉及国家发起的残酷。为了征服我父母,匈牙利当局故意封锁他们两名幼女的任何信息(父母被捕前不久,祖父母突然获得去澳大利亚与我叔叔团聚的移民许可,从而确保我们姐妹孤苦伶仃)。甚至在监狱里,父母都无法享有内心深处的思维或情感。父亲的牢房难友/告密者汇报:“[马顿]说他已不抱希望,他对孩子们的处境一无所知……在审判时,他将使用最后的发言机会来保护妻子,希望给她的案件提供转机。对自己的案件,他则不存丁点的奢望。”
当我父母在十年前先后去世时,强加于我们过往经历的禁忌终于解除。我回到自己的故国,直奔那个黑暗时代的心脏——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所找到的监视记录触目惊心,几近全方位,这促使了这本回忆录的问世。我父母不会喜欢这本书,因为它袒露了他们最为隐私的秘密。但这是一个国家的所作所为,他们是在收集不利于我父母的证据,而我是在寻找真相。在这过程中,我翻译了数千页监视记录:当父母以为自己“自由自在”时,他们的每一通电话和信件,其实都在受严密的监视。我在这个研究过程中,真正认识了父母:不再是我儿时推崇的高大人物,而成了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既有缺点又有失败——犹如我们每一个人。我现在觉得,自己离他们更近了。例如我了解到,超脱、矜持、不动声色的父亲,其实是非常关爱自己女儿的——在开学的第一天,他因为不知道我们能否上学,而在牢房中向隅而泣。事实上,我曾考虑过将此书献给匈牙利秘密警察,以感谢他们巨细无遗的监视,让我真正认识了自己的父母。理查德提出明智的反对,他担心有些读者可能会误读其中的讽刺。
那是一个可怕的年代,我们姐妹与雇来照看我们的陌生人同住,没人提及我们的父母,好像他们从人间蒸发了。小孩子是富有韧性的生物,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爱,我就在那两年中转向了宗教。一名天主教修女,当时只能被叫作“阿姨”,不得穿修女袍、戴十字架,却向我传授了教义问答,以及对圣母马利亚的祷告。我一整天咕哝这样的祷告,希望受到不公正囚禁的犯人(如此之多!)能得到佑护。等到父母终于出狱,我反而有点失望,因为他们并没有对我的祷告表示感谢。一旦我们抵达美国,当地人星期日都去教堂,宗教失去禁果的魅力,我也就变得兴趣索然。
尽管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我家有机会在美国开创新生活——但幼时被迫与父母分离,却在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讨厌例行的告别,无法克服自己取悦于他人的难民心态,亟欲证明自己无愧于美国的热情好客。流亡不是自然状态,孩子应在自己的国家长大;周遭的人不但知道如何叫出小孩的名字,而且熟悉小孩的家族轶事。
众多的秘密在读者面前暴露无遗,对此,父母可能不尽满意;但我认为,他们最终还是会准许的。在《布达佩斯往事》中,父母是20世纪人类最糟糕的试验中的英勇幸存者。写出他们的故事,又让中国读者获悉这一切,我希望为确保那些黑暗日子的一去不复返,略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卡蒂·马顿
美国纽约,2015年8月15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