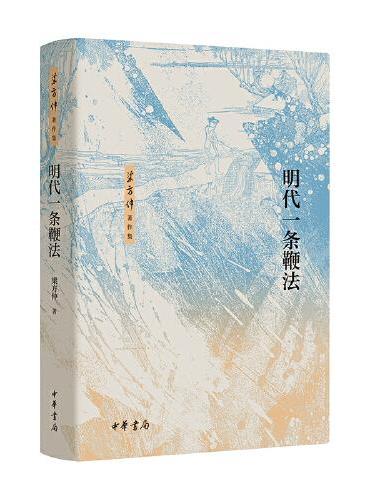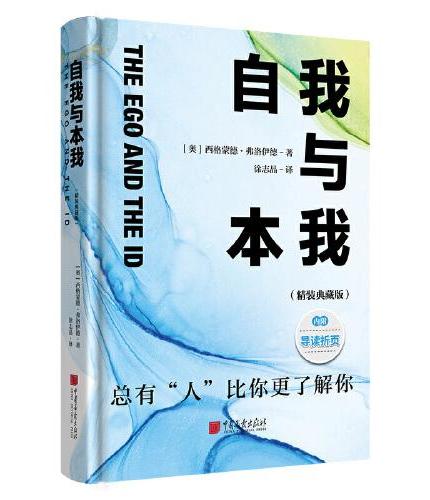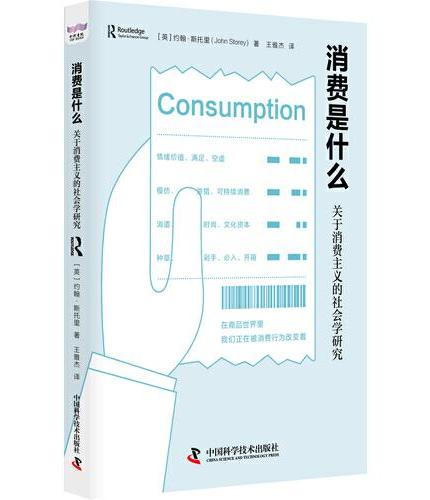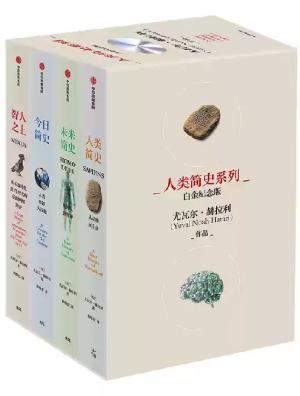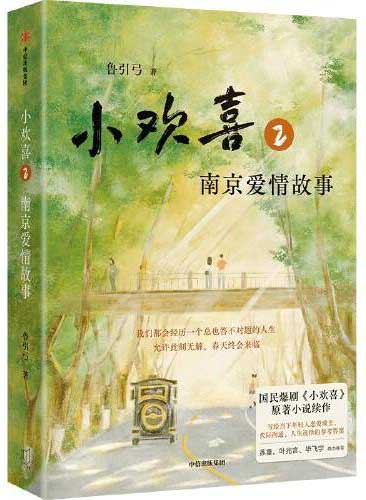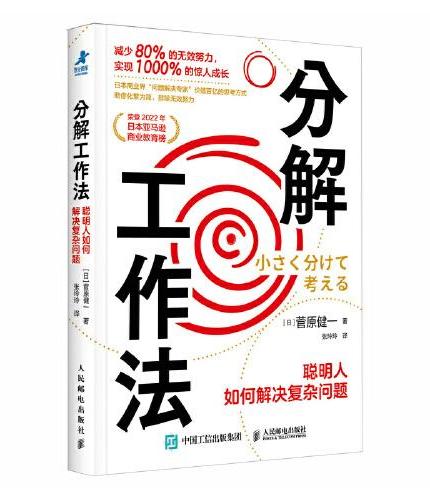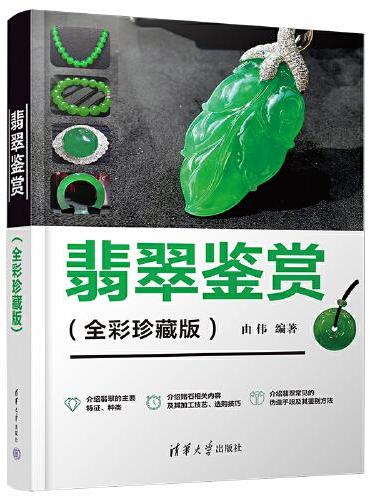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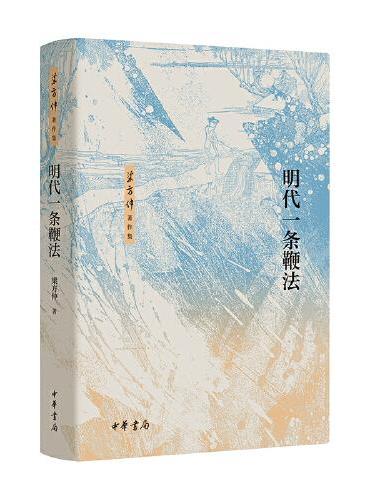
《
明代一条鞭法(精)--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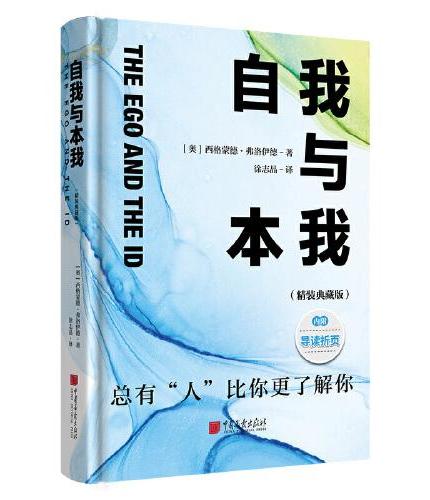
《
自我与本我:弗洛伊德经典心理学著作(精装典藏版)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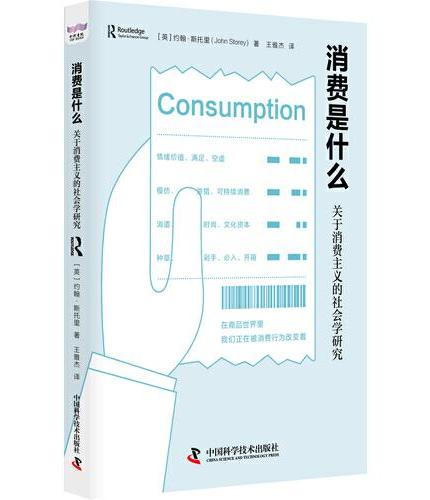
《
消费是什么 : 关于消费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一本书告诉你为什么买买买之后也有巨大空虚感)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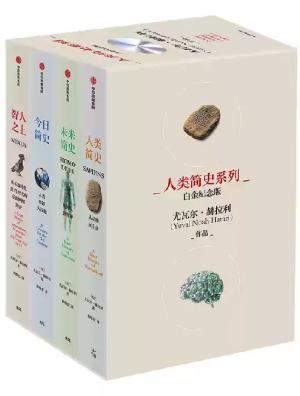
《
人类简史系列(白金纪念版)(套装共4册)
》
售價:NT$
1612.0

《
深度学习推荐系统2.0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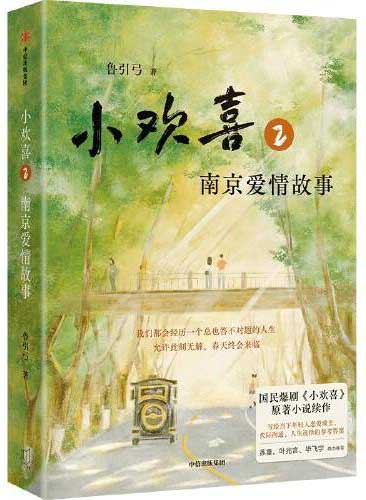
《
小欢喜2:南京爱情故事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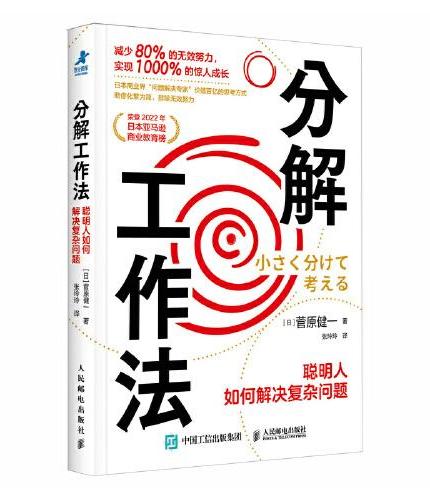
《
分解工作法:聪明人如何解决复杂问题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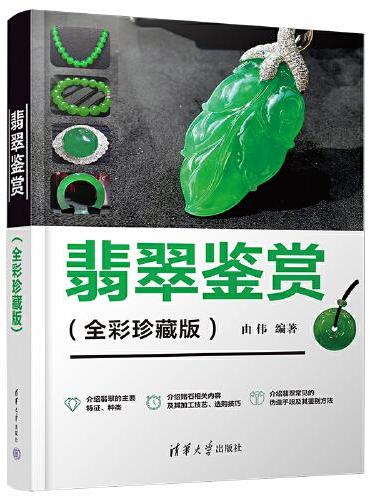
《
翡翠鉴赏(全彩珍藏版)
》
售價:NT$
352.0
|
| 編輯推薦: |
|
不一样的乡愁,拨动每个人心中那根脆弱而敏感的神经
|
| 內容簡介: |
|
美文《故乡在童年那头》打动了无数人的心。这是作家老愚关于故乡的系列文字,他以细致、深邃的笔触,为读者描画了一幅关中农村的风情画卷,其中有对自然伟力的礼赞,也有对幽暗人性的探究。故乡正在消失,我们生命的原点即将被不可遏制的洪流淹没,惆怅,伤感,百味杂陈……乡愁都是相似的,但每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情感总令人回味不已。行文妩媚、妖娆,态度诚恳、坦白,既是一部美妙、丰沛的散文,也可视为作者的精神自传。
|
| 關於作者: |
老愚
1963年出生于陕西扶风,自幼在关中农村长大,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多年从事记者、编辑等工作,先后在工人出版社、南方周末、新浪网等机构工作,现为FT中文网专栏作家,获得2011年度亚洲出版人协会评论大奖。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倡导新生代散文革命,所编选的《上升——当代中国大陆新生代散文选》等书曾产生了重要影响。
著有:
《在和风中假寐》新星出版社,2012年
《正午的秘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
《蜜蜂的午后》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
《世纪末的流浪》(与张力奋合作)工人出版社,1989年
|
| 內容試閱:
|
自序
老愚
故乡只在童年那头。
即使是童年那头,也并非一个诗意的乡土。
诗意,是原初事物在童稚心中生发的意趣,天然而自足。我文字里抒情的调性,当由此而来。
故乡的人事,在心里转动、发酵,最终形成了一个个场景。我的书写,感情与理性处于持续的平衡之中,爱与憎的微妙转换,在不同时段的文字里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活在我心中和梦境里的故乡,不论是人物、土地、鸟虫、植物、屋舍,抑或是声息、色彩,似乎从未改变过,一直那样新鲜如初地存在着。记忆和想象重构的这个世界,就是我生命的伊甸园。
我幼年所见多为窘迫、悲苦的脸,极少有发自内心的天然的笑容。为生存焦虑的人们,无时无刻不惧怕被革命洪流吞噬。
强力改变了一切。从人性到地貌,旧伦理、旧事物悉数消失,我们置身于一个陌生而奇怪的所在。我写的是自然乡村的终结。因为被连根拔起,人们不免成为漂浮物,遵从布朗运动规则的卑微“分子”。在此,看似不相干的故乡和现场,就非常奇妙地连接到一起。
我相信,这些微小的观察和感受,自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仅仅想表明:我们曾经怎样活着,如今又如何生活着,由此可以推断我们未来的命运。
身处急剧变化的社会,我常常有眩晕感。我经常会想起童年,想起曾在梦里乘坐的那列通向远方的列车。幼时曾经这样幻想:命运将载我到达一个未知的地方,那里有可爱的人和事物,人们庄严地劳作,自由地呼吸,愉快地享受,我和他们融为一体,天真无邪地活着,最后,怀着感激离开这令人悲欣交集的世界。
2015年11月17日 于北京车公庄大街
公元一九六三年
母亲怀我三个月时,和乃雄他娘去赶集。
集,是农村贸易的主要方式,从牲口买卖到日常用度,全靠集市交易完成。就周期而言,有单日集、双日集,有一四七集、二五八集、三六九集(一四七集,指逢阴历初一、初四、初七、十一、十四、十七、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七有集,馀类推)。扶风县境内大的集市有齐家埠、杏林镇、召公镇等,毕公区一带的人,习惯去齐家埠赶集。齐家埠,坐落在渭河北岸,与哑柏、槐芽同为西府名镇,因东汉大儒马援的“绛帐授徒”而更名为绛帐镇,逢双日有集。
她们手挽手朝塬下走去。
五月天,麦子快熟了,田里黄橙橙的,空气在隐隐传递着什么秘密。窄窄的土路上,偶尔会有人走过,布鞋漾起的尘埃,在阳光下迷离片刻便复归平静了。俩人一路说着贴己话,孕育生命的女子,走在蓝天下,内心涌动着莫名的快乐。她们并不想买什么东西,赶集不过是散心的由头罢了。平日里被“人民公社”役使,卖苦力,挣工分,从早到晚不得歇息。生活,就是打粮食交给“国家”,再从生产队手里分到活命的口粮。
走了五六里路,来到双庙坡坡口。朝南望去,眼前是一幅打开的关中平原风景图:十几里外,横亘的秦岭作成屏风,挡住了外面的世界;腰身粗大的渭河,在不远处泛着波光;紧靠着塬的陇海线,火车哐嘡有声,往东是省会西安,往西是宝鸡。
走了十五六里路,她们终于到了集市。戏台,牲口,百物,吃食,人们挤来挤去,一张张干涩愁苦的脸,这时都略微舒展开来。路过卦摊,俩人被算命的叫住了,“不灵不要钱——”
摸骨算命先生摸了乃雄他娘的手,说了句:“带把儿。走不远,爱哭。”乃雄他妈嗤的一声笑了,“我还不想让我娃离家太远哩!”轮到我母亲,她不免有点儿紧张,她不知道算命是好是坏,怕知道谜底。身为无产阶级革命对象的“地主”后代,她惶恐不安。嫁给贫农汤老大的二儿子,图的就是安全。丈夫官做上去了,也许就更踏实了。现在,肚子里的孩子是她最珍贵的财产,也是她人生的指望。
她不太相信算命,但既然来了,就不妨听听“预言”,二十五岁的人,对命运不免有一些好奇。当算命的抓过她的手,依次从掌心捏到指头,她的心也在噗噗乱跳。
“男娃,耳大有福,往大地方走了。”
听到这话,母亲一下子踏实了。她掏出一毛钱酬谢人家,“灵验了再谢忱你!”
我在母腹中孕育的这一年,世界上发生了几件大事。
朝鲜战争之后形成的冷战格局延续依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紧张对峙。但双方都在寻求妥协,核大国美英苏开始缔结《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笼罩在核战阴云下的地球人总算喘了一口气。曾宣称要埋葬资本主义的苏联元首赫鲁晓夫,在共产主义运动停滞之际,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政治方针。这让夹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中国异常愤怒,信奉斗争哲学的毛泽东奋起反击,在“九评”苏共“修正主义”的论战文章中,中共重申自己的主张: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总理周恩来为国民绘制了一幅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蓝图,毛泽东则发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最高指示。
“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主义精神符号“雷锋”出笼。
“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一系列运动,正引发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崩溃:城镇裁人,知青下乡,计划生育。
外面的世界却是另一种情景。《铁臂阿童木》当年元旦在日本富士电视台开播。这部根据手冢治虫漫画拍摄的电视动画片,讲述了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少年机器人阿童木的故事。十七年后,中国孩子才能看到这个聪明、勇敢、正义的少年。同时期的中国孩子正端详着“共产主义”——“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制度”。一九六二年七月修订的《新华字典》这样解释道:“共产主义分低级、高级两阶段。在低级阶段,即在社会主义社会,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高级阶段,即在共产主义社会,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呼吁政府给予黑人与白人平等的权利,“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真理是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柏林墙”前发表“我是柏林人”的演说:“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
……
母亲念了几年私塾,但没读过多少书。那时,只要有耳朵即可。村子与外界的联系,是通过架在老皂角树上的高音喇叭实现的,中南海的声音当天即可传到这里。
每个人的命运都与远方的“最高指示”息息相关。新政权将人们从私有制的自生存状态变为国家的一分子,谁能牢牢粘在“国家”这张皮上,谁就能衣食无忧。
母亲从喇叭里感知这个国家的脉动。她心里想的是父母会否安生,弟弟妹妹们能否长大成人。作为长女,她有天生的责任感。
我不能妄自揣摩母亲的情绪,但可以想见的是,从刚刚过去的三年大饥荒里熬过来,生存的忧虑无时无刻不压在她心头。外祖母常常念叨,说民国十八年的“关中大年馑”如何吓人,绝户,人吃人,饿殍阻路,母亲眼前恐怕经常浮动这样的景象。活下去!怎么才能在蒸笼般的社会里活下去呢?她决心学习裁缝,靠为人做衣服挣点儿活钱。
院子中央,那丛茂盛的黄花透出一丝耀眼的喜气。
地里长满了庄稼,社员们把汗水洒在土里,丰收的果实却要送到扶风县国营粮站。红光满面的干部说,这些粮食,一部分送到北京,给毛主席老人家擀面吃;一部分送到咱们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让他们吃饱了跟美帝国主义作斗争;一部分藏起来,准备跟苏修打仗。口粮按工分和人头分,得盘算着吃,才能勉强把一年撑过去。
日子缓慢。太阳从东边升起,慢慢爬到头顶,再磨磨蹭蹭掉下去。
在半饥饿状态下,母亲的肚子一天天鼓起来。
我来到人世的那天是癸卯年十一月初五,冬至前两天,公元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我猜想,外婆一定从绛中村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汤家村,陪伴在她女儿身边。
那时候没有大路,五里多地的阡陌小道可够小脚外婆走的。老人家拄了一根拐棍,颤巍巍地行走在窄窄的土路上,手里还提着一篮鸡蛋。
一路上,外婆恐怕无心看伏在地里的麦苗。收秋后,渭北台地除了轮休的闲地,大都种上了麦子和油菜,冬天,正是它们埋头假寐的时节。或许还有一些景色,比如五泉人民公社修筑的沟渠,新栽的白杨树,干枯萧索,想必不会让她有多少愉悦之感。
在平展展的阡陌间,散落着一个个瘦瘠的村子,黄墙灰瓦,聚落上空冒出的枯黑枝条,拽出一丝可怜的生机。
从窑洞里走出来,外婆心里有了些许敞亮感。她已经习惯了低头走路,“地主婆”的身份改变了她的行为,她害怕人——一切出身比自己好的。她是出名的善人,叫花子上门讨饭,碗盛得满满的,临走还要往手里塞一个馍,怕可怜人吃不饱。
夫家靠祖上积攒的家底添置了百十亩地,十几头高脚牲口,住的是窑洞。关中平原的窑洞,大致有两种类型。常见的是在崖面凿洞,方便易成,但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富有的人家,发明了一种特别的洞穴:从平地中央挖下去一个长方体或正方体深坑,大约十来米深的样子,四面凿出孔洞,洞深约在十米许,宽四五米,盘炕起灶。这样的独立窑洞部落,大都坐北朝南,从东南角掏一斜坡作出口,安上厚重结实的大门,崖外再版筑一圈土墙,一方让主人心安的栖息地便成了。当然,讲究的还要在崖上植迎春花若干,不出几年,旺盛的枝条沿崖头一路探下来,耀眼的金黄色小花让人心里一亮。到晚上,牲口、大车悉数入窑,任你土匪有十八般武艺也奈何不了。
一九四九年夏天,西北野战军首领彭德怀率部发动“扶眉战役”,驱走了国军胡宗南部。随后便是一场颠倒乾坤的“土改”。之前,有人从陕北回来,劝说外祖父赶紧卖地卖牲口,外祖父生性倔强,他觉得不可理喻:祖祖辈辈都认的理,难道要被人打翻了?机灵的把值钱的都卖了,跟胡宗南将军往西南撤了;不愿离乡离土的就地趴倒,静观其变。
直到血汗换来的土地被没收,原来的二流子烟鬼摇身变为新时代掌权者,外祖父才明白:世道真的变了。做人的信仰骤然崩塌,他从此一蹶不振。土地、牲口、油坊等被劫掠一空,新政权赏赐给他唯一的礼物是一顶高帽子——“地主”。
他留给五个子女的几百枚银元,侥幸留存下来。他以为捱过了“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坏日子就到头了,没想到更凶残的“文革”降临了。“红卫兵”掘地三尺,掠走了大部分银元。唯一幸免的是埋在猪槽下面的一袋,他特意多挖了几尺。我母亲出嫁时,箱子里藏着外祖父送给她的四十九枚银元。
子女婚配让做父母的操碎了心。儿子不敢娶同“阶级”的女子为妻,一来有坏人勾结之嫌,二来又怕后代受歧视。出身好、模样周正的女子,根本轮不到地主崽,最后能娶上一个姿色平平的,就算老天开眼了。至于女儿,只要出身好的人家愿意接收,就该烧高香了。母亲嫁给下中农汤老大二儿,就是这种情势下的产物。早年丧妻,爷爷一手把三个儿子拉扯大。大儿在西北农学院当伙夫,二子参军,三子在西安当工人。
降临人世的那个夜晚我看到了什么?
昏暗的煤油灯下,一定闪烁着三双喜悦的眼睛。母亲,外祖母,爷爷。
这天夜里,最重要的角色是接生婆。
她是迎接我的使者,也是第一个看见我的人。按照西府的规矩,孩子满月那天,是要好好谢忱她的:一包红糖,十枚煮熟的大个鸡蛋。
爷爷在院子里搓手,他急于抱孙子,尽管还不知道是男是女。我能想象老人家的神态,不时望一眼里屋。接生婆隔着厚实的门帘吆喝着:端热水啊——拿剪刀啊——外婆一边应着,一边忙活,一个生命就要降生了。
生父这时还在克拉玛依油田,他心里会有对我的期盼吗?已经升任排长的他,眼前有一条上升的道路正等着。
母亲,外婆,爷爷,我永远也不知道姓名的接生婆,你们在等着我的降生。
推算起来,父母在这一年雨水前后孕育了我。
当我哇的一声来到人世,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吃过晚饭的人们,舍不得点煤油灯,他们或在黑夜里枯坐,或在院子里看星星和月亮。刚刚度过大饥荒,人们没有多馀的粮食养猫狗。村庄是安静的,冬日的田野,只有麦子在积蓄力气。如果下了雪,它们便在被窝里睡觉,来年侍弄它们的人就有白馍吃了。
那个时候,每个村子都是一座孤岛。
在嗤嗤燃着的煤油灯下,三张喜悦的母性的脸看着我。
每个出生的孩子都是相似的,但亲人们却能从中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他们把眼前的这个生命视作奇迹。
母亲后来说,奶水不旺,外祖母急得睡不着觉,花钱买了一只老母鸡,才有奶喂饱我。
生下我,坐满月子,母亲下地干活,我就躺在外婆的怀抱里慢慢长大了。
咪咪猫,
上高窑,
金蹄蹄,
银爪爪,
上树树,
逮雀雀,
逮下雀雀喂老猫。
箩箩,
面面,
杀公鸡,
擀细面。
婆一碗,
爷一碗,
两个小伙两半碗。
屎巴牛点灯,
点出先生。
先生算卦,
算出黑娃。
黑娃敲锣,
敲出她婆。
她婆碾米,
碾出她女。
她女刮锅,
刮出她哥。
她哥上柜,
上出他伯。
他伯碾场,
碾出黄狼。
黄狼挖枣刺,
挖出他嫂子。
……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外祖母的怀抱里听过这些歌谣。
五岁
一些人从房子里蹦出来,另一些人从土窑里凫上来。
鸡鸣狗叫,雀儿跳跃,树影罩住了村庄,把太阳挡在外面。
我在爷爷背上睡着了。
我的世界里只有三个人,爷爷、妈妈和我。
母亲为人家做衣服,缝纫机发出的嗒嗒声,回响在空旷的院子里。
起风了,“哐当——”黑漆大门像是被醉汉推开了,雨斜着扫进来。
屋顶上好看的青苔,皆弯腰让水顺着瓦楞流下来,“嘭嘭”掉在地上。
一道道激越的水流,摔在地上,变成一串串水泡……摇曳着往地沟里奔去,一个个相继破碎,随之又焕然新生。
父亲在遥远的边疆服役,不知过多少日子才寄回来一封薄信。母亲把信藏在柜子里。
院子里种了一畦忘忧草,初夏开出无数朵金灿灿的花儿。在我的记忆里,老有蜜蜂围着花儿绕圈子,它们不知在忙些什么。
一天中午,母亲还在收拾碗筷,一群男人突然闯进来,抬走了缝纫机。等母亲发现动静,大门已从外面箍死了。母亲晕倒在地,爷爷赶紧唤人来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母亲?
后来,听干大说,他曾专程去宝鸡,费了很大周折,找到我的生父,劝阻他别离婚。但生父主意已定,不为所动。
母亲只好另做打算。她曾设想过把我和妹妹送人,这样能嫁个好人家。但最后,她还是决心找一个能接受孩子的男人,“我们娘仨,死也要死在一起!”我懂事后,外婆说:你母亲为你险些哭瞎了眼。
四月里,媒婆带我们去看新家。
一路上,母亲攥紧我的手。
走进邻村一户人家的院子。大人们说着话,我在院子里玩耍。一株丰腴的桃树,结满了硕大的果子。
吃完饭,经过那株桃树时,主人家婆婆摘了两颗桃塞到我口袋里:“我娃,以后想吃就能吃了。”
五月天,蝉拉长声调叫唤,我们上路了。
母亲低头扛着车子,上面放着我们一家的行李,妹妹坐在行李上,我在后面推着车。
爷爷把我们送到村口那株树荫匝地的皂角树下,就止步了。我不知道这就是分别,也没有跟爷爷说什么。
村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
窄窄的土路上,也看不到人。
在两村界河边,有一只羊埋头吃草。
世界安静极了。
太阳刺眼。车轱辘发出“吱吱吱吱”单调的声响,看母亲哀婉的表情,我隐约感到这就是离别。
风吹过来,扬起一阵黄尘。麦子快熟了,空气里逸出麦子的清香。
我们得吃新家打的粮食了。
继父给我的见面礼是一副扑克牌,随手翻出一张,竟然是猩红的红桃A,心不由一惊。
“叫爹——”母亲对我说。
“爹!”我还不知道爹是什么,但知道眼前这个男子并不是自己的亲爹。
称呼族人,于我是一件窘迫的事情。因为在心里,我并未接受这个地方。这是继父的村庄,而我是多馀的,我的血缘关系在东边那个村庄。
按辈分叫每一个大人,并把他们记在心里,常常让我感到痛苦。母亲让我借东西,我便支使妹妹去,母亲把这理解为我怕羞,多少年后,她还经常用这来作我幼年羞涩的证明。
——母亲,那不是羞涩。
一天,因为拉风箱烧火时看连环画入神,忘了添加柴火,继父踢了我一脚,而母亲无动于衷,于是我决心去死。
我跑到村北高台上,设计着自己的死法。
我能想到的是,不吃不喝,睡在里面,直到饿死为止。我知道母亲会心痛得四处找我,而继父也会很不乐意地寻找,可我害怕被他找到,我不知道他还会对我做出什么事情来。
场上立着几十个秸秆堆,偷情男女常在此勾连,村里人打牌也在其中。他们铺好了麦草,把里面弄得很暖和,还留了透气孔和透光孔,嗅着植物的香味,在里面纵情叫喊——“大小王炸了你!”
在里面躺了半天,迷迷糊糊竟然睡过去。等我醒来时,天已黑下来,人家的炊烟浮动在村庄上空,不时有驱赶牲口的声音,“吁——吁,狗日的,走啊!”
我饿了。我想母亲蒸的白面馍馍了。扒拉掉身上的秸秆屑,我往家里走去。
当我背起书包走进涝池边的小学校,童年便戛然而止。
曾经设想,当我从外归来,一切都不变化:我喜欢的女老师还是那样好看,也没有嫁人;小伙伴还等着我和他们结伴去野地拔草;亲人不会老去,我喂食的鸡和猪都不会死去……
人们所说的那个故乡,其实只在童年那里。当你找寻它时,就只剩下两个汉字了。
“故—乡”,就是逝去的、永不再来的那个东西。
钱
最快乐的事情,便是过年。
天空安静下来,大人的嗓门也小了许多,他们劳作一年的心松弛了,孩子们才有了自己的欢乐。
雪落下来,村庄白得干净。
铺满雪花的路,在我眼里就是一床棉絮,是让我们随意践踏的。我的脚踩下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听着这声响,心里充满了喜悦。
寄生在这个异姓的村子里,我屏息静气,生怕发出让别人不悦的声息。我像一只卑微的老鼠,藏身于自造的地洞里,思量外面的世界。
学校是让我放松的地方。学的那些东西,一点点支撑起我的精神,那些神奇的汉字将我唤醒了,我隐约看见了自己的命运。写作业带给我难以言说的快乐,当我驱动铅笔在纸上描画出一个字时,感到自己生出了一股微小的力量。字写在粗糙的本子上,得压住笔头,用力划动,一不小心笔芯就折了。所谓本子,是母亲用上坟用的纸裁成,订好,我再用尺子打上格子。一支铅笔我往往要用到最后一截,用手捉不住的时候,再把剩下的笔芯用硬纸裹起来,直到尽头。在这么粗糙的本子上写字,是需要耐心的,全神贯注才能写好每一个字。
我在写字的时候,心里想起的是母亲的劳作。供销社里一个薄薄的本子卖八分钱,我是买不起的。家里的日常开销,已经压缩到极致。粮食和油是队里发的,醋自己做,很少吃菜,家里有织布机,除了过年做新衣裳买几尺布外,盐,是唯一需要花钱的。
一天早上,母亲对我说:你去卖几个鸡蛋吧,没盐吃了。
当局实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不准农民养鸡。事实上,每家每户都偷偷养一两只鸡补贴家用。多了也养不起,人都没东西吃呢。
母亲从罐子里取出鸡蛋,一个一个装入布兜,再放到拔猪草的筐里,又在上面遮了一些干草,审慎地放到我手里,眼神里蓄满期待和信任。我拎着沉甸甸的东西,朝七八里外的绛帐火车站走去。
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临行前,母亲交待过“千万不能让人看见”,如果有公家人追过来就跑,可不能给没收了。走到坡口,我歇了口气。透过长长的陡坡,我看见了镇东头的砖厂。下了坡,就到车站了。这是十里八乡的人最眼热的地方,陇海铁路线上一个三等小站,扶风县唯一一个通往远方的车站。秋天的风吹过来,我感到一阵轻松。
从坡底上来一个推自行车的大人,他慢慢靠近我。我下意识攥紧了篮子里的布口袋。我感觉对方不像是坏人,一身制服,头戴前进帽,一副和蔼的干部模样。
两人几乎碰到一起时,他停下来,俯瞰着我。我有点慌张,从小到大还没有一个陌生人这样接近我,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心在扑通扑通地跳。时间漫长,其实也就几秒钟吧,这个人轻轻开口道:“你的鸡蛋卖吗?”
哦,原来是买鸡蛋的。他怎么知道我有鸡蛋呢?
“我不卖鸡蛋。”我用母亲教的话应付道。
他笑了,“你把我当成那些人了!”随即朝我伏下身,“一毛钱一个,卖吗?”
我很快地看他一眼,他脸上绽放的是让人放心的笑容。
“车站东头就坐着那些戴红袖章的人,他们专门没收鸡蛋。”他对我说。
我愿意相信他,决定把鸡蛋卖给他。母亲吩咐,一个鸡蛋至少卖八分钱。现在人家出一毛钱,已经很好了,我赶紧说:“好吧。”
那人熟练地扒拉开干草,解开口袋,从里面掏出一个鸡蛋,放到耳边晃晃,又对着太阳照照,才一个个收到自己的皮包里。他从皮夹里抽出一张崭新的一块钱,轻轻放到我手里。
我紧紧握住那张票子,手心里隐隐出汗。等他走远了,我才张开手,仔细打量着珍贵的人民币。这是我第一次拥有一块钱。我双手展开,把钱朝向太阳,纸面上神采飞扬的拖拉机女司机,是那么可爱!
我第一次拿钱,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天说要去参观烈士纪念馆,母亲给了我一毛钱,我仔细装入裤兜,拍拍外面才放心上路。老师带着我们一大早出发,扛着红旗,沿着与陇海线平行的渭惠渠一路向西,靠双脚走到了常兴镇。
那是我第一次远行。没有带水,也没有带吃的。饥,渴,一路走过去并不觉得。到了烈士墓前,才感觉干渴,就打开旁边的水龙头喝了几口。吃是舍不得的。硬挺着赶回家,河里的水,河边的树,岸边的青草,不再引起我的兴趣。一边走,心里一边在想,何时能吃上母亲的饭。走到村口,腿走向供销社,手不由自主地伸进裤兜,指头在那张纸币上摸了又摸,下决心买块面包吃。平日里,一到供销社门口老远,就能闻到面包的香味。经常有好吃的孩子偷了钱自己去买。每次去那儿,唾液便不由自主地分泌出来。我一直忍着。今天我想满足自己的心愿。
我掏出一毛钱,寄给售货员。一块面包七分钱,我用剩下的三分钱买了一根针。
走出供销社,见四下无人,我先掰一小块面包塞到嘴里。只是一小口,烤面包的那种香酥焦脆就让我迷醉。面包,你不知道,你是多好吃的东西啊。
一小块面包就这样被我一小口一小口吞下去。回家的路上我充满了力量。
卖鸡蛋的这天,把一块钱叠好,揣进口袋,我就回家了。我想让母亲高兴,她的儿子能卖鸡蛋了。
在路上,我想,母亲忙碌一天,也就像下了一只蛋。生产队男人每天十分,女人只有八分,八分也就是八分钱,母亲一天辛劳就值八分钱。
快要过年了,我多想早早穿上母亲用旧衣服做成的新衣裳。
走在雪地里,几个小伙伴专心踩窟窿,看谁踩得深。几只麻雀叽叽喳喳站在枯黑的枝头,他们饿了,这是讨食的语气,但大人们也吃不饱,谁会管它们的死活呢。
过年是要做梦的,大雪天,睡在热炕上,我的梦也是好的,我有一次梦见路上躺了无数只硬币,有一分的,二分的,还有五分的,自己两只手不够用,只管捡五分的大钢镚。心想,回去交给母亲,她就再也不用为油盐发愁了,那只懒母鸡爱不爱下蛋,我也不管了。
青草
地肥,随便撒一把种子下去,地里便长满了。
油菜,小麦,玉米,棉花,芝麻,萝卜,苜蓿……记忆里,一年四季是由植物的荣枯描画的。
那个时候,只有架在皂角树杈上的大喇叭是亢奋的,革命的音符爬满了天空。
大人们忙自己的事情,就剩下孩子和草。
夏天是少年的。
壕沟、河渠、地头,到处长满了野草。一把镰刀映现在空中,少年用井水滋润磨刀石,有时也吐口唾沫,一下下磨利刀刃。思量差不多了,便学大人,把刀尖搁在食指上比试一番,眯上眼瞅瞅,设想它触碰在草儿腰身上的情景:我会利索地收拾了它们。
天刚亮,我和小伙伴背起背篓出发了。
露珠濡湿布鞋,地里静悄悄的,草儿好像在等我们似的昂起脖颈,在微风中摇摆不已。对草,我们心里是有区别的。有的草会引人怜悯,轻轻攥在手里,温柔地一割,它们便温顺地躺在手掌里,往背篓丢的时候,也不用操心,它们轻盈地飘落,好像回到了故乡。有的就让人生出蹂躏的欲望,一把抓住头颅,一刀砍下去,它们不服气,在倒下去的同时喷出粘人的汁液,把它们扔进背篓是要用一些力气的,听到落地的声响才放心。
毛毛草让人喜欢,要是地里全是它晃动的脑袋就好了。
草看着可爱,刈割后也还活着,直到晒成细小的一缕,还是活着的。在我心里,草最坚韧,直到被粉碎机吐出来,它仍然活着,喂进军马肚子里,它就变成了奔驰的力量。
累了,一屁股坐到地上。田野干净,连一块糖纸都见不着。四周皆绿,杨树的绿贴在蓝天上,宛如新鲜的补丁。看不见虫子,却被它们细微的排泄物击中,头上、脸上、衣服上全是。即便如此,也不愿意挪动屁股,图的是树荫的庇护。
最无奈的是坐在椿树下,白白胖胖的“臭大姐”从脸前飞过,熏得人作呕,若落到手上、脖子上,用肥皂使劲洗,两天后那股味道方能散去。花纹,气味,样子,无一不叫人厌恶。当椿树上落满“臭大姐”,椿树也就不美了。
风吹过,少年心里什么也不想。红旗,标语,高挂着的毛泽东画像,让他紧张和害怕。世界尚未打开,坐在关中平原腹地,他被连绵的秦岭包围了。什么能让少年兴奋呢?——天上偶尔飞过一架飞机,机尾拉出一串长长的云彩;深夜里,火车轮子触碰铁轨所发出的激越的声响;浑浊、奔涌,永不驯服的渭河。
太阳落山,背篓装满了青草。
把草晾晒在家门口,人走过,脚踩;牲口经过,践踏,太阳晒过,两三天后便剩下枯萎的一撮,贴在地面,令人心生怜悯。过几天,将晒干的拢成堆,码放在旮旯里。一个暑假积攒下来,装了高高一车。用绳子捆扎好,几个小伙伴各自扛起架子车,朝太阳露头的地方奔去。
下坡路陡,我们将车把仰起来,使车的后轴贴地,负重的车子才会缓缓下行。肩膀扛在车把上,感受车子的颠簸,草的重量传到身上,让人不敢轻视。降到塬下,一身轻松,和风吹过,被汗水打湿的衣裳很快就干了。
沿河渠一路飞奔,树高蝉欢,清凉的河水发出欢悦的声息。我们不说话,只是发出各种叫声,“呃呃——嗬嗬——哈哈——呜呜——呀呀——”
到了杨陵军马场,草被巨大的粉碎机吞没,旋即变成碎末,世界充满青草的味道。想象它们进入骏马的腹中,生出无穷的力,马儿奔驰在祖国的原野上,践踏更茂盛的青草、土地和敌人,心里便生出一丝骄傲。
一个夏天的辛劳,换来崭新的七块钱。
又可以读书了,妈妈。
少年把钱揣进裤兜,面向天空,微微地笑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