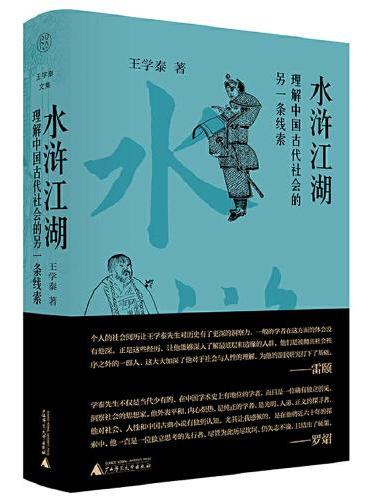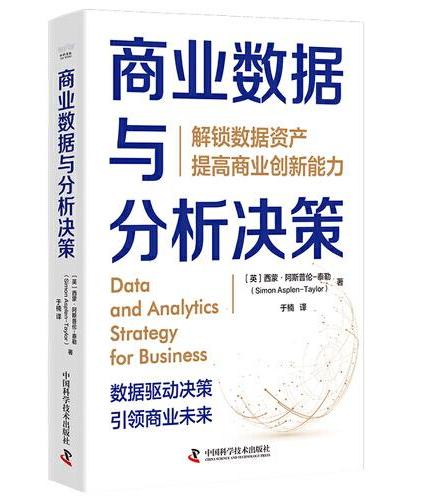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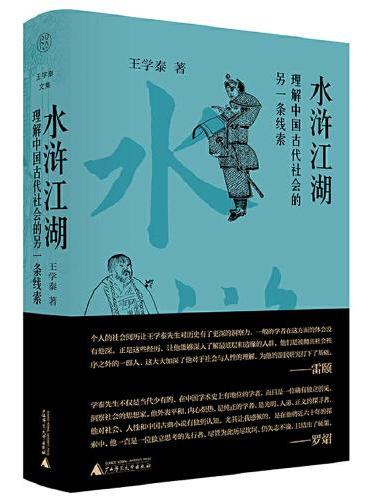
《
纯粹·水浒江湖: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另一条线索
》
售價:NT$
469.0

《
肌骨复健实践指南:运动损伤与慢性疼痛
》
售價:NT$
1367.0

《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MySQL版)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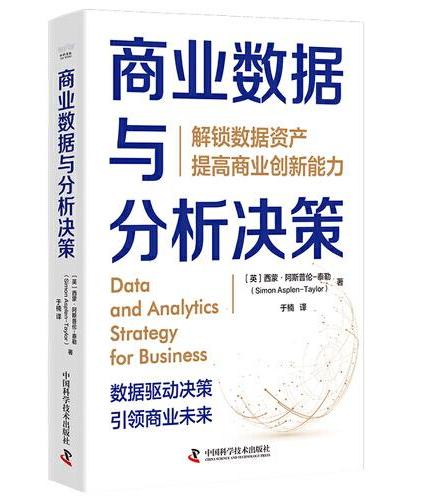
《
商业数据与分析决策:解锁数据资产,提高商业创新能力
》
售價:NT$
367.0

《
倾盖如故:人物研究视角下的近世东亚海域史
》
售價:NT$
357.0

《
史学视角下的跨文化研究(一): 追踪谱系、轨迹与多样性
》
售價:NT$
485.0

《
历史文本的文化间交织:中国上古历史及其欧洲书写(论衡系列)
》
售價:NT$
551.0

《
1688:第一次现代革命(革命不是新制度推翻旧制度,而是两条现代化道路的殊死斗争!屡获大奖,了解光荣革命可以只看这一本)
》
售價:NT$
1010.0
|
| 編輯推薦: |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当代著名作家张炜长篇成长小说力作
★一部少年的成长史诗,一段心灵的蜕变之旅,一次对生命、自然的叩问和回归
★似曾相识的世界,唤醒久违的激情、梦想和勇气
★作者创作40年深情回望
★作品首次出版后,作者又续写缀章数篇,本书是其续写完整版
★王蒙、王安忆、韩少功等诸多名家诚意力荐
“回首往事,有时不免生出阵阵惊诧:我竟然经历了这么一沓子杂事和怪事,还有这么多美好动人的事;特别让我惊奇的是时间的速度:彷佛刚刚一转身,五十年就过去了……” ――就像《远河远山》的主人公少年恺明一样,从1975年19岁发表首部诗歌算起,张炜已从事文学创作整整40年。这部作品是张炜读者zui多的小说,也是他zui为得意的作品,更是有着他个人经历折射的作品。40年之际,谨以此作献给所有已经走过、正在行走和即将走向青春的人,愿为青春zui好的致意。
|
| 內容簡介: |
十二岁少年“我”的父亲早在“我”一岁多即逝去,善良慈爱的母亲带着“我”改嫁,遭遇到冷酷暴虐的继父。与这样的“父亲”共同生活,“我”变得沉默寡言,内心却波涛汹涌。“我”把所有的爱恨情仇,把现实、梦境、幻想,无休止地倾注于笔端纸上……冰河对岸的护林小屋中有一个与“我”一样不爱说话只爱书写的女孩,“我”们相遇相知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少年时光。然而,童年伙伴的死亡,至亲母亲的早逝很快便接踵而来,“我”不得不离家远行,一次次走向未知的远方……
该书1996年第一次在台湾出版,即在两岸三地引起巨大反响。经过八年沉积酝酿,作者张炜再度提笔,增补“缀章”四万余字,把原书以“续写完整版”的形式,完整地呈现给读者。全书笔法纡徐从容,完全内心剖白似的语言舒缓流畅,成长的磨砺和阵痛饱含在对梦想和温情不懈的追寻与向往中,别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
| 關於作者: |
张炜,当代著名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1956年生于山东省龙口市。1975年开始写作。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古船》《远河远山》《九月寓言》《外省书》《刺猬歌》及《你在高原》等19部,散文《融入野地》《芳心似火》等20部,文论《精神的背景》《当代文学的精神走向》《午夜来獾》,长诗《松林》等。
作品曾获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等海内外70多个奖项。2011年凭借《你在高原》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鄂尔多斯文学大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作家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亚洲周刊》“全球十大华文小说”之首等十余奖项。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日、法、韩、德、瑞典等文字在海外出版。
|
| 目錄:
|
自序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第六部
第七部
缀章 · 碎片
|
| 內容試閱:
|
仿佛刚刚一转身,
五十年就过去了。
一个人如果真的有了一种癖好就难以根除,
无论什么时候写和看常常是我最大的乐趣,
给了我一切,
一切的一切……
3
其实最早阻止我的是妈妈。她生下我这么个孩子,却又埋怨我,为我痛惜。我不知该说些什么。那涌进心里的阵阵灼烫,让我只想面向南山大声呼喊。可我喊不出,像往日一样沉默。什么时候染上了写个不停的毛病?回想一下,像是刚上学不久,大约三年级吧――很平常的一天,我突然觉得心里一热,就趴在床上写起来。我写看到的一只鸟、一只蝴蝶,写它们可爱的模样。我在纸上与它们热烈交谈……妈妈走进来,我没有发现。妈妈站在身后看了一会儿,喊了一声。我抬起头,吓了一跳,因为她脸上是很害怕的样子。她说:“你不能,孩子,你不能!”妈妈是说我不能在纸上写。为什么不能?她说不出。
可我需要这样。我学会了写字,越来越多的字,我渴望记下什么啊。许多许多的字,连接起来是一句话;许多许多句话,连接起来就是我心里的意思了……神奇的字组成的东西包含的奇异说也说不完。
我们家的阁楼上有一个粗糙的木箱,我爬上阁楼的那一天,就知道真正的珍宝藏在哪儿了。
这个木箱也是妈妈携来的,就像当年携我而来一样。她没有把它遗在远方,可见她仍是可爱的妈妈。就这样,我怀着对妈妈说不出的爱和感激,一点一点读完了木箱里的书。我是嚼了、咽了,世上最令人回味的美食。
感谢神灵让我走近了那个木箱。我开始了无穷无尽的幻想。我认为自己来到人间,来到继父这个小城,特别是有这样一个妈妈和死去的父亲,都是很怪的事情。我自己就很怪。到底是谁给了我这个生命呢?我开始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了。这是老师和同学告诉我的,也是我自己越来越清楚地感到的。
我长大了一岁,又长大了一岁。令我不解的是,如今我简直是一天天地痴迷起来了,简直是发疯般地在纸上写。继父把我的这个毛病看得极为严重。他确信我是着了魔怪。但由于他的百般阻挠、千方百计的折磨都未能奏效,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放弃了努力。他对一帮狐朋狗友说,家里有一个痴子、傻子,也许是个妖怪。
今天的人或许不能理解,一个大人为什么会对一个少年倾注这么多的愤恨。但我理解。因为他是我的继父。我们是为了互相仇恨、互相折磨才走到一起的。我心里明白。他无论是在别人眼前,也无论是白天、黑夜,只要看见我在纸片上写,就一把扯过,团成一团扔了、撕了。
他好像挺恨在纸上写字的人,因为他自己就从来不写、从来不看。他用狠毒的话骂我、咒我,说我将来一准不得好死。妈妈渐渐看不下去,劝他几句,反而惹起更大的火气。他用一根带铁钉的皮带抽打桌子,一次用力太大,桌子的一角都抽裂了。这一下抽到身上会是什么滋味?我也许会被他弄死。
他无数次对我动手脚,但从未使用那根皮带。这让我觉得奇怪。
“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发疯地写呢?可怜的孩子!”妈妈搓着眼睛,但每次不等我回答就转身做事情去了。她明白,她什么都明白。
不明白的是我自己。我只知道我离不开纸和笔,是它们给了我一切,一切的一切,包括全部欢乐。我写下的字,只有一小部分,很少的一部分被老师和同学看过。那是写在作文本上的。有两三次,老师把我写的东西念了一遍。所有同学都转脸看我,有几道目光里还有小小的嫉妒。我的脸肯定变得通红。高兴啊,高兴得想哭。
但我知道,他们无法懂得我写的这些。因为这是在跟自己说话,跟一些他们所不认识或从来不曾留意的人和事说话。平时跟我说话的人太少了,我只能自己寻找一些人、动物,还有我喜欢的任何一件东西说话。我跟梦中的父亲说话,边说边记――这有点像给他写信。一只白头翁鸟每个星期都悄悄飞到我的窗前。我们也互相分享了一些秘密。我对继父的仇恨它心里也清楚。我甚至请教了解脱之方。它为我流泪,为我歌唱。在长长的时间里,我和白头翁成了最好的朋友,直到它后来一去不返。
我知道一朵花、一棵草,都有奇特的心事。一只浆果,在它成熟发红的时候,肯定变得和蔼善良。我与它无所不谈。我真的具有与其互通心语的能力。有一次实在忍不住,我就跟妈妈说了。她毫不觉得惊奇,只是低下头去。好像妈妈在回忆一个熟人旧友――那个人好像也具有类似的能力。
半夜,我突然听到了床边木柜的呻吟。这呻吟像老人一样凄怆。我睡不着,就一下一下抚摸这木柜。它渐渐没有声音了。我们家所有的器具之中,数这只木柜最老旧了,它也是母亲的。
我觉得这只木柜与外祖母有关。我从未见过外祖母,也很少听妈妈谈起过她。但我认定这木柜是老人家的,于是它就等于是她了。真的,我依偎在柜子上时,就觉得是在老人怀里。它有体温,有一动一动的脉搏。
4
我们居住的这座城市不大,西靠大海。记忆中的这座城市一直是潮湿的,到处撒满了煤灰。因为城里人做饭、生火取暖全要用煤,而煤是从码头上运来的,搬动时撒在了砖路上。码头上的大船是我心中的花瓣,我一看见它的烟囱、翘翘的船首,心里就绽开了花。我真高兴。
如果没码头和码头上的大船,这个小城就一点也没意思了。从码头上出来的人花花绿绿,什么样的都有。这些人是从船上下来的,天南地北都有。最奇怪的服装都是他们穿来的:雪白的大翻领洋装、缎子长袍、漆黑的西服、白蓝两色的水兵服……我有时就为了看这些新奇,长时间地站在通往码头的大路旁。
有一天我正这样看着,突然记起了许久前的一件事。这件事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决定了我的大半生。我仿佛亲眼看到一个三四十岁的妇人――脸色苍白,手牵一个一岁左右的男孩,小心翼翼走下大船,登上岸。那长长的、边上系了铁索的木板一颤一颤。小男孩叫:“妈妈!”妈妈弯腰亲他,说有人会来接他们的。
(那一天没有人接他们母子。这个小城里有他们的远亲,但远亲没有接到电报。当时这儿的电报局十有八九要弄错点什么。不过这最终没有影响什么。他们在此地落脚,而且住了下来。)
那就是我和妈妈。
就这样,我不久就遭遇了继父。当时这个男人在城里是个高高在上的人物。他倒不是什么官,而只是码头上的一个闲人。他在岸上转转,吆吆喝喝,从货仓到客运站,随便来去。所有人都敬他怕他,港长也一样。因为他是一个有过战功的人,据说战功很大,只是不小心误伤了一个人,才下放到这个码头上工作。有人说如果不是那次意外,他早就是个将军了。对于一个马马虎虎可以做将军的人,人们的敬畏之情说也说不完。比起他来,这座小城就显得太小了。关于他的故事惊天动地――一半是真,一半是出于虚荣心的小城人自己编造的。因为任何人都愿说自己那块地方如何如何了不起,出过怎样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大人物,他们就会编造出一个。继父就是他们编造出的英雄。
他们忘乎所以地传颂他的功勋,其实只为了自己心里的满足。因为我渐渐发现,码头上的人,还有所有认识继父的人,他们一点也不喜欢他。他们有时当面逢迎,那不过是怕他。
妈妈也多少有点像那些人,怕他。她过去爱他,但只爱一点点,而且时间很短。我这辈子搞不明白的事情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妈妈为什么会嫁给这样一个人。好像妈妈来这个小城之前很久就认识继父。她说:“那时啊,那时我们幸亏有他啊!”到底是什么事,“那时”又是何时,她再不说了。
继父喝了酒格外吓人。他不刮脸,胡子又浓又长,像铁丝。他嘴里喷着酒气,摇摇晃晃走上大街。他不太上班,码头上的人也不希望看到他,因为他说不定逮住谁就一顿臭骂。他硬把码头上的一辆破摩托抢来,骑上出城,到海滩林场去打猎。他共有长长短短几支枪,有打散弹的,有打独子儿的;有气枪,还有真正的钢枪――部队使用的武器。全城没有任何人可以拥有这么多武器,只对于他,谁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平时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崩了他!”说是说,他的枪只打一些动物。那些小鸟、狐狸和兔子,凡是遇上的,都要倒霉。每逢看到他提着血淋淋的猎物走回院子,我就恨死了他。他倒高高兴兴,一进门就大声喊妈妈,喊不应才骂,笑着骂。
我们家住在离码头围墙不远的一幢平房里,院子很大,而且长了无花果树、橡子树。这房子原来是副港长的,副港长搬了新居,这儿又被他儿子占了。因为继父来回搬摩托车,爬上爬下心烦,就对副港长的儿子说:“年轻轻的,滚吧!”那个年轻人哭着去求自己父亲,又找港长,结果全无济于事。那些人都说:“你快腾房子吧。”
这幢小院成了我最喜欢的地方。只要继父不在,这里就是真正的乐园。地上有数不清的花草,有出其不意的小虫子,飞来飞去的蝴蝶和蜻蜓。秋天,橡子成熟的时候,就扑到地上来。它们长得可太美了,毛茸茸的壳斗,圆圆的橡实,都让我长时间目不转睛地端详。我爬上了这棵枝叶繁密的大树,让树叶把身体笼住。这样我迎来一只喜鹊、一只野鸡、一只蓝点颏。有一天我正卧在那根粗斜枝上,突然有个机灵的小动物迈着难以置信的碎步跑过来。我首先瞧见了它银色的长尾。原来是一只松鼠。
后来我又发现了五六只不同的松鼠。它们在树上跑来跑去,有时顺着树干飞快蹿下,围着树玩耍。它们与我熟了,并不怕我。我一抛出馒头渣,它们立刻就凑近了。它们像人一样,用双手捧着食物吃。
5
我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了,妈妈更为不安。她走进我的房间,一推门,我赶紧把手头的东西藏到被子下。那是我刚刚写满的一张纸。我正激动得满脸通红。妈妈肯定发现了,但没有作声。她一下下抚弄我的头发:“妈妈就你这么一个孩子啊,这么一个。”她说完再也不吭声了。后来她紧紧地抱住我。只一会儿我就想哭。我一这样挨近妈妈就想哭。这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太幸福了,就得哭。我想一个人到了没有妈妈搂一下的时候,又深又长的悲痛就该来了。这种悲痛躲也躲不开。妈妈搂紧了我。
“孩子,你整天不说话,为什么?整天写,写,这会得病的……能告诉我你怎么了吗?告诉妈妈。”
我直盯盯地看着。我没有可说的。因为我不爱说话是天生的,这并不为什么。平时,我最感动、最喜悦,想大声嚷叫的时刻,也是缄默,最多只不过是找一张纸,飞快地写画一阵。这才给我欢乐,让我痛快。妈妈说老写会得病,她错了。我的笔和手给缚住,才会得病。
妈妈离开后,我长时间什么也没做。我在想妈妈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不说话呢?真的,在家里,我常常一整天不吭一声;还有时时间更长,可能是一个星期不吭一声。有一次,最长的一次,我大概一个月没怎么说话。为此继父暴跳如雷,说要把这个哑巴的嘴用铁棒撬开。幸好他没有那样做。那次妈妈把我领到一边,一个劲儿催问:“为什么,为什么?”我像没有听见,两眼发直看着。她急哭了。我的心软下来了。我爱妈妈。凭着这爱,我用小得只有她和我两人才听得清的声音说了一句:
“我的喉咙疼。”
后来当然有医生来家里,用竹板压我的舌头,又翻我的眼皮,脱去我的衣服仔细看。结果医生摇着头走开。医生留下的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药片,不是维生素就是钙片,我一粒也没动。医生第二次离去时对妈妈说了语重心长的一句话:“性格啊!”
妈妈有时坐在我面前,摸摸我的额头,表示着她的欢欣。她还多次吻我的额头,不过那是以前了。现在她用手代替了嘴唇。我暗暗观察过自己的额头,我得说它不算难看。不过它让妈妈喜欢成那样,我总还是不解。她说:“你爸不大声呵斥就好了,你呀,就不会这样闷着了。”
她的叹息是我最熟悉的声音。直到我长大了,长得比一般人都要大一些时,还是常常记起妈妈的叹息。有时偶尔听到人群中有谁发出一声长叹,我立刻会想起妈妈。善良无奈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出这长长一叹了。
妈妈从来无法阻止继父的狂躁。他有颗帝王心,当不成,就在家里撒野使威。他发火是随时随地的,大瞪双眼看妈妈、看我,动不动就嫌我妨碍了他。我也只能躲着他。我更不敢吭声;从刚有记忆的时候就是这样――那时还没有这个继父。奇怪,我怎么那时也不敢吭声?
我一想起这些就暗暗吃惊,有时真想大声问一句妈妈:是谁吓着了我啊?是什么时候?是在娘胎里,还是更早更早的时候?有人说一个人投生之前只是游动在空中的无形颗粒,它的名字叫“灵魂”。大概我的“灵魂”被什么给惊吓了,一定是这样。
所以,尽管妈妈把一切罪过都推到了继父身上,我却不以为然。我宁可相信那个医生留下的格言般的短句:性格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