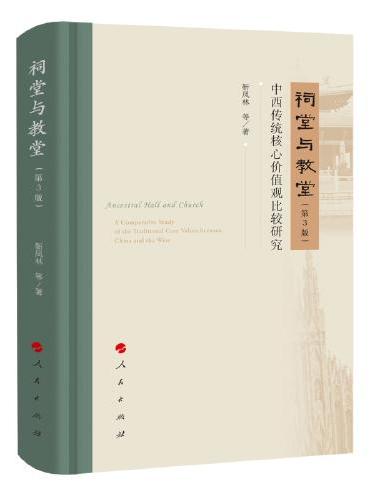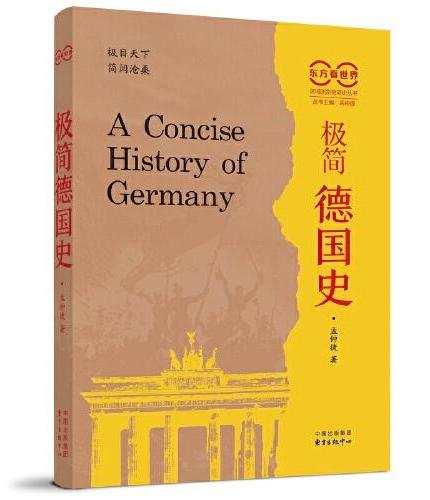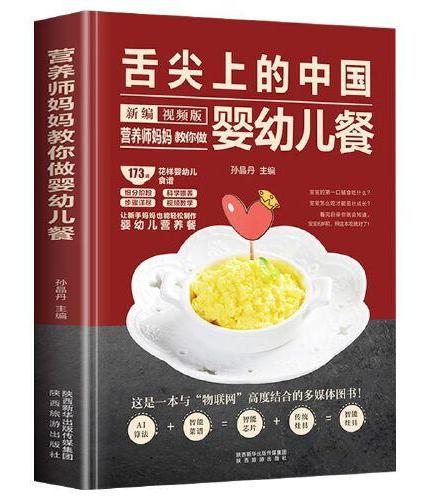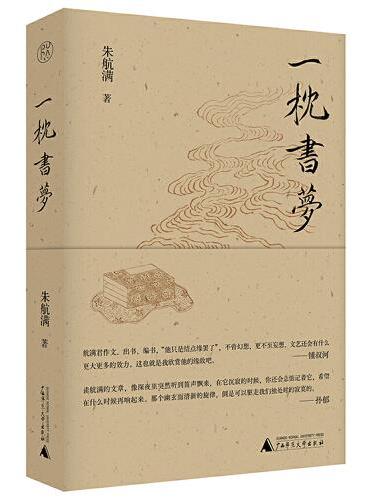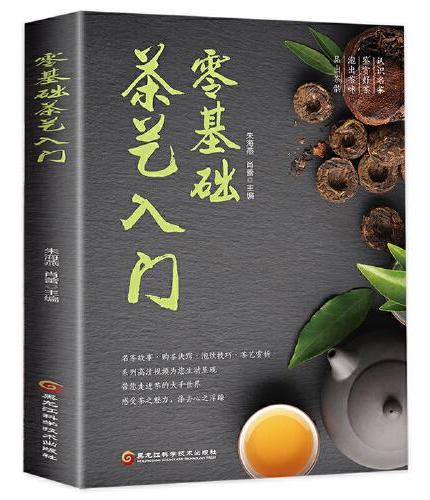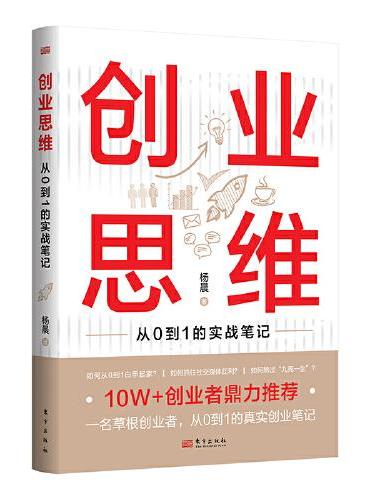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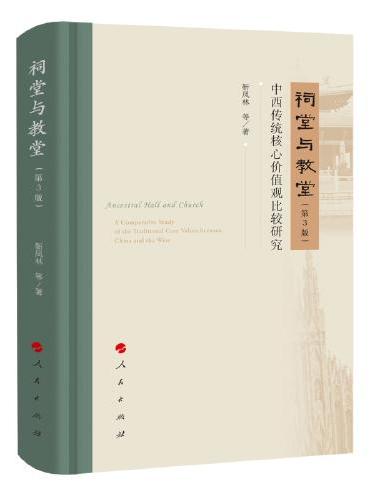
《
祠堂与教堂:中西传统核心价值观比较研究(第3版)
》
售價:NT$
5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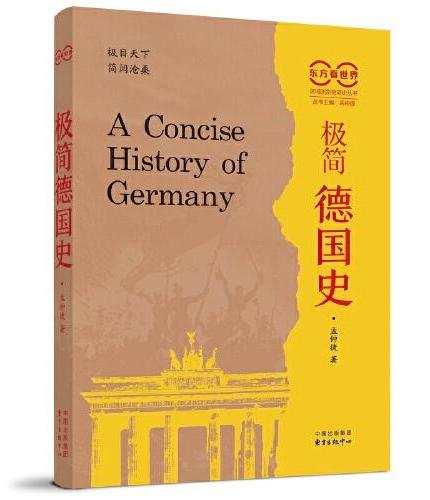
《
极简德国东方看世界·极简德国史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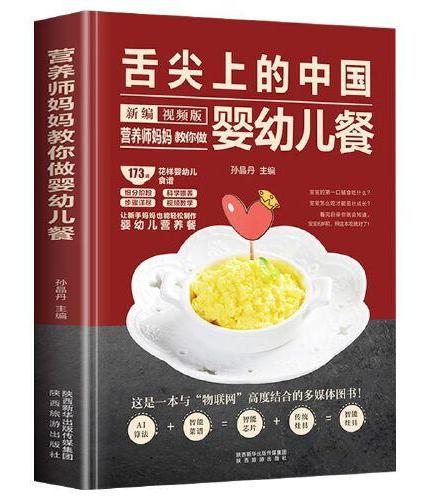
《
舌尖上的中国新编视频版营养师妈妈教你做婴幼儿餐
》
售價:NT$
296.0

《
Scratch创意编程进阶:多学科融合编程100例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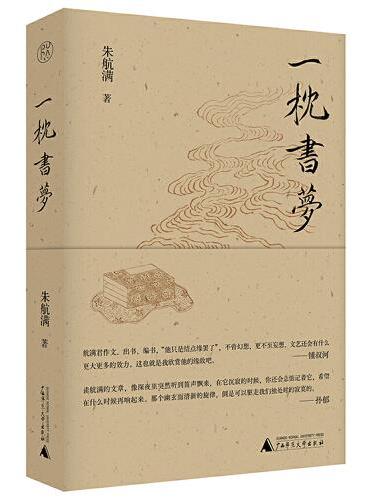
《
纯粹·一枕书梦
》
售價:NT$
3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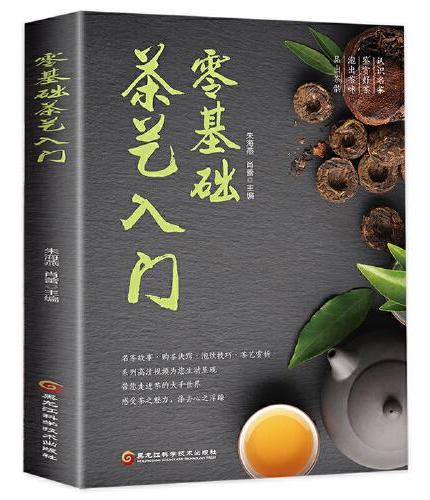
《
新版-零基础茶艺入门
》
售價:NT$
17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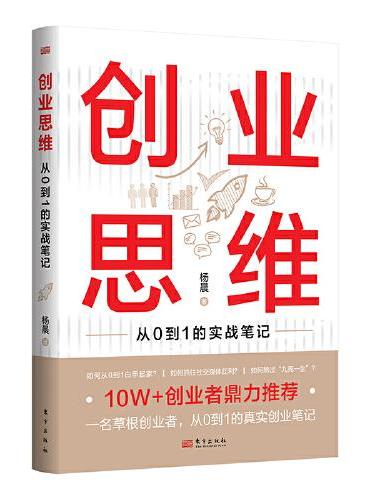
《
创业思维:从0到1的实战笔记
》
售價:NT$
356.0

《
家庭财富管理指南
》
售價:NT$
398.0
|
| 編輯推薦: |
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费曼的传奇人生,一个好奇之人的有趣活法
世上的天才分两种,一种让人觉得努力就能做到;另一种则如魔术表演师,充满好奇、从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后一种,正是费曼。
不要动辄问“这有什么用”,当不了科学家,至少做个有趣的人
不能成家成名,至少要会开保险柜、会破译玛雅象形文字、会打桑巴鼓
“我不喜欢获奖,我只为自己的成就高兴,为别人欣赏我的成就高兴。从发现中所得到乐趣,让别人可以利用我的研究成果,就是我所期望的一切。———理查德?费曼(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的答谢辞)
|
| 內容簡介: |
《你好,我是费曼》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的自传式随笔。
费曼在参与“曼哈顿计划”时,成为开保险柜高手。
费曼在默数一二三时,发现了每个人大脑工作的方式截然不同。
费曼在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时,抱怨没有人赞赏他的桑巴鼓技艺。
费曼在调查挑战者号失事时,靠一杯冰水、一个橡皮圈,打破了威权,还原了“挑战者号”失败的真相。
对费曼来说,这一生就像个孩子一样,好奇地寻找着前方的未知 。他最希望的,是想留给未来的人们一双自由的手。
|
| 關於作者: |
理查德?费曼(Richard P.Feyrman, 1918-1988
1918年,生于美国纽约。
1939年,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
1942年,加入美国原子弹研究项目小组,参与秘密研制原子弹项目“曼哈顿计划”。
1965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86年,参与调查“挑战者号”事故,当场做实验证明爆炸起因。
1988年2月,因癌症辞世。
除了作为一名物理学家,在他一生中的不同时期,他还是无线电修理者、保险柜密码破解高手、艺术家、舞蹈爱好者、手鼓演奏者和玛雅象形文字的破译者,以及“呼麦唱法”的发现者,曾一直期待去呼麦的发源地——图瓦,最终未能成行。
|
| 目錄:
|
目 录
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
科学家的养成 3
你为什么在乎别人怎么想 13
像数一、二、三那么简单…… 49
积极向上 56
城市旅馆 59
赫曼到底是谁? 66
费曼,歧视女性的猪 69
我刚跟他握过手,你信不信? 73
信件 81
费曼先生调查挑战者号事件
简要介绍 105
自杀 108
冷酷的事实 111
注意六点钟方向 147
侦探 152
不可思议的数字 170
引发争论的附件 182
第十条建议 192
会见媒体 200
事后的思考 205
科学的价值 213
附录F :航天飞机可靠性观察报告 225
|
| 內容試閱:
|
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
科学家的养成
我有一位艺术家朋友,他的某些观点让我无法苟同。他会拿起一朵花说:“看,多美啊。”我也表示同意。可接着他就会说:“身为艺术家,我能看到这朵花的美丽之处。而你们这些科学家,只会拿去做解剖,多无趣。”我觉得这种看法很无知。
首先,他能看到的美所有人都能看到,当然也包括我。我不具备他那样的美学素养,但我还是能欣赏花朵之美的。但与此同时,我能看到更多他无法欣赏的美。我能想象花朵内部的细胞排列,那也是一种美。美不仅存在于厘米量级,也存在于更小的量级中。
细胞有着复杂的运动和排列方式。在植物的进化过程中,花朵的颜色起到吸引昆虫授粉的作用,这一点很有趣,意味着昆虫能分辨颜色。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我们看到的美对于低等生物是否成立?此类有趣的问题都是从科学角度引申出来的,这只会增加人们对花朵的好奇心、神秘感和敬畏之心。只是增加,根本无损于花朵其他方面的美。
我一直是个偏科的人,年轻的时候,我几乎将全部的精力倾注于科学。那时,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太多的耐心学习所谓的人文学科。虽然大学里设了很多必修的人文课程,可我总是尽可能逃掉。直到后来,年岁渐长,心灵也更加从容之后,我才逐渐涉猎了一些。我学习过绘画,又多读了些书,但我仍是个严重偏科的人,知识面不广。我的智力有限,只能把它用在特定的方向。
在我出生之前,父亲曾对母亲说:“如果是个男孩,就让他当科学家吧。”①当我还是坐婴儿椅的小婴儿时,有一天,父亲带回一些浴室用的小瓷砖,不过是残次品,颜色花花绿绿。我们拿着玩,父亲把它们在小餐椅上排成一条直线,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然后我从一端一推,它们就全倒了。
过了一会儿,我会帮着把它们立起来。很快,我们开始摆出更复杂的形式:两片白一片蓝,两片白一片蓝,依次排列。母亲看到后说:“你就随他去吧,如果他想摆蓝色的瓷砖,就由着他摆蓝色吧。”
可父亲说:“不行,我想让他知道什么是模式,以及模式的有趣之处,这也是初等数学的一部分。”就这样,他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告诉我,世界是什么,世界有多奇妙。
我家里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父亲常常让年幼的我坐在膝头,给我念《大英百科》。比如,我们正在读关于恐龙的内容。有可能正读到霸王龙,里面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这只恐龙有二十五英尺高,脑袋有六英尺宽。”
父亲会停下来说:“来,让我们看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如果它站在我们家的院子里,一伸脖子就能够到窗户。”(当时我们在二楼。)“但它的脑袋太大,没法从窗户探进来。”每念到一处,他都会想尽办法跟现实联系起来。
想象那样的庞然大物真是让人兴奋又深深着迷。而且这些巨兽都灭绝了,没人知道灭绝的原因,因此,我一点儿也不担心会有恐龙真的从窗户探进头来。我从父亲那里学会了转换:读到任何内容时都会想想其现实意义,即那到底在讲什么。
我们以前常常去凯茨基尔山——纽约人夏天经常光顾的避暑胜地。父亲们工作日都在纽约,只有周末才过来。到了周末,父亲会带我在树林里散步,给我讲森林里正在发生的趣事。其他孩子的母亲看到了,觉得很不错,便要求她们的丈夫也带孩子去散散步。她们试图做自己丈夫的工作,可是一点儿效果也没有,于是便请求我父亲带上所有的孩子。可父亲不愿意,因为他和我有着特殊的关系。最后,其他的父亲也只好周末带着孩子去散步。
等到周一,父亲们都回去工作了,我们这些小孩儿聚在一起玩。其中一个小孩儿对我说:“看到那只鸟了吗?那是什么鸟?”
我说:“我可不知道那是什么鸟。”
他说:“那是棕颈鸫。你爸爸什么也没教你呀。”
事实正好相反。我父亲其实已经教过我:“看到那只鸟了吗?”他说,“那是斯氏莺。”(我很清楚,其实他并不知道正确的名字。)“哦,在意大利它叫‘查图拉皮提达’。在葡萄牙,它叫‘波姆达培达’。中文名字是
‘春兰鸫’,日文名字则叫‘卡塔诺·塔凯达’。即便你知道它在世界各地的叫法,可对这种鸟本身还是一无所知。你只是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这些不同地方的人是这么叫它的。所以我们还是来观察一下这只鸟吧,看看它在做什么……这才有意义。”(所以我很小就懂得,知道某个事物的名字与真正了解这一事物的区别。)
他说:“比方说,你看,这只鸟不时去啄自己的羽毛。看到了吗?它一边走一边啄羽毛。”
“嗯,是的。”
他说:“你觉得鸟儿为什么要啄自己的羽毛呢?”
我说:“可能它们飞的时候把羽毛弄乱了,所以要啄一啄,把羽毛理整齐。”
“好吧,”他说,“如果是那样,它们刚刚停下来的时候会啄得勤一些,而落地后过了一段时间就不会啄得那么勤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他说:“让我们来看看它们是不是刚落地时啄得比较勤。”
不难发现,鸟儿落地一段时间之后跟刚刚落地时啄羽毛的频率并没有太大区别。于是我说:“我想不出。为什么鸟儿老要啄羽毛呢?”
“因为有虱子在作怪,”他说,“虱子吃羽毛上掉下来的蛋白质皮屑。”
他接着解释:“虱子的腿上有某种蜡质,比它更小的螨虫就吃这个。螨虫不能充分消化这些蜡质,会用屁股排出一种类似糖的物质,这里面又繁殖了细菌。”
最后他说:“你懂了吧,凡是有食物的地方,就会有某种以它为食的生物。”
现在我知道,鸟儿腿上未必有虱子,虱子腿上也未必有螨虫。父亲所说的细节不一定正确,但他告诉我的原则是对的。
还有一次,那时我大了一点。父亲从树上摘了一片叶子,这片叶子上有个奇特的裂纹,我们之前没怎么见过。叶子基本坏死了,表面有个C形的棕色图案,C的一头位于叶子正中,一头位于叶子边缘。
“看看这条棕色的线,”他说,“它起始的一端比较细,越接近边缘就越粗。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一只苍蝇,一只黄眼睛、绿翅膀的绿头苍蝇在这儿产了一颗卵。然后卵又孵成了蛆(跟毛毛虫有点像),蛆就整天吃这片叶子。它咬过的地方会留下这种棕色的痕迹。蛆长得越大,斑痕就越宽,等吃到叶子边缘的时候它就完全长成了,变成了一只苍蝇——黄眼睛、绿翅膀的绿头苍蝇。然后它也飞到其他叶子上去产卵。”
同样,我知道其中的细节不一定全对,也可能是甲虫造成的,但他要告诉我的道理是生命的可笑之处:一切都是为了繁衍。无论过程多么复杂,主题只有一个:循环往复。
我没有接触过其他孩子的父亲,也不知道我父亲有多了不起。他是如何发现这些科学的深层法则并且热爱它、钻研它的?他这么做的意义何在?我从没正式问过他,因为我以为所有的父亲都知道这些事情。
父亲还教育我去观察事物。一天,我正在玩“马车快递”,就是一辆带车斗的玩具马车,里面有一个球。当我拉动马车的时候,我留意到了球的运动方式。我找到父亲,说:“爸爸,我发现了一件事。我拉动马车的时候,球会往后滚。而如果我拉着马车走着走着忽然停下,球会往前滚。为什么会这样?”
“哦,没人知道。”他说,“大体的规律是,运动中的物体趋向于保持运动,而静止的物体则趋向于保持静止,除非你用力推它们。这种趋向性叫作‘惯性’,但没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你要知道,这是更深层的理解。他不会仅仅告诉我一个名称。
他接着说:“如果你从旁边观察,会发现,拉动马车时,小球相对于车斗有保持静止的趋势。可事实上,马车刚动起来时,摩擦力使得它相对于地面向前运动了一点儿。而不是向后运动。”
我跑回玩具马车旁边,把球重新摆好,然后拉动马车。从旁边观察,我发现父亲说的果然是对的。相对于地面,球往前移动了一点儿。
父亲教育我的方式就是这样,给出各种各样的实例,并加以讨论——毫无压力,只是愉快、有趣的讨论。这激励了我的一生,让我对所有的科学领域都饶有兴趣。(只是恰好我在物理方面做得更出色些。)
我深深为之着迷,这么说吧,就像有人因为小时候尝过某种美妙的滋味,长大后便不断寻找那种东西。我一直像个孩子一样,寻找着前方未知的奇迹,尽管不是每次都能如愿,但也不时能够成功。
那时,比我大三岁的表哥正在读中学。他对代数很头疼,于是请了一个补习老师。补习老师教课的时候,允许我坐在一边旁听。我听到他说到了x。
我问表哥:“你要干什么?”
“我要解出2x+7=15中的x等于多少。”
我说:“是四呀。”
“答案没错。不过你是用算术算的,得用代数。”
幸好我学过代数,学校里没教,但我在姨妈家阁楼里的旧课本上读到过,并且明白,最终目的就是得出x的值,用什么方法其实无所谓。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必须“用算术”或“用代数”的想法。“代数方法”仅仅是一套让人盲目效仿就能得出答案的规则,类似于“方程的两边各减去七,然后同时除以x前面的系数”。这一系列的步骤能够帮你得到答案,即使你根本不理解这么做的目的。而发明这些规则只是为了让不爱学习代数的学生通过考试而已。所以我表哥从来没有真正弄懂代数是什么。
本地的图书馆里有一套数学丛书,第一本就是《实用算术学》,然后是《实用代数学》和《实用三角学》。(我从书里学到了三角学,但很快就忘记了,因为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大概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图书馆打算购入《实用微积分》。我从《大百科》中知道微积分是一门重要也很有趣的学科,所以那时我觉得,我应该学会它。
终于在图书馆看到微积分的书时,我非常兴奋。我去跟图书管理员借书,她看着我说:“你这么小,借这本书干什么?”
这是我人生当中为数不多的几次因为尴尬而撒谎,我说是给我父亲借的。
我带着那本书回到家,开始学习微积分。在我看来,里面的内容简单明了。父亲看到了,也开始读,但却觉得很复杂、很难懂。于是我试着解释给他听。在这之前,我从没想过他的智力也是有限的,这让我有点不开心。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在某些方面的知识已经超过他了。
父亲还教给我一样物理以外的东西,那就是对大人物的不敬之心,虽然不知道是对是错。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让我坐在他膝头,给我读《纽约时报》,那时候报纸还是凹版印刷的,上面刚刚开始刊登照片。
有一次我们看到一张所有人向教皇行礼的照片。父亲说:“你看,这里站着一个人,其他的人都在向他鞠躬,他们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是教皇。”父亲讨厌教皇。他说:“区别只在于他戴的帽子。”(如果是个将军,他会说区别只是肩章。总之就是装扮、制服和职务的不同。)“可是,”他又说,“这个人跟其他人一样,也要吃饭,也要上厕所。他也是个人。”(顺便说一句,我父亲做制服方面的生意,所以他知道,一个人穿着制服跟脱去制服后其实是同一个人。)
我想,他对我挺满意的。有一次,我从麻省理工回来(我已经在那里上了好几年学了),父亲说:“你现在学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了,有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却一直没弄明白。”
我问他是什么问题。
他说:“我知道,当原子从一种状态跃迁到另一种状态时,会发散出一种叫光子的粒子。”
“是的。”我说。
他又说:“那光子是早就存在于原子中的吗?”
“不,光子不是预先存在的。”
“那么,它从哪儿来?是怎么跑出来的?”他说。
我努力向他解释:光子数是不固定的,它们因电子的运动而产生。但我解释得不是很好。我说:“就像我现在说话发出的声音,在这之前,它们并不存在于我的身体中。”(这就好比我儿子小时候忽然说他不能用某个词了,后来我们知道那个词是“猫”,因为他的“词语口袋”里没有这个词了。人们说的话并不从“词语口袋”里来,同理,原子中也没有“光子口袋”。)
他对我的解释不太满意。我也从来没能解释清楚他不懂的问题。所以这方面他没有成功:他送我上大学去寻找那些问题的答案,可他自己从来也没能找到。
虽然母亲对科学一窍不通,可她对我的影响很深。特别是她有很强的幽默感,我从她那儿懂得,理解的最高层次就是欢笑和人类的同情之心。
你为什么在乎别人怎么想
不知为什么,当我还是十三四岁的少年时,总爱跟一帮年龄稍大的、成熟点儿的小伙们混在一起。他们认识很多不同类型的女孩子,会一起出去玩,经常去海滩。
有一次我们在海滩上玩,大多数男孩都跟女孩们去了堤坝上。我对其中某个女孩有好感,就自言自语地说:“哦,我真想跟芭芭拉一起去看电影……”
我只是说了这么一句,旁边的男孩却兴奋起来。他跑上石堤,找到芭芭拉,一边推她过来,一边大声说:“芭芭拉,费曼有话跟你说。”真是太尴尬了。
很快,男孩们都围了过来,说,“嘿,说呀,费曼!”于是我邀请她去看电影。那是我的第一次约会。
回家后我告诉了母亲,她给了我各方面的建议,应该如何如何。例如,如果我们一起坐公交车,我应该先下车,然后伸手去扶她;如果我们走在大街上,我应该走在外侧。她甚至教我应该怎么得体地说话。她传递给我的是一种文化传统:当母亲的教导儿子如何绅士地对待女孩。
晚饭后,我穿戴得整整齐齐去芭芭拉家约她。我很紧张。她还没准备好(女孩总是这样),于是她的家人让我在餐厅里等一会儿。当时他们正好和一群朋友在吃饭,大人们说着“看他多可爱”之类的话。我可一点不觉得可爱。太丢脸了!
我仍然记得那天的所有细节。我们从她家走到镇上新建的一个小电影院,路上聊起了弹钢琴。我告诉她,我小时候也被送去学钢琴,但一连六个月都只练习《雏菊之舞》这首曲子,让我很受不了。是的,我怕自己变成个娘娘腔,连着弹上几周的《雏菊之舞》已经让我受够了,于是我放弃了钢琴。我那时候太怕自己变成娘娘腔,连帮母亲去店里买薄荷饼、烤香饼之类的事情都不想沾边。
看完电影后,我送她回家。我称赞她的手套很漂亮。最后我在她家门口跟她说“晚安”。
芭芭拉说:“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愉快的晚上。”
“不客气。”我回答她。心里乐翻了天。
下一次我再出去约会,跟另外一个女孩,我说“晚安”,她也说“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愉快的晚上”。
我就没那么开心了。
当我跟第三个约会的女孩道晚安时,她刚张嘴,我抢先说出了“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愉快的晚上”。
她说:“谢谢你……嗯……哦……是的……我也很开心,谢谢你。”
有一次我跟那帮海滩朋友聚会,其中一个年龄大点的男孩在厨房给我们演示怎么接吻,对象是他的女朋友。他说:“嘴唇要像这样,角度要对,这样鼻子才不会撞上。”就是这一类的话。于是我去了客厅,找到一个女孩。我坐在沙发上,抱着她,练习起这项新艺术来,这时突然所有人都兴奋起来:“艾琳来了!艾琳来了!”我还不知道艾琳是谁。
然后有人说:“她在这儿!她在这儿!”所有人都停下手中的事情,跳起来去看这位女王。艾琳非常漂亮,我能理解大家为什么这么倾慕她,她的确很迷人,但我觉得没有疯狂到仅仅因为这位女王驾到,就让所有人停下正在做的事。
所以,在所有人都跑过去围观艾琳的时候,我还是和我的女孩坐在沙发上。
(后来我与艾琳更熟悉了之后,她告诉我,她记得在那次聚会上,所有人都很热情,除了一个在沙发一角跟女孩亲吻的家伙。但她不知道,两分钟之前,所有人都在做同一件事!)
我第一次跟艾琳说话是在一次舞会上。她太受欢迎了,所有人都想插进去跟她跳舞。我记得当时我也想跟她跳舞,正琢磨着什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