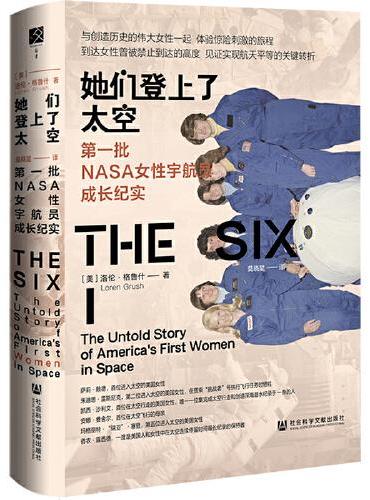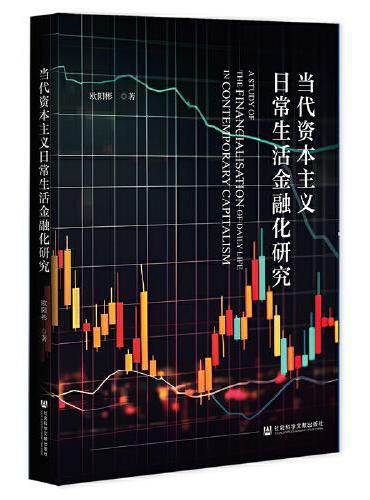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倾盖如故:人物研究视角下的近世东亚海域史
》
售價:NT$
357.0

《
史学视角下的跨文化研究(一): 追踪谱系、轨迹与多样性
》
售價:NT$
485.0

《
历史文本的文化间交织:中国上古历史及其欧洲书写(论衡系列)
》
售價:NT$
551.0

《
1688:第一次现代革命(革命不是新制度推翻旧制度,而是两条现代化道路的殊死斗争!屡获大奖,了解光荣革命可以只看这一本)
》
售價:NT$
1010.0

《
东方小熊日本幼儿园思维训练 听力专注力(4册)
》
售價:NT$
408.0

《
粤港澳大湾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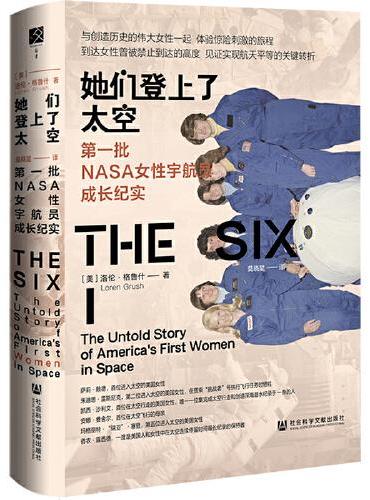
《
她们登上了太空:第一批NASA女性宇航员成长纪实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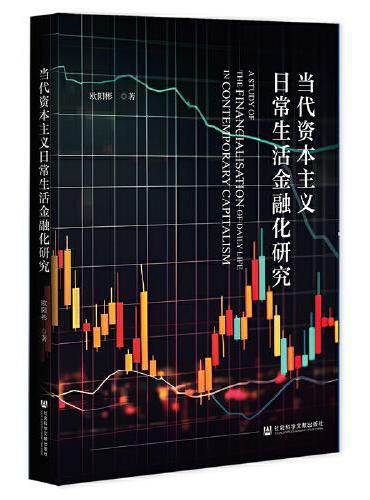
《
当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金融化研究
》
售價:NT$
653.0
|
| 編輯推薦: |
★磨铁中文网黄金联赛获奖作品,过千万点击、下载,数十万忠实读者保驾护航,连载伊始,每一章都有数万粉丝付费催更,深受90后年轻读者喜爱。
★这是一个关于古代名门世家的故事。以国子监为主体背景,全方位展现了古代书院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同时也包含了名门士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更融合政治权谋、政局更迭,描述一幅从轻松的现世到波澜壮阔的乱世画卷。
★这里有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也有有理想有才干的奋进青年;有养尊处优的娇小姐,当然也有端庄雅正的大家闺秀;有女汉子,当然也有腹黑毒舌的帅哥老师。他们从无忧无虑的课堂走进乱世,共同演绎了一曲历史长歌。
|
| 內容簡介: |
因为一个赌约,大司马家的独女桑祈成了国子监历史上第一个女弟子。最令她最头疼的不是学业,而是和各路同窗的恩怨情仇。今天惨遭逼迫联姻,明天又遇校园凌霸。
桑祈表示很无奈:你们真是来念书的吗?还能不能让人好好打个酱油了?
风流俊彦的青梅竹马,率直张扬的傲娇公子;气节清绝的没落贵族,高冷睿智的闷骚司业;又到底哪个才是她的真命天子呢?
最终桑祈被第一公子晏云之俘获芳心,二人的结合却为皇室所忌惮。几经坎坷后,时当政局动荡,战乱爆发,伤人最深的,不是敌人的长枪,而是身后的暗箭。家族罹难,桑祈为难之际,晏云之奇迹般带来一纸婚书,和请其为麾下先锋的诏令。夫妻二人最终携手御敌,缔造一段辉煌传奇。
|
| 關於作者: |
花千辞
新生代人气写手,磨铁签约作者。风格百变,脑洞丰富,尤擅复古小清新。文笔诙谐,画面感强,读来有极深的代入感。愿用笔下笑中带泪的故事致敬所有有爱的人。
|
| 目錄:
|
第一卷 国子监逸事 001
第一章 初入国子监 003
第二章 悄然风波起 032
第三章 郎君何所思 062
第四章 佳人何所惑 112
第五章 翩翩月下剑 156
第六章 脉脉花底情 189
第七章 感君有此意 215
第八章 愿言两心知 260
第九章 奈何秋霜覆 297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初入国子监
阴天,下雨,国子监里,一个用厚厚两层蓑衣把自己裹得像个鱼篓一般的身影伸出苍老的手来,颤颤悠悠地推开了门。一解衣带,两件蓑衣间夹层里的水哗哗啦啦洒了一地,更像是打翻了的鱼篓,可惜没有鱼。
老博士冯默须发花白,到底上了年纪,被冰冷的雨水泡得全身都冻僵了,又像古墓里刚爬出来的僵尸般颤颤悠悠往火炉边围着的人群走,哆嗦着嘴感慨了句:“天杀的,这么大的雨。”
火炉边的几个人早到一些,已经把外衣脱下来,陆陆续续烤干了。有人一边起身给他腾地方,一边皱着眉头看了一眼窗外巨大的雨做的帘幕,跟着骂了句:“都怪那桑祈。”
一旁有不明真相的小天真不懂了,怎么下雨还跟人有关,莫非是这叫桑祈的求的雨不成?这大冬天的……要是夏天干旱的那会儿也这么灵多好。
不远处的另一间屋子里,桑祈打了个喷嚏,皱着眉头甩了甩衣袖上的水。
这屋子里全是模样俊俏、锦衣华服的少年公子,如今清一色变成了落汤鸡,在各自的座位上狼狈不堪,不分青红皂白地甩着被打湿的书本。
有人咒骂了句:“天杀的,这么大的雨!”
另一个人转过头来盯着桑祈,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憋屈表情,仿佛在心里也道了句:“都怪那桑祈!”
桑祈感觉到了这视线,却看也没看他一眼,只是盯着被泡透了的书册发愁,用手一拎,就撕掉一块儿下来,心道,什么破纸。
冯博士也把书拿着凑近火炉烤干,忧国忧民地叹息:“你说圣上怎么就这么任着桑家胡闹?”
“唉。”旁边的人更用力地叹了口气,“还能怎么办?西昭是桑将军平的,南部乱党也是桑将军歼灭的,这天下都快成他桑家打下来的了,圣上现在也是无奈。”
“要我我也愁,可这规矩礼法……唉,乱套,全乱了套。桑家这么闹腾,就等着老天爷上门来收吧。你看这惊雷暴雨的……哎哟哎哟……”最后这句是因为冯博士一激动上前一步,被火燎了衣服,险些自己先行被收走。
桑祈又打了个喷嚏,缩着脖子,瑟瑟发抖,把湿透了贴在身上的衣服揪起来一点,试图暖和过来,却无济于事。因为她身边人更少,气氛更冷了。
周围的几个人心照不宣地默默离她远了些,阴阳怪气地咳了咳,绷着脸不去看她。
都不看我看吧,桑祈无奈地低头瞄自己。
好吧,虽然是和别人一样的宽袍缓带大袖襦衫,可是一水儿湿身诱惑的情况下,她那只有女子才有的凹凸身形还是欲盖弥彰地显露无遗。
她耸了耸肩,表示很无辜,作为国子监历史上第一个女学生,第一天就这样,实在也非她所愿。
却说三天前,大司马桑公毫不害臊地第七次提出要让自己家的独女进国子监读书,并称皇上要是不让就是歧视他桑家。他桑家为国捐躯、出生入死是多么不容易,前仆后继地死了那么多男人,如今只有个女娃娃了,居然连个和其他世家子弟平起平坐、共同识文断字的权利都没有,说着说着居然还觍着老脸为桑家后继无人哭天抹泪了一番,好像遭受了多大虐待似的,皇帝为此怄得差点撒手人寰。更有甚者居然还配合地跟着伤感,一时满殿擤鼻涕声。
识文断字在家里谁拦着你啊,非得去国子监演的是哪一出?皇帝有槽无处吐,直把龙椅的把手都捏出个坑来,才从牙缝里硬生生地挤出了三个字——着男装。
如今看来,这三个字也是白挤。
十月里,洛京其实还不算到冬天,教室里没备火炉。这雨来得突然,杂役们现烧了几个都给博士们送去了,还没送到教室,所以全屋人的取暖基本靠抖。
桑祈也在那儿和其他人一起忙着哆嗦。
教室里乱哄哄一片,谁也没注意有个迟到的人刚刚悠然进来,一路左拐右拐,一直晃悠到了桑祈身边,大大方方地坐下,解开斗篷,甩了甩头发上的水。
桑祈脸一黑,好嘛,又甩书上了,这下课算是彻底没法上了。
卓文远的视线顺着水滴抛洒的轨迹瞥了一眼桑祈案上的破书,又落在桑祈身上,唇角轻勾,从怀里掏出一个物件:“给你。”
居然是个小暖手炉!
桑祈也不客气,乐得接过来捧在怀里,感慨道:“卓夫人真是溺爱,这才什么时候就给你备下这玩意了,不是前儿风大,你冻着了吧?”
卓文远本就生得俊美,挑眉一笑,桃花眼角就漾出了几分风流暧昧。
“我特地回去为你取的,你倒挖苦我?哎哟,我胸口疼……”
“为我?”桑祈瞥了他一眼,做感激涕零状拍着他的肩膀道,“这么会疼女人,公子的未来一定前途无量。”
卓文远施施然把自己的笔墨纸砚一一摆好,顺着她的话接茬儿:“那嫁给我的事,你考虑得怎么样?”
桑祈抱着暖手炉心满意足地摇头晃脑,假装没听见。
“你看,嫁了我,我保证你天天有暖手炉抱。我还可以自我牺牲一下,给你当人肉火炉。你摸摸,热和不热和?”
她不回话,卓文远就自顾自地说了下去,还捉了她的手往自己额头上放。
桑祈眼疾手快地抽了回来,吸了吸鼻子,帮他总结刚才那番话的中心思想:“嗯,看来你比疼女人更擅长的是臭不要脸,更加有前途了。”
卓文远收回手,不置可否地笑笑。
俩人闲闲拌了几句嘴,桑祈也暖和过来了,开始把书页放到暖手炉旁边将其烘干。教室里的其他人也在三三两两地闲聊,不无公子哥儿坐得东倒西歪形象惫赖,也有人唾沫星子横飞地聊起哪个勾栏新花娘弹的曲儿多好听。
桑祈听到小曲儿的时候,拎着书页的手微微晃了晃。正在这时,屋子里突然安静了下来,她抬起头,发现众人竟不知何时都规规矩矩地盘腿坐好了,毕恭毕敬地低着头。
她正寻思这是怎么回事,能让这帮纨绔子弟如此矜持,莫不是皇上亲自来视察她第一天上课了?卓文远在她耳边低低提醒了句:“晏司业。”
桑祈被这三个字戳了一下心口,再把眼往上抬,只瞄见一袭雪白的衣角,而后便见宽袖轻扬、黑发如瀑、全身干爽的夫子进入了视线。
他身量颀长,高大威仪,看上去并不比房间里坐的学生们年长,却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符的沉稳气度,容貌远比她见过的最好看的男子昳丽,龙章凤姿,皎如玉树,最吸引人注意的,还要数那双眸子,眸光中有种说不出的高洁浩然,淡泊邈远。
桑祈挑了挑眉,想,这号称“第一公子”的晏云之,倒是生了副好皮囊。
可内里如何呢?
她只能用两个字形容——呵呵。
自视甚高、装模作样,是她对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大燕第一公子的两大印象。
想当初,她跟人家打赌,说定会在三月之内让晏云之收下自己的荷包,并答应她上元节赏灯之邀,否则她就要代替名伶在灯会上弹唱的时候,以为不过是小事一桩。
却未曾想到,打从她应下赌约,前去晏府拜访了晏云之几次,都吃了闭门羹。别说送荷包了,连人家面都没见上。
不就是被人称作姿容绝世吗?至于小气到连个脸都不露吗!多被看一眼能少块肉是怎么的!害得她不得已,只得出此下策,跑到国子监来堵他。一想到方才同窗们说的唱小曲儿一事,再想想自己那两把刷子,桑祈不由得狠狠将晏云之腹诽了一通。
为了不在上元节丢桑家的老脸,她容易吗?让他收个荷包,又不是让他投河上吊,举手之劳,何必如此孤高?
这边厢正吐着槽,那边厢晏云之已经坐了下来,翻开书册,清冷的目光淡淡地从众生面上扫过。
桑祈抬眸直视着他,目光挑衅,丹唇轻勾,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晏云之与她对视之时,神情却波澜不惊,就跟在看一方空荡荡的桌案没什么区别。
哟,居然这么镇定,桑祈心道。新来了一个这么另类的学生,国子监里的风言风语,她自然是有所耳闻,也做好了心理准备的,而今他这样从容处之,倒是令她有些意外。
仿佛教室里并未多出此人一般,晏云之如常开始讲习,开口的嗓音温润清澈,带着几分舒雅高远之意,仿佛山巅的皑皑白雪、静夜的熠熠月华,声如其人,美好动听。
可再好听的声音,也架不住说的内容无趣。他专司讲授百家经典,桑祈本就听得云里雾里,书又被泡烂了,根本看不清上面的字迹,更加摸不着头脑,没多大会儿,就因着手炉的暖意,生出了几许困倦,忍不住掩嘴打了个哈欠,同时眼皮沉沉地向周围看去。
只见除她以外,其余人都听得很认真,连一向慵懒散漫的卓文远也不例外,眸中凝着难得一见的专注,整个人都显得英朗了许多。
于是桑祈又意外了一下,暗暗揣测,这么无聊的课,他们还能一本正经地听下去,怕是这晏云之高傲得过了头,有什么动不动就打骂学生的癖好吧?
正想着,她又打了个哈欠,头部渐渐向面前的桌案倾去。
马上就能找个地方放头,好好眯一会儿了,她精神一缓,便忽地听到有人叫了一声自己的名字。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桑祈,你来解释一下此句为何意。”晏云之的声音不大,但清晰地传入她的耳朵里。
话音一落,教室里格外寂静,气氛十分微妙。
她条件反射地一个激灵坐直,微微蹙眉。他说了八个字,每个字她都再明白不过,可全部连在一起竟又不懂了。想去看看书上的原文揣摩一下,又悲哀地发现:似乎这一章恰好是刚才被她扯烂揉成一团丢掉了的那页。
全班同学都屏气凝神等待着她的回答,当然,其中大部分是等着看热闹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桑祈自然不想第一天就下不来台,用胳膊肘推了推卓文远,寻求解救。
而她误交损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方才还对她甜言蜜语的俊俏公子,此时长眉一挑,耸了耸肩,做了个爱莫能助的表情,眼神又恢复了慵懒玩味,中书五个大字——我也不知道。
好吧,桑祈无语,只得在他腰上狠狠拧了一把,淡定地清了清嗓子,硬着头皮道:“圣人若是不死光的话,盗窃案就不会停止发生,所以要想平息所有盗乱,须得把品德高洁之人全部杀掉才行……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她脱口说了这番话后,眉头紧锁,盯着书页,连自己都觉得解释得非常不着调,自然是大错特错了。
晏云之还没作反应,先有人忍不住轻笑了一声。
而后他依旧用那从容淡定、沉稳清冷的嗓音,附和了一句:“原来想治个盗乱,还需用这么惨绝人寰的方式……”整间教室便都哄堂大笑起来,只有他表情如常。
桑祈安静地坐着,面色微红,却不羞也不恼,听着听着,也笑了。
女子甘甜的笑声清脆悦耳,犹如清泉,混在男孩子们张扬粗犷的笑声中,显得格外突兀。桑祈坦然道了句:“我是不懂,我要是什么都懂,还要你这司业干什么!正因我才疏学浅,才更显得您睿智高明不是?”
他将了她一军,被她反将回去,还顺手小拍了一下马屁。
晏云之此时才抬起头来,目光在她身上多停留了几秒,又毫无波澜地再次移开,若无其事般,将方才这句话的正确解读道过后,继续讲了下去。
桑祈紧盯着他,在他俊雅高冷的面容上捕捉到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眼眸一亮。
她又不是来做什么才女,令人刮目相看的,只要不惹毛他,顺着他来,能把荷包送出去,完成赌约,也就大功告成了。
好不容易熬到下课,晏云之潇洒离去,桑祈赶忙把暖手炉丢给卓文远,跟了上去。
对方身高腿长的,步伐很快,不大会儿工夫便绕过重重雕廊,进了一间房里。
这里是他平时休息办公之处,待到桑祈追来时,他已放下手中的书卷,正在拿伞,听桑祈轻咳一声,转头看去,见她正半倚在门框上,手里拎着一个小荷包,笑眯眯道:“晏司业,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学生有一件礼物想孝敬您。”
晏云之视线淡淡地扫过她,道了句:“哦。”
桑祈一口气没接上来,哦……哦是什么意思?!
“那司业收是不收呢?”她扯着荷包晃了晃,目光落在他的伞上。那是一把极低调亦极奢华的伞,看似乌漆墨黑的不显眼,仔细观察便会发现,伞骨乃由千年乌木雕出,不加藻饰,浑然天成。伞面则是滴水不沾的上好油布,暗有光华,于不动声色中彰显出主人的品位。晏云之正提着它,一步步朝她走来。
然后,他视若无睹地与她擦身而过,走了出去,路过时疑惑地反问了一句:“为何要收?”
桑祈眨眨眼,怔在原地,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雨势渐小,晏云之白衫飘飘,修长如玉的手指撑着那把优雅又有风骨的伞,在雨中信步走远,声音友好温润地飘来:“桑二小姐,冯博士最讨厌弟子迟到。”
正在这时,传来阵阵通知上课的铃声。
桑祈来不及追上去,恨恨咬牙,火速跑了回去,却还是不可避免地迟到了。老博士本来就对她跑到国子监来窝着一肚子火,对她好一通吹胡子瞪眼,害得还算尊老爱幼的桑祈整个下午都在低眉顺眼地给他赔不是。
终于放学,才算松口气。
之前跟卓文远约好了,为庆祝第一天上学,他做东去庆丰楼吃饭。虽然雨恰逢时宜地停了,夕阳瑰丽,空气清爽,天边还悬着一道远虹,桑祈的兴致却提不大起来。
卓文远叫了几个合她口味的招牌菜,折扇一甩,慵懒地靠在雅间的窗棂边,眉眼含笑望着她:“怎么,有点受挫?”
桑祈白他一眼,埋怨了句:“见死不救。”
他给她倒了杯茶,连连赔罪道:“好了好了,你知道我也不爱琢磨那些玩意,是真不明白,不是有意看你笑话。”
因着他那似笑非笑的眸子,桑祈拿不准这句话几分真几分假,哼唧两声,喝完了茶,才愁苦地叹了口气,将自己追晏云之出去,结果完全被无视一事与他说了一番,托着下巴皱眉求教:“你从小长在洛京,应该和他相熟,快教教我应付之法。”
虽然穿了一身宽袍大袖的男装,她依然是个眉目生辉的俏丽佳人,用这样一副信任恳求、又带着几分倚仗的目光看着他,教卓文远很是受用,享受了好半天,才摊手道:“并无。”
“晏云之油盐不进,全洛京人都知道。想他刚刚加冠便拜了中书令,本是国之栋梁,前途无量,却仅仅就任半载,便自请辞去,跑到国子监来任教。其间皇上几次想召他入朝,都被他推拒了。连皇上都拿他没办法,我能有什么高招?”
这时菜陆续端了上来,他夹起一块桂花甜藕放在桑祈的盘中,解释道。
桑祈长叹一声:“唉,看来只好从长计议。”
“当初你就不该应下这个赌约。”卓文远喝了口酒,挑眉道,“那家伙出了名地洁身自好,从来不收礼,更何况是女子给的荷包。这摆明了是个坑,也就你能傻得往里跳。”
“我刚回洛京半年多,又不常出门,怎么会晓得其中的弯弯道道?”桑祈白了他一眼,“不说这个了,既来之,则安之,世上又没有后悔药。”
接下来这顿饭,两人真没再提晏云之的事,专心品评菜品。桑祈久闻庆丰楼大名,吃得还挺满意,走的时候手轻轻搭在微凸起来的胃部,懒洋洋地下楼。
不料今天的倒霉事儿还没完,刚一出店门,竟然碰到了宋佳音——她在洛京相处欠佳的娇小姐,当初挖坑让她跳的主使。
桑祈本想当没看到,穿了一身艳丽罗裙的姑娘却一声娇笑,故意扬声唤道:“哟,这不是阿祈吗,荷包送得怎么样了?”
哪壶不开提哪壶,桑祈瞥了她一眼,不愿搭理,扯着卓文远便走。
却听宋佳音银铃般的笑声阴魂不散,还自顾自地在她背后高声道:“还特地追到了国子监去?还真是卖力,可惜就算纠缠到上元节,他也是不会收的。到时候要表演的小曲儿,你近来可要好好练习呀。”
“别理她。”卓文远抬手拍了拍桑祈的头哄道。
“习惯了。”桑祈自然地耸耸肩。
她生在父亲的军营里,长在父亲征战的草原上,自在随性惯了,回到洛京,自然跟都城这些养尊处优的公子小姐们合不大来。所以像宋佳音这样的对头颇多,朋友却很少,亲近的只有卓文远一个。还是因为几年前,卓文远曾经随父出征,跟她一起在边关厮混过一段时间。
没有朋友事小,可丢人现眼真的事大……她扶了扶额,暗暗咒骂晏云之两句,在岔路口与卓文远告别,拖着疲惫的脚步回了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