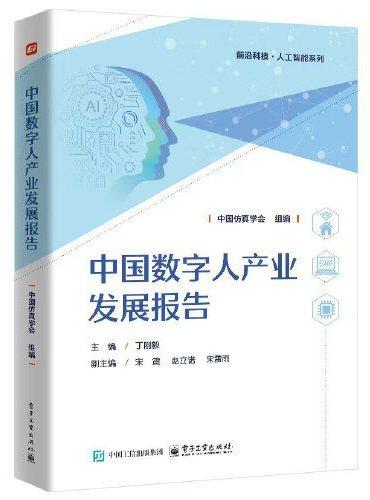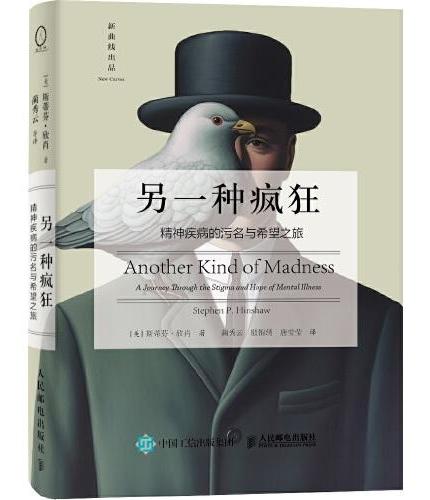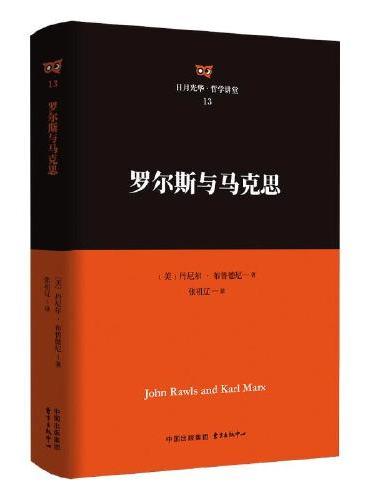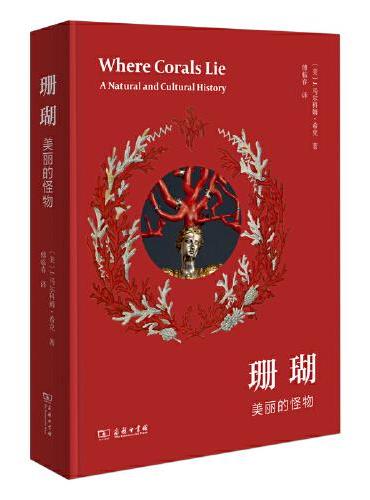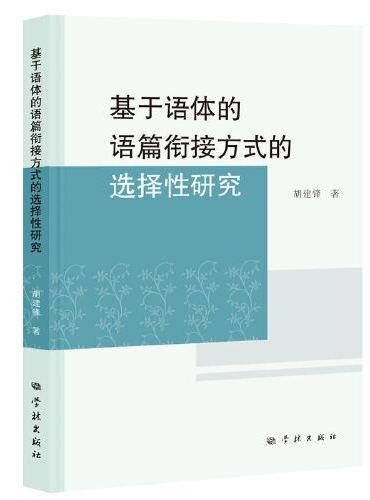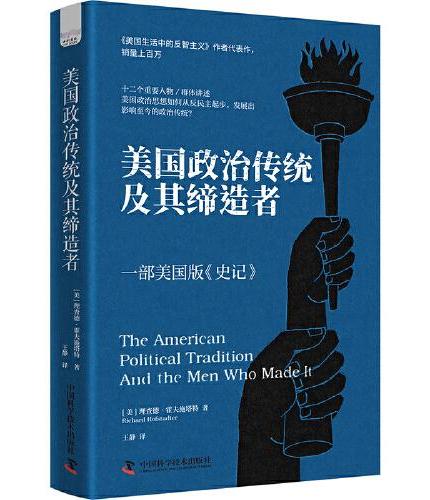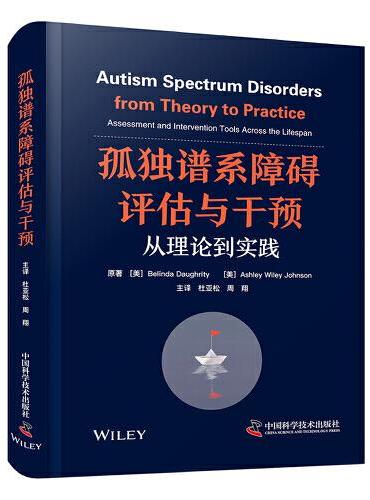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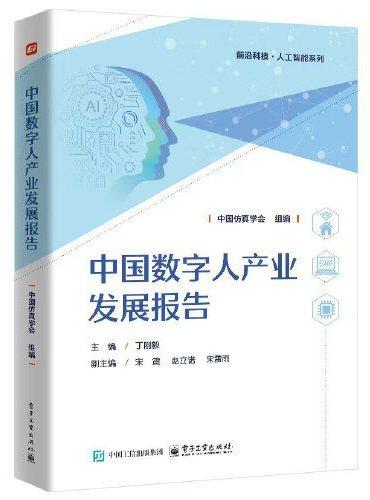
《
中国数字人产业发展报告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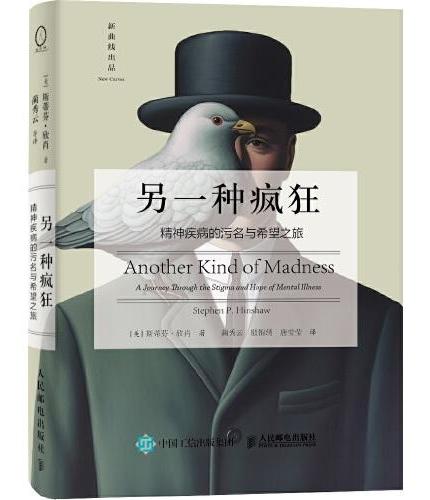
《
另一种疯狂:精神疾病的污名与希望之旅(APS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斯蒂芬·欣肖教授倾其一生撰写;2018年美国图书节最佳图书奖)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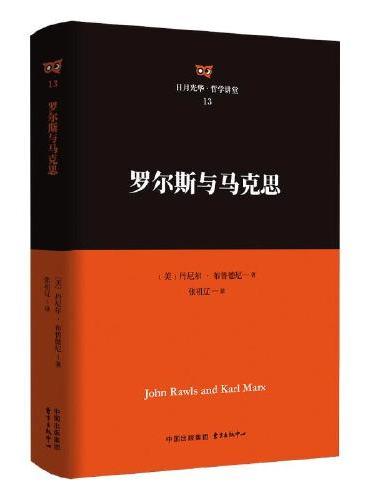
《
罗尔斯与马克思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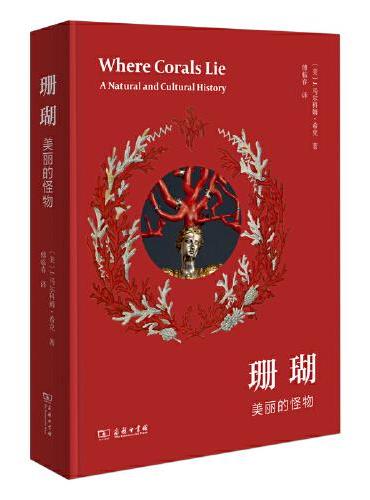
《
珊瑚:美丽的怪物
》
售價:NT$
58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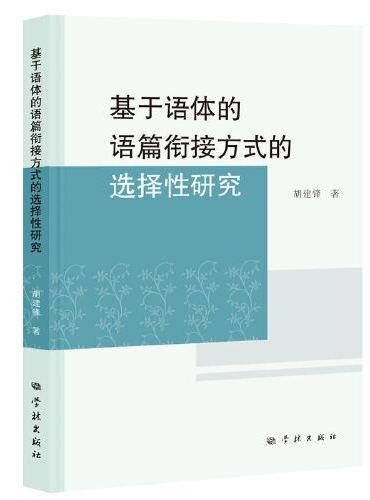
《
基于语体的语篇衔接方式的选择性研究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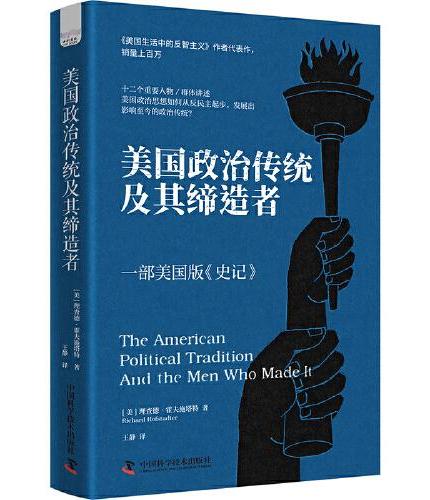
《
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一部美国版《史记》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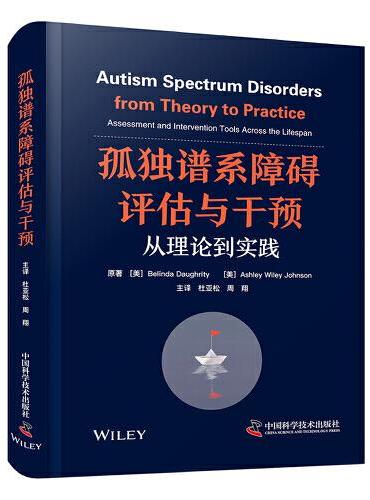
《
孤独谱系障碍评估与干预:从理论到实践 国际经典医学心理学译著
》
售價:NT$
1061.0

《
大数据导论(第2版)
》
售價:NT$
352.0
|
| 編輯推薦: |
|
端木露西具有较强的女性独立意识,其作品文字不脱隽永、自然、朴实的风格,也留下了战火离乱中人们的心绪和忧乐。本书中的有些篇目以前仅在报刊上登载过,现经搜集整理而编辑成册出版,具有极大的出版价值。
|
| 內容簡介: |
|
《蔚蓝中一点黯淡》这本书,辑录了民国才女端木露西的小说和随笔的部分代表作。《蔚蓝中一点黯淡》一篇重点论述女性如何成为真正独立的人,在民国时期曾引发一场关于妇女问题的论争。《前线之边》《送X去前线》《秋行》《秋的波浪》等主要刻画了战火离乱中人们的心绪和忧乐,写出了普通人的感情和爱憎。《两地雾》则写作者在伦敦的生活。书中蕴含着女性特有的细腻感情,字里行间充溢着一种善良和淳朴的美。
|
| 關於作者: |
|
端木露西(1912-1995),原名端木新民,苏州人,上海光华大学肄业。1935年4月任《中央日报o妇女周刊》编辑。1937年1月留英,在伦敦大学旁听修课。1939年4月3日,接替梁实秋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1940年以后,端木露西离开报界,先后任教于成都光华大学附中、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附中、重庆交通部扶轮中学、上海敬业中学。1951年起担任上海培进女中校长直至退休。
|
| 目錄:
|
《妇女周刊》发刊献辞(1 )
这三年(3 )
海外一国民(8 )
送X 去前线(15 )
《平明副刊》编者献辞(21 )
蔚蓝中一点黯淡(23 )
秋的波浪(32 )
秋行(39 )
幸福的婚姻(46 )
前线之边(78 )
中国家庭生活随笔(108 )
两地雾(124 )
|
| 內容試閱:
|
蔚蓝中一点黯淡
这一年来,我心中常常蕴藏着一个问题,总想将它写下来,以供社会上许多热心或关心妇女运动者研讨。虽然就整个问题言之,自抗战以来,有许多妇女在前方或后方都有可歌可颂可赞扬的表现,但这赘疣的一面自亦无法抹杀一切。*近,读到沈从文先生的《烛虚》,不禁又鼓起我自己那种潜伏着的意识,所以毅然将这个心愿了之。
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民族在思想上和形态上*足以说明这个运动所赐予民族生活上之直接影响者莫过于两性问题。当时在新文学运动中,许多作家也将两性解放的思想输送到读者的血液里去,从此大家对两性之间有一种新的认识,新的觉悟了。妇女解放运动由此得到的成就是男女同学和男女社交公开。于是许多人以为男女平等了,我们所需要的或所要求的,一切正和男子一样。
我在民国二十四年间,承乏一个妇女刊物,那个刊物的宗旨有两点:一,鼓吹一般妇女要从自身的觉悟中谋取心灵上的、智慧上的解放。我们既不欲单单做"女人",我们即需知道怎样做一般"人",和怎样去享受做一般"人"的乐趣。二,鼓励一般家庭妇女尽力作一个好母亲,好主妇,所以我们当时提出了一个新贤妻良母的口号,经常刊一些文章供给家庭妇女作为治家育儿的智识与方法。我们的刊物当时受到其他妇女刊物的非议,说我们太保守了,太落伍了,简直觉得我是罪孽深重的样子。我想,我今天这篇文章如能刊出来,我之挨骂仍是可以想象的。
当时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两个宗旨呢?简单地说,从五四到民国二十三年,妇女运动所得到的成就除了男女同学,机关里有了少数的女职员女官吏以外,我们实在看不出这一运动对于一般妇女的心灵的修养上给了什么解放的效果。妇女摆脱了旧礼教的枷锁,跑到社会上去,于是可以和男子同学,我们即看到了"皇后";可以和男子同事,我们即听到了"花瓶";而实际上不依赖丈夫而能单独地贵为"达官贵人"之流者能有几人!这一种情形,很显明的在说明了一种事实,即过去妇女运动太注意解放的形式,而疏忽了妇女跑进社会以后一种更重要更基本的做人的态度和知识。
在现代的社会制度组织之下,我们不能否认在二万万多的女同胞中,无论她的阶级如何,十分之九的妇女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在家庭里做主妇,做母亲的。在这种社会制度没有彻底改革以前,一个女子为了她自身的幸福,似乎也有权要求享受一个幸福的家庭吧,而这一种家庭*主要的是必须她自己先做一个好主妇,一个好母亲。而我当时看到许多年青者如女学生,年长者如已儿女成群的母亲,大家共同都有一种为人意识,以为妇女既解放了,管理家务琐事已是不屑为之,且不值得为之。家务与儿女皆可付之他人(如保姆、女仆等),自己既不工作,又不治家,其自然的趋势乃是玩玩吃吃,电影麻雀,消磨一生,嘴里还嚷嚷人生无聊。这一种心灵上的消沉堕落,懒惰苟且不能不使致力于妇运的人感到一种痛心。就妇女自身言,既无宁静的和平的家庭享受可言,同时昏聩终日,生命在浑噩中毫无目的,又无光彩的将它埋葬到坟墓里去,没有一点崇高的美丽的理想去管束她之一生,则当初的学校教育对她岂不是一种浪费?妇女解放乎?但是她连狭义的母性爱都糟蹋了啊。
事隔数年,今天我重复论及这一类型的妇女,因为我这一年来见到的事实并没有比从前进步多少。这一类型的妇女大都属于上中社会,并且更重要的是她们都受过与男子相同的教育,有的已是主妇,有的或服务社会,或正在向着这两条路上迈步着的女学生。而*可怕的是:正在充满着幻想、希望、憧憬着美丽的时期的女学生,不少是贪图现实,单顾"胃"与"眼"的放纵,没有光明的憧憬,没有完整的人生观,其程度之深,远在我们想象以上。我们可以很容易找一个女学生来和她作二十分钟的谈话(而这位女学生是属于中等家庭的子女,她可以给你的印象是衣服漂亮,打扮入时,也许带三分美丽,又有一张会说会笑的嘴。)我们立刻可以知道这个女孩子教养上之贫乏以及她的人生漫无目的到了如何可悲哀的程度。她所要求的是男朋友、吃馆子和看电影。她成为一种麻木和刺激的混合物了。绚烂的阳光被云雾遮障着,生命成了一种没有灵魂没有真义的空架子了。对于她为什么受教育,受了教育以后怎样,恐怕有很少时间来思虑这类问题。
有某女学生,在高中读书,她的日记上每天所写的是"今天XX请我**看电影……","XX来追我,真讨厌……","XX长得不错,我喜欢他……"一类日记文学!她告诉我重庆所有的大小馆子她都吃过,言下沾沾自喜。与她同学所谈的不外谁美,谁的衣服好看,男朋友,吃馆子,看电影;这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事物可以引起她们兴致与注意了。而且谈到两性问题时,其用辞之不修饰和胆大决非我们这辈人做姑娘时所能梦想到的。*令人痛苦的是这类奇异的思想渐渐的有在同阶级的青年女子中普遍开展的趋势。我曾和许多朋友谈及这一问题,其中有在教育界服务多年者,有的亲历管教的职务,大家都从内心感到一种悲哀。
我曾经私下做过一次试验:在五十个年龄皆在二十岁左右的中大女学生中竟有三十四个人选择配偶的条件是这样的:一,地位,二,金钱,对方的年龄虽在四十以外也无关紧要。假使有财有势的人不够分配,退而求三十余的男子。对于二十开外的男子都有一种瞧不起的神气,说二十多岁的男子不懂爱情。其实一句话,因为三十岁以内的男子大半生活清苦,正在刻苦奋斗重要的阶段,谁愿意跟他去吃苦。享受,享受,魔鬼的享受,是她生命的全部的意义。这些青年女子,一般被认为是"摩登女郎"。
这类青年女子,将来大半皆为主妇,而那时她们消磨生命的**办法也只有吃吃玩玩,电影麻雀。这一类型的人,在她们的无知之中,物质上自然是尊贵舒适,但是在民族的意义上言之,她们实在是一堆渣滓而已。
从文先生指出这是因为五四运动以来,提倡男女应受平等教育一原则下,教育当局者忽略了女子所特有的个性以及她们职业上的习惯所产生的因果(大意如此)。因此教育出来的女子,很容易成为一种庸俗平凡类型,这类型的特点是生命无性格,生活无目的,生存无理想。
作者以为对于女子教育没有一种中心的目标自应负下它的一部分的责任,但是*重要的还在于妇女解放运动没有能贯彻它的全部的使命。形式的结果,可以力争几位议员席,或者解放了青年女子的私人的纵欲。在心灵上说来,我看不出一个解放了以后的女子与"我们的母亲"之间有什么区别,前者并不多了解一点人生。旧的教育弃之如敝履,新的教育太笼统了,不足以使她了解将"教育"渗入于生活中去,以及了解"教育"是追求崇高的生命的工具。而妇女运动的片面的解释,反足以促进她认为"我既做不到女要人,我也不屑做主妇"的不合理的路上去。这类型的病菌在近年来加速度地在都市里弥漫着。事实上,能有多少人能成为女要人、女官吏……甚或至于女医生、女作家?目前的许许多多青年女子,在五年十年以后,我相信大部分人皆为主妇,皆为母亲,她非但是一个家庭的主妇,同时也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中的一个细胞,则她之不应懵懂一生,自不待言了。假使我们不希望在十年二十年以后,再看见那种以"玩牌"、"放纵胃、眼"为满足的堕落的妇女类型,我们对于妇女运动具有热忱的人是不是也应感觉到心灵的智慧的解放重于形式的解放呢?我们要解放,我们也要"做人",正如一个男子"做人"一样。
我们应有严肃的人生态度,勇于负责的服务精神,将教育与生命永远联系在一起,从智慧中获取更美丽更勇敢的人生观,明了追求人生,创造人生和享受人生,而不作"生"之魔鬼的奴隶。扩大我们的母性爱,对人类崇高的真理满怀着热忱,对自然之华丽我们懂得去欣赏,以丰富我们灵的生活。在小我的家庭中,安于治理一个家庭,而作一个"人",不作一个"寄生虫",将所受的教育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一旦献身于大我的国家,则必须不屈不挠,勇往直前,表现我们新中国新精神。形式的解放与智慧的解放相辅相成,两轨并进,那么,对于抗战建国所能发挥的力量将更在历史上划下一笔不可磨灭的功绩了。
原载一九四〇年七月六日《大公报》(重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