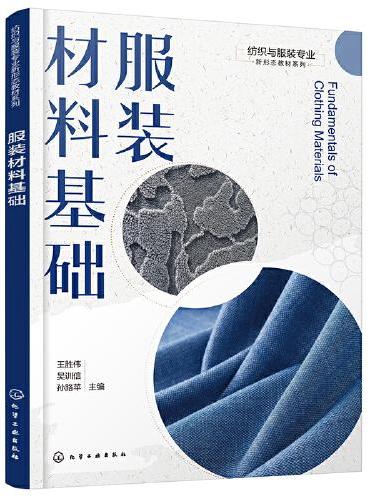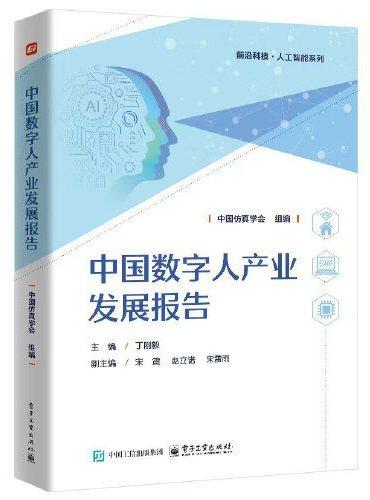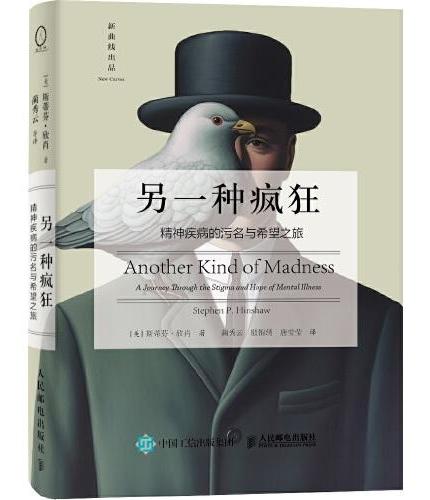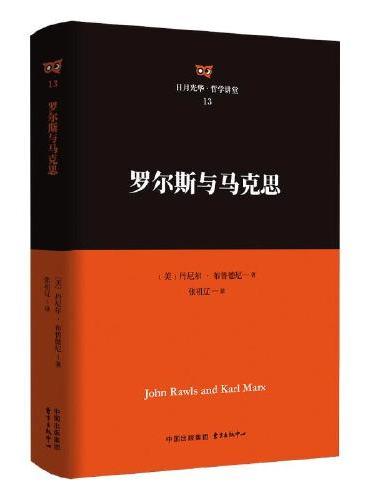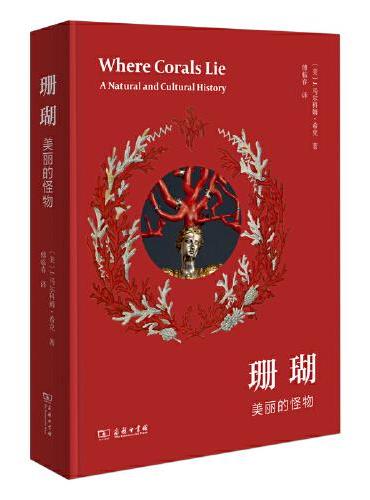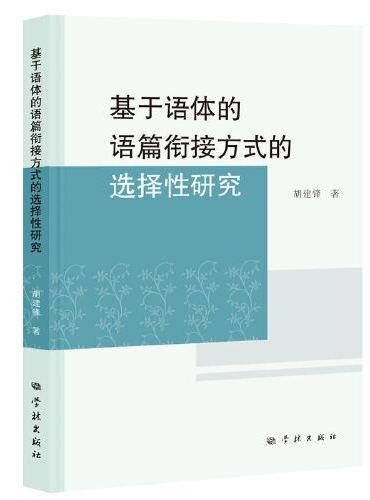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家庭财富管理指南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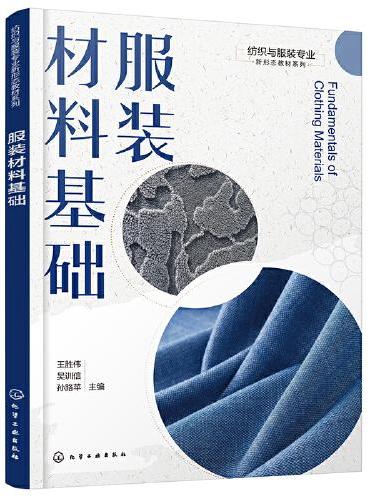
《
服装材料基础
》
售價:NT$
296.0

《
国家名片C919(跟踪十余年,采访百余人,全景式呈现中国大飞机C919,让读者领略到中国航空科技的最新成就)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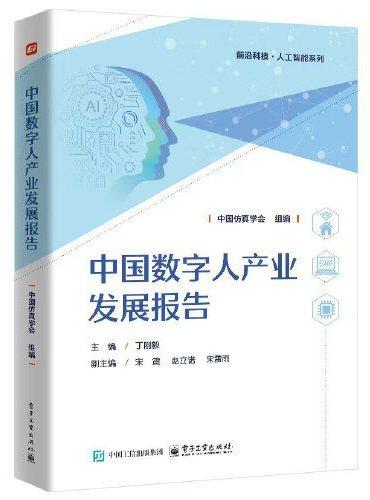
《
中国数字人产业发展报告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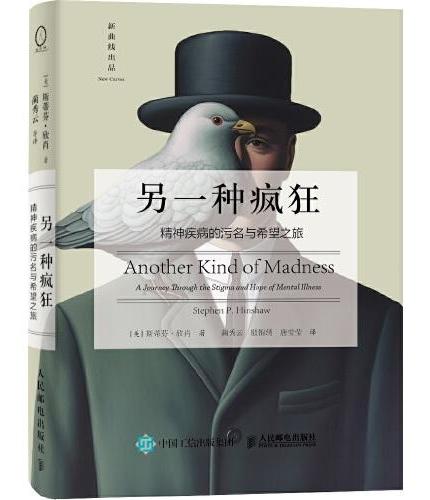
《
另一种疯狂:精神疾病的污名与希望之旅(APS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斯蒂芬·欣肖教授倾其一生撰写;2018年美国图书节最佳图书奖)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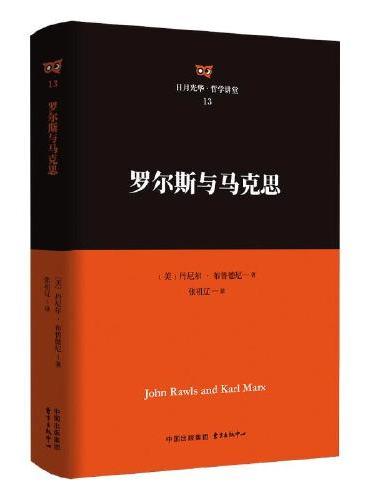
《
罗尔斯与马克思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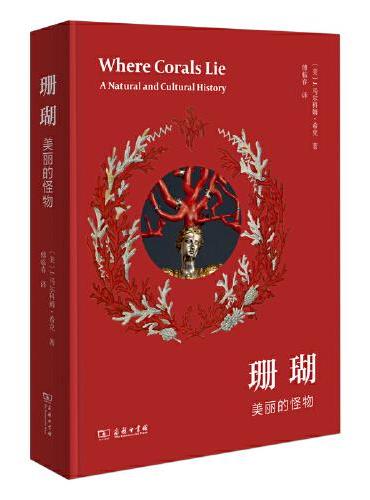
《
珊瑚:美丽的怪物
》
售價:NT$
58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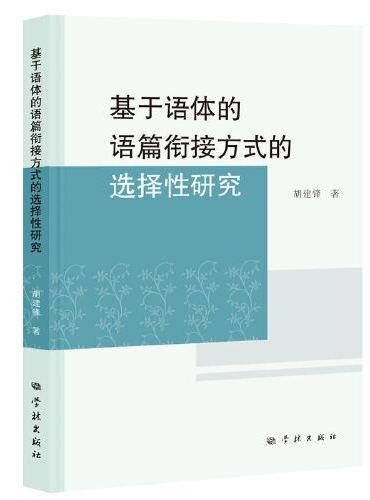
《
基于语体的语篇衔接方式的选择性研究
》
售價:NT$
347.0
|
| 編輯推薦: |
斯特林堡是瑞典国宝级作家,他的《红房子》等小说深受中国读者喜爱。《海姆素岛居民》是斯特林堡本人认为最好的作品之一。出版至今已被译成25种文字,故事的本身、精美的语言、绝妙的譬喻都激励着译者前赴后继接受一个巨大的挑战。此次首个中文译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郑重推出,旅居瑞典多年的译者王晔精心翻译,瑞典学院院士、翻译家马悦然教授亲自审阅译稿,并由著名作家阎连科作序推荐。斯特林堡在《海姆素岛居民》中展示的是活生生的一切。鲜活的风景,鲜活的心脏的跳动,血液的流淌、沸腾和凝固,可让人感同身受的喜悦、愤怒、尴尬、绝望。它是小说,却比生活还真实。它从生活中提炼的那份真实,有一种让人面对着生活和生命中让人害怕又热爱的,所有肮脏又纯净、荒诞又合理、残酷也柔软的事实的力量。在这样一种远离了做作,远离了小盆景的真山真水面前,我们只能和小说主人公卡尔松一样屈膝于它的壮丽。
在斯特林堡笔下,大海就是生活,那里有所有的故事和情感;那里有风平浪静也有狂风暴雪,那里滋生着一切,也可以埋葬和收容一切。生活继续,也许是永远哪怕是经由不同的人的传递。
|
| 內容簡介: |
|
小说的主角是个有健康神经和良好血液的雇工,来自韦姆兰省,40岁上下的卡尔松。他到比他年长的寡妇福洛德太太拥有的海姆素岛打点农庄。主人的独子古斯藤只爱打猎和捕鱼。卡尔松懂农活,有生意头脑,他在休耕的地里种苜蓿,将空着的房子租给夏天的度假客,等等,成功进行了改革,改善了农庄经济。福洛德太太出于农庄经营的需要,更出于性的欲望,用农庄主的身份诱惑卡尔松,卡尔松在一段与城市姑娘的无望恋爱后积极响应了福洛德太太,两人成婚。婚后的卡尔松怠惰起来,妻子小产,他逼她立遗嘱,让自己承继农庄。妻子在冬夜跟踪私通的卡尔松和女佣,冻出了病。垂危时,她让儿子烧毁遗嘱。在将卡尔松太太的棺材运往教堂的长途跋涉中,棺材掉进海里的冰窟窿。突起的东风让冰冻的海面崩裂成大海。在海水的追赶下,卡尔松淹没;幸存的古斯藤成为海姆素岛新主人。
|
| 關於作者: |
|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剧作家、小说家、诗人。生于斯德哥尔摩。早年丧母,内心敏感。曾入乌普萨拉大学,后辍学,当过报社记者、图书馆管理员等。1879年以小说《红房子》成名。斯特林堡虽成名很早,且在瑞典文坛独领风骚40年,但长期生活窘迫。社会问题上的激进态度使他被放逐,妇女问题上的保守、三度婚姻的波折让他频受打压,一度陷入精神错乱。著作丰富,代表作有《朱丽小姐》《结婚》《疯人辩词》《海姆素岛居民》等。 王晔:作家、翻译家,瑞典作协会员。《万象》《书屋》《文汇报笔会》作者。著有散文与短篇小说集《看得见的湖声》《十七岁的猫》,散文集《欧洲人文地理》,文学评论集《这不可能的艺术瑞典现代作家群像》,译有《格拉斯医生》、《巴托克:独自对抗第三帝国》《海姆素岛居民》等。
|
| 目錄:
|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9
第三章
039
第四章
073
第五章
105
第六章
149
第七章
171
译后记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卡尔松去做雇工,被看成一只轻佻的、松鸡那样在求偶期表演的鸟。
他像旋风一般,在一个四月的晚间来了,脖子上用皮带挂了一只赫格奈斯陶罐赫格奈斯hgans是瑞典南部一个以产陶瓷出名的城市。。克拉拉和洛藤摇了鲱鱼船去达拉岛码头接他。然而,等他们再回到船上,真像是被耽搁了永久。他们得上零售商那儿弄上一桶焦油,进药房去拿给猪杀害虫用的汞软膏,再跑邮局买张邮票,去大拐弯处的费娅勒弗斯特罗姆那儿,用半磅旧重量单位,半磅约两百克。左右的编网细线跟她借一只公鸡,最后,他们到了客栈,在那儿,卡尔松请姑娘们喝了咖啡,还外带小点心。这么着,他们终于回到船上。卡尔松要掌舵,他其实不会,先前压根没见过横帆船,可他喊道,得升高前桅的大帆那其实根本就不存在。
海关码头上站着领航员和搬运工,他们对着小船上的指挥咧嘴大笑;这时,船帆让风吹偏了方向,朝向了萨尔特塞肯。
喂,你船上有洞有洞是有双关语意的玩笑话,为岛民常用,指船上有女人。,一名见习领航员的喊声透过风传来,堵住!堵住!卡尔松忙着找船上的洞时,克拉拉挤开他,抓过舵去;洛藤操起桨,把小船又弄成了侧迎风,现在能以蛮不错的速度朝着阿斯普海峡开了。
卡尔松是个小个头、四方脸的韦姆兰人,蓝眼睛,鼻子弯得活脱就是姊妹钩。他精力充沛、顽皮、好奇,可海上的事他一点不懂,他是被唤到海姆素岛该岛是故事的发生地,岛名的瑞典文有家的意思。照管田地和牲畜的自打福洛德老头走了,寡妇孤单单呆在农庄,可就没别的人愿意管这些了。
不过这会儿,卡尔松打算着手从姑娘们那儿挤点岛上生活的情形和人际关系出来,他得到了典型的岛民式答复:
哎呀,我可不知道!哎呀,这我可没法说!哎呀,我压根就不知道。
结果从她们那儿,卡尔松什么也没打探到!
小船在多岩石、少植被的小岛和不毛的石头小岛间飞溅着水花向前,长尾鸭在岩石后嘎嘎叫唤,黑色的雄松鸡在云杉林里低鸣,小船穿过海湾和激流,直到暮色沉降,星星一个个列队跑出来。这会儿,小船进入一片宽阔水域,那里赫乌德斯雪尔的灯塔眨了眨眼。有时,他们漂过一只扫把航标旧式的红色杆形浮标,上端扎有常用来做扫把的秸秆。,有时漂过一只看起来跟鬼一样的白航标。忽而是残留的飘雪,像是在漂白的亚麻布;忽而是漂浮的渔网浮标跳出黑色水面,船从那上头驶过时,浮标刮擦了龙骨;忽而一只假寐的鸥受惊地从它的孤岩上立起,燕鸥和海鸥们吹打出一片噪音,活像拉警报,比魔鬼还糟。而最远处,星星走进大海的地方,能看见一艘大蒸汽船的一只红眼睛、一只绿眼睛,蒸汽船拖了一长排圆形的、从沙龙的舷窗透射出来的光亮。
对卡尔松来说,一切都是新的,他打听着每一件事。这会儿,他得到了答案,那么多,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撞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地。
他是陆上的。这话基本就跟城里人在乡下人面前想说的一样。
小船拍打着水花进入一片海峡,到了避风处,于是他们得落下帆,划起桨。很快,进入另一片海峡,他们能看见在深处,在桤木和松树间,一座农舍里发出的亮光。
现在我们到家啦。克拉拉说,小船驶入一条狭窄的港湾,有一条水道在芦苇间被劈开,芦苇抵着船舷上缘,发出沙沙声,吵醒一只产卵的、被饵钩诱惑了的梭子鱼。
农庄的杂种狗吠叫,看得见一盏提灯在农舍那儿移动。
小船在这当口固定在了木桥码头的尾端,卸货开始了。船帆卷在桁端,桅杆放下了,拉索拿木滑钩卷了起来。焦油桶被推上了岸,桶、罐、篮子和包袱转眼间都立在了木桥码头上。
在半明半暗中,卡尔松打量四周,只瞧见新奇和不熟悉的东西。木桥码头外有绞车,上头荡着鱼篓,沿木桥长边的一侧有扶手,上头挂满浮标、系船绳、钩锚、砝码、线、延绳、钩子,而鲱鱼桶、水槽、鱼虾篮、大桶、大缸和延绳盒子堆在支架板上。桥头有个船屋,里面挂满了做猎鸟诱饵用的,塞得鼓鼓的欧绒鸭、红胸秋沙鸭、斑脸海番鸭、鹊鸭;而在檐下的架子上,有帆、桅杆、橹、船钩、桨架、水舀子、碎冰锥、淡水鳕棒。岸上立着树桩子,挂着的鲱鱼网那么大,跟最大的教堂窗户似的。比目鱼网的网眼简直伸得进手臂,新结的鲈鱼网白得仿佛是最好的雪橇网放在雪橇前方的网状布,用来挡住马蹄腾起的雪块。,从木桥码头往上,延伸着一条路,像是绅士宅第的通道,道旁是两行叉状柱子,柱子上挂着拖拉大围网。路的最上方,提灯晃了过来,把光柱打在沙石道上,道上有贝壳和干鱼鳃的闪光,而拖拉大围网里残留的鲱鱼鳞闪烁,就像是白霜落在蜘蛛网上。灯也照射着一张看来被风吹得干巴巴的老女人的脸,一双小小的、和善的眼睛,因为常年盯着炉火而缩皱着。杂种狗跑在她前头,那是个毛茸茸的家伙,它在海边看来和在陆地上一样自在。
喂,亲爱的,是你们到家了吗?老女人招呼着,把小伙子也带来了?
是呀,我们回来啦,卡尔松也在,大婶你瞧!克拉拉说。
老女人在围裙上擦干右手,把它伸向雇工。
欢迎啊,卡尔松,但愿你喜欢我们这儿。姑娘们,你们买了咖啡和糖没有,帆都收进船屋了?上来吧,得吃点什么了。
一群人走上斜坡,卡尔松没吭声,心里直好奇,等着看他的生活在这新地方怎么个立脚。
大房间壁炉里的火燃着,白色活腿桌一种通过改变可移动的桌腿的位置来改变大小的桌子。上铺着干净桌布,上头立着烧酒瓶,瓶子中间收腰,像只沙漏,酒瓶周围是几个带玫瑰和勿忘我花图案的古斯塔夫贝里牌瓷杯子;一只新烤的小圆面包、几块脆面包片、一盘黄油、糖罐和奶油壶完成了餐桌的摆设,这让卡尔松觉得阔气,他可没指望这海角天边会有这些。而大房间本身看来也很是不错,他在燃烧的炉光中评估这房间,摇曳的火光和铜台上的烛光给桃花心木的雪纺橱因起初摆放雪纺绸料得名。橱有前板,可合起可放下,放下可作写字台。打上了某种朦胧的光泽,反射在打蜡的盒子和挂钟的黄铜钟摆上,闪烁在镶嵌了银色波纹的鸟枪桶上,让《训诫书》、《赞美诗》、《日历》和《农人实务手册》的烫金书脊跳了出来。
来吧,卡尔松。老女人邀请道。作为新时代的孩子,卡尔松没跑着躲进仓房,而是立刻走过去,坐在沙发长椅上,在这当口,姑娘们把他的箱子放在了走道另一头的厨房里。
老女人取下咖啡壶,放进鱼皮干鱼皮干早先用于煮咖啡豆,鱼皮中分离出的蛋白质和将咖啡弄得浑浊的成分一起沉淀于壶底。,把咖啡壶重新挂在火上,让它多煮上一会,同时,再次邀请着,这回加了一句,卡尔松该坐到桌边。
雇工坐了下来,卷了卷帽子,察看着风向,琢磨该怎么起航;因为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他决定要和雇主处好了,可他还没弄清楚,老女人是不是那种能容忍别人说话的人,在他弄明白地形之前,他不敢径直打开话匣子。
那可是张呱呱叫的雪纺橱!他试探着指了指橱上的黄铜玫瑰。
嗯!老女人说,可那里头没几个钱。
哦,肯定有。卡尔松巴结道,一面把小拇指伸进拉盖的钥匙孔里,我敢打赌,这里头有不少钱!
当初从拍卖会上弄回来时可能还有几个钱,可福洛德死了,古斯藤服了兵役,农庄就没什么动作。还有,他们盖了新房子,对活着的人和牲畜可没一点用处,就这么越来越糟啦。放糖,卡尔松,喝杯咖啡。
我先开始吗,我?雇工讨好地问。
是呀,也没别人在家。老女人回答说,那上帝保佑着的孩子扛着枪到海上去了,把诺尔曼也拖着,所以,就没啥是拾掇了的。不过是他们出去打鸟,牲畜和鱼都没管好,卡尔松,你看,所以才找你来,好把一切理顺了,因此,你要比他们高出一头,看住小伙子们。卡尔松要不要来片面包干?
是吗,大婶,要说叫我比其他人高出那么一点儿,好叫他们听我的,那就得有个规矩,我就需要个撑腰的,因为我知道要是跟小伙子们平起平坐、客客气气的,会是个什么样。卡尔松快速推进,觉得抓到了要点,海上的活我不懂,我不干涉,可地里的,那个我在行,我要能说了算。
哎呀,这我们等明天再安排,明天是礼拜天,可以在白天里慢慢合计。现在,卡尔松你再喝上一杯,然后好上床去。
老女人给他倒上第二杯咖啡,卡尔松拿过沙漏状的酒瓶,斟上酒,约占杯子的四分之一,然后呷了一口,他想继续刚才被打断了的、特别合自己心意的谈话。可老女人起身去拨炉火,姑娘们快速地跑进跑出。狗在农庄里叫唤,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啊,是小伙子们回来了。老女人说。
听得见外头的说话声,靴底的钉子踩在石头上的咔嚓声,在窗台上的盆栽凤仙花之间,卡尔松看见外头月光下两个肩头扛枪、背上驮了包裹的男子的轮廓。
狗在门口叫唤起来,大房间的门立刻给推开了。穿着橡胶高帮套鞋和又长又厚的渔民夹克的儿子带着猎人自信的骄傲,大步跨进来,随手将打猎包和一堆欧绒鸭扔在门口的桌上。
晚上好,妈妈。给你的肉!他招呼着,根本没注意到新来的人。
晚上好,古斯藤。你们出去好长时间了。老女人回答着,一面对那些漂亮的有着炭黑和纯白的羽毛、玫瑰红胸脯和海绿色脖子的欧绒鸭投去不由自主的喜悦一瞥,看得出你们收获不赖啊!哦,你瞧,卡尔松来啦,我们等的人。
老女人的儿子用他那双让浅红眼帘半遮着的锐利小眼睛对卡尔松探寻地勾了一下,表情立即从开放变成警戒。晚上好,卡尔松。他短促而有保留地说。
晚上好。雇工掂量好了这儿子,用一种随意的、准备好要占上风的调子搭了腔。
古斯藤在桌头坐下,胳膊支在窗台上,让妈妈给他倒了杯咖啡,自己立即在其中掺上烧酒。他一边喝,一边偷偷瞄着卡尔松,卡尔松拿起鸟来察看。
好货色,这些个!卡尔松说,他捏了捏鸟的胸脯,瞧它们多肥,你可是个好猎手,我看得出,枪法好,都打在了要害上。
古斯藤回复了一个狡黠的笑。他立刻明白雇工根本不懂打猎,因为雇工在夸枪法,那打在顺着的羽毛上的,其实是把鸟弄得不值钱,只能做诱饵了。
可卡尔松无所畏惧、喋喋不休,他夸了海豹皮包,赞了枪,表现出他完全是个对海上的事一窍不通的蠢蛋。
你把诺尔曼怎么着了?老女人这会儿问,她开始有些瞌睡。
他在把东西搬到船屋里,古斯藤回答,不过,马上就来了。
隆德克维斯特已经睡下了,唔,也确实是时辰了,卡尔松一定累了,在外头颠了一天。卡尔松,要是你跟我来,我这就领你去看睡觉的地方。
卡尔松想留下来,看沙漏瓶里的液体流出,但暗示已太明显,他不敢造次。老女人随卡尔松进了厨房,但很快就回转到恢复到坦然状态的儿子跟前。
哎,你觉得这人怎么样?老女人问,我看他蛮可靠,挺想干,也机灵。
哦才不是!古斯藤拖着嗓子道,别信他,妈妈,他说的全是狗屁,那家伙!
哎哟,瞧你说的。哪怕他话多,照样也能做事地道。
相信我,妈妈,这是只轻佻的求偶鸟求偶鸟,如松鸡一样在求偶期会舞蹈的鸟,指轻佻,不负责任的人。,我们从他那儿脱身之前,会被他拖苦。不过,不要紧。他干他的活,吃他的饭,不许离我太近,不许。是啊,你从不信我说的。可你瞧着好了,瞧着好了!你后悔时就太晚了!老隆德克维斯特不就是那样的嘛!他也是软舌头,可他的脊梁更软,我们只好对付着,现在看来是要拖到他老死了。这种爱夸夸其谈的人唯一靠得住的是他们的好食欲。相信我!
好了,古斯藤。你和你爹一个样,从不把人往好处想,还总要求些不可能的。隆德克维斯特也不是什么渔民,也是从陆上来的,可他能做好多其他人做不了的事。我们这儿可再也雇不到渔民了,他们都去了海军或海关,还有领航站,现在也就只有陆上的人来这儿。是呀,你明白吗,人得接受能得到的。
嗨,这我明白。谁也不想在农庄里多干,都想替国王服务。这儿集合的全是陆上来的垃圾。别以为没啥原因,会有什么正经人到海岛来,所以我重复先前说过的话:睁大眼睛!
哎呀,你呀,你是该睁大眼睛,老女人回道,好好看着你的东西,反正这一切到头来都是你的。你得在家多待着,别老到海上去,至少别老像你总做的那样,还拉上其他干活的人。
古斯藤指着一只欧绒鸭说:啊唷,妈妈,假如一冬天烧的都是咸肉和干鱼,你总也希望桌上来点烤肉吧,所以你可别唠叨。何况我又没上酒馆,我总得有点乐子。吃的我们不是有嘛,这就够了,银行里还有点钱存着,农庄烂不了,它要是烧了,随它烧去好了,反正上了火灾险。
是,农庄烂不了,这我也晓得,可其他所有的那些都破了。篱笆得修了,沟得挖,仓房顶通了,雨都漏到了牲畜身上,没一个码头是结实的,船干得跟火种一样,网得浸泡,牛奶棚需要新顶。唉呀呀,天知道有那么多必须做、还根本没做的事。现在我们倒要看看,会不会给收拾好了。因为我们请了人来安顿这些,就看卡尔松是不是这么个人了。
好,你让他收拾就是了。古斯藤回嘴,指头插到短短的头发里,头发都竖了起来,诺尔曼来了!来喝一杯,诺尔曼!
诺尔曼这会儿进了大房间,他有着粗短身材,浅色金发,开始发灰的金胡子,蓝眼睛,他跟老女人打了个招呼,然后坐在他的狩猎同伴身边。两个英雄都掏出陶土烟斗,装上黑锚牌烟叶后,开始像猎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喝上一杯掺烧酒的咖啡,仔细检查每一枪、每一弹,所有他们在海上的战绩。手指伸在弹口里把鸟儿们查验了,小球儿都数了,不确定的几枪全讨论过,出行的新计划也拟定了。
这当口,卡尔松在厨房里打量着他的夜间庇护所。
这是个小木屋,看上去像是只带着朝天龙骨的纵帆船,装了全世界所有的货物在漂浮。最上端,在烟灰色屋脊下,梁上挂着网和钓鱼的齿轮;其下是待风干的木板和支架,还有一束束亚麻和大麻线、挠钩、熟铁、一串串大蒜、牛油蜡烛、木头饭盒;在一根大梁上挂了一长串新填好的诱饵鸟,另一根梁上担着羊皮,第三根梁上荡着钓鱼用防水长靴、毛线衫、亚麻内衣、衬衫和袜子;横梁间架着串了脆面包的木杆,挂鳗鱼皮的棍子以及有着曳钓绳和底延绳吊锤的树枝。
山墙窗边有一张未油漆的木桌,靠墙是三张拉开的沙发床,铺好了还算干净的粗布床单。
老女人指给卡尔松看其中一个是他的位置之后,就带着蜡烛消失了,把新来者抛在昏暗里。只有壁炉里一点微弱的余烬和让窗框分裂了的月影短短地打在地板上。出于谨慎和安全的考虑,上床时间不点蜡烛,因为姑娘们的床也在厨房里。卡尔松开始在暗色里脱衣服。他脱掉外套和靴子,把表从背心口袋里掏出来,就着壁炉余烬的光上发条,表只在周日和一些重要日子才使用,他刚把钥匙插在发条眼里,用多少有些不大习惯的手转动,听见床上的一堆衣服里冒出个低沉、刺耳的嗓音:
哎哟喂,他还有只表呢!
卡尔松跳了起来,借着微光,低头看去,两只窥视的眼睛和一颗乱糟糟的头被两条毛乎乎的手臂支撑着。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卡尔松说,想表现出自己可不是没话好回。
教堂的钟会敲两遍,告诉人啥时候该去可是我从来不去。那颗头说。
可是,可是,可你要是坐直了,我就给你浇盆水。
这主意不坏。对方回嘴,不过你倒是个时髦家伙,靴脖子上还有摩洛哥皮呢。
是啊,再告诉你一声,我还有橡胶套鞋呢。
老天啊,还有橡胶套鞋!那你一定也能请我喝酒了!
没错,这我办得到,假如你想要的是那玩意。卡尔松干脆地说,然后去拿陶罐,给,自己喝吧。
隆德克维斯特拔下塞子,呷了一口,然后把罐子递还过去。
上帝保佑你,我敢说这是烧酒。干杯,欢迎来岛上!打现在起,我就称呼你卡尓松了,你可以叫我滑稽的隆德克维斯特,我往往是叫这个。
说着,他又缩回被窝筒里去了。
卡尔松脱了衣服,把表挂在盐罐上,把靴子搁在地板当中月光让红色摩洛哥皮饰看得见,然后他滑进了床。除了隆德克维斯特在壁炉那头的鼾声,屋里一片寂静。卡尔松醒着,想着将来。福洛德太太关于他要高出一头,把农庄转动起来的话像颗钉子钉在他脑子里,这钉子周围疼痛、发胀,像是脑子里长出了什么肿瘤。他躺着想那桃花心木的雪纺橱和那儿子红色的头发、怀疑的眼睛。他看见自己走着,裤子口袋上铁丝拴着的大串钥匙哗啦作响。然后,有人到他面前要钱,他撩开皮围裙,摇着右腿,手伸到口袋里,感觉钥匙抵着大腿,他找着钥匙,像挑麻絮那样,等他抓到最小的那把,开雪纺橱的,他把它插在钥匙孔里,就像今晚他用小拇指做的那样,可这钥匙孔,像是有着眼珠的眼睛,变得圆圆的、大大的、黑黑的,仿佛枪口,而在枪杆另一头,他看见那儿子锐利又狡猾的红眼睛在瞄准,好像在捍卫自己的金子。
有人进了厨房,卡尔松猛地从瞌睡中惊醒过来。地板中央,格子状条纹的月光所在的地方,两个穿白色衣服的人形站着,又迅速沉到一张床上,床嘎吱作响了好长一阵,像是船只正对抗着摇晃的码头。接着是床单的蠕动声和吃吃的笑声,直到归于沉寂。
晚安,小姑娘们,听得见隆德克维斯特快要熄灭了的声音,请梦见我。
行,我们会留意。洛藤回答。
嘘!别跟那糟老头说话。克拉拉警告说。
你们是那么好,那么好!但愿我也能那么好,和你们一样!隆德克维斯特叹口气,哦,上帝,人会变老,再也得不到想要的,生活里就只有垃圾。晚安,孩子们,你们得留神卡尔松他有只表,还有摩洛哥靴子!啊,卡尔松,他是个幸运的家伙!幸运来,幸运走,幸运的人得到姑娘。你们躺那儿格格地笑个啥!喂,卡尔松,我能再喝口酒吗,这儿可实在是冷死了,壁炉那儿有冷气透过来。
不,现在你没得喝,我要睡了。卡尔松说,他关于将来的梦被搅断了,那梦里既没酒也没姑娘,而他的位置已比人高出一头了。
沉寂重新降落,只有穿过两道门透来的猎人故事的低沉声音,以及在此中间,夜风轻轻碰触壁炉风门的声音。
卡尔松合上眼睛,半睡中听见洛藤低低的叽咕,像是在背诵什么,开头他没听明白,接着听到一句长长的不打顿的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这段祷告文的全文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晚安,克拉拉,睡个好觉。
不一会,姑娘们的床那儿传来呼噜声,而隆德克维斯特是在拖着木头不管是当真的还是玩笑把窗户弄得咔嗒作响。卡尔松躺着、迷糊着,不清楚自己是醒着还是睡着,直到他觉得被子给掀开了,一个胖胖的、汗津津的身子爬到了自己身边。
是我诺尔曼。一个讨好的声音低低地说,卡尔松明白了,自己要和这名雇工合用一张床。
哦,射手回来了,隆德克维斯特生锈的低音嘟哝着,我猜着年轻人是会在周六晚上出去射两枪。
你也可以呀,隆德克维斯特,可你没枪了,不行了。诺尔曼嘘道。
我不行吗?老头儿不想服输,我能拿气枪打乌鸫,我能,我在床单里也行!
喂,你们把火都灭了吗?门厅外传来老女人亲切的声音。
灭了。他们同声说。
那么,晚安!
晚安,婶子。
接着是长长的叹气,然后是喘息和吸气声,直到呼噜声又打了起来。
可卡尔松还是半梦半醒地躺了一会,数着窗格子,好让自己真做上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