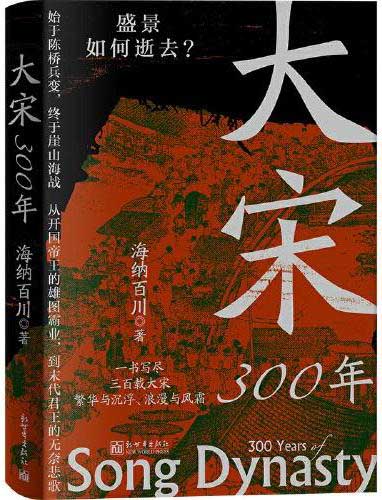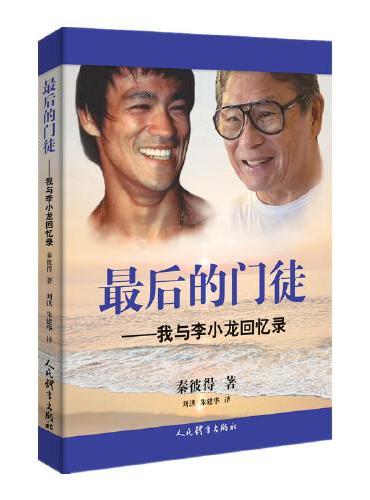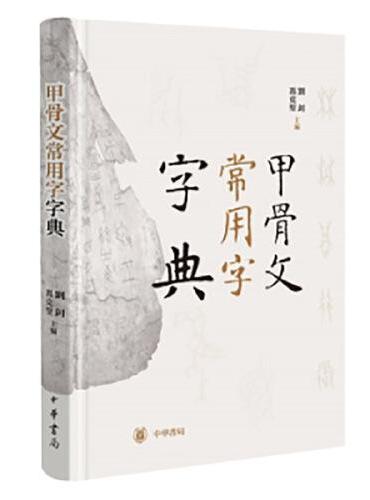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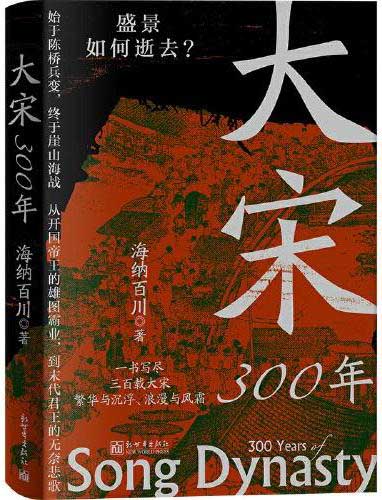
《
大宋300年(写尽三百载大宋繁华与沉浮、浪漫与风霜)
》
售價:NT$
352.0

《
害马之群:失控的群体如何助长个体的不当行为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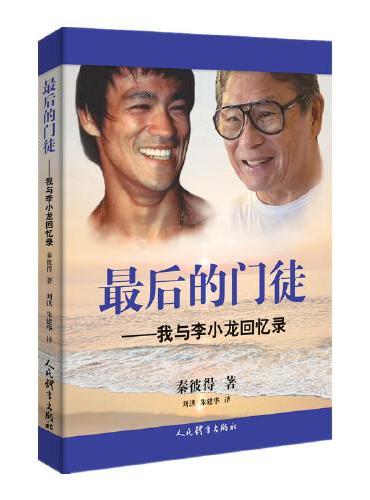
《
最后的门徒——我与李小龙回忆录
》
售價:NT$
347.0

《
没有明天的我们,在昨天相恋
》
售價:NT$
218.0

《
流动的白银(一部由白银打开的人类文明发展史)
》
售價:NT$
296.0

《
饮食的谬误:别让那些流行饮食法害了你
》
售價:NT$
296.0

《
三千年系列:文治三千年+武治三千年+兵器三千年
》
售價:NT$
9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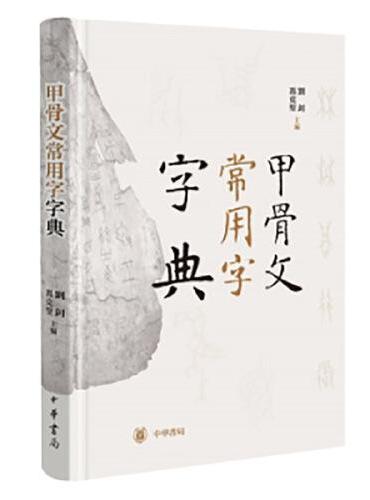
《
甲骨文常用字字典(精) 新版
》
售價:NT$
347.0
|
| 編輯推薦: |
我在这场战争中的角色无足轻重,留下的回忆也大多不愉快,但我仍庆幸自己曾经参与这场战争。
奥威尔
奥威尔首先是先知,其次才是圣徒。
止庵
奥威尔是我们这一代人中仅有的几位重要的作家之一。
Desmond MacCarthy
他能够在目睹*糟境况的同时为*美好的东西而战。
Granville Hicks
这样一个人,记住,他曾经为了自由身陷危难,几乎失去生命。他或许会开玩笑说自己的信念不可理喻,但我们明白,那其实是真诚,因为他终其一生都在坚守着那份信仰。
Granville Hicks
|
| 內容簡介: |
|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奥威尔来到加泰罗尼亚,参加了反佛朗哥政权的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部队。他在前线待了近6个月,直到被狙击手击中才不得不回国休养。基于这段经历,他以黑白胶片般冷静的语言客观展示了战争的艰辛、民众的热情、局势的变幻、媒体的歪曲,讲述了对战争的理解,剖析了战争的表象与实质,揭露了关于内战的谎言。
|
| 關於作者: |
乔治奥威尔 19031950
英国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新闻记者、社会评论家。他一生颠沛流离,但始终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笔记录着他所生活的时代,致力于维护人类自由和尊严,揭露、鞭笞专制和极权主义,并提出了超越时代的预言,因此他被尊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
|
| 目錄:
|
目录
**章 1
第二章 17
第三章 27
第四章 45
第五章 57
第六章 89
第七章 107
第八章 127
第九章 137
第十章 153
第十一章 187
第十二章 225
第十三章 243
第十四章 265
|
| 內容試閱:
|
我们此时的生活极不寻常。晚上我们是罪犯,但在白天却是富有的英国游客至少我们摆出这样的姿态。哪怕一整晚露宿街头,只要刮个胡子、洗个澡、擦擦鞋,就能让面貌焕然一新。目前*安全的做法是让自己尽可能看上去像个资产阶级者。我们出没于城里无人认识我们的富人区,光顾高档餐厅,在服务员面前摆出十足英国人的架子。有生以来**次,我喜欢上了在墙上涂鸦。我在几家豪华餐厅的过道里尽可能大而潦草地写上马克思统一工人党万岁!在此期间,虽然严格说来我是在躲躲藏藏,但并不觉得自己处于危险之中。整个事情看起来太荒谬了。我观念里那种英国式的除非触犯了法律,否则不会被拘捕的信念根深蒂固。在政治大屠杀期间抱有这种观念是很危险的。当局已经签发了逮捕麦克奈尔的拘捕令,我们其余的人可能也在名单上。逮捕、突袭、搜查仍在无休止地进行,我们认识的所有人中,除了那些仍在前线的,此时几乎都进了监狱。警方甚至定期登上法国船只,带走难民并逮捕托派嫌疑分子。
多亏了英国领事,我们的护照终于准备妥当,他那星期一定为此大费周折。我们越早离开越好。晚上7点半应该有一班火车前往布港,通常在8点半左右开车。我们商量好,由我妻子事先预订一辆出租车,然后收拾行李,结账,并在*后一刻离开旅店。如果她引起了旅店人员的注意,他们肯定会报警。我大约7点到火车站,发现车已经开走7点差10分就离开了。司机一如往常临时改了主意。幸运的是,我们还来得及通知我妻子。第二天早晨也有一班火车。麦克奈尔、科特曼和我在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吃晚饭,经过谨慎试探,发现餐厅老板是劳工联盟成员,为人友善。他不仅给我们腾出了一个三人间,而且没有通知警方。5天以来我**次不必和衣而眠。
次日早上,我妻子成功溜出旅店。这列火车晚了近一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我给军事部写了一封长信,向他们讲述了关于科普的情况即他毫无疑问是被误抓的,前线急需他,无数人可以证明他的无辜,等等等等。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看了那封信,那封用颤抖的手(我的手指仍然不太灵活)和磕磕巴巴的西班牙语写在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页纸上的信。总之,无论是这封信还是其它努力都没有见效。就在我写作本书之际,也就是事发6个月之后,科普(如果他还没被枪毙)仍然在监狱里,既未受审判也未被指控。起初我们还收到他的两三封信,是由被释放的囚犯悄悄带到法国寄出的。信的内容如出一辙被囚禁在肮脏黑暗的小屋子里,食物又差又少,由监禁条件引发的严重疾病,拒绝送医。我从英国和法国的若干个其它渠道证实了这些消息。*近,他消失在一所秘密监狱里,我们无法取得任何联系。他的遭遇也是数以百计的外国人以及成千上万西班牙人的遭遇。
我们*终平安越过边境。这列火车设有头等车厢和餐车,这可是我在西班牙头一次见到。直到不久前,加泰罗尼亚的列车仍只有一类车厢。两个警探在车里来回巡视,登记外国人的名字,不过当他们看到我们在餐车就餐时,似乎对我们的体面颇有好感。真奇怪,一切都变了。仅仅半年前,当无政府主义者仍在掌权时,表现得像个无产者才会让你获得尊重。在从佩皮尼昂到塞贝尔的路上,车里的一个法国商人曾严肃地对我说:你不能这副模样去西班牙。把领结和领带摘了。在巴塞罗那,他们会把这些玩意儿扯碎的。他的话虽有些夸张,但足以说明加泰罗尼亚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当时守卫边境的无政府主义卫兵将一个衣冠楚楚的法国人和他的妻子遣返回去,仅仅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看起来太像资产阶级。而现在却恰恰相反:看起来像资产阶级反而能得救。在查验护照的办公室里,他们在一张嫌疑犯名单上查找我们的名字,幸亏警方效率低下,别说我们的名字,甚至连麦克奈尔的名字都尚未在列。我们被从头到脚搜了身,但除了我的退役证明之外没有发现任何罪证,而那个搜查我的卫兵不知道第29师隶属于马统。于是我们蒙混出关,时隔6个月,我再次站在了法国的领土上。我从西班牙带出的的纪念品是一只羊皮水壶和一盏阿拉贡农民用的烧橄榄油的小铁灯这盏灯的形状几乎与两千多年前罗马人用的红陶土灯一模一样我是从一间小屋子的废墟里拣到的,不知怎么就进了我的行李包。
无论如何,事实证明我们走得还算及时。我们看到的**份报纸就刊登了麦克奈尔因间谍罪被通缉的消息。西班牙当局公布这一消息有点为时过早。幸好托洛茨基主义不是可以引渡的罪行。
刚刚从一个战乱之国踏上和平之地,我有些手足无措。我的**个反应是冲进烟草店,把雪茄和香烟塞满口袋。之后,我们去自助餐厅喝了杯茶,一杯我们向往了数月的加了鲜牛奶的茶。我过了好几天才习惯可以随时买到香烟的事实,总是担心烟草店关门,窗户上贴出烟草售罄的通知。
麦克奈尔和科特曼打算去巴黎。我和妻子想休息一阵子,便在**站巴纽尔斯下了火车。当地人发现我们来自巴塞罗那,表现得不太热情。我好几次遇到了相同的问话:你从西班牙来?你为哪一方作战?政府?哦!于是态度明显冷淡下来。这个小镇似乎是铁杆亲佛朗哥派,毫无疑问是因为众多西班牙法西斯流民不断涌入。我经常光顾的那家咖啡厅的服务员是个亲佛朗哥的西班牙人,他给我端开胃酒时对我翻白眼。在佩皮尼昂则恰恰相反,那儿的人支持政府军,但各个派别间彼此明争暗斗,几乎与巴塞罗那的情形一模一样。在有一家咖啡店里,只要说出马统这个字眼儿便能立刻交上法国朋友,服务员也会笑脸相待。
我们在巴纽尔斯停留了3天,这是段怪异而心神不宁的日子。在这个宁静的渔业小镇里,远离炮弹、机枪、购买食品的长队、政治宣传和阴谋,我们本该深感欣慰,但却丝毫没有这样的感觉。在西班牙的所见所闻并未随着我们的离开而淡却,反而涌上脑海,较之以往愈发鲜明。我们成天回忆着、谈论着、甚至梦到西班牙。几个月以来我们曾一直对自己说离开西班牙以后要去地中海附近,安安静静地待一段时间,或许可以钓钓鱼。但现在真的到了这儿,却只有无聊和失望。天气寒冷,海风呼啸,黯淡的海面波涛汹涌,码头边的水里漂浮着杂物、软木片和死鱼内脏,撞击着岸边的礁石。或许听起来有些疯狂,不过我们都想返回西班牙。虽然这不仅对任何人都没好处,反而可能造成严重的伤害,但我们俩都希望当时留在那儿与其他人一起被关进监狱。我恐怕无力表达出在西班牙的那几个月对于我意味着什么。我已经记述了一些事件,但我无法描述那些事件带给我的感受。那感受混合了景象、气味和声音,绝非文字能够承载:战壕里的气味,山谷的黎明向四周蔓延,冰冷的子弹碎片,炸弹的呼啸声和闪光,巴塞罗那清晨凛冽的曙光,军营里靴子的踏响,那个人们仍相信革命的12月,等待买食品的队列,红黑色的旗帜,西班牙民兵的脸孔。尤其是民兵的脸孔那些我在前线结识的人,此刻天知道飘零在何方,有的战死沙场,有的落下残疾,有的锒铛入狱我希望他们中的大部分仍安然无恙。祝他们所有人好运。我希望他们能打赢这场战争,把所有的外国人赶出西班牙,不管是德国人、俄罗斯人还是意大利人。我在这场战争中的角色无足轻重,留下的回忆也大多不愉快,但我仍庆幸自己曾经参与。你看如此一场灾难即便抛开大屠杀和肉体上的痛苦不谈,西班牙战争仍是一场令人震惊的灾难然而结局未必只是黯淡绝望。奇怪的是,我的整个经历反而令我更加坚信人类的善良。我希望我的叙述不会给读者造成过多的误导。我相信在这样的问题上,没有人能够给出完全真实的描述。除了你亲眼所见的,很难确信任何事,而每个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某个党派的立场去阐述。如果我没有在本书之前的篇幅中做出声明,那么现在我要说:请注意我会有党派偏见,会弄错事实,我的一面之词不可避免地会有失偏颇。当你阅读其它讲述这一时期的西班牙的书籍时,同样要注意。
尽管无事可做,但出于应该有所作为的想法,我们比原计划提早离开了巴纽尔斯。前往法国北部的旅途中,每多走一英里,景色就更加葱绿柔和。我们远离了山峦与藤蔓,重新回到草地和榆树的怀抱。当初我途经巴黎前往西班牙时,巴黎给我的印象既腐朽又灰暗,与我记忆中8年前当物价尚低廉、希特勒还是个无名之辈时的巴黎相距甚远。我早先所知的咖啡馆中有半数因顾客稀少而倒闭,每个人都饱受物价高昂之苦,对战争充满恐惧。如今,见识过了可怜的西班牙,就连巴黎似乎也显得生机勃勃。展览会正如火如荼,不过我们却设法避免前往。
再接着回到英格兰英格兰南部,这儿也许是世界上*平坦的地方。当你经历了漫长的旅途,尤其是刚刚从晕船中恢复过来,坐在联运列车的长毛绒靠垫上,你很难相信某个地方真正的有什么事情发生。日本在地震,中国在闹饥荒,墨西哥在革命?别担心,牛奶一定会在明早送到家门口,《新政治家》一定会在周五出版。那些工业城镇远在他方,硝烟和苦难隐藏在地球的另一端。这里仍然是我童年所熟悉的英格兰:铁轨隐没在野花丛中,骏马徜徉在广阔的草原上,缓缓流动的溪水绕过柳树,榆树的绿荫,农舍小院里的飞燕草;接着是伦敦郊外一望无际的宁静的荒野,浑浊的河道里的驳船,熟悉的街道,海报刊登着板球比赛和皇家婚礼的消息,戴圆顶礼帽的男人,特拉法加广场的鸽子,红色巴士,身着蓝色制服的警察所有这一切都在沉睡,英格兰的沉睡,有时我不由担心我们会长睡不醒,直到炸弹呼啸而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