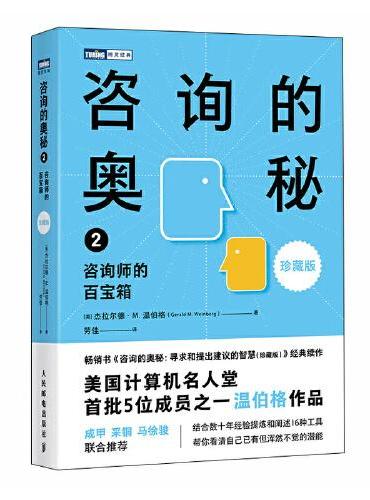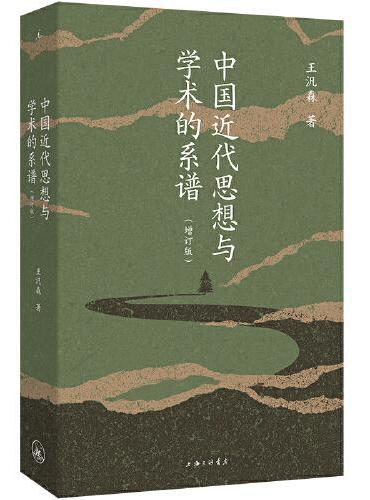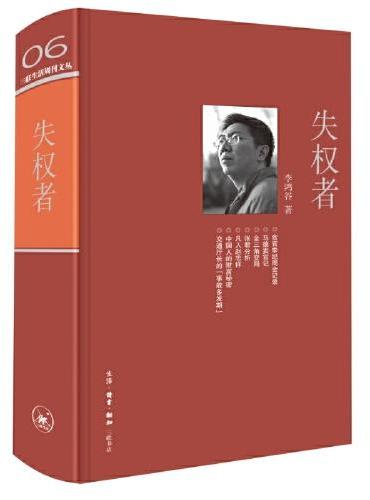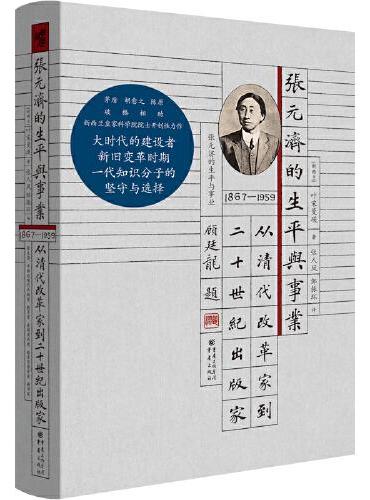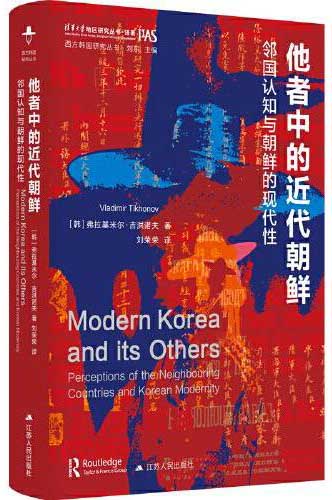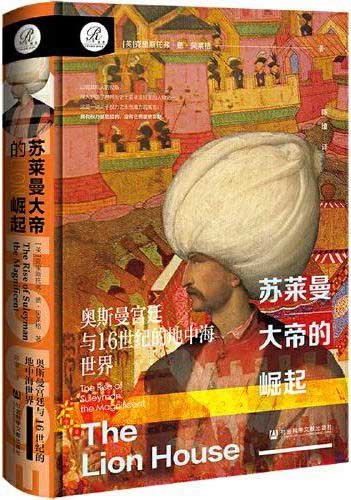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咨询的奥秘2:咨询师的百宝箱(珍藏版)
》 售價:NT$
356.0
《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
》 售價:NT$
500.0
《
失权者(三联生活周刊文丛)
》 售價:NT$
352.0
《
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
》 售價:NT$
398.0
《
他者中的近代朝鲜(西方韩国研究丛书)
》 售價:NT$
398.0
《
索恩丛书·苏莱曼大帝的崛起:奥斯曼宫廷与16世纪的地中海世界
》 售價:NT$
403.0
《
攀龙附凤: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增订本)宋代将门百年兴衰史
》 售價:NT$
454.0
《
金钱的力量:财富流动、债务、与经济繁荣
》 售價:NT$
454.0
編輯推薦:
作者从其儿时熟悉的被雾霾笼罩的伦敦讲起,用一个个精彩纷呈的故事,从细节处为古今城市作传:从第一座城市加泰土丘的诞生到古罗马城的衰亡,从克利夫兰的兴起到斯德哥尔摩的理想城市规划,从马德里的定都再到战后柏林的重建,进行了一次次引人入胜的探索。追随作者完成这次穿越古今、环绕世界的城市之旅后,我们不难发现:城市不是制造麻烦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这些世界著名都市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方兴未艾的城市改造运动和城市化进程不乏有益的启迪。
內容簡介:
城市,人类文明的结晶,自诞生之日起便饱受争议。城市的拥趸以华美的辞藻热情讴歌其博大宽容、时尚新奇与激情碰撞,而厌弃者则将其置于自然的对立面,不遗余力地抨击城市带来的空间冲突、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
關於作者:
约翰里德(John Reader),作家、摄影记者,拥有伦敦大学学院(UCL)人类学系的荣誉研究学位,是皇家人类学研究院和皇家地理科学院的成员。作品包括《非洲:一个大陆的传记》(Africa: A Biography of the
目錄
前言 1
內容試閱
第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