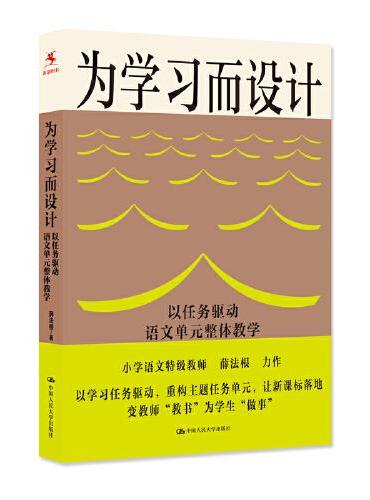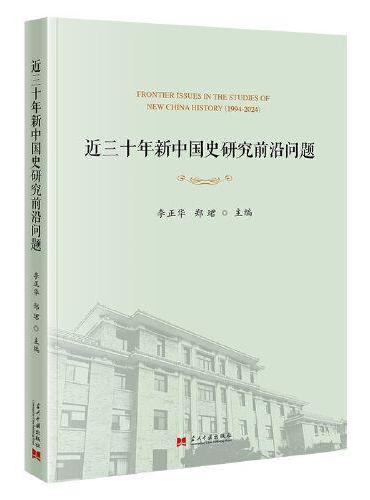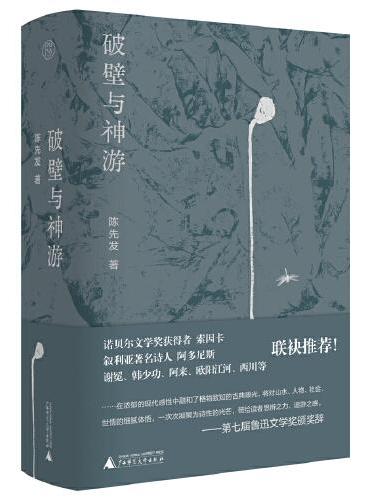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为学习而设计:以任务驱动语文单元整体教学
》 售價:NT$
347.0
《
近三十年新中国史研究前沿问题
》 售價:NT$
500.0
《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 售價:NT$
449.0
《
纯粹·破壁与神游
》 售價:NT$
418.0
《
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新版)
》 售價:NT$
449.0
《
女人们的谈话(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最佳改编剧本奖 原著!)
》 售價:NT$
286.0
《
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境管控的全球化(共域世界史)
》 售價:NT$
653.0
《
一周一堂经济学课: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 售價:NT$
500.0
編輯推薦:
如果你爱毛姆,不妨也读读艾格尼斯。
內容簡介:
这是美国作家艾格尼斯凯斯的自传式随笔之一。20世纪30年代,嫁给大英帝国北婆罗洲林业长官哈里凯斯的艾格尼斯随夫远行,旅居当时的北婆罗洲首府山打根。在山打根,她需要适应烈日与暴风雨交替的热带气候,也流连过南洋诸岛的碧海蓝天,在土著居住的险峻丛林里探险。虽为殖民者身份,艾格尼斯和丈夫并未站在殖民者的立场看待他们所处的环境,反而以一种包容甚至是谦逊的姿态与当地人相处,以平和、幽默的笔调描绘出当地的风土人情、人性复杂而闪光的一面。在艾格尼斯笔下,沙巴有了风下之乡的别名,并流传至今。
關於作者:
艾格尼斯凯斯(Agnes Keith,19011982),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橡树园,出生后不久随家人迁居加州好莱坞。青年时期年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一度任职当时很具影响力的《旧金山观察家报》。1934年与大英帝国北婆罗洲林业长官哈里凯斯书中的哈里结婚,隧随夫远行,旅居当时的北婆罗洲首府山打根,生活写作。其主要作品为其自传体三部曲:《风下之乡》(Land Below The Wind),《万劫归来》(Three Came home)(好莱坞 1950 年改编拍摄了同名电影),以及《白人归来》(White Man Returns),叙述了她所经历的二战前、二战期间以及其后在南洋的生活及感悟。
內容試閱
滑进苏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