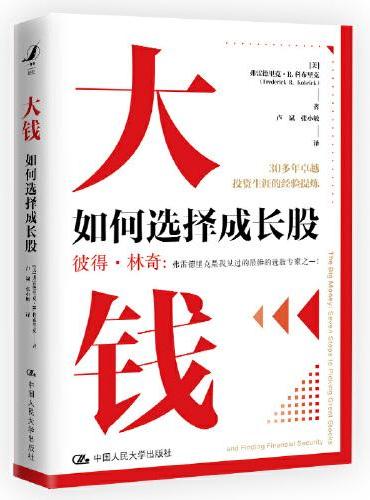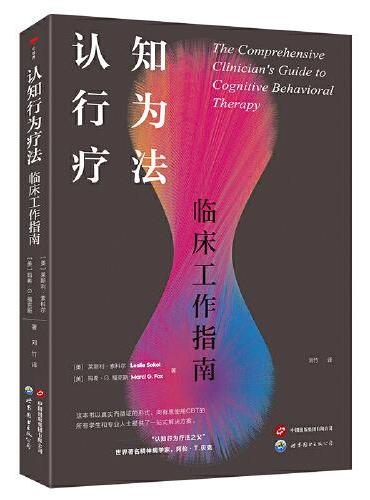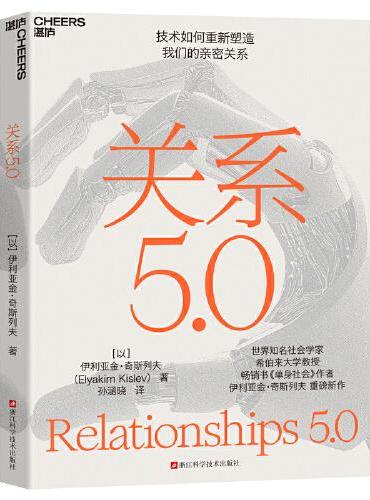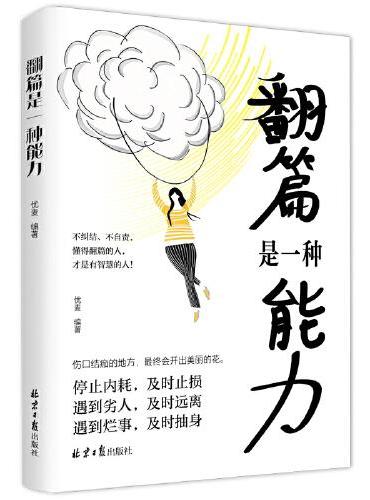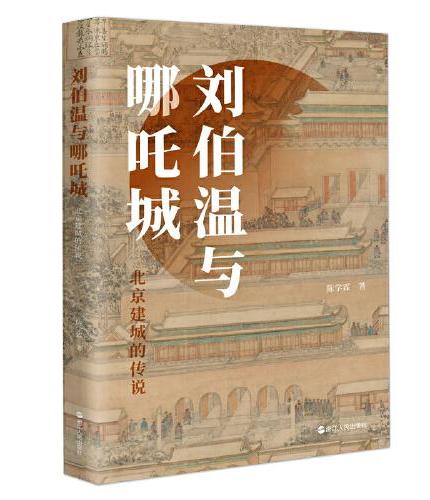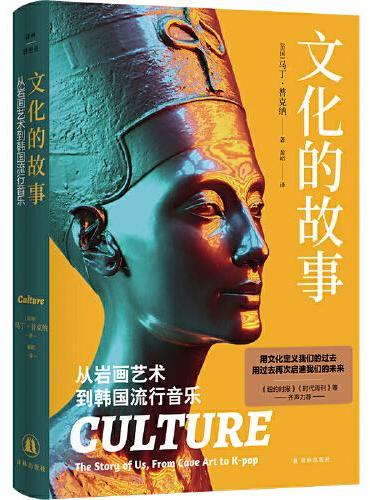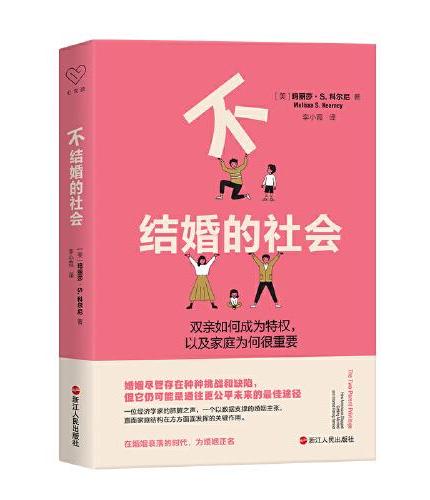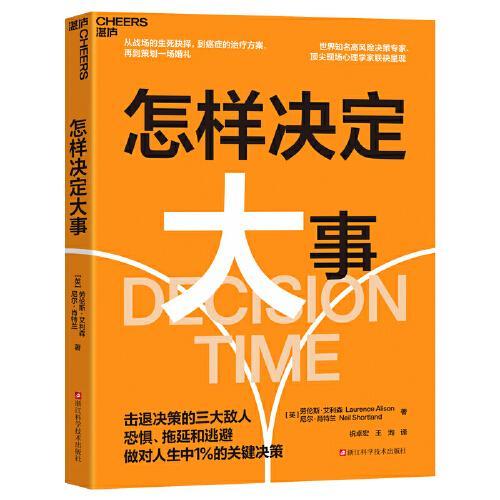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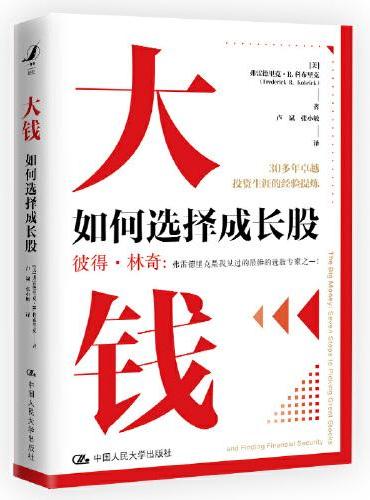
《
大钱:如何选择成长股
》
售價:NT$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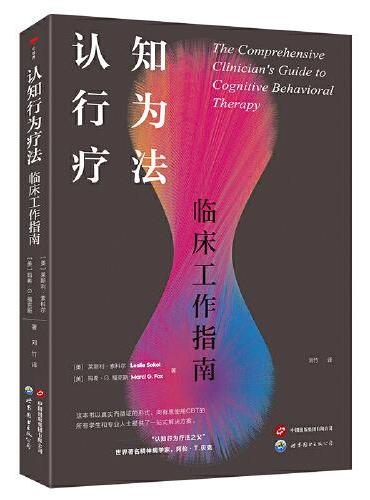
《
认知行为疗法:临床工作指南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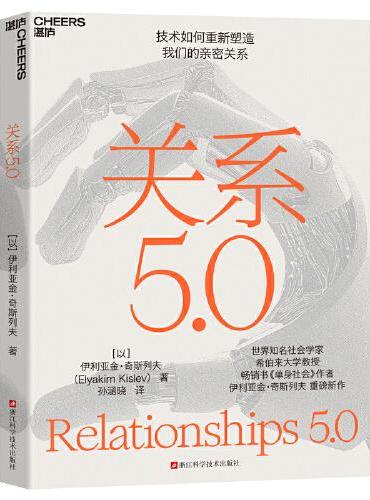
《
关系5.0
》
售價:NT$
6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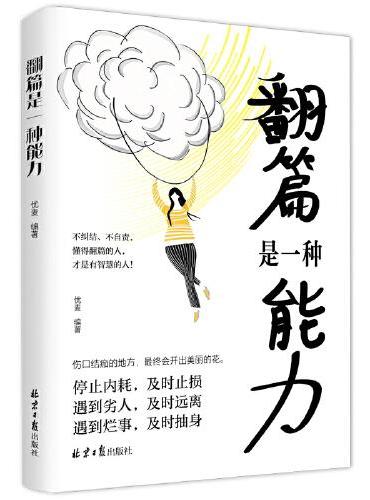
《
翻篇是一种能力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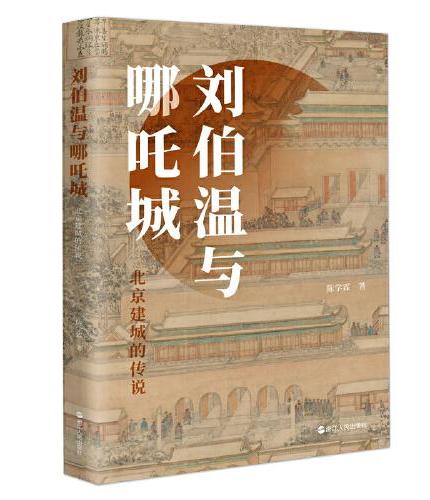
《
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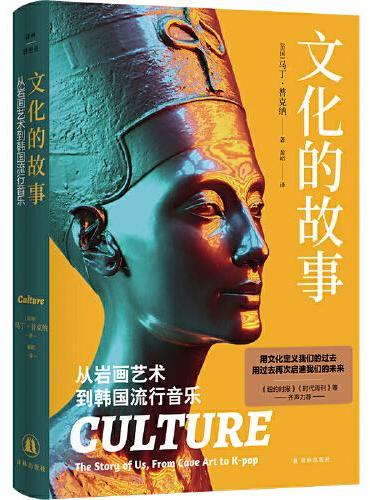
《
文化的故事:从岩画艺术到韩国流行音乐(译林思想史)哈佛大学教授沉淀之作 获奖不断 全球热销 亲历文化史上的15个关键点 从史前艺术到当代韩流的人类文化全景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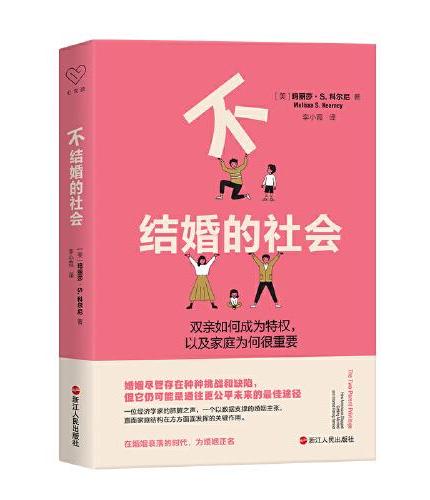
《
不结婚的社会:双亲如何成为特权,以及家庭为何很重要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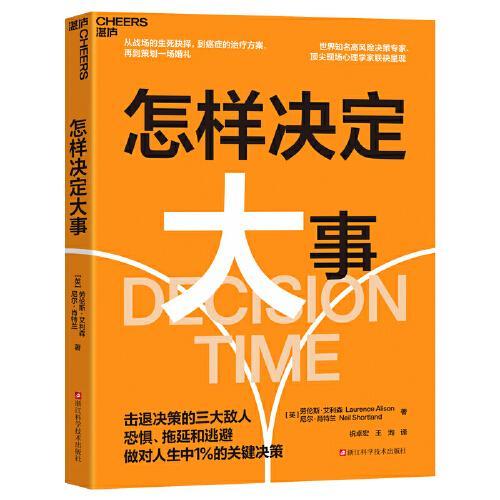
《
怎样决定大事
》
售價:NT$
510.0
|
| 編輯推薦: |
|
尤金尼德斯备受期待的第三本小说,他的*本小说《处女自杀》和他的第二本小说《中性》在美国已经家喻户晓。本书背景设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布朗大学。在那里,一位崇拜已经过时的简奥斯汀和亨利詹姆士的女孩玛德琳爱上了莱昂纳德,一个爱嚼烟草的、狂躁压抑的生物学学生。在一堂枯燥无味的文学理论课上二人相识。书中还描写了研究生生活的烦恼,不时来点儿哲学、符号学知识,非玛德琳不娶的老朋友米切尔,让这本书成为一本厚实多汁的爱情小说。
|
| 內容簡介: |
|
《婚变》讲述以专出作家而闻名于世的美国布朗大学三位文科生毕业前后所经历的波折与迷惘。婚姻情节线是英语专业的马德琳的论文主题,她在论文中阐述婚姻情节对传统小说的重要意义,现实中她也陷入婚恋困境。马德琳与才智过人的伦纳德尽管出身与个性截然不同,但依然是一对令人羡慕的校园情侣,不料伦纳德由于家族遗传及破损的童年而患上躁狂抑郁症,二人感情蒙上阴影。爱上患有精神疾病的伦纳德令她既痛苦又割舍不下,甚至一度为此放弃对未来的思考和努力。马德琳在父母羽翼下长大,不可能像叛逆的姐姐那样事事出格,但耳濡目染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氛围,其内心渴望独立。她原想摆脱父母管束毕业后与恋人生活,可伦纳德的疾病使她无法拒绝父母帮助。另一方面,马德琳的学术之路同样迷雾重重。在八十年代初流行解构与符号的美国大学校园,她不合时宜地酷爱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她曾试图赶潮流选修一门符号学课,却总是被言必称罗兰巴特、德里达的同学驳得哑口无言,也没能从教授那里学到这门显学的精要。身处以父母为主导的家庭之中、以男友为主导的恋情之中、以流行理论为主导的学术圈之中,马德琳的自我又在何方?
|
| 關於作者: |
美国希腊裔作家,1960年4月13日出生于美国底特律。
祖父母是从小亚细亚来的希腊移民。曾就读于美国著名私立大学布朗大学,并于1986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英语及创作专业硕士学位。1993年发表了首部长篇《处女自杀》,这部引人入胜的小说介绍了密执安州格罗斯角上五个神秘姐妹以及那些命运被她们永远改变的男孩子们的故事。书一上市就好评如潮,成为畅销书,荣获1993年怀汀奖以及同年美国艺术协会年度风云书,并由著名导演科波拉之女索菲娅科波拉搬上银幕。《中性》(Middlesex)出版于2002年,是他用九年时间创作的第二本小说,获得了2003年度普利策文学奖。作者以遗传学理论为基础,故事开始是女身最终变成男身的叙述者讲述了一个希腊裔家族历史遭遇的传奇故事。这位雌雄同体的叙事者也象征了美国移民身份的无奈。此书获选《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时报书评》、《旧金山纪事报》、博得书店、邦诺书店,以及亚马逊网络书店评选的2002年的十佳好书;并荣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旧金山纪事报》畅销书榜。迄今已荣获诸多奖项,包括2003年美国普利策文学奖、2003年德国魏尔特文学奖、2003年美国学会大使图书奖、2004年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文学奖、古根汉姆研究基金会奖、美国国家基金艺术奖、怀汀写作奖、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亨利D伍尔塞尔奖。
|
| 目錄:
|
献辞
引诗
恋爱中的疯子
朝圣者之湖
明智之举
安睡在上帝怀中
单身女子救生包
|
| 內容試閱:
|
恋爱中的疯子
首先来看看她所有这些书。伊迪斯沃顿 的小说,按照出版日期而不是书名排列着;现代图书版的全套亨利詹姆斯作品,二十一岁生日时父亲送的礼物;书页折了角的平装本,都是她大学课程的必读书,包括大量狄更斯,少许特罗洛普,还有不少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以及令人敬畏的勃朗特姐妹。有新方向出版社的整套黑白封面平装本,主要是诸如希尔达杜利特尔
或丹尼丝莱弗托夫 等诗人的诗集。有她背地里读的科莱特 的小说。有属于她母亲的初版《夫妇们》,马德琳读六年级时曾偷偷浏览一过,如今她用来为以结婚计划为主题的英语专业学位论文作文本参考。简而言之,藏书规模中等,便于搬动,几乎就是马德琳在大学里读过的所有东西,看似随意选择的一堆书籍,所涉范围渐渐缩小,仿佛一项复杂巧妙的性格测试,让你无法依靠预知问题的含义来作弊,最终被搞得晕头转向,唯有以基本事实作答。之后你等待测试结果,希望会是艺术气质,或热情奔放,想着若是敏锐有悟性也能勉强接受,又暗自担心会是自恋或恋家,而最后呈现的结果则是两者兼备,全因约会碰上的日期、钟点或对象的不同而感觉不同,那就是:无可救药的浪漫。
这些就是马德琳大学毕业那天早晨蒙着枕头大睡时放在她房间里的书。每一本她都读过,常常不止一次,时不时划出某些段落,但现在这一切都已无助于她。马德琳尽量不去理会这房间和房间里的一切。她希望自己能重新遁入已安稳持续三小时的沉睡状态。再清醒一点点都会迫使她不得不应对某些令人不快的事实:比如,昨晚究竟灌下多少不同种类的酒,以及她睡下时还戴着隐形眼镜。这些具体细节,继而令她回想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喝那么多,明明她一点都不想喝成这样。于是马德琳移了移枕头的位置,挡住早晨的阳光,试图再睡个回笼觉。
但这无济于事。因为就在此时,她公寓的另一头,门铃响了起来。
六月初,普罗维登斯,罗得岛,太阳升起已将近两个小时,照亮了暗淡的海湾和纳拉甘塞特发电厂的烟囱,如同布朗大学校徽上的太阳那校徽醒目地打在校园里悬挂的所有锦旗、横幅上一个有着睿智面孔的太阳,代表知识。但这个太阳普罗维登斯上空的太阳比那个用作比喻的太阳表现得更好,因为布朗大学的缔造者们出于浸礼会教友的悲观主义,将知识之光表现为被乌云所笼罩,象征愚昧尚未从人间驱散,而这真实的太阳如今正奋力穿过云层,投下斑驳的光线,给那许多整个周末都在挨淋受冻的学生父母带去希望,希望反常的天气不致毁了这一天的喜庆气氛。太阳照耀着整个学院山,乔治王朝式建筑的几何形花园和木兰花飘香的维多利亚式前庭,查尔斯亚当斯
卡通或洛夫克拉夫特 故事里的那种黑色铁栅栏以及沿着铁栅栏铺就的砖石人行道;罗得岛设计学院的艺术工作室外面,一名绘画专业学生刚熬了一个通宵,正大声吼着帕蒂史密斯
的摇滚乐;两名布朗大学军乐队队员他们的乐器(分别是大号和喇叭)在阳光下闪烁提前达到集合点,正神情紧张地四处张望,不知道其他人都上哪儿去了;被阳光照亮的一条条鹅卵石小街通往山下已被污染的河流;太阳正照耀着每一个铜门把、每一片昆虫翅膀、每一枚草叶。这时候,仿佛配合着这一泻而下的阳光,马德琳的那间四楼公寓的门铃,如同一声发令枪响开启所有活动一般,持续高嚷起来。
那传进她耳朵的震动,与其说是声音不如说是感觉,是对准她脊椎的一记电击。马德琳一下子抛开枕头,从床上坐起。她知道是谁在按对讲机。是她父母。她和奥尔顿、菲莉达约好七点半一起吃早饭。她早在两个月前的四月份就跟他们说好的,现在他们来了,恰在约定的时间,一如既往地急切而可靠。奥尔顿和菲莉达从新泽西驱车赶来参加她的毕业典礼,他们今天来这里庆贺的不仅仅是她所取得的成就,还有他们作为父母的成就,这丝毫没有错,也丝毫不出乎意料。问题是马德琳生平第一次不想参与。她并不觉得自豪。她没有心情庆贺。她不再相信这一天的意义及其代表的一切。
她考虑不去开门。但她知道如果她不去,就有个室友会去,随后她将不得不向她们解释昨晚她去了哪里,和谁在一起。因此,马德琳只好跳下床,不情愿地站起身。
站在地上,起先似乎还好。她的头出奇地轻,仿佛被淘空了似的。但紧接着血液开始从头颅中流失,仿佛沙子流出沙漏,击中瓶颈,然后她的后脑勺像炸开一般疼痛。
就在这弹雨齐发之际,处于疯狂火力中心的对讲机再次怒吼起来。
她走出卧室,光着脚跌跌撞撞地走向客厅里的对讲机,啪地按下说键。
喂?
怎么回事啊?你没听见铃声?是奥尔顿的声音,还是那样深沉而威严,虽然只是来自一个小小的话筒。
对不起,马德琳说道。我刚才在洗澡。
说得跟真的似的。可以让我们进去吗?
马德琳不想让他们进来。她得先洗漱一下。
我马上下来。她回答道。
这回她按说键的时间太久,切断了奥尔顿的回答。她再次按下键,说道:爸爸?但她说话的同时,奥尔顿肯定也在说,因为当她按下听键时话筒里传来的是杂音。
马德琳趁这对话的间隙将额头靠在门框上。木头凉凉的。她突然想到,假如她能一直把脸贴着这沁凉的木头,也许就能治愈头痛,而假如她能整天把额头都贴着门框,同时依然能离开公寓,那也许就能顺利地和父母吃完早餐,参加毕业典礼游行,拿到文凭,最后毕业。
她仰起脸,又按下说键。
爸爸?
但答话的是菲莉达。马迪?怎么回事?让我们进来。
我室友还在睡觉。我马上下来。不要再按门铃了。
我们想看看你的公寓!
现在不行。我马上下来了。别按门铃。
她从对讲机上抽回手,撤后一步站定,眼睛盯着对讲机,仿佛在看它是不是还敢出声。它安静了,于是她从客厅往回走。还没到盥洗室,室友阿比冒出来,挡住了她的路。阿比打着哈欠,一只手拢着浓密的头发,这时她看见了马德琳,会心地笑了笑。
我说,阿比说道,昨晚你溜到哪儿去了?
我父母来了,马德琳说道,我得去吃早饭。
得了。实话告诉我。
没什么好说的。我来不及了。
那你怎么还穿着这一身呢?
马德琳没有回答,却朝自己身上看了看。十个小时之前,她向奥利维娅借来这条贝齐约翰逊 黑色小礼服,觉得穿在她身上很合适。但现在她只觉得这裙子又热又紧,那条宽皮带仿佛性虐狂的束带,裙边还有一块污渍,她都不想弄清楚是什么。
与此同时,阿比敲敲奥利维娅的门,径直走了进去。马迪的伤心事到此为止了,她说着。醒醒!你快来看啊。
通往盥洗室的路已然畅通。马德琳迫切需要洗个澡,几乎是为疗伤了。至少她得刷刷牙。但现在她听见了奥利维娅的说话声。很快马德琳就会面对两个室友的盘问。她的父母随时都可能又一次按响对讲机。她蹑手蹑脚地退回客厅。门口放着一双平底鞋,她一脚踩进去,踏扁了鞋跟,一边找回身体平衡,匆匆逃进外面的走廊。
电梯正等在印花地毯的尽头。电梯之所以等着,马德琳意识到,是因为几个小时前她踉踉跄跄走出电梯时没有把拉门关上。现在她把拉门关严,按下到大堂的按钮,这台旧式机器顿然一颠,缓缓沉入大楼内部的黑暗。
马德琳所住的这幢楼叫做纳拉甘塞特,环绕恩惠街和教堂街相交的地势下沉的街角而立。这座建于世纪之交的新罗马风格的大楼,留存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某些建筑细节彩色玻璃天窗、黄铜挂壁烛台、大理石大堂,还有就是这部电梯。电梯由弯曲的铁条围成,像一个巨大的鸟笼,奇迹般地居然还能用,但走得很慢,于是趁着升降箱下降的工夫,马德琳把自己整理了一番。双手手指捋一捋头发,食指擦了擦门牙,揉去眼睛上粘结的睫毛膏,舌头润了润双唇。最后,当电梯经过二楼栏杆时,她看了看后墙小镜子里自己的形象。
长到二十二岁,或者说作为马德琳汉纳,优点之一便是三个星期的失恋和一个晚上的狂饮并没有造成多少显而易见的伤害。除了眼睛周围的浮肿,马德琳看上去仍是平常那个漂亮的黑发女孩。她脸庞的对称度挺直的鼻子、凯瑟琳赫本
般的颧骨和下颚轮廓堪称精确。只有额头的一丝皱纹显示出些许焦虑,马德琳觉得自己内心深处就是这样一个有些许焦虑的人。
她看见父母正等在楼下。他们被困在大堂大门和街门之间,奥尔顿穿着泡泡纱夹克,菲莉达一身深蓝色套装,配同色的镶金扣手袋。刹那间,马德琳竟有停下电梯的冲动,就让她父母身陷公寓大堂,围困在乌七八糟的大学城产物中间取名为苦痛或阴核之类的新浪潮乐队的海报,住在二楼的罗得岛设计学院学生仿埃贡席勒
风格的色情画,都是些闹哄哄的复印件,传递的潜台词无非是她父母那代人健康、爱国的价值观如今已成历史灰烬,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后朋克时代的虚无感,对此马德琳虽然并不理解,但她佯装接受,好乐不可支地看父母大为震惊的样子然后电梯在大堂停下,她拉开电梯门,向他们走去。
奥尔顿抢先跨进门。她可来了!他热切地叫道。大学毕业生!他做了个网前冲刺的动作,冲上前去紧紧抱住她。马德琳僵直了身子,担心被闻出自己喝过酒,或更糟的是,被闻出做过爱。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去看看你的公寓,随后迎上前来的菲莉达说道。我还想着见见阿比和奥利维娅呢。等会儿我们想请她们一起吃晚饭。
我们不准备留下吃晚饭的。奥尔顿提醒她道。
喔,我们可以留下。就看马迪怎么安排了。
不,没这计划。计划是和马迪一起吃早餐,参加毕业典礼,然后打道回府。
那就是你爸爸和他的计划,菲莉达对马德琳说道。你就穿这身衣服去毕业典礼吗?
我不知道。马德琳回答道。
我看不惯年轻女孩穿的这种垫肩。太男性化了。
这是奥利维娅的。
你看上去很疲惫,马迪,奥尔顿说道,昨晚的聚会很隆重吗?
不算隆重。
你没有自己的衣服可穿?菲莉达问道。
我会穿学士袍的,妈妈,马德琳回答道,为了以防进一步盘问,她抢在他们前面穿过了大堂。外面,太阳在与乌云的战斗中败下阵来,彻底消失了。天气似乎并不比周末更好。上周五晚上的校园舞会因为下雨而延期。上周日的大学毕业临别宗教仪式
是在绵绵细雨中进行的。现在,到了周一,雨已经停歇,但气温感觉更接近圣帕特里克节 ,而不是阵亡将士纪念日 。
马德琳站在人行道上等着父母跟上来,这时她突然想到自己当时并没有做爱。这倒是一种安慰。
你姐姐说很遗憾,菲莉达走出来,说道,她今天得带狮心理查去作超声波扫描。
狮心理查是马德琳九个星期大的外甥。其他人都叫他理查德。
他怎么了?马德琳问道。
他的一个肾明显过小。医生说要观察。要我说,这些个超声波扫描无非就是自寻烦恼。
说到超声波扫描,奥尔顿说,我得去查一查膝盖。
菲莉达没理他。不管怎么说,阿莉因为不能来参加你的毕业典礼而深感不安。布莱克也是。但他们希望你和你的新男友今年夏天去科德角的时候到他们那儿玩。
和菲莉达在一起你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表面上在说狮心理查的小肾,而实际上她已经设法把话题转向了马德琳的新男友伦纳德(菲莉达和奥尔顿还没有见过他)还有科德角(马德琳曾宣布准备去那里和他同居)。要是在常日,马德琳脑子运转正常,她倒能先菲莉达一步作出反应,但今天早上她所能做到的只有把她的话当耳旁风。
还好奥尔顿转换了话题。那么,你推荐去哪儿吃早饭呢?
马德琳转过身,心不在焉地朝恩惠街看了看。那儿有个地方。
她慢吞吞地沿人行道行走。行走行动似乎是个好主意。她带着他们经过一排古色古香的房子,房子保存完好,还挂着旧时的招贴,又经过一幢人字形屋顶的大型公寓建筑。普罗维登斯是一个破败的城市,犯罪猖獗,暴民出没,但在学院山上这一切倒是难得见到。山下,隐约可见的闹市区以及一些即将或已经倒闭的纺织厂铺展在阴沉的远方。这里,狭窄的街道大多用鹅卵石铺成,攀过一幢幢宅第,蜿蜒绕过清教徒墓地,墓地中林立的墓碑如天堂的门一般狭窄;这些被冠以前景、仁慈、希望、礼拜之名的街道,统统汇入山顶树木茂盛的校园。体力的高度暗示着智力的高度。
这样的石板人行道很可爱,是不是?菲莉达边说边跟着走。以前我们那儿的大街也是石板人行道。可漂亮了。但后来区政府重新铺成混凝土了。
还把费用摊到我们头上。奥尔顿说道。他有点跛,走起路来撅着屁股。他那条黑裤子的右腿因为穿着护膝而鼓胀,无论是不是在网球场上,他都护膝不离身。在他那个年龄组,奥尔顿是连续十二年的俱乐部冠军,是那些老家伙中的一员渐渐稀疏的脑门上缠一条吸汗带,急促的正手球,眼睛里全是杀气。马德琳从小到大一直想打败奥尔顿,但始终没有成功。这更令人生气,因为如今她的球技已经胜过了他。但每当她赢下奥尔顿一盘他就开始威吓她,耍小动作,对判决提出异议,她的比赛便彻底崩溃。马德琳担心这其中会包含某种模式,担心这辈子命中注定会始终受制于能力逊于自己的男人。由此,和奥尔顿的网球比赛对于马德琳个人的意义被放大了,于是每次和他比赛她都无法放松,结果可想而知。而奥尔顿赢球之后依旧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容光焕发,沾沾自喜,仿佛纯粹是靠本事打败她的。
在恩惠街和船夫街的交叉口,他们从第一浸礼会教堂的白色尖塔下穿过。为了准备毕业仪式,草坪上架起了扩音器。一个系着蝶形领结的训导长模样的男人,一边紧张地吸着烟,一边仔细检查着系在教堂庭院栅栏上的许多气球。
菲莉达终于赶上马德琳,挽住她的胳膊,小心跨过被路边虬曲的法国梧桐树根拱得高低不平的石板。还是小姑娘的时候,马德琳觉得母亲很美,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随着岁月流逝,菲莉达的五官显得越发粗糙;双颊也开始像骆驼一般松垂下来。保守的衣饰慈善家或女大使的风格大有遮掩身材的趋势。菲莉达的头发是她的权威所在。煞费苦心地盘成一个溜光的圆顶,仿佛为上演一出长期好戏而搭起的露天音乐台,而那出好戏便是她的脸。在马德琳的记忆中,菲莉达从来不曾有过词穷或胆怯失礼的时候。和朋友在一起时,马德琳喜欢取笑母亲拘泥礼仪,但她经常发现自己实际上认为别人的举止并不如菲莉达。
而此时此刻菲莉达正以再合时宜不过的眼神看着马德琳:为典礼排场而兴奋,盼着向她巧遇的任何一位马德琳的老师抛出几个聪明问题,或者和其他毕业生的父母寒暄一番。
总之,她对一切都显得如此应付裕如,与这社交与学术的盛典如此协调合拍,而这偏偏加剧了马德琳的失调感,对于这一天乃至对于她余生的失调感。
然而,她继续往前猛冲,穿过船夫街,爬上卡尔大楼的台阶,想找个地方藏身并喝一杯咖啡。
咖啡馆刚开门。柜台后面的那个家伙,戴着埃尔维斯科斯特洛 式的眼镜,正在冲洗煮咖啡机。靠墙的一张桌子旁,一个留着粉红色硬直发的女孩,抽着丁香香烟,在读《看不见的城市》
。《被玷污的爱》的曲调从冰箱顶上的立体声音响中飘出。
菲莉达将手袋护在胸前,停下来观赏贴在墙上的学生杰作:六幅为头戴漂白剂瓶颈圈、患有皮肤病的小狗而作的画。
很有趣,是不是?她不无宽容地说道。
艺术家嘛。奥尔顿说道。
马德琳将父母安顿在靠近凸窗的一张桌子前,尽可能远离那个粉红色头发的女孩,然后走向柜台。那个家伙不紧不慢地迎上来。她点了三杯咖啡其中大杯给自己和硬面包圈。面包圈在烤,她先将咖啡端给了父母。
奥尔顿坐在早餐桌前是非得读点什么的,于是他从隔壁桌子上拿了一份别人扔下的《乡村之声》认真读起来。菲莉达则毫不掩饰地注视着那个粉红色头发的女孩。
你觉得她那样舒服吗?她压低声音问道。
马德琳转身看见那女孩的黑色破洞牛仔裤是用好几百根安全别针别在一起的。
我不知道,妈妈。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问她呢?
我怕被她捅。
据这篇文章所说,奥尔顿边读《乡村之声》边说道,同性恋一词一直到十九世纪才出现。是人杜撰的。在德国。
咖啡很烫,救命稻草般及时。啜一口咖啡,马德琳稍稍觉得不那么糟了。
过了几分钟,她站起身去拿硬面包圈。面包圈有点烤焦了,但她不想再等新烤的,便把它们端上了桌。奥尔顿满脸不悦地瞅瞅自己的那个面包圈,挥动塑料刀惩罚似的刮起来。
菲莉达问道:那么,我们今天会见到伦纳德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