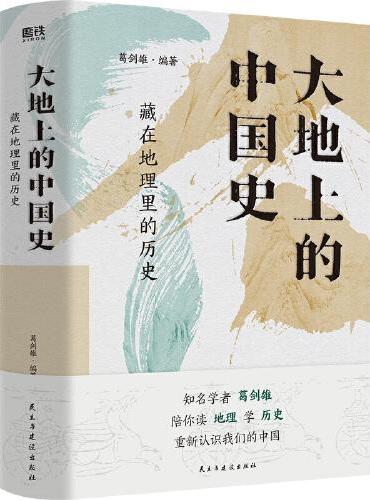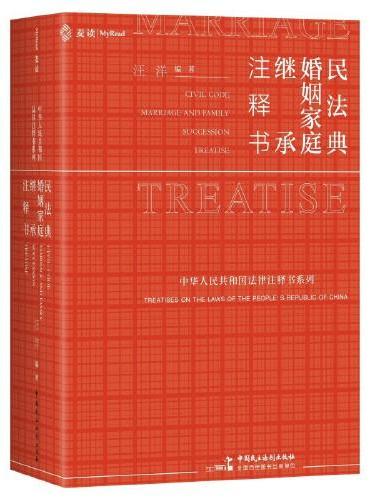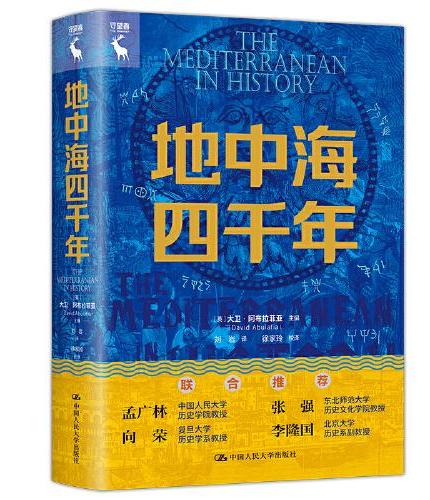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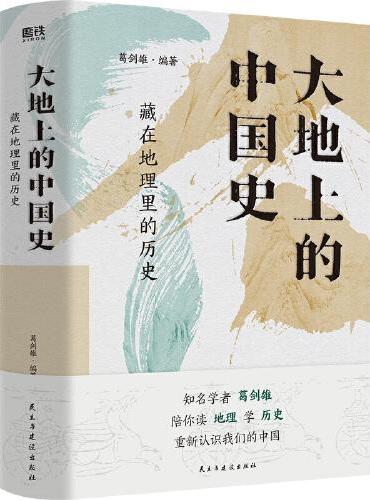
《
大地上的中国史:藏在地理里的历史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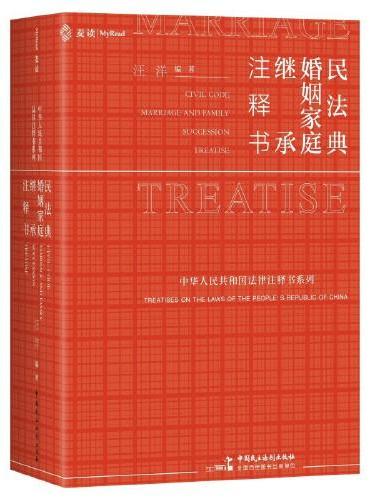
《
《民法典·婚姻家庭继承注释书》(家事法专用小红书,一书尽揽现行有效办案依据:条文释义+相关立法+行政法规+地方立法+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地方法院规范+权威案例,麦读法律54)
》
售價:NT$
6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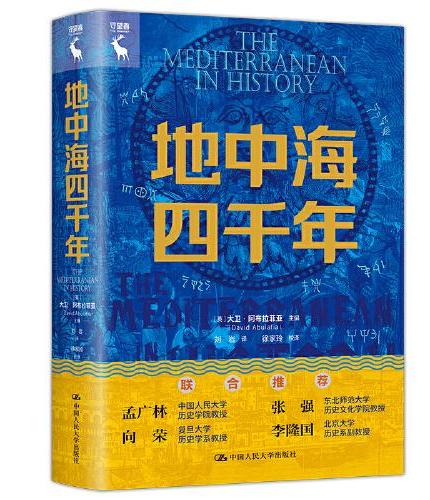
《
地中海四千年
》
售價:NT$
857.0

《
君子至交:丁聪、萧乾、茅盾等与荒芜通信札记
》
售價:NT$
316.0

《
日和·缝纫机与金鱼
》
售價:NT$
194.0

《
金手铐(讲述海外留学群体面临的困境与挣扎、收获与失去)
》
售價:NT$
347.0

《
五谷杂粮养全家 正版书籍养生配方大全饮食健康营养食品药膳食谱养生食疗杂粮搭配减糖饮食书百病食疗家庭中医养生药膳入门书籍
》
售價:NT$
254.0

《
七种模式成就卓越班组:升级版
》
售價:NT$
296.0
|
| 編輯推薦: |
|
◆ 强调文章的考究和精彩,深入挖掘每一个主题的特色,并追求知识的准确性与文字的趣味性,收入的作品优中择优,品质至上。 ◆ 奉行给读者带来细节、新意和趣味为原则,用精美的图文排编和优美的文字内容给读者带来阅读快感和思想深度。 ◆ 资深历史、军事作家宋毅主编;追求卓越至上,内容为王。
|
| 內容簡介: |
|
1896年,在巴西巴伊亚州腹地的卡努杜斯,3万名几乎一无所有的贫苦农民,在“劝世者”安东尼奥?孔萨尔埃罗的率领下揭竿而起,与武装到牙齿的官军展开了一场实力悬殊的激烈战争。他们在战斗中成长,他们在战斗中牺牲,他们在战斗中骄傲地挺起不屈脊梁。百年过后,发起讨伐的达官贵人早已被人遗忘,唯有拼死一搏的起义者们,世世代代扎根于腹地居民的心坎之上……《卡努杜斯悲歌——南美第一强国的农民战争》就讲述了这群反抗到底的起义者的故事。 《被折断的上帝之鞭——沙隆会战》讲述了公元451年在沙隆爆发的以匈奴军队与西罗马军队为主的会战,此战堪称改变欧洲命运的关键一战,有“上帝之鞭”之称的阿提拉挥军直指高卢,“最后的罗马人”力挽狂澜,使得阿提拉铩羽而归,欧洲基督教文明免于被毁灭的命运。 17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东部和西部分别崛起两个伟大的君主——康熙大帝(又称博格达汗)和准噶尔部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可汗的战争——噶尔丹与康熙草原征战记》描述了二人为争夺对蒙古高原的控制权,先后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战争。这中间,既不乏双方健儿的奋勇搏杀,更有层出不穷的阴谋诡计。噶尔丹以两万骑兵先在乌尔会河大败清军,继而在乌兰布通与10万清军主力打成平手,最终敌不过清朝倾举国之力来袭,在昭莫多一战中精锐尽丧。 波澜壮阔的圣地十字军东征绵延两个世纪,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1世纪末建立的十字军诸国一方面给中东人民带来铁与火的创痛,另一方面也成为连接东西方文化、贸易的纽带。然而月盈则亏,随着一代枭雄萨拉丁的崛起,十字军国家缓缓走向了末路。哈丁会战的惨败为耶路撒冷王国敲响了一记丧钟,尽管狮心王理查力挽狂澜,为十字军王国保住了半壁江山,但拉丁人依然丧失了往日的锐气。蒙古人的入侵和马穆鲁克的兴起让十字军诸国千疮百孔,终于,1291年阿卡的陷落宣告了十字军时代的结束。《圣地十字军的末日——从哈丁会战至阿卡沦陷》讲述了这段历史。
|
| 關於作者: |
|
宋毅,《铁血文库》系列MOOK主编,中国散文协会会员,上海作协会员,著名历史、军事作家,曾获《现代兵器》杂志2009 年度优秀作者一等奖等荣誉。出版有《战争特典:隋唐英雄》《壬辰1592 :决战朝鲜》《祖先的铁拳:历代御外战争史》等多部畅销著作。
|
| 目錄:
|
|
卡努杜斯悲歌——南美第一强国的农民战争 001被折断的上帝之鞭——沙隆会战069可汗的战争——噶尔丹与康熙草原征战记 087圣地十字军的末日——从哈丁会战至阿卡沦陷 127
|
| 內容試閱:
|
|
卡努杜斯悲歌——南美第一强国的农民战争作者:张宏轩引子我今天所讲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一个对大部分读者来说都不陌生的年代。在远东,北洋水师仅凭将士的热情与人员素质迎战吨位、火力、后勤全面占优的日本联合舰队,光荣惜败,甲午战争的结局随之奠定;在西欧,饱含屈辱的法国立志收复在普法战争中的失土,英德之间的海军竞赛同时也拉开帷幕,老牌列强之间的摩擦愈演愈烈,全面冲突显然已经不可避免;而在美洲,北方的美利坚合众国正将刀叉移向加勒比海,这个经历惨烈内战浴火重生的强大工业国,既有信心也有能力吃下西班牙帝国的最后一点遗产,让这个古老的殖民帝国彻底沦落。美国是新大陆的明星,正在迎接来自旧大陆各个角落的目光。唯有南方那个面积相近、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巴西,相较之下有一些黯然失色。这个以咖啡与桑巴闻名于世的农业大国,此刻却连自家里那点儿家务事,都还远远没有梳理清楚。一、暴风眼中的南美第一强国19世纪90年代,巴西正经历着自建国以来最为剧烈的内部变革,整个国家就像一壶煮沸的咖啡,蒸汽滚滚,浪花欢腾,白亮水泡咕嘟咕嘟毫无停顿地向上翻涌。这个国家看上去确是热闹非凡,但在沸腾逼人的表象之下,依然蛰伏着那些被有意无意留下来的种种残渣。最早的残渣甚至可以追溯到1822年。在那一年,葡萄牙布拉干萨王朝王子、巴西摄政王佩德罗顺应时势,抓住民族自决思潮席卷南美各殖民地这一有利机会,果断动手驱逐葡萄牙驻军,宣布巴西正式独立。这场豪赌收获颇丰,原本的佩德罗王子摇身一变,正式成为了巴西帝国皇帝佩德罗一世陛下,原地平升二级;大庄园主、种植园主和贵族爵爷不仅旧有财产与政治权力不受影响,更因从龙之功荣获新赏,不禁弹冠相庆。一个崭新的国家诞生在古老的大陆,里约热内卢在耶稣山的俯瞰下成为了崭新的首都。尽管有些联邦党人和共和主义者在议会里吵吵嚷嚷,甚至试图通过一部限制皇帝权力与旧葡萄牙官僚被选举人的宪法,但精明的佩德罗一世旋即解散议会,流放首相,让这些不自量力的家伙再也无法阻挡崭新帝国的脚步。可这位陛下忘了一件事,如果使不了绊子,不自量力的家伙还可以直接抡棍抽他的腿。“赤道邦联叛乱”“破衫汉战争”“马腊尼昂市民起义”,巴西帝国从成立之日起,可以说没有一天安稳统治的日子。试图扩大自治权的各州豪强心怀不满,与过去一样饱受压迫的雇工和小农心怀不满,充满理想的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心怀不满,从非洲家乡被贩卖而来的黑人奴隶更是绝对心怀不满……佩德罗一世皇帝最重要的精力,就这样全部放在了镇压叛乱与强化中央集权上,并且最终被迫下野,携妻赴欧洲长途旅游。继任皇帝是他的儿子,佩德罗二世。为求国内稳定,这位新帝在能力所及范围内试遍了可用的各种方法:与议会妥协,缓和政治危机;引入英国资本,大力发展咖啡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限制奴隶制,强化道路建设,让更多的人口可以自由流动,等等。这些措施成功延长了巴西帝国的寿命,但归根究底仍是小打小闹的改良,与洋务派在清廷内部从事的那些裱糊一样,无法触及根本。面对重重的内部矛盾,皇帝陛下就像古往今来无数的统治者同道那样,选择了对外诉诸武力。1864年至1870年,巴西、阿根廷两强联手,捎带乌拉圭一起组成三国同盟,对悍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十恶不赦的侵略者巴拉圭发动惩戒战争。为制服这个人口仅50万的小小的国家,三国同盟耗费整整7年时间,付出了多达十余万人的巨大伤亡代价。但胜利依然是胜利,征服者的辉煌仍使佩德罗二世陛下扬眉吐气,威望在国内一时如日中天。“‘高尚者’佩德罗二世陛下万岁!”各阶层的人们振臂高呼,沉醉在如昙花般美丽的爱国热情之中。不过,战争给巴西带来的,可远不止君主头顶上那层光环。无论古代、现代或是未来,任何军队都离不开后勤的支持,它就像一只贪婪的饕餮,大口吞噬着成吨的军需物资。为满足前线对弹药、粮秣、被服、马具、卫生用品的需要,巴西本土工业开足马力生产。因此,巴西工业在7年间得到了长足发展。为将这些急需的后勤补给送上前线,巴西国内大兴基建,铁路里程在7年间增长数倍……有了充足的军需供应,军队便有了在敌方领土扎根的基础。但想要彻彻底底地制服敌人,军队还需要另外两样不可或缺的条件:不致误事的指挥效率和广大民众的支持。为达成第一点,指挥官们渴望对部下如臂使指,尽可能地避免贻误战机;为达成第二点,新闻媒体渴望对战况了解实时,用翔实文字牢牢抓住读者的眼球。迫切的现实需求逼迫技术做出改进,有线电报开始在巴西各州迅速拓展。前线的战况、首都的逸闻、带有神秘感的各色谣言,以往需要辗转几个月才能传过来的,如今却是地点与日期齐备,有时还会有准确(至少看上去像是准确)的配图新闻报道。巴西社会开始了不可逆转的改变。资本家的钱囊迅速鼓胀,新贵们第一次有了足够实力,开始在各州议会与帝国议会提出自己的主张;英国资本的渗透随着铁路建设愈加增强,维多利亚女皇开始对帝国的内政外交施加越来越不可忽视的影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新闻刊物,令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数量成倍增长,使他们发出的声音更为洪亮。原有的矛盾随之放大,崭新的冲突不断产生,“高尚者”佩德罗二世很快发现,国内的反对声在沉寂片刻后,竟然以数倍的规模卷土重来,堪比雨季的亚马孙洪峰。知识分子们鼓吹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各式思潮,左、中、右三翼今天斗得不亦乐乎,明天又一致枪头对外,在街头演讲中把皇室骂得狗血淋头;新兴资产阶级在议会中气势汹汹,指责皇帝陛下给予了外国投资者太多优惠,要求更多的工人、更便宜的原料、更广泛的贸易保护;至于大捷之后的军队,那更是一刻不停地鼓噪,任何裁减军费的打算,对他们来说都是太岁头顶直接开刀……皇帝陛下很快就处于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反对者们要的不是改良,而是彻底改变游戏规则,想要重新分蛋糕。病急乱投医的佩德罗二世别无他法,只能费尽心思在国内外搜罗支持力量。为此不惜假女儿伊莎贝拉公主之手,在1888年5月13日敦促议会表决通过法律,彻底废除国内延续数百年的黑人奴隶制,向古老的传统体制击出重重一拳。这位皇帝陛下向全世界展示出一名高尚者的伟大魄力,但也惹恼了帝制一直以来的追随者。对那些长久以来享受奴隶免费劳动的大庄园主、种植园主及贵族爵爷们来说,动他们的财产比动他们的性命更为严重。解放奴隶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和巴西平民的交口称赞,就连知识分子也为伊莎贝拉公主欢呼,但皇室却在各统治阶层中陷入空前孤立,并且根本没有机会把美名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支持了。早已心怀不满的军队敏锐地抓住时机,高层将领迅速串联通气,推举德奥多罗?达?丰塞卡与弗洛里亚诺?阿劳霍?佩绍托两位元帅为首领,在佩德罗二世最缺乏盟友的1889年发动军事政变,一举控制议会,改元共和。巴西帝国就此覆灭,整个皇室流亡欧洲。进入19世纪90年代,这块辽阔土地的统治者变成了联邦制的巴西第一共和国,一个国旗照搬美利坚,军服模仿法兰西,左民主、右自由,平等、博爱张扬在胸前的国家。不仅国际社会一时有些不太适应,就连巴西国内也是议论纷纷,很多知识分子都对军队的突然发难表示愕然,认为军队独裁代替皇帝独裁根本就是换汤不换药,证据便是丰塞卡、弗洛里亚诺两位元帅轮流坐庄,相继成为了共和国的第一任与第二任总统……围绕权力的分配,平民议员、地方政客与军队发生了激烈斗争。议员们发动新闻媒体,针对军队的任何一点错漏口诛笔伐,丘八们则对此置之不理,坚决用铁腕镇压一切地方骚动。“在这个阶段,唯有军队的独裁才能保护共和,才能保证祖国的繁荣。”弗洛里亚诺元帅的忠实助手,陆军上校安东尼奥?莫莱拉?西塞(Ant?nio Moreira César,César即恺撒的葡萄牙语变体)如此声称。他以狠辣的手腕将卡泰里纳叛乱平定,不留一个活口。事后,面对要求给个说法的鼎沸舆论,面对里约热内卢措辞严厉的质询,这位帝国时期曾在大街上亲手刺杀对军队不恭记者的上校,回复电报仅仅只有短短的三个字:“用不着。”这样的态度显然不能令平民政治家们满意,政治争斗于是继续,哪怕是首位平民总统莫拉伊斯的当选,也只是令双方的矛盾稍稍有所缓和。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间关于经济的纠纷也愈加紧张,资本家们要求更进一步地分割庄园,清理佃农,掌握更多人力资源为己所用,同时制定更向自己倾斜的商业政策,而庄园主老爷们不肯再从口袋里多掏一个瑞斯。更加微妙的是,这两个阵营还都是军民混杂。面对如此混乱的政经形势,面对从中央到地方无休无止的争吵,共和国政府的高层官僚们可谓焦头烂额,他们是如此忙碌,如此鞠躬尽瘁,以至于没人还有精力去管那些细枝末节的小事,例如城市之外那广袤土地上寻常百姓的民生。二、贫瘠的腹地,贫穷的人民尽管里约热内卢的咖啡壶烧得快要爆炸,但这些上流社会的争吵,似乎并没怎么影响远离首都的巴伊亚州。这里位于巴西高原东北角,平均海拔下降到300至400米,见不到巍峨的高山,亦少有肥沃的平原,热带草原气候使这里的年降水量不到500毫米,季节也仅仅剩下单调的干湿两季。每年的4月到8月,珍贵的降雨会为大地短暂铺上绿色绒毯,灌木与野草四处蔓延,仙人掌挺直饱满的躯干,分叉的河谷洪流奔涌,反射出破碎而湿润的柔和粼光……但在一年里另外的一半时间,巴西内陆的这块腹地,却完全呈现出一种代表炎热的赤红。烈日当头,空气沉涩,退化的草皮暴露出底下土丘,随风卷起阵阵尘砂;岩石剥落,流水萎靡,升腾的热浪拿捏着地表景象,令那些紧贴地面、粗重喘气的各色生物更显怪异。这里有着成片的卡汀珈——对荒凉草原上树林的统称。但这所谓的树林,足以让任何一个来自北半球的旅行者目瞪口呆,汗流浃背地挠着头顶,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落脚。这里没有大叶的榆树,也没有秀美的柳树,只有各种各样最多长到两人多高、名称古怪的异国树种:在茎里蓄满水的马坎比拉树,把根扎到惊人深度的卡朱依树,有着伸长叶子的法维拉树,果实酸甜的契克契克树……在干季,所有这些树的枝干都呈现出同样的扭曲,蜿蜒伸长的枝条被阳光烤得苍白发亮,仿佛一根根被吃光啃净的兽骨,又被挂上了密密麻麻、比刺猬还要茂盛的棘刺。响尾蛇与蜥蜴穿行其间,咝咝的吐舌声早已融入背景。这里无法支持远东那种精耕细作的高产农业,围绕各个庄园、村镇,人们只能种植一些耐旱的玉米,绝大部分的生计都要依靠畜牧。屋前屋后,可以喂鸡,村落左近,可以放羊。广阔平坦的腹地高原虽然贫瘠,但环绕着河谷、道路与卡汀珈,总能找到草丛与水井,供给牛群足够的食料与饮水,让它们从哞哞叫的欢快小犊,慢慢成长为膘肥体壮、能用肉奶回报主人的合格牲口。因此,腹地居民的主业便是牧牛。他们并非在里约热内卢、萨尔瓦多这类大城市聚居的欧洲移民与土生白人,除少量土著居民卡波克洛人(即印第安人)外,大部分都是族名拗口的混血种人:莫拉托人(黑白混血)、库里包加人(白印混血)、卡夫索人(黑印混血),以及由上述三个族群更进一步混血而成的其他族群。他们不会跳优雅的交际舞,也不懂波尔多与勃艮第的红酒有何区别,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更是茫然无知。他们在家中接生,在小教堂接受洗礼,又在小教堂与同居伴侣成婚,一辈子也许不识一个大字。每当太阳初升,他们便会穿上防御卡汀珈棘刺的坚硬皮衣,头顶用于遮阳的宽檐皮帽,骑着温顺的马匹开始放牧牛群。在外人看来,他们在马鞍上晃晃悠悠,紧眯双眼,仿佛随时有可能睡着,可一旦有牛只离群,这些腹地牧人便会闪电般地睁开双眼迅疾出击,在牛群奔至危险的卡汀珈深处之前,用尖头棍准确地刺戳,将这些茫然的生灵重新引回正途。他们当中有单干的自耕农、货郎与商人,以及在大宅中为老爷们提供服务的男仆女婢,但大部分腹地居民都是世世代代为某一庄园效力的佃客。依据古老的习惯法,每四头出生的小牛中有一头属于佃户,剩下的三头则要交给主人,其他收获大体如此。他们不是南方潘帕斯草原上那些桀骜不驯、衣着华丽的高乔人,在通常年景,庄园主和贵族爵爷们根本用不着雇人催债收租——实际上,很多主人压根儿就没和佃客们打过照面。不需要命令,不需要监督,腹地人会忠实地遵从古老习俗,为属于自己的那头小牛打上独特烙印,而将剩下的按时送去庄园。有时还会请教士帮忙写信,将一年来牧场上发生的每一件事,详细地汇报给“我亲爱的主人”,虽然对方不见得会屈尊开封。年复一年,风雨不变,直至那每32年一次准时降临的全州大旱。有人说,是封闭的内陆环境造成了这种旱灾。还有人说,大西洋的洋流与北方的雨林同样负有责任。起初,只是第一场降雨没有按时到来,人们纷纷自我安慰,这只是上帝偶然的考验,与往年并无差别。但下一月无雨,下下一月依然无雨,直到整个雨季结束,滚烫的腹地仍是滴水未落。河流与小溪一条接一条慢慢干涸,本就面积不大的各个湖泊随之水位下降,直至见底,暴露出古老年间牛群走出的串串足迹。鱼蛙在残存的烂泥中绝望扑腾,直至最后气绝,腐败的气息引来乌云般的成片蚊蝇;口渴的牲畜钻进枯干河道,在烂肉之间徒劳地拱顶翻找,带血的涎液沿着唇舌蔓延,旋又被灼热的喘息蒸发个底掉。烈日炙烤低矮的群阜,将这些石包化作悄无声息的赤红火炉。石块崩裂,顺着缓坡成群滚下,掀起的黄雾竟比山高。在这无风的炎热时日,往往过上一整个弥撒的时间,尘土才会慢慢飘进不远处的村镇,扑向牧人们布满沟壑的铜红色面庞。大旱往往会持续整整一年,任何努力似乎都是徒劳。望着绝收的庄稼地,望着因缺水少粮一头头倒毙的牛羊,整个腹地很快陷入惊慌。人们高举圣像,吟唱圣歌,在圣多山等本土天主教圣地举办大规模的宗教游行,心甘情愿地掏出口袋里最后一枚硬币,但这种虔诚通常并不会得到回应。大地开裂,细纹密如龟甲;牲畜气绝,干尸皱如侏儒。成群结队的响尾蛇逃离卡汀珈,沿着官道小路疯狂奔向两脚猿类的聚居地,试图获取这些危险生物藏起来的最后一点窖藏。它们很快也加入到了人类的存粮当中,连同蚂蚁、草皮以及干瘪的蜥蜴。但也只能让牧人们多维持几天。当主人允许自己保留的牲畜粮食最终耗尽,当供人饮用的水井接连告竭,社会的秩序终于崩溃了。人们开始哄抢商店,像保护至宝一样紧紧抱住哪怕一小袋面粉;人们开始聚众逃荒,赶出最后几头还能动弹的牛马,辅以人拉肩扛,哭泣着、抱怨着,整村涌向依然留有湿润的海边乞讨就食。也有那类胆大包天之徒,他们留在家乡,留在腹地,头顶花里胡哨的草帽,腰插锋利弯曲的短刀,或掠庄园,或劫村庄,干起了在灾荒年景格外泛滥的没本钱勾当。强人的马队穿过尸骨遍布的道路、踏碎空无一人的废屋,野蛮的咆哮胜似狗嗥,这些土匪与逃难队伍连日交火,同庄园保镖激烈枪战,黑火药烟云一直飘到了州城萨尔瓦多。直到此时,对大旱束手无策的官府方才开始行动,大批的军警开始出动剿匪,砍下的各色人头就像腌咸鱼一样层层叠叠装进木桶,充分证明他们是多么的辛苦。当然,要让如此尽心除害、保道护庄的丘八白干,天理岂容?军警所到之处,庄园的支持、村镇的摊派、难民过卡时的孝敬,哪个能拖?哪个敢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