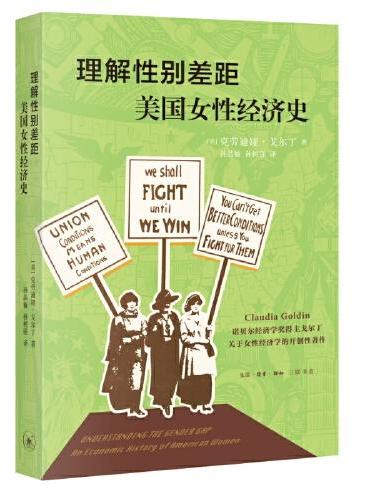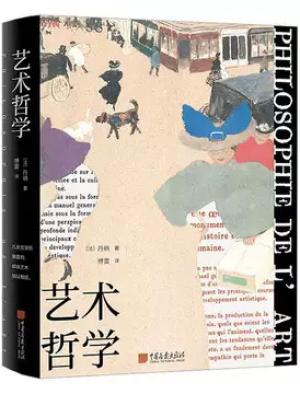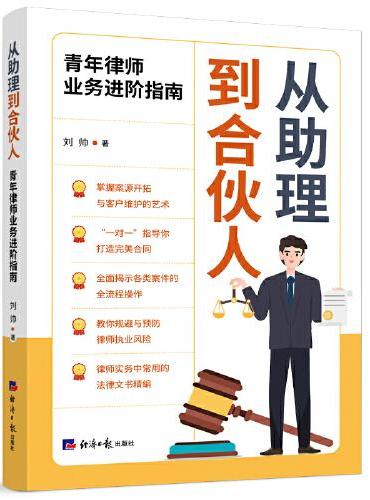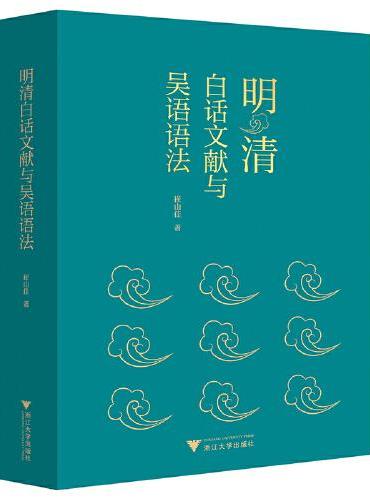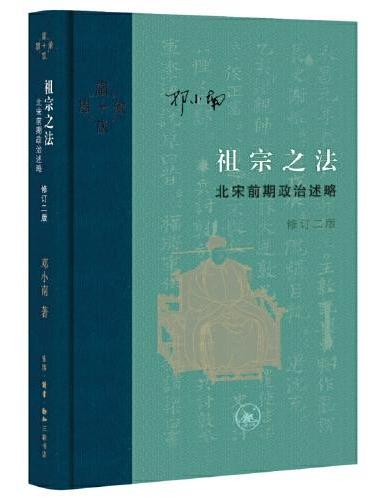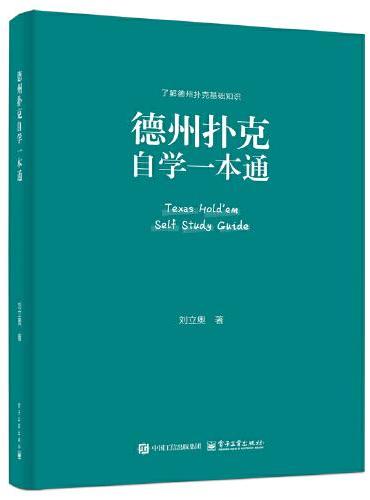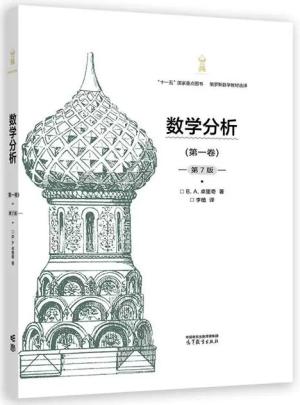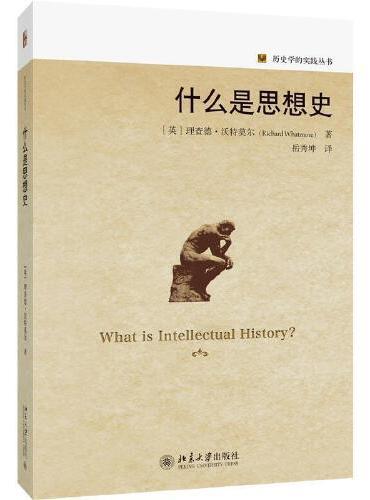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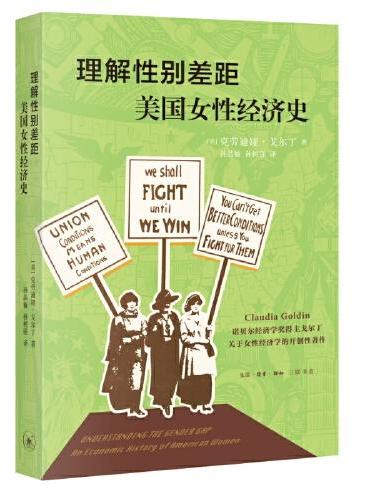
《
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经济史
》
售價:NT$
4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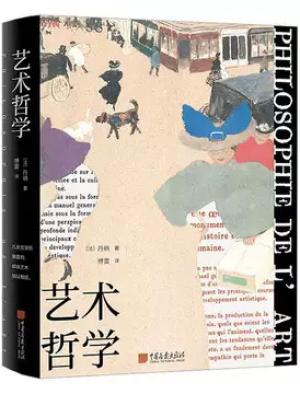
《
艺术哲学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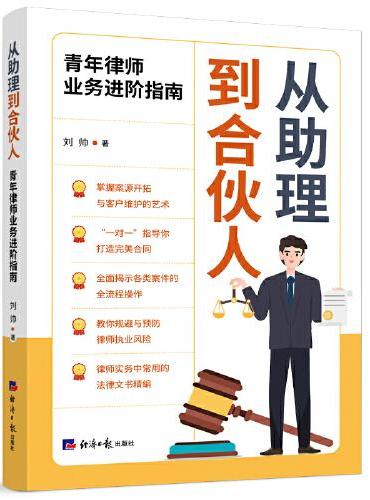
《
从助理到合伙人-青年律师业务进阶指南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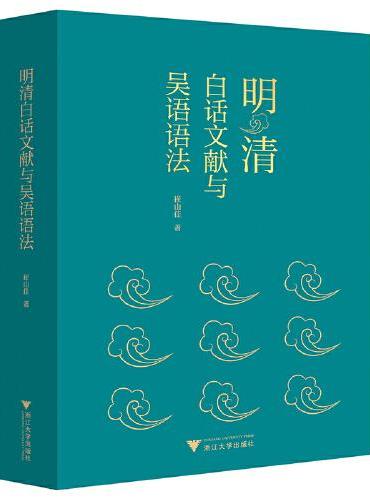
《
明清白话文献与吴语语法
》
售價:NT$
1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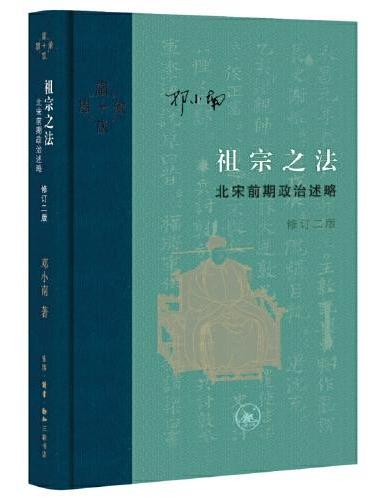
《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二版)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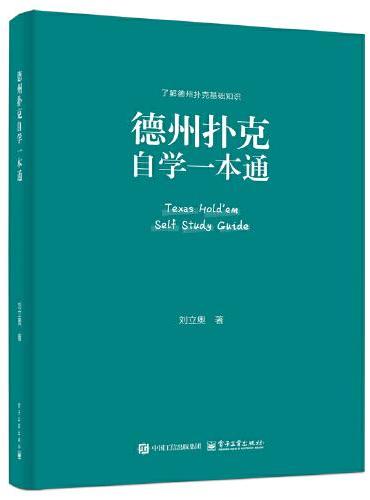
《
德州扑克自学一本通
》
售價:NT$
25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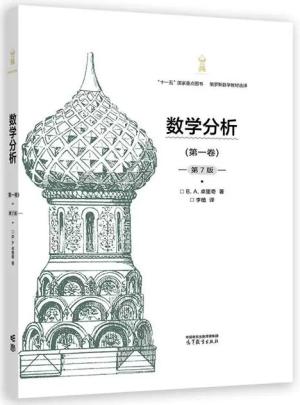
《
数学分析(第一卷)(第7版)(精装典藏版)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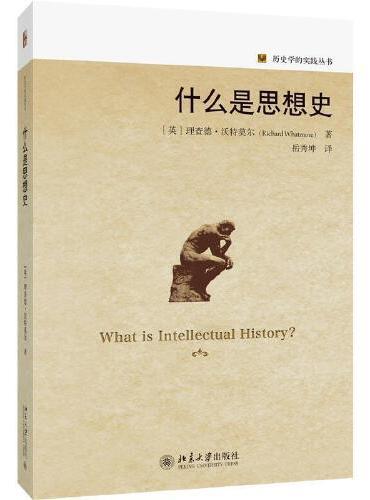
《
什么是思想史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
售價:NT$
286.0
|
| 編輯推薦: |
☆
本书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与现实敏感性,展现了葛兆光、汪荣祖、姚大力、欧立德、杉山正明等二十位中外知名学者对于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等问题的邃密思考。
☆
通阅本书,可以使我们深入地了解当前中国史研究的前沿论题,启发我们对传统的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史研究范式进行检讨与反思,进而丰富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宏观思考。
|
| 內容簡介: |
何为中国?元朝、清朝不是中国的王朝吗?清帝国通过怎样的统治政策获得了奠定今日中国版图的疆域?新清史、内亚史研究为什么在国际学术界这么火?
近年来,在新的理论视角与新的理论框架的冲击下,中国史研究日益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葛兆光、徐文堪、汪荣祖、姚大力、张帆、罗新、沈卫荣、钟焓、狄宇宙、欧立德、杉山正明等二十位中外知名学者,在本书中展开了精彩的论述与对话,对上述种种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也具有鲜明的学术史意义。
本书可以使我们比较深入地了解当前中国史研究的前沿论题,启发我们对传统的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史研究范式进行检讨与反思,进而丰富对中国历史的宏观思考。
封面图片取自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清人明福绘《西域图册》。
|
| 關於作者: |
葛兆光,1950年生,复旦大学教授,曾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著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中国禅思想史》、《中国思想史》、《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等。
徐文堪,1943年生,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审。长期从事汉语语文辞典编写,参与《汉语大词典》编纂、订补达三十余年。同时致力于古代中亚和内亚文明(尤重吐火罗学研究)、古代中外关系、欧亚大陆史前史、语言学、辞书学、人类学和域外东方学史等方面的研究,出版著译多种。
汪荣祖,1940年生,著名历史学家,曾在美国执教三十一年。现任台湾中央大学人文中心讲座教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暨总咨询委员、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荣誉教授等职。著有《史家陈寅恪传》、《康章合论》、《史传通说》、《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史学九章》、《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等。
姚大力,1949年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特聘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元史、中国边疆史地,著有《北方民族史十论》、《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读史的智慧》等。
|
| 目錄:
|
前言
从历史看中国、亚洲、认同以及疆域
关于《宅兹中国》的一次谈话
葛兆光再谈从周边看中国
多元脉络中的中国
许倬云新著《华夏论述》解说
如何拯救历史?
徐文堪谈西域研究
维也纳归来谈吐火罗学
悼印度杰出学者纳拉扬教授
钟焓谈辽史与内亚史研究
《辽史》的纂修与整理
寻找契丹后裔
墓室壁画中的辽人
元朝不是中国的王朝吗?
杉山正明谈蒙元帝国
张帆谈元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狄宇宙谈内亚史研究
世上本无黄种人
蒙古学家柯立夫其人其事
沈卫荣谈西藏与藏学热
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形式的腐败与改革
美国藏学主流的学术传承和学术批评
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
不再说汉化的旧故事
新清史之争背后的民族主义
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
为新清史辩护须先懂得新清史
敬答姚大力先生
略芜取精,可为我用
兼答汪荣祖
学术批评可以等同于打棒子吗?
欧立德谈满文与满族认同
清史研究岂能无视满文文献
朱玉麒谈清代边塞纪功碑与国家认同
奥斯曼帝国崩溃了,中国却没有
|
| 內容試閱:
|
从历史看中国、亚洲、认同以及疆域关于《宅兹中国》的一次谈话
葛兆光口述 盛 韵整理
一
最近,我会在北京的中华书局和台北的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一本新书。这本书用了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一句话宅兹中国当书名,主要是想讨论亚洲或东亚、中国以及民族国家、认同、疆域这样一些问题,大部分章节都是由这八九年来发表的论文构成的。也许,这就是我最近这些年所思所想所做的一些事情,因为其中的问题、思路和旨趣有一定的连贯性,所以,我把它编成了一本完整的书。
你也知道,关于认同、国家、民族、疆域以及亚洲或东亚,在现在中国学界已经有很多讨论,一些新理论、新概念和新话题很吸引人。不过你也可以发现,有些议论,你说不清它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但会占据很大的言论空间,有很大的影响。有一些人挪用来自西方学院的一些时髦词儿,又填上一些似乎有关中国的空洞话题,所以,读者会认为他们既能够跟国际接轨,又能够谈中国问题,而且他们在政治和思想的论题里,能够提供来自最前沿的学术性资源,有人觉得这样才既有思想也有学术。还有一些人常常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发表高屋建瓴的意见,好像在谈历史,其实,这些人未必真的能够深入中国,又未必真的拥有历史知识,却形成一定的气候,这也是与似乎有着学理资源的提供和历史论述的提供有关的。所以,如果你与他们一样讨论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相当的学理支持和历史论述,很难正本清源,说服读者。王元化先生曾经说,应该是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这话很对,我也觉得思想和学术应该有互相支援的关系。
不过,我写这本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当下思想论争所刺激的结果,但主要还是出于学术上的考虑,包括资料、角度和视野的考虑。我和余英时先生所说的一样,对于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所以,基本上还是讨论历史,希望从历史,也就是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角度来讨论这些问题。
二
《宅兹中国》有一个副标题,叫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虽然我这本书里也涉及亚洲、东亚、东海等等,但大体上我聚焦的是中国,就算是讨论日本关于神道教的争论、日本关于满蒙回藏鲜的学术史,讨论朝鲜的史料中的一些问题,其实也还是聚焦在中国的。不过,什么是中国?这是一个看上去普通,却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为了讨论什么是中国,不得不涉及周边,通过周边现在时髦一些叫他者的眼睛、资料、视角来看中国。比如说,17世纪以后,东亚诸国的彼此认同和互相排斥,就涉及民族、国家和历史;而民族、国家和历史的自我认识与他者认识,又会涉及一国和周边诸国的关系;而周边的话题,又牵出来如何理解中国和亚洲的关系;既然讨论中国和亚洲,又会讨论到疆域、族群和历史等问题。
你也许会说,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些问题吗?你看,有人讨论天下,有人讨论帝国,有人讨论多民族国家,有人讨论知识共同体。是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多少有些担心我的论述方式会被误解的缘故。现在的一些讨论,其实,常常是先引入西方的一些概念工具,用这些概念工具去重组中国历史、文献和资料,把这些抽取过的材料推导出一些宏大的结论。你知道,现在讨论想象的共同体、讨论帝国、讨论超越民族国家的区域研究、认同的政治,都是很时尚的,看上去他也是在讨论中国问题,实际上,这些论述多来自西方,而有时候讨论者的眼睛也瞟着西方,看看人家的反应。坦率地说,有的人不大有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背景和学术基础。用我们过去的说法,这叫以论带史,一方面会给国人以误导,觉得这是在讨论历史,另一方面它会把中国历史整编到西方的一些时尚大论述中去,让洋人觉得这就是中国。
我很担心。
三
你问我,我的论述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却又必须回答。
我自己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主要是通过两个历史的角度去讨论,一个是文献资料中所见的思想史,一个是关于这个问题本身的学术史,而且也许还会针对这些话题,逆着这些风气,重新进行论述。比如,这本集子里最早的一篇写亚洲的文章,就是有很强的论辩性的。因为当时我觉得,有的中国学者急匆匆地跟着日本、韩国学者,去讨论所谓亚洲文化共同体,或者亚洲知识共同体,也许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我记得那一年,在台湾大学开会的时候,就争论得挺激烈。我总觉得,如果我们对日本人从明治以来常常使用的亚洲一词不加检讨,对日本学界使用亚洲作为空间单位来写历史的学术传统不加了解,就会被一种抽取出来的概念误导。所以,这里首先需要的就是文献资料的研究和学术史的清理,什么是亚洲?为什么会从亚洲出发思考?为什么亚洲可以成为一个历史空间?中国为什么不太有亚洲的连带感而日本却有?如果仔细梳理日本习惯使用的亚洲这个历史概念,你可以看出,一方面日本从明治时起,关于亚洲研究或者东洋研究就伴随着现代性的知识背景,另一方面使用亚洲作为历史单位,也有日本的国家主义、扩张主义的政治意图。我当时的疑问就是,你怎么能把这些背景都剔除了去谈亚洲呢?这些问题都必须从学术史出发去清理,才能讲得清楚。
我相信,最近这些年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将是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中国与周边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如何相处的问题。我们已经遇到很多麻烦,政治上的麻烦,当然应当由政治家根据国际法去处理,可是你也可以看到,有人相当轻蔑历史知识却动辄讲历史,在这些问题上,既不会把历史疆域与现实领土问题分开,也无法讲让周边都接受的道理。可是,还有些学者虽然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意义,也特别想介入这些领域,但是,他们要么一下子就落入带有政治意识形态性的论述,不是学术立场的讨论,要么一下子就投入时髦理论的窠臼,拿了大理论大概念说一些空话。
四
再说一遍,我讨论的是学术意义上的历史,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现实,所以我想强调:第一,这些问题的讨论,应当是从有关中国、亚洲或者世界的认识的历史资料,包括中国和朝鲜、日本的历史资料中出发,把问题放在思想史脉络或学术史语境中去讨论,而不应当是从来自西方的理论预设下去倒着看历史,或者从现实利害的角度做提供证据似的历史论证。第二,我也不想从政治和策略,而是从历史和文化,也就是说,从中国的文化认同和历史渊源去追溯中国,所以我才会再三强调,在所谓认同的问题上,历史、政治和文化应该有适当的差异;同时,你也必须认清国家(祖国)、政党(执政者)和政府(王朝)的不同,而不是把认同和国家一锅烩在一起,让所有人都必须在这个问题上,一二一齐步走。第三,由于东亚尤其是中国的皇权,如同史华兹和林毓生说的是普遍皇权(Universal Kingship),不仅朕即国家,而且朕即信仰、朕即真理,所以,我强调国别史的意味,也强调历史研究常常很难摆脱民族与国家的立场,就像我这本书里提到的日本学者关于神道教、中国道教以及天皇制度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这并不是给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提醒历史研究者要小心翼翼地警惕这种不自觉的立场影响。所以,咱们一方面得承认,历史上的国家常常是流动的,仿佛罗布泊一样,空间有时大有时小,民族有时合有时分,历史有时整编在一起,有时又分开各成一系;但另一方面又得强调,在书写历史上,有民族、领土、认同的国家是要承认的,特别是在东亚,这个国家(其实国家往往只是政府)自古以来,是相当强有力地控制和形塑政治、历史和文化的。东亚国家跟欧洲国家很不同,文化控制和历史建构的能力非常强,所以,如果你简单地谈超越民族国家,恰恰会忽略对民族国家(尤其是专制皇权)的批判。所以,你要把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分清楚,你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论述,是理论的后设叙述,还是来自资料的历史论述;你的历史论述,是在批判这种高度的政治权力和集权的国家控制,还是论证政治一统和国家控制的历史合理性。
我觉得,目前有一些讨论,基本上不是在中国语境中讨论中国问题,如果真要在中国语境中讨论中国问题,那么,就要问:你是要从中国历史资料中展示出来的中国国家形成、民族认同、疆域变化讨论问题呢,还是通过一套舶来理论来讨论问题?你是基于当下的某种政治意图来讨论问题呢,还是没有预设地去讨论历史?如果要避免一种民族主义的论述,必须要考虑你的出发点,究竟是政治还是文化。
五
这本书,可能呈现的是我这十年来的一些想法。自从2000年写完《中国思想史》以后,我就开始想这些问题,我在序言里面说,这本书里的好些想法,是从《中国思想史》最后一节1895年的中国引发出来的,真是这样。为什么?因为1895年以后,中国被整编进世界、亚洲或者东亚的历史里面,你就不得不思考这些认同、疆域、族群等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原本好像并没有显题化,可是在1895年以后,这些问题都出来了,到了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政治、文化和经济在国际环境中的变化,它就越来越不可回避了。
很长时间以来我就有个想法,这跟梁启超的说法有关。梁启超说,中国历史有三个阶段: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我觉得,这个说法可以稍稍变通一下。的确,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想象天下的国家,所以有天朝观念,也有朝贡制度,这就是中国之中国;明代中叶以后,西学东渐,特别是晚清以来,便进入第二个阶段,逐渐变成时时事事以西方为尺度来打量中国,中国的好坏美丑都是在西方背景下讨论的,便成了世界之中国。这个阶段认识中国的尺度或镜子都来自西方,非苏俄即欧美,从晚清起,不是中体西用,就是西体中用,从五四以来,又讨论你是热的我是冷的,你是动的我是静的,你是唯物的我是唯心的,你是特殊的我就是普遍的,你是普遍的我就是特殊的;可是,现在是否应该增加一些观察的角度和尺度?可以从周边的资料、立场和眼光重新打量中国,我们能看到中国跟周边其实也有很多细微差异,也可以互相观看,这样,就成了世界、亚洲之中国。我一直很强调,千万不要以为所谓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就具有同一性,这其中是有差异的。有一次我在日本的飞机上看到《读卖新闻》编辑委员藤野彰写的评论,那时他刚刚从中国回去,就写了一篇社评叫作《相互理解从对差异的承认开始》,这话很对。我强调东亚诸国之间的差异,就是因为这能够帮助我们反过来清醒地认识中国。
所以,我一直建议推动从周边看中国,因为这实际上既包含了中国观即中国自我认识的改变,也涉及文化交流史研究方法的改变。我一直用一个比喻,说过去的文化交流史(常常也可以称为中外交通史)注重的是中外交通,而我们更注重文化互相观看和交流后的结果,就是过去讨论的是结婚,现在讨论的是生孩子。中国文化其实很杂,这是文化杂交的结果,我们不能老是觉得我们还在汉唐时代,只有文化输出,没有文化输入,也只有华夏文化,而没有蛮夷之风。所以我说,17世纪以后,其实朝鲜和日本,跟我们已经渐行渐远了。我特别反感把中国文化看成是单一不变的汉族及儒家文化,把孔子以来的思想看成至高无上的传统。其实,我们的传统跟我们的人种一样,早已混杂不清了。现在的人对汉、唐无限自豪,可汉、唐恰恰是种族混融的时代。三十六国九十九姓成了河南之民,渐渐又到关中成了京兆人,唐代首都长安好多人就是胡种。老祖宗们原本觉得,中国和夷、蛮、戎、狄,最好井水不犯河水,所以有《徙戎论》。可事实上中国仍是种族交错的天下,不要说李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刘禹锡是匈奴裔,元稹也是鲜卑后裔,更不要说李渊、李世民了。经过通婚,好多人血缘已经杂糅胡汉,所以陈寅恪说他们因为胡汉杂糅,才创造了唐代的空前之世局。
所以,我觉得也应当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虽然我在书里面强调,应当在历史中研究民族国家,而不是把历史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出来,要注意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分歧由来已久,不可以简单地说有一个同一性东亚,但是,我绝不是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只是希望,当你注意到亚洲诸国特别的形成史,亚洲诸国形塑文化和政治的强烈的国家意识,当下亚洲诸国之间由于文化认同崩溃而彼此警惕和戒备的时候,要注意到在历史叙述中国家的存在。所以,我也支持在学术研究中,不要只看到国家,不仅西域可以像一个地中海,东海也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历史世界。我觉得正确的态度是,一方面看到简单地提倡超越民族国家是一种忽略历史的想象,另一方面要注意,简单地强调国家的独立品格会导致对国家意志警惕的丧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