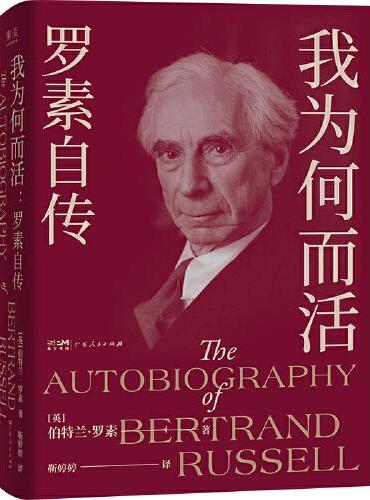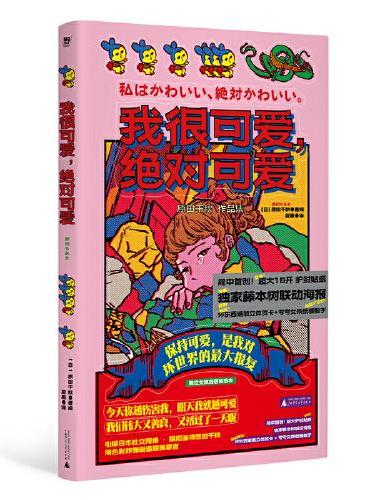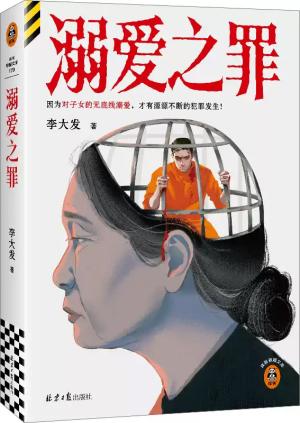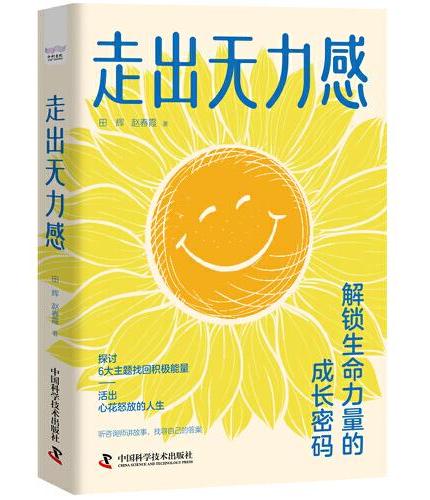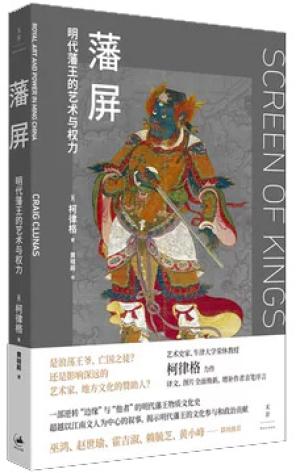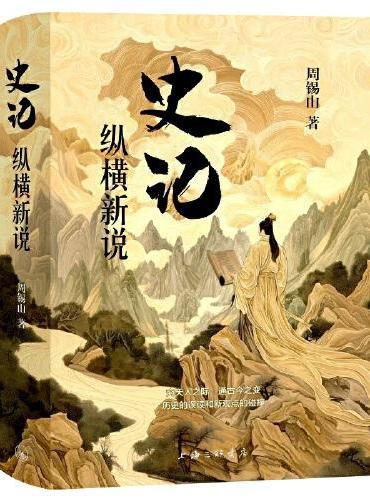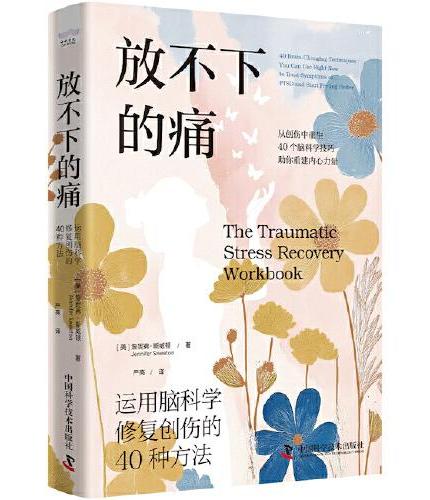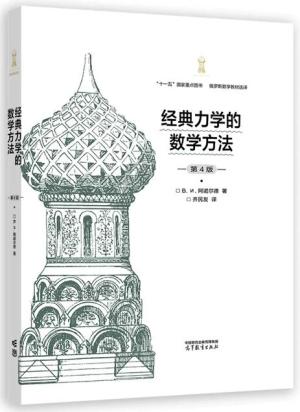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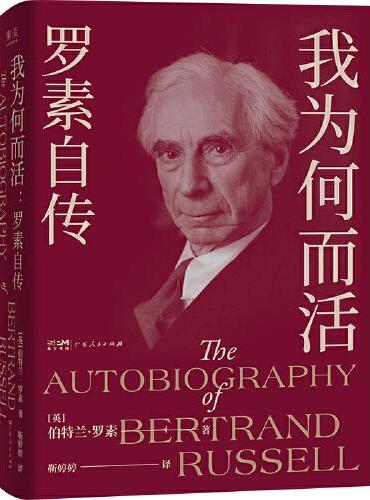
《
我为何而活:罗素自传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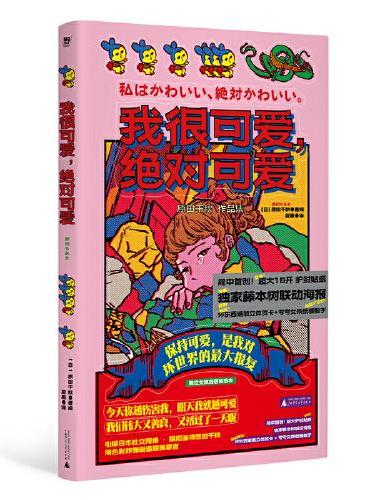
《
我很可爱,绝对可爱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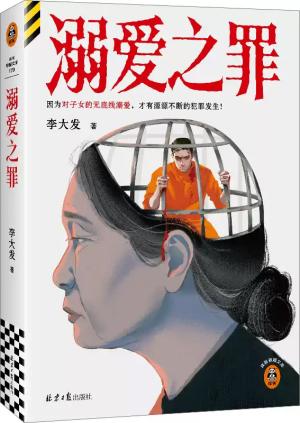
《
溺爱之罪
》
售價:NT$
25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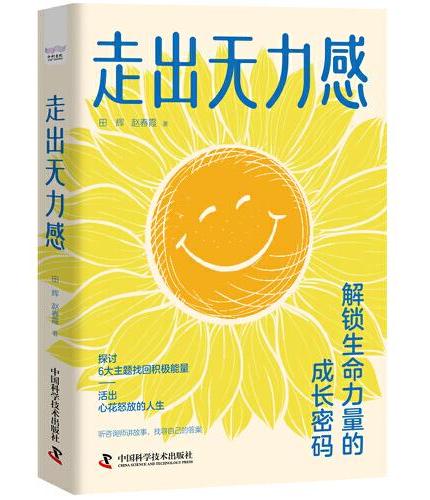
《
走出无力感 : 解锁生命力量的成长密码(跟随心理咨询师找回积极能量!)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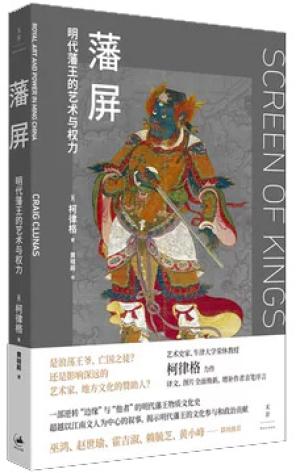
《
藩屏:明代藩王的艺术与权力(柯律格代表作,一部逆转“边缘”与“他者”的明代藩王物质文化史,填补研究空白)
》
售價:NT$
5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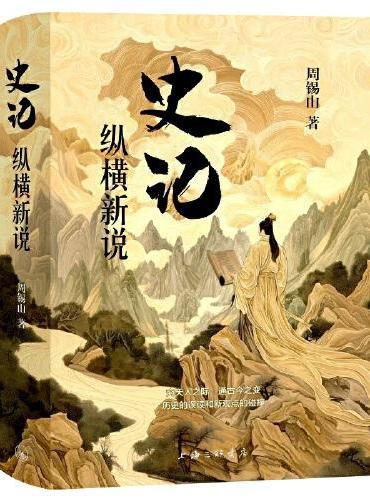
《
《史记》纵横新说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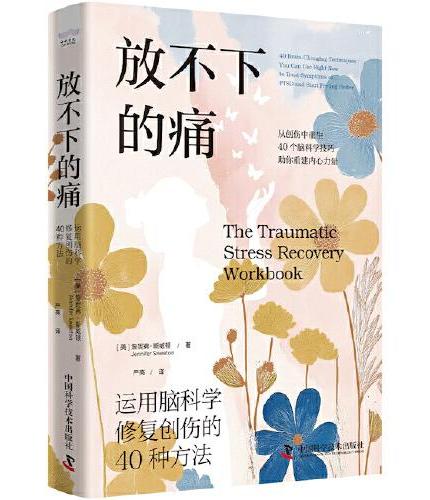
《
放不下的痛:运用脑科学修复创伤的40种方法(神经科学专家带你深入了解创伤背后的脑机制,开启全面康复之旅!)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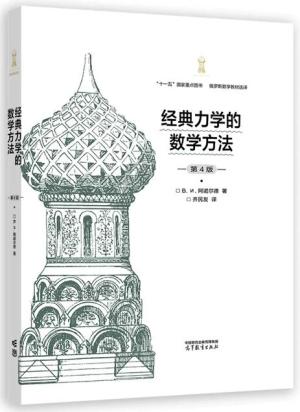
《
经典力学的数学方法(第4版)
》
售價:NT$
403.0
|
| 編輯推薦: |
|
王祥夫的作品精于叙事,善于铺陈,浪漫恣肆,传神写意,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弱势群体的百态人生,成功地刻画出当代中国北方城乡中处于政治与经济边域地带形形色色的小人物的群像。本书精选了王祥夫的几篇精彩的中短篇小说,充分体现晋军文学的实力和影响。
|
| 內容簡介: |
|
本书选取了王祥夫早期创作的多篇作品。这些作品对一些众所周知的合法性历史进程进行了重新的分析和反思,为我们对快速版画的世界进行多向度的考察和再认识提供了事实可能和文本依据,对我们解读王祥夫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
| 關於作者: |
王祥夫,1953年6月出生,辽宁省抚顺市人,现居山西大同。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大同市作家协会主席。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曾任《羊城晚报》《北京日报》《今晚报》《文艺报》《光明日报》专栏作家。
著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共三十余部。代表作有《上边》《归来》《浜下》《榴莲榴莲》《愤怒的苹果》《顾长根的最后生活》等。其作品多次被国内重要期刊选刊转载,部分作品被翻译到国外。小说《西风破》《驶向北斗东路》等作品被改编成电影。
|
| 目錄:
|
西牛界旧事001
永不回归的姑母031
沙棠院旧事074
非梦113
拾掇那些日子151
守望大草垛163
尘世180
我们呼啸着奔跑到黑暗之中 金宇澄230
王祥夫创作年表233
|
| 內容試閱:
|
在西牛界插队那几年,日子过得寂寞极了。西牛界离县城太远,坐上拉粪的牛车慢慢晃去,要大半天。四野无人,站在车上撒尿,尿水便湿湿的一道在尘土很厚的路上拉开,很快就干了,翘成一个壳。两边的土山是荒的,静静的,几乎什么也不长,只长沙蓬,毛茸茸的像野生灵,在山缝儿里缩着。知青们平时很少进城,要去就是一大群,像去打仗,澡堂一下子,理发馆一下子,电影院一下子。洗完澡,脸红红的,软得发呆,在街头笑嘻嘻坐着看女人。日子过得太寂寞了,又太苦,除了几顿饭,真没什么意思。
那几年的生活,最令人回忆的是夜晚。和我住一个宿舍的一位北插,叫窝脖儿。七一年,学校不知怎么看准了他是澡堂的料,分他到澡堂去搓泥垢,他一想那许多热腾腾、赤条条,出来进去老的少的,便马上红了脸死也不去。竟愿下来插队!记得他有一支俄式双铳,知青们便找来火药拿出去乱放,你一下,我一下,天上,地下。有一天,终于把队里在甜菜地埂找烂叶子的花犍牛嘭的一声打出肠子,白花花、热腾腾的一段。牛老汉骂着又把那段肠子给填进去,后来伤口竟长住!阴天下雨,那花犍牛就没完没了舔那地方。痒哩,狗日的!牛老汉说。用铁牛梳给它梳,用指甲哔哔地把梳下的牛虱挤死,牛虱像一粒粒黑的芝麻。有时候,那双铳竟能打到东西,那便是众人的节日。男女知青和西牛界的土著们都来。油腥汤水,竟吃出十分的滋味!然后就笑闹一气,说些惊人的荤话!
有时候夜里又要耍牌,外边多半下着雨或呼呼刮着老黄风。风打着窑窗。男的一家,女的一家。热炕上你靠我我靠你地围坐上。两幅黑得冒油的老牌轮番搬来。男的赢了,女的要从男的裤裆下钻过,她们也乖乖钻。钻时身子极小心地伏着,男的却尽力把身子往下压,故意大惊小怪:碰着了!啥?手震弹!。
手震弹的震在西牛界这里念真。狗日的小日本的飞机扔下颗瓮大的手震弹炸塌了半个崖!。
西牛界是老区。村后山脚那堵墙上还写着驱走日寇,当兵为国。村上不少老人还能讲抗日年间的事,比如瓮大的手震弹者流。
男插一说手震弹,女插就笑骂起来,就一跃而起,反倒不夹一丝邪念。女的赢了,也照样要让男插钻。男插也嘻嘻哈哈地钻,把身子反而弓起来,像猫。女插就骂,就笑。把牌噼噼啪啪一收,不打了。去睡觉。洗脸盆叮当响一气,水哗哗往外泼一气。第二天一开门,外面一片雪光耀眼;山也白了,塬也白了,草垛白了。雪还在纷纷扬扬
那样的夜晚是令人怀念的,一张张给太阳熬煎得发黑的笑脸,热灶里烤的沙山药,穿大皮裤的车倌们,光脚儿听房的光棍儿们
西牛界离我是太遥远了,三百四十多里!还不算上走的那段路。但夜里一想起它,它又离我很近,近在心上!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时值夜晚,外面正刮着风。西牛界该是怎样一片爽朗的月光啊,还有这午夜时分像有人轻轻走动的秋风
瞎貉
秋天的太阳朗朗地照在坡地上时,倘若坡上突然蹦起一只挺肥的野兔,或出现一只用后腿立起来的小田鼠,我便总会想到瞎貉。瞎貉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我至今不清楚,但我总以为它是一种视力极差的小生灵。
我刚去西牛界,顺着那条弯弯的沟进村,正是大冬天。
娃们正在井畔上耍冰,鼻涕拖老长。看见我,就都围上看。
唏呀!又来个瞎貉!孩子们嚷。什么是瞎貉,想一想,还是不懂。
又过了好长时间,那天我去冷得冒气的井畔上洗脸,眼镜在饮牲口的青石槽上搁着,洗完,一摸,没了。我又看不清,就听得有人在身后嘻嘻地笑。听声音是个乡下婆姨。呀咦!声音抑扬顿挫,很好听。
我朝她要,那女人咦!咦!地和我转圈。我一下绊在她的木桶上,火了!她才跑过来,把我从地上拽起来,我看见她那双又赤又红的粗手。我带上眼镜,才看出这是个和我差不多年岁的女人,瘦瘦的,但仍不失俊秀。她弯腰打起水来,嘴里喷着一团团白气。一长绺乌黑的秀发垂下来,像乌鸦翅膀,遮半个白生生的脸。打好水,她直起腰来,一掠那绺头发,呵呵冻红的手,咯咯笑起来说:瞎貉也有这物件,平日不戴。她又瞅瞅我说,人家不像你这洋歪的劲儿。她又捂上嘴笑,人家瞎貉过年戴一次,写对子,猪羊撞圈五谷丰登斗私批修。正月十五村里有戏,看戏哩,照看台上的二毛眼才戴。还有一次哩她不说了,她笑,捂着嘴。另一只手搁在衣襟下暖着。我看见她腕上的一只镯,擦得很亮。她问我从什么地方来,好像吃了一惊:呀咦大同远!她不再说什么,唏唏溜溜提着水走了。天真冷。她穿一件蓝底白花棉袄,有补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