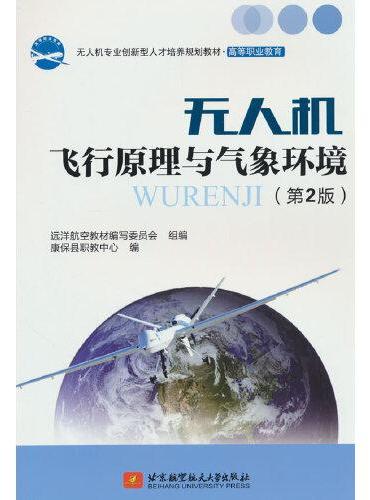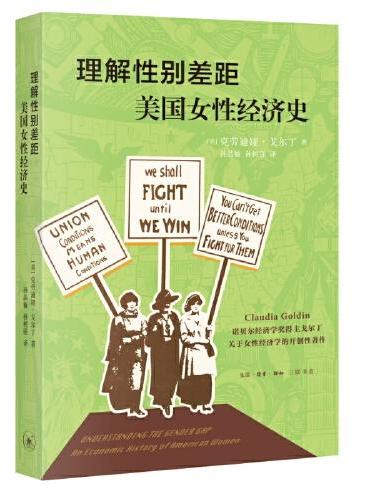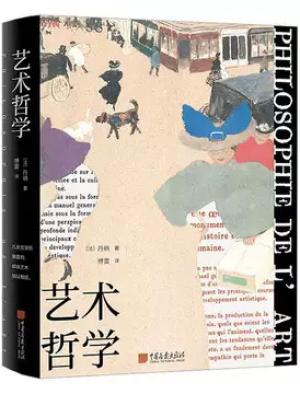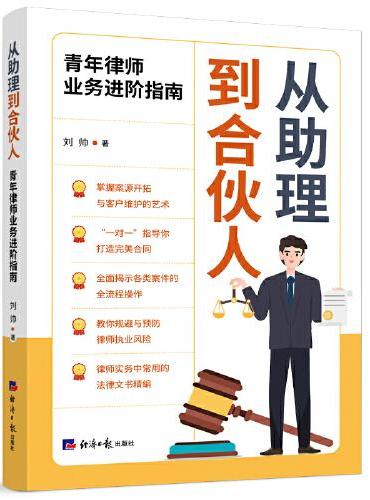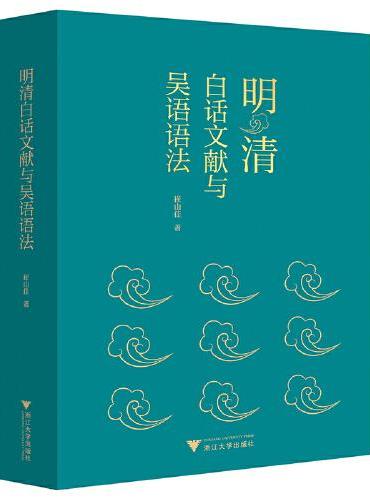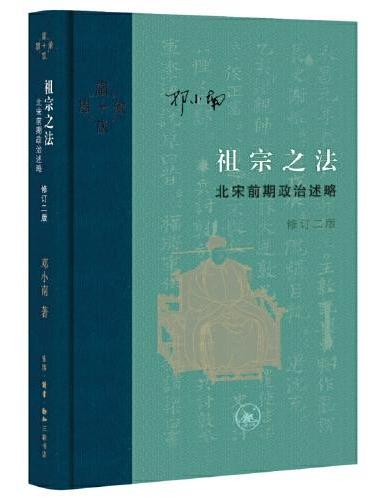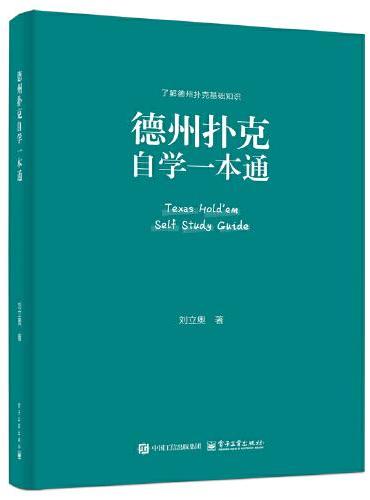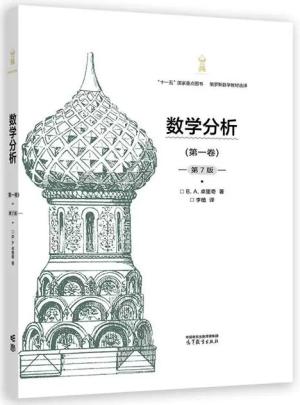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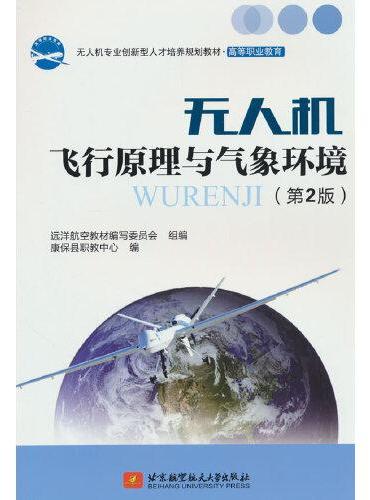
《
无人机飞行原理与气象环境(第2版)
》
售價:NT$
14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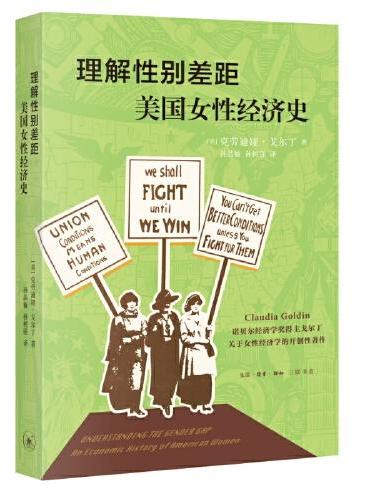
《
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经济史
》
售價:NT$
4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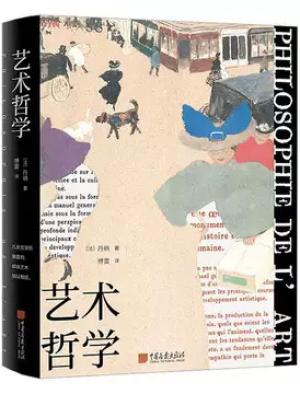
《
艺术哲学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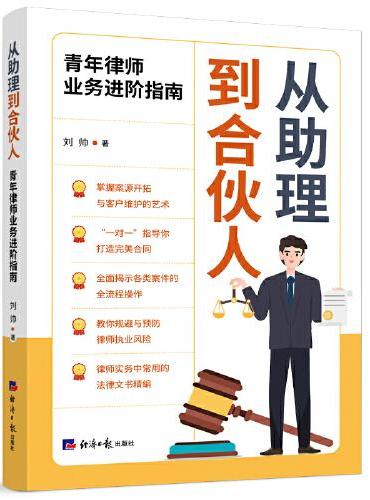
《
从助理到合伙人-青年律师业务进阶指南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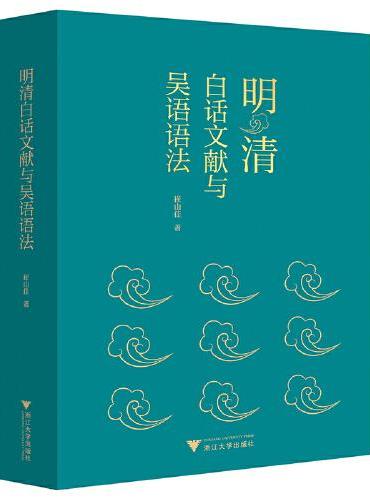
《
明清白话文献与吴语语法
》
售價:NT$
1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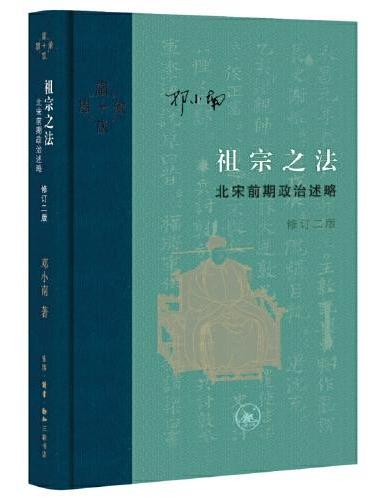
《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二版)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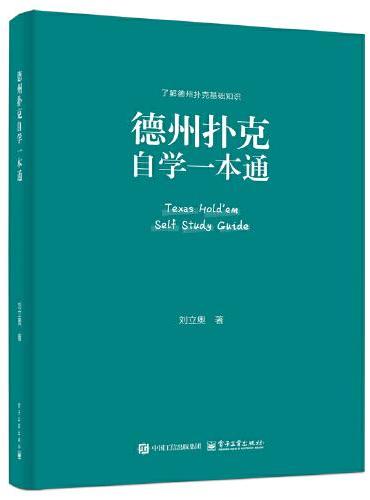
《
德州扑克自学一本通
》
售價:NT$
25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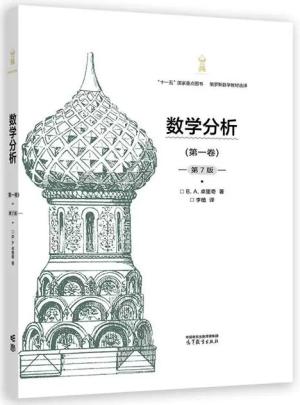
《
数学分析(第一卷)(第7版)(精装典藏版)
》
售價:NT$
454.0
|
| 編輯推薦: |
这可能是互联网时代很值得期待的汉语文字。
美国《时代》推崇的作家李傻傻,沉寂十年重新写作,告诉我们好文字依然存在。
|
| 內容簡介: |
李傻傻(蒲荔子)在沉寂十年后重新写作,带给我们对于好文字的信心,以及爱这个残缺世界的能力。所有我们经历过的人和事,见过的光,看过的书,最后,都是空虚,都是光荣;最后,都会在时间里足以令我们感觉到虚荣和满足。
最后,爱这个世界的能力,才是我们的虚荣。
这就是蒲荔子这本书要说的,只有一句话:爱是空虚,爱是光荣。
无论写女人,写朋友,写青春,写阴暗的心理、窘迫处境、温暖细节,都不过在说一个字:爱。
30个故事,30种情感,30个回忆的出口,不过是在说一个人爱这个世界的可能。爱她的白天,也爱她的夜晚;爱光明新鲜,也爱自己暗黑的阴影。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但只要你有过青春,有过记忆、疼痛,尤其是有过爱,
那么,让这些故事带领你回到过去不可磨灭的生活;让这些故事证明,好的文字依然存在,她打动人心,并且一直打动。
书中30篇故事,不仅保留了作者流传甚久的成名作《火光》《女人》《被当作鬼的人》《虚构:铜鼓潭》《打口古都》等,还新增添了这十年中新写的篇章,如《不知道有没有人给她写这样的情书》《我见过广州的白天和夜》等。在一本书中,我们看到从李傻傻到蒲荔子的成长,也看到一代人的青春纪念,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自己。
名人推荐:
一直很期待蒲荔子的新作品,他的文字混合了潮湿的雾气和粗烈的蛮力,有着浑然天成又出人意料的意象;他写生活的暗与黑,疼痛与放纵,笔触所及,又有写作者难得的坦率和真诚。
——苏童
蒲荔子的成熟和自信建立在更为经典的阅读之上。他的故事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充溢着张力、迷惑和玄机。他的文字充满弹性,永远带着暗示意味。
——马原
“我们这种人,无论怎样,最后总觉得要写点东西。”荔子这句话让我等了很久。好的文字,时间越久越见光彩;这本书里很多篇章写在十几年前,今天看依然无比动人,甚至更为动人。
——蔡崇达
媒体推荐:
人生的一切美好部是虚荣——空虚和光荣,于是文学有了存在的理由:见证多么光荣终是空虚,亦见证纵然空虚仍是光荣。李傻傻的作品是有力的双重见证。
——周国平作家
一直很期待蒲荔子的新作品。他的文字混合了潮湿的雾气和粗烈的蛮力,有着浑然天成又出人意料的意象;他写生活的暗与黑、疼痛与放纵,笔触所及,又有写作者难得的坦率和真诚。
——苏童作家
蒲荔子的成熟和自信建立在更为经典的阅读之上。他的故事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充溢着张力、迷惑和玄机。他的文字充满弹性,永远带着暗示意味。
——马原作家
“但无论怎样,我们这种人,最后总是觉得要写点什么。”荔子这句话让我等了很久。好的文字,时问越久越见光彩;这本书里很多篇章写在十几年前,今天看依然无比动人,甚至更为动人。
——蔡崇达作家
|
| 關於作者: |
蒲荔子,曾用笔名李傻傻,出生于1981年11月,湖南隆回人,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
2004年起陆续出版长篇小说《红X》、散文短篇集《被当作鬼的人》、作品集《李傻傻三年》等。
2005年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幽灵作家”。2015年和朋友创办中国精选美宿平台“朋友家”,并重新写作。
|
| 目錄:
|
序言
爱是空虚,爱是光荣
第一辑
我最难忘的一双女人的手?
我最难忘的一次“偷窃”
不知道以后有没有人给她写这样的情书
诳语
第二辑
火光?
妈妈
我把对一个女人的思念写出来
第三辑
最让人感到满足和安慰的
超越爱情的永恒之死
女人
第四辑
这样??
无名之地?
被当作鬼的人
虚构:铜鼓潭?
闹马山??
云
飘满鱼的天空?
溺水记??
两个少年
一个喜爱出走的朋友??
鸡毛鸭毛
第五辑
一只懒鸟的神庙??
一九九三年的马蹄
下半夜??
三百块和一寸黑白免冠照片
他们去抢劫??
西安、流行病和青年??
打口古都
第六辑
我见过广州的白天和夜,和每一刻??
苏东亮退学一事
我有一个老师??
脸红的流氓
附?录
如果有一天,我在平庸面前低了头,请向我开炮
|
| 內容試閱:
|
序言
一
二○一四年,我做的很多事都不记得了,不记得其中有什么情绪。有一件小事还很清楚。
那时我和朋友欧亚做第三届南方国际文学周,邀请了小说家朱文来分享。其实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就不写小说,改拍电影了,他来分享的也不是小说,而是新片《小东西》,但我还是愿意叫他小说家。
毕竟,除了美艳妖娆的姑娘,没有几个男小说家是我想见的;如果是导演,就更没有了。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但我觉得,看过朱文的小说的人,应该不会不想见他,那个把日常生活写得波澜起伏,把平凡者写得沟壑密布的写作者,那种要胀破的才华,还有荷尔蒙的气息、欲望和生命之中的光。就像看过纳博科夫《洛丽塔》的人不会忘记这个开头:“洛丽塔,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同时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看过《尖锐之秋》,看过《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看过《段丽在古城南京》,看过《看女人》,看过《我爱美元》……人们不会不想:靠,这个作家在哪里啊,真想见他一面。
最后他来了。因为是组织者,忙得满地鸡毛,除了在酒店打个照面,作为一个迷弟,都没空去听他说了什么。走的那天,我在他上车前请他签名,他签上“幸会 朱文”。我记得那天的情形是:君悦酒店的空调很冷,其他人像空气一样,我忘了是谁。那天我很紧张,说话有点发抖。
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那本《金蔷薇》里写了俄罗斯的诸多作家,很多都是一副迷弟的模样,诸如“我们都生活在他的天才的轻微的反光之中”的巴别尔,诸如写出“那么,放大胆子/永远和我在一起”的亚历山大·勃洛克。但当我按图索骥去看这些作家,很多时候并没有他所描述的那样战栗的感觉。我想是因为,除了被翻译丢失的那部分生气,更重要的是,我们并不是帕乌斯托夫斯基本人,因此我们在书里看不到他所沉迷的事物;令我们沉迷的,是帕乌斯托夫斯基,那个穷其一生在灰烬中捡筛出金粉铸造一朵金蔷薇的作者。
除了杀时间之外,艺术的功用,不过就是在世界之外找出自己没有发现的同类,找到别人说出自己未能描述的灵魂。
因而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重读朱文的书,每一次除了吃惊并惭愧于他的感觉要刺破空气的才华,我想更令我沉迷的是书中那个无处不在的人。我感觉那是自己,或者另一个我,或者我的另一个时空。无聊又想着改变,欲望膨胀却又不想行动,心存石破天惊的妄想却又拼命安于现状。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承认自己是这样一个人。又花了很长时间,我才稍微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我们需要面对自己全部的真实。严格来说,很长时间我都不认识自己,我作为各种角色在各种空间行动,经常有那种事后追悔莫及的想法;我觉得应该有一种洗涤剂,把我内心阴暗的部分洗净晾干;应该有一个完美的模具给我,使我追逐靠近,变成某一种人。庆幸的是,这么多年之后,我终于敢于真诚地面对自己的虚荣、怯懦、妄想、粗暴、冷漠、骄傲,以及我暂时未能想起的一些毛病。这并不是因为我变得自暴自弃,而是恰恰相反,我觉得这些不再是一种毛病而是一种存在,每种存在各有比例,每种比例总在变化,每种人最后总是一个独有的配方。我想做的是看看自己内心的构成是什么,它有多亮以及有多暗;我不再想取悦那些不能理解我的人,不再想为莫须有的目标修改自己的信条,也不再为一些事失落,而是为所有的经历感到庆祝。
二
常常看的另一本书是《聊斋志异》。蒲松龄在开篇《聊斋自志》里最后几句说:“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一介穷书生,天天招呼路人喝茶,收集鬼故事,估计被不少人视为怪物,可是他觉得有知音,在梦魂所历,在冥冥之中。我常常想着改动他几个字,最终的结果当然是不可能。
到三十五岁,我才明白自己究竟要做什么,我承认就是这种虚荣的事:与寂寞为伍,与黑暗同行,就是创造的刺激。就像爱是空虚,爱是光荣,就像爱是与生俱来的虚荣让人垂涎,作家们创造出了我们不能描述的灵魂,他们在山顶等着我们去看风景,我想和他们在那里碰杯——怀着这种想法,我在山脚徘徊了很久,现在准备上路。我想我会成为上山路上的一块砖,或者路边白骨及草丛,但一想起山顶的风,我就觉得高兴起来。
这么多年,我已经完全知道写作是个什么玩意。大部分时候,它令你抓耳挠腮,抽烟喝酒无济于事,你想着去跑一身汗,去做一次爱,可是都不能解决词穷这种问题。当她终于来到,可能你却睡着了,于是你只能梦见,第二天起来早已忘得干干净净。只有当她真的恰巧来到的时候,那种幸福的感觉,足以抵消这一切等待。
有一次,写到半夜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突然“啊”地一声大叫,惊醒了睡梦中的家人,吓得他们不轻;有时候和朋友喝酒,我突然消失了,因为她突然不请自来。慢慢地,你大概会知道她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因此你必须在那时候做好准备,严守你们之间的纪律,不然她就可能消失很长时间。
我浪费了最 好的时光,并且得到了浪费的快乐,现在我看看能不能有另外一种挥霍。我曾经迷恋夏天的篝火,和陌生姑娘们一起喝酒,围着火堆跳,像是在做一些把自己投进火里的准备工作,现在我准备走进去,走入火中。
没有这种更远更能唬住自己的远方,就感觉迈不开步子。也许我这是在骗自己。可是谁能说清楚,闪光的记忆中有哪些是自己制造的幻象;面对迷途,和头顶星空一样浩瀚的迷途,我们除了屏住呼吸告诉自己未来一片光明,又怎么压抑住慌乱往前走。
三
这本书很多文章写于二○○○~二○○四年,写于西安那个昏暗的6103宿舍和同样昏暗的图书馆。重看自己这么些年的零碎文章,就像看一个人的延时摄影,看自己内心秘密的局部细节图。像看别人的成长一样看书中的人,我常常觉得这个人很可笑,可是不得不承认,这个可笑的人就是我,就是此时此地。我想着什么样的人会在梦魂之中看到他自身的影子,就像我在那些莫名其妙的书中看到自己一样。
感谢有人还等待这本书。献给所有爱这个世界的人,你是我的虚荣。
重新写新小说《虚荣广场》,预计会有很多困难。感谢有人依然期待这本书。
还有很多感谢不一一具名,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我的感觉。
“但作天籁,不为好音。”我已在书中暴露所有的黑暗和光明,你们已经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蒲荔子?2016年10月9日
后记
如果有一天,我在平庸面前低了头,请向我开炮
“在悲伤与虚无之间,我选择悲伤。”
——《筋疲力尽》
一
有一次给人推荐一本书,叫《四十大惑》,差不多是二十岁那年看的了。作者是默默。
没想到十几年之后我对这本书依然印象深刻。大概是因为书里那个醉生梦死的人,属于让人喜欢的坏蛋。更可能的原因是:大学时我经常引用里面的句子和女网友聊天,一来二去就熟了。
整本书的三观在普通人看来有点问题,但普通人的看法有一些是不对的。这本书的大意是,惑是必然的,比起浑浑噩噩、蝇营狗苟,还不如醉生梦死。当你想醉生梦死时,不要影响别人;当你不想醉生梦死时,你要让自己活过来。
我曾经历很长时间的浑浑噩噩,也有一段醉生梦死的日子。
随波逐流,挥霍。彻夜饮酒。
逆流将我击退,而我美其名曰顺其自然。
我几乎放弃了写作,每当有人问,就说,以后再说。配上个傻瓜似的笑脸表情。
感觉每天都很忙乱,其实每天心里都很慌乱;感觉一切都很平静,其实每天都想一走了之。
不过,除了到书里去寻找莫须有的答案,我没咨询过我该怎么活的问题。这个世界上有人可以让你活得很惨,但很少人能代替或者指导你活得更好。
因为事实证明,悲观很容易传染,乐观却难以复制。
一个快乐的人看到悲伤的电影,会哭;可是一个悲伤的人看到快乐的电影,并不一定会笑;一个积极的人看到热血的话,会沸腾;可是一个悲观的人看到热血的话,会觉得说这话的人是个傻帽。
直到有一天,我想,既然只活一次,我总该做点什么。
二
其实想过很多次,并不是只有这天想了。暗暗下定决心然后又抛诸脑后这种事我很拿手。
把朴树那句歌词“我活得不耐烦,但是又不想死”改改,就能形容这种现象:我过得很不爽,但是又不想改。
只有这次,想了之后,我列了一个清单,列了20多项我想做的事。可能还不止这个数,因为我本来要求自己想破脑袋也要列100项的。
一项项删除,最后剩下两项:写作、做一个有逼格又能赚钱的产品。
剩下的这两项,对我而言是一样的:暂时我将失去收入;我将投入持久的热情和精力;我要用力创造能让自己欣喜的东西。
总之,“仅仅一次,就可以干得一场完美。”(这不是我说的,是戈麦的诗)
不同的是,写作是一个人加一台电脑的事,而后者需要一帮志同道合的人。
在搞清楚要怎么取舍前,我曾经尝试两件事一起做。每个晚上,写完5000字后,换个频道,做APP原型。就这样分裂了1个月,写了5万字,再也分裂不下去了。即使把所有网线都拔掉,也难以静下心来。
我想我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我只能专心做一件事。
要么专心做喜欢的,要么专心做最想做的,我想我应该选择后者。
三
像深夜写小说一样,我在深夜画出了这个APP的原型。我想做更酷更有趣的社交民宿平台,比现有的任何一个都更酷更有趣一点。
泰戈尔的《飞鸟集》里有句诗:“我的地球,我登临你岸像异客,我住在你家像房客,我离开你家门时像朋友。”——我给这个APP起名叫“朋友家”。
因为我要找到那些自由的人,那些美好的房子;我能想到的最 好的住宿,就是“像住在朋友家一样”。
离开待了11年的报社,第一次做一个产品经理。就和第一次写小说差不多,大部分时候在模仿。但感觉像遇见一个陌生姑娘,她对我解开上衣的三颗扣子,开启了一个足够神奇的世界,足够让人产生一种被幸福地吞噬的感觉。
常常在深夜,我一个页面一个页面地翻看这个初生的东西,就像灯下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地看喜欢的女人。虽然那时候它其实长得挺丑。比现在你看到的还要丑一些。
幸运的是,它被铂涛集团郑南雁先生看上了,还帮我召集了一帮愿意为之努力的朋友。
四
世界上有那种唯我独尊的写作者。《麦田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或是“雷普利”系列小说的作者帕特里夏·海史密斯,都只是安静地写作,不愿在公众面前出现。
而我,其实希望得到大家的赞赏,私下的或公开的都可以。
被批评会脸红,被赞扬一样会脸红,既然都会脸红,那还是努力被赞扬好了。
你奋力前划,总有逆流斜出将你击退,但一切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此,在于创造的刺激。这种刺激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别人对你所创造的东西发出惊叹:“啊,竟然可以这样!”
那些对任何创造都没有感觉的人,不会发出这种惊叹,就像一个悲观的人不会对落日惊叹一样。
五
俞心樵有一句诗:“在我的祖国……只有你还没有爱上我。”我最初很希望这样的奇迹发生,但现在反而不急了。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会真的爱上另一个人,所以只有很少的人会看完这篇文章,更少的人会受好奇心驱使,下载“朋友家”这个APP。
这样正好:我们只需要那1%真正爱我们的人,而不需要那99%看上去热情的过客。
写到这里,我有点激动。就以凯鲁亚克《在路上》的结尾来结束这篇文章:“我要再和生活死磕几年。要么我就毁灭,要么我就铸就辉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在平庸面前低了头,那么请向我开炮。”
蒲荔子?2016年3月10日
文摘
我最难忘的一双女人的手
一九九九年,人们所说的“冬天已经来到,春天还会远吗”那时候,我在湘西南喜欢一个女孩。
有一个下午,我走进奶奶家的木板房子,发现屋里真黑。灶台边却有一双很亮的眼睛。那个人身子小小的,灶火的红光照在她脸上。我问坐在一旁的姑妈:“这就是樱子吗?”姑妈笑着对小姑娘说:“叫哥哥呀。”
在此之前我见过樱子几次。那时她很小很小,但是她的眼睛很大很大,有一对罕见的单眼皮。我跟她说:“有一次在堂屋里,我轮流背着你和你弟,满屋子跳,像只袋鼠。”她咯咯直笑,又说,一点也记不得了。
又问她多大。说是满十一岁,吃十二岁的饭。一九九九年冬天的最后几天,阳光像一群毛茸茸的小鸡在资江之滨那个小城的各个角落跑。我的手却是冰冰的。只是因为我的手一到冬天就很冰。在街道与街道之间,我拉着樱子小小的手,她的左手放在我右手的手心,有奇异的温暖。我在近乎金黄的河边反复说:“你不要放,一放我就冷了。”樱子睁大了双眼,也许她认为我的手不应该像冬天的江水那样冷得不像个样子。但是她的手还是如我所愿地抓得更紧了,她一边摇晃我的手臂一边说:“你的手为什么这么冷呢?我回去以后,你怎么办?”我说:“走,我带你到山上去玩。”
山是县城背后还没被挖开的山,还很胖的一座山。山上有很多树,还有各色野花野草。山深处草色很青,虫子安静地待在自己的领地,春色关不住。不过高高的树的枝丫上仍然什么也没有,朝天伸出硕大的手臂,天上待满了动物。我们穿过一大片丛林和茅草,来到一小块草地上。樱子抱着沿途采来的野花,让我给她编个花冠。我依言照办,花枝上的小刺刺破了我的手指,一抹淡红的血印在白色的花瓣上。我把那些小刺一个一个弄掉,她问我疼不疼。我说:“不疼,你呢?”她说:“我也不疼。”她问我的时候盯着我的眼睛,眼神清澈得很。我笑了一下,很累地躺下。她把小小的头靠在我的臂弯里说:“哥哥,你看那儿有一只鸟。”我朝她手指着的方向看,那里什么也没有,但是有些云在飘动。我摸到她脖子上有根细线,她说刚才真的有只鸟经过那里,不过一下子就不见了。我问:“这是什么?”
“这是一根线。”她说。她把那线解开。那是一根红线,勾着一个小小的玉坠,散发出浅蓝色的光。她爬起来把那东西系上我的粗脖子,勒得我很舒服。她说:“哥哥,你的脖子怎么这么粗啊?”我感觉冬天忽然一闪不见了,像那只鸟。看来春天打算在这里住下,打算在我们身边修一座小茅屋。当然这是后话,当时的情形是我在樱子的手心上画来画去,问她:“暑假还来吗?”樱子咬住她的而不是我的下嘴唇,出神地偏头思索,说:“不知道。”
我们下山时,发现路消失在杂树野草丛中。只听见各种声音在树外面响。我跳下一堵不高的山崖下去找路。路找到了,路口就在我膝盖跪下的地方。我把膝盖碰在一块尖石上,血流出来,裤腿红了。我把樱子接下来,樱子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嚼一把茅柴叶子,嚼成糊状了就糊上伤口,血神奇地止住。我觉得她的泪有点多了,影响了她眼睛和脸庞的美,就给她把泪水擦去,我觉得她唇上的绿色汁液颜色有点深了,就过去尝尝,我说:“真苦啊,樱子。”樱子笑了。
第二天她就走了。在车站我拉过她的小手亲了一下。姑妈看到了,樱子的脸飞起红云。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应该可以猜到,那就是开学了。在这一年里,我很想念樱子。我记起了日记。每天花一些时间想她我觉得很不够,就记起了日记。还是不够呀,我必须让她知道我想她。我按她给我的地址写了三封信寄过去,我每天去一趟收发室,但是并没有收到她的回信。后来我才知道她把给我的信投进了邮政局的意见箱。在上述情形下,我想我必须见到她。
我悄悄摸黑起床,清早搭上去她那里的汽车。
我从来没有去过湘西。姑妈家会在哪里?我只想见到樱子,于是去她的学校。在车上我看见放学的学生背着书包在路上打闹。天色渐黑。我有点伤心。又担心。站在他们学校门口,里面的操场空空的。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儿走。这时,两个小女孩走过我的面前。其中一个打着伞,我没有看清她的面容。我看着这个拿伞的小女孩的背影,心想那真的是樱子吗?我跟着她们两个,穿过了两条街,来到一个斜坡上。这是这个小镇最后一条街了,透过层层叠叠的房子,可以看见去年收割过的稻田。我试探着轻轻叫了一声“樱子”,她转过头来了!我跑过去举起她小小的身子,她鞋上的泥巴高兴地跑到我的裤腿上。
同行的小女孩说她先走了。樱子紧紧拉住我的手,说:“哥哥,你怎么找到我们学校的?哥哥,你的手又冷了。”路边一群一群放学回家的学生看着我们,我心里只想着我的小樱子,因此对不起我无法告诉你那些学生中的女生长得如何。
甚至那个湘西的小镇是什么样子,我都记不清楚了,只觉得十分亲切,仿佛不是第一次去那里了。樱子陪我来到集市,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我听她背课文,背的是那篇《武松打虎》。樱子用她好听的声音对我说:“店家,筛三碗酒,切二斤熟牛肉来!”
但是我只这样了一天,就不得不回去。姑妈说:“高三了,你怎么能跑这么远出来玩呢?”我不知说什么好。樱子送我到一条叫渠河的河边,说:“哥哥,等你再来我带你到这里来玩。”
现在两年没见到樱子了。一九九九年冬天我曾经告诉樱子我很喜欢她。不管在我身上发生多少游戏,这总归是句真话。现在,二〇〇一年的冬天到了,我的手又开始冰凉冰凉,这使我很不舒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