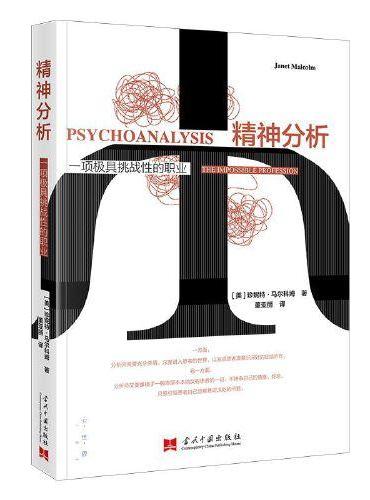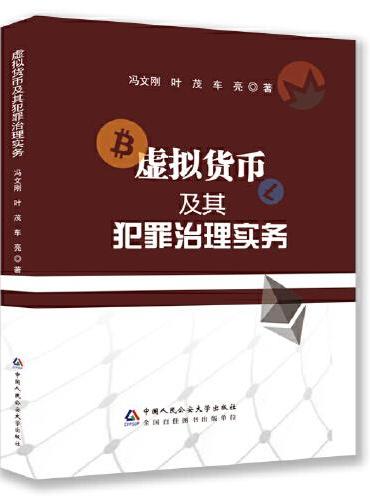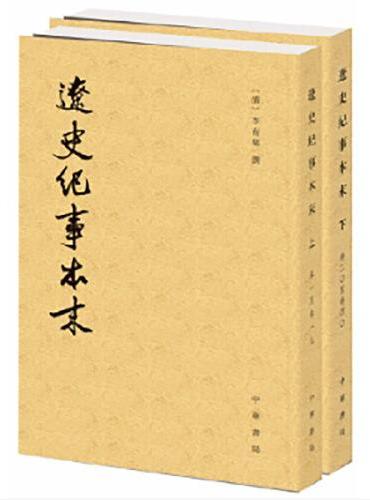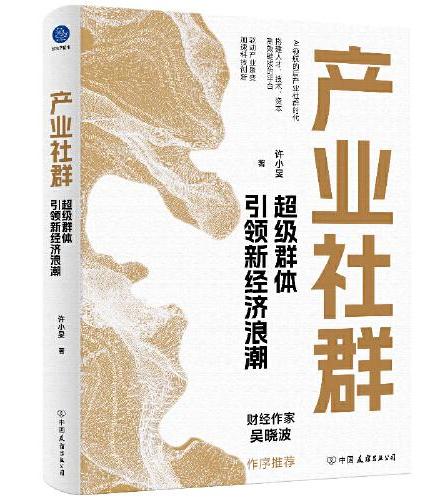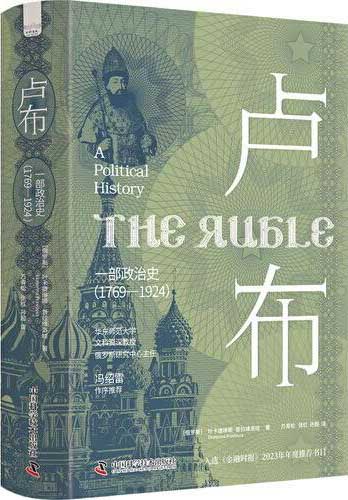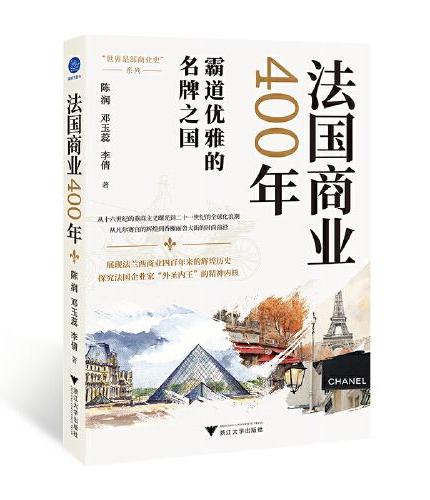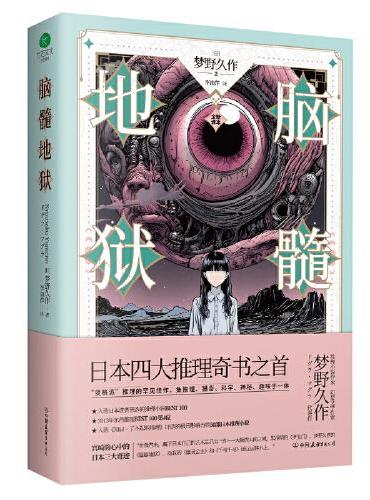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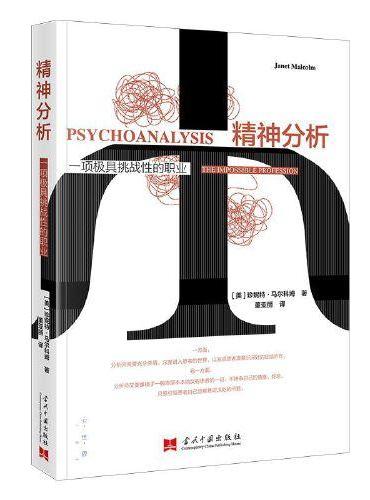
《
精神分析: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职业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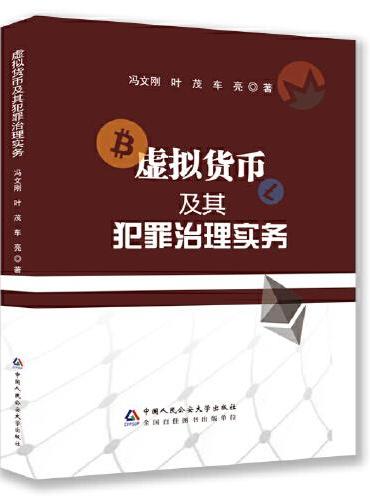
《
虚拟货币及其犯罪治理实务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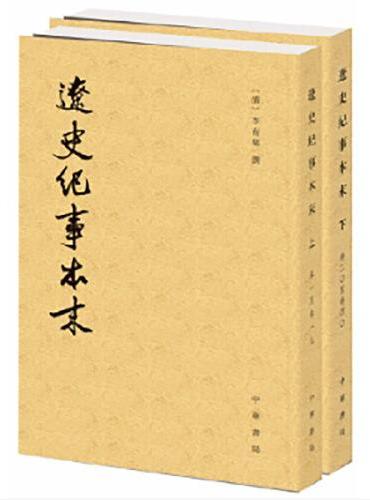
《
辽史纪事本末(历代纪事本末 全2册)新版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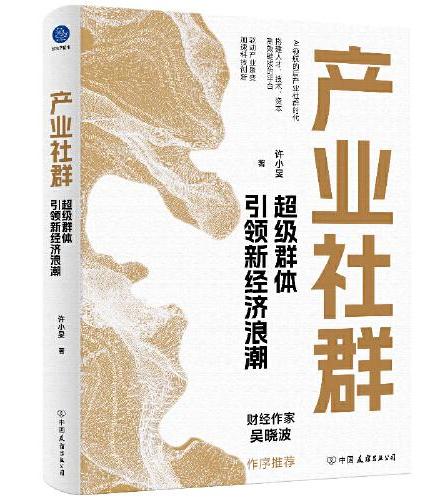
《
产业社群:超级群体引领新经济浪潮
》
售價:NT$
3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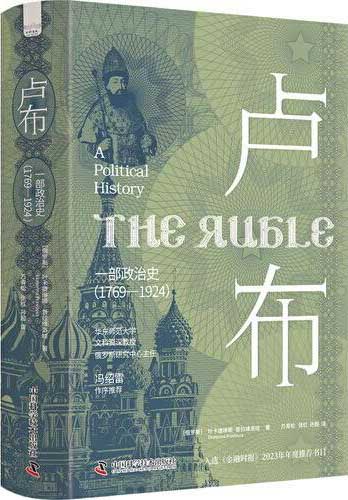
《
卢布:一部政治史 (1769—1924)(透过货币视角重新解读俄罗斯兴衰二百年!俄罗斯历史研究参考读物!)
》
售價:NT$
5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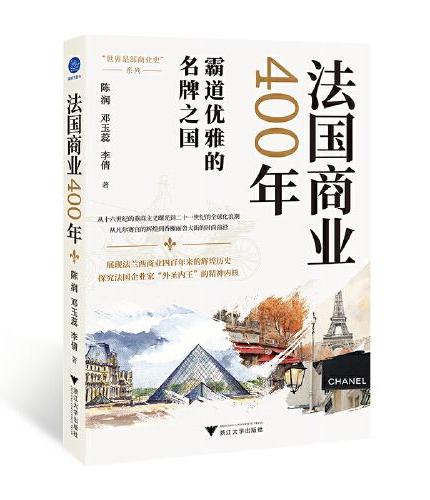
《
法国商业400年(展现法兰西商业四百年来的辉煌变迁,探究法国企业家“外圣内王”的精神内核)
》
售價:NT$
347.0

《
机器人之梦:智能机器时代的人类未来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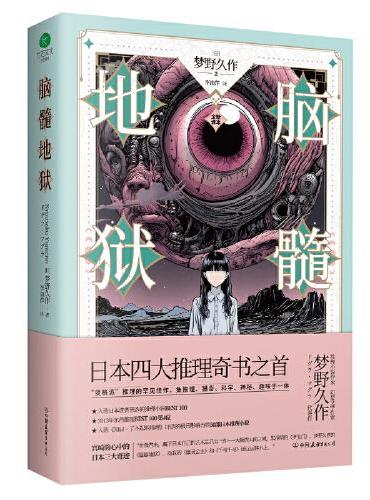
《
脑髓地狱(裸脊锁线版,全新译本)日本推理小说四大奇书之首
》
售價:NT$
286.0
|
| 編輯推薦: |
史杰鹏*先是以汉代历史小说独树一帜的。在他的学术随笔和杂文中,深厚的学养和知性的光芒一以贯之地闪耀着,而对于社会和人性中的畸形和丑
恶,则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极其锋利的攻击性,其摧枯拉朽的力量常常让人想起鲁迅,想起他那句著名的话:我一个也不饶恕。
赵长征
史杰鹏君幽愤深广如鲁迅,议论风发赛柏杨,嬉笑怒骂胜李敖,一往情深似晋人。其文汪洋恣肆,于传统间窥见新知,在旧曲中发现新声。
方麟
我觉得,他对汉语文学的贡献,在于淡然说出人性的凉薄与肮脏。鸡毛蒜皮,不妨锦心绣口;走街串巷,却是出史入经。
廉萍
|
| 內容簡介: |
|
本书精选作者散文随笔五十余篇,内容主要是对童年的点滴回忆。作者以淡然的笔触描绘了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剧变的大背景下,市井生活之艰难,揭示出世情的凉薄与人性的丑恶仗义不从屠狗辈,负心亦多读书人。全书回忆亲人、桑梓,不落温情与敬意的窠臼,独有一种冷眼旁观的觉醒。
|
| 關於作者: |
|
史杰鹏,笔名梁惠王,1971年生,江西南昌人,作家、学者。文学创作有长篇小说《亭长小武》《婴齐传》《赌徒陈汤》《赤壁》,自传体小说《户口本》,历史散文《文景之治》等。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文字学、训诂学及先秦两汉文献学。
|
| 目錄:
|
目 录
香港电影《三笑》
绳金塔
夏天的记忆
纪念我的二伯父
小时候的中秋
对外婆的悼念
冻疮
童年
看电影
打老婆的小柳
苜蓿
端午
冰棒
学武术的回忆
拾稻穗
游泳和水鬼
关于狗的记忆
一只鸭子
小时候的零食
牛头山
早米和晚米
画画的回忆
说说我的外公
写春联
妈妈和一个故事
和鬼、死亡有关的记忆
和姨父一起洗澡
读诗词的回忆
恐高症
害怕黑暗
做苦力
两个回忆
舅舅的录音机
考试恐惧
自行车的故事
说说我的二姨
压岁钱
西瓜
童年轶事
七月半
青云谱
戏曲
正月初七及其他
救护车
剁椒鱼头
京师忆旧年
瘟猪肉
池塘的死鱼
桑葚
绳金塔记之外公本纪
绳金塔记之老姜列传
绳金塔记之香菊传
城南记之邻女传
城南记之堂弟列传
乡下记之城南流氓列传
那些炎热的夏日和青春
|
| 內容試閱:
|
纪念我的二伯父
前两天听到二伯父去世的消息,没感到有多少悲伤。据说他是一跤跌死的,躺在家门口没人知道,最后来了一位常伴他一起打发时光的老朋友,才赶紧叫车送去医院,可是已经没有进的气了。
总觉得二伯父不该这么晚景凄凉的,他有知识,有文化,在家乡以聪颖著称,很早就考上了工学院,读了五年书,邻近毕业时,却碰上下放:农村考出来的照旧回到农村去。他又是个顶老实的人(我们家族的大多老实),就乖乖回去了。可是据他一位老同学讲,班上有些人就坚决赖在学校,不肯回乡,最后上面也没有强迫那些人就保住了他们来之不易的城市户口。
二伯父很擅长画机器图纸,因此在乡里的一个翻砂企业上班,早年厂子经常依靠他出差联系业务,因为内行实在不多,所以他年轻时跑遍了大江南北。我曾经披览他积攒的经典门票,故宫、颐和园、定陵博物馆什么的,非常艳羡。年轻的时候,我是多么渴望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啊,哪怕去外省的一个小地方,也许都有说不明白的新奇。这想法的幼稚是显然的了,如今我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连大门都不愿意多迈,那个定陵博物馆,至今也没有谋面,可见时光是多么能催老一个人的心灵。
九十年代末期,企业转轨,被几个官承包,像二伯这样的人便被一脚踢出,失业了。他是个书生,除了画图纸,根本没有别的谋生技能。于是家境逐渐困窘,只好为一些乡间私人企业看看大门,甚至为养鸭专业户看鸭棚、做饭,我当初听到这些,简直信不过自己的耳朵。在我多年的印象中,二伯是从来不沾任何家务的,每天下班就是捧着一张《参考消息》,冬天的新年,则穿着笔挺的呢子大衣到处访客。近几年我寒假回家时,他照旧穿着那件呢子大衣来找我攀谈,问问外间风物。我注意到他苍老得厉害,嘴巴里竟然缺了几颗牙齿,有一次甚至惊异地发现他连裤扣都没系上。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精神面貌?要知道,他并不是放浪形骸的艺术家。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是衣衫笔挺的。
家道衰落至此。我父亲常常慨叹,二伯是一条龙命作成了蛇命,说他年轻时候,刚学成回乡,在乡中学教书,有个中学女老师想嫁他。可是那时闹文革,到处贴大字报,披露那女教师是破鞋,因此被他拒绝了。最后他找了一位乡下女人,比他小近十岁。可是依我父亲的话说,没文化的妇女,生下的儿女很难有出息,因为遗传基因相对差。这话既刻薄,又胡说八道,也不科学。不过倒很符合他的性格,我母亲和我们兄弟姊妹三个,从小也都在他这种侮辱和损害中长大,真不知道他哪来的优越感。在他心目中,能当上城里人才算有出息,而对农村孩子来说,想达到这个目标,除了考学,几乎没有别的途径。但是,由于环境限制,农村孩子从小家里见不到一册书,从小就没培养出读书的习惯,最后能有多少能考上大学?不得不承认,如果二伯父娶了个中学女老师,一切自然会两样。家庭环境,对塑造一个人起着无法估量的作用。
那个小二伯近十岁的妻子,五六年前就早早先去世了。据说是生了病没钱治,但真实情况,据我堂姐说,却不是这样。而是她以为自己的病不重,想挺挺就过去,省下钱可以为儿子娶媳妇,可是终于没挺过。死了老婆,二伯的生活更加一落千丈,虽然我二伯母也不是什么很爱清洁的人,可是她活着的时候,二伯还不至于落到裤扣也懒得系的地步。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一个凉薄的人,总之现在对于死亡,真的很难在心里起什么波澜了。虽然刚听到二伯去世的噩耗时,也吃惊了一下。而转念人终究是要死的,也就觉得很淡然。时常会有这样悲观的想法:这世间的每一个人死亡,或许都有一些为他悲痛的人,证明他来这世上走过一遭,有过轨迹。但是等到连为他悲痛的人也都死光了的时候,那他的存在过与否,就完全成为一个谜了。人生有什么意思?
我对于二伯和二伯母鲜活的印象,是二伯聚精会神地画图纸的时候,是二伯母躺在一个倒置的竹床上被抬往医院生产的时候。那时他们还风华正茂,可是属于他们的时间不知不觉就全部用完了,人世间是最喜新厌旧的,它很快抛弃了他们。我能做的,也就是作一个短短的铭文,当成对他的祭奠。铭曰:
愿者贫窭,黠者尊荣。
百无聊赖,奚必久生。
昔王侯之厚棺椁兮,
欲驻万世之精灵。
恨穷魂而下九原兮,
无郁郁之佳城。
对外婆的悼念
我的可爱的外婆终于死了,享年八十四岁。
前几天接到母亲的电话,说外婆病危,要我回家乡看她一眼。然而医生都说她没治了,我回去又能怎么样?何况她儿孙成群,实在并不缺少我一个。于是终于没有去。
今天接到妹妹短信,说外婆已经下葬。真快!从此我熟悉的那一个老妪,真的作别人间,成了古人。作古这个词,小时候听到,哪里能理解它内涵的精微。长大了才明白,人的生命一旦消失,就确实成了历史。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它并不忙于送往迎来。
我记忆中的外婆是个很懂得享受生活的人,然而生活得并不优雅。每天凌晨,星光熠熠的时候,她就要和我母亲拖着板车去酱油厂装酱油,然后运送到市内的各个商店。酱油厂在原来的爱国电影院对面,当年上小学,放暑假的时候,我也经常去给她们母女俩帮忙助推。满载一板车酱油出来向南,有一段长坡,行起来很吃力。推上去之后,我们就会放下酱油车,到路边的冷饮店喝一杯冰水,顺着喉管灌下去,直凉到心脏发紧。这是我记忆犹新的一个享受,也许,我每每要求加入她们推酱油的队伍,仅仅是为此吧!
那时的外婆也有五十五岁左右了,这项劳作,她一直干到近六十岁,有一次被车把撞断肋骨才退休。或者不应该叫退休,因为她并不享受任何劳动伤残保险和退休金。
每天拖着空板车回家,外婆就会坐在院子里,点上一支香烟,惬意地过把瘾。没有的时候,则拿出三角钱,叫我去对面的小杂货铺:买包庐山,剩下的钱归你。庐山烟大约二毛五分钱,偶尔她会抽四毛一的壮丽,那是极少数,抽大前门的时候更是屈指可数。我为什么对她抽烟的事如此记忆犹新呢?可能是在她能有兴趣抽烟的年代,仍旧那么生龙活虎的缘故吧。人谁不希望自己的亲人永远生机盎然?当然,这是妄想。近十来年,我每次回南昌去看她的时候,她都像一只干透的虾米,蜷曲着在灶台上忙碌,热情地招呼我吃饭。她早已不抽烟了,而在还热衷抽烟的时节,她的腰曾经是挺得那么直的。
时光催人老,岁月忽晼晚!
抽完烟的外婆,会极快投入到操办晚饭的行动中去。她还有极爱的娱乐,比如看戏。我就跟着她看过很多戏。和我母亲拖酱油的路上,经常会经过电影院。如果看见想看的电影,就会事先买好票。回家后,快速料理完家务,再偷偷出门,去享受这一天中难得的愉悦。而之所以要偷偷的原因,在于外婆要瞒过外公,母亲要瞒过我。
我外公是个相当吝啬冷酷的老头,还是个醉鬼。整天骂骂咧咧的,外婆的一生,或者至少在我能亲眼目击的后半生,简直就是他的下饭菜。所以,要出去看电影,必须躲过他。至于我,年龄还那么小,母亲不带我去,说得过去吗?有一傍晚,我看见这母女俩穿戴整齐出门,就赶忙尾随在后,走到半路,她们大概也发现我跟踪,不时停下来往后看,我则即时隐没在电线杆后。她们张望一阵继续前行,我再继续尾随。我想造成这样一种既成事实:一旦到了电影院门口,再赶我就来不及了。总不能你们俩不看电影,跟我一块回去吧?给我这个小孩补张票进场,是完全做得到的。这个得失你们自己能够掂量。
事实也的确证明了,她们给我补了一张儿童票,让我得以看到那场著名的《月亮湾的笑声》。
外婆最爱的电影是越剧《红楼梦》,还有《三笑》,前者尤甚。有一个夜晚,我看见她和母亲静静站在对面一户人家的窗外,鬼鬼祟祟的。于是蹦蹦跳跳跑过去,问母亲:妈,你们站在这干什么?母亲说:不要吵,听广播《红头梦》。红楼梦三个字,外婆很容易把它念成红头梦,她的口音也影响了我妈。我感觉很无聊,这个电影我是听说过的,因为外婆已经看过它三十遍,不知为什么还这么有瘾,深夜跑到人家窗外听录音剪辑。我正无聊地要跑开,突然听见外婆痛心疾首地说:包车走了。包车走了。这叫声惊动了屋里人,一个人头从窗户探出来,看见外婆,好像恍然大悟,笑着说:进来听嘛!进来听嘛!
外婆赶忙推辞:不了不了,快圆(完)了。后来我回忆外婆那句包车走了,一直不明白什么意思,大概包车就是宝钗吧,我想。但宝钗能走到哪里去呢?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开始播出的时候,我才明白,外婆的喜欢《红楼梦》,其实是叶公好龙。很明显,她根本看不懂这个复杂的电视剧,对里面千头万绪的人物关系不知所措。她所喜欢的《红楼梦》,不过是宝玉、黛玉、宝钗的三角关系,以及尤三姐自刎谢情人这样的爱情故事。当我知道她原来和外公就是姑表兄妹结婚之后,更加清楚了这一点。
抛弃了《红楼梦》的外婆,七十岁开始信奉了耶稣,每个周末,她都要去东湖边的基督教堂去参加礼拜。原先目不识丁的她,也买了一部繁体字版的竖排《圣经》,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读。大概人的年龄大了,做人的时日愈少,离鬼的时日愈近,愈想在精神上寻找一个寄托。靠着寻找精神寄托的伟大毅力,这个七十多岁的刘媪很快自我完成了扫盲工作,甚至还能写繁体汉字,这不能不让人感叹,人类对自我生存意义的怀疑和悲哀。
然而,她这种追随上帝的虔诚之心,遭到了我那醉鬼外公的粗暴干涉。那个据说年轻时像个书生的醉鬼驼子,是这样辱骂外婆的:你这个老屄,你说你的基督是在十字架上死的。方志敏也是在十字架上死的,那方志敏也是基督了。
外婆只能无力地反驳:我不跟你这个老东西说。你根本就不懂。我跟杰鹏说,杰鹏懂。她把求援的目光望着我,我能怎么办?只能哭笑不得。
最近几年寒假回南昌的时候,惊奇地发现外婆家的墙上已经没有更新的耶稣受难像。后来就连以往的也不见了,也不再见外婆读《圣经》,教堂也不去。曾经试着问过一次,外婆隐约地说:你外公不允许。这个理由似乎不充分,因为信奉基督从来就是受外公反对的,然而她一直坚持通过《圣经》成功地进行了自我扫盲,绝不可能为此放弃信仰。也许,是衰老的外婆日渐没有精力去教堂,也没有精力应付外公的蛮横所致。
不知她临终的那一刻,是否想到了基督。如果是,那就幸福了。活在这世上,无论信奉什么,有个信仰就行了。
我对外婆的前半生是空白,只知道她很小就当作童养媳嫁给外公,经常受婆婆的打骂。后来躲避日军轰炸,在江西境内四处逃难,再后来通过引车送油挣钱糊口,一直处于劳顿之中。好在于劳顿中,她能找到自己的快乐,并生了七八个孩子。对她来说,生命大概是不算虚度的。谨以此铭结束对外婆的怀念,愿她的灵魂永远受到仁慈地母的呵护:
产于乡鄙,饮食计粒。
流离赣汭,奔飞斯急。
新鼎肇造,灾荒荐集。
于彼人生,所求盖寡。
颠沛道路,宛如骡马。
红楼三笑,泪珠频下。
衰年惶恐,向彼耶稣。
半世文盲,一旦蠲除。
遭夫不造,向壁而嘘。
今魂归泉壤,
壹郁且发抒欤?
宁永归虚无。
打老婆的小柳
有一天晚上,舅舅们突然说,吃了饭去工人文化宫看电影。这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而且突然宣布,更是喜上加喜。但这不是舅舅们的功劳,因为电影票是小柳临时带来的。
小柳长得獐头鼠目,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把我大姨娶走,因为他是个工人。
大姨幸福地成了工人小柳的老婆,不过没有房子,暂时租住在外公所在的村里。我去过那间房子,是一间院子里搭的违章建筑,要换到现在,一定会有城管上门收贿赂,但那时大家的经济意识还没这么强。我看见大姨满面尘灰,弯着腰站在门口烧饭,用的是一口煤油炉,很让我觉得新鲜。我仔细蹲着看了一会,又跑到旁边的菜地里去玩了。旁边的菜地很多,大姨就近上工比较方便。虽然小柳上班,还得骑车走几公里路。
在大姨结婚后,外公就经常去找小柳谈话,请小柳不要打大姨。他说:我屋里爱珍是农村户口,你开始又不是不晓得,那哪个骗了你啊?你也不过是只普通工人,有什么了不起哦?爱珍如果不是农村户口,不一定会嫁你哦。
小柳就闷着头不说话,三句才答一句:上一日班回来,累得死,开水都没一口。不打不得乖哦,哪家的女人不挨打?
外公这下发怒了:我吐痰给你洗脸哎,你老婆坐在屋里吃你的?你一个小工人,那点工资养得起老婆?要是养得起,你老婆要是不拿饭给你端到床上,我都会帮你打哦。你有本事,还租房子住?你怎么不叫工厂分你一套房子?
小柳是个很有修养的人,他不跟老丈人正面冲突,答应会改。
大姨长得高高大大,白白净净,跟我的矮子鬼妈妈相比,她真的很像个知识分子,就是缺个眼镜,还喜欢抹雪花膏。我妈妈有一次背地议论:爱珍啊,她好抠的,参加工作后,一分钱都不交,偷偷存起来当嫁妆,她才会活命哦。我爸爸在旁听到,就插一句:哪个女人不这样嘛?都跟你这样,带着一队红卫兵去家里挖金子,那不要完蛋?妈妈讪讪地说:我那时又不懂事,响应毛主席号召嘛铁公鸡爸爸一点不留情面,咬牙切齿地说:人家都不响应,就你响应,傻绝了灭。
有一天傍晚,又听见外公在院子里骂:有什么了不起哦,屋里也是乡下的,比我们还乡。老子种菜的,总比他屋里种田的好。妈妈给我做了笺注:爱珍又被小柳打了。我睁大天真无邪的眼睛看着她:为什么要打?我爸爸在一旁接嘴:肯定有原因,你们刘家生女儿,就是为了嫁出去害人的。妈妈怒了:我怎么害人了?你好了不起,一个民办教师,双抢时还要下田,农哥哥,说得出去,你还配不上老子。爸爸说:老子要不是民办教师,还会找你?一个尽料的扇头(傻瓜)。你屋里爱珍肯定也是这样,你没听她房东说啊,好别有人谋,臭别挂上楼,你以为有几了不起哦。
这里需要打断叙事节奏解释一下。爸爸用的是人民群众嘴里活生生的语言,还押韵。我们那里把女性的生殖器读成别。这句谚语是一种借代的修辞手法,尽管有些不堪入耳,但不可否认它浓郁的文学性。它的意思是:好的女人大家都想谋求,差的女人挂上楼也无人问津。
咱们继续。妈妈听了这句侮辱女性的谚语,倒也没显出丝毫不适,她只是提出一个细节上的反驳:我屋里爱珍会差啊?配不上他高小柳啊?又矮又丑,一节冬瓜。
爸爸说:可人家是工人,吃商品粮,找了个农村户口的,心里能不委屈?
妈妈说:那节矮冬瓜,找得到工人还会找我家爱珍?她到底还是承认小柳的优势。
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放学,我经过村办塑料厂,看见白嫩的大姨坐在塑料厂门口,认真细致地剪塑料瓶盖子。我走过去哎了一声,算是打招呼。我从小就不会叫人,连我爸爸都不叫,还给他取了绰号。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样太变态了。可是,想起我舅舅称自己的爸爸为阎王,难道还不足以明白一切吗?
我蹲在地上,跟她说了两句话,感觉一阵亲情的温馨。但没料到,这是最后一次看见农村户口的大姨,不久后,她因为村里卖地招工,成了铁路系统的工人。从那时起,我再也没听到老公打她的消息。
说说我的外公
昨天晚上八点四十九分的时候,收到妹妹一个短信,说外公去世了。我马上想起去年,也就是在这个月,外婆山陵崩的事。他们夫妻俩的凋逝,相隔整整一年。
很久以来,我就几乎一年才能见到他们一次。比较早时候,是羞于去,因为怕被误会是打秋风;晚近则没有去的可能,因为我远在北京。以他们的高龄,时日无多,我也是早有心理准备的。然而一旦真的发生,仍不由得怆然暗惊。
一个人,当他的祖父母俱存的时候,不管他自己有多大年纪,仍会感觉自己春秋尚富,算是青年。因为他的祖父母才代表老年,父母则象征中年。将近二十年前,我的祖父母就物故了,然而正因为外祖父母还活着,我从未觉得自己有多么老大。现在,他们两人在两年中相继殂没,我感觉自己才算正式跨入了中年。
中年的心境是凄凉的,这时候卧在客舟中听雨,绝对感受不到韦庄所说的春水碧于天的意境,所见的大概只有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吧!
因此,想起外公,就难免会想起自己蒙茏暗碧的青春年华,我生命力最艳丽的年月,是和他们住在一起的。
就我现在的评价来说,外公根本算不上什么好人,仁厚、慈祥、温良、煦妪,这些形容长辈的好词统统和他沾不上边。相反,他有个凌厉的尊号阎王,那是我妈妈和舅舅们集体给他奉上的。一个人当父亲当到这种地步,是不是可以算得上失败?
他最怕的是我们占他的便宜,尤其是我们这些外姓的。所以,如果外婆好心给我一点吃的,必定遭到他百般辱骂。他自己的儿孙呢,大概基于孔孟伦理,他不得不有所荫庇,但似乎终究有些想不通。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赚的钱,儿孙有天经地义拿去用的权利。他对我的舅舅们最常用的一句控诉就是:我吐痰给你洗脸哦!我的就是你的,你的我没有份!
我现在很激赏这句话,认为可以当作惊天动地的战斗檄文。世界上有某些貌似合法的黑社会政权,其实就像我那些舅舅们一样,毫无廉耻地对他们的父亲予取予求,然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却连吼这么一声的资格都没有。它貌似没有文采,可是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又有什么文采,我疑心也是汉代那些像我外公一样的半文盲吼出来的,现在却成了经典。
他是个驼子,好饮酒,醉后常在院中骂人,但并不懒惰。每天早上,朝阳初升,我站在人行道上,会看见他一摇一摆的身影融入朝霞之中,行进在去农场的路上。他的脚步是那样的刚劲有力,那时他也将近六十岁了,不知道为什么精力还这么充沛。一直到近八十岁,他的精力似乎都不错。可是后来数年,酒醉摔了一跤,很快垮了下来。去世前几年,几乎都缠绵床榻。然而仍旧对人生有莫大的眷恋,外婆在世的时候,不许任何人在他面前谈死亡的事,因为他害怕。
我并不觉得他的贪生有什么好笑,反而要怨恨造物主,为什么一定要把那些热爱活着的人推向死亡。早知如此,你又为何要生他们?相比那些春秋鼎盛而自杀的情况,前者似乎更加残忍,这相当于杀人。
翻开案边一堆堆的历史书,想到几千年来,中国人就这样换了一代又一代。最悲怆的是,那过往的几千年,一代一代人经历的人生并没有什么变化。祖父过的日子,和孙子过的日子几乎毫无区别。相比现代科技背景下的人生,古今中国人,实在宛如生活在两个星球。
外公大概经历过民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大饥荒、文革,真是日新月异,每种经历,它的背景都可以说是沧海桑田,我们简直梦想不到。假若有一天中国人实在不幸,又要经历同样的变革,那细节也会完全不同。这就是现代背景下人生的丰富性所在。
他活了八十九岁,生于一九一九年。那一年的五月四日,北京城很热闹。
乃为之铭曰:
生而好饮,无以肉粱。
醉而好诟,无以暴强。
弥生黄耇,终有其疆。
千秋万岁,永閟其光。
玄泉阴壤,孰侑之觞。
呜呼哀哉,人世之常。
说说我的二姨
寒假回去,大年初一,大舅请兄弟姐妹们吃饭。按照南昌的风俗,大年初二,是妈妈他们兄弟姐妹一起去外婆家吃饭的日子,也是一年中不多的相聚齐全的机会。现在外婆外公都已经去世,妈妈的兄弟姐妹们也越来越老,代代轮回,他们初二也要在家和自己子女团圆,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所以,这样的机会是很少的。
进了大舅订好的包厢,我的表弟们都已成人,个个挈妇将雏,一脸疲惫。嘘寒问暖的间隙,忽然看见二姨也坐在那里,犹自是那么木然而瘦骨嶙嶙,看见我,微微笑了笑,笑容也一如以前那么古怪。
也许我外家真有不大正常的血统,因为外公外婆是表兄妹结婚的。还好,除了大舅,我另外两个舅舅都比较正常,所以也就没什么好写的。我的大姨、小姨也正常,也几乎没什么好写;但是中间这个姨,或者叫二姨吧,又太不正常了。她还不是大舅的那种名士般的不正常,大舅那种,《世说新语》上比比皆是的;而二姨不一样,毫不风雅,按照古典文学传统,没人会理会这样的人物,但我却想写一下。
我记事的时候,二姨还很正常,有一段时间,她放学回来就唱一首歌:
ABCDEFGHIJKLMNOPQRST
UV达掉了热水瓶达掉了热水瓶
捞油水
哎啃什么ABC
上初中后,我才知道这是那首有名的英文字母歌,但唱到W的时候,我老感觉听起来像南昌话意思为摔的词答,这是一个记音字,念入声,本字当怎么写,我也不知道。总之因为它的误导,后面的字母也就讹听成热水瓶了。当时很奇怪学校里还教这样的歌,后来听妈妈说,二姨小时候读书还可以的,小学毕业参加工作,才开始出现奇怪的症状。她的工作是承父业当菜农,每天劳作间歇,社员们都齐齐坐在地头的大树下休息,她却默默拿起笤帚扫起地来,把大树周围的一块空场地扫得干干净净。要说她想当劳动模范,也不像,没有哪个劳模是扫地得来的。后来才知道,这是疯的前兆。
很快她全面崩溃,但并不仰天数繁星,也不咧嘴怪笑,对空书咄咄。她最大的不正常,就是见到我爸爸,会突然大声断喝一句:乡下人。其实她自己也是农村户口,而且还不过是高小毕业,而我父亲若不是身体突然出了毛病,就是个大学毕业生了。她为什么这么有优越感呢?就因为她是菜农,住在绳金塔下,算是城里?户籍制度真是我们伟大的党的伟大发明,强悍无匹,连神经病都不能从脑中将它抹去。
我那时也经常被她惊吓,比如当我拿起瓢在院子里放置的水缸里舀水喝时,她会像鬼一样突然出现,一把抢过我的瓢,喝道:不许吃。为什么?对不起,没有理由。舅舅安慰我:碰到这种人,将她搁高些。南昌话搁高些,意思是别去招惹,让对方自己觉得无趣。但是,我不能连喝水都鬼鬼祟祟避开她呀!何况她不是正常人,自己并不会觉得无趣。
全家人就此都不惹她了,但她很快就碰到了强硬对手。那就是我大舅的老婆,我应该叫大舅母。
大舅母不知是哪个乡下的,总之刚嫁给大舅时,口音带着浓郁的乡下味。我感觉城里人一般是以他(她)自己的口音为中心,来评判城乡差别的。他(她)会有这种感觉:一个人的乡味之浓淡,和他(她)离城市中心的远近成正比。这种微妙的读音差别,可以制成类似地质学上的等高图,我相信世上的每个人都有亲身体会。大舅母的口音离南昌市绳金塔的距离应该相当远,远远超过我们将来要搬迁至的城南乡下。城南的发音和绳金塔的发音,有些词汇不同,比如城南把蜻蜓叫作苍格燕里,词尾里其实相当于普通话的虚词儿,是无意义的后缀。迄今为止,我也不知道苍格燕三个字当怎么写。某年暑假结束,我从城南回到绳金塔,一日看见蜻蜓,伸指而呼苍格燕里时,小舅当即笑我:一个暑假就学得满口乡下话了。而在绳金塔,则把蜻蜓称为丁顶,虽然读音略有不同,但至少可以看出两者的亲缘关系,与苍格燕里的乡味不可同日而语。当然,绳金塔也并不是什么高尚住宅区,它的居民口中绝大部分词汇和发音,和城南还是相同的,两处的人完全可以轻松自如地交流。然而大舅母的发音,不仔细分辨,有时几乎不知道她说什么,要好一会才能反应过来,可见其乡味之浓重。
以大舅母口音之乡,能嫁给我那公交公司工人的大舅,显然是件喜上眉梢的事。但她性格非常强悍,我那可怜的大舅完全屈服于她的雌威,每月按时将他的工资袋上缴,只留下少许零花。她没嫁来时,大舅和二姨发生冲突,二姨会像僵尸一样立在院子里骂大舅强奸的。为什么这么骂,据我妈妈说,是因为大舅之前谈过一个女朋友,双方可能情浓之时出轨,女方怀孕,而且是宫外孕,导致了葡萄胎。在精神不正常的二姨看来,这就是强奸。大舅之前拿二姨没办法,对她的骂也懒得理会,反正谁也不会当真。大舅母一来,那就完全不同。某日听到二姨这么骂,她勃然大怒,冲上去揪住二姨的头发就打。她身材高大健壮,瘦弱的二姨哪里是她的对手。我只看见二姨低头弯腰,身体无可奈何地朝着自己头发被揪的方向前进,脚步踉跄,却不敢有少许停留,因为吃不起痛。大舅母一手揪着二姨的头发,一手猛扇二姨的耳光,啪啪作响。二姨徒自哭嚎,两手乱抓,但头都抬不起来,哪能触及目标?被大舅母一阵阵耳光抽得找不着北,嘴角鲜血狂流。我在旁边看呆了,没想到大舅母这么剽悍。所有的亲人都在旁观,悠然事外。直到外婆听到声音,从屋里冲了出来。
人说护犊情深,的确不是虚言。见自己的女儿被揍,外婆当即像疯了一般,扯着嗓子吼道:她一个神经病,你也跟她计较?
大舅母打人好整以暇,绰有余力,嘴里回应:神经病?骂人怎么就不神经病了?不打烂她的嘴,学不乖各。
身材瘦小的外婆这时已经像疯牛一样冲到大舅母面前,使劲去拨大舅母的手,尖叫道:你打,你先打死我。打死了我再打死她。外婆酷爱《红楼梦》,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从贾母那学来的。当贾政猛捶贾宝玉时,贾母颤颤巍巍地赶到,急吼吼地说: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岂不干净。她一发言,贾政只好惶恐谢罪。但外婆并无贾母的权威,大舅母一手轻松拨开外婆,一手继续抽二姨的耳光。这场战事最后是怎么结束的,我真的忘了。总之二姨的嘴肿了好几天,此后见了大舅如羊见狼,哪里还敢再骂。人说鬼也怕恶人,何况神经病,信然!也只有我爸爸这样的老实人,才肯始终如一地忍受她乡下人的侮辱。其实二姨不知道,我爸爸还是城镇户口呢。
不过二姨的户口不久也变为城镇的了。因为村里的菜地被征用,除了钱之外,每家还能分到一两个招工名额。究竟因为二姨有病,家里人想帮她混一份正式工作以为依靠,因此以大舅母之凶悍,虽然寻死觅活要夺取招工指标,竟然没有得逞。而二姨也竟然逃过了体检,成了一名南昌床单厂的工人。但很快她的症状愈发严重,无法胜任本职工作。床单厂的领导来到外婆家,嘘寒问暖,言辞中颇有怀疑她骗过招工体检之意,但并无证据。于是送往精神病院治疗,未几出院,病发如初。床单厂无奈,只能让她回家休养,每月发点基本工资。
二姨的一生就是如此的惨淡,亲人们绞尽脑汁,找了无数偏方对她进行治疗,甚至瞒着给她吃煮蚯蚓的偏方,仍旧毫无效验。
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在绳金塔住了十六年的家被无敌城管宣布为非法违章建筑,遭到野蛮拆迁。而我们全家都是良民,不敢以自焚来恶意抗法,只好悲愤迁往城南乡下。多年后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物权法》这么神奇的东西,据说英国一名乞丐,因为在某闹市区露天住宿达十三年之久,突然天降喜事,按照《物权法》,那片闹市区的黄金地域从此成为他的私人财产,价值上百万英镑。而我们全家在南昌的一个破街道上居住了足足十六年之久,并非露天,却不得不灰溜溜地被赶去乡下。写到这里,我想偷空感慨地叹一声:这世道,真是冰火两重天哪!
城南乡下的生活是枯燥的。某天,突然迎来了二姨,她带着一个男子,亲热地向我母亲介绍说:这是保国。
保国也是个有精神病史的人,但是那次,他们两个人看上去都极为正常。他们面貌安详,衣装整洁,言笑晏晏,和我爸爸妈妈寒暄,叫我爸爸姐夫,叫我妈妈姐姐,一点也不厌恶我们居住在乡下。我感叹不知是谁这么好心,把他们俩撮合在一起。在我家吃完饭后,他们又礼貌地与我们告别,仿佛贵族。妈妈看着他们相依相偎的背影,欣喜地说:这回好了,看来有了老公,她就能变好。我也想,是啊,爱情的力量真伟大,竟能让疯子脱缰野马般的心灵也变得宁静。
然而好景不长,很快传来消息,保国的父母不同意他们的疯儿子和我的疯二姨在一起,说是二姨疯得厉害些,配他们儿子不上,活生生地把两个年轻人拆开了。不久我的二姨又恢复了原先的模样,瘦骨嶙峋。每次新年初二的时候,我们一家去外婆家团聚,她见了我爸爸又是暴喝:乡下人。见我长得老高,又工作了,问我要钱,之后出门,买回来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东西。外婆就告诫我:别再给她钱,她见了人就讨钱,讨到后见东西就买,不花光不罢休。有一次没钱还去拿人家的,差点被人打残了。
外公外婆在世的时候,二姨能跟他们相依为命,现在他们二老已经魂归天国,她将怎么过?有谁会像父母一样宽容她?据说外婆临死时,将她托付给了二舅,说如果能将二姨收留照料,生前自己住的这套房子将来就归二舅。
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看到相依为命的高龄父母逝去,自己独身在这冷酷的世上再无依傍,不知情何以堪?虽然有众多的兄弟姐妹,谁又能代替父母?但我不知道二姨会怎么想,我只为她感到难过。
绳金塔记之外公本纪
吾外公,南昌县岗上乡人也,姓刘氏。父曰招发,祖某,乡医,号刘一贴,以治疮一贴必愈得名。招发亦传其技,为乡里所称,家故小康。民国三十三岁,日寇犯岗上乡,百姓鸟兽窜。招发亦赁一车,帅家人走南昌,停城外之千佛寺。寺僧悯之,以一屋与居,使守寺产,由是一家为南昌市人。
日寇败,不数年国朝立,焚寺庙,招流民立一乡,招发亦与焉,遂编为菜农,犹私习医,无所知名。里中有一妇病笃,送医院,皆束手,家人方治下里具焉。招发往,一针而起,名遂大震。妇亦拜招发为义父,终身事之,远方慕而来求医者乃不绝。吾幼时,招发尚存,蒙其看视,至今记其相貌。
招发产三子,长曰明玉,即吾外公,面白善书,尝为皮鞋店经理。国朝十一年,天下大饥,外公不耐,以种菜略可疗饥,遂逃归乡里,终身为农民。晚节遴,长女傍其屋居,外孙饿,一粥不许施与,以父招发看视外孙,迫其女偿费。同姓孙略宽贷,然犹常骂其子:我的就是你的,你的我没份。其无人性如此。
外公少时,娶表妹细姑,细姑年裁十二,长不及灶台,甚悍,稍有忤则滚地叫号,外公惧之。既壮,细姑转温和,而外公翻暴戾,子女乃上尊号阎王。及耄,益得意,尝洋洋言:吾解放前,亦为妓院常客,许我青眼者多矣。外婆大恚,又妒,私语吾母曰:阎王老而弥无耻矣,此龌龊事,语我何为?
外公年四十即驼背若龟,然康强壮健,八十九岁乃殁。以视女若敝屣,故临终无肯看护者。三子递陪,亦不耐。吾母曰:其死以前列腺肥大,尿不得排也。余乃忆家父尝告余曰:昔阎王之父之卧病也,口渴欲饮,呻呼,一屋无应。吾以水与之,为其孙所阻,曰:已耄乱矣,饮必尿床,谁与料理者?竟渴死焉。殊为相似。
绳金塔记之老姜列传
余少时居绳金塔,屋附外家垣。垣内有空房数间,赁于一姜姓者。家主老姜,年可五六十,好饮酒,每饮必醉,醉必诟骂,其妻不耐,时有违言,辄遭其棰楚。育三子三女,三子无论,女皆端丽。其长子长女已婚,中子婴癫痫,时吐白沫,匍匐叫号,若野兽焉,然体魄健,食兼数人,力能投席。独孝母,视其父蔑如也。
一日老姜又醉,方欲诟詈为乐,癫痫子忽至,袖菜刀数劈,刀刀中首。老姜偾,急送医,得苏,然有后遗症,见风即痛。尝小酌后仰视树叶瑟瑟,曰:此中子聪慧,吾夙所钟爱,尝倾家为疗疾,不意待我若此。垂泣太息。
异日平旦,老姜妻惊叫号哭,众人醒,就其屋视,则老姜仰卧于床,一利剪菑于颅顶,溅朱半墙,残血犹滴沥若泪。吾舅趋至第三医院,呼急救车,一护士讥之:汝谓拍影视耶?若等穷酸,安得救护车?吾舅惭,走归,老姜遂死。其妻泣云:昨夜将寝,老姜曰头痛,无生人乐。吾意其寻常牢骚,今思之,是早萌死志矣。众以此皆谓老姜自尽,叹息,劝慰而去。
后数月,老姜妻改嫁。亲迎日,一中年男忽来,号泣曰:始汝言夫死即嫁我,何为更盟?汝使傻儿杀亲父,为吾不知乎?若真狠毒矣。老姜妻结舌,甚慌乱。人渐麇集,癫痫子忽溃众出,怒而前,横举中年男,奋臂挥,倏忽飞出数丈矣。宛转呻吟,不能起,众中有人笑曰:尔欲寻死乎?彼精神病,杀汝亦不偿命。走矣!中年男寤,强起,奉头鼠窜。
后数年吾归乡,与家人言及老姜事。吾妹曰:老姜妻再嫁,夫甚悭吝,亦不乐。其中女初中辍学,奔粤打工,以貌美为一港人收为外妇,产一男,遂得宠;复引其妹嫁一港翁为小妻。其姊早嫁人,夫亦不良,乃离婚从其妹,再嫁一广东富人。三姊妹既兴,乃迎其老母众兄至粤,一家团圆,甚欢焉。余叹曰: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绳金塔记之香菊传
余冲幼时,比邻有业裁缝者,耇鲐,养一孙女,长余一岁,常来院中与余熙。余时持大姨所贻连环画数册,彼欲借观。余恐大姨不喜,坚拒之。彼见不能逞,沉吟顷刻,忽曰:若借我观,吾让若观吾阴。余时年方四五岁,然已知男女之有异矣,即应允。
女名甚伧楚,唤曰香菊,虽长余一岁,而不甚乐学。后数岁事模糊不能记,复能记者,其年已长,延颈秀项,乌发垂髫,宛然一美少女矣。某日余放学归,见其门前聚闲人若干,裁缝老妪则箕踞嚎啕。询之,方知香菊午时忽饮药自尽,不知其由,然多指目其旁邻一绰号为气鼓卵者,云女即为其强奸怀孕所致云。
城南记之邻女传
余少时居城南,邻家有一女,面目清秀,娟婉可爱。门前有一小院,院中立一柳树,尝见此女夏日执一扑囊,仰颈凝视柳叶间,若听蝉鸣,真一美妙之图画。余痴立观之移时不忍去,彼似有所觉,侧首见余,粲然而笑。余窘,乃旋踵,心犹惊跳。后数岁,余外出求学,久不见之。某年归,间与家人言及,则已死数年矣。
余惊愕不已,叩问其详。母曰:汝求学于外未一年,彼骑车访亲。天雨路滑,狂风击面,又值黄昏,天色晦暗,十步之外,不辨牛马。彼上一高坡,低首蹬车,不知对面一大卡车呼啸而降,乃毙命轮下。言毕叹息。余喃喃曰:向日凝眄柳枝,流波明灭,今都逝矣!
余母慨然曰:皆彼柳树之为患也。方彼死前数日,有老者过其家,曰:屋前种柳,宁为藏鬼乎?是家当有祸患?不意正应于彼身也。且其真为强死矣,死已数月,一至暮夜,家中鸡飞狗跳声不绝,似有物惊扰驱赶者。算命者云,即其强死之魂魄,恋眷人间,不忍和亲人携离也。
城南记之堂弟列传
堂弟某,小名憨头,母产其未久,须上班,无暇看护,乃请外婆代劳。外婆半盲,殊无力任之,然知女家贫,难雇人,强诺。余常隔天井闻憨头哀嚎,若中弹之犬。奇之,因攀窗棂窥,见盲媪持一碗粥食憨头,以调羹抵其颈,力呼:恰(吃)嘛恰嘛恰嘛。憨头摇头摆尾,抵死不从,若一颈部被扼之蚯蚓焉,粥溢出调羹,滴其胸脯。犹烫,故哀嚎。盲妪不觉,反颔首笑曰:诚当如是。复进勺,能入口者,不过十之二三。
憨头幼而徇齐,稍长,意豁达,好狗马,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其上初中也,尝以学业负殿为某教师侵辱,衔之。辍学之次日,即纠众往教室。教师方授课,见憨头至,大恐,夺门奔。憨头逐之,教师无可如何,自二楼跃下,一足触地而折。憨头走窜,由是始欲混黑。族人皆不可。其母慨然曰:大丈夫宁当羸死陇亩哉?混黑,太上美衣甘食,其次亦可温饱,最下亦不过归南亩耳,何虑?皆默然。
憨头混黑道,始不顺,尝为人以三棱刮刀堵至厕,臀被三创,为乡里所笑。族人皆惭,其母独坚执如初,曰:人前长脸,人后受罪。安有不困苦而可功成者?憨头益发愤,广结交。既贵显,而母已死,具牲祭,悲曰:微吾母,吾羸死稻田矣,安能似今收保护费哉?乡里由是益服其母之智。其父脑溢血死,憨头方避吏事,不敢归。而乡里长者亲赴其家为主丧,殡日,自远方而来会葬者,豪车无虑百余辆,多企业家老板者,其得人心如此。至今为城南霸。
乡下记之城南流氓列传
大扇,南昌市郊城南村人也,少以盗窃输大西北狱,廿年乃还,头已二毛。城南少年与接风,唱卡拉OK,呼小姐陪之,极欢。大扇酒酣,引小姐至屏处,泻火毕,归座捭胸言:与吾同狱南昌人无虑四五十,皆释还矣。电话一拷,无远近倏忽可至。即有事,吾聚兄弟为汝平之,孰敢多言者?
少年阳誉之。既罢,其首领名小辉者笑曰:吾视其前辈耳,又同宗,故略示敬。今城南,乃公之天下,干彼老货何事哉?皆大笑。然犹命人致大扇柴米,又钱若干。大扇气益壮,出门蟹行,常自伐,又数至村政府索田宅。书记患之,召小辉谋。小辉谢曰:勿忧,彼不晓事,吾为公教训之。
即命人至大扇所,索前所致钱。大扇不肯,又无钱。索益急,大扇怒,乃电召二毛军数人至,夜缚小辉笞之。小辉既脱,立征城南混混上百,堵大扇门曰:今日死若残,君择之。大扇曰:死吾不惧,然人命大,恐累君入狱耳。请致残。小辉乃以自制枪抵大扇双膝,轰之,膝骨尽碎,遂残。
大扇腿既愈,日拄拐至村政府,气不少索。书记异之,惭恧,转敬之,语小辉曰:是真豪杰,若少汝廿岁,汝之位岂不归他乎?小辉然之:方吾以枪抵其双膝也,色殊不少桡,虽共产党员不过也。书记莞尔:于影视中求之乃得尔,现实安有?乃出资为大扇装假肢,皆进口材,又与其附近一菜市场,曰:今日起,畀汝收保护费矣。
大扇以此家日丰,犹茕独。某夜,一青年妇人来,语大扇曰:君识妾否?大扇张目视:是市旁大鹅妇?妇人颔首:然。吾夫庸奴,与居不乐,愿改侍君。大扇难曰:吾年老,又残,且与大鹅同族妇人曰:始谓君豪杰,旷久,何反作君子态?旗杆已竖矣。大扇大笑,即于榻上尽欢。
明日,大鹅来,索其妇。妇出坐庑下,曰:吾爱者大扇,不喜君,请离婚。大鹅欲怒,见大扇执一刀出,不敢,嗫嚅曰:叔如此,人当有闲话矣。且叔豪杰,何妇不可得,岂必夺侄妻。大扇摇头,曰:是人耳,安分叔侄。人不爱汝,又值新社会,婚姻岂可强迫哉?大鹅嘿然,后竟离婚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