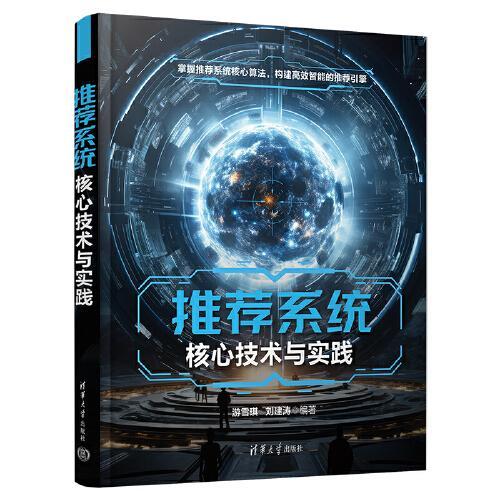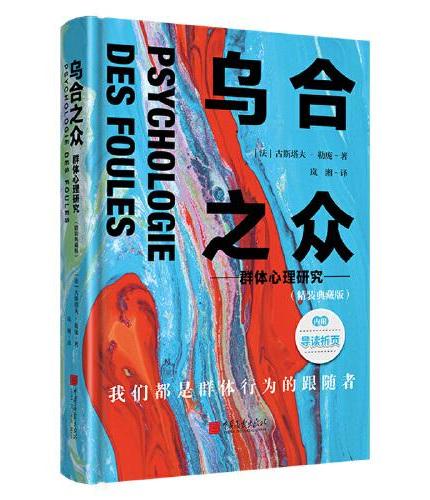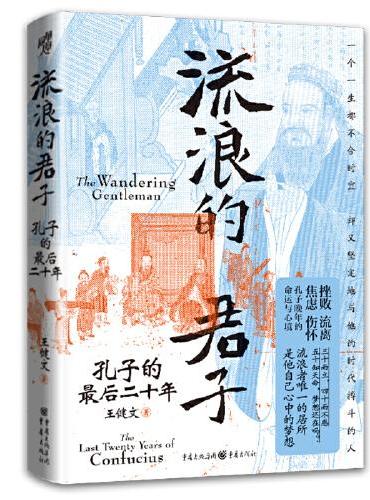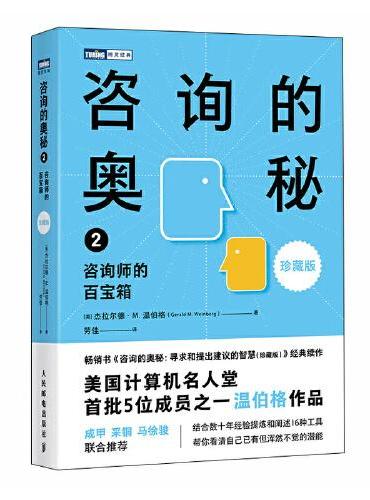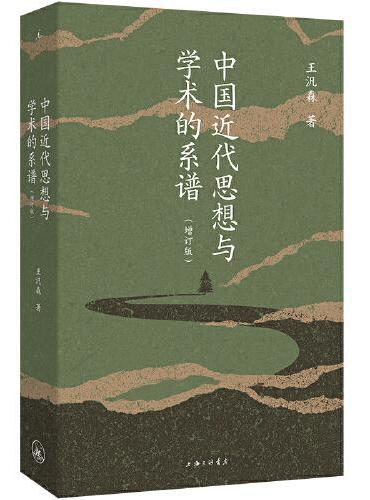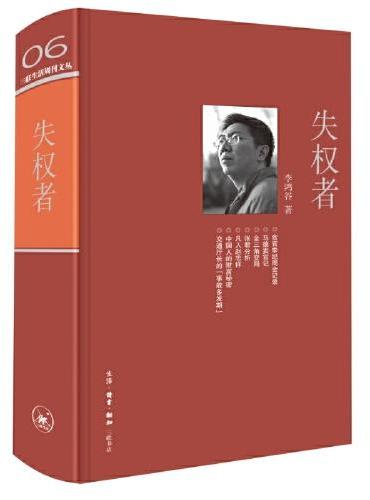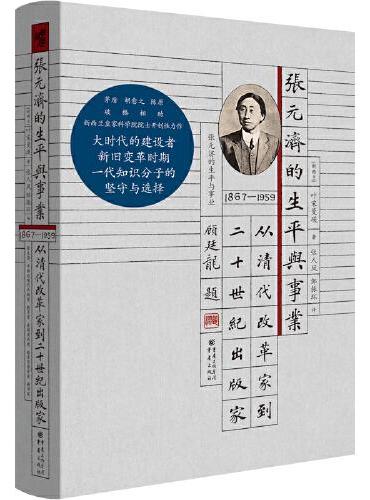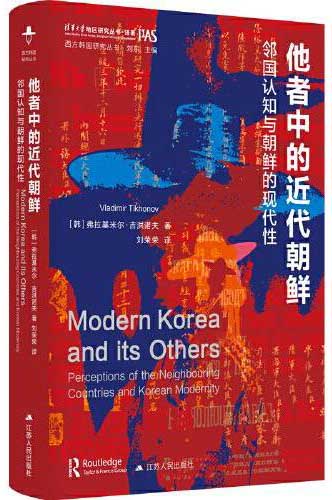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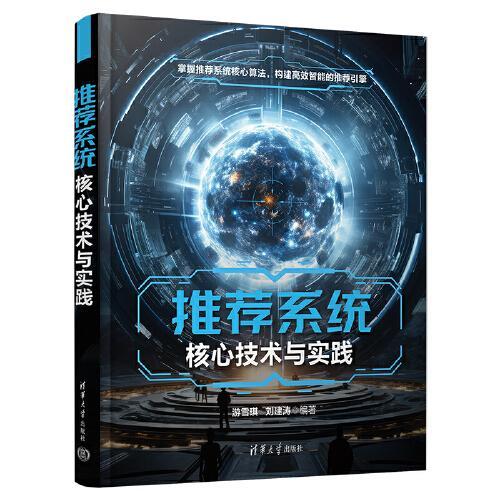
《
推荐系统核心技术与实践
》
售價:NT$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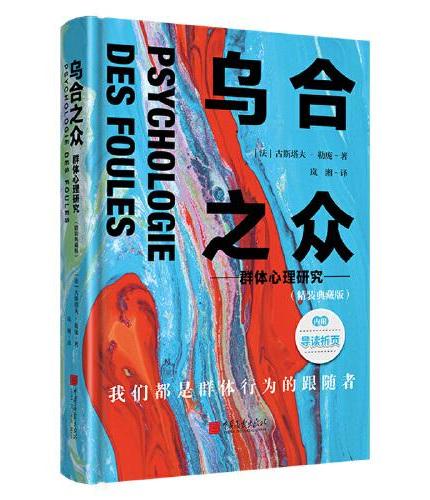
《
乌合之众:群体心理研究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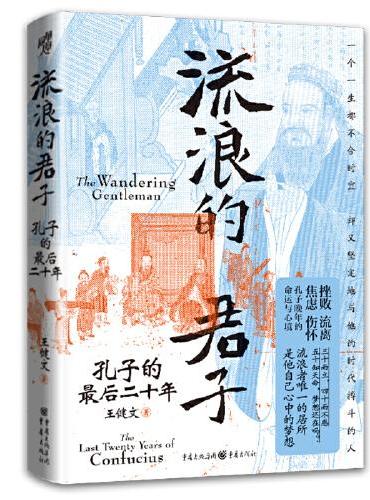
《
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 王健文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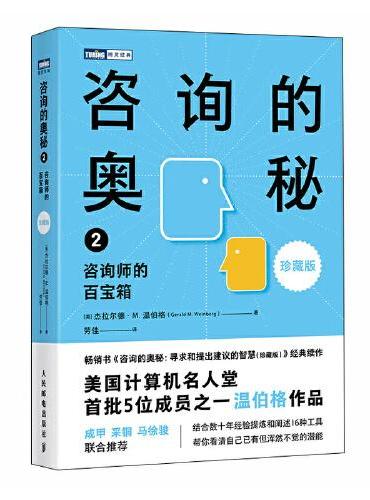
《
咨询的奥秘2:咨询师的百宝箱(珍藏版)
》
售價:NT$
3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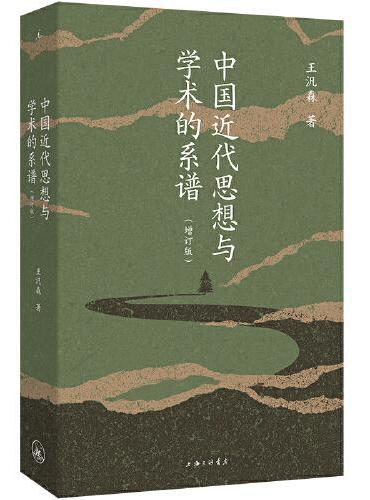
《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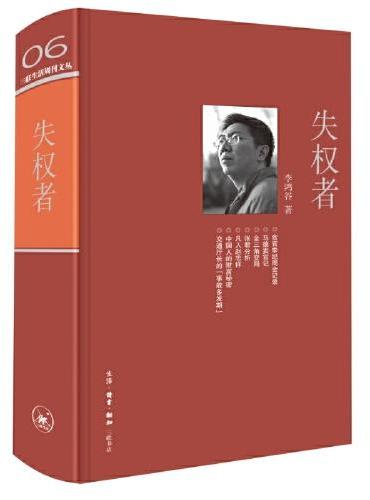
《
失权者(三联生活周刊文丛)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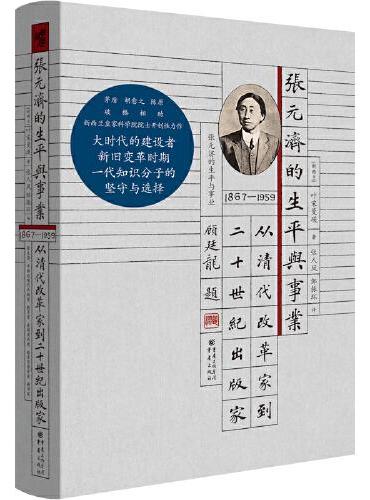
《
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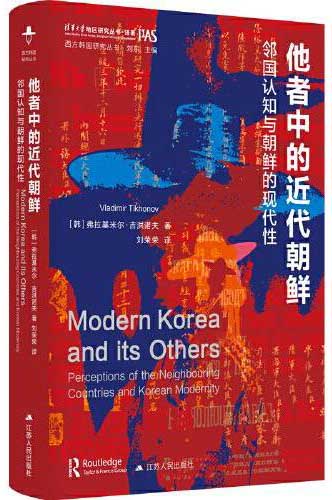
《
他者中的近代朝鲜(西方韩国研究丛书)
》
售價:NT$
398.0
|
| 編輯推薦: |
|
《千百种罪》被称为理查德福特迄今令人坐立不安的短篇小说集。书中每一个故事都与男女之间的亲密、爱情、婚姻和失败有关。
|
| 內容簡介: |
|
《千百种罪》是理查德福特2002年出版的第三部短篇小说集,收入十个短篇小说,被称为理查德福特迄今令人坐立不安的短篇小说集。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大都是美国中产阶级夫妻,每一个故事都与男女之间的亲密、爱情、婚姻和失败有关。作者深刻、坦率地揭示出婚姻失败、出轨背后,人生的种种荒诞、尴尬、痛苦和绝望。一对从事法律工作的夫妻去缅因州度周末,试图找回他们早已在婚姻生活中消失的激情;一个春天的夜晚,妻子在开车赴宴途中,向丈夫坦白她与当晚宴会的男主人出轨了;两个分别已婚的男女房产经纪人,在行业会议中偶遇出轨,他们心血来潮一起去看附近的自然奇观大峡谷,却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理查德福特说:《千百种罪》里的故事都是关于失败的,其中有些失败还非常惨痛。但它们不仅仅是关于出轨的,虽然大多数故事中有出轨的人物。它们还是关于被出轨这种罪过所掩盖的另外一些失败的不经意导致的失败,疏忽导致的失败,诚意导致的失败,各种失败。有时候,那些我们应该爱的人所遭受的失败,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是我写这些故事的原因。
|
| 關於作者: |
理查德福特,美国当代重要作家。1944年出生于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他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毕业后曾担任初中教师,后在华盛顿大学法学院读了一学期,即转学加州大学厄湾校区攻读创意写作硕士学位,师从著名作家奥克利霍尔和E.L.多克托罗。
1976年,他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我的一片心》,但销售惨淡。他相继在大学任教、为体育杂志撰稿。1986年,他发表长篇小说《体育记者》,第二年发表短篇小说集《石泉城》。这两部作品令他在美国文坛站稳了脚跟,他和雷蒙德卡佛、托拜厄斯沃尔夫等人一起,被称为肮脏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性作家。1995年出版的小说《独立日》是《体育记者》的续集,相继获得美国笔会福克纳奖和普利策小说奖。迄今,理查德福特一共出版八部中长篇小说,三部短篇小说集,并选编了多部美国短篇小说选。2016年,他获得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储奖。
目前他担任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写作教授。
|
| 目錄:
|
隐私
好时光
呼唤
重逢
小狗
托儿所
视线之外
支配
慈善
深渊
|
| 內容試閱:
|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隐私
那时还是我们婚姻的快乐时期。
我们住在东北部的一座大城市里。冬天。二月。最冷的月份。我那时,理所当然地还在尝试写作,我妻子在一家专门出版捷克科学论文的出版社当翻译。我们已经结婚十年了而且还沉浸在那份奇怪的、令人兴奋的幻想中,以为我们已经熬过了生活里最大的苦难。
我们租的那间公寓在城市南头的旧工厂区,居住空间只是一件大而空的房间,前后都有高窗,基本没有电灯。全部光源都来于自然光。之前的住客是一位著名的先锋戏剧导演,他就在这里上演了他那些晦涩的虚无主义的戏剧,所以四面墙都漆成了黑色,一面墙前还排着为他那一小群不满的观众所准备的坐席。我们的床--我妻子和我--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我们挂了一些黑色的背景幕布来保护自己的隐私。尽管,那是当然的,这里也根本没有人会来窥探我们的隐私。
每天晚上我妻子下班后,我们会走在冷而亮的街上找家饭店吃晚饭。之后我们会在某个酒吧里待上一个小时喝杯咖啡或者白兰地,激烈地讨论着我妻子在做的翻译工作,但是(幸运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我当时已经失败的作品。
我们所抱的希望,不用说,就是尽可能久地远离那间公寓。不仅仅是因为那里几乎没有光,而且每晚七点房东都会关掉暖气,所以到十点的时候--我们住的那一层,最高的一层--那里就会冷得只能待在床上盖上所有的毯子,动都不能动。那时候我妻子的工作时间很长总是处于疲惫状态,尽管偶尔我们回家时会有点小醉,会在毯子底下做爱,但大多数情况下她都是筋疲力尽地直接躺倒在床上在我爬上床之前就打起了呼噜。
所以有很多个冬夜,在那间寒冷,几乎空无一物的大房间里,我就这样醒着,经常由于刚喝的浓咖啡而直愣愣地醒着。我经常会从一扇窗走到另一扇窗前,看着外面的夜,向下看着那空荡荡的街道或者向上看着鬼域般的天空里城市建筑闪烁着的光亮,那些我甚至都看不见的建筑。我通常会披上一条毯子或者有时是两条,脚上穿着我童年时留下来的粗重的袜子。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寒冷的夜晚--透过公寓后墙的窗,最初是底下的小巷子,接着越过一片被拆除的电线工厂的空地,能看见和我们平行的街上的一栋公寓楼--我看见,在一间狭长的开着黄灯的公寓里,有一个女子正在慢慢脱掉衣服,看似完全遗忘了窗外的世界。
因为相隔的距离,我没法看得很清楚,或者可以说根本看不清楚,只能看出她身形很小,貌似很瘦,有很短的深色头发--从各方面看都是一个娇小的女子。她房间里的黄色灯光像是在燃烧,让她的皮肤显出闪亮的黄铜色,而她的动作,透过窗看上去有点仪式感并且略显不真实,如同一个剪影或者某部老电影里的动作。
而我,独自在这寒冷的黑暗中,把毯子像围巾一样裹住头,我妻子在睡觉,在我几步之外,毫无知觉--我被这一景象迷住了。起初我靠近窗子,近到我的脸颊都能感受到冷。但接着,意识到即使隔着这样的距离我也可能被注意到,我又闪回房里。最终我走到房间角落关掉我妻子放在床边的小台灯,这样我就完全隐身在黑暗中。又过了几分钟我打开一个抽屉找出那个戏剧导演留下的一幅银色歌剧眼镜,把它放在窗前,穿越窗外的黑暗空间看着那个女子,而我自身也处在黑暗中。
我不知道我都在想些什么。毫无疑问我被激起了性欲。毫无疑问着迷于在黑暗中向外窥探的秘密感。毫无疑问我爱其中含有的不正当性,我妻子就睡在身边却对我所做的事一无所知。还可能我甚至喜欢那包围着我的寒意,如同夜晚一样完整,甚至可能感受到那女子的形象--在我眼里她年轻而不够谨慎甚至不够庄重--抓住了我,使我与世界隔离,让世界停止并完全得以表达,就像是被我视线连接起的两极。我现在很确定所有这些都和我即将到来的失败有关。
事情仅此而已。在之后的几个晚上我一直醒着看着这个女子,任我的妻子在疲惫中睡去。每一晚,接下去的一个星期都是,这个女子会出现在她的窗前慢慢脱掉衣服,就在她的房间里(我从来没有去想象的一间房间,尽管她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像是一头跳跃的鹿的画)。当她脱完衣服,展现出她瘦骨嶙峋的肩膀,小小的乳房,细瘦的腿,胸腔和微微凸起圆润的肚子,这个女子会在黄铜色的灯光里在房间里搜寻着什么,从一扇窗到另一扇窗,在我看来这举动像是一种倦怠的仪式化的舞蹈或者可能是一种戏剧动作的模式,起身,俯身,伸展双臂,弯下脖子,同时她的手做出各种优雅轻快我无法理解也不想去理解的手势,我被她的裸体以及偶尔看到的她双腿间的黑色地带所吸引。这一切带来的全部就是激起的性欲,秘密感和不正当性,至于其他真的没有什么了。
我这样持续了一星期,如我所说的,然后我就停止了。有天晚上,我再次裹着毯子,拿着歌剧眼镜来到窗前,看见那片空地后面的灯光亮起。过了一会儿我什么人都没有看见。接着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我转身回到了床上我妻子身边,她的身体温暖,有白兰地的味道,出着汗,在毯子底下熟睡,我自己也就这样睡去了,从没想过要再去看那窗外的景象。
一周以后的某天下午,我在一阵挫败感和无意义的绝望情绪中离开书桌,潜入寒冬的日光中,走过一排由老旧建筑改造成的服饰店及成功艺术家画廊组成的时尚产业。我向着河的方向右转,河面上结着大片的灰色的冰。我继续向前进入大学区,差不多要到我妻子正在工作的地方了。接着,随着天光渐暗,我转身往回走,我的脸又冷又硬,双肩僵硬,没有戴手套的双手冻得发红。当我转过一个街角准备抄近路回我的街区时,突然意外地发现我正经过那栋被我窥视了多日的公寓大楼。尽管我以前从来没有经过它,甚至没有在白天见过它,但它的某种特质让我认出了它。而就在那个时刻,一位女子正要进入这栋大楼高大的前门,她就是那个我偷窥了几个晚上,给我带来欢愉及毫无疑问的秘密的安慰的女子。我认得她的脸,这是很自然的--小而圆以及,如我所见,令人印象深刻。而令我惊讶的是,虽然并不至于让我懊恼,她是个老人。她可能有七十岁或者更老。是中国人,穿着单薄的黑裤子和单薄的黑外套,那里面的身体一定和我一样冷。事实上,她一定快冻僵了。她手上挎着拎着装着食品杂物的塑料袋。我停下脚步看着她的时候她也转过身向下盯着我看,那表情我现在能想到的只是漠然夹杂着一丝最细微的感觉的威胁的神色。毕竟,她是个老人。我可能突然有一种冲动去伤害她,而且也很容易做到。但当然这不是我的想法。她转回身匆忙拿出钥匙塞进锁里。我听见门闩深沉地弹回时,她又朝我看了一次。我什么也没有说,甚至没有再看她一眼。我不想让她去思考我脑子里在想的东西或者是我没有在想的东西。我接着向前走,感觉有点怪但丝毫没有感觉被意外地背叛,只是走过那栋大楼来到那条通向我的房间,我自己家的房门的街道,我的人生,以其在那一刻的状态,进入了第一次,为了生存的循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