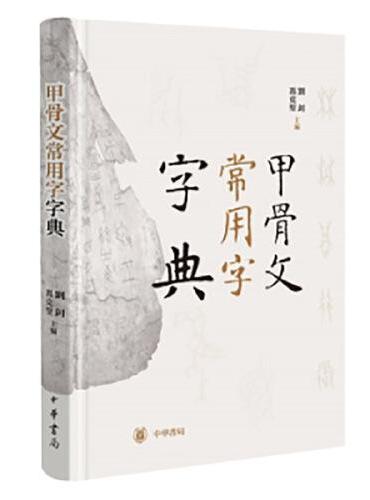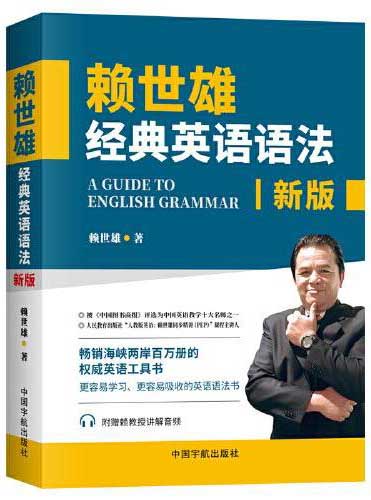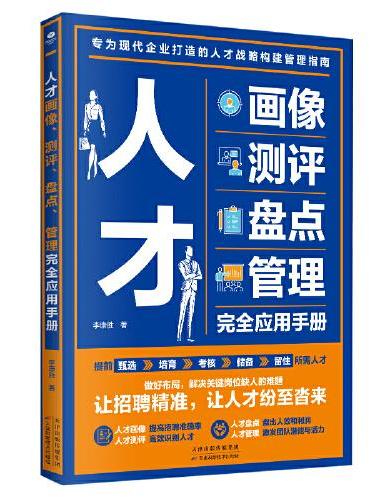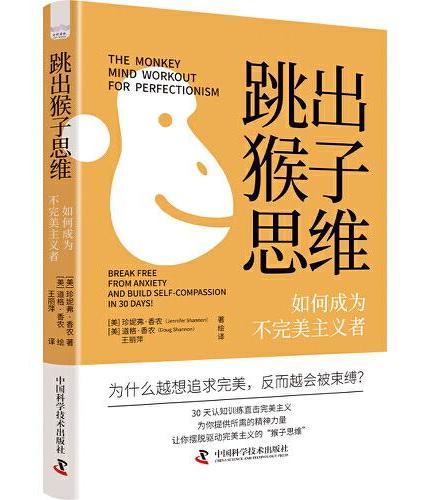新書推薦:

《
饮食的谬误:别让那些流行饮食法害了你
》
售價:NT$
296.0

《
三千年系列:文治三千年+武治三千年+兵器三千年
》
售價:NT$
9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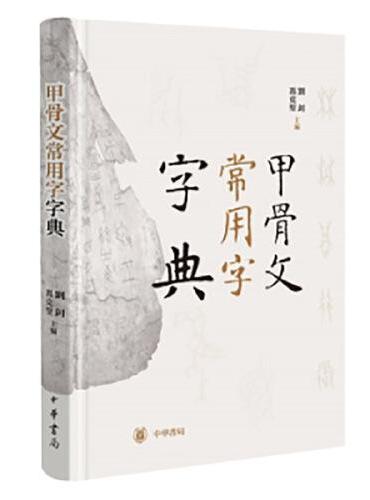
《
甲骨文常用字字典(精) 新版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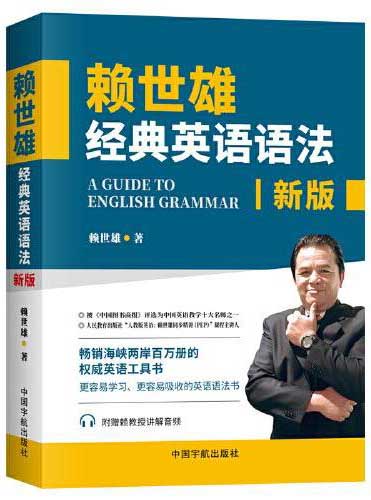
《
赖世雄经典英语语法:2025全新修订版(赖老师经典外语教材,老版《赖氏经典英语语法》超32000条读者好评!)
》
售價:NT$
305.0

《
影神图 精装版
》
售價:NT$
653.0

《
不止于判断:判断与决策学的发展史、方法学及判断理论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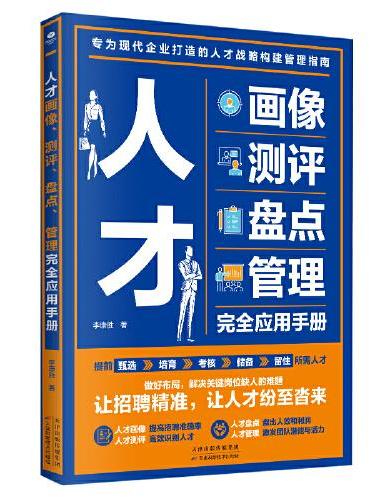
《
人才画像、测评、盘点、管理完全应用手册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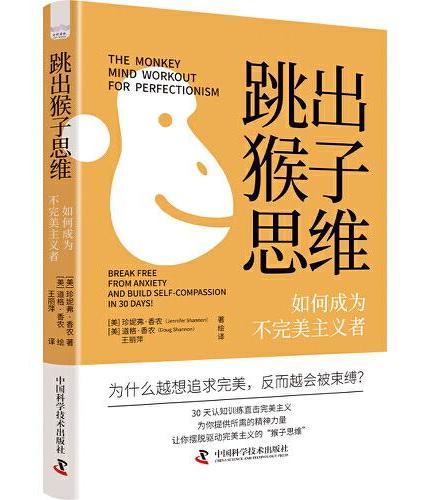
《
跳出猴子思维:如何成为不完美主义者(30天认知训练打破完美主义的困扰!实现从思维到行为的全面改变!)
》
售價:NT$
301.0
|
| 編輯推薦: |
《典型的美国佬》
1.美国华裔文学代表作家任璧莲zui受瞩目的长篇小说。
2.著名华裔作家汤亭亭、谭恩美、哈金诚挚推荐。
3.《纽约客》《大西洋月刊》《波士顿环球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新闻报》联袂推荐。
4.荣获纽约时报年度图书奖,入围全美书评人协会奖。
5.华人追寻美国梦的心路历程,中国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谁是爱尔兰人》
1、美国华裔文学代表作家任璧莲zui受瞩目的短篇小说集。内容并不仅仅限于移民经历,还涉及宗教、艺术以及其他方面的主题,如家庭关系、自我追求、寻根之旅等。
2、著名华裔作家汤亭亭、谭恩美、哈金诚挚推荐。
3、《纽约客》《大西洋月刊》《波士顿环球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新闻报》联袂推荐。
4、入选《纽约时报》年度书单、二十世纪zui佳美国短篇小说。
5、华人追寻美国梦的心路历程,中国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
| 內容簡介: |
《典型的美国佬》是一个美国故事。小说讲述了三个中国知识分子20世纪四十年代来到美国追寻各自的美国梦的一段痛苦挣扎。拉尔夫张、姐姐特雷萨、妻子海伦组成的张家人刚入驻美国的时候,由于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使得张家人对美国文化特别的排斥,还具有一定的鄙夷态度。 然而,在追寻自己的美国梦的过程中,张家人面对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陷入一系列困境,在迷失与绝望中自省,他们逐渐理解了典型美国佬的实质,并也成为了之前被自己所蔑视的美国佬。
《典型的美国佬》获得1991年度纽约时报年度图书奖并入围全美书评人协会奖。
《谁是爱尔兰人?》是任璧莲zui负盛名的短篇小说集,出版于1999年,共收录其zui有代表性的八篇短篇小说,分别是《谁是爱尔兰人?》《同日生》《水龙头旁的幻觉》《邓肯在中国教英语》《守得云开》《秦》《在美国社会》《房子,房子,家》。同名短篇小说《谁是爱尔兰人?》通过一个华人移民老太太之口,讲述她对混血外孙女的生活方式和爱尔兰亲家的做派,由zui初的看不顺眼到zui后的习以为常,并且在爱尔兰人的逐渐影响下,zui终连自己的族裔属性也搞不清了,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华人还是爱尔兰人。
|
| 關於作者: |
|
任璧莲(Gish Jen),第二代美国华裔作家。1949年前后,其父母从上海迁往美国。她于1955年生于纽约长岛,197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得英语文学学士学位,而后在斯坦福商学院进修,1983年在爱荷华大学写作班获得小说艺术硕士学位,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文学创作。任璧莲和谭恩美、李古思构成第二代美国华裔文学的主将。
|
| 目錄:
|
《典型的美国佬》
第一部 甜美的反叛
初出茅庐
情窦初开
坠入情网
风云迭变
在地下室
解救
特雷萨
继续解救
第二部 家
远离家庭的海伦
新生活
冷彻肌骨
为姑子做媒
胡思乱想
一见钟情
格罗弗驾车
等待
海伦在家
最后的进展
第三部 如此新生活
张家佬
拉尔夫驾车
激情
考试
爱的激励
新居
终身教职
坐在牛奶瓶洋铁皮箱上
第四部 结构松弛
神秘莫测
拉尔夫得到了回音
魔力商标,千真万确
悦耳的音乐
从前的张家佬
海伦在呼吸
拉尔夫的新主意
痛得及时
靠数字生活
盖房
留心屋顶
第五部 寝食不安
钢铁巨人
海伦的房屋
一个黑洞
阖家团聚
在猫屋里
拼命
喂狗
走进白色走廊
方寸已乱
信念
译后记
《谁是爱尔兰人?》
谁是爱尔兰人?
同日生
水龙头旁的幻觉
邓肯在中国教英语
守得云开
秦
在美国社会
房子,房子,家
|
| 內容試閱:
|
典型的意义
这一个故事说的是中国人。小说开篇第一句话是这样的:这是一个美国故事。确实如此,尽管说的是中国人的故事,发生的场景在美国,追求的目标是典型的美国梦。主人公拉尔夫张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很久以前了,但走过的路,留下的痕迹和现在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比较起来,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从这个角度而言,似乎可以说美国梦的道路一直没有多少变化。
拉尔夫到达美国时,那是1949年前。他来读书,他要学位,他要做学问,他想过要留在美国吗?也许没有。但是时局变化超过他的想象,他被留在了美国,这以后他走过的路重复了此前和此后很多中国人踩出的足迹。先是身份黑了,无法继续读书,被迫到餐馆打工,没日没夜,人鬼不知,落魄到了想死。正在这个时候他的姐姐也从中国到了美国,非常碰巧地把他从水深火热中救了出来,继而继续读书,拿到学位,留下当了助教,还结婚生子,购车买房,这不,一步一步成为了美国人。有一阵子生活的目标就是为了继续努力攻下终身教授一职。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实现了这一目标。终于成为了典型的美国人。不过,惬意的生活似乎并没有最终带来成功的感觉,他还要什么?钱,做一个有钱人?靠什么路子?开饭馆。典型的美国人用的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办法。他又一次成功了,辞去教授职位,干上饭店老板行当,每天点钞票入迷。一步一步美国梦蒸蒸日上。
远离家庭的海伦 远离家庭的海伦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海伦在中国的生活都是一帆风顺的。她前面曾有过一对孪生姐姐,但都死掉了。所以,尽管她是个女孩,而且一生下来就险象环生,呼吸极不正常,但是她父母仍然感到欢天喜地。后来,她有幸生存了下来,又时不时地染上重病,从而使她赢得了格外的照应。或许她本来也不需要那么多的照应,诸如牵涉到她祖父解雇医生之类的事情。她妈妈总是忧心忡忡,要不就在海伦的床边轻声嘀咕,声音很低,海伦听不到,但却可以感觉到。她的话激起了一种感觉,一阵骚动,她发誓,这种东西决不会来自身外。
但是她仍感到满足。她生性淳良,所以,她的两个妹妹和三个弟弟本来是应该讨厌她的,结果却争先恐后地去讨她的喜欢。他们送她上楼下楼,为她唱歌。她是全家的娱乐。她的生活抱负就是永远呆在家里。美国人一般好动,而中国人则好静。动是一种堕落,一种流放。对海伦而言,静特别正确。她童年的一个麻烦事就是,她知道她如果没有病死,那么最终就会出嫁,和婆婆家住在一起。与其这样,她希望还不如死掉。她感到非常虚弱,成天听其他女孩讲故事,例如什么一个邻居的女儿从杭州一直走回家啦,却又被送了回去。当然,这个故事比较极端,但是她朋友的表妹怎么样呢?嫁到乡下,在一只大的铜锅里洗澡。锅下是一坑的柴火,好像她是一条猪后腿,而锅里的水则已经被她公公,丈夫,丈夫的七个弟弟和婆婆所用过。不要担心,海伦的父母安慰她说,我们会给你找一个好人的,一个你也喜欢的人。没人会打你。但是海伦知道,至多他们会送她去一个新奇而贫穷的地方,在一个奇怪的世界边缘,好像有一个狂暴而漆黑的大洋将她和她所热爱的人分开。
如今她在美国。头几个月里,她几乎是一坐下来就想,如果她那仅有的几件衣服穿破了,她会怎么样?她得多么地小心啊!特蕾萨到处奔波,要找出她那位躲避着的弟弟。海伦尽量走得少些,走得轻些,这样鞋子就可以节省下来,延续到国民党解放中国,那时她就又可以回家了。她的学习和她走路一样轻,她为什么要拼命去学英语?上课的时候,她给家里写信,每天都希望有回信,但是音信杳无。她一个星期去三次唐人街,将它看作上海的另一个外国区,就像英租界或法租界。她学会了烹调,这样她就有中国饭吃了。没有中国饭吃的时候,她就不吃。特蕾萨(什么都吃,甚至奶酪和沙拉也吃)当然觉得她傻。在上海你吃外国菜,特蕾萨说[她叫它dacai(大菜)],为什么在这儿就不吃了呢?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海伦还是不吃,她们两人都认为这会使她生病。
但是她过不惯,就是生病也是这样。
不能老是这样下去。最后,信仰动摇,海伦学习更用功,路走得也更多。她买新衣,给父母的信少了。她依然整个下午独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呆望着,就像希望幽灵前来拜访,或染上消耗病似的。但是她也培养出一种对美国杂志和美国报纸的爱好。美国收音机她把菲尔科牌收音机放在起居室角落里,靠近桌边,这样她就可以不停地听。她跟着收音机一起唱:玉米和象的眼睛一样高她不再坚持要把所有的衣服都叠起来,而是用衣橱。她开始说红,白,蓝,而不说蓝,白,红,区分兴趣和感兴趣和使人感兴趣。她得了几次感冒。她嫁给了拉尔夫,正式接受看上去已经是事实的东西她确实已跨越了一个狂暴而漆黑的大洋。现在是她尽量习惯这种流放生活的时候了。
新生活 新生活
除了她自己真正的家,海伦哪儿也过不惯。不过,拉尔夫和特蕾萨对他们的新安排所流露出的极大热情有时候也不禁使她受到感染。一切看上去多么的合理!拉尔夫应当娶她,特蕾萨的朋友这就好像他们的父母将会如此安排似的。
你不认为她有点像我们的小妹吗?有一次,拉尔夫问特蕾萨。
有点像。特蕾萨说。
海伦脸红了。
这么凑巧,拉尔夫说,你知道,那天,学校里有个人在谈论一个人,他将房子拆毁,然后重建,好像这一切是理所当然似的。
这就像我们,像我们这个家。特蕾萨深有同感。
奇怪的是,这个房子有个漏洞。所以说,如果有漏洞,那么这个人为什么要搬?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他一直不喜欢房屋的内部结构。太小了。
嗯,特蕾萨说,漏洞不漏洞,或许他已习惯了。
我猜是这样的吧。拉尔夫不太肯定地说。
海伦叹了口气。在家里,谈话总要给她留有余地。人们谈下去之前要停顿一下,看看她。这里,她得将自己投入会话之中,比方说就像现在的暂停一样。
你知道那句有关妻子脚踝的谚语吗?她轻声地说。
什么?拉尔夫问。
不要插嘴,特蕾萨说,她正在说。
我听不见。
那句谚语。海伦放大了声音。你知道那句谚语,有关妻子脚踝的?拴在她丈夫的脚踝上?
当然了,特蕾萨鼓励道,用一根长长的红绳子。从她生下开始。
那么,我想我的脚踝被拴到了我丈夫和姑子两个人的脚踝上。
什么!两个人?还有我的脚踝?特蕾萨一边抗议,一边大笑。接着她又用英语问道:你是在拖我的腿吧?这是双关语,意为:你在拿我开玩笑吧?译者
他们一齐笑了起来。妙!拉尔夫嚷道。
是妙!海伦表示同意。
不过,他们快活吗?至少搬家之前是这样,现在他们该搬到125号大街北面一座年久失修,没有电梯的公寓里了,这里有一股霉味和狗味。这就是最穷的学生所居住的地方。这里,学生们尽量操持好家务,因而房间和过道大为迥异。要节省。拉尔夫,海伦和特蕾萨都同意这一点。然而,他们后来感到震惊。这么多的黑人!多年之后,他们常摇摇头,说他们受到了歧视,但是在当时,他们感到非常困窘。还有,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公寓?这套公寓倾斜。特蕾萨用手指碰了一下柔软的灰泥,结果,潮湿的灰泥就像雪崩似的落了下来。我们不是那种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的人。她说。
但是他们的房屋管理人似乎认为他们就是这种人。那个彼得!他期望他们一直站在他的门口,他在锅炉旁闲逛的时候,他那条半德国种的牧羊狗就向他们扑来。至于他们的境况紧急吗?他会问。只是无论是与不是,他都不会来不来看他们的水管问题,不来看他们的天花板问题,不来看卧室后面墙上的裂缝,而这裂缝看上去是要越裂越厉害。
裂缝。拉尔夫一边说,一边将狗赶跑。油漆剥落,大裂缝。起先还挺礼貌。后来火气上升:你什么也不管!这座房子要倒下来了!结果彼得有一次说他会过来转转。有一次,他解释说他的老板这座公寓的主人几个月前已经在屋顶上作了点修补。
是吗?
咳,我不知道这家伙说的一切是否有道理。他说。
Fantong饭桶,拉尔夫叫他。海伦和特蕾萨都笑了起来。最令人烦恼的是:裤子的拉链已经张开,双脚搁在那张无腿的办公桌上,狗在门口,他要经常去翻查课程表,一张,又换一张,有时两张一起翻。他应该做律师?医生?工程师?好像他可以做工程师!好像他可以拿到博士学位!
彼得说,一个人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这个人在愚弄自己!拉尔夫摇了摇头。
与此同时,海伦雇了一个水工,刮掉了松散的涂料,这样,它就不会悬挂在那儿,又将拉尔夫的文件柜推进卧室,挡住裂缝。这个地方还可以称作家吗?文件柜旁,她放了一只高高的书橱,跨在它们两个之间的是一个宽大的小书橱,站在上面正好可以清理天花板。
不错。拉尔夫称赞道。
我从杂志上看到的,海伦告诉他,这叫组合壁橱。
组合壁橱。拉尔夫重复道。后来他评论说,正是从她这种解决办法中,人们可以看出他们张家是如何地适应新生活。
不像那个彼得,拉尔夫说,他在欺骗自己。
消遣:拉尔夫喜欢模仿彼得的走路。他会颓然倒下,一只手指擦着耳朵,但是特蕾萨兴致勃勃地喊道:不,不像这样。她又拖着脚慢吞吞地走着,露出了她的膝部。海伦哈哈大笑起来。他们研究彼得擤鼻子的样子,这样他们就不会搞错;他们研究他的喷嚏,他的笑,还有他妄自尊大翻阅年历的方式。好了,让我看看,特蕾萨大声吼道,典型的彼得!拉尔夫大声响应:典型,典型的彼得!拉尔夫甚至还模仿彼得的杂种狗博依博依,神气活现地到处游荡,炫耀似的狺狺狂吠,称他自己为拉尔夫,拉尔夫。他来回踱着步,一只刷子尾巴一扫一扫地挡在门口;他向海伦和特蕾萨扑去,她们就用杂货袋来躲避。不久,不知怎么的,典型的彼得变成了典型的美国佬,变成了典型的美国佬这个,典型的美国佬那个。典型的美国佬不好。拉尔夫会说。特蕾萨说:典型的美国佬不知道如何行事。海伦若有所思地说:典型的美国佬就是想做万物的中心。当然,他们确信,他们在美国这儿不会变疯,这儿没人管他们。当他们对欺骗他们的店员摇头时,他们更确信:典型的美国佬没有道德!他们讨厌一个邻居猛地折断门锁上的钥匙时说:典型的美国佬使用蛮力!或者他们讨厌另一个邻居的小孩,他声称民主党的对立面是一只企鹅。民主党的对立面共和党(Republican)和企鹅pelican两个英文词谐音。译者(企鹅?拉尔夫问道。一种鸟。特蕾萨解释道。接着他也笑了起来。典型的美国佬正好是哑巴!)他们到处都发现故事。一个小男孩偷了他父亲weiyi的一条裤子。一位母亲将她女儿拴住。一位动物训练员一气之下,将他老婆的耳朵咬掉了。
是用他的嘴吗?拉尔夫不相信这个故事。
但是这是真的。海伦在美国报纸上读到了这个消息。有一天,报纸诚实地承认,他们是正确的。二战以来,美国人已经堕落。至于原因却极为复杂。坐在兼做起居室和特蕾萨卧室的绿色房间里,海伦大声朗读着报纸上的一篇文章的全文。拉尔夫和特蕾萨则全神贯注地听着。
那正是我们所说的。拉尔夫最后发表了评论。他看了一下特蕾萨;她点了点头。
美国人现在要放松一下,好好享受一番,她说,他们厌倦定额分配。
你再读一遍好吗?
海伦很高兴她在家中至少有了这么一个摇摇晃晃的席位。当然,表明他们聪明的证据还有。想想看,他们在外国所能看到的是事情的真相!在他们头顶上,随着他们的聆听,天花板灯光在他们的头发上落下了光晕。他们听到的一切都会好起来。
weiyi的问题是为什么拉尔夫彻夜不眠,聆听隔壁一张床上海伦睡觉的声音。这不仅仅是和一个女人同房使得他和街灯一样彻夜不眠。再也不是这个问题,他已习惯了这个伴侣,或者说已差不多习惯了习惯她早上隔着床罩穿衣,光着柔软的膀子去打扮,习惯她有时候隔着门和他姐姐讲话。他多多少少已适应了叫妻子,适应了别人叫他丈夫,不管这意味着什么。他甚至适应了性生活,对此他一天再也不想要两次了。一次就足够了。笨手笨脚地摸索已成了记忆。他已开始轻松自如。他会绕到她床上,抚摸一番,于是她就会转过身来。再抚摸几下,解纽扣,接下来就是轻点,轻点,听听会不会吵醒他的姐姐。这很简单。安静,安静。
但是海伦从不说什么,或者说连一点响声都不想弄出。她太安静了,拉尔夫感到着急,不仅仅是一起在床上,而且是整个晚上,在他们自己的床上。她怎么了?她隐藏东西而他找寻:钥匙,电池,还有信。她把杂志放在床垫下面。她还会向他藏什么?或许是一种病,他想。他使劲地听着。因为她不仅仅呼吸,她吸进,然后停止,然后再一点一点地将气吐出。他斜视了一下圆形天花板,想弄出她所弄出的声音。轻轻一声,好像她一直不在出气。或者说好像有什么阻力哪儿?在胸腔里?不,在喉咙里。他感到他自己的喉咙里或许就有一小扇门钉着。他想象他出去看医生。肿瘤。手术。她想埋在哪儿?他甚至都不知道。或者说更糟的是,他头脑里有一幅妻子没有喉咙的图画。她怎么呼吸?她怎么吃东西?他咽了一口。如果他知道会出这种事,那么他会娶她吗?如果他不愿意,那么他会娶她吗?
他希望有个人谈谈,有个人能够告诉他,在新婚夫妇中,爱的比重是多少,履行新责任和新义务的热情有多少,在各种纷繁的人类情感中,这些责任和义务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他们两人的对话超出一般人?少于一般人?他们的吻够吗?架打得多吗?出了什么事?他希望他是在中国,这样,如果他的婚姻出了什么问题,他可以讨个小妾。他想,那是一个更好的制度,毫无疑问。尽管他现在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他却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知道出了什么事。因为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他早就知道这辈子他会结婚,但是他从没有停下来想想,一旦结了婚,他会是个什么样子。他认为,结婚就是一个故事的结束,就像攻读博士学位,只是结婚故事更短,事情也更少。不是生活不会再起,而是生活处于其他领域。在家里,丈夫会发号施令,妻子顺从。他们在枕头下面找到和谐,就像孩子们在新年的早上找到栗子一样。
他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实际上,他呆在这里,凝神细听。这会儿她半转了个身子,这样她的脸就掉过去了。他根本听不到她。她停止呼吸了吗?他稍稍坐起了一点。一辆卡车撞上了一个坑洼,轰隆一下子过去了。远处的收音机,女高音,但是很微弱。他从背后将睡衣从头上脱下。
什么也没发生。他尽量镇定下来,像大地一样耐心。直到最后,这想法像曲折的雨水一样落到了他的头上这不是他等待的声音,而是别的东西,一种认可他所要做的一切就是保护她。他不想让她浮游到历史中去,浮游到时间中去,浮游到膨胀的浮团中去。他要她成为永恒,要她成为大厦,高大的建筑就根植于大地深处。
依然什么也没发生。他翻身起床,绕过通道,来到她的床前,浑身颤抖。他是多么地爱她啊他这么爱她,真可怕爱她的声音和存在,爱她的肉体相伴,爱她的做事方法卷起浴巾,用鸡毛掸掸灰。能够了解另一个人的习惯,知道她什么时候梳头,而且还知道她藏东西,这是多么地荣幸啊!他希望她不要藏东西。尽管如此,他还是喜欢她。他无法想象20年后他会怎么想。50年呢?让她到街上去走走会怎么样?他想把她放到一个缎纹盒子里。
他用手指碰了碰她的枕边。屋里的电灯呈电弧形上升,一直通向天花板,形成了半拱形条纹,灯下,他几乎可以看出她身体的起伏波动。但是他仍把手放在腋窝里取暖,然后又轻轻地捧起她的头。头枕在他的手上很沉,他想抓住她的头发,但这比他想象的要困难,他的一个手指悄悄地伸进她的耳洞。但是,他想把她的头转向他这一边。啊!她又呼吸了,好多了。她打了个呵欠,似乎受到了影响。
他唤醒她了吗?他一动不动,弓着腰,凝神细听。
她安顿下来了吗?
他决定数10下,然后再走。1,他开始数起来。2。
但是等数到11的时候,他还是悬在那儿她呼吸的时候他就屏住气,让呼吸停止,就像她让她的呼吸停止一样。
但是清晨一到,白日又再次降临。拉尔夫问海伦她是否有什么事要告诉他。结果什么事也没有(或者说她至少什么也不承认),于是孩子般的爱变成了青年的困窘,变成了成人的专横。
这样。拉尔夫做示范动作,吸进,吐出。要均匀,你明白吗?你应该这么呼吸。
海伦模仿着他,怯怯地问道:这样对吗?
对。拉尔夫发表了他的看法,再来一遍。
海伦又来了一遍。
再来一遍,他吩咐道,再来一遍。
海伦想了一下,然后尝试着屏住了呼吸。
不对,拉尔夫说,这样不对。
再做一遍给我看?她歪着个头,很高兴地看着拉尔夫兴致勃勃,像quanwei一样吩咐她的样子。
就这样循环往复,拉尔夫扮演丈夫,海伦扮演妻子。
后来,操练结束之后,拉尔夫走向正在切菜的海伦。在此期间,他已经见过了他的新导师,这一回不是平克斯他很想念平克斯,平克斯现在正全天咨询而是皮尔斯,罗得尼斯皮尔斯教授,他那把油乎乎的山羊胡子使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手艺人,而不是工程师。一个瘦骨嶙峋,爱吹毛求疵的家伙。不管如何,拉尔夫按照规定和他见了面,然后走了回来,现正准备学习。如果不是皮尔斯的声音在他耳边轰鸣,那么他一定会专心学习。这种轰鸣就像是将贝壳放到耳边,聆听大海的呼啸。详细一点,张先生。所以,他现在准备怎么办?我们是否可以说,这是一种爱好问题。爱好。工程师很多,我不想去预测。但是我要告诉你。帮一个忙。请相信我。你自己什么也没意识到。
他自己什么也没意识到。结果,这是他一个小时内第四次到厨房去。第一次是去尝汤,第二次是让海伦给他泡杯茶,第三次,他又尝了一些汤。放点盐。他当时说。她于是亲自尝了一口汤,然后充满深情地回答道:你知道什么?她叫他fantong饭桶,这正是他父亲从前所常说的。当然,她是在开玩笑。她不大开玩笑,但有时候她确实开玩笑。这时,她称此为戏弄,一个奇怪的字眼,有时候他感到奇怪,不知道她是否将这种字眼和她抽屉里的其他秘密藏在一起。不管如何,这一次她将下巴靠在洗涤槽上,以防她开玩笑的时候口水会流下来。当他呵她喉咙的痒时,她笑了起来,这使他感到很高兴。
但是现在,当他再次站到门口,回到她的身边,他想他看到她的肩膀担心似的耸了一下,她的肘缩了回去。不了,不了。她身子也不转地说道。或者说他认为她是这么说的,反正他进来的时候,她问的是:再来点汤吗?
他摇了摇头,只是站在那儿,想再呵她喉咙的痒,但不知道怎样去做。他知道有一种办法,但是他知道这种办法就像是船长靠着星星来掌舵。他凝视着头上一眨一眨的荧光圈。深不可测。当然,过了一会儿,他说道,来点汤。
她给他舀了一点。
放点盐。他笑了起来。
但是这一次她没有叫他fantong(饭桶)。相反,她用英语温顺地说了一句好吧,然后去取盐瓶。她想加点盐。有什么不对?但是,看着她一只手加盐,另一只手去抓鼻子,他感到自己不是一家之主,一个学者,而是一个高高站在木凳上的孩子,孤立无援,周围充满了活泼的气氛。他听到了一个温顺的声音:你父亲连我也会打的。
房间里回荡着温顺。
不对。
不对?
他听到自己在说:你的呼吸。
他们结婚时很年轻,但是重复以前说过的话已经是很容易的事情了。再做一遍给我看看。她说。头没有歪。他做了示范。她完美地模仿着他,同时切着胡萝卜。
那些胡萝卜有什么意思?
不对?仍然在切。
你连看都没看。
她抬眼看去。
很好,他说,我要你一直这样呼吸。
她同意了。但是十分钟后,他又看到她在屏气。
你在听?海伦问,从墙角那儿?
他勉强点了点头。
有什么不对的吗?
你在藏东西。他说。
藏什么?
一切。你有事情没有告诉我。
她削去胡萝卜上一块粗糙的皮。
说点吧,我要你说一点。
她想了一下。你要汤吗?
不要。
你要茶吗?
不要。
你要
不要!他大嚷着离开了。
他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情,使得他们产生了斗争而不是和平?几天以后,他们又吵了起来。过了一个星期,他们又吵了一次。一次又一次,直到他们对此已驾轻就熟直到吵架已成为他们婚后生活的一个核心他们所熟知的亲密形式。可悲的改进。拉尔夫敲着海伦的脑袋。什么话也没有?这儿有什么人吗?快点打开。敲打使拉尔夫感到凶猛,但却使海伦感到茫然,结果,他敲得更多。他命令她呼吸,指控她有意屏住气(实际上她一点也没有),直到她跑进另一个房间。有时候她会把门堵住,这样他就无法开门,于是他就会砰砰地敲门。他从未梦想过在自己的势力范围里竟会出现这么一个弱者。但是他会在那儿嚷叫:我是这一家之父!你听到了吗?是父亲,而不是儿子!她会放声痛哭。每到这时,他就会温柔而充满歉意地后退几步。这些是他们共同生活中最富有激情的时刻,也是最为焦灼地缠结在一起的时刻。那时,海伦感到这些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不可缺少啊!
与漫长的时间相比,她似乎处于某种更为深沉的事情里,而不仅仅是婚姻。这算正常还是不正常?海伦不知道,也不想去忌妒,但是她仍不住地看到,这些天来,拉尔夫对特蕾萨是言听计从,哪怕是他对她所说的话没有多大兴趣。例如:我们说典型的美国佬,这是错的。这是特蕾萨的新话题。她不止一次地解释说彼得只是一个工人,和他们一样,而博依博依只是一条狗。真的吗?拉尔夫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凝神细听,好像要去发现他那基本的人的价值。他歪着头。他皱着眉。有一次,他甚至拿小指去清理耳朵,好像耳垢就站在他和某个更为重要的拿学位的自我之间。
除了将希望寄托在时间上,海伦还能做什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