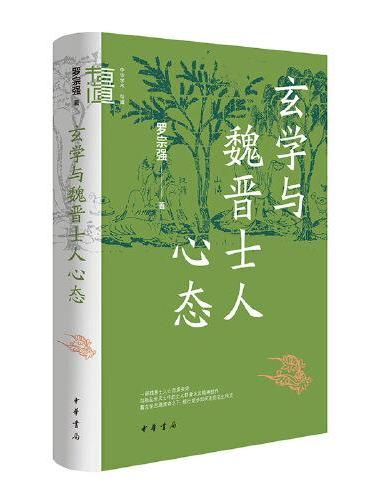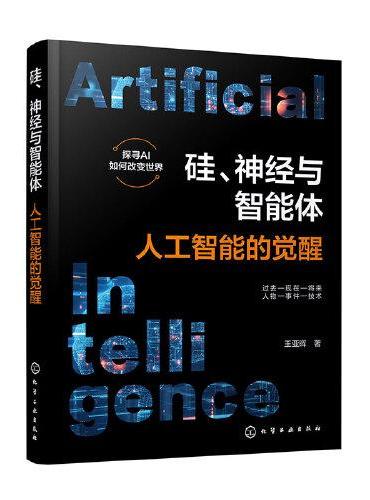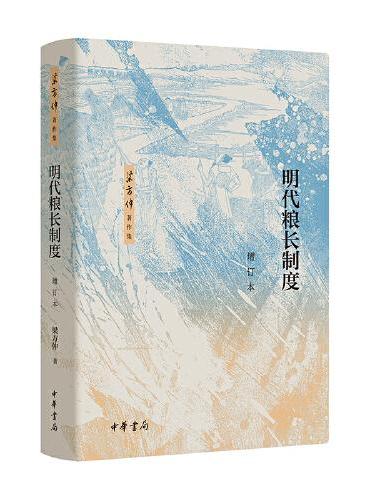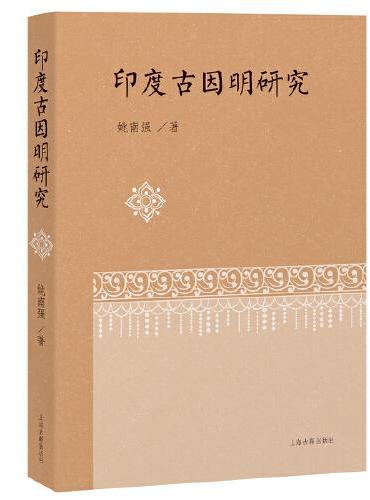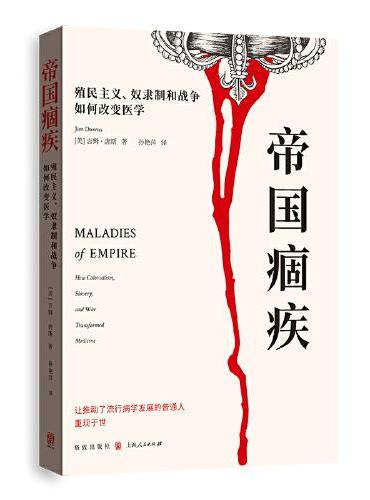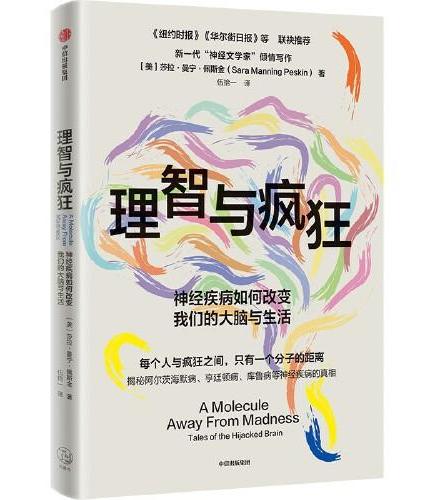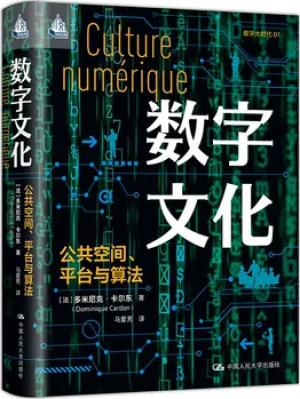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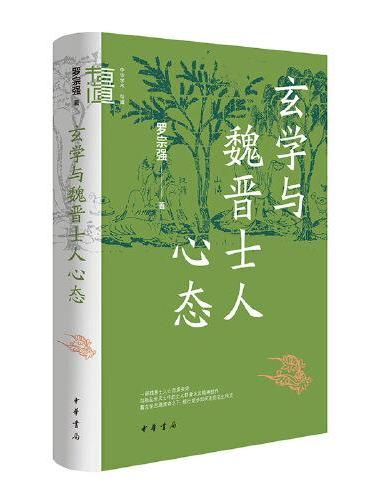
《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精)--中华学术·有道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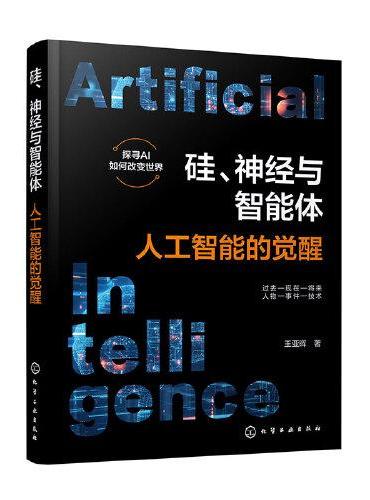
《
硅、神经与智能体:人工智能的觉醒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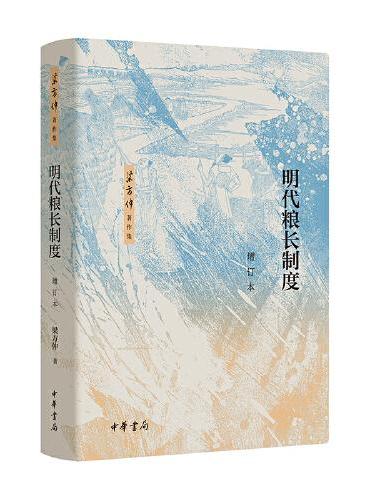
《
明代粮长制度(增订本)精--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NT$
316.0

《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本雅明精选集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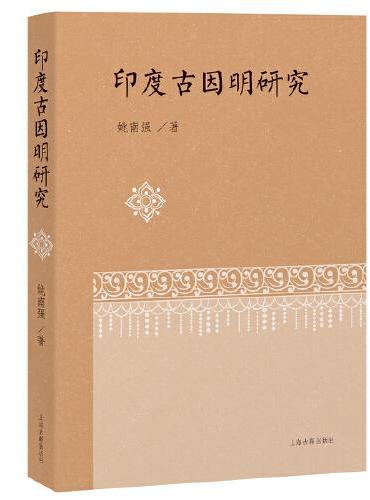
《
印度古因明研究
》
售價:NT$
6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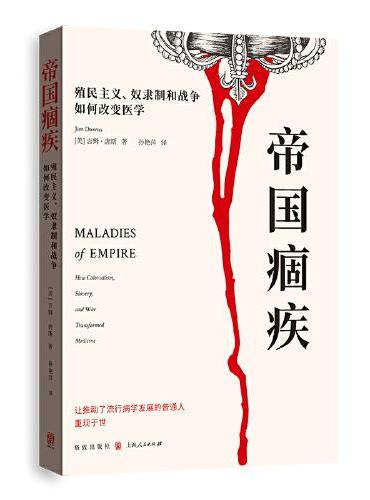
《
帝国痼疾:殖民主义、奴隶制和战争如何改变医学
》
售價:NT$
3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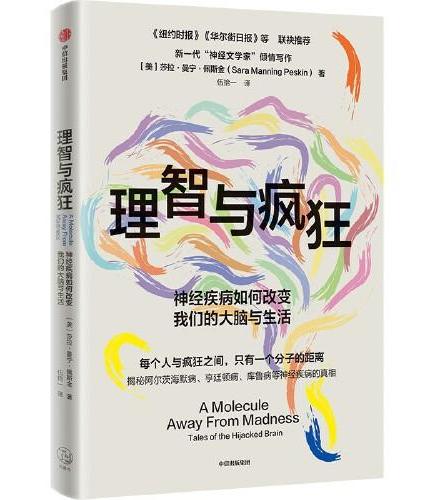
《
理智与疯狂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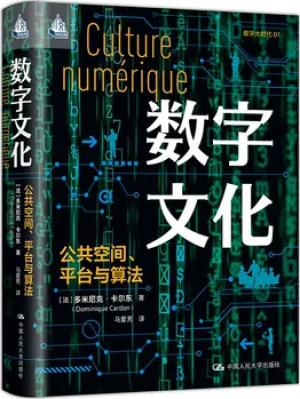
《
数字文化:公共空间、平台与算法
》
售價:NT$
505.0
|
| 編輯推薦: |
入围2016年布克奖的*华裔作家
邓敏灵 首部作品
一举斩获加拿大四项文学大奖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盛赞:
这*是一位杰出作家的首次亮相。作品的清晰度、从容度和那种纯洁的感情令我感到惊讶。
《简单的菜谱》是入围2016年布克奖的*华裔作家邓敏灵的首部作品,包含七个短篇故事,大多是以孩子或移民家庭中的子女的口吻,讲述了家庭成员或朋友之间的关系、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和文化之间的冲击,描写了移民所面对的各种适应问题、生长在破碎家庭的孩子的疏离感和混乱、对暴力的反应、孤独者的渴望和希望。本书因超出作者实际年纪的成熟思想、简洁而老练的文笔,一举斩获加拿大四项文学大奖,进入英联邦作家奖*处女作奖决选,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的赞赏。
|
| 內容簡介: |
《简单的菜谱》
入围2016年布克奖的唯一华裔作家
邓敏灵 首部作品
一举斩获加拿大四项文学大奖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盛赞:
这绝对是一位杰出作家的首次亮相。作品的清晰度、从容度和那种纯洁的感情令我感到惊讶。
《简单的菜谱》
入围2016年布克奖的唯一华裔作家
邓敏灵 首部作品
一举斩获加拿大四项文学大奖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盛赞:
这绝对是一位杰出作家的首次亮相。作品的清晰度、从容度和那种纯洁的感情令我感到惊讶。
《简单的菜谱》是马来西亚华裔作家邓敏灵的出道之作,写作本书时她才26岁,但其思想成熟,超过她的实际年龄,而且文笔老练、自然,2001年一经推出便斩获加拿大四项文学大奖,包括2001年加拿大作家协会30岁以下最具潜力青年作家奖、加拿大亚裔作家工作坊虚构类新兴作家奖等,并进入英联邦作家奖最佳处女作奖决选,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的赞赏。
《简单的菜谱》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包含七个短篇,叙述者大多是孩子或移民家庭中的子女,讲述了家庭成员或朋友之间的关系、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和文化之间的冲击,描写了移民所面对的各种适应问题、生长在破碎家庭的孩子的疏离感和混乱、对暴力的反应、孤独者的渴望和希望,等等。全书文笔简洁,但感情浓烈,故事不注重情节而着重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思想状态。
煮米饭可以用一种简单的方法,那是父亲在我小时候教我的。那时,我常常坐在厨房的台子上看着他用手又快又准地把米中的小土块、沙粒以及其他杂物剔出。他用手在水里搅动两下,水就变混浊了。他清洗米粒时发出很响的声音,听上去就像是一群昆虫在鸣叫。他一遍又一遍地淘洗,把水滤尽,再往锅里装满水。
煮饭的程序很简单。米淘净之后便可放水衡量水量的方法是把食指放进水里,让指尖碰到米的上方,水位不得超过手指的第一个关节。父亲对这些了如指掌,从来不用量杯。他闭上眼,用手指去感觉水的多少。
我仍旧不时地梦见父亲,他的光脚板平贴着地面,站在厨房中间。他上身穿着件前襟开扣的旧衬衫,下身是一条褪色的、腰间束条松紧带的便裤。他看上去与周围的环境洁净的台面、棱角鲜明的炉子、冰箱和明亮的水池很不协调。他在我记忆中的这一形象细节逼真、栩栩如生,时常让我感到惊异。
每天晚饭前,父亲都要履行这套淘米仪式:淘洗、滤水,然后把锅放进电饭煲。我长大些以后,他把烧饭的任务交给了我,可我从来没像他那么仔细。我总是走过场,把水弄得一阵哗啦啦响,而后把食指戳进锅里,去衡量水的多少。有时我把饭烧成稠糊一团。我对自己连这样一件简单的事也做不好感到不安。对不起。我会低声难为情地对大家说。可父亲听了之后却若无其事,大口大口地把饭往嘴里扒,好像他根本没注意到我和他的煮饭能力之间的天壤之别。他总是让筷子迅速地走遍自己的盘子,吃完最后一口。然后,他会吹着口哨站起身来,清理饭桌。他的一举一动是那么利索、笃定,让我确信世界上万事大吉。
妈妈有一次与我谈到负疚感。她自己的负疚感就在手心里攥着,就像是件祭品。但是,你的负疚感是不同的,她说。你不必抓住不放。想象一下,该是这样,她说,她的两只手摸着我的前额,然后伸进我的头发。你想象一下,她说。用脑子去看,你看见什么了?
皮肤上有块青紫,又宽又黑。
一块青紫,她说。集中精力看着它。现在,这是块青紫。但如果你集中精力,就能把它缩小,把它变得像针尖那么小。然后,如果你愿意,如果你能看见它,就能把它像颗灰粒一样从你身上吹掉。
她用双手摸着我的前额。
我试图照她说的那样去想象。我想象着把虚无的东西吹走,只是这些毫无意义的小东西,这样一种让我能神奇地一走了之的复杂局面。母亲让我相信自己的思想的力量,似乎我能让从来不存在的东西出现。或者反过来说,让存在的东西翻上几番,就会变得无影无踪。你看不见后果,整个东西也就烟消云散了。
|
| 關於作者: |
保邓敏灵 Madeleine Thien
1974年出生于温哥华,父母是七十年代早期移民加拿大的马来西亚华裔。她曾在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学习现代舞,后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文学。2001年推出短篇小说集《简单的菜谱》,迅速在国际文坛大放异彩,赢得加拿大四项文学大奖,并进入英联邦作家奖最佳处女作奖决选,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的赞许。其长篇小说《确然书》手稿完成后不到一个月即售出美国、英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等十六国版权,2006年出版后成为加拿大年度畅销书,获《环球邮报》最佳图书提名,倾倒全球无数读者;她凭此力作与村上春树、获得布克奖的印度作家基兰德赛一起入围美国桐山文学奖决选名单。2016年,她的最新长篇小说《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入围布克奖。
邓敏灵曾参加许多国际文学节和文学交流项目。2008年,她参加上海市作家协会首届上海写作计划,成为驻市作家。
|
| 目錄:
|
目录
001 简单的菜谱
017 俄勒冈记事
046 我和波拉
065 电讯稿
083 房子
106 子弹头列车
132 温哥华市的地图
|
| 內容試閱:
|
简单的菜谱
煮米饭可以用一种简单的方法,那是父亲在我小时候教我的。那时,我常常坐在厨房的台子上看着他用手又快又准地把米中的小土块、沙粒以及其他杂物剔出。他用手在水里搅动两下,水就变混浊了。他清洗米粒时发出很响的声音,听上去就像是一群昆虫在鸣叫。他一遍又一遍地淘洗,把水滤尽,再往锅里装满水。
煮饭的程序很简单。米淘净之后便可放水衡量水量的方法是把食指放进水里,让指尖碰到米的上方,水位不得超过手指的第一个关节。父亲对这些了如指掌,从来不用量杯。他闭上眼,用手指去感觉水的多少。
我仍旧不时地梦见父亲,他的光脚板平贴着地面,站在厨房中间。他上身穿着件前襟开扣的旧衬衫,下身是一条褪色的、腰间束条松紧带的便裤。他看上去与周围的环境洁净的台面、棱角鲜明的炉子、冰箱和明亮的水池很不协调。他在我记忆中的这一形象细节逼真、栩栩如生,时常让我感到惊异。
每天晚饭前,父亲都要履行这套淘米仪式:淘洗、滤水,然后把锅放进电饭煲。我长大些以后,他把烧饭的任务交给了我,可我从来没像他那么仔细。我总是走过场,把水弄得一阵哗啦啦响,而后把食指戳进锅里,去衡量水的多少。有时我把饭烧成稠糊一团。我对自己连这样一件简单的事也做不好感到不安。对不起。我会低声难为情地对大家说。可父亲听了之后却若无其事,大口大口地把饭往嘴里扒,好像他根本没注意到我和他的煮饭能力之间的天壤之别。他总是让筷子迅速地走遍自己的盘子,吃完最后一口。然后,他会吹着口哨站起身来,清理饭桌。他的一举一动是那么利索、笃定,让我确信世界上万事大吉。
*
父亲站在厨房中间。右手拿着一个装满水的塑料袋,袋里装的是一条活鱼。
尽管那鱼的嘴仍在一张一闭,很难说它还在呼吸。我伸手去摸它,用手指隔着塑料袋触摸鱼的腮和它那柔软但鼓出来的身子,还用指头去按它的眼珠。那鱼直愣愣地看着我,无力地左右扭摆。
父亲把厨房的水池里装满水。他迅速地把袋子口朝下一倒,鱼便顺着水游出,身体扭动着,蹦跳着。我们用眼睛盯着它,我两脚踮着,下巴撑在台面上。那鱼有我的手腕到胳膊肘那么长,贴着水池边游动着。
父亲开始做晚饭,我继续在一边看鱼。在头顶上的水的挑逗下,那鱼把身子折起来,想要转身或游动。尽管我用手指在它的身子周围划了些小圈儿,可那鱼还是原地不动,只是在冷水里左右摆动着身体。
往往一连几个小时,家里只是我和父亲两人。母亲工作,哥哥在外面玩,我和父亲坐在沙发上选看电视节目。他喜欢烹调实况表演节目。我们一道看《与甄共厨》时,父亲时常对甄厨师的烹调技艺加以评论。当甄厨师把橘子皮变成天鹅时,我都看呆了。可父亲有些不屑一顾。这我也会,他说,并非天才才会弄这两下。他把一根葱放在水里,叫我看他怎么让葱像花一样开放。这种小招数我可知道不少,他说,比老甄多多了。
可是,当甄厨师演示如何烧北京烤鸭时,他却很认真地记笔记。而且,对甄厨师用的双关语他会很开心地笑起来。让我们一道走野道来烧这菜!甄厨师用他的扁勺指着摄像机说。
哈,哈!父亲笑得双肩都抖动起来,他说,走野道!
早上,父亲送我上学。下午三点,我们又从学校走回家。一路上,我会忙不迭地把一天所学的东西全告诉父亲。腕龙(恐龙的一种)只吃软软的蔬菜类植物。我对他说。
父亲点着头说:那跟我一样。来,我来看看你的前额。我们在路上停下,面对面地站着。他俯身仔细看了我的前额之后说:你的前额很高。聪明的人前额都高。
我骄傲地向前走,步子迈得和父亲一样大。先右,再左,再右,当我的脚步与父亲的合上拍之后,我高兴极了。我们走起路来像是一个人似的。父亲的手很巧。他会坐上一个小时不动窝,用个圆勺把西瓜掏空,而后把瓜皮刻成一座城堡。
我父亲出生在马来西亚。他和母亲一道在我出生前几年移民来加拿大。先去蒙特利尔,最后在温哥华定居。我出生在雨绵绵的温哥华,可父亲则出生在一个水滂沱的雨季国度。我小的时候,父母曾经试着教我学他们的语言,可谈何容易。父亲表情和蔼地用拇指轻轻地摸着我的嘴,像是要发现是什么让我在学习语言方面与他们不同。
我哥哥出生在马来西亚。可和父母一起移民到加拿大以后,他的母语便离他而去。要么是他忘了,要么是他拒绝接受那个语言。对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忘记或拒绝一种语言倒也是常见的。可是,这事很让父亲恼火。一个孩子怎么会把母语给忘了?他常问母亲。那是因为这孩子太懒,不想记。我哥哥十二岁以后,下午放学后就不回家。他在屋后的小路上来回踢足球,直到吃饭时才回家。白天,母亲在市中心的沃尔伍德商场(那商场的楼顶上有个旋转的字母W)当营业员。
我们家的天花板上沾有黄色的炊油,空气里也充满油烟的成分。我记得我曾经很喜欢那有分量的空气,那空气里凝聚着在一间小厨房里做出的无数餐饭菜的味道。所有那些美味都竞相争夺空间。
水池里的鱼在慢慢死去。它全身发亮,那鱼皮像是用发光的矿物质制成的。我想用双手去推它,它的身体在我手指的压力下变得很紧张。我想如果我用手抓紧它,会感受到它跳动不停的心。可我没用手,而是用眼睛与它的眼睛对视。你是太困了,我对它说,你太累了。
父亲在我旁边快速地切着葱。据他说,他用的那把菜刀比我的年龄还大好几岁。他那刀刃前后滚动,在他的手腕边垒起一圈切碎的青葱,像座金字塔似的。切好葱,他把右边的袖子卷起,伸到水里去把水池的塞子拉掉。
池里的鱼浮起来,我们一声不响地看着。先是它的鳃,而后是它的肚子都露出水面。最后水放干了,池子里没水了。那鱼侧身躺着,张着嘴,身子一起一伏。它朝侧面跳起,撞在水池上。又跳起来,将身体卷起来,猛然一转身,朝自己的尾巴冲去。它又朝空中跃起,很重地掉下来,身子猛烈抽搐着。
父亲把手伸到池子里,抓住鱼的尾巴,轻轻地把鱼放在台子上。他用一只手抓住鱼,另一只手则用刀面去敲那鱼头。鱼不动弹了,父亲便开始洗鱼。
*
我把自己公寓的墙擦洗得干干净净。每次烧饭都打开窗户,并把风扇打开。我刚搬进自己的公寓时,父亲帮我买了个电饭煲,可我很少用。所以它一直被搁放在橱柜的深处,电线还齐整地环绕在它的腹部。我并不向往过去吃过的那些饭菜,但我很想念全家人坐在一起,饥饿的身子略向前倾,等着父亲像魔术师一样将一盘盘菜揭开的那种情景。全家人边吃边笑。白色的蒸汽把母亲的眼镜罩上雾气,她不得不把眼镜取下,放在桌上。她常常闭着眼睛吃饭,筷子里夹着青脆的蔬菜,那鲜绿至极的蔬菜。
*
哥哥走进厨房,他身上沾着土。他走到哪儿,哪儿就有一路土跟着他。他用一只手臂挽着那沾满泥土的足球。他从父亲的身边擦过,一脸紧张的神情。
母亲在一旁往鱼上撒蒜蓉。她叫我把一只手伸到鱼头下面托住鱼头,而后把鱼向后扳,好让她往鱼肚子里塞生姜。我很小心地把鱼翻个个儿。那鱼的身子又紧又滑,布满了小而尖的鳞片。
父亲从炉边拿起一把旧茶壶,里面装满了油。他将油像根细丝带一样倒进炒菜锅。过了一会,油开始炸锅,他拎起鱼,把它放进锅。他往锅里加些水,烟雾便腾空而起。煎鱼的声音就像是车胎开在碎石路上的声音,其音量之响盖过其他所有的声音。然后,父亲走出烟雾。盛饭。他边说边把我从台子上抱起来,让我站在地上。
哥哥这时才回到厨房,手上尽是泥,他的膝盖简直就是泥砖的颜色。他走起路来,足球短裤忽扇忽扇地蹭着他的腿后侧。他气呼呼地坐下来,父亲假装没看见他。
电饭煲里的米饭平平的,就像是块馅饼。我把饭勺放进锅里,搅了下米饭,一股热气冲上来,凝聚在我的皮肤上。父亲还在炉边灵巧地动着手臂炒菜,我就开始盛饭了。第一碗给爸爸,第二碗给妈妈,然后是哥哥,最后是我自己。在我的身后,鱼仍在用大火烧。蒸锅里父亲在蒸花菜,他一遍又一遍地搅动着。
哥哥用脚踢了下桌腿。
你怎么了?父亲问道。
哥哥先是不吭气,然后说:我们为什么要吃鱼?
你不喜欢吃鱼?
哥哥把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我看见他胳膊上糊着黑黑的干泥块,心里想着用小勺子一点点把泥从他身上刮下来的情景。
我不喜欢那鱼眼珠,让人看着恶心。
听了这话,妈妈咂起嘴来。她胸前还别着上班时的名片,上面写着沃尔伍德商场,售货员。别再说了,她说着把手提包挂在椅背上,快去洗手,准备吃晚饭。
哥哥先是瞪了会儿眼睛,然后便开始抠胳膊上的泥块。我正把装了米饭的盘子端上桌。那泥块从他的皮肤上飞下来,变成颗粒落在桌布上。别抠了。我很生气地说。
别抠了。他模仿我的声调说。
嘿!父亲用手中的菜勺敲了下台面。砰,那菜勺发出一记音调很高的声音。他指着哥哥说:这个家里不许打架。
哥哥眼睛看着地板,嘴里嘟囔了几句,就拖着脚步走开饭桌。他又走开几步后,开始跺脚。
妈妈摇着头,脱去上衣。上衣从她的肩膀上滑下来。她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对父亲说了些什么,父亲只是耸耸肩。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回答妈妈。我认为他说的话非常熟悉,好像那些话我本该听得懂的,好像那些话我似曾能听懂,可后来忘了。他俩说的那语言充满了柔软的元音,词语都连在一起,使我无法分清他们停顿换气的间隙。
妈妈有一次与我谈到负疚感。她自己的负疚感就在手心里攥着,就像是件祭品。但是,你的负疚感是不同的,她说。你不必抓住不放。想象一下,该是这样,她说,她的两只手摸着我的前额,然后伸进我的头发。你想象一下,她说。用脑子去看,你看见什么了?
皮肤上有块青紫,又宽又黑。
一块青紫,她说。集中精力看着它。现在,这是块青紫。但如果你集中精力,就能把它缩小,把它变得像针尖那么小。然后,如果你愿意,如果你能看见它,就能把它像颗灰粒一样从你身上吹掉。
她用双手摸着我的前额。
我试图照她说的那样去想象。我想象着把虚无的东西吹走,只是这些毫无意义的小东西,这样一种让我能神奇地一走了之的复杂局面。母亲让我相信自己的思想的力量,似乎我能让从来不存在的东西出现。或者反过来说,让存在的东西翻上几番,就会变得无影无踪。你看不见后果,整个东西也就烟消云散了。
父亲用勺子的边去翻鱼。靠盘子那面的鱼肉是白的。勺子一提,烧鱼的汁顺着鱼的一侧流下来。他舀起一块鱼肉,小心地放在我的盘子上。
他的勺子又把鱼皮弄破了。父亲很小心地舀起另一块鱼,想放在哥哥的盘子里。
我可不想要。哥哥说。
父亲的手犹豫了一下。尝尝看,他微笑着说,吃饭也可走走野道。
我不要。
父亲叹了口气,把那块鱼肉放在妈妈的盘子里。我们吃饭时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用勺子去舀不同的盘子里的菜。我父母用筷子吃饭,他们把碗端起来,用筷子把食物往嘴里送。整个房间充满了饭菜的味道。
父亲吃得很慢,全神贯注地品尝嘴里的美味,每口饭都吃得很香。母亲的眼镜蒙上雾气,她把眼镜摘下,放在桌上。她吃饭时低着头,像是在祈祷。
哥哥把一块花菜送到嘴边,深深地叹了口气。他的嘴嚼着,可不一会儿,他的面部表情变了。突然,我脑海中浮现他即将被淹死的情景,他的头发像水草一样飘扬。他咳嗽了,把那口花菜吐在自己的盘子里。他又咳嗽一声,用手摸着脖子,噎住了。
父亲砰的一声把筷子放在桌上,伸出手去,一把抓住哥哥的肩膀。我是想忍着不治你的,他说,可我不知道你这儿子怎么做的?如此无礼!他的另一只手从我身边抽过去,把哥哥的脸扇出了血印。
母亲的身体向后抽搐了一下。哥哥的脸很红,嘴巴张着,眼圈湿了。
哥哥还在咳嗽,可他抓起一把叉子,叉尖对着爸爸,不顾一切地向父亲扔去。那叉子击中父亲的胸口,落在地上。
我恨你!你狗屎不如。你他妈的狗屎不如,眯眼中国佬!哥哥手里拿着自己的盘子,砰地一下掼下来,盘子里的食物撒得满桌都是。他边咳嗽,边气狠狠地说:我希望你不是我的父亲!我希望你死了才好。
父亲的手又一次落下来,这次是朝下狠砸下来。我闭上眼睛。我只听见有人在叫喊,大声地叫喊。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用手蒙上自己的眼睛。
回你的房间去。父亲说,他的声音在颤抖。
我认为他在跟我说话,所以就不再用手捂眼睛了。
可是,他在看着哥哥。哥哥也在看着他,小胸脯一起一落的。
几分钟之后,妈妈开始清理饭桌。她把盘子里的食物逐一刮进垃圾桶里时,脸上露出一副疲劳的神情。
我离开自己的椅子,从妈妈的身边走过,踩上地毯,走上楼去。
我蹲在哥哥卧室外的墙边。然后,我走上前去一看,只见父亲两手拿着一根竹竿。那竿子很光滑,每隔一段就有个竹节把像头发一样细的竹纹绑在一起。哥哥趴在地板上,像是被推倒或是被拉到那儿的。父亲把竹竿高高举起。
我想哭。我想走进去,站在他俩中间。可我不敢。
那情景就像是一棵树要倒下,树身开始倾斜,在空中慢慢形成一道弧线。
那竹竿无声地落下来,打破了哥哥背上的皮肤。我没听见他发出任何声响,只见他身上有条横过来的血印。
竹竿又举了起来,又一次落下。我害怕这下要把骨头打断了。
父亲又一次举起双臂。
哥哥躺在地上,脸埋在地毯里哭,手指紧紧地抓住地面。他的双膝弯曲在胸前,头顶朝下钻。他的背弓着。我可以看见他的脊梁,皮肤上出现很多小疙瘩。
那竹竿打到骨头里。我脑子里顿时出现了一百万个白点。
妈妈把我从地上扶起来,拉着我走过房子中间的走廊,走进我的卧室,让我上床。所有的东西都是湿的床单、我的手、妈妈的身子、我的脸。她用我听不懂的话来安慰我,可我只听见有人在尖叫。她用自己的凉手抚摸着我的前额。别叫了,她说,请别再叫了。可我感到精神失常,无法控制自己,好像这个世界里的一切即将到此结束。
第二天早上,我一醒来就听见油在锅里炸东西的声音,还闻到法国土司的香味。我还听见妈妈正忙着把碗盘放进碗橱的声音。
哥哥没下来吃早饭,可没人说什么。父亲把法国土司堆放在一个盘子里,上面浇上糖浆。妈妈倒了一杯牛奶,然后把这些东西一道送到楼上哥哥的卧室里去。
我像往常一样,跟着爸爸在厨房里转。我追随着他的脚印,跟在他的后面,躲在他的影子里。他不时地俯下身来,用手抚摸我的头发。我想,我们像是着魔似的。你看,我们俩绕着圈来回走动,他不假思索地做饭因为这是他不费任何工夫就能完成的任务。他低头对着我笑,但他的微笑不知怎的就不再使我着魔了。父亲站在那儿,双手垂放在身体的两边,好像忘了正要做什么。墙上的漆正在脱落,地板已有好几天没扫了,上面留有我们脚上沾着的灰粒。
我想,我如此执著地跟在他后面,如此专注地爱着他,使父亲感到迷惑。他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发现,要忽视我所不能理解的事情越来越难。不要多久,我就会丧失对他的缺点和优点区别对待的能力。他知道,我对他的无条件的爱会像哥哥对他的爱一样,持续不了很久。父亲站在厨房中间,不知所措。妈妈终于从楼上下来,用双臂拥抱着他,并对他低声说了些什么。可她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是,她却一个一个音节地用这个从别处偷来的语言与他交流,直到他低下头来,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
后来,我用身子倚着楼上哥哥卧室外的门框,我听得见金属的叉子刮盘子的声音。母亲已到哥哥的房间里,她说话的声音时升时降。她用叉子在盘中刮动,叫哥哥吃盘子里的法国土司。
我朝哥哥的床走去,他房间的地毯粗得扎脚,我总算用双手抓住他的木头床框了。妈妈坐在那儿,我走到她身边,用手去摸她衣袖上的扣子。我把那些扣子转来转去,想让那扣子把屋里的阳光反射在墙上。
你不吃饭啊?我问哥哥。
他哭起来。我看着他,他半个脸用毯子盖着。
吃点试试。妈妈轻声说。
他哭得更凶了,可没发出任何声音。他毯子上的阳光投影随着他身体的抽动而移动。他的头发因出汗太多粘在一起,他的头像老头的头一样前后移动。
有一阵我感到父亲站在门口,但我不能回头看他。我想面对着墙,保持现有的姿势。我害怕如果我转身,走到他身边,就会让自己搅进去,接受一部分(无论多小一部分)的负疚感。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这样的事不再发生。尽管我现在知道,这些事最终会让我们分道扬镳,这样的暴力会把我所有的爱变成耻辱和悲伤。所以我站在那儿,既不看父亲,也不看哥哥。即便连父亲本人,那样一个可以凭空变出美丽东西的魔术师,现在也只能站在一旁观看。
一个人的脸随着时间变化,越变越清楚。在父亲的脸上我看到了所有发生过的事。我既能看到让他判若两人的愤怒愤怒使他的脸变得皮包骨头。我又能看到他脸上显露出不可忍受的疼痛疼痛使他的脸布满悲伤,像是要吞噬他的脸庞。我该如何看待他的长处和短处,而不减少对他的爱?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小时候爱父亲不是因为他复杂,有人所固有的两面性,或因为他需要我爱他。孩子并不知道那样去爱一个人。
再简单不过了。温水淌下来,我的双手能感到米粒在手里,那声音就像石子沿着铺好的路面滚动发出的声音。父亲总是把米淘了又淘,用手指去寻找杂物,把它们一个个挑出来。瞧,他手指上放着一个几乎看不见的混在米里的小杂物。
如果真有解救的办法,我是会采取的。张开的手里抓上一把米,把米摊平在手掌上,寻找杂物,然后把疵物逐一挑出。这样,手里剩下的就都是好的。
在我记忆的某个角落,水池里的鱼在慢慢死去。我和父亲看着水越来越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