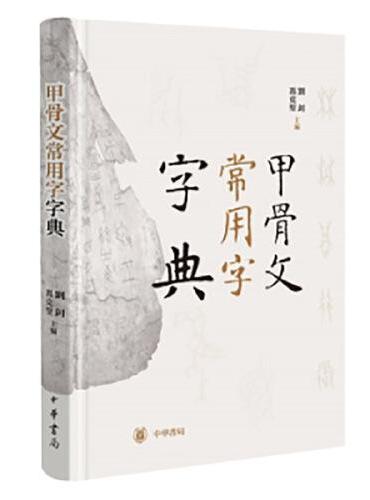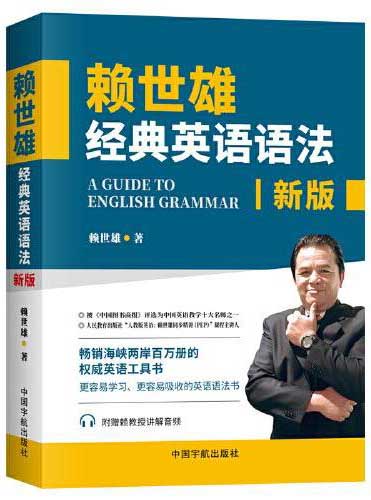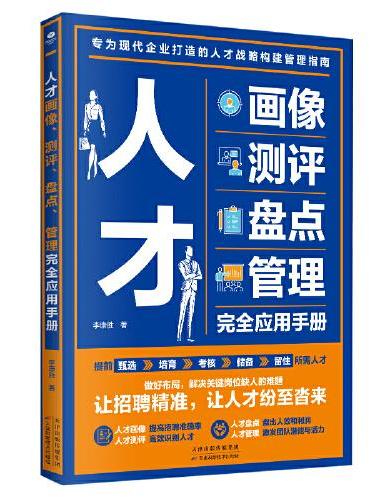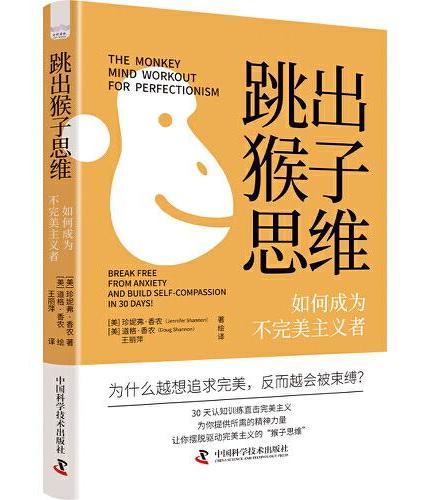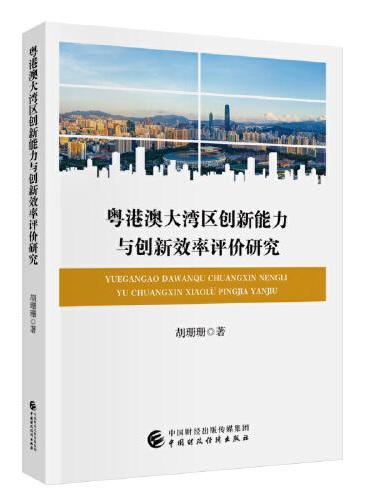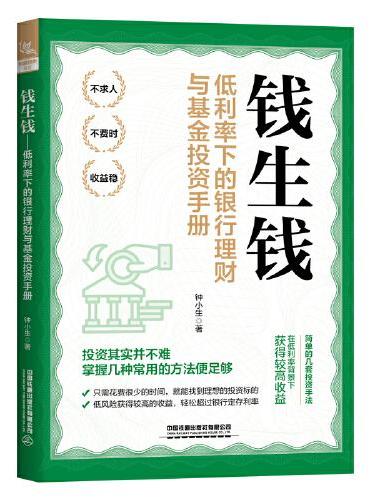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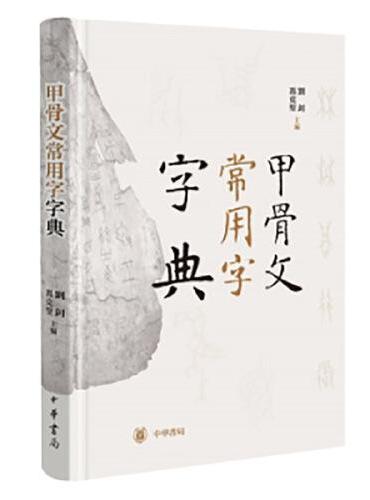
《
甲骨文常用字字典(精) 新版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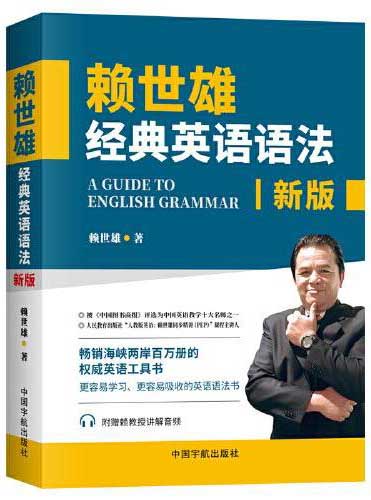
《
赖世雄经典英语语法:2025全新修订版(赖老师经典外语教材,老版《赖氏经典英语语法》超32000条读者好评!)
》
售價:NT$
305.0

《
影神图 精装版
》
售價:NT$
653.0

《
不止于判断:判断与决策学的发展史、方法学及判断理论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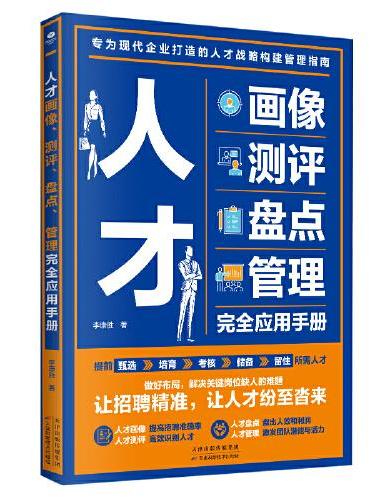
《
人才画像、测评、盘点、管理完全应用手册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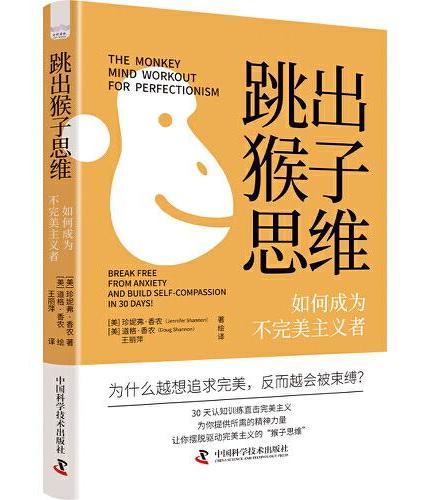
《
跳出猴子思维:如何成为不完美主义者(30天认知训练打破完美主义的困扰!实现从思维到行为的全面改变!)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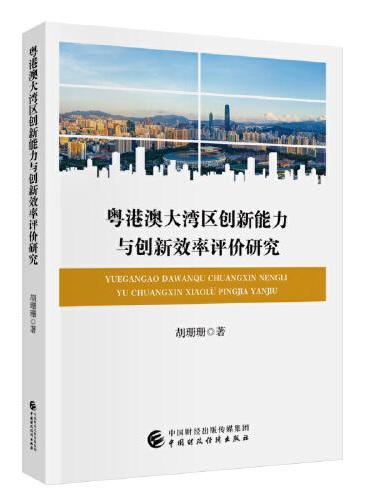
《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能力与创新效率评价研究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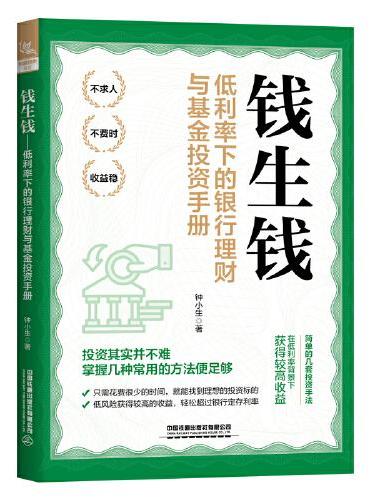
《
钱生钱:低利率下的银行理财与基金投资手册
》
售價:NT$
352.0
|
| 編輯推薦: |
老西安朴野之美的发现者,用嫡秘嫡传的方言和本色纯正的土语构筑成的土语文学帝国,老西安俗门打开风罡土厚扑面而来。
我一直认为,在这个城里,*能熟知西安的,尤其老西安,没有谁胜过鹤坪,他的才华确实在万人之上。
贾平凹
这些老东西有股子味道。历史的味道,民间的味道,陕西的味道,似乎还有点鹤坪的味道。
冯骥才
|
| 內容簡介: |
西安的作家中,作者鹤坪的经历是*丰富的。他父母是鞋匠,在老西安的大车家巷住了一辈子,见识了五行八作的万千世事,又从老辈子那里听来了一十三朝的掌故和风情,就有了一肚子的古经和一笸篮的市井故事。贾平凹说:我一直认为,在这个城里,*能熟知西安的,尤其老西安,没有谁胜过鹤坪,他的才华确实在万人之上。
这部《俗门俗事》精选的鹤坪的十来篇短篇小说的合集,小说都是写的老西安的人和事。有庄户人、拾娃婆、媒婆、寡妇、手艺人、刀客、神医、王傻子、站门汉、奶妈子等等鲜活的人物。虽然小说是虚构的,但作者所使的材料却是真材实料。小说的语言浸润着老西安的生活与民俗风味,并且从细节的真实性和陕西语言的独特性,具有独特的魅力。冯骥才和贾平凹都给本书做了序。作者还为本书配上了他的水墨人物插图。
|
| 關於作者: |
西安的作家中,作者鹤坪的经历是最丰富的。他父母是鞋匠,在老西安的大车家巷住了一辈子,见识了五行八作的万千世事,又从老辈子那里听来了一十三朝的掌故和风情,就有了一肚子的古经和一笸篮的市井故事。贾平凹说:我一直认为,在这个城里,最能熟知西安的,尤其老西安,没有谁胜过鹤坪,他的才华确实在万人之上。
这部《俗门俗事》精选的鹤坪的十来篇短篇小说的合集,小说都是写的老西安的人和事。有庄户人、拾娃婆、媒婆、寡妇、手艺人、刀客、神医、王傻子、站门汉、奶妈子等等鲜活的人物。虽然小说是虚构的,但作者所使的材料却是真材实料。小说的语言浸润着老西安的生活与民俗风味,并且从细节的真实性和陕西语言的独特性,具有独特的魅力。冯骥才和贾平凹都给本书做了序。作者还为本书配上了他的水墨人物插图。
|
| 目錄:
|
上卷:
序一:鹤坪笔下的老东西冯骥才第壹页
序二:我说鹤坪贾平凹第伍页
自序:从「腌酸菜」「炒葱花」说到「皮匠铺子」第柒页
庄户人进城第拾柒页
拾娃婆和她的糙爷们儿第贰拾伍页
媒婆红喜儿第叁拾叁页
撞干大第肆拾页
一个卖金鱼的「寡妇」第肆拾捌页
穷人的小年第伍拾陆页
从俗传说到俗生活(四则)第陆拾柒页
没底是人心第陆拾玖页
巧媳妇第柒拾贰页
竹笆市的传说第柒拾陆页
手艺人的「饭碗」第捌拾壹页
慈禧太后在西安的传说(四则)第捌拾柒页
金花落在黄土窝第捌拾捌页
刀客「黑脊背」第玖拾肆页
回坊,庚子年的那一道曙光第壹佰零叁页
神医雷云章第壹佰壹拾柒页
王傻子第壹佰贰拾肆页
站门汉第壹佰肆拾壹页
还愿第壹佰伍拾壹页
食客和袖狗第壹佰柒拾叁页
下卷:
序三:鹤坪和关于西安的写作贾平凹第壹佰柒拾柒页
春女第壹佰捌拾壹页
一、杠铺记事第壹佰捌拾壹页
二、杠花子第壹佰玖拾叁页
三、丧棚第贰佰零叁页
四、喜棚第贰佰零捌页
五、洋车时代第贰佰叁拾壹页
奶妈子第贰佰肆拾壹页
楔子第贰佰肆拾壹页
奶妈子第贰佰伍拾叁页
蛮子和奶妈第贰佰陆拾肆页
主仆之间第贰佰柒拾叁页
断奶第贰佰玖拾壹页
老东西们第叁佰零叁页
一、夯班第叁佰零叁页
二、民国的杂碎第叁佰贰拾叁页
三、一种旧俗第叁佰伍拾肆页
四、杂痞们在风雨中成长第叁佰柒拾壹页
后记:头发丝上吊圆宝写在《俗门俗事》后面的话第叁佰捌拾壹页
附录:形上形下说鹤坪陈黎第叁佰捌拾肆页
|
| 內容試閱:
|
序一:鹤坪笔下的老东西
冯骥才
鹤坪我见过三次。我从未造访过西安,故而都是他来瞧我。在我每天往来匆匆的客人中,鹤坪却让我记得清清楚楚。
他个子小,瘦硬爽健,说话热气扑人。年岁不大,人挺老到,却不精熟。还有几分侠义劲儿,倒是对我的胃口。他每次来,总带点老东西。好像老东西是陕西的土特产。一个黑黑的陶罐,一件木人,一块瓦;虽然都是半残,带泥带土,但年代足够,绝非当今各地古董市场上那些铺天盖地的假货。由此我看出他有挺不错的眼力,能识别出这些东西是真是假,凭的又绝不只是眼睛。我最怕人家把假古董当做宝贝硬送给我。但鹤坪捎来的这些老东西,却一直摆在桌上。
这些老东西有股子味道:历史的味道、民间的味道、陕西的味道,似乎还有点鹤坪的味道。
这次鹤坪来天津,把他的《俗门俗事》书稿给我,请我写序。我看过便笑了。原来他写在纸上的也是这些西安的老东西!肯定他认为我一准识货。
鹤坪写得蛮好。虽然是虚构的小说,但所使用的材料却是真材实料。我不懂得老西安的生活与民俗,我是从细节和语言的独特性来考察这些生活材料的真实性和可信性的。
有两种小说:一种小说故事是真的,但材料是造的,就像当今旅游化的名人故居房子是真的,里边的东西全是假的;还有一种小说,故事是虚构的,但里边的材料全是硬邦邦的,真格的。这便可以借尸还魂,硬叫画上人走下来。
可是材料若要地道,并非易事。作家的功夫一半是在手里边的材料上。作家手里的材料不同于泥瓦匠手里的沙子灰儿,这些材料都是作家使用非凡的眼力从生活里瞧出来的。也许这就是鹤坪这本《俗门俗事》的价值了。
提到价值,还有一层,便是文化的价值。
如今中国人也许还没弄明白,几千年来,只有当下的生活才称得上巨变。连文革之变,也变不过今天,其原因便是农耕文明的瓦解。于是在这昔日文明框架里有形与无形的一切,都在迅疾变化。留之不得,挽之不住,失之无痕,去不再来。
于是,作家要干的一件事,便是将昨日的形态记录下来。当代作家也许是农耕文明最后一代的经历者。我辈不去做,后者做不得。就像本书中的老城、老宅、老人首、老手艺,鹤坪不写,谁人能知?因故,鹤坪的文学创作便有了一层记录文化的意义,在这层意义上,这本《俗门俗事》比起他的那部长篇小说《大窑门》则是十分自觉的。此亦可称作文化的自觉。
于是,鹤坪这本书自然就超越了市场上那些民间传奇。民间的事物和人物充满着神奇的魅力。但这种神奇的魅力不是在鬼狐、巫术、野合与秘方里,而是在实在又鲜活的民俗生活之中包括这些老人首的门道里。那就要看作家有没有把双脚真的踏进民间,有没有真切的民间情感。我相信鹤坪的两只脚是踏入民间的。因为他书里书外的这些老东西,不假不虚,全都靠得住。
鹤坪的文学创作,不仅仅只属于陕西,应该说他是行走无羁的。
序二:我说鹤坪
贾平凹
从来的文艺界,有富贵人如张大千的,也有孤寒人如陶博吾的。鹤坪瘦身子小脑袋,说话急躁,走路雀跃,虽然有两支笔,一支写文章,一支画水墨,却就是养不好他。于是,送过煤,卖过饭,极尽折腾,四处漂泊,仍未解决温饱。
但我一直认为,在这个城里,最能熟知西安的,尤其老西安,没有谁胜过鹤坪。他的才华确实在万人之上。
他的文章水墨,尽写了老西安社会底层的众生,形象饱满,性情奇崛,语言幽默,你不得不为他的发现称道,不得不为他的文笔叫好,同时浩叹着世事的无常、生命的悲凉。
上天如此对待他,或许他的前身是南门上空曾经的一颗冷星、钟楼檐下曾经的一只蝙蝠、城墙根的草丛曾经的老鼠和蛇。或许,让他生不如人而使其作品传之后世。
当然,他生活窘态太久了,在社会底层待多了,少不了也有了那里的一些习气,但不影响到他的境界,他现在需要捞面和锅盔,还有春天吹来的风、云层里射来的阳光。
自序:从腌酸菜炒葱花说到皮
匠铺子
鹤 坪
到了通和适这儿,俗开始呼吸了。
不论通俗还是适俗,都首先是生存的技术,其次通和适显然与审美有关。
俗就是了,没有文野之争、雅郑之辩,俗是私事。切入了大众生活和社会生活,你才能切身感到:惟有俗是真正关心与写生的人生艺术。
好的小说就像自家院子里不打眼处窝着的那一老瓮腌酸菜。老瓮虽说灰头土脸甚至蒙尘藏垢,但这一瓮酸菜远比美国历史悠久。隔些日子,你总会想起老瓮和瓮里的腌酸菜。每次,当你搂底子翻搅起老瓮里的腌酸菜,瓮底早已沉积许久的那股子气浪咕嘟咕嘟地释放出本真本分的自家的气味;这气味或隐忍暗香或酷辣刚暴,顷刻使你产生种种复杂的联想。打开腌酸菜的老瓮,很容易沁入时间的深流,任气味或者味气绑架你挣脱浮华与骄奢的欲望峡谷,进入大众生活、俗世生活本清则静、本真则正的原生原发的境界。
然后,然后你不吭不响地把镇缸石(压在腌菜上面的一块石头)压在酸菜上面,并且用瓦盆做瓮盖,扣上老瓮,那股子令你透彻肌骨、灵魂出窍的气味和味气还在屋子里弥漫,并且破门而出,穿街透巷越飘越远。气味是无孔不入的,可以覆盖理智与思考;气味具有极强的渗入作用,调动情绪与感觉,直达心脾。气味也是任何艺术最撩人的密钥之所在,可惜知道的人并不多,因为气味神乎其技!
到了老西安土语这儿,气味仅仅只指常规常识的物质气息,而把通心透窍或者撩人魂魄的气味一概地称为味气!
老西安人说的味气,气字要轻读,是味气而不是气味,其中包含德性、神采、味道、韵味等诸多方面。
小说往直白里写,像炒葱花那样简单。
炒葱花的主角就是青葱一苗、油盐少许。关键在于火候。火候就像戏台上的锣鼓点儿,或徐或疾,要恰到好处!
炒葱花用急火烹饪,所谓炝锅。炝锅之下,葱花在热油锅里翻个身就得起锅。然后,油香裹着青葱的暗香,急火攻击出的油盐的隐香,荡漾开来好的小说,你读就是了,评论它干什么?!写什么,怎么写还有为什么写,这是三个问题。
别老惦着把小说写成国宴,更别惦着把小说写成满汉全席;吃腻了山珍海味、生猛海鲜的当代读者,真需要通过吃素,进入文学体态增格调与减赘肉境界。
说到吃素,讲究大了,比写小说讲究。吃素人的心门打开了,直通窍道,能听到雪的声音和土地的呼吸。吃素并不古奥,吃到妙处新妍竞放、晶光迸溅。
往直白里说,小说的根在民间俗世那里,写出的只能是平易简淡的俗浮世事、浮沉浪事、油盐琐事。讲出的花招花活、孰雅孰俗那是小说家个人的事情。
过去说书的、唱太平鼓的、打着小锣说前朝的,甚至举着牛胯骨说莲花落的、打着竹板儿报升平的,都是小说家。小说最宜小猫吃小鱼,小说也可以是小胡同里赶猪,但小说绝不是盲人摸大象。还是鲁迅公说得好:
一条小溪,明澈见底,即是浅吧,但是却浅得澄清,倘是烂泥塘,谁知道它到底是深是浅呢?!
小说家要把自己的角色把握准确,在社会生活的大舞台上,小说家顶多就是个卖白菜的。卖白菜的就别操心卖白粉的事,这也算本分。
小说家本分了,必然带动整个阅读界的清静与归心。并且巨大地增容当代文学的尊严和激活读者对欧风美雨以及之后的日蚀韩侵的抵御!
写到这儿,我躬身而起,给小说和小说家这个小字脱帽致敬!
小说家不是历史的书记官,也不是时代的秘书,小说家就是一种中国文人的生存手艺;小说哩,就是熔铸传奇、杂学与语言的手艺活。别把小说家支太高,也别把小说架到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肉架子上做烤串。小说轰动了,算你命里有,你可以啃着红烧肘子作种种如是说;小说放了哑炮,算你点儿背。当然你也可以举着牙签肉把玩其间的柔可绕指与余音绕梁!
过去商街草市的买卖讲究要有个利益利市的吆号,所谓吆号,其实就是醒目的字号招牌。长发祥是绸缎庄的吆号,德茂恭是糕点坊的吆号,房打颤是房屋牙狎客(也就是房屋中介)的吆号,日升昌是钱庄的吆号。最属皮匠作坊门前的吆号稀奇,没词,皮匠作坊门前就挂窄窄两绺风干了的牛皮和一根被岁月磨砺得油光水滑的牛宝(牛鞭)。据老辈子说,牛鞭这玩意儿避邪。你不信我信。
皮匠人老八辈都是大字不识的睁眼瞎子,门首的招牌匾额再招摇、再有词采也白搭。这两绺子风干了的牛皮和那根梆梆硬的牛宝就是吆喝,有风叮咣响、无风响叮咣。这就是城乡百姓对皮匠铺子约定俗成的认知,但它就是百姓对皮匠铺子的图符记忆。中国人对约定有着发自心底的虔诚,而俗成之后的皮匠铺子的幌子似乎更忠实主子,给了那两绺干巴牛皮一个足够响亮的吆号:皮干板儿!
是先有皮匠铺子还是先有皮干板儿,今无考。
皮干二字在西安土语里明里暗里都意指:杂话连篇、语含讥弹、话锋咸酸的说话方式,其间不乏对皮干者没有尊严的前提设置。而板儿指的是爱皮干的人手上的道具,可以是快板儿,也可以是皮干的事情。
约定俗成和入乡随俗,应该算小说家的双脚。约定显然有契约作用,而俗成明显具有传承意义。往实在处说,不论书房还是草市,契约精神都属华夏子孙优秀优良的私德和公德结构出的共同遵行的生存原则;纵是勾栏、宝场(赌馆)它也务必尊崇嫖情赌义这个约定俗成的行当讲究。
小说家的契约精神是和谁制订呢?当然是和读者,而不是衙门。
在我的心底里,读者就是我的爷,就是我的天,就是我的地。
说起皮干板儿,学问大了。衙门的役吏杂差有世代相传的杖责拷打罪囚的刑具讲究,有《狱吏谣》说:外伤五花棍,内伤皮干板儿。另,关中道上的吆车把式尤其讲究要拥有一根能甩得出炸鞭一样脆响响声音的用皮干板儿拧成的马鞭子。而那根皮缠棍(牛鞭)早就让城里的郎中写进了药方,并且让红馆馆子的大厨请进厨房,有了新的名称钱肉。钱肉的烹饪技艺已经基本失传,但小说家大可扯开性情壮美钱肉的滋味: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钱肉!
所以,不论到了什么地方,小说家都得先找到皮干板儿。皮干板儿可能是个腰缠万贯的土豪,也可能就是个腰扎草绳的苦讨,但他煮不熟、炖不烂的那股子筋头巴脑的顽皮劲儿,却凝聚着对这个地方的风物土俗及其精神气质的深层蕴藏。
我想,从腌酸菜炒葱花说到皮匠铺子,也就说清楚了小说家的职能和妙用。再往细处说,那就是腌酸菜、炒葱花和皮干板儿所潜隐的对生活的启示和警醒了。
小说是病还是药,这得问小说家。在传统中国文化那儿,卜赌同源,药毒一家。
逢事都得辩证,读书也不例外。
十字街头,货分东西,人走南北,顶盘挑架的,箍瓮捏笼的,全都是人生,全都有传说。医家有医不自治的祖训,松肩拿背的也都有给后人留口饭吃的讲究。小说家也似乎有应当遵行的规矩。在行当祖训有医政同理的说法,但小说家不敢说这话,小说家不是背着个小字在讨生活吗?!
小说之说,名堂大了。惊堂木一响,说书匠一字一板地说:说书人的口那是无量的斗!
或者无量到无限,抑或无量到虚无。总之,让小说家承载高台教化,那是依靠狗拉大车,只能把大车拉到炕洞里去;抑或把小说往娱乐和消费归类,插科打诨,搞笑搞闹,耍牙耍嘴,那样又明显委屈了小说。
再次向小说鞠躬,这回是为小说之说致敬。
话必关心方传远,语必入俗始动人。
俗门打开了,俗人俗事弓马娴熟地朝外面在走。
天目可鉴,芸芸众生中最苦焦的是小说家,因为小说家从皮面到里子都是一门经心灵、接地气的关心术!于心交往,不谋利市,难免居贫清贫,难免寒酸艰辛。小说载道,而道不远人。我以为饱吹饿唱才是小说艺术的正道。
是为自序。
时于2016年7月的天目书院。
序三:鹤坪和关于西安的写作
贾平凹
鹤坪的文章看得多,在西安的报纸上几乎隔三差五就能见到他的文章。西安人庆幸鹤坪的出现,我庆幸他的成功。
鹤坪是西安的老户,曾经和我住在一条叫大车家的巷里。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他时常携着他的诗稿来我家给我念,一口纯正的西安话,激情充沛。我为他的才华叫好,却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怕冷,耳朵上要戴毛线织的耳套,手上是一双手套,但十个指头却裸露着,是那个年代劳动人民特有的手套。大车家巷里有一位身体残疾的小儿科医生,医术不错,我常领孩子去术治,不止一次见到鹤坪在巷中与卖甑糕的吹糖人的人闲聊,或者用自制的安有铁轮的小木板去拉水,响声刺耳,水滴淋淋,甚至见他在那全巷唯一的公厕排队等候出恭时与人争执闲人一词产生的渊源。后来,我搬出了那条巷子,与鹤坪见面的机会少了,似乎很多年月未在报刊上读到他的诗作,听说去下海了,听说去了云南去了四川,听说做书商没有发财开饭馆没有赚钱又窝在家里写小说了。终是在一个午后,他突然在敲我家的门,胳膊下夹着一部书稿让我读的。我已经很惋惜他停止了写诗,但我也知道他的秉性里有散人的质地,浪荡了这么多年,还真能写什么小说?待他走后,我读那部书稿,这就是《大窑门》,竟使我读得很有兴趣,立即推荐给北京的作家出版社。第一部小说的成功,给西安文坛一阵惊喜,也给了他莫大的激励,小说写作便一发不可收拾。现在,他是一名自在的职业写作家,大车家巷的民居业已改造,谁也不知道他搬迁哪儿去住了,又在什么地方烟腾雾罩地作他的小说,但许多朋友都在说他们在某街某巷看到过鹤坪了,瘦瘦小小,扑兮邋遢,一肩低一肩高,跳跃着步子在城里游走。我笑了,这是鹤坪最悠闲的生活状态和最自在的文人状态,他无所不能地熟知着这个城市,认识着这个城市,或许正在孕育着关于这个城市的又一个故事。
相对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西安在文学上是特点逊色的城市,多少年里,我们一直在鼓吹为这个城市写作,写出这个城市的特色,但都因种种原因未能达到预期效果。鹤坪的出现,是一道亮色。他的根在这座城市,几十年来自己又在这个城里沉沉浮浮,饱尝了下层社会的艰难困苦,他首先是以一个普通市民的角色为生存而奋斗着,然后方是小说家从事自己的事业。所以,他的小说有真正的人的东西在里边,有生活的原汁原汤,或许,他的叙述语言对于外省读者有一定的阅读障碍,而西安市人读起来却受活不已。依我的观点,也同意他以后在语言上做一些筛选和提炼,却更希望在时下让他尽最大的力量发挥西安土语的特点,先用加法,后用减法,保持浑厚和鲜活,以求往后的大的气象。
描写出了一个地方,抑或一个城市的味道,这并不等于作品的价值走向,而在于为了获得这种味道所摹写的琐琐碎碎的生活能传达出一种诗意,使整个作品能升腾起来。鹤坪在《大窑门》里,我们可以嫌其不足,但到了这本《俗门俗事》,既有现实,更有精神,令我们感到欣喜,而使文坛关注了他,对他寄予大的希望。
与鹤坪已经相识了数十年,知道他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都十分突出的诗人和作家,他十足聪明,悟性极高,但往往乏于忍耐,反复无常。我是多么愿意看到他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使更大的作品出现。西安需要他,文坛需要他。
庄户人进城
老西安的城祖是谷神后稷。从古往今,老西安城都以农耕立基,不论城民还是农民都以稼娃自诩。在城里的热闹处,你跳着脚骂皇帝没人搭理,但一俟你的言语伤及四乡的庄户人,你肯定逃不脱要挨万人捶的。
所谓万人捶,也就是对触了众怒的或痞或奸者的惩罚。在西安人心底里,欺穷和欺农远比欺天之罪恶劣!
农历四月初八是西安城祭祀城祖稷王爷的日子,古称忙农会,也称忙笼会。四乡庄户人有在城会期间逛城的讲究。
眼瞅着要开镰收麦子啦,这时天角轰隆隆的闪电驾着乌云笼罩了四城。不等呼噜大白雨降临,老西安家家户户的老辈子就在巷道里张罗着酬神。
等到大雨浇头盖脑的时候,老西安家家户户的院子中间都由长子长孙亲自栽一根够顸够莽的棒槌;棒槌直冲着天庭的龙王。这是俗。俗到了老西安除了敬天祈地,多了诅咒的意味!
老西安,小麦和棉花的老西安,粗瓷老瓮粗瓷老碗的老西安。老西安,周吴郑王的老西安,睁眉豁眼的老西安。
天麻麻亮,吆车的和逛城的四乡庄户早早就赶到了城门楼子底下。城门还没放闸,庄户人借着天光刚刚能够辨识出老槐树上栖落的是黑老鸹(乌鸦)还是花大姐(喜鹊)。吆车把式搂着鞭杆子窝在车辕上打瞌睡,车上坐满了逛城的庄户人和他们的孩子。男孩子都在额顶蓄一绺头发,俗称金盖瓦,后脑勺上再蓄一根小辫子,俗称富贵根;女孩子都用红丝线扎帽盖儿,也有用靛蓝绸子或花青缎子扎帽盖的,这是进了私塾或者学馆的女子。庄户未出阁的女子都蓄刘海,只有出阁那天才讲究盘头。日子宽展一些的庄户还讲究女子逛城这天给脸上搽胭脂粉,把个小姑娘打扮得简直就像哪吒,透着喜气。两只喜鹊在城门边的老槐树上呼扇着翅膀,叫声嘎嘎的。远处的官道上还有骡马大车在往城门楼子底下赶,吆车把式许是个急性子,他把鞭梢子在冷空里甩出一串脆响响的声音,嘴上还不停地吆喝:驾,进了城头锅饺子、二锅面,想啥是啥!城外风硬,吆车把式的吆喝和搭车人的喧哗被风传得很远。
城门开闸,骡马大车哗啷哗啷地往城里面走,城门猴(城卒)贴着城门四脚拉叉地伸了个长长的懒腰。骡马大车洪浪一样地穿过城门洞时,车上的孩子们瞪大眼睛、憋着腮帮子,不发出一点声音。老辈子早在孩子们缠着要上城的时候就用祖传八辈的顺口溜交代过多次:上城的路油光光,进城不为喝米汤。城洞铺着钉子板,街面四处虎狼窝。滚过热闹都穷汉,莫羡孤寡住深院。
庄户人搂着鞭杆子坐在车辕上,咂吧着牙花子嘟囔:这就算进城了。城里可都是比咱乡下人高一头、大一膀的裂倔人物。你瞅,一个个看着牛气蜈蚣,日踏谁的江山呀!
裂倔是西安土语,就是豪横、霸悍的意思,没有丝毫贬义!但后面这句的日踏虽也是土语,但不含丝毫褒义,纯粹诅咒。城里人喜欢四乡庄户人说话欢眉瞪眼的样子,形容庄户人说话有了睁眉豁眼这句土语。而庄户人形容城里人则用周吴郑王来涵盖西安人的神色和貌意。
马车进了城,各奔东西,该歇店的歇店、该投亲的投亲。城里是石板路,骡马走在上面咯嗒咯嗒地响,硬箍的胶皮车轮把石板路碾轧出哗里哗啷的声音。马车上,小孩子把手抄在袖筒里,愣怔着眼睛来来去去地巡看,看啥都新鲜。
小女子问:妈,城里一满是房,咋看不见一亩半垄的庄稼呢?
小儿瓷头瓮脑地说:城里人喝风?屁哩,人家吃的是铁杆皇粮。
车把式一边抡圆鞭杆子,一边呵斥稚嫩的儿女:把屁嘴夹紧!进了城少说咸淡话,当心得罪了城隍老爷!
庄户人家的婆娘差不多都是大脚、大脸盘,胸膛也都足够大。大脚婆娘们儿穿葱白色的大襟衫子,大襟的襻系上挂缀着湖蓝色的印花手帕。看着临街拔地而起的楼廊和站在楼廊上望街景的镶着金牙的绸袍掌柜,大脚婆娘问吆车把式:大,城里人住这么高的楼房,到时候棺材咋抬下来呢?还把棺材立棱着(竖着)往出抬呀!?
吆车把式狠狠地在马臀上砸了两槌,掉转头对大脚婆娘吆吼道:没成色!过门都十年了,还是你娘家人荒腔野板的那个式子!出门时就该给你把咬嚼子绑上!
大,你说我就说我,跟俺娘家人有啥干连?!大脚婆娘翻嘴。大脚婆娘害气了,提着包袱闹火着要下车。大脚婆娘的爷们儿睁眉豁眼地说话了:你敢!今儿你再下了车就再也不要上俺家的车!后晌我就背着锅盔到窑子门上寻滋润!说着,咣咣在大脚婆娘胸口擂了两拳。大脚婆娘挣扎着要下车,翻眼翻嘴地嘟囔道:不敢?!不擀的那是煎饼!男孩、女孩抱住大脚婆娘的腿不让妈下车。
这时,字号门前穿长衫子的二掌柜招呼车把式:南乡的,牲口歇下了到咱字号上坐!刚到的杭纺料子,迟了就没货了!这是长发祥的二掌柜(领工的东家)在招呼车把式。
这边天香村门前的二掌柜也跟车把式搭上了话:捎二斤桂花糖,把娃甜一回!
吆车把式搭讪着街两边的吆喝,捋着白胡子嘿嘿地笑。他笑着说:甭忙,进城弄啥来了些?!后晌就来了,到时候手底下放宽展些。车把式这是给街两边的字号撂话。
嗨,这是啥话?咱大尺子的长发祥四乡摇了铃的!
庄户人进城谁不捎上二斤咱天香村的桂花糖,回到村他头都没法抬。
骡马大车咣啷咣啷地从南院门街上过去了。车把式应酬着左左右右的招呼,小孩子滴溜着眼睛来来去去地看街两边的热闹,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和疑惑。大脚婆娘不再闹火着要下车了,把娃们紧紧地搂在自己怀里。
大脚婆娘的爷们儿说话了:大,咱是先歇牲口呢,还是先下馆子?
车把式说话了:牲口歇下了咱再吃!庄户人不爱惜牲口,馆子里的炉头都不好好给你炒菜!
骡马大车踢踏踢踏进了马号。马号门前栽着高杆,杆子顶上悬挂着四盏桶灯做成的幌子,马号的幌子上挑着碗大炕热四个斗大的黑字。
车马店的掌柜掀开门帘,招呼伙计娃:快,快张罗给牲口卸套,给爷母子几个抢忙把碗子蒸上。
车把式把鞭杆子从空中扔给掌柜,从车辕上抱起男孩说:免了,今儿俺娃要坐在油漆板凳上吃饭哩!俺庄户人进城弄啥来了些?!
庄户人一家老小说话搭话地走出了马号。
马号的门前有饮马池。涝池不大,但名堂不小:相传,王宝钏的娘家就在饮马池边相王府。而薛平贵西征前在饮马池一边饮马、一边眺望着金碧辉煌的相王府,在心底发下毒誓:等吧,总有我薛平贵把蚯蚓耍成蟒的那一天。
饮马池里的荷花不争奇、不斗艳地为庄户人家盛开了。
拾娃婆和她的糙爷们儿
人常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其实一个生命来到这个阳世间是要经历许多繁琐的周折和内心的坎坷的。爹生娘养,这话我们挂在嘴边上,可你知道你的接生婆的名字吗?你知道你娘生你时还需要一个搂腰的吗?
听说现在产房门前都有了可供雇用的啦啦队,我为这个时代的进步高兴。尊生重养是老年间的讲究,厚生重葬也是老年间的讲究。生老病死是最朴素也是最高级的大众生活的四喜丸子,谁都逃不脱,谁也绕不开。
瓜熟蒂落,我的故事从收生婆说起。落下来的是金瓜哩还是苦瓜?难说。
拾娃婆是响名城南的收生婆子,男人在五味什字草市上箍瓮。老两口日子过得滋润,嘴里都镶得起金牙。拾娃婆是小脚,夜里有人喊她收生,常常由自家爷们儿背着她去。踩着月光,拾娃婆伏在自家爷们儿后背上,一双小脚跷得老高。拾娃婆扒着自家爷们儿的肩膀头嘟囔:脚底下放麻利,这是去收生呢,不是去箍盆箍瓮哩!男人一脚高、一脚低地紧着脚赶路,嘴上却唠叨个没完:老瓮裂开一道缝还讲究个时辰哩,急啥。老两口说话搭话地往前走,拾娃婆把自家男人的脖子搂得很紧。老汉走慢了,拾娃婆腾出一只手就掐就拧,还咬。
隔着半条街就听见孕妇在呻唤:哎哟,哎哟,好我的干大大呀!那时,孕妇生孩子都这样呻唤,都这么两句;孕妇生孩子时不兴哭爹喊娘,不吉利。
孕妇家门口,早有老辈子挑着风灯在迎候拾娃婆了。老辈子日急慌忙地把拾娃婆两口迎进街门,大老远就麻麻着声音说:来了就好,咱做老辈子的这就算把心放到肚子里了。俺儿在队伍上穿二尺五,年头里上了火线。
拾娃婆让男人放在了台阶上,她颠着小脚一跳一跳地往上房走。拾娃婆边走边问:搂腰的来了吗?搂腰的是肖家婆娘还是牛蛋他妈?
老年间生娃离不得个搂腰的,就像耍把戏的离不得猴。肖家婆娘和牛蛋他妈都是城南鼎鼎有名的搂腰的,两个人都是大脚快手,除了搂腰,还兼着烧水、扯腿和给孕妇及其全家人报喜。
老辈子背弓闪腰地跟在拾娃婆后面,焦苦着脸说:这娃争嘴,他要投生了这就邪事不断肖家婆娘过灞河回娘家了,让河水隔在了河对岸;牛蛋他妈在月子里呢。我这儿正提着裤子找腰没处挖抓!你看咋办?
掀开门帘,拾娃婆颠着小脚进了里间屋。孕妇见拾娃婆进了门,长长舒了一口气:婶,你来了我就把心放到肚子里了。拾娃婆一边往炕边走,一边喜眉笑眼地说:把灯挑亮,生娃哩又不是做贼哩。拾娃婆呼啦掀开被子,射眉弄眼地瞅着孕妇蚂蚱一样鼓起的肚子,伸出糙手就往孕妇裆里摸。拾娃婆一边摩挲着一边说:嗨,是个牛牛娃,正在宫门边上滚铁环哩。别张惊了,离娃投生还得有一灯油的工夫。
孕妇哧哧地笑,眼泪疙瘩在眼眶里打滚。
拾娃婆一边给孕妇掖被角,一边嘻嘻笑道:笼盖甭揭太早了,女子呀,工夫不大你就是妇道人家了,该问娃他爷、娃他奶要的金银细软现在就开口!迟了你就啥也得不上了,都是人家孙子的!女子开了怀就像老瓮裂了一道缝,再好的箍瓮汉也箍不浑全了。
孕妇噙在眼眶里的眼泪疙瘩流了下来,分不清脸上是汗水还是泪水了。
厅房里,两个粗皮糙脸的老汉周吴郑王地坐在八仙桌边噙着烟袋吧嗒吧嗒地在抽烟。孕妇的婆婆在佛台里跪在观音像前许愿,木鱼笃儿笃儿地响,像一挂金装银鞍的马车从远处驶来。
里间屋里传来拾娃婆的声音:娃他婆,烧一锅热水,娃赶了几百里旱路来咱家投生,尘土灰纤的,还不得浇头盖脸地洗个痛快。
木鱼哑了,风箱扑沓沓响了起来。
孕妇一声长、一声短地在里间屋里呻唤,还是那两句:哎哟哟,好我的干大大呀!拾娃婆撩开嗓子在里间屋里喊:娃他婆,抢忙,搭手把腰给咱抱住,娃跟他妈扭成一把子对付我哩。
娃他婆颠着小脚从伙房里走了出来,拄着拐棍就往上房里走。娃他婆也是小脚,噔噔地进了上房,掀帘子进了里间屋。里间屋里,两个小脚老太太在围着老瓮一样臃肿着身子的孕妇使劲:嗯,嗯嗯,这娃就这么争嘴,使蛮力跟俺俩小脚婆娘撕挖!娃她婆身单力薄,搂不住儿媳的碌碡粗腰,也就丝毫使不上劲。
拾娃婆嘟囔道:娃他婆,你这哪儿是在搂腰,只扯住了娃他妈个衣裳襟子!得找个体量大的人来搂腰!
娃他婆哝腔哝调地说话了:黑灯瞎火,你让我可到哪儿给你找个搂腰的呀?
这时,在大炕上挣扎的孕妇一声长、一声短地说话了:哎呀我呀,这娃是阎王爷派来索我命的厅房里谁在说话,顾不得羞臊了,哎呀我呀。
拾娃婆撩开声音喊:娃他妈这会儿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都说胡话了。顶多再能扛一袋烟的时间!厅房里的两个大老爷们儿,是人的你就进来一个,这是生娃哩,又不是做贼呢!娃的脚都出来了,横生倒养,这可是性命纠葛的事情!
听到横生倒养,厅房里八仙桌边坐着的娃他爷腾地站了起来,娃他爷撩起袍襟扑通就给拾娃婆的男人跪下了:兄弟,只有你进去给搂腰了,你是箍瓮匠,有的是力气!再说,我是娃没出五服的长辈。
箍瓮匠从地上搀扶起娃他爷,顺手摘下娃他爷架在鼻子上的石头镜,戴在自己的脸上,木讷着说:戴着这石头镜,我两眼一抹黑就啥也看不见了。我去搂腰,碎碎个事。
娃他爷拍着大腿说:嗨,葫芦锯开是两瓢,天底下就只有两套有用的下水!你去你去!
箍瓮匠低头埋脑地掀帘子进了里间屋,上了大炕,搂着孕妇的后腰如搂着老瓮:嗨,嗨嗨
很快,里间屋里传来了婴儿哦儿哦儿的啼声。拾娃婆长长出了一口气,她说:哎嘘,让我猜准了,是个牛牛娃!
拾娃婆给新生儿洗了涮了,把新生儿塞在了他妈怀里。新生儿偎在他妈的怀里张着小嘴寻找奶头。这时,天光已经放亮,不大会儿,太阳就腾腾地攀上了窗台。
收拾停当,拾娃婆把娃他爷用红纸包着的孝赏揣进大襟,张罗着要走。娃他婆端详着戴着石头镜的箍瓮匠嘿儿嘿儿地笑,她笑着说:兄弟,这石头镜架在你鼻疙瘩上太合适了,你瞅坨大,色重,但只可惜你人是个窄脸子!说着,娃他婆伸手就从箍瓮汉鼻梁上把眼镜摘了下来,递给了自家爷们儿。
踩着晨光,拾娃婆在自家男人背上低声地抽泣。她说:没成色,你咋就把人家的石头镜架在自己鼻梁上了,让人家说咱窄脸子!知道吗,这比给我脸上吐口唾沫还恶心!你说呀你当时咋不给她几句?拾娃婆伏在自家爷们儿的后背上,掐,拧,还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