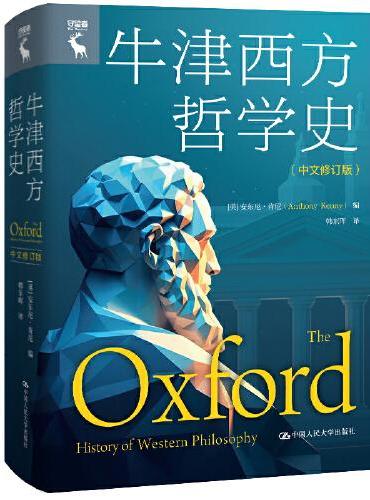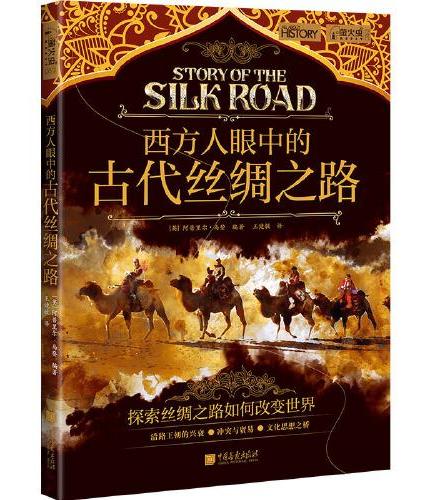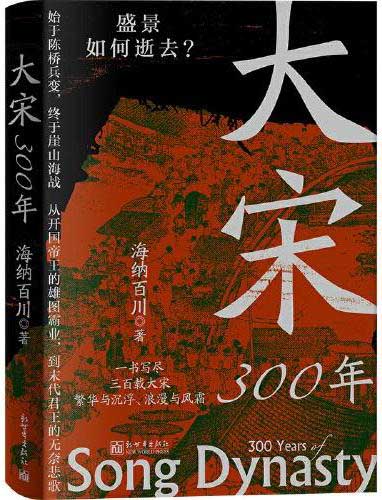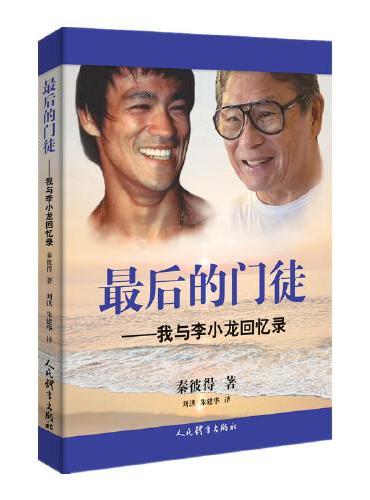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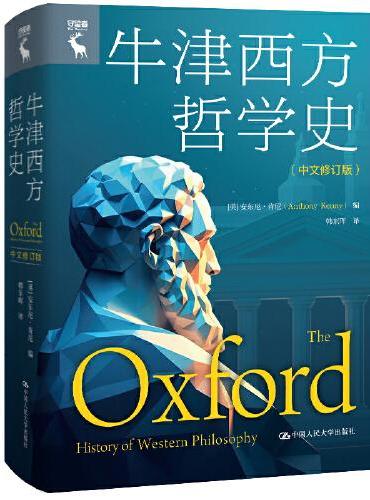
《
牛津西方哲学史(中文修订版)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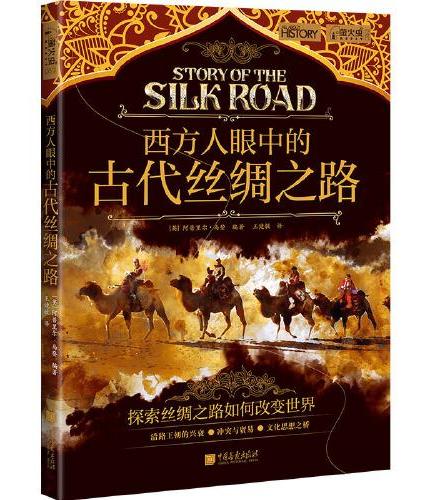
《
萤火虫全球史:西方人眼中的古代丝绸之路
》
售價:NT$
38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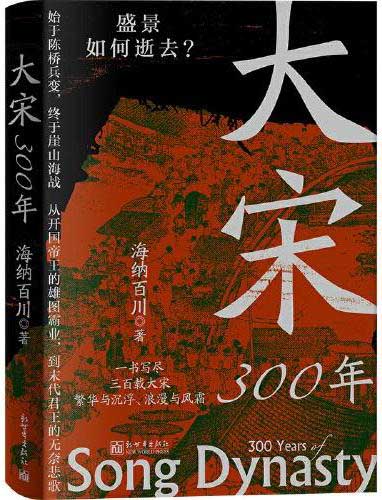
《
大宋300年(写尽三百载大宋繁华与沉浮、浪漫与风霜)
》
售價:NT$
352.0

《
害马之群:失控的群体如何助长个体的不当行为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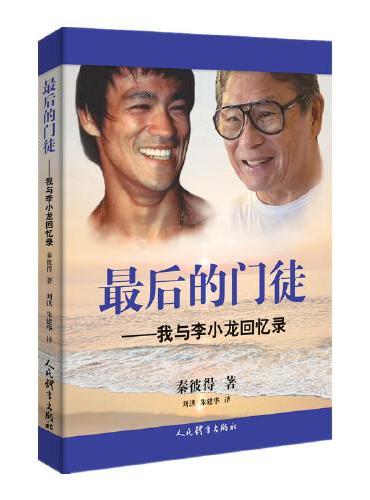
《
最后的门徒——我与李小龙回忆录
》
售價:NT$
347.0

《
没有明天的我们,在昨天相恋
》
售價:NT$
218.0

《
流动的白银(一部由白银打开的人类文明发展史)
》
售價:NT$
296.0

《
饮食的谬误:别让那些流行饮食法害了你
》
售價:NT$
296.0
|
| 內容簡介: |
第四部《巫师与玻璃球》又被称为铁汉柔情卷,讲述了冷酷的枪侠罗兰少年时的爱情故事。在这一部中,我们看到罗兰是如何邂逅他一生的挚爱苏珊并*终失去她的。
在命悬一线的*后关头,埃蒂终于想出了一道谜语,摧毁了布莱因。单轨火车在托皮卡停了下来,这儿已被超级流感侵袭。在罗兰和他的朋友们沿着光束的路径继续行程之前,吊足了塔迷们胃口的金大师终于开始讲述罗兰十四岁时的初恋故事,慰藉了一下从*本开始就被罗兰的过去这个巨大的悬念勒得透不过气来的读者。
内领地危机四伏,为了保护罗兰,他的父亲将罗兰和他*好的伙伴库斯伯特与阿兰一起,化名派往眉脊泗的海滨小城罕布雷。三个稚气未脱的少年很快就敏锐地发现这儿正酝酿着极大的阴谋,形势甚至比内领地更为严峻。在到达罕布雷的*个晚上,罗兰就与十六岁的金发女孩苏珊一见钟情。但苏珊为拯救她的家族刚刚做了一个可怕的决定,这意味着她与罗兰已经可不能坦然相恋。两个年轻人一方面无法对抗自己内心的强烈情感,另一方面又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爱将会置他们于*凶险的境地
|
| 關於作者: |
一九四七年出生于美国缅因州波特兰市,后在缅因州州立大学学习英语文学,毕业后走上写作之路。自一九七三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魔女嘉莉》后,迄今已著有四十多部长篇小说和两百多部短篇小说。其所有作品均为全球畅销书,有超过百部影视作品取材自他的小说,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肖申克的救赎》。
一九九九年,斯蒂芬?金遭遇严重车祸,康复后立刻投入写作。二○○三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其后又获得世界奇幻文学奖的终身成就奖和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爱伦坡奖的大师奖。
在斯蒂芬?金的众多作品中,以历时三十余年才完成的奇幻巨著黑暗塔系列(共八卷)最为壮观,书里的人物与情节,散见于斯蒂芬?金的其他小说中。近年来的新作有短篇小说集《日落之后》,中篇小说集《暗夜无星》,以及长篇小说《112263》《穹顶之下》《乐园》《长眠医生》等。
目前斯蒂芬?金与妻子居住在美国缅因州班戈市。他的妻子塔比莎金也是位小说家。
|
| 目錄:
|
序言:关于十九岁
前情概要
序幕布莱因
第一卷 猜谜
第一章 魔月之下(Ⅰ)
第二章 猎犬瀑布
第三章 猜谜节白鹅
第四章 托皮卡
第五章 轧公路
第二卷 苏珊
第一章 吻月之下
第二章 清白证明
第三章 路遇
第四章 月落已久
第五章 欢迎来到城里
第六章 锡弥
第七章 鲛坡
第八章 商月之下
第九章 西特果2
第十章 鸟、熊、兔子和鱼
第三卷 来吧,收割
第一章 猎女月下
第二章 窗边的女孩
第三章 城堡游戏
第四章 罗兰和库斯伯特
第五章 巫师的彩虹
第六章 年结时分
第七章 取回玻璃球
第八章 灰烬
第九章 收割节
第十章 魔月之下(Ⅱ)
第四卷 上帝的儿女都有鞋子
第一章 堪萨斯的早晨
第二章 路上的鞋子
第三章 巫师
第四章 玻璃球
第五章 光束的路径
后记
|
| 內容試閱:
|
序言:关于十九岁
(及一些零散杂忆)
1
在我十九岁时,霍比特人正在成为街谈巷议(在你即将要翻阅的故事里就有它们的身影)。
那年,在马克思雅斯格牧场上举办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就有半打的梅利和皮平在泥泞里跋涉,另外还有至少十几个佛罗多,以及数不清的嬉皮甘道夫。在那个时代,约翰罗奈尔得瑞尔托尔金的《指环王》让人痴迷狂热,尽管我没能去成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这里说声抱歉),我想我至少还够得上半个嬉皮。话说回来,他的那些作品我全都读了,并且深为喜爱,从这点看就算得上一个完整的嬉皮了。和大多数我这一代男女作家笔下的长篇奇幻故事一样(史蒂芬唐纳森的《汤玛斯考文南特的编年史》以及特里布鲁克斯的《沙娜拉之剑》就是众多小说中的两部),《黑暗塔》系列也是在托尔金的影响下产生的故事。
尽管我是在一九六六和一九六七年间读的《指环王》系列,我却迟迟未动笔写作。我对托尔金的想象力的广度深为折服(是相当动情的全身心的折服),对他的故事所具有的那种抱负心领神会。但是,我想写具有自己特色的故事,如果那时我便开始动笔,我只会写出他那样的东西。那样的话,正如已故的善辩的迪克尼克松喜欢说的,就会一错到底了。感谢托尔金先生,二十世纪享有了它所需要的所有的精灵和魔法师。
一九六七年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写什么样的故事,不过那倒也并不碍事;因为我坚信在大街上它从身边闪过时,我不会放过去的。我正值十九岁,一副牛哄哄的样子,感觉还等得起我的缪斯女神和我的杰作(仿佛我能肯定自己的作品将来能够成为杰作似的)。十九岁时,我好像认为一个人有本钱趾高气扬;通常岁月尚未开始不动声色的催人衰老的侵蚀。正像一首乡村歌曲唱的那样,岁月会拔去你的头发,夺走你跳步的活力,但事实上,时间带走的远不止这些。在一九六六和一九六七年间,我还不懂岁月无情,而且即使我懂了,也不会在乎。我想象不到简直难以想象活到四十岁会怎样,退一步说五十岁会怎样?再退一步。六十岁?永远不会!六十岁想都没想过。十九岁,正是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十九岁这个年龄只会让你说:当心,世界,我正抽着TNT,喝着黄色炸药,你若是识相的话,别挡我的道儿斯蒂夫在此!
十九岁是个自私的年纪,关心的事物少得可怜。我有许多追求的目标,这些是我关心的。我的众多抱负,也是我所在乎的。我带着我的打字机,从一个破旧狭小的公寓搬到另一个,兜里总是装着一盒烟,脸上始终挂着笑容。中年人的妥协离我尚远,而年老的耻辱更是远在天边。正像鲍勃西格歌中唱到的主人公那样那首歌现在被用做了售卖卡车的广告歌我觉得自己力量无边,而且自信满满;我的口袋空空如也,但脑中满是想法,心中都是故事,急于想要表述。现在听起来似乎干巴无味的东西,在当时却让自己飘上过九重天呢。那时的我感到自己很酷。我对别的事情毫无兴趣,一心只想突破读者的防线,用我的故事冲击他们,让他们沉迷、陶醉,彻底改变他们。那时的我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做到,因为我相信自己生来就是干这个的。
这听上去是不是狂傲自大?过于自大还是有那么一点?不管怎样,我不会道歉。那时的我正值十九岁,胡须尚无一丝灰白。我有三条牛仔裤,一双靴子,心中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我稳握在手的牡蛎,而且接下去的二十年证明自己的想法没有错误。然而,当我到了三十九岁上下,麻烦接踵而至:酗酒,吸毒,一场车祸改变了我走路的样子(当然还造成了其他变化)。我曾详细地叙述过那些事,因此不必在此旧事重提。况且,你也有过类似经历,不是吗?最终,世上会出现一个难缠的巡警,来放慢你前进的脚步,并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宰。毫无疑问,正在读这些文字的你已经碰上了你的巡警(或者没准哪一天就会碰到他);我已经和我的巡警打过交道,而且我知道他肯定还会回来,因为他有我的地址。他是个卑鄙的家伙,是个坏警察,他和愚蠢、荒淫、自满、野心、吵闹的音乐势不两立,和所有十九岁的特征都是死对头。
但我仍然认为那是一个美好的年龄,也许是一个人能拥有的最好的岁月。你可以整晚放摇滚乐,但当音乐声渐止,啤酒瓶见底后,你还能思考,勾画你心中的宏伟蓝图。而最终,难缠的巡警让你认识到自己的斤两;可如果你一开始便胸无大志,那当他处理完你后,你也许除了自己的裤脚之外就什么都不剩了。又抓住一个!他高声叫道,手里拿着记录本大步流星地走过来。所以,有一点傲气(甚至是傲气冲天)并不是件坏事尽管你的母亲肯定教你要谦虚谨慎。我的母亲就一直这么教导我。她总说,斯蒂芬,骄者必败结果,我发现当人到了三十八岁左右时,无论如何,最终总是会摔跟头,或者被人推到水沟里。十九岁时,人们能在酒吧里故意逼你掏出身份证,叫喊着让你滚出去,让你可怜巴巴地回到大街上,但是当你坐下画画、写诗或是讲故事时,他们可没法排挤你。哦,上帝,如果正在读这些文字的你正值年少,可别让那些年长者或自以为是的有识之士告诉你该怎么做。当然,你可能从来没去过巴黎;你也从来没在潘普洛纳奔牛节上和公牛一起狂奔。不错,你只是个毛头小伙,三年前腋下才开始长毛但这又怎样?如果你不一开始就准备拼命长来撑坏你的裤子,难道是想留着等你长大后再怎么设法填满裤子吗?我的态度一贯是,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年轻时就要有大动作,别怕撑破了裤子;坐下,抽根烟。
2
我认为小说家可以分成两种,其中就包括像一九七○年初出茅庐的我那样的新手。那些天生就更在乎维护写作的文学性或是严肃性的作家总会仔细地掂量每一个可能的写作题材,而且总免不了问这个问题:写这一类的故事对我有什么意义?而那些命运与通俗小说紧密相连的作家更倾向于提出另一个迥异的问题:
写这一类的故事会对其他人有什么意义?严肃小说家在为自我寻找答案和钥匙;然而,通俗小说家寻找的却是读者。这些作家分属两种类型,但却同样自私。我见识过太多的作家,因此可以摘下自己的手表为我的断言做担保。
总之,我相信即使是在十九岁时,我就已经意识到佛罗多和他奋力摆脱那个伟大的指环的故事属于第二类。这个故事基本上能算是以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为背景的一群本质上具有英国特征的朝圣者的冒险故事。我喜欢探险这个主题事实上,我深爱这一主题但我对托尔金笔下这些壮实的农民式的人物不感兴趣(这并不是说我不喜欢他们,相反我确实喜欢这些人物),对那种树木成荫的斯堪的纳维亚场景也没有兴趣。如果我试图朝这个方向创作的话,肯定会把一切都搞砸。
所以我一直在等待。一九七○年时我二十二岁,胡子中出现了第一缕灰白(我猜这可能与我一天抽两包半香烟有关),但即便人到了二十二岁,还是有资本再等一等的。二十二岁的时候,时间还在自己的手里,尽管那时难缠的巡警已经开始向街坊四处打探了。
有一天,在一个几乎空无一人的电影院里(如果你真好奇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是在缅因州班哥尔市的百玖电影院里),我看了场瑟吉欧莱昂内执导的《独行侠勇破地狱门》。在电影尚未过半时,我就意识到我想写部小说,要包含托尔金小说中探险和奇幻的色彩,但却要以莱昂内创造的气势恢弘得几乎荒唐的西部为背景。如果你只在电视屏幕上看过这部怪诞的西部片,你不会明白我的感受也许这对你有些得罪,但的确是事实。经过潘那维申一种制作宽银幕电影的工艺,商标名。译者注。如无特别说明,后文中的注解一律为译者注。镜头的精确投射,宽银幕上的《独行侠勇破地狱门》简直就是一部能和《宾虚》相媲美的史诗巨作。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看上去足有十八英尺高,双颊上挺着的每根硬如钢丝的胡茬都有如小红杉一般。李范克里夫嘴角两边的纹路足有峡谷那么深,在底部就变得有些窄小(见《巫师与玻璃球》)。而望不到边的沙漠看上去至少延伸到海王星的轨道边了。片中人物用的枪的枪管直径都如同荷兰隧道般大小。
除了这种场景设置之外,我所想要获得的是这种尺寸所带来的史诗般的世界末日的感觉。莱昂内对美国地理一窍不通(正如片中的一个角色所说,芝加哥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边上),但正由于这一点,影片得以形成这种恢弘的错位感。我的热情一种只有年轻人才能迸发出的激情驱使我想写一部长篇,不仅仅是长篇,而且是历史上最长的通俗小说。我并未如愿以偿,但觉得写出的故事也足够体面;《黑暗塔》,从第一卷到第七卷讲述的是一个故事,而前四卷的平装本就已经超过了两千页。后三卷的手稿也逾两千五百页。我列举这些数字并不是为了说明长度和质量有任何关联;我只是为了表明我想创作一部史诗,而从某些方面来看,我实现了早年的愿望。如果你想知道我为何有这么一种目标,我也说不出原因。也许这是不断成长的美国的一部分:建最高的楼,挖最深的洞,写最长的文章。我的动力来自哪里?也许你会抓着头皮大喊琢磨不透。在我看来,也许这也是作为一个美国人的一部分。最终,我们都只能说:那时这听上去像个好主意。
3
另一个关于十九岁的事实不知道你还爱不爱看就是处于这个年龄时,许多人都觉得身处困境(如果不是生理上,至少也是精神和感情上)。光阴荏苒,突然有一天你站在镜子跟前,充满迷惑。为什么那些皱纹长在我脸上?你百思不得其解,这个丑陋的啤酒肚是从哪来的?天哪,我才十九岁呢!这几乎算不上是个有创意的想法,但这也并不会减轻你的惊讶程度。
岁月让你的胡须变得灰白,让你无法再轻松地起跳投篮,然而一直以来你却始终认为无知的你啊时间还掌握在你的手里。也许理智的那个你十分清醒,只是你的内心拒绝接受这一事实。如果你走运的话,那个因为你步伐太快,一路上享乐太多而给你开罚单的巡警还会顺手给你一剂嗅盐嗅盐,是一种芳香碳酸铵合剂,用作苏醒剂。。我在二十世纪末的遭遇差不多就是如此。这一剂嗅盐就是我在家乡被一辆普利矛斯捷龙厢式旅行车撞到了路边的水沟里。
在那场车祸三年后,我到密歇根州蒂尔博市的柏德书店参加新书《缘起别克8》的签售会。当一位男士排到我面前时,他说他真的非常非常高兴我还活着。(我听了非常感动,这比你怎么还没死?这种话要令人振奋得多。)
当我听说你被车撞了时,我正和一个好朋友在一起。他说,当时,我们只能遗憾地摇头,还一边说这下塔完了,已经倾斜了,马上要塌,啊,天哪,他现在再也写不完了。
相仿的念头也曾出现在我的脑袋里这让我很焦急,我已经在百万读者集体的想像中建造起了这一座黑暗塔,只要有人仍有兴趣继续读下去,我就有责任保证它的安全即使只是为了下五年的读者;但据我了解,这也可能是能流传五百年的故事。奇幻故事,不论优劣(即使是现在,可能仍有人在读《吸血鬼瓦涅爵士》或者《僧侣》),似乎都能在书架上摆放很长时间。罗兰保护塔的方法是消灭那些威胁到梁柱的势力,这样塔才能站得住。我在车祸后意识到,只有完成枪侠的故事,才能保护我的塔。
在黑暗塔系列前四卷的写作和出版之间长长的间歇中,我收到过几百封信,说理好行囊,因为我们十分内疚之类的话。一九九八年(那时我还当自己只有十九岁似的,狂热劲头十足),我收到一位八十二岁老太太的来信,她并无意要来打搅你,但是这些天病情加重。这位老太太告诉我,她也许只有一年的时间了(最多十四个月,癌细胞已经遍布全身),而她清楚我不可能因为她就能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罗兰的故事,她只是想知道我能否(求你了)告诉她结局会怎样。她发誓绝不会告诉另一个灵魂,这句话很是让我揪心(尽管还没到能让我继续创作的程度)。一年之后好像就是在车祸后我住院的那段时间里我的一位助手,马莎德菲力朴,送来一封信,作者是得克萨斯州或是佛罗里达州的一位临危病人,他提了完全一样的要求:想知道故事以怎样的结局收场?(他发誓会将这一秘密带到坟墓里去,这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我会满足这两位的愿望帮他们总结一下罗兰将来的冒险历程如果我能做到的话,但是,唉,我也不能。那时,我自己并不知道枪侠和他的伙伴们会怎么样。要想知道,我必须开始写作。我曾经有过一个大纲,但一路写下来,大纲也丢了。(反正,它可能本来也是一文不值。)剩下的就只是几张便条(当我写这篇文章时,还有一张阒茨,栖茨,葜茨,某某某某篮子这是在黑暗塔中出现过多次的一段童谣。贴在我桌上)。最终,在二一年七月,我又开始写作了。那时我已经接受了自己不再是十九岁的事实,知道我也免不了肉体之躯必定要经受的病灾。我清楚自己会活到六十岁,也许还能到七十。我想在坏巡警最后一次找我麻烦之前完成我的故事。而我也并不急于奢望自己的故事能和《坎特伯雷故事集》或是《艾德温德鲁德之谜》归档在一起。
我忠实的读者,不论你看到这些话时是在翻开第一卷还是正准备开始第五卷的征程,我写作的结果孰优孰劣就摆在你的面前。不管你是爱它还是恨它,罗兰的故事已经结束了。我希望你能喜欢。
对于我自己,我也拥有过了意气风发的岁月。
斯蒂芬金
二○○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个完美的银盘吻月,满土的时候人们是这样称呼它的悬挂在起伏的山峦上,山峦在罕布雷以东五英里,爱波特大峡谷以南十英里。夏天即将过去,但太阳落山两小时以后山脚下还是闷热无比;然而在库斯山的顶上,阵阵微风裹挟着寒气,人们觉得好像收割季节已经来临了。住在山顶的女人除了一条蛇和一只畸形的老猫以外就没什么人作伴了,所以这个夜晚显得尤其漫长。
这没关系;亲爱的,没有关系。只要很忙,就会开心。的确如此。
她坐在茅屋大房间的窗边(此外只有一间房,一间只比壁橱大一点点的卧室),一直等到来访者的马蹄声渐渐远去。姆斯提,一只六脚猫,趴在她肩膀上。月光泻满她的大腿。
三匹马,带着三个人离开了。他们自称是灵柩猎手。
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男人很滑稽,是的,但最有趣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滑稽。男人,用华而不实的名字称呼自己。男人,总是夸耀自己的肌肉、酒量和饭量;而且永远都对自己的性能力无比自豪。是的,即使他们的精子孕育出的孩子呆傻畸形,只配扔到离家最近的井里,他们仍然死性不改。哦,但那不是他们的错,对不对,亲爱的?不,总是女人的错她的子宫,她的毛病。男人都是懦夫。那个上了年纪的跛子倒还像有点勇气的样子他瞪着明亮的,过分好奇的眼睛看着她但他眼神里没有任何能让她害怕的东西。
男人!她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女人怕他们。难道上帝缔造男人的时候不是把他们最脆弱的部位放在体外了么,就像一段放错位置的肠子?在那个部位给他们一脚,他们就会像蜗牛一样蜷缩起来。在那个部位爱抚他们,他们的大脑就会化成一摊水。要是有谁怀疑第二条,就看看她今晚剩下的那点事情好了,那点还没做的事情。托林!罕布雷的市长!领地的守卫者!没什么比一个老傻瓜更傻的了!
但是那些想法对她一点作用都没有,也对男人们没有一点损害,至少现在没有;这三个自称是灵柩猎手的男人给她带来了一个大大的惊喜,她要好好看看;嗨,她可要看个仔细。
跛子乔纳斯坚持要她把这样东西放到别处有人告诉他,她有个地方专门放这些东西,并不是他想去这个地方看看,上帝作证,他可不想看这个女人的任何秘密处所(听到这个俏皮话,德佩普和雷诺兹放声大笑)所以她也这样做了,但现在他们的马蹄声已经被风声吞噬了,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哈特托林已经为那个女孩的双乳魂不守舍了,而那丫头要至少一个小时才会过来(那老女人坚持要让女孩从市里走过来,理由是月光有洁净身心的作用,其实她不过是为了在两个约会中间留出安全的时间间隔罢了),在那个小时里她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
哦,真漂亮啊,我可以肯定地这么说。她嘀咕着,她有没有觉得她的两条O型腿之间有些发热呢?那条隐藏的久已干涸的小溪终于有了些湿气?天哪!
哎,即使透过装它的盒子,我都能感受到它的魅力。姆斯提,它真是漂亮,就像你一样。她把肩膀上的猫拿了下来,举到眼前。那只公猫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把一张大脸凑到她面前。她亲了亲它的鼻子。姆斯提很享受地闭上了那双浑浊的灰绿色眼睛。真是太漂亮了,就像你一样你真漂亮!你真漂亮!哦!
她把猫放下。那只猫慢腾腾地朝着壁炉走去,刚刚点燃的火不温不火地烧着,漫不经心地吞噬着一块孤零零的木头。姆斯提的尾巴顶端分了岔,看上去就像是一副古老图画里魔鬼的叉子形尾巴。它就在这个房间昏黄的光线里前后摇晃着尾巴。多出来的两条腿从身子两侧垂下来,漫不经心地抽动着。猫影子在地板上移动,在墙上越变越大,真是很可怕的一幕:就好像是猫和蜘蛛生出来的杂种。
老女人站起身来,走进自己的卧室,乔纳斯给她的东西就放在那里。
要是你把这个弄丢了,你脑袋也就保不住了。他这样说。
别担心我,我的好朋友。她回答道,脸上的笑容恭顺而又谦卑,但她心里却一直在想:男人!趾高气扬的笨男人!
她走向床边,跪了下来,用一只手摸向泥土地面。肮脏的地面随之出现了一条条细线。它们形成了一个正方形。她把手指伸到其中一条线上;在她的手碰到之前,这条线就后退了。她提起隐藏的嵌板(藏在很隐秘的地方,如果不是用手去摸的话是根本无法发现的),这时出现了一个约摸一平方英尺大,深有两英尺的小隔间。里面是一个硬木箱。箱子上面蜷缩着一条细长的绿色小蛇。当她碰到蛇的背部时,蛇头就抬了起来。蛇无声地打起了哈欠,发出几乎让人难以察觉的咝咝声,同时露出了四对毒牙两对在上面,两对在下面。
她拿起蛇,对着它轻轻哼唱。等她把蛇的脸靠近自己的脸时,蛇的嘴巴张得更大了,咝咝的声音也可以听见了。她也张开了嘴;从满是皱纹的灰白嘴唇中她伸出了发黄的、散发着臭气的舌头。两滴毒汁要是混在酒里的话足以把所有来参加宴会的人都毒死滴到了上面。她咽了下去,感觉自己的口腔、喉咙和胸腔仿佛在燃烧,就像喝下了很烈的烧酒。一时间她面前天旋地转,她能听见浑浊的空气里窃窃私语的声音是她所谓的看不见的朋友的声音。她的眼睛里流出了黏糊糊的液体,一直流到时间在她脸上刻下的痕迹里。然后她呼出一口气,整个房间又恢复了稳定。说话的声音消失了。
她在爱莫特没有眼皮的双眼之间吻了一下(她想,对啊,现在正是吻月呢),然后就把它放在了一旁。蛇钻到床底下,蜷成一个圆圈,看着她用双手抚摸着硬木盒子的顶部。她能感觉到自己的上臂肌肉在颤抖,还有就是身体下部的热量加强了。她有好几年没有感受到身体的欲望了,但是她此时感受到了,明明白白地感受到了,而这跟吻月无关,或者说关系不大。
盒子锁上了,乔纳斯没有给她钥匙,但是那对她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她活了很多年了,做了很多研究,还和各种动物们交流。而很多自诩厉害的男人们见到那些动物都像屁股着了火一样溜之大吉。她把手伸向那把锁,上面刻有一个眼睛状的东西和用高等语写的一句话(我看见谁打开了我),然后又把手缩回来。突然她闻到了平时闻不到的气味:霉味和灰尘,脏垫子以及在床上吃饭后留下的食物碎屑;灰烬和古老的香混合起来的味道;一个老女人那湿润的眼睛和(这是很普遍的)干燥的阴道散发出的味道。她不会打开盒子来看个究竟;她想走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那里只有豆科灌木和鼠尾草的味道。
她要借着吻月的光芒来看。
库斯山的蕤嘟哝着把这个盒子从洞里拉出来,站起身来,又嘟哝了一声(这次的声音是从下面发出的),把盒子掖在胳膊下面离开了房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