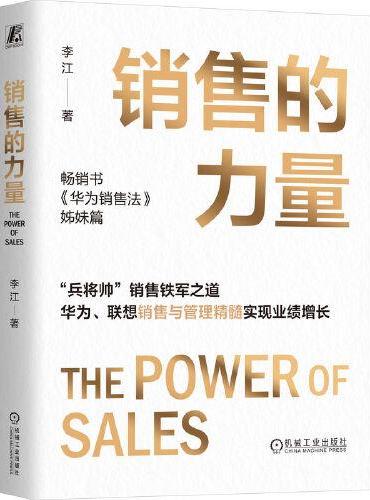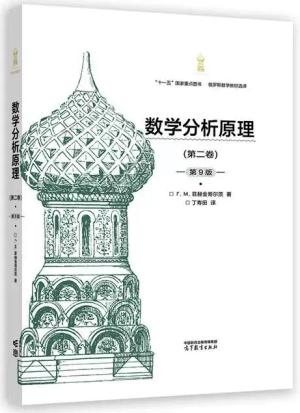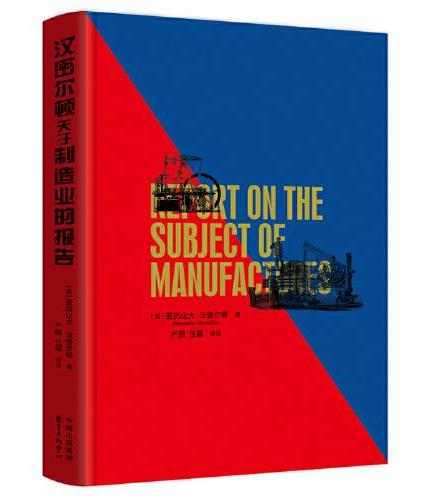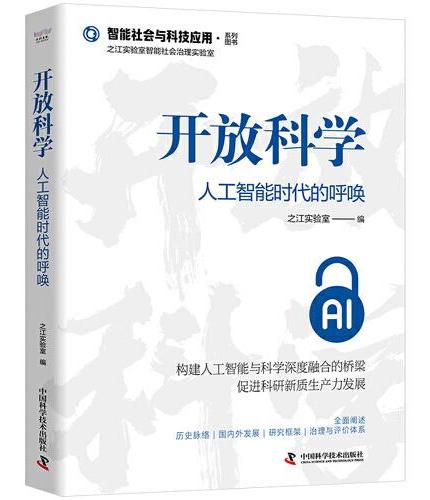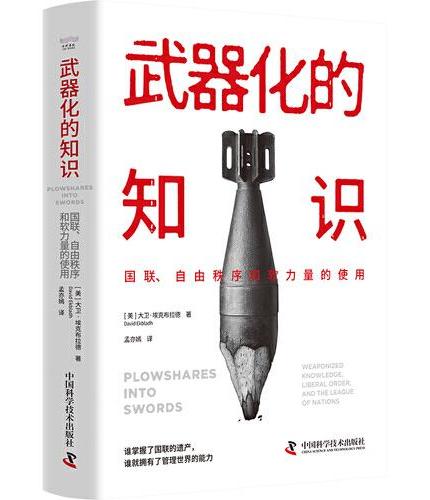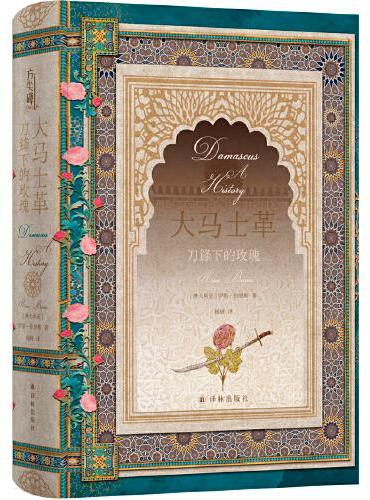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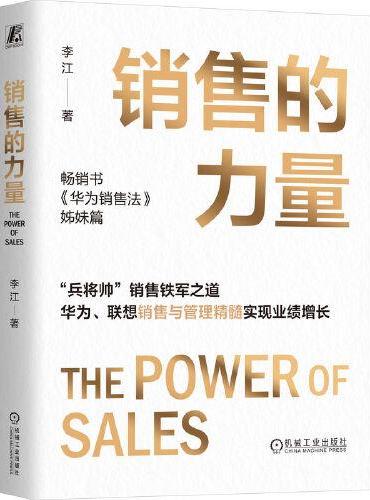
《
销售的力量
》
售價:NT$
454.0

《
我活下来了(直木奖作者西加奈子,纪实性长篇散文佳作 上市不到一年,日本畅销二十九万册)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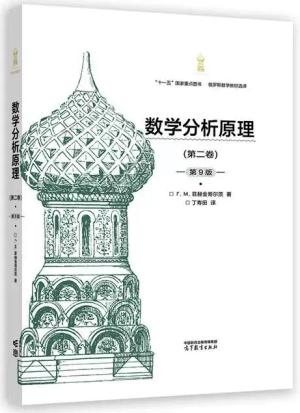
《
数学分析原理(第二卷)(第9版)
》
售價:NT$
403.0

《
陈寅恪四书
》
售價:NT$
146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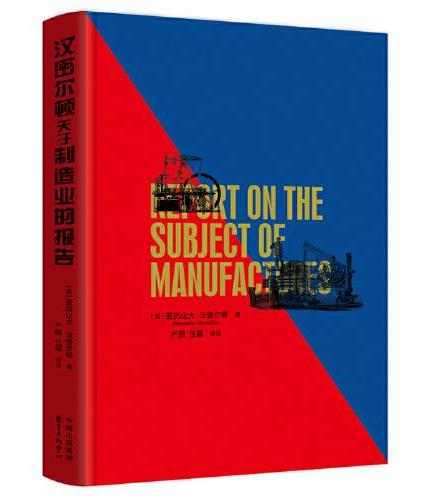
《
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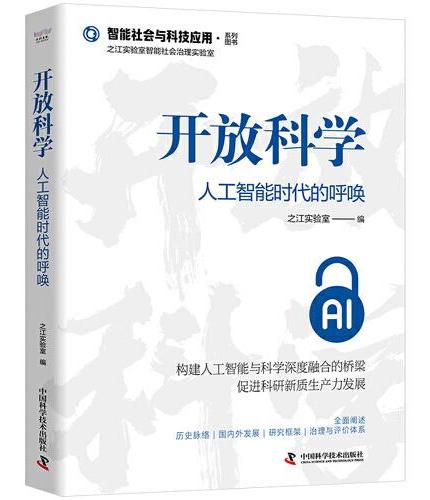
《
开放科学:人工智能时代的呼唤
》
售價:NT$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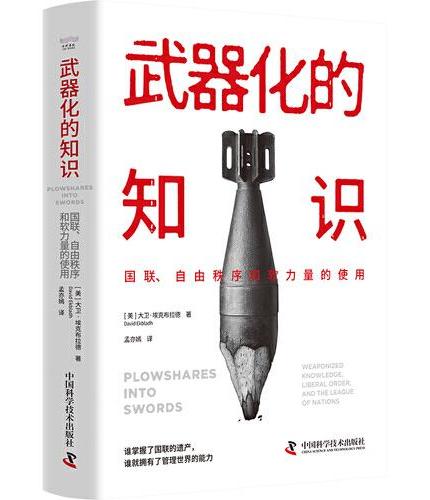
《
武器化的知识:国联、自由秩序和软力量的使用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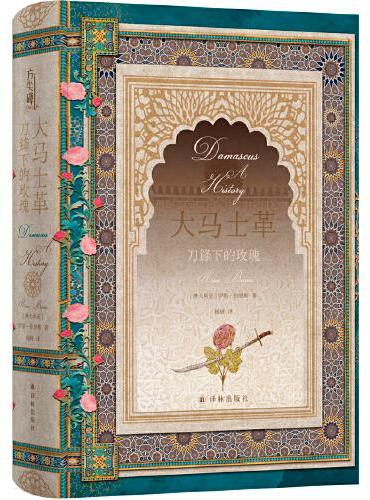
《
大马士革:刀锋下的玫瑰(方尖碑)
》
售價:NT$
607.0
|
| 編輯推薦: |
|
是一部传记,是一种研究,更是两个灵魂的对话。
|
| 內容簡介: |
|
余华是当代中国卓有建树、影响深远的作家,其经历、创作、思想,历来受到不少学者、评论者关注与研究,在普通读者那里,也因为对他的作品的阅读,而产生进一了解的兴趣。著名评论家洪治纲穷数年之力,不仅细读了余华所有的散文、随笔、小说、访谈,更与作家本人及其家人、亲朋好友有过范围宽泛的采访、交谈,掌握了*手的资料。在此基础上,以学者的睿智、批评家的激情,写就了一本有关同时代作家余华的评传。这是一部了解余华,了解其作品的必读之书。
|
| 關於作者: |
洪治纲,男,1965年10月出生于安徽省东至县。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浙江省钱江学者特聘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及评论三百余万字。出版有《守望先锋》《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无边的迁徙》《中国六十出生作家群研究》《主体性的弥散》《心灵的见证》《邀约与重构》等个人专著十余部,以及《国学大师经典文存》《最新争议小说选》《年度中国短篇小说选》等个人编著三十余部。
曾获第四届全国鲁迅文学奖、首届全国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浙江省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当代中国文学评论家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
| 目錄:
|
第一章 从杭州到海盐
一出生 / 1
二举家之迁 / 3
三胆小的男孩 / 6
四医院里的风景 / 10
第二章 无序的成长
一阅读是如此的温暖 / 14
二墙上的风景 / 17
三快乐的写作 / 20
四高考 / 24
第三章 川端康成的启蒙
一牙医生涯 / 28
二川端康成的魅力 / 31
三雄心初展 / 37
四闪烁的《星星》/ 40
五幸福的文化馆 / 42
第四章 刀锋上的行走
一从小偷到大盗/ 47
二先锋出击 / 51
三暴力与死亡 / 58
四人性悲歌 / 69
第五章 内心的真实
一北京:另一种现实 / 77
二虚伪的写作 / 85
三在细雨中绝望地呼喊 / 92
四寻找突围 / 98
第六章 悲悯的力量
一人物开始了奔跑 / 106
二《活着》意味着什么 / 112
三《许三观卖血记》/ 123
四无边的悲悯 / 141
第七章 我能否相信自己
一写作是为了回家 / 149
二他没有自己的名字 / 156
三往事并不如烟 / 162
第八章 阅读与交流
一音乐的魅力 / 168
二寻找大师的智慧 / 178
三网络与文学 / 189
四与世界对话 / 196
第九章 艰难的超越
一艰难的超越 / 200
二半部《兄弟》的遭遇 / 205
三李光头的奇迹 / 216
四海外旋风 / 226
第十章 继续出发
一重审文学的原点 / 234
二差距里的疼痛 / 242
三《第七天》:寻找或见证 / 254
四喧嚣中的缅想与沉思 / 274
结语 孤独的远行
一回望先锋,穿透现实 / 282
二伟大的梦想是一部杰作 / 287
三喧哗中的远行 / 292
附录 余华生平年表 / 294
后记 / 320
|
| 內容試閱:
|
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没有一种人生是可以轻易读懂的。在2004年完成《余华评传》时,我曾由衷地写下了这句话。如今,十二年过去了,我和余华都已迈入知命之年。除了喟叹岁月的流逝,于我而言,探求未知事物的激情,也在渐行渐远。
这部评传的初版,是在匆匆状态下完成的。当时,我正处在博士论文写作的关键阶段,一手抓论文,一手抓评传,结果是,两手抓,两手都硬不起来。这导致了此书的初稿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记得当时,我与出版社补签了一份合同,以近乎武断的方式,只同意了五年的版权期限,希望尽快进行重新修订,形成一本相对准确和完整的书稿。
谁知道,转瞬之间,两个五年已飘然而过。工作的调动,生活的迁徙,使我一次次启动了重新修订的计划,却又一次次地被迫放弃。总想着更准确、更客观的修订版问世,我为此还不得不婉拒了几家国外的版权。其中的人生况味,自然是一言难尽。但是,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对余华创作的追踪,也一直没有放弃对余华生平材料的搜集。无论是他发表的小说或随笔,还是他有段时间热衷操作的微博,我都一一收录在案,希望在将来重新修订时,能够更准确地呈现余华生活和创作的轨迹。
在生活渐渐安稳之后,从2015年年底开始,我便着手这部评传的修订工作。然而,繁重的行政和教学工作,让我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也致使修订工作时断时续。历时半年之久,如今我终于完成了这部评传的修订,内心颇感欣慰。在修订过程中,我的首要目标,就是想努力解决初版中存在的诸多史料模糊或错漏之处。为此,除了与余华本人不断求证之外,我还请求同事张薇女士借助方言调查的机会,不断地前往海盐查阅各种第一手资料。张薇是一位热情且认真的老师,多年来一直从事方言的田野调查,这也给她提供了丰富的调研经验。所以,她不仅找到了余华的小学和中学同学,还将海盐县教育局、海盐县档案馆跑了个遍,并帮我确认了余华成长的每个关键时间,成功地弥补了以往的很多错漏之处。
作为评传的修订本,当然还需要补充初版之后留下的漫长的创作空白。为此,我增写了两章多的内容,完善了余华后期的创作情况及其生活轨迹。应该说,这十多年来,是余华人生最为复杂的历史时期。一方面,他的创作不断引起争议,尤其是《兄弟》和《第七天》的出版,在国内外的评价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几乎可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另一方面,他的作品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着令人瞩目的销售量,尤其是国外,很多世界顶尖的出版社都与余华签订了版权合同。与此同时,我还深切地感受到,面对中国这些年来愈加粗鄙、放纵却又生机勃勃的社会,面对差距不断扩大、矛盾此起彼伏的现实,余华的内心充满了各种难以言说的焦虑和无奈。如何把握这些芜杂现象背后的本质,呈现余华真实的内心镜像和精神历程,无疑是相当困难的。我只能以我有限的体验和思考,面对这位具有无限丰饶的内心质地的作家,展示我所理解的余华。
我要由衷地感谢余华本人,事实上,没有他的倾力相助,我不可能经历这种百感交集的温暖之旅,也不可能完成这部评传的修订稿。我还要由衷地感谢余华的父母和哥哥,他们不断地从悠悠的往事中为我捕捉了许多精确的记忆。同时,我更要感谢给我提供大量帮助的朋友,他们是张薇女士、姬汉民先生、王侃先生、薛荣先生以及海盐县向阳小学、海盐中学的现任领导,有很多具体的事件和时间,都是他们通过对原始资料的查找而获得的。当然,我最需要感谢的,还是我的博士生、华侨大学青年教师欧阳光明先生,在本书的修订过程中,他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我衷心地感谢他们。
洪治纲
2016年6月28日于杭州
第一章从杭州到海盐
一 出生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一千多年前的某个早春时节,风流倜傥的北宋词人柳永步入杭州。在这座江南古城,柳公子所到之处,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市列珠玑,户盈罗绮,满眼皆是前所未有的奢靡景象,使得他三步一惊,两步一叹。于是,在西湖里的某只画舫上,酒酣耳热之际,柳永终于情不自禁,挥毫写就了千古名词《望海潮》,几乎将天下的美誉之辞,都堆砌到杭州的身上。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尽管人们照例不忘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类的古话,但是,在经历了全国性的三年困难时期之后,1960年的杭州,似乎已没有了柳永笔下所形容的那种奢华。大多数的杭州市民,虽然还不至于像其他地方的老百姓那样,饿得两眼昏花,乃至浑身浮肿,然而生活无疑已变得相当严峻。所谓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已是不可能了,在这个江南的米鱼之乡,为一日三餐而奔波,便成为人们不折不扣的生活事实。
就在这一年的4月3日,随着浙江省立杭州医院(现为浙江省中医院)的某个产房里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后来叫余华的男孩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当然不知道,自己居然能降生在这座叫作天堂的城市;他也不可能知道,守在产房外的父亲得知又生了一个男孩,差点动了换婴的念头;他更不可能知道,自己出生的时候,正是大灾了三年且又青黄不接的时节。他的哥哥,一个正在蹒跚学步的小男孩,此时也以十分好奇而又激动的表情,欢迎着陌生弟弟的到来。
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家庭一样,多一个孩子,看起来无非是多一张嘴而已,但是,身为父母的华自治先生和余佩文女士,还是隐隐地感到自己的肩上又多了一份重量。因为他们都是医生,优生优育的意识自然要比一般人强得多;而且,华自治先生当时还在浙江医科大学进修专科,正处在事业进取的关键时期。至于物质生活的困顿,那就更不必说了。历经了三年困难时期,身高一米八几的华自治先生,当时的体重还不足一百二十斤,整个人瘦得像根麻秆。尤其是晚上读书回来,经常饥肠辘辘,彻夜难眠,万般无奈之际,他只好弄些咸菜泡开水裹腹。所以,余华的出生,在令父母欣喜之余,多少也给这个家庭增添了一些淡淡的焦虑。
无论是欣喜还是焦虑,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他们仍然保持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理想和热情,对未来充满了憧憬。据华自治先生回忆,余华出生时,也是他的人生道路不断发生转折的时期。这位一生只读过六年书,并在部队里锻炼了多年,怀抱火热理想的山东汉子,原本供职于浙江省防疫大队,专门负责全省家禽牲畜的防疫工作,后来因为社会主义教育(通常简称社教)而下派到了浙江省海盐县,并根据组织上的安排留在那里,当上了沈荡镇卫生所所长。为了能够成为一名医术高超的医生,实现自己靠技术吃饭的朴实理想,他又考取了浙江医科大学的专科,再度回杭州进修。读书的生活苦虽苦矣,但毕竟可以回到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家,享受几年家庭团聚的天伦之乐。
所幸的是,余华的母亲余佩文女士当时在浙江医院工作。浙江医院一直是浙江省的高干医院,专门负责省管干部的疾病诊治与医疗保健,包括上至省委书记和省长,下至各厅局的厅局长。所以,这里的医护人员即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物质供应也比一般市民相对充裕一些。余华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比一般人幸福得多。
随着灾荒岁月的渐行渐远,日子开始晴朗起来。杭州毕竟坐落于江南水乡,北有杭嘉湖平原,南有宁绍平原,自古而来,都是典型的富庶之地,一旦没有了极为罕见的自然灾害,生活便迅速恢复了生机。
余华便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了温暖的人生之旅。
二 举家之迁
余华出生后的第二年,父亲华自治在浙江医科大学学习结束。出于对医学的热爱以及对某种革命理想的强烈追求,华先生毕业之后,自觉地放弃了重返浙江省防疫大队工作的机会,再次选择回到海盐。这次,他调到了海盐县人民医院,并夙愿以偿地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当然,他们的家还是在杭州,余华和哥哥也跟在母亲身边生活。华自治只好像候鸟一样,在交通并不方便的年代里,每月艰辛地往返于杭州和海盐之间。
与杭州相比,海盐的生活当然要贫乏得多。但是,对于一生只想成为一名脚踏实地的医生的华自治来说,这里的事业实在是充满了无与伦比的美妙前景。尤其是作为一名主刀医生,看到一个个病危之躯,在自己的努力下重新焕发出生命的光泽,他更为自己的这份职业而自豪。经过再三权衡之后,华自治觉得,海盐虽小,与素有天堂之誉的杭州自然是无法相提并论,但这里毕竟是自己事业和人生的重要舞台,况且,数年的社教生活,他对这里的山山水水、村村镇镇早已非常熟悉了。
于是,经过一番努力,华自治终于做通了妻子的工作,一家四口便于1962年初从杭州正式迁往海盐。华自治继续在海盐县人民医院做他的主刀医生,而妻子余佩文则成为该院的手术室护士,夫妻二人成了工作中的紧密搭档。对此,余华和哥哥当然都没有多少记忆。只是在多年之后,余华才从他父母的复述中回忆道:当时,父亲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将海盐这个地方花言巧语了一番,于是我母亲放弃了在杭州的生活,带着我哥哥和我来到了海盐。我母亲经常用一句话来概括她初到海盐时的感受,她说: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
在《最初的岁月》中,余华曾这样描述他的童年
我的记忆是从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的海盐开始的,我想起了石板铺成的大街,一条比胡同还要窄的大街,两旁是木头的电线杆,里面发出嗡嗡的声响。我父母所在的医院被一条河隔成了两半,住院部在河的南岸,门诊部和食堂在北岸,一座很窄的木桥将它们连接起来,如果有五六个人同时在上面走,木桥就会摇晃,而且桥面是用木板铺成的,中间有很大的缝隙,我的一只脚掉下去是不会有困难的,下面的河水使我很害怕。到了夏天,我父母的同事经常坐在木桥的栏杆上抽烟闲聊,我看到他们这样自如地坐在粗细不均,而且还时时摇晃的栏杆上,心里觉得他们实在是了不起。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第6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
余华所描述的,便是当时的海盐县县城所在地武原镇。这是一座江南典型的水乡小镇,面积虽然不大,但城内河流纵横,小桥密布,石巷宛转幽深。从地域风情上说,它与当时的杭州差别并不是很大,只是现代生活的气息稍显滞后罢了。
但海盐也有自身的特殊韵味。该县地处浙江省北部富庶的杭嘉湖平原,东濒杭州湾,西南与海宁市毗邻,北与嘉兴秀州区、平湖市接壤。它以平原为主,南部为平原低丘区,西部是平原水网区,水域宽阔;东部属平原海涂区,沿海有明代修筑鱼鳞石塘十余公里,号称海上长城。自古以来,该县便以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化之邦而著称,早在秦代,即因海滨广斥,盐田相望而得名设县,所以生活一直相对安逸富足。早在1959年,中国考古学家就曾在此发现了沈荡彭城桥古遗址,属于典型的马家浜文化;以后又陆续发现魏家村、祝家汇、尚胥庙、低田里、九曲港等遗址,出土文物都保持闽浙越族土著文化特点,充分说明新石器时代中期,先民已在该县境内渔猎耕种。
余华全家举迁海盐,选择这个江南小镇作为生活的依托,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风土人情上,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那个年代普遍存在着物质匮乏的情形,海盐没有一辆自行车,也完全有可能。重要的是,这座江南小城不仅为余华的成长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某种独特而丰沛的文化资源。
多少年之后,余华曾深情地说道:如今虽然我人离开了海盐,但我的写作不会离开那里。我在海盐生活了差不多有三十年,我熟悉那里的一切,在我成长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长,河流的成长。那里的每个角落我都能在脑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语时会脱口而出。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于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第6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我觉得,这句话不仅道出了一个人内心深处无法排遣的文化记忆,也表明了地域文化在作家成长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的精神辐射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