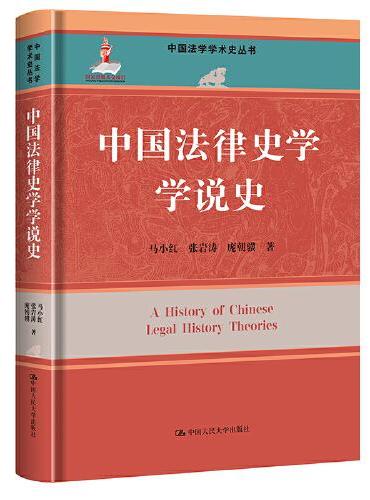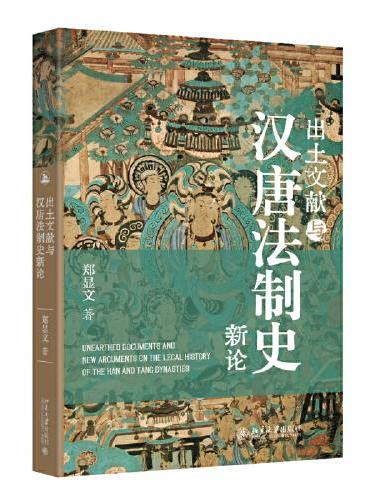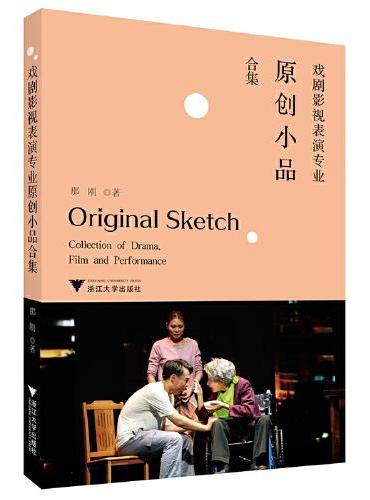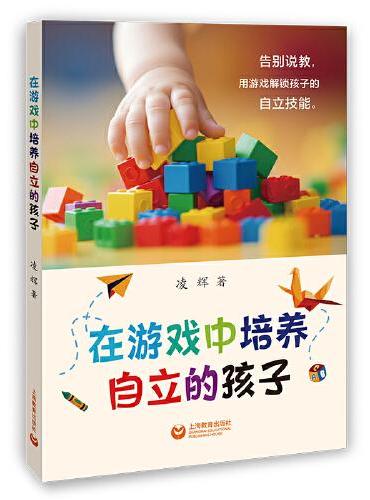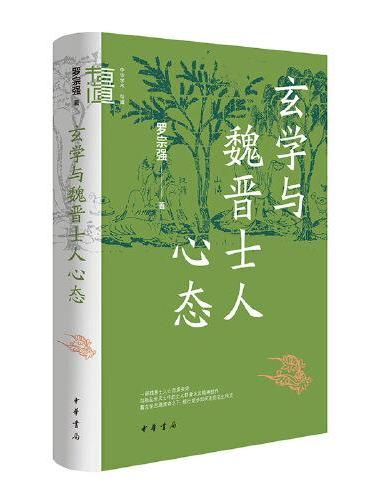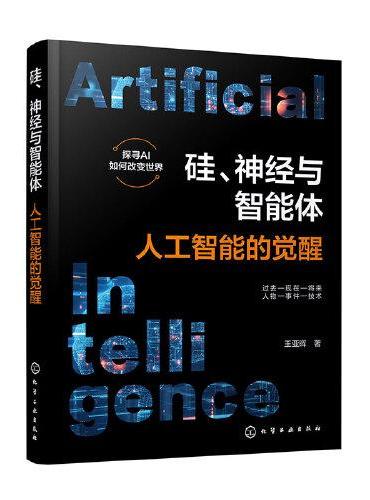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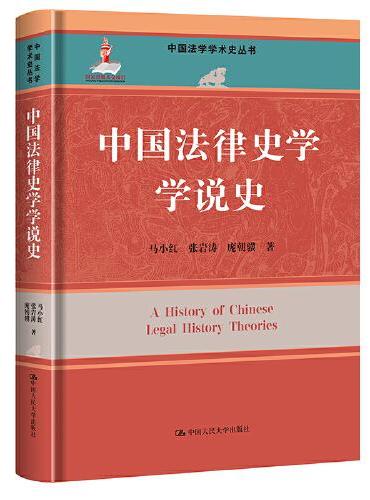
《
中国法律史学学说史(中国法学学术史丛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
售價:NT$
857.0

《
方尖碑(全2册)
》
售價:NT$
4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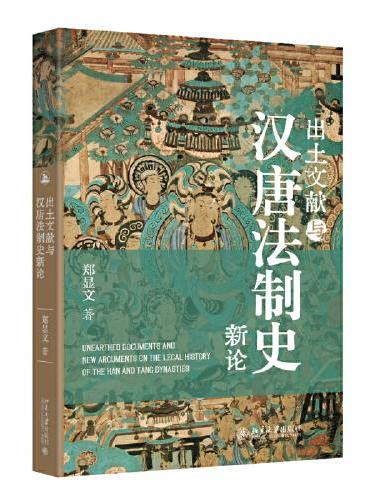
《
出土文献与汉唐法制史新论
》
售價:NT$
398.0

《
最美最美的博物书(全5册)
》
售價:NT$
7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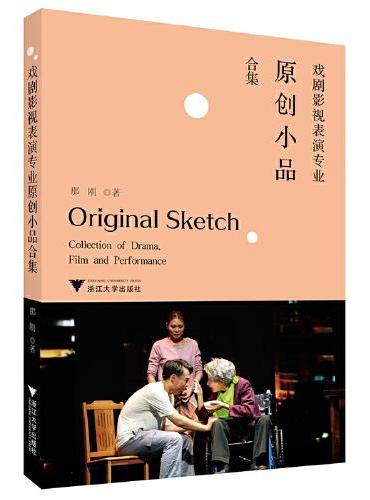
《
戏剧影视表演专业原创小品合集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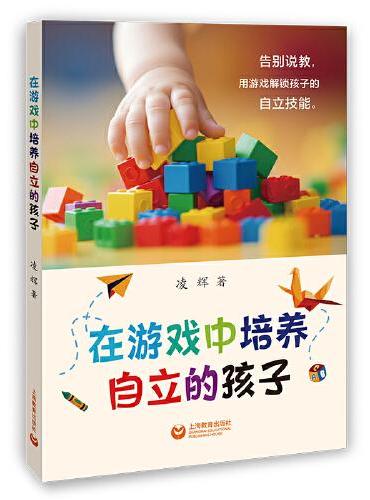
《
在游戏中培养自立的孩子
》
售價:NT$
2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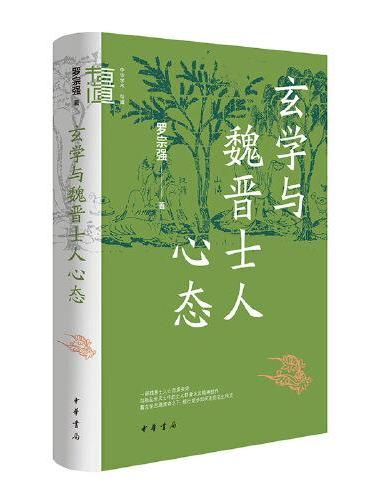
《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精)--中华学术·有道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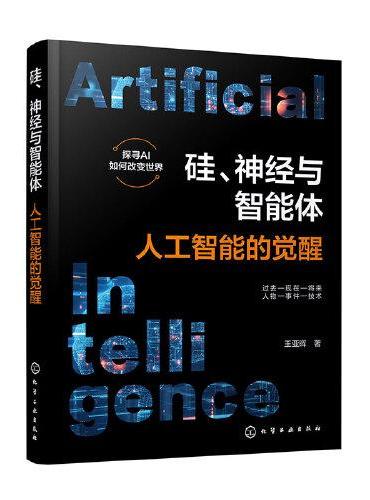
《
硅、神经与智能体:人工智能的觉醒
》
售價:NT$
398.0
|
| 編輯推薦: |
|
对于迷茫的年青人来说,这是一本带来解脱的书。对于空虚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本带来方向的书。对年度散文的梳理,选材广泛,内容充实,将读者带到一个新的高度,是值得收藏的一部好书。
|
| 內容簡介: |
王剑冰、陆春祥、陈世旭、鲍尔吉原野40余位作家的40余篇佳作,或着眼现实,或回眸历史,无论思辨文字,还是抒情篇章,在认识历史和人生、呈现观察与思考的深度和广度等方面,均有直指心灵的力量。
本书由中国散文界选家从全国近百种文学刊物中精心编选,视域广阔,旨在全景呈现2016年度散文的创作实绩,力求公正客观地推选出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作品。
|
| 關於作者: |
|
贾兴安,男,生于六十年代,河北师大中文系毕业,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届高研班学员,河北小说艺委会副主任。现任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邢台市文联主席、《散文百家》主编,曾任河北临城县挂职副县长。
|
| 目錄:
|
在土地上睡着和醒来刘亮程(3)
戈壁任林举(17 )
陕州地坑院王剑冰( 21 )
长江与黄河石厉(24 )
鲁城的城也果(34 )
村庄的脊梁李光彪( 37 )
马武印象刘克邦( 40 )
失落的马家浜玲珑诗芸( 47 )
坐立谁安詹谷丰( 53 )
安眠的思想者马力(72 )
笔记的笔记陆春祥( 76 )
夷门民国书法人物张晓林( 85 )
那所破房与两株枣树
老舍逝世五十年祭孙洁(94 )
淳厚的一切都值得回忆石英(99 )
万寿邮票上的甲午风云乔忠延(104)
祖先的故事聂元松(108)
血芦花吴光辉(111)
方纪回乡尧山壁(118)
杨沫,渐远渐近王宗仁(121)
这个柳庄还在樵夫(126)
城市的性灵陈世旭(135)
没有人在春雨里哭泣鲍尔吉原野(142)
合川的水贾兴安(152)
自然札记惟岗(156)
水下六米的凝望苏沧桑(164)
田野胡慧玲(168)
家居小品凸凹(172)
漫话传播王力平(183)
随笔四题刘益善(189)
文明的困境谢宗玉(195)
乐诽乐祸吴克敬(202)
再说天气陈传席(207)
王三堂随笔王三堂(211)
汉语短制许松涛(219)
找到宁静(外一篇)白天光(226)
拯救与祈祷:穿越天堂等你宋晓杰(230)
故乡的人,他乡的我马语(239)
流落在乡间的人和事崔东汇(251)
母亲的市民之路张暄(257)
向死而生徐海蛟(270)
转身罗张琴(277)
镰刀的虚空石淑芳(283)
陈言新语陈风波(290)
我在洞庭等一片帆张灵均(296)
少居颍州沈俊峰(303)
你是我的亲人焦喜俊(312)
|
| 內容試閱:
|
《夷门民国书法人物》
张晓林
石臣
石臣1821一?,晚号粪叟。有楷书墨迹在开封民间流传。
石臣,夷门书法名家。工行楷,兼擅篆隶。楷书宗法颜真卿,能得《颜勤礼》《自书告身》神韵。
颜真卿是晚唐名臣,八十岁还驰骋疆场,亲到安禄山叛军营帐谈判,谈不拢就大骂叛军,气若长虹。书法一如其人,行书遒劲而具古风,气势磅礴,令宵小之辈不敢近观。石臣身子骨单薄,清癯的脸上生着稀疏的三缕长须,手指竹节一般瘦长,他能得颜书神韵,按传统书如其人的说法,确让人感到有几分不可理解。
石臣是他的名,起初,他没有像其他文人那样,字什么,号什么,他也没有别署。有人很奇怪,问他:上海某书法家给自己起了二百多个号,你怎么不也起上一个呢?石臣笑笑,打趣道:号多了,书法就能写得好吗?但他还是给自己起了一个号:粪叟。怎么起了这样一个号呢?
读书、练书法之余,石臣就到郊外走走,溜达溜达。秋天里,他喜欢到楝树下捡金黄色的楝楝枣,放鼻子下嗅一嗅,然后装进长衫的口袋里。再然后,就忘记了。他老婆洗衣服时,总想不起来去掏一下他长衫的口袋,啪,啪,扬起棒槌,只几下,楝楝枣就面目全非了,黏糊糊的,散发着一股子难闻的气道。妻子就埋怨他,他改不了,下次还照旧。
石臣住的是三间麦秸草房。
石臣的三间草舍很好找,夷门往西走,有一个白水胡同,他的草舍,就坐落在胡同口的拐角处。在开封城,大都是带有脊兽的青色瓦房,像石臣这样的麦秸屋,已是很难见得到了。
为盖这三间茅舍,石臣赶着个毛驴,拉着平头车,往乡间整整跑了一个月,才把屋顶的麦秸拉够了。那些日子,他人更清瘦了,长衫胖了一圈,穿在身上,咣当咣当的,若戏子身上的戏袍一般。
茅屋的前边,是一处院子,不大,有三分多的样子。种着一棵老槐树,是他的父亲种下的?抑或是他的爷爷种下的?已经无可考证了。槐花开的季节,每天早晨,石臣都会到院子里弹琴。
他坐小石凳上,面前是一个青石板桌,琴就放在那上边。这是一把焦尾琴,是开封天籁堂出品,也就是几块钱的样子。石臣竹节一般的手指在琴弦上来回划几下,琴音清越,一纹一纹荡漾开去,唤醒了尚在梦中的蜜蜂,她们嘤嘤着,开始绕着奶白色的槐花起舞。
这时,石臣正弹到入巷处,他半眯了双眼,脸高高地仰起,高高地仰起一只小蜜蜂嘤嘤着,打着旋,停在他的鼻头,他也浑然不知
这是一幅画。
偌大的开封城中,石臣只有一个朋友。那朋友是个糊灯笼的,据说祖上给宋徽宗糊过宫灯,姓李,人们都喊他灯笼李。灯笼李隔三岔五地来茅舍找石臣闲喷,他二人喷得来。
灯笼李给他介绍个徒弟。是开封最大生药铺子同济堂的二掌柜,姓胡,字三丰。胡掌柜拿了两三幅书法习作让石臣点拨,临的是颜真卿楷书《麻姑仙坛记》,已有几分形似。石臣不语,手里拿了把折叠纸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胡掌柜很尴尬,僵笑着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糊灯笼的朋友打圆场,把习作递到石臣手上。石臣接过,顺手就丢进了纸篓,说:废纸!
胡三丰脸上终于挂不住了。霍地扭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糊灯笼的朋友埋怨石臣。石臣说:不是那块料,不如专心做生药生意。很快,秋天到了。槐树上的叶子开始发黄,看上去有几分肃杀。这些日子,石臣的右眼皮总是跳,嘣,嘣嘣,跳得他心里都有焦躁了。糊灯笼的朋友有些日子没有来了。
一个秋雨连绵的黄昏,是那种雨打芭蕉的沙沙细雨,灯笼李来了。
闲话的时候,灯笼李话语有些迟缓,没有先前利索了。石臣不明白怎么回事。灯笼李一年四季总戴着帽子,原因是他的头顶长出一个粉疙瘩,长三寸有奇,没有生一根杂毛,通红崭新,很是饱满。后来,灯笼李脱下帽子挠头,石臣吃惊地发现,那个粉疙瘩不知什么时候瘪了下去,很丑陋地趴在头顶,没有了往日的神采。
石臣忽然把一件事想明白了。他心头咯噔一响,脸上有阴云飘过。
灯笼李这次来,是求他办一件事的。让他给开封驻军的马师长写幅字。这马师长虽说是行伍出身,却狂热地喜爱书法。他换防来到开封,已几乎把开封书法家的作品要遍了。
他以前托人找过石臣几次,都被石臣给拒绝了。
出乎意料,石臣这次答应了。灯笼李悬着的心落地了。石臣写了副对联,押了印,交给了朋友。
过两天,灯笼李又来了,说:这副对联,马师长很满意,只是嫌印文不雅,怎么能印粪叟污纸这样恶俗的内容呢?
石臣叹口气,也不说话,拿过一张宣纸,重新写了。找出原来的印章,在砂石上磨去印文,又刻了一枚印重新盖了。交给那朋友,朋友低头看上半天,也不说话了,阴了脸,告辞。
一天早晨,石臣起床,携琴到院子里弹,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点什么呢?那棵槐树被人锯走了。
槐树被锯走了,春天再来的时候,槐花摇曳,蜜蜂嘤嘤,一清瘦老人在树下弹琴,这幅画,也就消失了。
姜佛情
姜佛情18962001,字无情。擅小楷。晚岁书法作品传世不多。
第四巷是开封上等的窑子铺。每到黄昏,满巷子的窑子铺门口都会挂盏粉红色的灯笼。随着夜色的浓重,时而有灯笼被摘下。这时,就有微风偷偷钻进灯笼里去,蜡烛感到了羞愧和耻辱,有泪垂落。
下雨天气,成群的乌鸦打第四巷的上空飞过。妓女们难得遇见这样的日子,到中午的时候,她们才睡眼惺忪地从床上起来,坐在窗前梳妆,青丝如乌云般飞舞。脂粉掺杂肉欲的气味飘满了整个巷子,墙头的一只黑猫颤抖着胡须打了两个喷嚏,然后迅速地消失在爬墙虎后面。
与第四巷遥遥相望的会馆胡同,虽说也是窑子铺,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胡同里的空气中散发着恶臭,低矮的房屋无论是顶檐或是墙壁,都长满了霉菌一样的苔藓。如果是雨天,房前屋后,院子里,到处都是泥泞,猪屎、狗屎和溏鸡屎搅在其中,有说不出的肮脏。间或有妓女打开柴门出来倒秽物,也都是黄黄的脸孔,头发鸡窝一般杂芜。有的甚至上衣都不穿,乳房松垮地垂在胸前,一副邋里邋遢的模样。
这是下等的窑子铺。
第四巷的妓女们在挥霍凝脂般肉体的时候,会馆胡同已开始向她们招手微笑;进了会馆胡同,再过些年,汴梁门外衰草萋萋的荒野就是她们的归宿了。
来这两个地方的人很杂。去第四巷的,多是官吏、商贾、军阀之流;而进会馆胡同的,自是脚夫、挑担货郎和落荒的土匪之类。但对窑子铺来说,只要腰间有银子,来的都是客。来客挥洒银两,图的是红尘一笑。黑猫白猫,妓女们无权选择,她们忍受卑鄙和脚趾间的污浊,靠银子获得心理上的平衡。这样倒也算尘世间的一种规则。
然而,第四巷里不乏多情的窑姐儿,当春天万物萌发的时候,她们开始抛出注定只会开谎花的绣球。这个绣球,燃烧着危险的火焰,一般都会抛向多才多艺而又风流的公子哥。
第四巷的红妓金缕,就把她的绣球抛给了夷门才子姜佛情。
姜佛情曾跟邵次公学习诗词,颇得几分次公的神韵。书法学钟绍京的《灵飞经》,又参以钟繇《宣示表》笔意,灵动而又厚重,是夷门书法圈被认为能将二钟两种迥异书风融会得了无痕迹的书坛怪才。在一次文人雅聚的时候,金缕对姜佛情一见钟情。
二人很快陷入情网。芙蓉帐里,金缕梨花带雨,颤抖若娇羞的海棠。姜佛情豪气勃发,拔下金缕鬓头的银钗,刺破中指,挤出一滴血在金缕的罗帕上,让金缕收好,说:我要赎你出去,娶你!金缕杏子一般的眼里便朦胧了一梦,梦是金黄色的,有铜锈一样的花边,且有洁白的鸟儿依偎在垂杨柳柔软的枝头。
以后的日子,金缕再不愿意接客。夜阑人静之时,她燃上蜡烛,用清水一遍又一遍地擦拭自己的身体。擦拭过的身体在蜡烛的映照下,宛如阳春三月盛开的桃花。
老鸨开始恶毒地辱骂金缕。金缕用棉絮塞满耳朵,骂声变得渺茫,只看见老鸨的嘴在那儿滑稽地一张一合。金缕无邪地笑了,如玉般的小碎牙把老鸨暗绿色的长脸映衬得更加丑陋。老鸨收了客人的钱,夜半让客人硬闯进金缕的绣楼。金缕刚刚睡下,临睡,她把盛满洗澡水的木盆放在了绣楼的门口。客人拨开房门,一脚踏进去,踩翻了木盆,扑通,摔了一跤,后脑勺磕在门槛上,钻心的疼。客人感到无趣,落荒而逃。
姜佛情赎金缕的念头让父母残酷地捻灭了。他一急,就患上了一种古怪的病。睡到半夜,常常因喘不过气而被憋醒。醒来之后浑身大汗淋漓,他感到了深深的恐惧,恐惧慢慢地侵占了金缕在他心目中的位置。请遍了开封所有的名医,吃了无数剂药,这种古怪的病丝毫不见起色。
家人请来了相国寺静严禅师。号过脉后,静严禅师说:只有遁入空门,其他无路可走。
肃杀的秋风吹落了枝头最后一片树叶,憔悴的金缕叹了一口气。老鸨已经把她的小包裹扔出了窗外,会馆胡同的人在楼下等她多时了。金缕落下两行眼泪,她从贴身的亵衣中取出那枚银钗,用它刺破了自己的咽喉。
瞅着败絮一般的尸体,老鸨伏身上去号啕大哭。然后站起来捏了一把鼻涕,让人抬出西城门外,裹一张苇席,埋在了乱草丛中。
河大诗人叶鼎洛,曾与姜佛情有过一段交往,在姜佛情的寓所见过金缕几面,并暗恋上了金缕。听说金缕葬身荒野,他灌进肚子半瓶汴州醉,扛起一把铁锨,深夜独自一人摸到金缕的葬所,将土掘开,用铁锨砍下金缕的头颅,携到自己的住处,剔除腐肉,用清水洗涤干净,再用红漆漆了,日夜对着鲜红的头颅吟哦,得了佳句,就刻在头颅上,刻满再漆,漆好再刻,时而痛哭,时而大笑。
几个月后,诗人叶鼎洛被学校赶出了校门。他的几个校友把他捆绑起来,送进了疯人院。
叶鼎洛被赶出校门的当天夜里,金缕的头颅被两三条野狗你争我夺地衔去了。河大的老校工瘸腿老高以为那是个宝物,跟在野狗后面一颠一颠地撵有三里地远。
姜佛情做了大相国寺的居士,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焚香诵经,已修得满面红光。念经之余,每天习练书法,他又开始把明朝大才子文徵明的小楷笔意融进他的书法中去,书法大进。
姜佛情活到105岁,忽然去世。去世之日,有一盏粉红色的灯笼在空中闪现。
张铁樵
张贞18831967,字铁樵。民国开封榜书大家。
张铁樵的家就住在铁塔附近。他的祖上是开包子铺的,打出的幌子却是雷婆婆包子店。雷婆婆包子是开封著名小吃,它的渊源可追溯到北宋宣和年间,孟元老著的《东京梦华录》饮食一节中曾经提及。
明明姓张却打人家雷姓的旗号,这里面有着怎样的轶事,到了张铁樵父亲这一辈,已经是无可考据的了。
若按老鼠生来会打洞的老婆儿言去思考,张铁樵应该子承父业,继续卖他的包子,说得好听些,也就是继续做他的包子铺掌柜的。然而,就像端枪打兔子,准星突然跑偏了,结果出现了意外。
张铁樵痴迷上了书法。事情来得很蹊跷,没有半点的可解释性。那天,一个清瘦的道士在雷婆婆包子店门口摆下桌子,铺了宣纸在上面写书法。道士手握如椽巨笔,灰色的道袍在秋风中喇喇作响。巨笔在洁白的宣纸上飘过,一个大大的药字醒目地展现出来。
站在自家的包子店门口,几屉肉包子正待出笼,袅袅的白烟在张铁樵的眼前缭绕。他感到奇怪,他没有闻到诱人的肉香,却闻到了缕缕的药香。那个秋天的下午,道士的跌打膏药卖得非常快,几乎让围拢过来的人群给疯抢去了。
道士收拾摊子的时候,一抬眼看到了魔怔了一般的张铁樵。他招招手,张铁樵走了过去。道士站起身,在他的头顶轻轻拍了两下,暧昧地笑笑,然后把褡裢搭在驴背上,飘然而去。
张铁樵的学书经历充满坎坷。他父亲对他说:练什么书法,顶吃还是顶喝,我不练书法,只卖包子,不照样过得很好?张铁樵是个沉默寡言的孩子,他不说话,只拿眼睛默默地看着鬓发斑白的父亲。
父亲立即暴跳如雷,将张铁樵狠很揍了一顿。挨打后他一言不语,连着三天坐在家门口的池塘边发愣,看着两只黑蜻蜓围着一朵粉红色的荷花调情,然后落落停在了花蕊上,花蕊立即颤悠悠兴奋起来。
母亲害怕了,和父亲狠狠哭闹一顿。父亲再不管他练书法一事。张铁樵在心底一叹,自己对自己说:我坐在池塘边,是在想怎么像王羲之那样把池水给练黑了。
张铁樵在书法上有着超人的天赋。他的书法端庄而浑厚,颇有颜真卿的遗风。短短几年里,开封街头的匾额大都换成了他的墨宝。之所以他的书法会迅速风靡古城,除了书法本身以外,再就是他这个人不拿架子,不耍大腕,好说话。他也没有什么润格之类,你只要求到了他的门下,他都会尽最大努力让你满意。有一个阿九婆,在开封街头卖扇子。她是从扇庄批来,然后?着篮子大街小巷去卖,生意不好。她的儿子被抓了壮丁,儿媳妇跟着一个小银匠私奔了,撇下两个小孙子。她们三口人,就靠她卖扇来糊口了。
哪天扇子卖不出去了,她和两个孙子就一起饿肚子。阿九婆脸上的皱纹,很少有舒展的日子。张铁樵找到她的门上,把写好字的二十把扇子递到她手上,说:去卖吧,卖完了就去找我。等下次阿九婆来找张铁樵的时候,她脸上的皱纹一缕一缕地都舒展开了。
汴古阁的马老板让人送来请柬,请张铁樵去第一楼喝茶。汴古阁是开封唯一做书画生意的商铺,它的店主马老板曾跟大军阀孙殿英挖过东陵,后来解甲归里,就来开封城开了这样一个店铺。马老板虽说人生得粗糙些,但见人都是三分的笑颜,然而,那笑却让人感到浑身的不自在。
第一楼喝茶回来,张铁樵几天都很少说话,他的脸色很难看。
日子依旧如往常那样,一天一天地过去,张铁樵书法的名头在开封城越来越响亮。省里的要员已开始把他的书法往京城里送了。据说,京城四大公子之一的袁寒云私下也曾打探过张铁樵的名字。
秋天到来了。一个阴雨连绵的黄昏,张铁樵结束了一个应酬往家走。眼看走到家门口时,从暗处蹿出两条大汉,劈头盖脸一顿拳打脚踢。张铁樵还没有反应过来,嘴就被人堵上了。黑暗中听一个人说:把右手的手指头拧折,中指剁掉!张铁樵忽然感到一阵钻心般的疼痛,接着他就昏了过去。
不久,开封街头就有了传言,说张铁樵的右手被人打残了,怕从此再也不能写字。有人甚至愤恨地骂道:他会写字吗?傻大黑粗,一点笔法都没有!阿九婆听到这个消息时,昏花的眼里落下两行浑浊的泪水。
那个时候,张铁樵正躺在医院里,他的左手打着绷带,右手和前来探望者一一握手。
张乐天
张受祜18821974,字乐天,号乐道人,云烟山馆主,听香馆馆主。书法擅甲骨、金文、石鼓、小篆、隶书。精于篆刻。
张乐天是土生土长的开封人。在夷门,他也算得上是出身书香世家了。他的爷爷是清朝的举人,父亲张梦公是清朝的贡生。张梦公在大相国寺旁边设馆课徒,教出了晚清末科亚魁李秋川等一干才俊。
贫寒的家境使张乐天自幼饱受生活艰辛的熬煎。他兄妹八人,油盐酱醋、吃喝穿戴,全靠父亲那张嘴巴不停地吧嗒吧嗒着支撑。科举废除,学馆关门,16岁的张乐天辍学了。不久,入开封石印馆做了学徒。干了两年,升为石印馆缮写,这个时候,他父亲的一个学生拉了他一把,把他保送进了河南简易师范学堂读书。毕业后,直接进了河南省政府做了职员。
命运刚有转机,他就和父亲的那个学生闹翻了。事情的起因其实很简单,那个学生听说他爷爷有一本诗词手稿《藏剑集》,要他拿来一看。看后,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以那个学生的名义刊印发行,发行所得全归张乐天,他分文不取。张乐天听过这个建议后满脸涨得通红,一把抓起那本手稿头也不回地走了。父亲的学生愣在那里,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
这一时期,张乐天练习书法达到痴迷程度,坐在办公桌前常常用指头蘸水背临篆书《石鼓文》。那个学生站在阴暗处,看着张乐天冷冷而笑。1934年的春天姗姗来迟,河南省政府在开封举办河南现代书画展览会的消息却早早地发布了出来。张乐天异常兴奋,他整个心思几乎都用在了备战展览作品的创作上了。这次展览,张乐天共有山水画4件、花鸟画3件、大篆1件、行书2件入展。展览刚一结束,父亲的学生就把他叫了过去,摇晃着手里的几页纸说:检举你的!以耽于书法影响公务为由解雇了他。看着张乐天离去的背影,父亲的学生淡淡地说:我可以给你个饭碗,同样也可以给你砸碎!
迈出省政府的大门,张乐天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卖画!他是艺术领域的一个通才,于书法,真草隶篆行,都有着很深的造诣;于绘画,山水、花鸟皆精,人物也能来几笔。这次全省的书法大展说明了这一点。早些时候,张乐天在篆刻上也曾下过苦功夫。他的篆刻,上溯秦玺汉印,下涉明清诸家。尤其对吴让之用功犹勤,颇有心得。若干年后,我在京古斋曾见到他用青田紫檀石刻的朱文焦氏应庚之印,与吴的朱文印几可乱真。1937年西泠篆刻名家方介堪陪同他的老师丁辅之游历到开封,对张乐天的篆刻一见钟情,便请张乐天治名章方岩一枚。方介堪原名文渠,后改名岩,字介堪,以字行,其名倒几乎被人忘却。印刻好,丁、方二人大为赞誉,由方介堪出面在开封又一新饭店宴请张乐天作为答谢,丁辅之出席了这次宴会。
丁辅之给张乐天留下一封信函,让他持函去上海拜访书坛泰斗吴昌硕,或许对他的篆书和篆刻都不无裨益。秋风乍起的季节,张乐天拎着两只寺门老白家的桶子鸡坐上了东去的列车。到了上海,由于秋老虎肆虐,那两只桶子鸡已经有了异味。在一家小客栈里,张乐天就着白开水吃完了那两只鸡,连夜坐火车又回到了开封。这一次,虽说没见到吴昌硕,他却用身上全部剩余的钱买了一本新刊印的《吴昌硕临石鼓文》法帖回来。坐在大坑沿自己的家中,开始揣摩起这本从上海买回来的法帖。一天深夜,他对着这本法帖忽然狂笑不止,黎明的时候才趴在书案的一角睡去。《河南近代书法概览》一书对张乐天之后的篆书评价说:大字石鼓左右参差取势,简穆高运,苍润不俗,酷似枯树春深著花。也有评论家站出来,拿他的石鼓篆书和吴昌硕做了比较:吴书拙中有巧,而张书巧中带拙。于吴昌硕之外,可谓另辟蹊径。
张乐天曾写过一篇《自叙》的文章,透露了他从艺的大致途径。他说:吾诗、书为先父家传,画学乃生性所近。诗歌一技,是那个时期文人的童子功,自小必须修炼的。张乐天的诗歌,不见结集传世,今天已很难窥其全貌了。他曾与夷门名士关百益、许钧,相国寺净尘大法师等结艺林雅集社,但也没有发现他们之间有什么诗词唱和之作。张乐天的诗歌,今天能见到的,只有寥寥几首题画诗了。譬如《题秋林读书》:秋高红树老,日冷青松秀。《题深山古寺》:巍巍千古寺,数里入云峰。皆有唐人风韵,深得王摩诘神髓。
一年后,张乐天退出艺林雅集社。因为他深切地认识到,诗歌不能当饭吃,他得靠卖画来养家糊口。起初,他的画风走的是黄子久一路,作画时用笔很大胆,把浓墨用到了极致,这些画画出了他对自然物象的认知和感受。然而,画挂到京古斋等字画店里,过一阵子去看,还依然纹丝不动地挂在那儿。他很是困惑。净尘大师对他说:要为艺术,你为自己画;要为生计,得为世俗画。张乐天如醍醐灌顶,改学王蒙、王石谷诸人,画风为之一变。
此后的十年间,张乐天的画风靡汴上。他画室的门口,常有数家字画店的伙计等候。为争到他的画,字画店之间常常哄抬画价。博雅轩和古天阁的伙计为争夺他的画曾大打出手,为此瘦弱的博雅轩伙计被对方一拳打落了两颗焦黄的门牙。解放后,开封市政协工作人员和他闲聊时,他无限怀恋地说:当年我凭着一支笔,挣下了9处院落,上百亩的良田!但是,他避而不谈的是,他的院落和良田后来都被分给了翻身得解放的劳苦贫民,他还被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受尽苦头。
晚年,张乐天在开封书店街景古山房门前摆了一个小摊儿,清瘦的身躯穿着一件满是补丁的长衫,已看不清是什么颜色的了。小摊上胡乱摆放一些廉价的青田石和他自己画的书签、折子之类。画的内容很单一,淡墨画个山头,在远处勾几只飞鸟,然后题上望断南飞雁字样。这些物什都很便宜,大都是几分钱一个。然而,却极少有顾客来到他的摊前。
除非下雨,他每天清早出摊,黄昏收摊,颤抖着花白的胡子,孤苦伶仃的,在摊前一坐就是一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