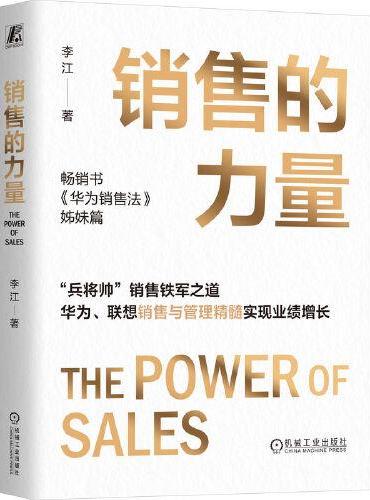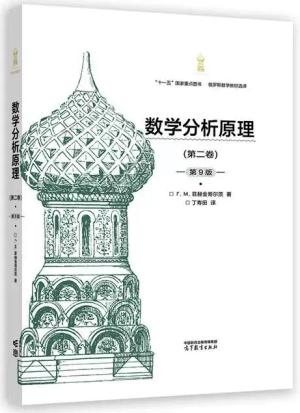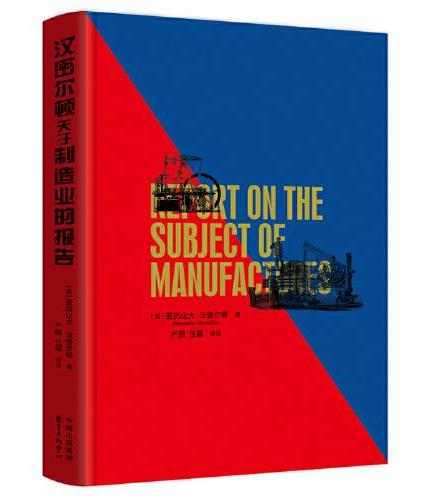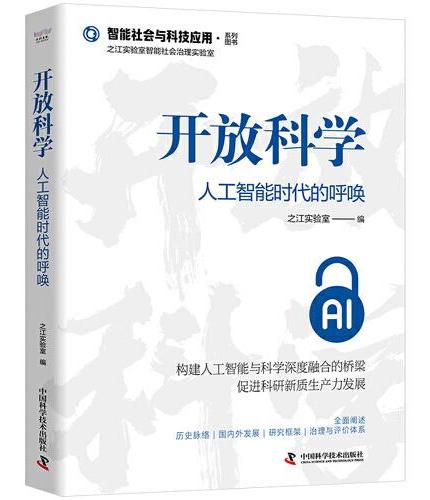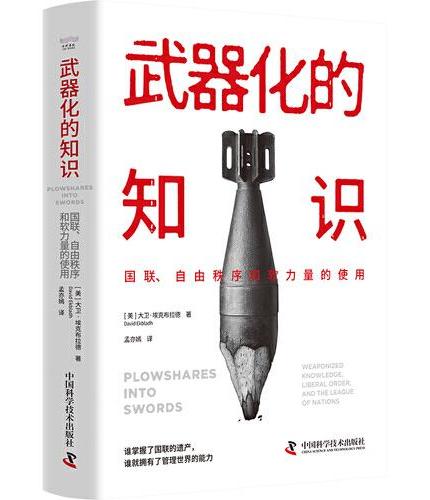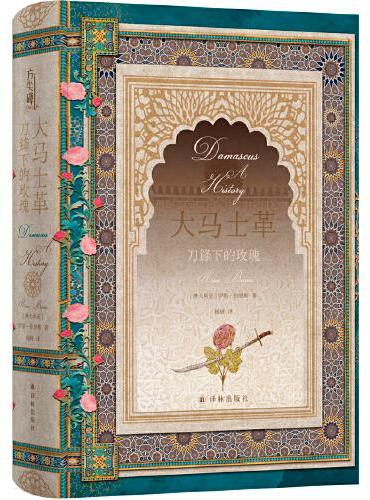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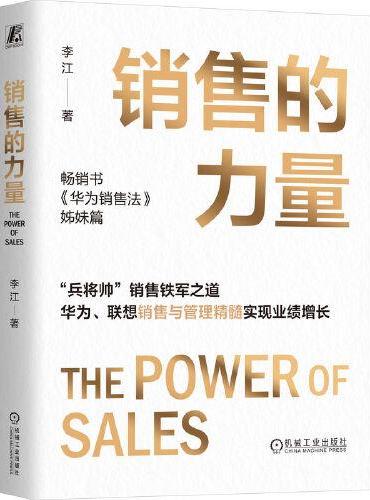
《
销售的力量
》
售價:NT$
454.0

《
我活下来了(直木奖作者西加奈子,纪实性长篇散文佳作 上市不到一年,日本畅销二十九万册)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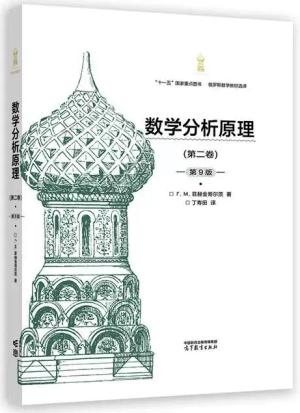
《
数学分析原理(第二卷)(第9版)
》
售價:NT$
403.0

《
陈寅恪四书
》
售價:NT$
146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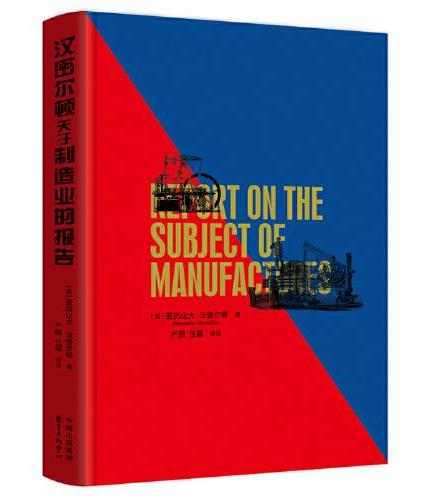
《
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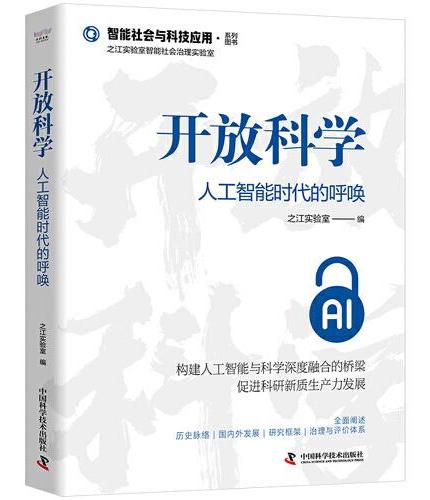
《
开放科学:人工智能时代的呼唤
》
售價:NT$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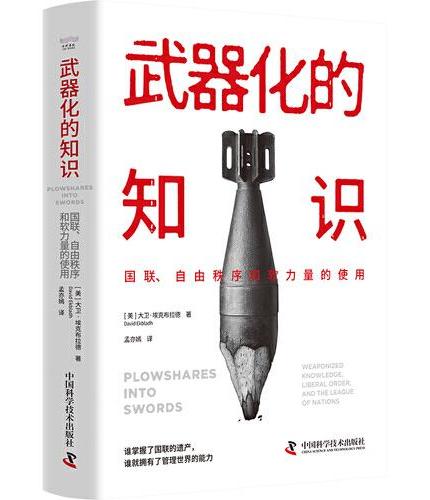
《
武器化的知识:国联、自由秩序和软力量的使用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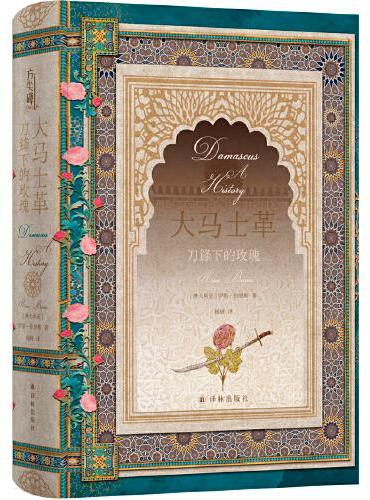
《
大马士革:刀锋下的玫瑰(方尖碑)
》
售價:NT$
607.0
|
| 編輯推薦: |
1.独特荒诞的悬疑视角
作者很会讲故事,在悬疑的基础上,增加了浓厚的恐怖感,文风类似周德东,能以诡异的文字将读者迅速带入小说场景,让人身临其境。作者还加入了很多幽默元素,深深的恐惧,不经意的幽默,构成了本书的特点。
2.立意深刻,启发性强
作者的故事大多都是从平民大众入手,对生活细节观察到位,各个阶层的人的生存状态也分析入微,读起来很有代入感。每一个故事都讽刺了人性的贪婪,使人向善。
3.破解恐怖的玄机
每个人都有自己害怕的东西,故事一波三折,构思巧妙,首尾呼应,结局十分出人意料。作者用别人的经历讲述了他们所担心、害怕的事情,而故事的*后,破解恐惧的根源,只能靠你自己。
|
| 內容簡介: |
这是一部中短篇悬疑恐怖故事集,书名取自《山海经》,夜啼是一种中医病名,婴儿白天能安静入睡,入夜则啼哭不安,称为夜啼。在本书中可以理解为一种人与生俱来的恐惧。
本书每篇都是一个单独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大多都是普通大众,几乎每篇故事都刻画讽刺了人性的劣根,对人们所担心、害怕、渴望的东西提炼为故事的元素。
|
| 關於作者: |
|
支离婴勺,女,医学院教师。其文字里渗透的诡异和恐怖扣人心弦,让人身临其境。作品在网上一经发表,即引发追捧。 原创微信公众号:婴勺夜啼
|
| 目錄:
|
前 言 001
一条金鱼的爱情 002
捞尸人 035
八万055
剁椒鱼头079
隔壁老王108
摸出来的祸事130
毛氏红烧肉 162
红嫁衣 177
|
| 內容試閱:
|
一条金鱼的爱情
那是一条极其珍贵的金鱼,那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古董,那是三个让人想入非非的女人,面对这一切,他该如何取舍?
1.木勺镇
讲一个爱情故事。
确切地说,是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爱情故事,对了,还有一条金鱼。
有点乱。
没关系,会讲明白的,请相信我。
这个故事有点长,看完大概需要一顿饭的时间,前提是你得细嚼慢咽,而且饭量不能太小,至少也要比一条金鱼吃得多。
爱情故事就应该长一点,三言两语就能说完的那不是爱情,是一夜情。
故事发生在木勺镇。
那里有一条老街,两边有许多上百年的老房子,黑瓦白墙,雕梁画栋,笨重的木门,看起来颇有古味。
木勺镇北边有一条河,河水清澈见底。这么好的河水不能让它闲着,有人就把河水引到自家院子里,养起了金鱼。闲着没事的时候,端着一杯茶,看着金鱼在水池里慢慢地游动,挺好。慢慢地,大家都跟着养上了。
木勺镇的人很懒散,喜欢鼓捣一些有趣的玩意儿,除了养金鱼,还有人玩蛐蛐、唱京剧、遛鸟、养狗、收藏核桃、逮兔子,还有人熬鹰。在木勺镇,没有钱不会遭人耻笑,如果没有兴趣,那就没有伙伴了。
木勺镇人的言行举止和他们的房子一样,属于一个逝去的朝代。
五花毕业之后,没找到工作,经一个亲戚介绍,到木勺镇一家旅馆上班。据说,那是当地最大的旅馆。下了火车,又坐中巴车,终于到了木勺镇。
太阳已经落山了,光线暗淡,木勺镇有些不太真实。
远处传来一阵突突突突的声音,像是拖拉机。很快,一辆古怪的摩托车拐个弯,驶到了五花面前。那是一辆老式的摩托车,军绿色的,有一个挎斗。骑摩托车的是一个干瘦的男人,三十岁左右,头发挺长,眼神有些阴冷。
坐车吗?他开口了,口音很重,怪腔怪调的。
五花问:去这里最大的旅馆,多少钱?
五块钱。
五花上了摩托车。
老天一下就黑了,似乎是在预示着什么。
也许是因为到了吃晚饭的时间,街上没有人。石板路弯弯曲曲,似乎没有尽头。路两边的人家都拉上了窗帘,那窗帘大部分都是黑色的,十分古怪。
远处,群山静静地伏在那里,轮廓像一个身材走形的女人。
几分钟以后,摩托车停下了。
五花下车,付了钱。
眼前是一个孤零零的院子,不大。它依山而建,后面是深不可测的松树林。大门口挂着一个红灯笼,仿佛某种史前怪物的眼珠子。有风,灯笼左右摇摆,有一种恐怖电影的氛围。
大门敞开着,里面亮着灯。
五花走了进去。
院子里有一栋三层小楼,有些老旧,四四方方的,很呆板。楼底下种了几棵爬山虎,张牙舞爪地生长着,把小楼完全包裹了起来,显得有几分阴森。小楼门口也挂着两个红灯笼,其中一个灯笼里面的灯泡坏了。
旁边竖着一块招牌,上面有五个红色的黑体字:最大的旅馆。
五花这才知道,最大的这三个字只是这家旅馆的名字,并不是一个形容词。
这个名字有点意思。
他走进了小楼。
进了门,是一个厅堂,摆着两张厚重的木桌,围着几把木头椅子。厅堂的角落里藏着一间小屋子,有一扇很小很小的窗户,里面有昏黄的灯光。窗户上方,挂着一块长方形木牌,上面用红油漆写了三个字:登记室。
五花走过去,透过窗户往里看。靠近窗户的地方放着一张长条桌,上面有一个落满灰尘的显示器,还有几本登记簿。一个男人趴在长条桌上睡觉,他的头发灰白,稀稀拉拉的。他的身后有一个货架,上面摆着一些日用品和吃食。角落里有一个鱼缸,个头挺大,里面似乎有一条金鱼,因为角度的问题,看不真切。
五花敲了敲窗户。
那个男人一下抬起了头。他五十岁左右,是个麻子,脸上坑坑洼洼的,像是被风雨剥蚀了万年的花岗岩。他把窗户拉开一条缝,问:你干什么?
我是五花,我表叔介绍我来的。
他想了一下,似乎想起来了,说:你来得挺快,进来吧。
五花转到门口,伸手推了推门,没推开,就站在原地等待。过了片刻,他听见里面有拉开门闩的声音: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
这扇铁门有七道门闩。
厚重的铁门缓缓地打开了,他把五花拉进去,迅速关上门,又插上了门闩: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
他把七道门闩全插上了。
这间小屋子里空气不流通,有一股发霉的气味,还有一股淡淡的腥味。五花瞥了一眼鱼缸,一条怪模怪样的金鱼一动不动地浮在水面上。
我看一下你的身份证。他说。
五花翻出身份证,递给他。他看了半天,又对着灯光检查了一阵子,这才把身份证还给五花,说:以后,你就叫我表舅。
表舅。五花叫了一声。
他没答应,自顾自地说:你值夜班。
行。
今天晚上就上班,没问题吧?
没问题。
有人住宿,你就给他登记。除了上厕所,不要轻易离开登记室。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把门锁好。说完,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递给了五花。
那是一把黄铜钥匙,看上去有年头了。
知道了。五花接过了钥匙。
客房的钥匙在抽屉里,上面都有编号。
知道了。五花走到鱼缸旁边,低头看了一眼,问:表舅,这是什么金鱼?
不知道,河里抓的。表舅说。
河里还有金鱼?
多得是。木勺镇有很多人养金鱼,河里的金鱼想抓就抓,没人管。
这鱼缸挺好看。五花蹲了下来。
那是一口青花大缸,胎体厚重,造型简洁丰满,通体绘有龙纹,衬以祥云海水,花纹繁而不乱,层次清晰,营造出一种华丽而热闹的气势。
你表舅妈以前一直用它腌咸菜。
她不在家?
表舅考虑了半天,突然说:你表舅妈死了,这个鱼缸是死人的物件。
五花一怔:怎么回事儿?
表舅低头看着自己的脚丫子,长叹一口气,半天才说:说实话,我真不愿意再提起这件事儿
下面是他给五花讲的故事。
三十年前,表舅还很年轻。那一年,他结婚了,妻子是邻镇的曹凤梅。曹凤梅家很穷,她唯一的嫁妆就是那个鱼缸。鱼缸在她家很多年了,一直当咸菜坛子用。
结婚后,曹凤梅还用它腌咸菜,腌了二十年。后来,生活条件好了,不用每天都吃咸菜了,曹凤梅就打算把它洗刷干净,养金鱼。
当时,木勺镇流行养金鱼。
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太阳红红的。
曹凤梅抱着它去了河边,再没回来。
那一年夏天,老是下雨,河水变得又深又急。很多天以后,有人在下游的浅滩上发现了曹凤梅,她身上的肉被鱼啃掉了一半,还死死地抱着那个鱼缸。
鱼缸在河水里泡了那么多天,终于洗刷干净了,鲜亮如新。
表舅把她埋了,把鱼缸抱回了家。
故事讲完了。
五花哀叹不已。
表舅慢吞吞地说:我找人给看过了,这个鱼缸是不祥之物,上面有戾气,不能碰,谁碰谁死。
五花一下子站了起来,问:怎么不扔掉它?
你表舅妈就留下这么一个物件。
五花看见长条桌上的显示器开着,里面是监控画面,二楼和三楼的走廊里空无一人,还能看见大门口和院子里的情景。五花问:如果有人住宿,收多少钱?
住一天三百八十块钱,不讲价。
这么贵?
表舅没回答,转而说:我去给你弄点东西吃,你把门闩插上。说完,他转身出去了。他的脚步很轻,无声无息。
五花嫌麻烦,只插了两道门闩。他伸了一个懒腰,仔细地打量着四周。这里很简陋,与他想象中的木勺镇最大的旅馆完全对不上号。不过,他并不沮丧,因为他知道,找到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是实现理想的第一步。
五花的理想是开一家面馆。
无意间,五花瞥到了鱼缸里的金鱼,发现它正在看着他。他悄悄地走过去,观察它。它长得很古怪,身体是黑色的,尾巴奇大,脑袋呈深红色,长有肉瘤,从头顶一直向下延伸到下颚,眼睛、鼻子和嘴是黑色的,从正面看,很像是小孩儿的脸。
五花分不出它是雌是雄,直觉告诉他,它是异性。
他伸出手,想碰碰它。它敏感地往左边躲了躲,还是定定地看着他。他又伸了伸手,这一次,它干脆沉到了水底,把眼珠子翻上来,定定地看着他。
看了一阵子,五花觉得没什么意思,就走开了。
金鱼在鱼缸里扑腾了两下,不知道在鼓捣什么,那声音很像是一个人在打嗝儿。
五花有些好奇,又过去看它。
它低着脑袋,静静地趴在缸底,表情不详。在五花的印象里,金鱼总是游来游去,一刻也不消停。可是,它却十分深沉,似乎有极重的心事。
五花忽然觉得它有些恐怖。
有人敲门。
五花走过去,拉开门闩,看见表舅端着一个托盘站在门外,托盘上有一盘青菜、一碗米饭。表舅走进来,说:开门之前,记得问一声,不要给陌生人开门。还有,你怎么没把门闩全插上?他的语气有些严厉。
我忘了。五花低声说。
表舅压低了声音说:最近,木勺镇来了一个变态狂,天黑就出来,手里拿着一块砖,见人就砸,已经砸伤好几个人了。
五花吃了一惊。
表舅又说:那个变态狂像飞蛾一样,喜欢光。
五花想:怪不得那么多人家的窗帘都是黑色的,原来是怕变态狂找上门。
表舅凑到他耳边,用一种很阴冷的语调说:记住,千万不要给陌生人开门,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变态狂,不管他衣冠楚楚,还是邋里邋遢。
五花抖了一下。
表舅把托盘放到长条桌上,说:你吃饭吧,我走了。
五花凑了过去。
不用老是盯着外面,困了就趴在桌子上睡觉。记住,把门闩全部插上,千万不要给陌生人开门。表舅又叮嘱了一遍,走了。
这一次,五花很听话,把门闩全部插上了。
夜一点点深了。
五花无聊地翻看着登记簿,发现上面一个汉字都没有,只有性别、日期和一串身份证号码。今天晚上,这里住了三个客人,都是女人,都很年轻。
明天,肯定能见到三个美女,五花想。
怀揣着这个美丽的预言,他趴在长条桌上,睡着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