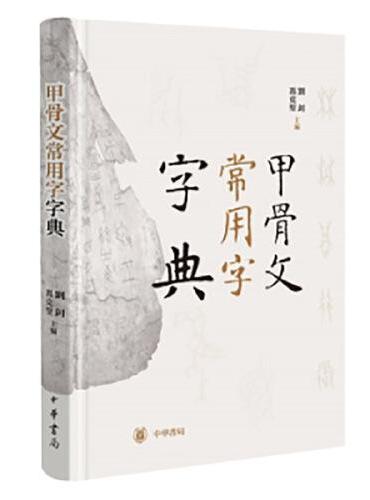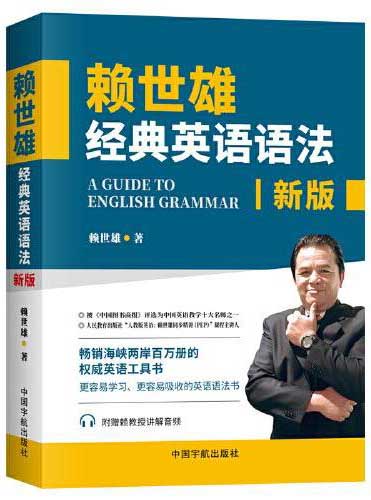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没有明天的我们,在昨天相恋
》 售價:NT$
218.0
《
流动的白银(一部由白银打开的人类文明发展史)
》 售價:NT$
296.0
《
饮食的谬误:别让那些流行饮食法害了你
》 售價:NT$
296.0
《
三千年系列:文治三千年+武治三千年+兵器三千年
》 售價:NT$
915.0
《
甲骨文常用字字典(精) 新版
》 售價:NT$
347.0
《
赖世雄经典英语语法:2025全新修订版(赖老师经典外语教材,老版《赖氏经典英语语法》超32000条读者好评!)
》 售價:NT$
305.0
《
影神图 精装版
》 售價:NT$
653.0
《
不止于判断:判断与决策学的发展史、方法学及判断理论
》 售價:NT$
347.0
編輯推薦:
《醒来的女性》是一部反映了整整一代美国女性生存境遇,令每一位普通女性心生共鸣,潸然泪下抑或热血沸腾的小说。出版以来全球销量超过2000万册,出版22种语言版本,堪称小说版的《第二性》,甚至间接推动了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无数女性认为这本书写出了她们一直被压抑的内心世界,甚至改变了她们的一生。
內容簡介:
我们来认识一下米拉。
關於作者:
玛丽莲弗伦奇(Marilyn
內容試閱
【瓦尔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