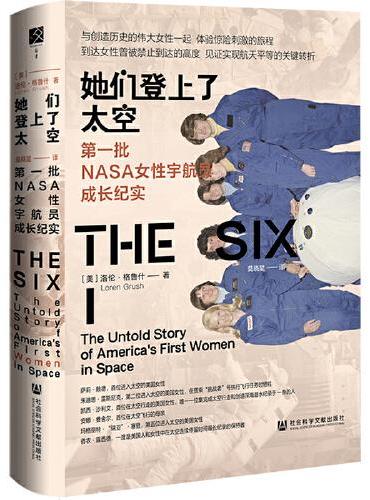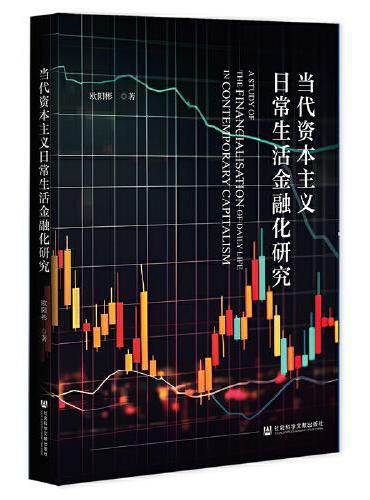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倾盖如故:人物研究视角下的近世东亚海域史
》
售價:NT$
357.0

《
史学视角下的跨文化研究(一): 追踪谱系、轨迹与多样性
》
售價:NT$
485.0

《
历史文本的文化间交织:中国上古历史及其欧洲书写(论衡系列)
》
售價:NT$
551.0

《
1688:第一次现代革命(革命不是新制度推翻旧制度,而是两条现代化道路的殊死斗争!屡获大奖,了解光荣革命可以只看这一本)
》
售價:NT$
1010.0

《
东方小熊日本幼儿园思维训练 听力专注力(4册)
》
售價:NT$
408.0

《
粤港澳大湾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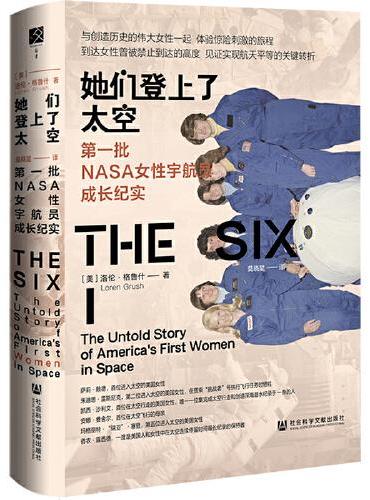
《
她们登上了太空:第一批NASA女性宇航员成长纪实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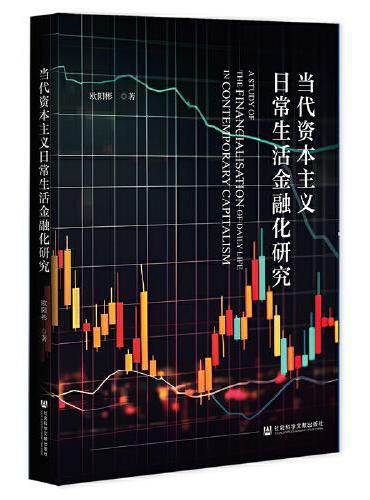
《
当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金融化研究
》
售價:NT$
653.0
|
| 編輯推薦: |
这是一本伟大而正经的小说,紧握时代情绪的文学经典。就连冯内古特自己都将这本书评价为A;
冯内古特是一位与马克?吐温、约瑟夫?海勒齐名的美国黑色幽默作家。是美国20世纪文坛zui重要的作者之一。
《囚鸟》作为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代表作,被认为是“美国后现代文学的里程碑”。
作品被翻译成15种语言,热卖30多个国家。
《1984》和《动物农场》的引进者、国内知名权威译者董乐山经典译作。
新增关于美国历史、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背景知识脚注。
我们都是受困于时代的“囚鸟”——既想要逃离,又踟蹰不前。在命运这个庞大的转轮里,倘若我们想要获得终极救赎,至少应当先学会心平气和。
这个世界欠冯内古特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
| 內容簡介: |
与《1984》、《第二十二条军规》齐名的伟大小说
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里程碑——库尔特?冯内古特经典代表作!多丽丝?莱辛、诺曼?梅勒等国际文豪鼎力推荐! 我们都是受困于时代的“囚鸟”:既渴望逃离,又踟蹰不前。联邦zui低限度安保措施成人改造所里,颓唐的小老头儿瓦尔特·斯代布克正在等待领他出狱的狱卒。
在他过去的人生中,他曾是斯拉夫移民的儿子,哈佛大学毕业生,前共产党党员,前联邦政府官员,“水门事件”的涉案者……
不久他还将获得一个新的身份,神秘的……
名人推荐:
“他是独特的……他属于这样一种作家,他们为我们画出了我们的风景地图,他们为我们zui了解的地点命名。” —— [英]多丽丝?莱辛
“冯内古特是几代美国青年的偶像,是我们自己的马克·吐温。”—— [美]诺曼·梅勒
“冯内古特本该极为搞笑,却总有几分反讽浸透纸背,从而成就其不凡。”—— [美]托马斯·沃尔夫
“冯古内特是当今美国zui有才能的作家。”—— [英]格雷厄姆·格林
媒体推荐:
“(《囚鸟》是我们时代的)摩西十诫。”—— 《纽约书评》
“《囚鸟》中有我们这个时代所需的所有精神食粮。”——《洛杉矶时报》
|
| 關於作者: |
作者
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1922—2007),美国黑色幽默作家,美国黑色幽默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囚鸟》《五号屠宰场》《没有国家的人》。他的作品以喜剧形式表现悲剧内容,在灾难、荒诞、绝望面前发出笑声。这种“黑色幽默”风格始终是冯内古特小说创作的重要特质。2007年4月11日,于曼哈顿因病逝世。
译者
董乐山,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长期从事新闻、翻译、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笔会中心会员、中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三S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译作有《第三帝国的兴亡》《西行漫记》《美国梦》《囚鸟》《一九八四》等,并编有《美国社会知识辞典》,以及论述翻译的著作《译余废墨》。他创作的小说《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曾译载于美国著名文艺刊物《巴黎评论》。
|
| 目錄:
|
冯内古特和他的《囚鸟》
序幕
囚鸟(1-23章)
尾声
|
| 內容試閱:
|
序言
冯内古特的作品介绍到国内来,《囚鸟》已不是第一部了。但是对冯内古特作品的分析,似乎还莫衷一是。
有人说他是科幻作家,有人说他是黑色幽默作家。读了《囚鸟》以后,我想中国读者不难自己得出结论来。他既不是科幻作家,也不是黑色幽默作家。
不错,冯内古特利用过科幻小说这一文学体裁。但是不论从他的初作《自动钢琴》,还是已译成中文的《猫的摇篮》都可以看出,他写科幻小说,不是为科学而幻想,而是有他更深刻的用意:借科幻以讽今。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写文章总是得有个借题发挥的因头。”同样,他的有些作品看似游戏笔墨,可以归为黑色幽默,但是亦岂仅幽默而已!
其实,一个作家用什么形式来表达他的思想是次要的,重要的事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思想。这当然并不是说形式在文艺创作中不重要,他还是很重要的。但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也是为内容所决定的。对形式的选择和追求,都是为了最好地表达内容。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必因为冯内古特究竟是科幻作家还是黑色幽默作家而争论不休了,也没有必要在文学争论中把作家贴标签分类了。文学评论家毕竟不是图书馆学家。如果要分类的话,唯一的类别恐怕是,某个作家是严肃作家,还是流行作家。但是有的时候,甚至严肃作家也写流行作品,流行作家也有严肃的主题。
但是文艺评论似乎脱不了贴标签的痼习,什么浪漫主义,什么现实主义,名目不可谓不多,但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就不得而知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对人类的贡献和由此而发出的光芒,并不因后人给他们贴什么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标签而有所增减。相反,在百年千年之后,他们的作品仍像丰碑一样屹立,而标签却没有不因风雨的侵蚀而剥落的。因此,文艺评论家最好还是多谈谈作品的本身,它的形式与内容,比较近似地探索了一下作者的用意,而不是简单地贴些标签。
我用“比较近似”一词,是因为我不相信文艺评论家有这么大的能耐,可以自称能够完全正确地理解作家写某一部作品的用意。他们多半是根据个人的理解对作品作主观的解释。至于这种解释在多大的程度上符合作家的原意,只有作家心里最有数。但作家多半对此保持缄默。他似乎没有这种闲工夫。不然他就不是个作家而是文艺评论家了。何况有些作家都已作古,即使他们愿意,要请他们出来写一篇“我为什么写XX”也办不到了。
话扯得远了,还是回过头来谈谈《囚鸟》。
《囚鸟》是一部与冯内古特其他作品迴然不同的作品,它既不是科幻小说,也不是黑色幽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但它又不是作家本人的自传,而是整整一代人的自传。这话从何谈起,且让我慢慢道来。 《囚鸟》写的时间跨度是从19世纪初到尼克松下台,它所穿插的历史插曲,从萨柯与樊才蒂事件起,经过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希斯和钱伯斯事件,朝鲜战争,一直到“水门事件”。它的主人公与其说是主人公本人,不如说是整整的一代美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它揭示了美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激进转向保守,并最终沦为“水门事件”中一个不光彩的丑角的堕落过程。
冯内古特就像中国的捏面人一样,把这整整一代人的历史当作素材,左捏右捏,捏出了一个个看似面目俱非,却又特别逼真的人物来。《囚鸟》仿佛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那面镜子,历史在这里究竟是遭到了歪曲,还是归璞返真,只有过来人心里才明白。但是这是一部多么心酸的历史!只有冯内古特那样的大师才能把它颠过来倒过去,而仍不失它本来面目。
对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来说,读《囚鸟》也许觉得有些费劲,对于其中一些历史事实也许觉得有些生疏。但是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读《囚鸟》仿佛是重温旧梦,我相信不少过来人会一边读一边点头,会有似曾相识或者逝者如斯夫的感叹。
就怕我也是个摸象的瞎子。
1984年12月14日于病榻
文摘
囚 鸟
日子还是过不下去,是啊—不过一个傻子却很快就要同他的自尊心分手了,也许到世界末日也不会再碰头了。
请读者注意,在我这本书中年代和人物一样,都是书中的角色。这本书是我活到现在为止一生的故事。一千九百二十九年毁了美国的经济。一千九百三十一年送我上了哈佛大学。一千九百三十八年让我谋得了联邦政府的第一个差使。一千九百四十六年让我娶到了妻子。一千九百四十六年给了我一个不肖的儿子。一千九百五十三年把我从联邦政府中开除。
因此我把年代用大写字母写,好像它们是人名一样。
一千九百七十年给我在尼克松的白宫中谋到了一个差使。一千九百七十五年因为我在现在被称作 “水门事件”的政治丑闻中的一份十分荒唐的贡献把我送进了监牢。
我写此书的三年前,即一千九百七十七年又要把我放出去。我觉得自己像垃圾一样。我当时穿的是一身灰绿色的囚服。我独自坐在监牢里的床上,床上的铺盖已被我收了起来。一条毯子、两张床单、一只枕头套,都整整齐齐的叠好,放在我的双膝上,就要同我身上的囚服一起退还给我国政府。我布满老年斑的双手握在一起,按在上面。我的双眼呆呆地瞪着前面的墙,这里是离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三十五英里的芬莱特空军基地边上联邦zui低限度安保措施成人改造所的一所营房的二层楼上。我坐在那里等一个看守把我带到行政楼去,领取释放证和便服。大门外不会有人来接我。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会有人不咎既往,拥抱我一下,或者请我吃一顿饭,给我一张床睡一两个晚上。
要是这时有人注意看我,他会看到我大概每隔五分钟就开始做一件非常神秘的事儿。我脸部的漠然表情不变,从床单上举起手来,连击三下,又放下去。为什么这样,我以后再解释。
那一天是四月二十一日上午九点钟。狱卒晚来了一个小时。有一架战斗机从附近一条跑道的尽头凌空而起,在空中呼啸而过,耗掉的能量足够一百户人家用一千年。我连眼也不眨一下。这种事情,对芬莱特的老犯人和狱卒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
这里的犯人犯的都是不动武的“白领罪”,大多数都给装在紫色的中巴里,到基地周围去干活了。只留下少数打扫的人员擦玻璃,拖地板。还有少数留下的人在写信,或者读书、打瞌睡—他们身体抱恙,一般都是心脏病或背痛腰酸之类的,干不了什么体力活。要是在平日,我这时就会在基地医院的洗衣房里把衣服送到烘干机里去。就像他们说的那样,我的身体很好。
我在监牢里有没有因为是哈佛大学毕业生而受到特殊照顾?老实说,哈佛大学毕业并没有什么稀罕。我遇到过或听到过的哈佛大学毕业生至少还有七个。待会儿我一走,我的床就给了维吉尔·格雷特霍斯,这位前任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部部长也是哈佛出身。在芬莱特,就教育水平而言,我算是很低的,只有个微不足道的学士学位。我连个全美优秀大学生联谊会的会员都不是。我们这里光这个荣誉协会的会员就至少有二十多个,十多个医生,同样数目的牙医,还有一个兽医,一个神学博士,一个经济学博士,一个化学博士,被剥夺从业资格的律师更是不可胜数。律师多得司空见惯,因此每逢有新人来到,我们就有这样一句笑话:“要是你发现自己在同一个没有上过法学院的人说话,你就得小心。他不是监狱长就是看守。”
我自己这个微不足道的学位是文科方面的,偏重在历史和经济。我原来进哈佛时打算将来做公务员,即政府雇员,不是民选官员。我认为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没有比终身在政府中服务更高尚的职业了。由于我不知道政府的哪一部门会录用我,是国务院,还是印第安人事务局,还是别的什么机关,因此我必须力求知识渊博,到处适用。所以我学了一个文科学位。
现在说起来好像这是我自己的打算,我自己的想法,而在那个时候,我未经世事,什么都不懂,当然很乐意把一个年纪大得多的人的打算和想法当作自己的打算和想法。这个人是克利夫兰市的一个亿万豪富,名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麦康,他是哈佛大学一八九四届的。他是丹尼尔·麦康那个隐居遁世、说话口吃的儿子,而丹尼尔·麦康是一个精明强悍的苏格兰工程师兼冶炼家,他创办了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我出生的时候,那家公司是克利夫兰市雇人zui多的一家公司。弹指之间,恍若隔世,真无法想象我是在一千九百一十三年生的!要是今天的年轻人听我一本正经地说,那时候俄亥俄州的天空常常因古生物翼龙飞啸而过,遮得暗无天日,或者体重四十吨的古生物雷龙在库耶霍加河淤泥中打滚,会不会有人表示怀疑呢?我想不会。
我在亚历山大·汉密哈顿·麦康的欧克里德大街宅邸中出世的那一年,他已四十一岁。他娶了洛克菲勒家的小姐爱丽斯为妻,她比他还有钱,大部分时间带着他们的独生女克莱拉在欧洲度日。母女两人无疑因为麦康先生说话极不利落而感到见不得人,也许还因为他一辈子除了整天读书以外别的什么也不想干而感到无比痛心,因此很少回家。那时候离婚是不可想象的事。
克莱拉,你还在人世吗?她恨我。过去和现在都有人恨我。
人生就是这样。
我同麦康先生有什么关系,竟会出生在他的没有欢乐气氛、静如死水的宅邸中呢?原来我母亲是他的厨娘,她生在俄属立陶宛,名叫安娜·凯里斯。我父亲是他的保镖兼司机,他生在俄属波兰,名叫斯坦尼斯拉夫·斯坦凯维奇。他们两人是真心实意敬爱他的。
麦康先生在汽车间楼上盖了一间漂亮的公寓给他们,也是给了我。我长大一些,就成了他的玩伴,不过总是在室内。他教我玩“老姑娘”、跳棋和多米诺牌—还有真正的象棋。没有多久,我们就只下象棋了。他下得并不好,我几乎盘盘都赢,很可能他偷偷地喝酒喝醉了。我觉得他从来没有心思想赢。反正,从很早开始,他就告诉我,告诉我父母,我是个天才—我当然不是—他要送我上哈佛大学。这些年里,他对我父母一定已说过千万遍了:“你们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是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上等人的父母,你们会为他感到骄傲。”
为此目的,大约在我十岁的时候,他让我们家把斯坦凯维奇这个姓改为斯代布克。他说,如果我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姓氏,我在哈佛大学就会得到器重。因此我的名字改成了瓦尔特·F·斯代布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