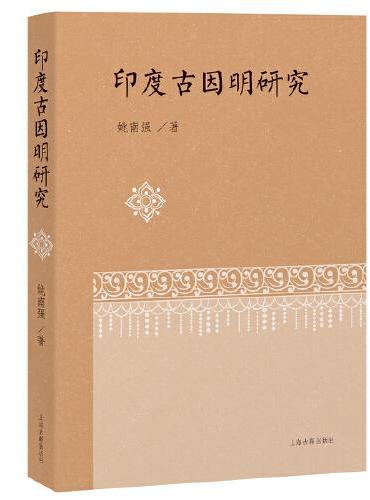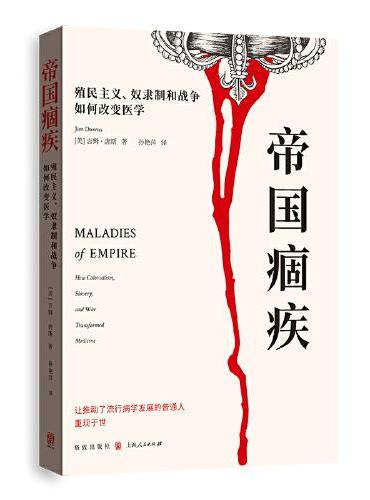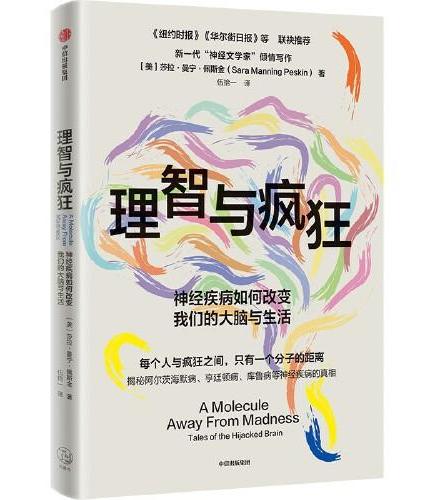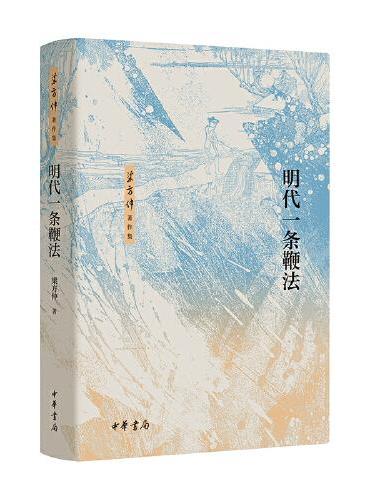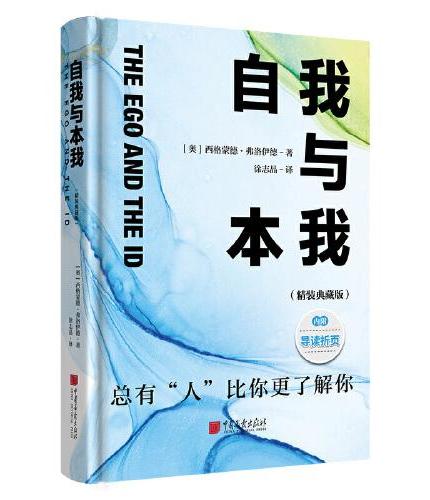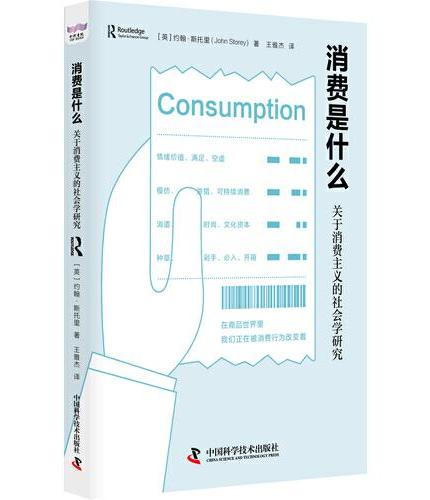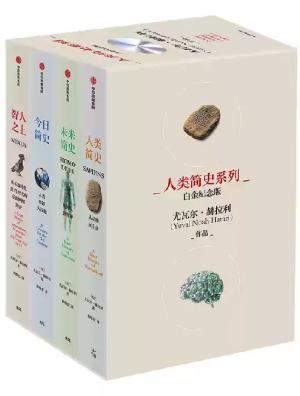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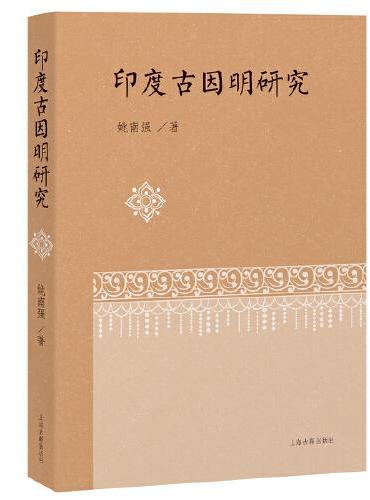
《
印度古因明研究
》
售價:NT$
6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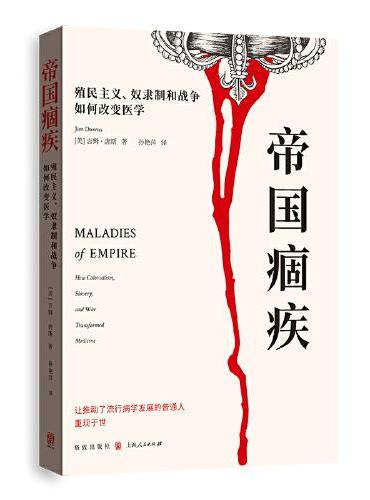
《
帝国痼疾:殖民主义、奴隶制和战争如何改变医学
》
售價:NT$
3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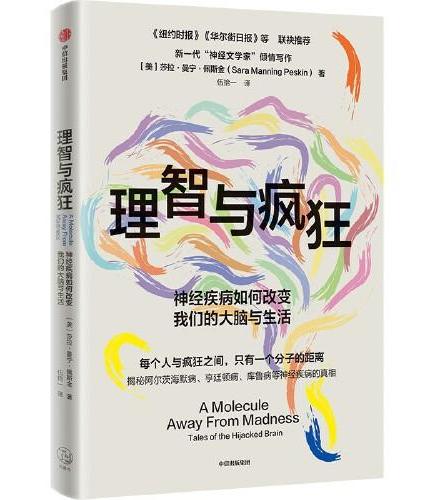
《
理智与疯狂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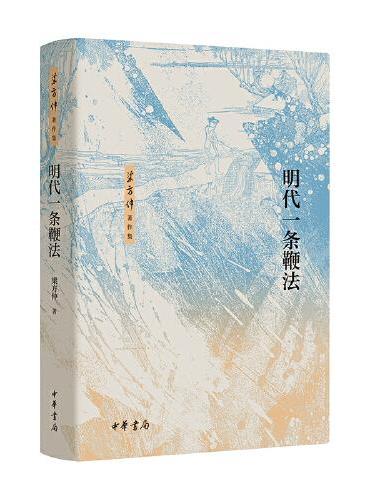
《
明代一条鞭法(精)--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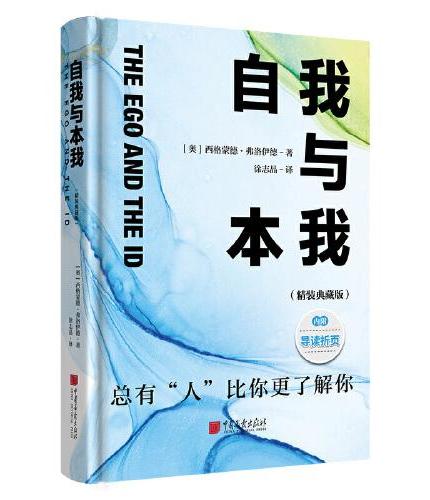
《
自我与本我:弗洛伊德经典心理学著作(精装典藏版)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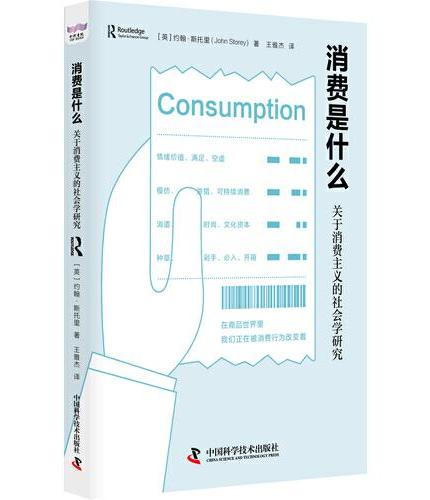
《
消费是什么 : 关于消费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一本书告诉你为什么买买买之后也有巨大空虚感)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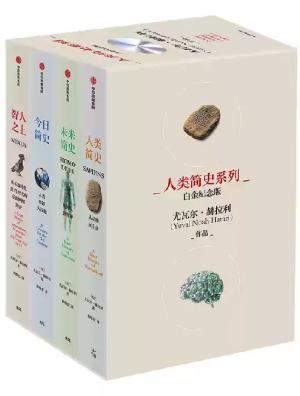
《
人类简史系列(白金纪念版)(套装共4册)
》
售價:NT$
1612.0

《
深度学习推荐系统2.0
》
售價:NT$
653.0
|
| 編輯推薦: |
|
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提出了很多对当代政治哲学深具启发性的概念和主题,以致她的好友、美国作家玛丽麦卡锡把《人的境况》比作携带了一个大量概念和洞见之地图的土地测量员。的确,这本书在古希腊和现代(1600-1900)两个时期穿梭,勾画出一幅理解何为政治以及西方政治思想的充满洞见的地图,为她的众多概念标出了它们在地图上的位置,同时也标出了这幅思想地图的界限以及未知的前景。
|
| 內容簡介: |
在本书中,阿伦特力图表明积极生活的三种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的区分是基于人的条件而做出的,她理解的人的条件,既不是所谓人的本质属性,也不是康德意义上规定人类经验方式的超验条件,而是人在地球上被给定的那些生存条件:劳动的条件是人们必需维生,工作的条件是人们必需建造一个人造物的世界,行动的条件是人们必需在交往中彰显自己,回答我是谁的问题。离开了这些条件,生活就不再是人的生活了。在此意义上,人是被条件规定了的存在(conditioned
beings)。但他们的活动又创造着自己下一步生存的条件,比如劳动超出家庭和国家界限的全球化发展,和人从宇宙的角度对地球采取行动,都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未来的生存处境。本书在结构上另一个值得关注之处是积极生活(vita
activa)与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的二元对照。*章给出的两种生活的对照,为全书确立了一个隐含的背景框架。实际上,只有在此二元对照下,劳动、工作和行动才可能有效地保持自身,因为与两种生活方式相应的,是古代西方对两个世界的想象:柏拉图的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或基督教的尘世之城和天上之城,前者是变化的、有死灭的,后者是永恒不变的。在那里,制作或工作被当成一切活动的原型,人在制作中模仿神圣世界的创造,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和荣耀都来自后者,后者才是他渴望回归之所。阿伦特认为这种沉思生活高于积极生活的等级秩序,在传统政治思想中导致了对政治的伤害,因为政治哲学家倾向于以制作模式把行动理解为按照某种真理来统治。但对立之消隐的灾难后果,要在世俗化的现代才清晰地浮现出来。在神圣世界不再被信仰,沉思被逐出有意义的人类能力行列之后,制作活动也失去了衡量他的产品真实性的标准,作为人造物的世界越来越相对化,丧失了它得以立足的持久性和稳固性。二元世界观的消失,一方面让现代人丧失了作为生存条件的世界,另一方面人被抛回到自身,返回到孤独内心来寻求真实性和确定性的基础。世界异化和向自身的回返最终以牺牲世界和牺牲行动为代价。虽然在现代早期,人作为制造者获得过短暂的胜利,那时人曾被高举为目的,但由于现代的世界异化和内省被提升为一种征服自然的无所不能的策略,也就没有哪种能力像制作主要是建造世界和生产世界之物的能力一样,丧失得如此之多(本书第242页)。在*后一章,阿伦特哀悼了技艺人(homo
faber)的失落:匠人精神始终预设了一个物的世界,在那里,物质闪耀、语词可听,但在世界塌陷,甚至被还原为生物循环意义上的自然的情况下,最终是劳动动物(animal
laborans)取得了全面胜利,而这就是我们已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
| 關於作者: |
|
汉娜阿伦特(19061975),德裔美籍犹太人,生于德国汉诺威。曾师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大学获博士学位。1933年因纳粹上台而流亡海外,于1951年获美国国籍。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先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她还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阿伦特以《极权主义的起源》、《在过去和未来之间》、《论革命》及《人的境况》等著作,为当代政治哲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20世纪较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
|
| 目錄:
|
导言 玛格丽特加诺芬 1
前言 1
第一章 人的条件 1
1. 积极生活与人的条件 1
2. 积极生活的术语 5
3. 永恒对不朽 9
第二章 公共和私人领域 14
4. 人:一种社会的或政治的动物 14
5. 城邦与家庭 18
6. 社会的兴起 24
7. 公共领域:共同 32
8. 私人领域:财产 39
9. 社会的和私人的 44
10. 人类活动的定位 48
第三章 劳动 60
11. 我们身体的劳动和我们双手的工作 60
12. 世界的物性 68
13. 劳动和生命 70
14. 劳动与繁殖 73
15. 财产的私人性和财富 79
16. 工作器具与劳动分工 84
17. 一个消费者社会 91
第四章 工作 105
18. 世界的持存 105
19. 物化 107
20. 工具性和劳动动物 111
21. 工具性和技艺人 117
22. 交换市场 121
23. 世界的恒久性及艺术品 127
第五章 行动 137
24. 行动者在言行中的彰显 138
25. 关系网和被实现的故事 142
26. 人类事务的脆弱性 147
27. 希腊的解救之道 151
28. 权力与显现空间 156
29. 技艺人与显现空间 163
30. 劳工运动 166
31. 制造对行动的传统替代 171
32. 行动的过程性质 179
33. 不可逆性和宽恕的力量 183
34. 不可预见性和承诺的权力 189
第六章 积极生活与现代 198
35. 世界异化 198
36. 阿基米德点的发现 205
37. 普遍科学对自然科学 213
38. 笛卡尔式怀疑的兴起 217
39. 内省和共同感的丧失 221
40. 思想和现代世界观 225
41. 沉思与行动的倒转 228
42. 积极生活内的倒转和技艺人的胜利 232
43. 技艺人的失败和幸福原则 240
44. 生命作为至善 246
45. 劳动动物的胜利 251
致谢 263
索引 265
重订后记 303
|
| 內容試閱:
|
1957年,一个人造的、在地球上诞生的物体,被发射到了太空中,在随后的数星期内,它绕地球航行,与不停地做旋转运动的天体太阳、月亮和星辰一样,遵循着同一套重力规律。准确地说,这个人造卫星既不是月亮或星星,也不是沿圆周轨道运行的天体,后者对我们受地球寿命所限的凡人来说,是永恒存在下去的东西。不过,在一段时间里,这个人造卫星打算留在太空中,它以与天体近似的方式在天上栖息和运行,仿佛它已被暂时地允许加入它们的高贵行列。
这一在重要性上无可比拟,甚至比原子裂变还重要的事件,如果不考虑它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带来的令人不快的影响,就应当得到人们无比喜悦的欢呼。但奇怪的是,人们的欢呼并非胜利的喜悦,也不是在面对人力掌控自然的巨大力量时,充盈于心中的骄傲和敬畏之情现在当他们从地球上仰望天空时,就能观看到一个他们自己制造的东西。在事件发生的一瞬间,直接的反应是大松一口气,人类总算朝着摆脱地球对人的束缚迈出了第一步。这个奇特的宣言不是某个美国记者随口说说的,而是恰好重复了二十年前刻在一位俄国伟大科学家墓碑上的惊人之语:人类不会永远束缚在地球上。
这样的情绪一段时间来很常见,表现为人们已处处不愿再慢吞吞地理解和适应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而且,他们在几十年里就把科学甩到了后头。在这儿和在其他方面一样,2科学家们实现了人们最大胆的梦想,证明这些梦想既不狂野也非荒诞无稽。新奇的只是这个国家中最受人尊敬的一份报纸,终于把直到那时还尘封在不太受人尊敬的科幻文学里的故事不幸的是,对科幻故事作为一种大众情绪和大众愿望的传达手段,没有人给予应有的重视登上了报纸头条。这个报道的平庸不应当让我们忽视它事实上的了不起,因为尽管基督徒说过尘世是一个泪之谷,哲学家把他们的身体视为思想或灵魂的监狱,但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人把地球本身看作人类身体的监狱,或表现出如此急切地想从地球上移居到月球上的渴望。难道肇始于一种背离不必然是背离上帝,而是背离作为我们在天上的父的一位神的现代解放和世俗化,要终结于更致命的对地球本身天空下所有生物之母的背弃吗?
人的境况前言地球是人类条件的集中体现,而且我们都知道,地球自然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能为人类提供一个栖息地的场所,在这里人类不借助人造物的帮助,就能毫不费力地行走和呼吸。世界上的人造物把人类存在与一切纯粹的动物环境区分开来,但是生命本身是外在于这个人造世界的。而现在大量的科学投入却致力于让生命也成为人工的,切断这一让人属于自然母亲怀抱的最后纽带。同样一种摆脱地球束缚的强烈渴望,也体现在从试管中创造出生命的努力,体现在从能力显著的人身上取出精子冷冻,混合后放在显微镜下制造出超人,并改变他们的体形和能力的愿望中。而且我猜想,摆脱人类条件的心愿,也体现在让人的寿命延长到百岁以上的期望中。
科学家告诉我们,他们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就可以生产出的未来人类,似乎拥有一种反抗人类被给定的存在的能力,拥有一种不知从哪里来就世俗而言的自由天分,只要他愿意,3他可以给自己换上他造出来的任何东西。没有理由怀疑我们实现这种自由交换的能力,正如没有理由怀疑我们当今有能力破坏地球上的所有有机生命。问题仅仅在于,是否我们真的想在这一方向上使用我们的新科学技术知识,而且这个问题不能由科学手段来决定,它是首要的政治问题,从而也不能留给专门科学家和专门政治家来回答。
即使这样的可能性还处在遥远的将来,但科学伟大胜利的首个令人振奋的结果,已经让科学家们感到他们自身处在自然科学的危机当中了。一个棘手的事实就是,现代科学世界观的真理,虽然可以用数学公式来演示并在技术上得到证明,但无法再让自身表达为普通的言说或思想。只要这些真理一得到连贯的概念表述,接下来的陈述就必定是或许不像一个三角形的圆那样无意义,但至少像一个长翅膀的狮子那样无意义薛定谔语。我们还不知道这种状况是不是最终的,但有可能的是,我们受地球限制却仿佛像宇宙的居民一样行动的生物大概永远都无法理解,即无法思考和谈论我们仍然能够做的东西。就此而言,我们的大脑构成了我们思想的物理和物质条件似乎没有能力理解我们所做的事,以至于从现在起,我们的确需要人造机器来代替我们思考和说话。如果真的证明了知识在现代意义上是知道如何与思想已经永远分道扬镳,那么我们确实变成了无助的奴隶,不仅是我们机器的奴隶,而且是我们的知道如何的奴隶,变成了无思想的生物,受任何一个技术上可能的玩意儿的操纵,哪怕它会置人于死地。
除了这些最终的和尚不确定的后果之外,科学所创造的形势还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凡言谈遭遇危险之处,事情就在本质上变成了政治的,因为言谈使人成为一种政治存在。4假如我们遵照如此频繁地催促着我们的建议,即让我们的文化态度也去适应当前科学成就的地位,我们就会不顾一切地采取一种让言谈不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因为今天的科学已经被迫采取了一种数学符号语言,虽然这种符号语言最初只不过用作口头陈述的一种省略形式,但它现在包含的陈述再也不能转译回口头言说。为什么说不信任科学家作为科学家的政治判断是明智的,首先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性格他们没有拒绝发明核武器,也不是因为他们天真他们不明白这些武器一旦被发明出来,就没有人会就如何使用来咨询他们的意见,而恰恰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生活在一个言谈已经丧失力量的世界里,无论人们做什么、认识什么或经验什么,都只有在能被谈论的范围内才有意义。或许存在着超越言谈的真理,或许这些真理对单个人来说非常有意义,即他可以是任何人,只要他不是一个政治的存在。但复数的人就生活和行动于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而言能够体验到意义,仅仅因为他们能够互相交谈,能够听懂彼此和让自己也弄明白。
当然更迫在眉睫的和也许同样重要的,是另一个差不多同样危险的事件:自动化的发明。这个东西在几十年里就使工厂变得空空荡荡,把人类从它最古老最自然的重负劳动负担和必需性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在这儿,人类条件的一个根本方面也处于危险之中,不过对这种条件的反抗,以及把人从劳动的辛苦操劳中解脱出来的愿望,并不是现代特有的,而是和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一样古老。摆脱劳动的自由不是一种新的自由,它曾经属于少数人最牢固的特权。就此而言,似乎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只不过被利用来达到从前所有时代都梦想过,但没有人能够实现的东西。
不过,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现代已经从理论上完成了对劳动的赞美,并导致整个社会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劳动者社会。5从而这个愿望就像神话故事中的愿望一样,在它实现的那一刻就自我挫败了。这个社会是一个即将从劳动的锁链中解放出来的劳动者社会,并且这个社会不知道还有什么更高级、更有意义的活动存在,值得它去为之争取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自由。这个社会是平等主义的社会,因为人们以劳动的方式共同生活,在这里没有阶级留下来,没有一种带有政治或精神性的贵族留下来,让人的其他能力可以得到保存和更新。甚至总统、国王和总理都把他们的职位看成社会生活必需的一项工作。在知识分子当中,只有孤独的个人把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当成一项创作,而非一项谋生活动。我们面临的前景是一个无劳动的劳动者社会,也就是说,劳动是留给他们的唯一活动。确实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的了。
对于这些当务之急和困境,本书不打算提供一个答案。这样的答案每天都在给出着,而且它们是实践政治的事情,服从于多数人的同意;答案也从来不在于理论考虑或某个人的意见,仿佛我们这里处理的问题能一劳永逸地给出解答似的。我下面打算做的,是从我们最崭新的经验和我们最切近的恐惧出发,重新考虑人的条件。显然,这是一个思想的问题,而无思想不顾一切地莽撞或无助地困惑或一遍遍重复已变得琐屑和空洞的真理在我看来正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因此,我打算做的非常简单,仅仅是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
我们正在做什么确实是本书的中心主题。它只处理人类条件的最基本区分,讨论那些传统上,以及按照通行意见,都在每个人力所能及范围内的活动。由于此点和其他原因,人之所能的最高级,或许也是最纯粹的活动思考活动,就不在当前的考虑范围内。从而本书限于系统地讨论劳动、工作和行动,这三者构成了本书的主要三章。就历史而言,我在最后一章处理现代,6对我们从西方历史上所知的、诸活动等级序列的多种概貌的讨论,也贯穿在全书当中。
不过,现代和现代世界还不是一回事。从科学上讲,肇始于17世纪的现代,已于20世纪初终结;从政治上讲,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世界,随着第一次原子爆炸而来临。这里我不讨论作为本书写作背景的现代世界。一方面,我把自己局限于对那些一般人类能力的分析上,这些人类能力出自人的条件,因而是永恒的,即只要人类条件本身不改变,它们就不会无可挽回地丧失。另一方面,历史分析的目的是追溯现代的世界异化人逃离地球进入宇宙和逃离世界返回自我的双重过程的根源,以达到对这样一个社会之本性的理解:这个社会从它被一个崭新、未知的时代的来临所征服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发展和表现自身了。
第一章人的条件
1. 积极生活与人的条件
我打算用积极生活vita
activa的术语,来指示三种根本性的人类活动: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这三种活动之所以是根本性的,是因为它们每一个都相应于人在地球上被给定的生活的一种基本条件the
basic condition。
劳动是与人体的生命过程对应的活动,身体自发的生长、新陈代谢和最终的衰亡,都要依靠劳动产出和输入生命过程的生存必需品。劳动的人之条件是生命本身。
工作是与人存在的非自然性相应的活动,即人的存在既不包含在物种周而复始的生命循环内,它的有死性也不能由物种的生命循环来补偿。工作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自然环境的人造物的世界。这个世界成为每个个体的居所,但它本身却注定要超越他们所有的人而长存。工作的人之条件是世界性worldliness。
行动,是唯一不以物或事为中介的,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与之对应的是复数性plurality的人之条件,即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人们,生活在地球上和栖息于世界的事实。尽管人类条件的所有方面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相关,但复数性却是一切政治生活特有的条件不仅是必要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而且是充分条件conditio per
quam。因此在罗马人也许是我们已知的最富政治性的民族的语言中,活着等于说在人们中间inter homines
esse,8死去等于说不再在人们中间inter homines esse
desinere。行动的复数性条件甚至最早包含在《创世纪》中他创造了他们男人和女人,假如我们理解这一关于人的被造的故事根本上不同于另一个故事版本的话。[在那个版本里,上帝最初创造了一人亚当,即创造了他而非他们,以至于人类众生只是繁衍的结果。][1]假如人仅仅是同一个模子无休止重复和复制的结果,其本性或本质就像任何其他东西的本性或本质一样,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和可预见的,则行动就是一场不必要的奢侈,一次对普遍行为规律的任意干预。复数性是人类行动的条件,是因为我们所有人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即没有人和曾经活过、正活着或将要活的其他任何人相同。
人的境况第一章人的条件所有这三种活动和它们相应的条件都与人存在的最一般状况密切相关:出生和死亡、诞生性natality和有死性mortality。劳动不仅确保了个体生存,而且保证了类生命的延续。工作和它的产物人造物品,为有死者mortals生活的空虚无益和人寿的短促易逝赋予了一种持久长存的尺度。9而行动,就它致力于政治体political
body的创建和维护而言,为记忆,即为历史创造了条件。劳动、工作以及行动,就它们都承担着为作为陌生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源源不绝的新来者,提供和保存世界并为之谋划的责任而言,它们三者都根植于诞生性。不过在这三者当中,行动与人的诞生性条件联系最为紧密;我们能在世界上感受到诞生所内含的新的开端,仅仅因为新来者具有开创新事的能力,也就是行动的能力。在此创新的意义上,行动的要素从而也是诞生性的要素内含在所有人类活动之中。而且,既然行动是最出色的政治活动,那么诞生性而非有死性,就是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有死性乃形而上学思想的核心范畴。
人的条件包括的不仅是生命被给予人的那些条件。人也是被条件规定的存在者conditioned
beings,因为任何东西一经他们接触,就立刻变成了他们下一步存在的条件。积极生活置身于其中的世界,是由人的活动所产生的物组成的,但是这些完全由于人方得以存在的物,常常反过来限制了它们的人类创造者。除了人在地球上的生活被给定的那些条件外,人也常常部分地在它们之外,创造出他们自己的、人为的条件;尽管后者来源于人,因而是可变的,但也跟自然物同样具有了制约人的力量。因而,任何接触到或进入人类生活稳定关系中的东西,都立刻带有了一种作为人类存在条件的性质。这就是为什么无论人类做什么,他们都总是受制约的存在者的原因。任何自行进入人类世界或被人为拉进人类世界的东西,都变成了人类条件的组成部分。世界现实对人类存在的影响,被感知和接受为一种限制人的力量。世界的客观性它的对象性或物性与人类条件互为补充;因为人类存在是被条件制约的存在,人类就不可能没有物而存在,而如果物不是作为人类存在的条件,它们就只是一堆不相干的物品的堆积,一个非世界non
world。
要避免误解:10人的条件不等于人的本性,与人的条件相应的所有人类活动和能力的总和,都不构成任何类似于人的本性的东西。无论是我们本书中讨论到的人类活动和能力,还是像思想和理性那样略去不论的活动或能力,甚至对活动和能力最详尽无遗的列举,都不构成所谓人存在的本质属性意即没有它们,存在就不再是人的存在。在人的条件中我们所能想象的最极端的改变,莫过于人从地球移居到另一个星球上。这一并非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意味着人将不得不生活在人造的条件之下,完全不同于地球给予的那些条件。的确,到那时,劳动、工作和行动,以及我们所知的思想都不再有任何意义了。然而,即使那些我们想象的离开地球的漫游者,也仍然是人;我们关于他们的本性所能做的唯一声明是:他们依然是受条件规定的存在者,即使现在他们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人自己造的。
人之本性的问题,奥古斯丁所谓的我对我自己成了一个问题quaestio
nihi factus
sum,似乎在个体心理学和一般哲学的意义上都是无法回答的。我们能认识、确定和定义我们周围万物的自然本性,但是我们无法对自己做同样的事就像无法跳出自己的影子一样。另外,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有理由假定,人像其他事物一样,有一种本性或本质。换言之,如果我们确有一种本性或本质,那么只有上帝才能知道或定义它,而首要的前提是他能像说出一个人是什么what一样说出这个人是谁who。[2]11此处的困难在于,人的认知模式只适用于认识有自然性质的事物,包括对我们自身的认识,也限于我们作为有机生命发展最高阶段的样本。但是当我们提出我们是谁?的问题时,人的认知模式就不起作用了。这就是为什么企图定义人的本性的各种尝试,都不可避免地终结于构造出某个神,哲学家的神的原因自柏拉图以来,这个神已经被思辨为某种关于人的柏拉图式理念。当然,神圣者的哲学概念被揭露为不过是人的能力和性质的概念化产物,并不是一个关于上帝不存在的证明或辩护;但是定义人的本性的尝试很容易导致我们产生某种超人的观念,并把它等同于神,这一事实足以让人对人之本性的概念投去怀疑的目光。
另一方面,人存在的那些条件生命本身,诞生性和有死性,世界性,复数性以及地球从来不能解释我们是什么或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原因很简单,这些条件从未绝对地限制我们。一直以来,哲学对此的意见不同于那些同样也关心人的问题的科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等等,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业已在科学上证明了,虽然我们现在,也许将来要一直生活于地球环境中,但我们不仅仅是局限于地球的生物。现代自然科学之所以能取得巨大胜利,就在于它能从一个真正宇宙的观点来对待地球所限的自然earth
bound nature,也就是说,明确大胆地从地球之外取得一个阿基米德点。
2. 积极生活的术语
积极生活一词承载且过度承载了传统的负担。这个词跟我们的政治思想传统一样悠久但并不早于它。而这个远没有把西方人全部的政治经验加以总结和作概念化表述的传统,产生于一种特定的历史聚合: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哲学家与城邦之间的冲突。这个传统取消了与其直接政治目的无关的许多更为远古的经验,并最终以一种高度选择性的方式,在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达到了终结。vita
activa本身是中世纪哲学对亚里士多德的bios
politikos政治生活的标准翻译,在奥古斯丁著作中已经出现,在那里作为交谈或实践的生活vita negotiosa or
actuosa,仍反映了这个词的原初意义:一种致力于公共政治事务的生活。[3]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自由人可能选择的三种生活方式。三种自由人的生活方式分别是后面谈到的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辨生活,见《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一章五。译者注,自由,意即完全不受生存必需品和由于生存必需而产生的关系的束缚。自由的前提条件就排除了所有首要目的在于维生的生活方式不仅包括劳动的生活劳动是奴隶的生活方式,为了活命,他忍受必然性的强迫和主人的统治,而且包括自由手艺人的制作生活和商人的敛财生活。简言之,任何人自愿或非自愿地为了他全部或暂时的生存,丧失了他运动或活动的自由倾向,就都被排除在了自由生活之外。[4]而其余三种生活方式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关注美的事物,13即关注既非必要又非纯粹有用之物:在享乐生活中,美是用来消费的;在致力于城邦事务的生活中,卓越产生了美言嘉行;在探索和沉思永恒之事的哲学家生活中,恒久的美既不会因为人们的营役而生成,也不会因为人们的消遣而改变。[5]
亚里士多德的用法和后来中世纪对这个词的用法的主要区别在于,亚里士多德的bios
politikos显然只用于人类事务领域,强调建立和保持人类事务领域的行动、实践praxis。在他看来劳动和工作都不够有尊严,不足以构成一种完整意义上的生活bios,一种自主的和真正属人的生活方式;因为劳动服务于必需的东西,工作生产有用的东西,它们都依赖人类的需要和缺乏。[6]政治生活能脱离这一论断,要归功于希腊人对城邦生活的理解,城邦对他们意味着一种十分特殊的、出于自由而选择的政治组织形式,而决非任何一种为了让人们有序地聚合一起所必需的行为模式。虽然不论希腊人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没有忽略这个事实,即人类生活总是需要某种政治组织,对臣民的统治也可以构成一种特定的生活样式,但在他们看来暴君的生活方式不能说是自由的,也跟政治生活没什么关系,因为它仅仅是一种必然性。[7]
随着古代城市国家的消失14奥古斯丁也许是最后一个至少知道作为公民意味着什么的人积极生活这个词失去了它特定的政治意义,开始意指所有致力于此世之事的活动。准确地说,古代城市国家的消失并没有造成工作和劳动在人类活动等级中的上升,乃至于后来上升到与政治生活享有同等尊严的高度。[8]实际出现的反倒是另一种情况:行动也从尘世生活必需性的层次上考虑,以至于沉思[理论生活bios
theōrētikos此时被译作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成了唯一真正自由的生活方式。[9]
不过,沉思相对于任何其他活动、包括行动在内的这种巨大优越性,在起源上并不是基督教的。我们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就可以发现这种优越性,在那里,对城邦生活的整个乌托邦重构不仅为哲学家的高超洞见所引导,而且除了使哲学家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之外没有其他目的。亚里士多德对不同生活方式的阐述也显而易见受到沉思theōria理想的引导在他对生活方式的排列中,享乐生活的地位微不足道。在古代人脱离生命必需性的自由和脱离他人强制的自由之外,哲学家们又加上了免于政治活动skholē[10]的自由,以致后来基督教宣称的脱离俗事,从所有现世活动15中解脱出来的自由,正是以后古典时代哲学的非政治化apolitia思想为起源和先导的。只不过曾经要求于少数人的事情,此刻被看成了一项所有人的权利。
从而包括了全部人类活动在内,并被从沉思要求的绝对宁静来定义的积极生活一词,就差不多等同于希腊的不宁静askholia,亚里士多德就用这个词来指代一切活动,而不仅仅指希腊的政治生活。与亚里士多德区别宁静和骚动,区别对外在物理运动无声的弃绝和各类活动的喧嚣同样早期,却更为重要的区别是政治生活和理论生活的区别。这种区别类似战争与和平的区别:正如战争是为了和平一样,每一种活动,甚至纯粹思想的运动,都必须在沉思的绝对宁静中达到完满和终结。[11]每一种运动,无论身体和灵魂的运动还是言说和推理的活动,都必须在真理面前止步。而真理,无论是古代的存在真理还是基督教永活的上帝的真理,都只在人的彻底沉寂中显露自身。[12]
传统上和一直到近代开端,积极生活一词从未丧失它不宁静nec
otium, a
skholia的否定性含义。这种含义本身直接关联到希腊人的一个也许更为根本的区分:自身所是的事物和由于人而存在的事物的区分,自然physei事物和人为nomo事物的区分。沉思的优越性在于这样的信念:没有什么人为的作品,在美与真上能与自然宇宙kosmos相比,后者自身永恒地转动,不受任何外在的、人或神的干预或帮助。只有当人的一切运动和活动都完全停止时,这种永恒才向有死者的眼睛显露自身。与此宁静状态相比,16积极生活之内所有的区分和表述都消失了。从沉思的角度看,到底是什么打扰了它必要的宁静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它被打扰了。
从而,传统上,积极生活一词从沉思生活中取得了它的意义;仅就它服务于一个活的身体的沉思需要和需求而言,它才被赋予了有限的尊严。[13]信仰来世的基督教宣布自己的喜悦在于沉思之乐[14],从而为把积极生活贬低到派生、附属的地位颁布了宗教的许可;不过这一秩序本身的确定,则是与沉思作为一种明显异于思想或推理的人类机能的发现,同时发生的。这一发现是苏格拉底学派做出的,从那儿以后,它就统治了贯穿我们整个传统的形而上学思想和政治思想。[15]就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言,讨论哪些原因造成了这一传统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显然那些原因要比引发了城邦和哲学家的冲突由此几乎偶然地,导致了沉思作为哲学家生活方式的发现的历史偶因深刻得多。它们必定存在于人之条件完全独特的一面中,积极生活的各种表述都不能穷尽它们的多种多样,而且我们有理由怀疑,即使把思想和推理活动都包括进来,也不能完全说明它们。阿伦特说促使她后来写作《精神生活》的一个原因就是想做此书没有完成的工作,即探索思想的人类条件。因为当前这本书虽然被出版商命名为人之条件,但其实只是对积极生活方面的考察此书的德文版就名为《积极生活》。促使她写《精神生活》的另一个原因则是由艾希曼审判引发的道德思考。见Hannah
Arendt: The Life of Mind, Harcourt, 1978, p.6。译者注
因而,17如果我这里对积极生活一词的用法与传统用法明显矛盾,与其说因为我怀疑作为这一区分基础的经验的有效性,不如说是因为我质疑这个区分从一开始就内含的等级秩序。这并不意味着我想要质疑或至少想要讨论传统的真理概念作为显露的真理,从而是某种给予人的东西,或者说我更倾向于现代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宣称人只能知道他自己制造的东西。我想要说的仅仅是,沉思在传统等级中获得的极大重要性,模糊了积极生活内部的各种区分和表述,而且至少从表面上看,虽然现代经历了与传统的断裂,马克思和尼采最终颠覆了传统的等级秩序,但这种状况在现代并没有根本的扭转。在他们对哲学体系和通常所接受价值的著名的头足倒置中,即在对这种秩序本身的运用上,传统的概念框架仍然完好无缺地保留着。
为现代的颠覆和传统的等级秩序所共享的假定是:一种主要的人类关切支配着人的所有活动,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囊括一切的原则的话,秩序就无法建立。这个假定当然不是事实,而且我对积极生活一词的使用就预设了,各类活动背后的关切是不一样的,其他关切不高于、也不低于沉思生活的主要关切。
3. 永恒对不朽
一面是积极投身于此世事务的各类活动样式,一面是在沉思中达到顶点的纯思想,它们分别对应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类主要关切,这一点自思想者和行动者开始分道扬镳以来[16],也就是自政治思想从苏格拉底学派中产生以来,就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显现出来了。实际上,18当哲学家发现政治领域并不理所当然地为人所有活动中的更高级活动服务时这个发现大概是苏格拉底本人作出的,虽然这一点无法证实,他们就立刻认定,他们找到了一种更高级的原则来代替城邦治理的原则,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在人们已知的原则之外发现了什么新的原则。表示这两种不同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突的原则的最简洁方式尽管有点表面化,是唤起不朽和永恒的区分。
不朽意味着在地球上以及这个被给定的世界中,长生不死,永远存在下去。按照希腊人的理解,自然和奥林匹亚诸神就是不朽的。在永恒往复的自然生命和长生不老的诸神背景下,站立着有死之人;他们是这个不朽而非永恒的宇宙中唯一的有死者,他们面对不死的诸神,但他们并不受一个永恒上帝的统治。如果我们相信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记载,那么早在哲学家对永恒作出概念化的表述,从而也早在希腊人具有关于永恒的特殊经验之前,不朽和永恒的差异就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希腊人的自我理解。希罗多德在讨论亚洲人对不可见之上帝的信仰和崇拜形式时,就明确地指出,与这种超越时间、生命和宇宙的上帝正如我们今天所谓的相比,希腊人的神和人不仅有着相同的形象,而且有着相同的本性,是神人同形同性的anthrōpophyeis。[17]希腊人对不朽的关切源自他们的这种体验:在有死之人的个体生活周围,环绕着不朽的自然和不朽的诸神。镶嵌于一个万物皆不朽的宇宙中,有死变成了人存在的唯一标记。人是有死者,唯一有死的存在物,因为他们不像动物一样只作为一个类成员存在,19通过种群繁衍保证生命的绵延不绝。[18]人的有死性在于这一事实:个体生命以一个从生到死的可辨认的生活故事,从生物生命中凸显出来。个体生命以它的垂直运动轨迹,即切断生物生命循环运动的轨迹,把自己从所有其他事物中区别了出来。这就是有死性:在一个凡运动的万物都做圆周运动的宇宙中,以直线运动。
有死者的任务和潜在的伟大在于他们创造作品、业绩和言辞[19]的能力,这些产物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属于长久存在之列,正是通过它们,有死者才能在这个万物皆不死除了他们自己的宇宙中找到他们的位置。人,虽然作为个体是有死的,但他们以做出不朽功业的能力,以他们在身后留下不可磨灭印迹的能力,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不朽,证明了他们自身有一种神性。人和动物的区别恰好不在于人的类属性:只有最优秀的aristoi人,始终证明自己是最优的aristeuein,一个在任何其他语言中都找不到对应词的动词,热爱不朽声名胜过可朽之物,才真正是人;其他满足于自然所能提供的享受的人,都是像动物一样活着和死去。这样的看法在赫拉克利特那里还保留着[20],但在苏格拉底之后的任何哲学家那里都找不到类似的意见了。
在本书中,20到底是苏格拉底本人还是柏拉图发现了永恒才是形而上学思想的核心,并不重要。答案之所以更倾向于苏格拉底,是因为他是伟大思想家中唯一一个不打算写下他的思想的人他在这点上跟在许多方面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显然,无论一个思想家多么关注永恒,当他一坐下来写他的思想,他就首先考虑的不是永恒,而是注意力转向了怎么样留下一些永恒的印迹。他进入了积极生活,在积极生活之中选择持久和潜在不朽的方式。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只有在柏拉图那里,对永恒和哲学家生活的关切,与追求不朽和对公民生活、政治生活的关切,才被看成是内在矛盾和相互冲突的。
哲学家关于永恒的体验,对柏拉图来说是不可言说arrhēton,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是无言aneu
logou,后来这二者都在悖谬的永恒当下nunc
stans中获得了概念化表达。哲学家关于永恒的体验只能发生在人类事务领域之外和人的复数性之外,如同我们从柏拉图《国家篇》的洞穴寓言中所了解的:在那里,哲学家挣脱了把他和他的同胞束缚在一起的锁链,在完美的独自中离开了洞穴,既无他人的陪伴,也无他人的追随。从政治上来讲,如果死亡意味着不再活在人们中间,那么关于永恒的体验就是一种死亡,与真实死亡唯一的区别在于它不是终极的,因为没有哪个活生生的人能长时间地忍受它。而正是这一点,在中世纪的思想中区分了沉思生活和积极生活。[21]关键是,与不朽相对的永恒体验没有任何相应的活动,也不能转化为任何活动。因为显然任何活动,哪怕仅仅是借助语词在一个人自身中进行的思想活动,不但不足以构成永恒,而且会打破和毁灭永恒体验本身。
用于描述永恒经验的词是Theōria理论或沉思,有别于其他一切态度,21因为其他态度充其量与不朽有关。也许是哲学家们亲眼见证了在城邦中追求不朽、乃至长久的机会已经变得微乎其微,从而促进了他们对永恒的发现;也许是对永恒的体验令他们如此震撼,以至于与之相比,所有对不朽的追求都不过是过眼云烟。无论如何,他们从此把自己置身于和古代城邦以及激励它的宗教公开对立的境地。当然,并不是哲学思想最终导致了对永恒的关注胜过所有对不朽的渴望。罗马帝国的倾覆清楚地表明了没有什么人手的作品能够不朽,随之兴起的基督福音将永生赋予个体生命,并上升为西方人的排他性宗教。这两者的结合,使得任何对尘世不朽的追求都变得无意义和不必要了。它们如此成功地把积极生活和政治生活都变成了沉思的婢女,以至于使世俗领域在现代的兴起,和同时发生的对行动和沉思的传统秩序的颠倒,都无法挽救不朽之渴望被湮没的命运,而那种渴望,最初曾经是积极生活的源泉和核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