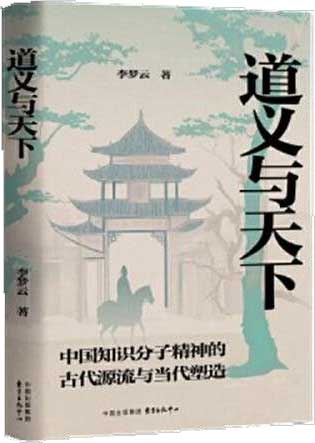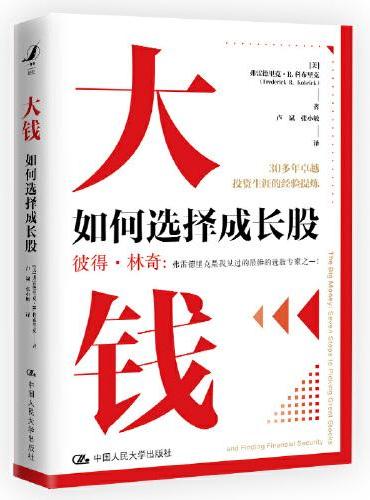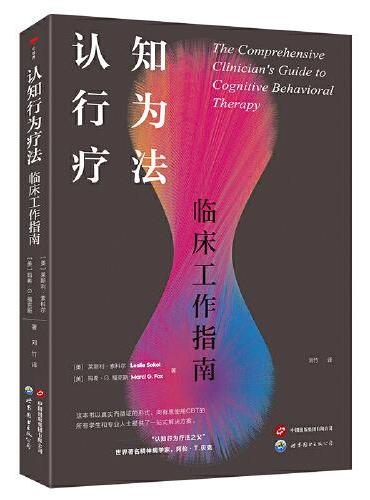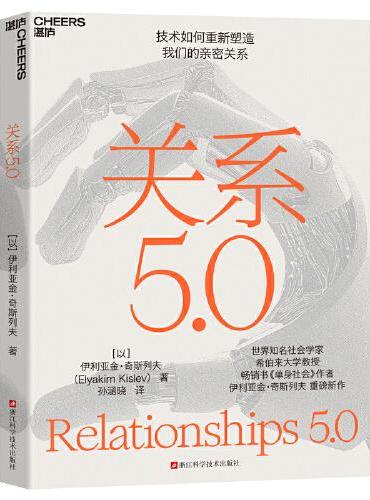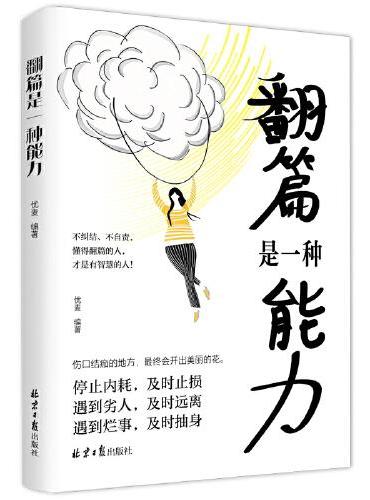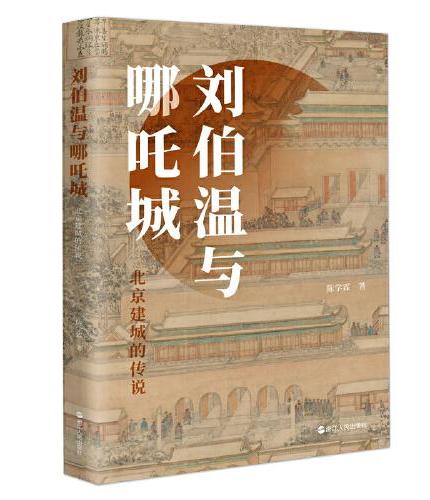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应对百年变局Ⅲ:全球治理视野下的新发展格局
》 售價:NT$
398.0
《
前端工程化——体系架构与基础建设(微课视频版)
》 售價:NT$
454.0
《
道义与天下: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古代源流与当代塑造
》 售價:NT$
407.0
《
大钱:如何选择成长股
》 售價:NT$
505.0
《
认知行为疗法:临床工作指南
》 售價:NT$
398.0
《
关系5.0
》 售價:NT$
612.0
《
翻篇是一种能力
》 售價:NT$
296.0
《
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
》 售價:NT$
449.0
編輯推薦:
电影《唐山大地震》原著作者张翎2017*力作
內容簡介:
《劳燕》是海外华语作家张翎的一部抗战背景的小说。故事开端于一个江南的采茶日,阿燕和刘兆虎这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在这春和景明中细数着各自的小心思。然而日军的突然空袭,留给这个美丽的茶园一个惊心的弹坑,也抽走了全书中*一段闲适的有序时光。母亲的惨死,将阿燕孤零零扔在这个凶险的世界。自此后,她要面临活下去的生计,要面临爱人离弃的无助,要面临众人歧视的屈辱中美合作训练营的成立,让两个美国人走进了阿燕的生活,一个是行医的牧师,一个是训练营的教官。而刘兆虎的入营,使得阿燕和这三个男人的关系更为复杂。牧师收留她并教会她行医,她就是凭借这个技艺,最终在艰难生活中完成自我的更新,一天天抬起头来,并在*危急的时候,为刘兆虎撑起一个遮蔽风雨的港湾。在这部让人动容落泪的小说中,阿燕这个形象温柔又有力量,宽容又有原则,坚韧却又丰沛,宽恕但不遗忘,独立却又承担。作者借由阿燕这样一个角色,展现了在苦难的磐涅和命运的蹂躏下,我们民族的女性所展现出来强韧的生命毅力和令人动容的情感动因。读者直面了残酷的战争,也了解到这世界上还有比爱情更好的男女之情
關於作者:
张翎,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现定居于多伦多市。90年代开始写作,代表作有《流年物语》《余震》《金山》《雁过藻溪》等。小说曾多次获得包括中国华语传媒年度小说家奖,华侨华人文学奖评委会大奖,台湾时报开卷好书奖,香港《红楼梦》全球海外华文长篇小说专家推荐奖等两岸三地重大文学奖项。
內容試閱
威廉.德.瓦耶-麦克米兰,或者麦卫理,或者比利,或者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