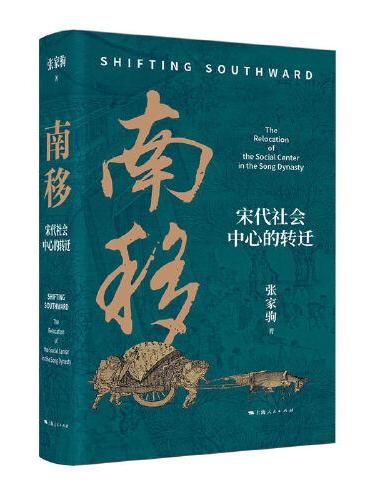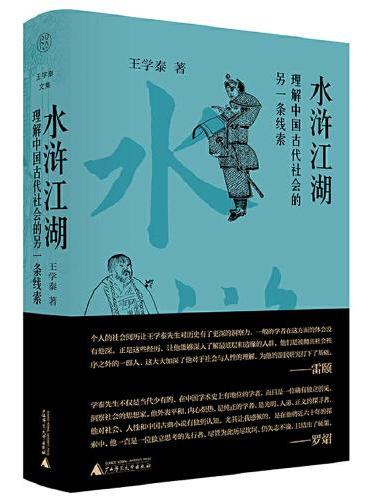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新版)
》
售價:NT$
449.0

《
女人们的谈话(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最佳改编剧本奖 原著!)
》
售價:NT$
286.0

《
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境管控的全球化(共域世界史)
》
售價:NT$
653.0

《
一周一堂经济学课: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
售價:NT$
500.0

《
慢性胃炎的中医研究 胃
》
售價:NT$
30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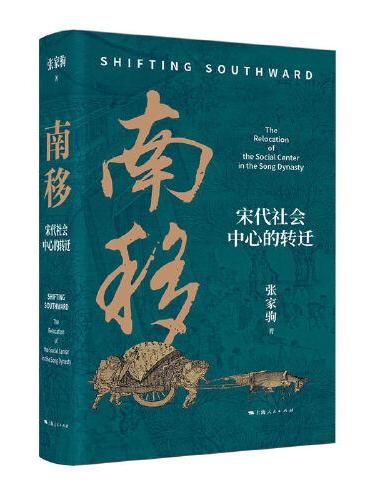
《
南移:宋代社会中心的转迁
》
售價:NT$
75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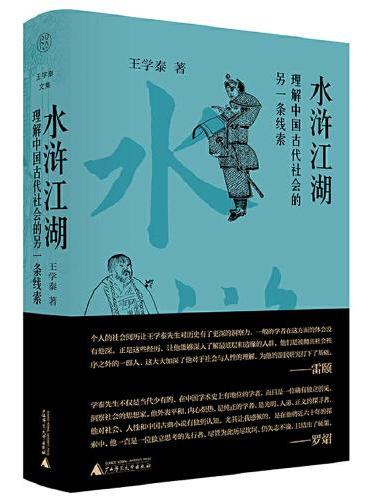
《
纯粹·水浒江湖: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另一条线索
》
售價:NT$
469.0

《
肌骨复健实践指南:运动损伤与慢性疼痛
》
售價:NT$
1367.0
|
| 內容簡介: |
|
本诗学论集从三个方面集中探讨了中国当代诗歌的价值和意义,并对存在的问题做了理性的审视与分析对百年新诗的历史发展与现实处境进行梳理,指陈当代诗歌所面临的难题与困境;从精神转型和美学流变着手,论述新世纪诗歌的写作技艺、思想与风格变化;从个案批评的角度,对北岛、王家新、余怒等重要诗人、诗作进行研究,从而透视个体写作的历史意识和现实精神。该诗学论集是作者与当代诗歌对话的结晶,因此,在独特的文体意识呈现中,也不乏理解之同情的批评风度。
|
| 關於作者: |
|
刘波,男,1978年生,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届客座研究员,湖北省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星星诗歌理论》杂志每月诗歌推荐栏目特约主持人。在《南方文坛》《当代文坛》《当代作家评论》《文艺评论》《扬子江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刊发表评论文章多篇,出版有《第三代诗歌研究》《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文学的回声》等。曾获得湖北文艺评论奖、后天批评奖、《红岩》文学批评奖等。
|
| 目錄:
|
|
有难度的写作就是一种创造(代序)第一辑传统、 境界和历史感 论百年新诗书写与传统之关系 3启蒙与困惑:80年代作为一种诗歌精神 20时代现实下的诗歌审视 34先锋诗人仍需叛逆精神 48论当代诗歌写作的日常性与神秘感 58论当代诗歌的精神处境与现实走向 75第二辑语言创造中要有思想的回声 论新世纪诗歌的精神转型和美学流变之一 91从书写自我到介入时代 论新世纪诗歌的精神转型和美学流变之二 105技艺修正、 经验转化与持续性写作 论新世纪诗歌的精神转型和美学流变之三 119力量的提升与精神的重建 论新世纪诗歌的精神转型和美学流变之四 132直面现实、 历史与传统的新格局 论新世纪诗歌的精神转型和美学流变之五 147第三辑为当代诗歌建立启蒙的传统 北岛诗歌论 163手艺人的悲剧意识和尊严写作 多多诗歌论 186承担意识、 批判精神与日常逻辑 王家新诗歌论 204当代汉语诗歌的神秘魔方 余怒诗歌论 224无欲写作通往力量之爱 朵渔诗歌论 251后 记 273
|
| 內容試閱:
|
有难度的写作就是一种创造(代序)在那部著名的励志电影《死亡诗社》(又名《春风化雨》)里,船长基廷的言传身教,给孩子们带来的影响就是使他们能打破常规的束缚,解放禁锢的思想,拥有自由的思考和独立的意志。当我们全部的生活都基于某种功利想法时,人生只会沿着有用而直奔终点,到头来我们可能会发现,那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因为人生旅程中的很多美好与秘密,都在那无用的行进途中。当年上大学时,我曾一门心思扑在小说创作上,总是幻想着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尤其是读了那么多经典之后,就想着自己的作品也应该位列其中,于是开始雄心勃勃地列出写作计划,结局当然可以预料到:所有的小说几乎都是一气呵成,事隔几年,再拿出来看,不堪卒读,真是羞愧不已,怎么也不敢相信乃自己所写。拥有理想主义精神,是写好作品的前提和保证。套用一句俗语,不想把作品写好的作家,不是好作家。要写好作品,进入的方式和路径则至关重要。当年我之所以那么急着想要写出伟大的小说,无非是想通过释放自己的情感、转化自我的经验,达到一种成功。然而,在写作中没有切入难度,没有在那种顺滑的下笔千言里投入一颗艺术之心,最后写出来的东西,也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而已,事实上,文字的肌体里潜藏着诸多的浅薄。我写得太快了、太顺了,根本意识不到快和顺背后的平庸,甚至还显得自己有那么一点悲壮:原来我是可以写出千言万语的。可这写作的危险性,早已暗藏在那无难度的倾泻里,它们因过于幼稚而遭到淘汰。当然,我并不是说当初的小说训练是没有用的,它至少还曾给我的文学梦想带来了飞翔之感。只不过,它因缺少必要的超越而无法获得长久存在的可能。后来,我开始了相对系统的阅读,这不是为了洗刷耻辱,报复自己,只是觉得写作成了兴趣、职业和爱好,继而更需要的是创造和阅读的自觉。写作的自由、阅读的独立,对一个作家来说,不是被迫的,它应是笔随心至后的一种精神境界。写作和阅读的独立性,首先就是不依赖于任何功利目的,它是一个人的精神王国,自由的空气在里面流动,于是,表达才有了底气,言说才有了立场。当我在阅读中感悟到了小说、诗歌和散文的美与诗意时,我愿意去阐释它们,为它们赋予我新的理解和认知,这样的分析文字,同样是一种创造。当作家的经验在作品中得以转化时,我能感同身受地找到自己人生的轨迹,也能捕捉到自己生活的影子。此时,文字与心灵的相通,就不在于写什么体裁了,小说可以,诗歌可以,散文可以,批评同样也能以入心的方式抵达我们的灵魂深处。我从事文学批评,首先是出于一种兴趣。当一个人沉浸在阅读中,他有话要说,不吐不快,这种表达源于情感释放,并渴望找到内心的共鸣。我愿意在守护意义与价值的层面上探寻文学的真相。只有挖掘真相的写作,才能说到每个人心里去,所以,我不太喜欢那些掉书袋和搬概念的批评文字,总觉得那些缠绕和繁复像是虚伪的遮掩,欲以高深来寻求自我安慰和知识炫耀。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我从来都不相信,自己都没搞清楚的东西,何以能写出来让别人理解和信任。以前我也曾有过这样一个阶段,学术虚荣心导致狂妄、无知,如今再看那时的文字,晦涩沉滞,想不脸红,都难。有些人忌讳读自己以前的文章,但没有勇气去面对过去的自己,又如何能真实地面对当下的自我?我希望自己能够从故弄玄虚中走出来,以明晰的表达呈现批评的风度,那唯一的标准,就是入心。要对自己的文字负责,仅以知识套知识,最后只能陷入自欺欺人的困境,唯有入心之论,方可让他人走进。我虽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但试图去学习、靠近,以求缩短与干净、纯粹、朴素之间的距离。为此,我不断阅读,不仅读更多的作品,也在接近个体真实的灵魂。灵魂的相通才是理解人世的密码,文学批评就给了我多次灵魂相通的机会。我通过那些真实的灵魂诉说,来带出自己对话的活力,让批评接近思考的本原,接近文学的真相。不知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动力,我还是倾向于去读那些厚重的文字,过于轻飘的东西,总是难以提起我的兴趣。我并不否认我的偏好,毕竟,文学与写作之事,难以完全客观。但我相信,有价值的作品,它一定从某些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创造性美学,要么是文字之美,要么是思想之力;二者兼有,则堪称完美。我从这些文学作品中获得了提升,当我再来为其写批评时,一方面是给作品以价值的延伸,另一方面更像是在进行自我启蒙。从事文学批评十多年来,除了基本的语言创造外,思想性和力量感越来越成为我评判作品的标准。当然,我也拿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写作:从文学层面来看,批评同样也是一种语言创造,它在诉诸理性的思考时,也应当给人带来精神和美的愉悦,这也是批评的职责。我们的批评文字不仅要在解读作品的基础上联结个人的内心,也要在更高的爱的层面对接当下时代,此为批评富有现实感和历史感的前提。吾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从当年读大学时写小说与诗歌,到如今以批评和学术为业,这一路走来,始终未离开写作本身,虽然思维和表达不尽相同,但我从来不认为它们的性质有多么大的不同。写小说时,真还领略过下笔如有神的感觉,但现在写批评文字,总感觉下笔艰难。这是一种倒退吗?我反而觉得是进步了。内心的创造精神让自己不可太随意,难度是我们时刻都必须面对的障碍,怎样准确地表达一个观点,怎样写好一个优雅的句子,甚至怎样搭配词语让它成为精彩的创造,这些最根本的问题,在任何有美学和思想追求的写作中,都是不可回避的。因为写作就是一种创造,小说、散文、诗歌和批评如此,我们平时写诗作文,当更是如此了。
无欲写作通往力量之爱朵渔诗歌论在诗集《最后的黑暗》后记中,朵渔说他写了这些年,真的还不知道诗到底是怎么回事,越写越深感诗歌的不可把握。有读者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无法理解他何出此言:写得那么好,那么清醒,怎么会不知道诗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理解朵渔的困境。这不是他谦虚,而恰恰是这种失败让诗人不至于那么志得意满,那么忘乎所以。多少比朵渔更年轻的诗人都在谈成就、谈胜利,以出全集的大师心态制造文字垃圾,但是朵渔小心翼翼,每一行诗出来,每一个字现形,他都要对其负责。这种自我要求让他在思考和写作中把深渊挖得更深一点,由来已久的困惑从此变成了一种自觉,不是要维持某种现状,而是选择向前或向后,要让自己看清深渊下的那一点光亮到底离自己还有多远。这个距离就是思考的动力,那束光亮就是写作的目标。思想性如何对接修辞很多人读朵渔的诗,可能会为其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性所折服,那种力道,那种韧度,都在于他和这个时代的抗争,而他所有的力量感和思想性,无不建基于一种修辞上的美感。诗歌和语言相关,这一本质性问题,朵渔认识得足够透彻,也足够清醒。在这一点上,朵渔虽没有多少可以言说的理论,但只要读一读他的诗,几乎不会让你失望。朵渔在语言修辞上的领悟,经过了感受、想象、转化和诗意生成的过程,这是写好诗的伦理与道义。而最重要的是,他拒绝一切平庸的表达。朵渔的修辞已经形成了一种风格,不需要我们对其做过多的阐释。甚至那些过度阐释,对其诗歌的整体审美来说就是一种破坏。除开对时代与社会的介入,朵渔的诗给我们带来的美感享受,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阅读的快感。当你读到那些出其不意的句子时,总会有一种共鸣和敬佩:他将很多句子写透了,以至我们无法置换新的词语;那种恰到好处全在于他对修辞本身的重视,这种重视不是刻意,而是一种高度的自觉。写诗首先不把语言表达处理到位,又何谈语言背后的思想内涵?虽然朵渔很少直接谈关于技艺的问题,与时代性的诗歌精神相比,技艺其实是个小东西朵渔:《羞耻的诗学关于新世纪十年诗歌的个人印象记》,载杨克主编《2011-2012中国新诗年鉴》,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第518页。,但他并不排斥技艺,而是巧妙地处理了技艺,让其完全内化于文字中,自然、贴切、合身,就像他看到了别人的好诗,觉得就像我写的一样,这种感觉是长期思考与自我训练的结果。朵渔对技艺一词不太感冒,他更欣赏手艺,并为此写过几篇文章。手艺和技艺不同,技艺重在技,手艺则重在手。现在炫技的东西太多了,很飘,有一股乌托邦的腐气。手艺人强调的是劳作,劳作就是身体与外界直接发生关系。手艺应是原创的,具有不可复制性。朵渔:《手艺》,载《意义把我们弄烦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189页。这虽是他十余年前的观点,现在看来仍然有意义,他道出了诗人写作时某种切实的劳作感:诗人何尝不是像农民一样劳动?每一粒稻米都有汗水的代价,每一首诗都不是上天所赐,而是个人的呕心沥血铁骨、王士强:《每一首诗都来自于呕心沥血朵渔访谈》,《山花(B版)》2013年7月号。,这种劳动支撑起来的诗扎实、厚重,有着不靠才子气来获取的信心。表达的手艺是基本功,很多诗人连这样的基本功都没有练好就出手,他带来的很可能就是一堆语言的残渣。朵渔不希望如此。诗无用,但有无用之用,这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它让我们从中感受到的是一种新鲜的审美,一种独特、别样的语感。朵渔早已有此觉悟,这是他比很多诗人走得远、也走得深的原因。他早期的一首《高原上》,单单感受那灌注其间的力量,就可捕捉到一种精神的光芒高傲、孤寂,从视觉到内心通电般的转换:当狮子抖动全身的月光,漫步在黄叶枯草间,我的泪流下来。并不是感动,而是一种深深的惊恐来自那个高度,那辉煌的色彩,忧郁的眼神和孤傲的心当初读完这首短诗时,我瞬间想到了里尔克的《豹》,但它们又不一样,从接受程度来看,我更理解《高原上》。那种凝练的诗意,是理性表达所透出的超验和神秘感。这首诗中,我们几乎无法去替换那些词,它们嵌在字里行间,如同那有孤傲之心的狮子一般真切、生动和踏实。就是这种生动的感悟,让朵渔的诗既在修辞的层面上接地气,又有围绕核心主题上升的超越感。他在整体意义上可能通向某种暧昧甚至是虚无,但在细部呈现上力求准确,不含糊、不混沌,让人信服。修辞的力量就在于此,精准的表达让意义变得丰富,文学之美也因此有了其秘密通道。梳理朵渔2006年以来的诗作,会发现他越来越注重对词语力量感的挖掘,他化用、转换,都基于一种创造。冬雨聚集起全部的泪湿漉漉的落叶犹如黑色的纸钱一个男人在上坡,他竖起的肩膀聚集起全部的隐忍松针间的鸟,聚集起全部的灰雨丝如飘发,聚集起一张美丽的脸我站在窗前,看那玻璃上的水滴聚集起悲伤的海什么样的悲伤会聚集成力取决于你的爱《聚集》由日常景观到内心世界,所有的聚集在此完成了,当那些单调的、为我们所忽视的意象在诗人笔下被聚拢起来,静观,琢磨,并最终指向某种真理。这种看似碎片化的表达,其实聚集起的是我们日渐消耗的心魂。我有时更喜欢这种灵光一现的散乱,它们很可能是诗人长久思索积累的结晶。他的想象有时很尖锐:如果需要暴力,我可以将肉体的一半留下,陪你练习情欲或将整个的心情寄去让空虚与抑郁在生活里相互抄袭(《我可以》);有时又带着错位的美感:这年头,什么都有可能。笼子可能等于飞鸟,三千可能等于二百五,美女可能倒在一个盲人的怀里(《愤然录》);有时还在形而上的思辨里触及信仰的内核:不要思考。思考乃上帝的特权。笛卡尔一心想抛开上帝单干,但他也需要上帝之手轻轻一碰,以便使世界运转起来。不要思考。思考无非是一种求偏见的意志,多数人需要麻木,就像少数人需要当头一棒。谁对无知再多一点无知,谁就离先知不远了,黄昏的哲人一声叹息:一觉醒来,又到天黑!(《〈思想录〉》)在轻与重的诗意对比里,朵渔可能更偏向于重,这是其作品在整体上所透出的情怀。近乎苛刻的内省,让他无法面对没有经过审视的文字。即便他渴望在轻与重之间找到某种平衡,但他的脾性拒绝游戏化,因为他对写作仍然抱持着理想主义精神。精益求精用在朵渔身上恰如其分,就像他在阅读书籍和生活之后所释放的感受,要打破惯常语言的束缚,摆脱人云亦云的重复性表达。对诗来说,规范可能走向腐朽,因此,我格外欣赏他写作中冒险的那部分,日常思考的边角料,或许就是诗歌的源泉。他在《消夏录》中把句子写得风生水起,既像是灵魂的独语,又像是与他者的对话。什么都不做时,感觉最忙,因此我没有真正闲下来的时候,我有时故意把一个字写错,以体验暴君的隐秘快感,生活就是一则四则运算,得负数和无理数是常有的事,我还是对自己太客气了,自己就像自己的一个客人。这些句子是切己及人的生活感受,虽然不一定通向日常生活的真理,但每一个词都安稳地落在了它应有的位置上。因此,牵强对于朵渔来说是无效的。没有什么样的诱惑比语言更具魅力,这是真正的诗人的日常功课:不管他是练习爱恨情仇,还是探索存在意义,修辞的手艺始终是关键。尽管其诗歌的外延通向爱、羞耻、责任与思想,但他所承担的汉语创造的使命,才是其诗歌最为内在的说服力量。写作的责任和精神的难度当初读到朵渔说自己还不知道诗到底是怎么回事时,我也有一种恍然大悟之感。诗人是清醒的,但诗本身始终有一块未明的区域,我们无法清晰地捕捉和把握,那可能就是诗意的另一半。以前,我总觉得诗越直白越好,那样的清晰才会通向真实,它无法欺骗我们的眼睛,然而,诗有神秘的维度,这是一种创造。这种创造或许就是朵渔所要挖的那道深渊,当然,挖得越深,难度越大;只有难度变大,有境界的审美才会成为可能。难度写作绝不仅仅是修辞意义上的,很多诗人可能都会这样认为。朵渔的那道深渊,是词语的深渊,也是思想的深渊,可能后者尤甚。2010年,他写了一首诗,名为《孤立与深渊》,虽然有着时代印痕,但现在来看,仍然契合他提出的深渊之论。日常的风景在修辞的陌生化中也获得了某种道义感,它们在这个时代显得沉重不堪,于是诗人写下了如此感慨:我只是祖国的异乡人我有候鸟颁发的暂住证飞鸟在申请一只笼子天空为兀鹰打开了栅栏孤独也曾为我架起梯子尽头搭在一片浮云之上攀登这么高,到底意欲何为难道真的要去做神马?我们不停地挖掉自身的基础以便让自己更加孤立孤立,但又不是在高处深渊显示了我们的残忍与贫乏。这是一场悖论吗?与不相容的孤立比起来,他是为了尊严,为了看清他者和自己,这种清醒不是简单的对抗,而是探究自我的孤立在什么意义上得以成立。孤立肯定有着必要的拒绝。作为诗人,你不能什么都占有,天赋、名利,以及那些身外之物。诗人占有语言和思想就够了,但要想拥有这两样东西,又是何其艰难。有的诗人努力一生,也未尝能在最后对自己说:我此生对得起自己的写作。有人越写越谦卑,他不敢妄自尊大;而有人还没写几首,就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掌握了诗歌的真理。诗人在现实中的狂傲和清高可以理解,但在表达和修辞上,那是需要灵魂进入的,不是几句口号、几个概念和强行命名就能让人信服的。诗歌的精神需要一种围观,也就是说不要太清高,要当得起狼籍,当得起耳顺者的聒噪(《对话》)写诗首先必须对自己负责,方可让读者信任。朵渔的这种责任来自某种精神高度:带着汉语诗人的使命感去写每一首小诗。只有对语言负责,书写才会有扎根和寻找源头的自觉。朵渔的根是很深的,他的思想之根扎在乡野和泥土里,并且越扎越深。这种深,不是深不可测的深,而是一种高度。他能用现代性文字写出扎根于乡土中国的思想,并不断的创造,这是其诗歌能富有深度的关键。对思想的追寻,往往与启蒙相关,这一方面是自我启蒙,另一方面是对更多人的精神启蒙。启蒙意识是朵渔作为有担当的诗人最隐秘的使命,他也在困惑中摸索着前行。写作从来不自由,很做作有时候我也会陷入沉溺的意志在一块思想的薄冰上战战兢兢跟坏人有什么道理好讲?但空洞的谦逊更令人反感。(《弄险》)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冒险,它不是一种放松的舒服姿态,需要诗人承担得更多、更深,这或许就是朵渔认为不自由的缘故吧。不自由,我们才会去争取自由,才会以追求自由的方式去完成对自己的反省,对时代和社会的审视。诗人的生命,就在这反省与审视中,不断地靠近语言的旷野,置换重量,实现理想。在此,诗人出示得更多的,是对自我的警示,而非对他人的批判,这是他之所以能坚定而决绝地前行,且义无反顾地奔向诗歌之域的理由。我们需要像诗人那样,将写诗当作一次次弄险,唯有如此,方可在语言的创造中把握精神的高度,同时又在对思想的探索中呈现语言的精彩。朵渔的写作,前后期的变化很明显,但从精神的角度来看,又有其延续性:对于乡村文明和大地的关注,对于父母、祖辈以及朋友的关注,对于自我意识觉醒的关注,对于社会批判的关注,对于历史记忆碎片的整理和改写。我一直在思考朵渔何以能不妥协,他的文字总是那么坚挺,不弯曲,不苟且。朵渔的毅力和耐性,很多诗人不是没有,比他更勤奋的写作者也不在少数,他们何以写不出力量感来?我觉得,还得归结到欲望和诱惑上。现在的朵渔没有了多少虚妄的欲求。当他站在外围往里看时,可以更清醒地讲真话,求真相,最终写出求真意志的诗,这就是他的诗歌伦理。诗人必须回到时代的现场中,而不是自我边缘化,才不会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诗人必须领受一项道德义务去感受自我和其他所有人之间的团结感,在有限之中而与无限相关联。朵渔:《诗人不应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载杨克主编《20092010中国新诗年鉴》,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第428页。这是诗人的自我要求,也是对其他诗人的勉励,只有如此,诗人们方可从中找到自我认同的价值,那是对幻灭感最有效的抵制。为了免于陷入虚妄,朵渔一度也追求行动的诗学。他和几位友人创办了民刊《诗歌现场》,这是一种责任的体现:他不仅将责任定位在语言上,而且更要将责任从修辞拉回地面,赋予其更切实的力量。现场是责任书写的源头,也是责任的载体。从凭空冥思到钟情现场,这里的转化有着清晰的演变路径。为了让自己不至于太偏离日常,诗人需要生活在真实中,肉身和精神的双重存在,当构成一个坚实的现场。朵渔曾将自己学习写诗的经历,比喻为追蝴蝶的过程,这像是一场长途跋涉,他认为这一长途有三个阶段:身体、发现、现场。身体,或许就是那场轰轰烈烈的下半身诗歌运动,但很快就过去了。事实证明:朵渔的诗歌也并不是简单的下半身写作,而是带有其自身独特的理性气质。2003年之后,朵渔开始从身体走向发现,这一发现,首先就是学习他人,从大师们那儿学到的东西,并不仅仅只是一些观念和技艺,还有发现诗歌的方式。发现的过程,就是真理与自由逐渐显现的过程。辞职之后,朵渔困在家里,开始了系统的阅读,这样的发现让他越来越清醒,也越来越警惕:有一段时间非常孤愤,与人通信也显得大义凛然。如果诗歌成了孤愤与狂躁,那么它可能已不再是诗歌。我开始让自己的诗歌转向现场,并与朋友们办一份叫作《诗歌现场》的民刊。面向现场的诗歌,不必是激愤的,但要有一种大力灌注其中;不必是战斗的,但要有一个合适的对手;不必是自我辩护的,但要有一颗自由的心灵。面向现场的事物,但现场不是自然呈现的,现场是在视野、眼光、判断力之下呈现的。什么样的识断,就会有什么样的现场。朵渔:《追蝴蝶》,《星星(下半月刊)》2009年第1期。这是朵渔为避免自己在激愤中迷失于现场的反思,他就是在一次次自我启蒙里,不断地调整状态,让写作越来越靠近自身的性格。除去技艺之外,真性情的流露,也是朵渔能从大多数年轻诗人中脱颖而出的重要缘由。朵渔诗歌的思想性,在于对自由的追寻和对尊严的守护,这也是其作品在这个时代能彰显价值的分量所在。拒绝平庸,让自由的境界成为信仰,这是他写作的标准。从另一方面来说,朵渔不仅是用语言在写作,而且是用生命在写作。每一次写作,都是独自一人站在一个新的开端,而不是尾随着一群人。铁骨、王士强:《每一首诗都来自于呕心沥血朵渔访谈》。拒绝平庸,是一种警醒,否则,就会止步不前或凐没于毫无创新的平淡里。因为他说过:平庸即是一种罪。反抗平庸,就是朵渔的写作起点。尽管他的每一次变化与调整,都是在冒险,而当冒险成为创作的常态时,朵渔的诗也因此焕发出异样的光彩。朵渔在新世纪的写作经由了一个由懵懂逐渐过渡到成熟的过程,他不仅在体验理想主义人生,也在验证一个时代的伦理底线。尼采在《最有影响的人》中说:一个人抗拒他的时代,把时代拒之于门外,更有甚者,还追究时代的责任。这样肯定造成影响。他是否想造成影响,这不重要;关键是他能。尼采:《快乐的知识》,黄明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146页。这样的抗拒者形象,对于朵渔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他的责任一方面是语言的创造,另一方面就是对时代的介入。每一位有良知的作家都应该介入公共生活,否则他的写作就是无效的。这应该是一部分常识。但是,诗人要谨防自己被黑暗吞噬,愤怒的拉奥孔不应成为美学的敌人。朵渔:《羞耻的诗学关于新世纪十年诗歌的个人印象记》,载杨克主编《20112012中国新诗年鉴》,第522523页。这样,对于朵渔的历史之诗、生活之诗和时代之诗,我们才能够解释,才得以在他的孤独中理解那份疼痛感。一组《民国》之诗,显示出了朵渔的视野和参透力,更重要的是,他将一种精神楔入我们时代的现实,一时显得触目惊心。他有向前看的责任,也有往后看的良知,既富有知识分子的良心,又带着诗人的美学情怀。这是责任的两端,也分属人生的两极。羞耻心与常识感2004年年底,朵渔彻底离开他工作了十年的单位,回到了家里,这也成了他写作生涯的真正开始。他终于可以返回到真实的内心了。他从责任所引起的激愤中回到了羞耻,羞耻感让自己不至于在虚无中沉沦。因此,他后来对羞耻之心格外看重,并写下了不少审视自我的羞耻之诗。有羞耻之心,有常识感,当属一个人的教养。而我们如何变得有教养,则是考验耐性和毅力的难题。这对于处在心灵黑暗中的人来说,更显必要。分裂、背弃信念、漂泊、与现实不调和、志在未来、向往更好的、更加公道的生活这是知识分子的特点。[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第26页。诗人同样如此。和那些西方知识分子一样,朵渔也向往更好的、更加公道的生活。他以批判性的思考,和对历史与时代的审视,为人生做了注解。带着审视的眼光看待自己以及写作,是诗人面对羞耻最好的回应。而被很多人所忽视的耻感,它在我写作的时候是一种反作用力,你在批判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朝向内心的力,两种力在平衡,让你不至于过分的偏执与黑暗。因为过于介入现实的诗歌,它也是会让你走火入魔的,人会偏离内心的,你会觉得自己在干一件高尚的事情、天底下最伟大的事情,会脱离常识。如果有一种朝向内心的力也在拽着你,就不会脱离中道太远,会找到一种平衡感。这种耻感就是对向外的批判的一种平衡。王士强:《其实你的人生是被设计的朵渔访谈录》,《新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朵渔早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对此做了深度反思,找到了解决之道。在第十五届柔刚诗歌奖的获奖感言中,朵渔这样说道:我的写作伦理基本上是对羞耻感的某种回应。但无所谓成绩,所有的成绩也只是失败。王阳明所谓持志如心痛,我感同身受。不可能有胜利。不可能有骄傲。不可能有尽头。我就是这样被无可名状的生命本能激励着,心怀恐惧上路,仿佛前方有伟大的事物就要出现。朵渔以对权力的抵抗和对自由的追求,成为这个时代最忠诚的诗歌守护者。他的守护是基于保持诗歌独立品质上的,是立足于他的诗不断追寻诗歌力量的生命基点上的。他的这种执着和与众不同,不是那种哗众取宠的媚俗和叛逆,而是自由思想的真切流露,是境界不断提升之后的自我解放。诗歌的境界,同样决定于思想的境界,美感的境界。不管是激进还是愤怒,都离不开他对自由的追寻,这种自由是有耻感的,它使朵渔从一个农家之子转变为独立诗人。他那首《我没想到失败也可以迎来它的荣誉》,就属于对羞耻感最好的回应:四月,我去蜀地领取一袋黄金犹如火中取栗,大海里捞针我没想到羞耻本身也可以获奖我没想到失败也可以迎来它的荣誉他们说这个人终于有了点坏名声他们终于从骨头里挑出了鸡蛋我知道,我知道诗写不好主要是光荣太多而光荣本应由乌云来安排如果一定要光荣和耻辱走在同一条路上何不将道路分裂成两岸现在好了,马已饿死在草原,牛也被赶进了牛角尖现在终于轮到小丑们登场了小丑却突然扭捏起来。深具一种失败感,是朵渔长期以来的精神处境,但就是这样的一种失败感,却让他结实地沉潜下来,有时他甚至伏在地面上,听自己的心跳,体验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承认自身的局限和脆弱,承认自己并不是一个英雄,这并不丢人。铁骨、王士强:《每一首诗都来自于呕心沥血朵渔访谈》。体验一种个人很难发觉的羞耻感,成为朵渔的日常功课,他时刻不忘将其当作警醒的训诫翻出来鞭策自己。这种自律性的反省,正是诗人能够以思想者的姿态立于诗坛的保证。这并非他刻意为之,而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应有的气节和立场。诗写不好主要是光荣太多,这的确是当下诗人写不好诗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是因为智力问题,也不在于勤奋程度,它关乎的是诗人的心态:到底是以什么样的目的来写诗,是自娱自乐,还是追名逐利?是止于发泄情感,还是满足精神需要?甚或是这些因素各占一部分?我想,存什么想法的诗人都有。但是荣耀对一个诗人来说,也不见得是好事,尤其是源源不断到来的荣耀,有时会毁了一个优秀的诗人。朵渔对诗人所获的光荣持警惕态度,这是道义使然:太多的光荣,容易让人活在自我陶醉中不可自拔,最后剩下的,不过是一堆虚幻的荣誉。只有不断地自我剖析,才可能彰显与命运抗争的勇气:你有没有勇气成为失败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它的邻居?连一次像样的失败都没有,你是不是得到的太多了?你这一生,可曾为自己修筑过一座抵挡溃败的堤坝?(《问自己你要诚实地回答》)带着惶惑和犹疑的追问式写作,是朵渔失败主义观念的话语实践,也是他能不断前行的动力。失败也可以是一种生活和写作的尊严,我们允许自己和他人有此权利,就像我们都应该有写小诗的自由。朵渔有一首诗名为《写小诗让人发愁》:写小诗让人发愁,看水徒生烦恼混世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无望的人练习杀人游戏大哥们在灯下说闲愁,你一支笔能做什么?写小诗让人发愁,看水徒生烦恼就那样在菜心里虚无着,在树干里正直着混世,混这时代夜色,太阳多余且迂阔。写小诗并不可耻,对于朵渔来说,小诗往往就是写作的常态,我们不可能每日都过得轰轰烈烈,诗中的起伏并不对应于生活的波澜。日常状态是我们写作的永恒主题,很少有诗人能跨越。可以看出,无论叫嚣着要多么高尚,诗歌写作终究还是会回到切实的生活中。诗歌写作如果仅仅是与精神生活有关,那么它很可能是一种狂热的、高烧的精神巫术,它的归宿往往是虚无的、蒙昧的。我看一个人的作品,往往会联系上他的生活,如果他的写作和生活是分裂的,我会对此人的写作保持怀疑和警觉。朵渔:《羞耻的诗学关于新世纪十年诗歌的个人印象记》,载杨克主编《20112012中国新诗年鉴》,第518页。就像诗歌处于边缘是文学的常态一样,那平淡的生活也是我们的日常,写小诗也就顺理成章了。没有羞耻感的人,言谈举止间往往就可能流露出膨胀的成就感,追求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的虚名,且认为是理所当然,这同样也成了一种诗坛常态。在《说耻》中,朵渔用诗的方式道出了真相,我们的病症就是:不诚实,不老实,不真实。如此坦率决绝,掷地有声。当下的诗人都在写些什么?似乎什么都在写,也似乎什么都没写。是因为诗太多,我们眼花缭乱,无法辨析?是因为太杂,我们无法受用,分辨不清?还是因为太浅,我们不屑一顾?因为太深,我们探不到底?都可能是,又或许都不是。我们陷入了混沌、尴尬,以及深深的失语中。作诗但求好句,已落下乘,做人若只做个文人,便无足观。(《说耻》)这已非常清楚和明晰:诗人苦吟写诗,若只是为了自我满足,很容易自我感觉良好。人是有追求的,而诗人的追求不仅仅是写一两句出其不意的诗,应该关乎一种精神。那种语言小格调,终究只是小技,而无大视野,更无大境界。就像诗人所言,仅仅满足于做一个文人,那种雅兴与酸腐应和,莫过于一种自我堕落。手中的笔,如果仅仅让它成为一支绵软的笔,而不能成为一柄锋利的剑、一把尖锐的刀,那它就失去了写的力量。写可能是一种批判精神和战斗思想,但更是一种身份认同和情怀担当。作为诗人,如果还有人格立于字词之上,良心在笔尖处滑动,就不能对时代与社会的暗角无动于衷,更不能对个人的苦难与群体遭遇的不公听之任之。介入性写作是及物的,如果反应冷漠,那是诗人在逃避担当。在朵渔看来,写好句和做文人,只是写作的初级阶段,但很多人一生所追求的,也不过如此。以当下读者对诗歌的期待来看,这种写作格局太狭隘了,它留给人的空间,自然也就小了。这也难怪一些诗人总在做表面功夫,沉缅于喧嚣的热闹,如此无知的高傲让谦逊的传统成了摆设。很多诗人乐在其中,迷恋小情调,像是还没入门。诗的终极通向爱的可能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朵渔在悲愤中写下了《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当时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的理性完全有别于那些应景的眼泪之诗、悲伤之诗和纯粹的哀悼之诗。时隔五年之久,很多人才明白此诗的持久影响和价值所在:灾难时期,诗歌何为?张清华先生认为这是地震诗中最好的一首,并给出解释:说它最好,不是因为它书写了更感人的人性和情景,更高尚的人格和故事,而是它提出了一个问题,面对这样的灾难,我们该写什么?张清华主编《19782008中国优秀诗歌》,现代出版社,2009,第307页。这正是它的独特性之所在,也是诗人没有出于一种公共悲愤而流于滥情的根本原因。他知道此时正义的力量该在何处得以彰显,他明白造成生命终结的除了自然的因素,还有我们自身的罪恶。与生命对峙的,除了那些邀功请赏的惯犯,还有那些掩人耳目的恶习。它们均与诗人心中的正义相背,他需要写出真相。这是知识分子责任意识的体现,也是诗人的真性情所致。刘波:《正义与力量之诗读朵渔〈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名作欣赏(下旬刊)》2011年3月号。在《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中,朵渔的批判意识很大程度上是由爱生出,而不是为了单纯的批判。他的写作在追求自由的同时,也崇尚正义,这两方面其实完全可以统一在诗人身上,并行不悖。尼采说:没有人比一个具有正义感和正义力的人更应得到我们的尊敬。因为最崇高和最珍稀的美德在其中融合而消隐,就像海纳百川一样。[德]弗里德里希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第4445页。这正是朵渔所追求的一种境界。如果说他现在还没有达至这种境界,那么,他也朝这一生命境界努力:一个诗人的纯粹。带着诗歌不是让人学会仇恨,而是让人变得善良之情怀,朵渔在面向时代的写作中,节制地写着他理想中的文字,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个性使然呢?在我们的诗歌写作里,需要这样的反叛之个性,需要如此坚韧之意志,更需要爱。朵渔曾有过激愤之时,但他没有陷入自我封闭和自我沉陷,而是在阅读、思考和写作中变得更加开阔和理性,朵渔从体制内走出,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自我放逐,其实,这样的举措又何尝不是诗人对自我的调整?他走出了体制,回到了诗歌与内心的慢,在坚定民间立场的同时,批判工业社会对乡村文明的侵袭;于思索和拒绝中参透现实的苦难,以让自己接续上民间知识分子向善和大爱的传统罗振亚、刘波:《在自由、爱与悲悯中落笔论朵渔及其诗歌》,《山花》2008年第2期。。写诗到底是为了什么?到语言为止吗?追求完全无用吗?这都不是最后的归宿。窗外,这么多人这么多人民,却没有一个具体的铁匠、锁匠、水果商带着心花怒放的决心,带着爱去生活,我就觉得在写出这么多诗之后,如果诗本身微不足道,在发出这么多问号之后,如果问号却转身来质问你那么,不如一句不写,不如闭口不说不如直接去买醉,不如马上去冬眠。《度夏》诗人去做这些了吗?没有。他的诗歌有用,他朝着爱的方向在写。虽然朵渔曾在诗中言说:爱,这绝望的艺术让我感到无力,虽然他也追问为什么没有爱,虽然他针对爱发出过一连串的质问:树枝上的鸟和果实,你爱哪一个?你爱她还是她?如果她已不再是她?也就是说,如果她已消失,你会不会爱上地上的影子和雪?当你说到爱,你到底是在爱别人还是爱自己?(《问自己你要诚实地回答》)这些自问和反问,都可能是出于爱的困惑,但只要内心之爱不通向虚无和谵妄,那就还存有爱的可能。从最细微的事物里重新学习爱,从书页间讨生活。(《从死亡的方向看,什么才是有意义的》)这才是足够真实的生活,也是足够真实的爱,爱就在日常生活中,也在我们每日的景观、行动和冥想里。手提一捆菠菜我感谢早起的晨雾感谢郊区的云和泥土我受之不虞一个赶鸭子的少年剥开薄冰谢谢谢谢那条裙子和它包裹的旧风景谢谢这瞬间的风和新栽的接骨木甚至那一声鸟鸣也应该衷心感激你们是一个丧家者心底的仁波切你们为平庸的天才送来影子和蜜的确我做着一些看似徒劳的事情不相信知音之稀,不相信千古愁相信每日的江郎才尽可化为诗意谢谢一滴鸟粪的鞭策,谢谢雨滴谢谢那个在厨房为我煮麻雀的人一粒米的教育胜过多少鼎镬之爱一首诗的逻辑近似于远山和绿意。这是朵渔为诗集《最后的黑暗》所写的序诗,形式上非常整齐,但并不影响形式之外的诗意呈现。诗人带着感恩书写的,是日常之爱,广博之爱,也是终极之爱。这种爱看似琐碎,不宏大,也不激昂,但它是一种教养,一份信念。其他的越来越不重要。但爱依然很重要。朵渔:《〈最后的黑暗〉后记》,载《最后的黑暗》,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第187页。在语言之外,似乎只有爱能支撑着诗人继续抒情和叙事,直面惨淡的现实,探寻这存在主义世界的荒谬之意。所以,朵渔也写荒谬之爱,难言之爱。我们从情欲的沟壑里取水在难言的爱中融冰生活多少有些戏子脾气现实消耗了太多的温情乌鸦和鸽子降低了天空的高度猛禽的目光中闪烁着泪花爱的结局往往就是不爱热情的生活只剩下呼吸(《你看,生活的尖牙》)爱是无私的,一旦自私,那也就不成其为爱了,那是一种变相的恨。虚假的爱,是空洞的、乏味的、无力的,也是没有任何力量的。当爱变得虚伪,爱就是逃避责任,虽然它也在责任的圈子里徘徊流连,但它终究只是昙花一现,而无法再生。爱被无名的障碍隔绝了,留下诗人无法隐藏的秘密。因此,变形之爱在一个人的内心似乎是无法修正的,不管它借助于怎样的对话与沟通,一切的努力都可能会是徒劳。朵渔不会让爱变得徒劳,他要让其有所指,也有所落实,落到人生命运里,也落到词间和笔端。爱是一种欢乐,虽然是一种夹杂着痛苦的欢乐,但仍然是一种欢乐。(《想不撒谎真难维特根斯坦:天才之为诗人》)诗不是让人学会仇恨,而是让人向善,诗人则是要让我们的人生变得美好,这是朵渔曾经的感言,至今依然有效,且会继续有效。这全在于他道出了诗人的本质和诗歌的功能,诗之善与爱,为写作最终的路向。人近中年,虚幻的成功已不够有趣而如果写下的一切只是一种折磨何不干脆将它酿成蜜?(《什么才是结实的人生》)人生靠欢乐之爱获得价值,而诗歌则是对善与爱最后的备忘。朵渔不仅仅在写爱之诗,其实,他提出了很多具有现实性的问题:我们该如何面对写作,尤其该如何面对头顶闪耀的光环写作?怎样在诗中去面对爱的困境和善的难题?这些都是很尖锐的问题。它们就那样结实地摆在面前,迫使诗人去努力理解,去解决发生在自我和他者身上的现实与精神困境。朵渔的诗与文,现在越来越带有思辨性,那可能是哲学阅读的结果。他也因此引起一些诗人的质疑:能不能把话说得明白点?这好像不是他的风格,因为他曾反对这一点。或许思辨是他必须要经历的阶段,越过了这一层次,或许另一种明晰之花会在他的诗文中重获绽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