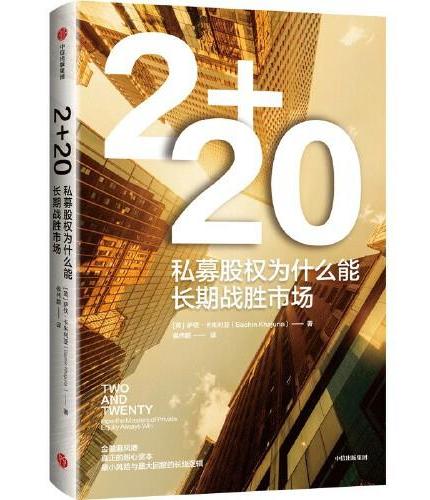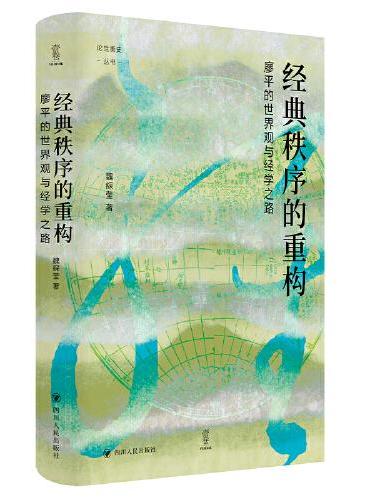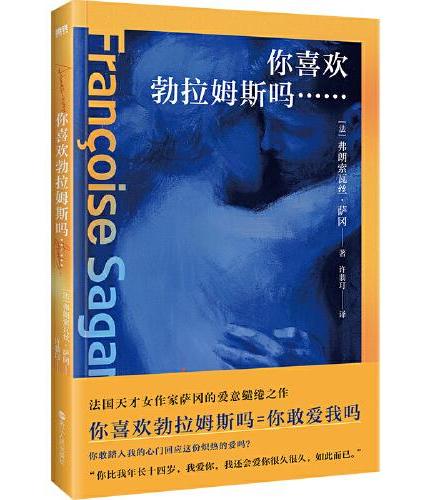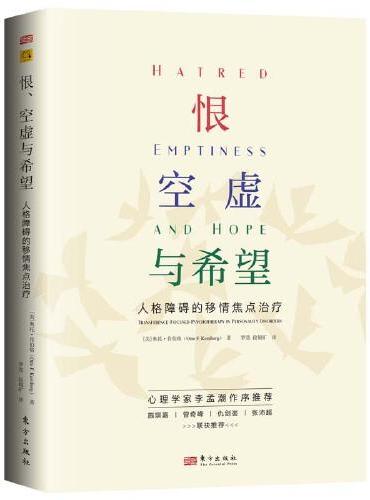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七种模式成就卓越班组:升级版
》
售價:NT$
296.0

《
主动出击:20世纪早期英国的科学普及(看英国科普黄金时代的科学家如何担当科普主力,打造科学共识!)
》
售價:NT$
403.0

《
太极拳套路完全图解 陈氏56式 杨氏24式和普及48式 精编口袋版
》
售價:NT$
1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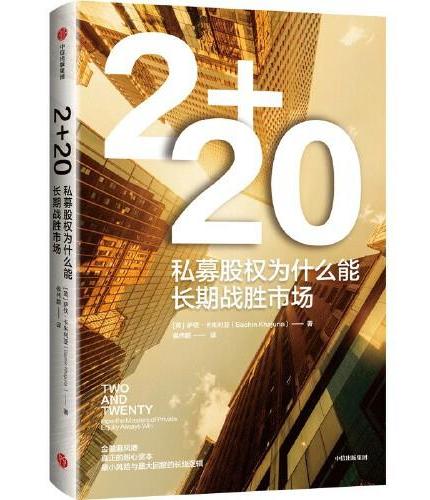
《
2+20:私募股权为什么能长期战胜市场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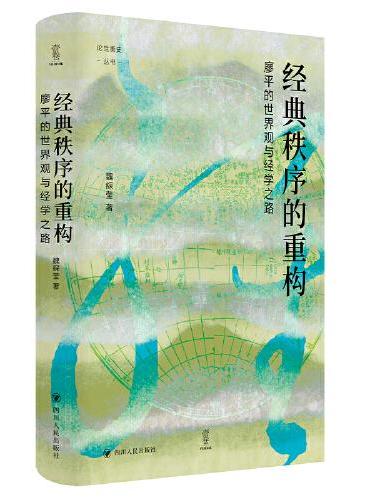
《
经典秩序的重构:廖平的世界观与经学之路(探究廖平经学思想,以新视角理解中国传统学术在西学冲击下的转型)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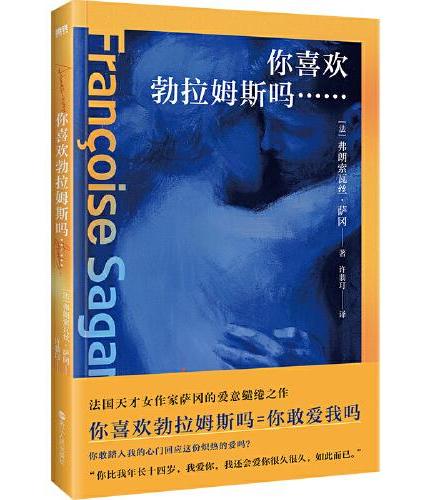
《
你喜欢勃拉姆斯吗……
》
售價:NT$
245.0

《
背影渐远犹低徊:清北民国大先生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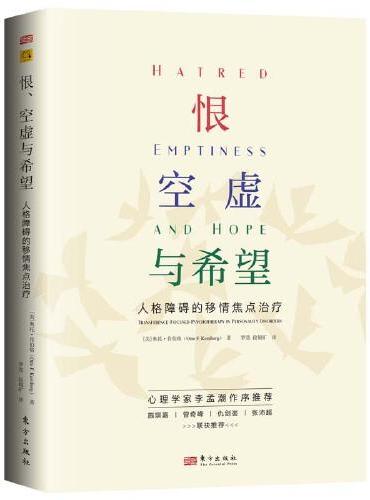
《
恨、空虚与希望:人格障碍的移情焦点治疗
》
售價:NT$
407.0
|
| 編輯推薦: |
|
品钦与塞林格,美国文坛两位以躲避公众而著名的小说大师。然而,品钦说自己与塞林格不同,他不是隐士。多年来,品钦公开的照片止步于大学时代的档案,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时,出版方安排了演员替他领奖。他虽然不曾露面,也在动画《辛普森一家》和YOUTUBE网站上现身(声)多次。他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不拒绝与外界交流。《慢慢学》中收录了他在1984年为首版所写的自序,作为中年成功作家,他分析了当时作品的缺点,袒露了年轻时写作的青涩。对于一向不愿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品钦,这篇坦率的自序意外地成为了解他思想世界的重要线索。短篇集中的5篇作品写于1959年至1964年,是他22岁到27岁的青年时代。在自序中,他认为保留这些有瑕疵的练手作品是有必要的,告诉写作者会犯的那些典型错误。此外,对于那些迷失在《万有引力之虹》之中的读者来说,这5篇风格气质各异的作品,向读者提供了了解品钦小说的独特通道。
|
| 內容簡介: |
|
《慢慢学》收录了托马斯品钦青年时代于1959年至1964年发表的五部短篇小说:《小雨》《低地》《熵》《玫瑰之下》和《秘密融合》。每一篇都包含着品钦小说创作标志性的主题与技法,更透露了许多有关他成长轨迹的线索:他的海军生涯、对勒卡雷的致敬、痴迷熵的起源
|
| 關於作者: |
作者:(美国)托马斯品钦
生于1937年5月8日。美国小说家,著有《V.》《拍卖第四十九批》《万有引力之虹》《葡萄园》《梅森和迪克逊》《反抗时间》《性本恶》《尖锋时代》,以及短篇集《慢慢学》。1974年因《万有引力之虹》被授予美国全国图书奖。
译者:但汉松
英美文学博士,副教授,现任教于南京大学英文系。主要学术兴趣为现当代美国文学及批评理论。业余从事文学翻译和书评随笔写作,著有个人随笔集《以读攻读》,译有托马斯品钦的《性本恶》,桑顿怀尔德的《我们的小镇》和《圣路易斯雷大桥》,朱利安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等。
|
| 目錄:
|
自序
小雨
低地
熵
玫瑰之下
秘密融合
译注
|
| 內容試閱:
|
自
序
在我记忆中,这些故事写于1958到1964年之间。其中四篇是我在大学里写的第五篇《秘密融合》(1964)才算像出自一个出师的学徒之手,而不是练笔之作。你可能已经知道,重读自己二十年前写的任何东西,都会对自尊心造成巨大打击,甚至包括那些付讫的支票。重读这些故事时,我第一反应是噢,天哪,同时还感受到了身体不适。我的第二个想法是彻底重写。这两种冲动还是被中年人的沉静压制了下来,我现在假装已经达到了一种清醒的境界,明白自己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年轻作者。我的意思是,我不能完全把这家伙从我生命里抹掉。另一方面,假如通过某种尚未发明的技术,我能和他在今日邂逅,我会乐意借钱给他吗?或者为了这次相逢,甚至愿意去街上喝杯啤酒,聊聊过去的事情?
我应该警告那些哪怕最善意的读者,这里有一些非常令人腻烦的段落,也充满了年少无知犯的错。同时,我最希望的是,尽管它们不时有点装腔作势,傻里傻气,设计不周,但让故事留着这些破绽是有用的,它们能说明那些刚入门的小说家会犯哪些典型的错误,提醒年轻作家最好避免某些做法。
《小雨》是我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一个朋友在陆军服役两年,其间我正好在海军服役,是他提供了故事细节。飓风确实发生过,我朋友所在的陆军通信小分队承担了故事中所描述的任务。我对自己写作最不满意的东西,大部分都以萌芽和更为高级的形式体现在这里了。我当时没能认识到,首先,主人公的问题真实而有趣,本身就足以发展成一个故事。显然,那时我觉得必须额外加一层雨的意象,必须要用《荒原》和《永别了,武器》的典故。我那时写作的座右铭是要有文学范儿,这点子很糟糕,完全是我自己捣腾出来的,而且就照这么做了。
还有我糟糕的耳朵,同样令人尴尬,它们破坏了很多对话,尤其是结尾部分。我那时对不同地区口音的认识还很浅薄。我曾注意到军队的人说话都被同化成了一种美国乡村基调。没多久,从纽约来的意大利裔街头小混混说话听上去就像南方农村人了,佐治亚州的水兵休假回来后,抱怨没人听得懂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的口音就像是北方佬。我来自北方,听到的所谓南方口音其实就是这种在军队里通用的口音,而不是别的。我以为自己听到了弗吉尼亚东部老百姓把ow音发成了oo,其实我不知道在真正的南方民间,不同地方(甚至是弗吉尼亚的不同地方)人们说话的口音都大为不同。在当时的电影中,这个错误也很明显。具体来说,我在酒吧那一段的问题,不仅是我让一个路易斯安那州的女孩刚开始就用我没听真切的南方东部二合元音说话,更糟的是,我坚持使之成了情节的一个要素它对于莱文而言很重要,所以对故事发展也如此。我的错误是,在自己还没一副好耳朵之前就去炫耀听觉。
在故事的核心,最关键、最令我不安的,是我的叙事者(他几乎等同于我,但不是我)处理死亡主题的方式非常糟糕。当我们说起小说的严肃性时,最终谈的其实是对死亡的态度
譬如人物面对它时会如何行事,或当它并非近在咫尺时,他们如何应对。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但这个话题很少向年轻作家提及,可能是因为他们尚处于打磨技巧的年纪,这种建议提了也是白搭。(我怀疑奇幻小说和科幻小说之所以能吸引那么多年轻读者,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书改造了空间和时间,人物可以轻易在时空连续体中任意旅行,因而得以摆脱身体面临的危险和时间流逝的定数,所以死亡也往往不是什么问题。)
在《小雨》中,这些人物在用未成年人的方式对待死亡。他们逃避:他们睡懒觉,用委婉语谈论死亡。当他们真的提到死亡时,就试着插科打诨。更糟的是,他们将之与性搅在一起。你们会发现在故事结尾,似乎发生了某种形式的性事,虽然从文本中难以确定。语言突然变得花哨难懂。也许这不仅仅是出于我年少时对于性的紧张。回想起来,我觉得这可能是出于整个大学时代亚文化中的一种普遍紧张。这是一种自我审查的倾向。这也是《嚎叫》《洛丽塔》和《北回归线》的时代,这些作品在当时激起了执法部门的过度反应。甚至在那时能读到的一些美国隐晦色情读物中,都会用极其夸张的象征手法去避免描写性行为。今天,这似乎都不再是问题,但在当时它确实是人们写作时能真切感受到的一种限制。
我现在觉得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并不是态度的老派和幼稚,而是其阶级视角。无论和平时期军队能有多少别的好处,它起码能对社会结构提供一种绝佳的观照。甚至对年轻人而言,有一点也很明显,即普通人生活中常常未获承认的等级差异在军队对于军官和士兵的区分中体现得格外明显和直接。人们惊讶地发现,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穿着卡其军装、戴着军衔徽章、肩负重要职责的成年人其实可能是白痴。而那些工人阶级出身的普通海军士兵,虽然按理说属于可能犯傻的那一拨,却更可能展现出才能、勇气、人性、智慧,以及其他受教育阶层自以为拥有的美德。虽然用的是文学术语,但肥腚莱文在这个故事中的冲突,其实是对谁忠诚的问题。作为一个1950年代不问政治的学生,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以现在的视角来看,我觉得当时的写作是出于一种两难的困境,在某种意义上,当时大部分作家都得应付这个问题。
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它与语言有关。我们受到了各个方向的鼓舞凯鲁亚克和垮掉派作家,索尔
贝娄在《奥吉 马奇历险记》中的用词,还有那些初露头角的作家,像赫伯特 戈尔德和菲利普
罗斯等从他们身上,我们发现在小说中至少允许同时存在两种非常不同的英语。居然允许!那样去写其实没问题!可当时谁知道呢?这种影响令人振奋,它使人获得解放,给人强烈的鼓舞。它并不是两选一,而是扩展了可能性。我认为我们并未有意识地去探索如何将之综合起来,虽然也许我们本应如此。大学生和蓝领工人在政治上并未成为同路人,这一点使得1960年代后期新左派的成功受到了限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两个群体在交流方式上,存在着真实而隐形的阶级力场。
当年,这种冲突就像大部分其他事物一样,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它在文学中形成的对立,就是传统小说与垮掉派小说的对立。虽然相距遥远,但我们时常听闻的一个事件就发生在芝加哥大学。譬如,那里有一个文学理论的芝加哥学派,广受瞩目和尊敬。与此同时,《芝加哥评论》发生过一次大震荡,催生了支持垮掉派的《大桌》杂志。芝加哥发生的事成了某种无法想象的颠覆性威胁的简称。当时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争论。为了抵抗传统的强势力量,我们当时喜欢向着圆心之外去运动,那些吸引我们的东西,有诺曼
梅勒的散文《白种黑人》,有随处可见的爵士乐唱片,还有一本书,我仍然相信它是伟大的美国小说杰克 凯鲁亚克的《在路上》。
还有一种次要影响(至少对我而言),就是海伦
沃德尔的《流浪的学者》,它在1950年代初重印,讲述了中世纪大批年轻诗人们离开修道院,走到欧洲街头,以歌唱的方式欢庆他们在学术院墙之外发现的广阔生活天地。考虑到当时大学的环境,这其中的影射并不难想见。其实并不是说大学生活枯燥乏味,而是因为那些底层另类生活的信息不断隐秘地渗透进大学的常青藤,我们开始感觉到校园外另一个嗡嗡作响的世界。我们中有些人无法抵抗诱惑,就离开了大学,去外面见识世界。其中相当一些人又回到大学,带着第一手见闻去鼓动另外一些人也如此尝试1960年代的大学生退学潮就是由此发端。
我与垮掉派运动只有萍水之交。与其他人一样,我常常泡在爵士俱乐部,小心享用着两杯啤酒的最低消费。我晚上戴着角质镜架的太阳镜,去参加阁楼派对,那里的女孩们都穿着奇怪的衣服。我很喜欢听那里各种各样的大麻笑话,虽然当时这种笑话讲得多,但那种东西其实很难弄到。1956年,在弗吉尼亚的诺福克,我溜达进一家书店,发现了《常青评论》的创刊号,这是当时垮掉派艺术的早期论坛。它让我大开眼界。我当时在海军服役,但早已知道人们会在甲板上围坐成一圈,演唱那些早期摇滚歌曲(有些唱得特别好),他们敲着邦戈手鼓,吹着萨克斯管,当大鸟去世时,以及后来克利福德
布朗去世时,他们是真心感到悲痛。重返大学后,我发现学术圈的人对当时那期《常青评论》的封面非常警惕,更别说里面的内容了。似乎有些搞文学的对垮掉的一代颇有成见,就像我所在军舰上某些军官对待埃尔维斯
普雷斯利的态度一样。他们曾经问舰上那些似乎懂行的人譬如发型像埃尔维斯的人。他想说什么?他们气急败坏地问,他到底想干什么?
我们当时处于一个转折关口,那是一个向后垮掉派过渡的奇特文化时代,我们在信仰上四分五裂。就像波普和摇滚完全不同于摇摆乐和战后流行乐那样,这种新的写作方式和我们当时在大学读到的那些更为正统的现代主义传统相去甚远。不幸的是,我们并没有什么选择余地。我们是旁观者:游行队伍已经走了过去,我们得到的一切都是二手的,消费的是那个时代的媒体提供给我们的东西。这并未妨碍我们采取垮掉派的姿态,运用他们的道具,并最终作为后垮掉派更好地去理解怎样以一种正常而合适的方式,确认我们所希望相信的美国价值观。当十年后嬉皮士开始复兴时,我们一度感到了某种怀旧和肯定。垮掉派的预言家被重新抬了出来,人们开始在电吉他上弹奏中音萨克斯的爵士重复段,东方的智慧又开始成为时尚。一切都没变,只是今非昔比。
然而,就消极的一面而言,这两种运动都过分强调了青春,这包括过度追求新花样。当然,那时的我虚度了青春,但重拾这个关于懵懂青春的视角,是因为除了那些对性和死亡的不成熟态度,我们还可以发现,某些幼稚的价值观会轻而易举地潜入故事里并毁掉一个原本值得同情的故事人物。《低地》中的丹尼斯
弗兰吉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例子。某种意义上,它更像是人物速写,而不是故事。老丹尼斯并未在岁月中成长。他不爱动弹,却非常喜欢绘声绘色的异想天开,故事就讲了这么多。也许焦点明晰了,却没有解决问题,故事里也没有太多情节变化或生活内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