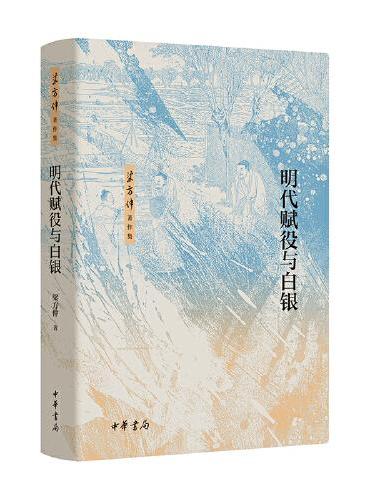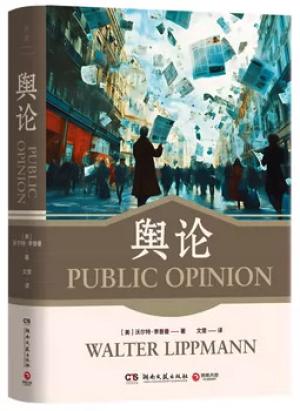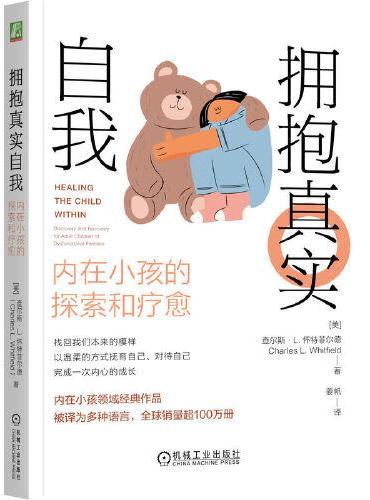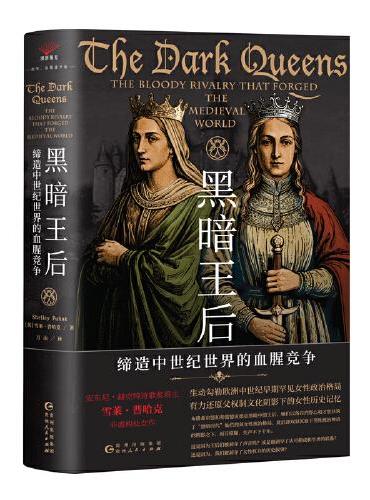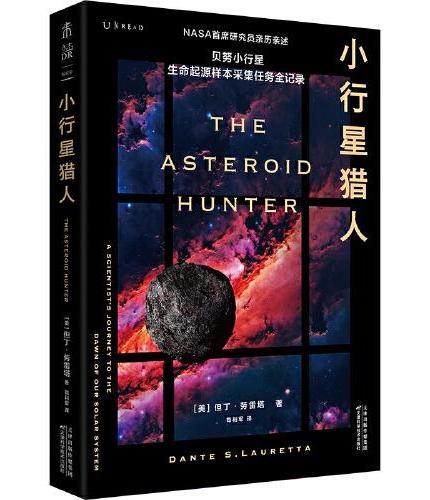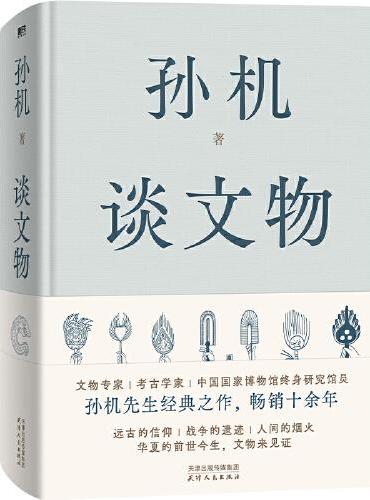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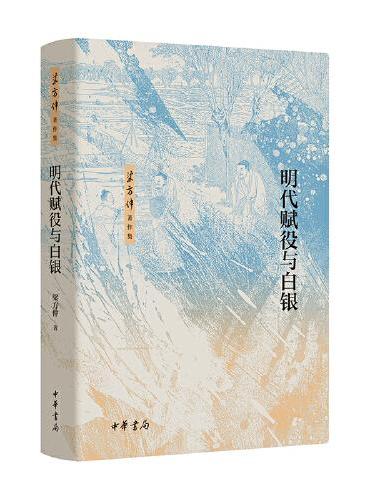
《
明代赋役与白银——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NT$
367.0

《
量子纠缠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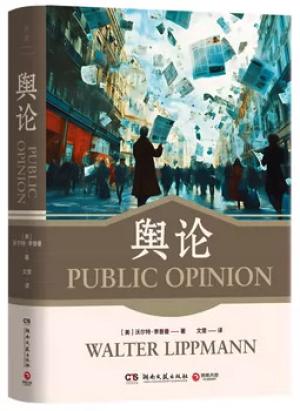
《
舆论(普利策奖得主、“现代新闻学之父”沃尔特·李普曼传播学经典)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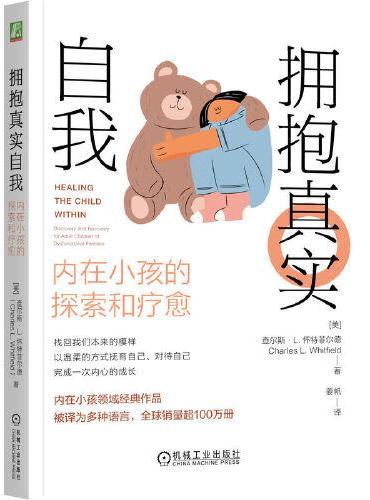
《
拥抱真实自我:内在小孩的探索和疗愈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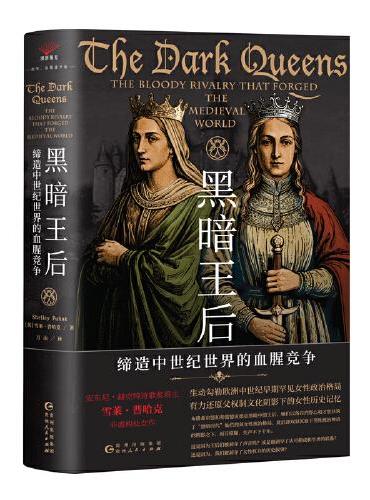
《
黑暗王后:缔造中世纪世界的血腥竞争
》
售價:NT$
6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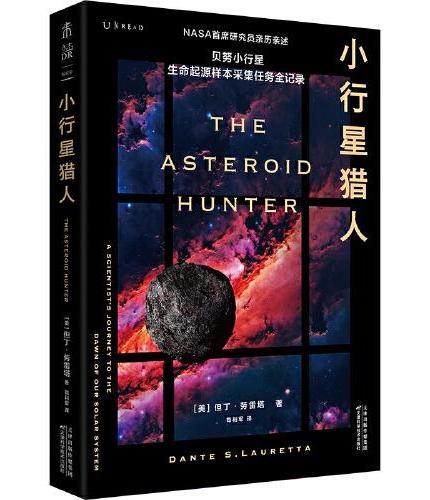
《
小行星猎人:贝努小行星生命起源样本采集任务全记录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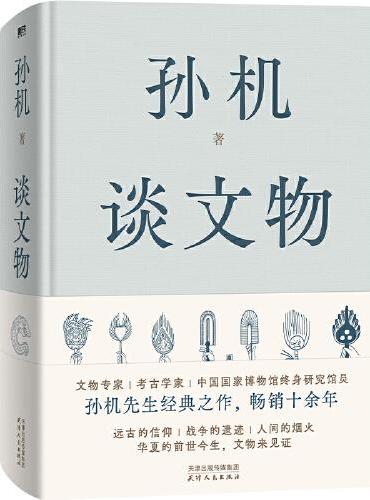
《
孙机谈文物
》
售價:NT$
551.0

《
诡舍(夜来风雨声悬疑幻想震撼之作)
》
售價:NT$
254.0
|
| 編輯推薦: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高峰陈平原为万千读者度身甄选,专业眼光,菁华品质。
名家名作荟萃,尽显人文之美。
《神神鬼鬼》堪称名人谈鬼神的合集,收录了现当代文学史上如茅盾、周作人、梁实秋、老舍、鲁迅等35位名家在鬼神观念上的看法和观点,介绍了鬼与神这两个在一般民众心目中完全不同的概念和先秦以来历代鬼诗、鬼画、鬼戏、鬼文的艺术特色。
3. 文学为经,文化为纬,用散文串起十个中国文化主题。
读文章就是读生活、读文化就是读人生。《神神鬼鬼》全书52篇文章,以文学为经,文化为纬,串起了中国人生活的另一个重要侧面。
4. 沙里淘金,淘汰了一些徒有虚名的名作,收入了一些未录于一般选本的遗珠。
丛书既囊括《谈狐仙》《水母》这样的名作,也选采了许多不见录于一般选本的遗珠,所选文章更具文化意味又妙趣横生,同时更全面、丰富地表现了20世纪中国散文精粹。
5. 专业主播团队,篇篇有声呈现,既上口又入耳。
紧跟大众听书时尚,特别邀请专业主播团队为全部文章录制音频,扫描每篇所附的二维码,即可收听朗读。上下班途中、跑步、休息随时随地,视听结合,拉近你与经典的距离。
6. 尊重版权,每一篇
|
| 內容簡介: |
|
1985年,被称为 燕园三剑客的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人共同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倡导以整体的眼光将中国现当代文学溯源至晚清,将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三个时段打通,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漫说文化丛书即是这一概念的具体表现,所选散文充满文化意味而又妙趣横生。"鬼"与"神"在一般民众心目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神神鬼鬼》一书节录了现当代文学史上名家如鲁迅、茅盾、陈独秀、胡适、老舍等在鬼神观念上的看法和观点,在理论上介绍了鬼诗、鬼画、鬼戏的艺术特色,并对若干以鬼为表现对象的文艺作品进行了介绍分析,是一代文人对鬼神及"鬼神文艺"潜在而浓厚的兴趣所在。
|
| 關於作者: |
|
陈平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座高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他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领域有着精深研究和独到见解。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
| 目錄:
|
目 录
contents
|再 记|
| 序 |
|附 记|
|导 读|
有鬼论质疑 ◎ 陈独秀| 001
辟《灵学丛志》 ◎ 刘半农| 003
送灶日漫笔 ◎ 鲁迅 | 007
捣鬼心传 ◎ 鲁迅 | 011
从拜神到无神 ◎ 胡适 | 014
谈迷信之类 ◎ 茅盾| 025
谈狐仙 ◎ 唐弢| 029
土地和灶君 ◎ 唐弢| 031
白昼见鬼 ◎ 薰宇| 033
迷信 ◎ 王力| 036
神的灭亡 ◎ 靳以| 043
人和鬼 ◎ 吴晗| 045
再谈人和鬼 ◎ 吴晗| 049
元帅菩萨 ◎ 丰子恺| 053
漫谈鬼神观念的枷锁 ◎ 秦牧| 056
从神案前站起来 ◎ 蓝翎| 061
说鬼 ◎ 李伯元| 067
鬼赞 ◎ 许地山| 069
我们的敌人 ◎ 周作人| 072
花煞 ◎ 周作人| 075
疟鬼 ◎ 周作人| 081
鬼的生长 ◎ 周作人| 083
刘青园《常谈》 ◎ 周作人| 089
说鬼 ◎ 周作人| 095
谈鬼论 ◎ 周作人| 100
失掉的好地狱 ◎ 鲁迅| 108
鬼的箭垛 ◎ 曹聚仁| 110
乡人说鬼 ◎ 老向| 115
鬼学丛谈 ◎ 种因| 120
鬼话连篇 有序 ◎ 李金发| 127
美丽的吊死鬼 ◎ 许钦文| 134
谈鬼者的哀悲 ◎ 陈子展| 138
水母 ◎ 汪曾祺| 141
中国的神统 ◎ 金克木| 147
文艺上的异物 ◎ 周作人| 150
五猖会 ◎ 鲁迅| 154
无常 ◎ 鲁迅| 159
女吊 ◎ 鲁迅| 167
鬼趣图 ◎ 唐弢| 174
论《封神榜》 ◎ 聂绀弩| 176
鬼与狐 ◎ 老舍| 181
画鬼 ◎ 丰子恺| 185
鬼话 ◎ 施蛰存| 193
德国老教授谈鬼 ◎ 陈铨| 197
说鬼 ◎ 林庚| 208
鬼故事 ◎ 邵洵美| 211
略谈莎士比亚作品里的鬼 ◎ 梁实秋| 217
神鬼人 ◎ 柯灵| 221
话中有鬼 ◎ 朱自清| 231
有鬼无害论 ◎ 廖沫沙| 235
怕鬼的雅谑 ◎ 廖沫沙| 239
《鬼趣图》和它的题跋 ◎ 黄苗子| 242
|编辑附记| ◎ 250
|
| 內容試閱:
|
|导 读|
陈平原
一
了解一个民族,不能不了解其鬼神观念。说到底,人生事不就是生与死?生前之事历历在目,不待多言;死后之事则因其神秘莫测、虚无飘渺,强烈地吸引着每一个民族的先民们。鬼之为言归也(《尔雅》)。问题是活蹦乱跳的人,归去后还有没有感觉,还能不能活蹦乱跳,这实在让人放心不下。据说,当子贡向孔子请教死人有知无知时,孔子的回答颇为幽默: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刘向《说苑》)可惜世上如孔子般通达的人实在不多,无事自扰的常人,偏要在生前争论这死后才能解开的谜。
在一般民众心目中,鬼与神是有很大区别的。前者祸害人间,故对之畏惧、逃避,驱赶其出境;后者保佑人间,故对之崇敬、礼拜,祈求其赐福。畏与敬、赶与求本是人类创造神秘异物的两种心理基因,只不过前者坐实为鬼,后者外化为神。这样,鬼、神仿佛有天壤之别,由此引申出来的各种词汇也都带有明显的情感趋向。鬼域与神州不可同日而语;君子必然神明,小人只能鬼黠;说你心怀鬼胎、鬼鬼祟祟,与说你神机妙算、神姿高彻根本不是一回事。只是在强调其非人间或非人力所能为这一点上,鬼、神可以通用。比如鬼工就是神工,神出鬼没与鬼使神差中鬼神不分。至于文化大革命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牛鬼蛇神,更是把鬼神一锅煮了。
也有努力区分鬼、神的哲人,着眼点和思路自然与一般民众不同。汉代的王充以阴阳讲鬼神,称阴气逆物而归,故谓之鬼;阳气导物而生,故谓之神(《论衡》)。宋代的朱熹则赋予鬼、神二名以新义,将其作为屈伸、往来的代名词,全无一点宗教意味:气之方来皆属阳,是神;气之反皆属阴,是鬼。午前是神;午后是鬼。初一以后是神;十六以后是鬼。草木方发生是神;凋落是鬼。人自少至壮是神;衰老是鬼。(《朱子语类》)如此说神鬼,已失却神鬼的本来意义:天下万事万物都是神鬼,神鬼也就没有存在价值了。
我之不想区分神、鬼,并非鉴于哲人的引申太远和民众的界说模糊,而是觉得这样说起来顺些。本来人造鬼神的心理,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根本无法截然分开。说近的,现实生活中多的是以鬼为神或者降神为鬼,鬼、神的界限并非不可逾越。说远的,先秦典籍中鬼神往往并用,并无高低圣俗之分,如《尚书》中的鬼神无常享、《左传》中的鬼神非人实亲、《礼记》中的鬼神之祭,以及《论语》中的敬鬼神而远之等。先秦时代的鬼、神,似乎具有同样的威力,也享受同样的敬畏与祭祀。
再说,详细辨析鬼神观念的发展变化,并加以准确的界定,那是学者的事。至于文人的说神道鬼,尽可不必过分认真,太拘泥于概念的使用。否则,文章可能既无神工也无鬼斧,只剩下一堆大白话。也就是说,如果是科学论文,首先要求立论正确,按照大多数经过科学洗礼的现代人的思路,自然最好是宣传无神论,或者大讲不怕鬼的故事。可作为文艺性的散文,则鬼神不分没关系,有鬼无鬼也在其次,关键在怎么说,不在说什么。只要文章写得漂亮,说有鬼也行,说无鬼也行,都在可读之列。有趣的是,大多数有才气有情趣的散文,不说有鬼,也不说无鬼,而是疑鬼神而亲之在鬼神故事的津津乐道中,不时透出一丝嘲讽的语调。或许,坚持有神鬼者和一心辟神鬼者,都不免火气太盛、教诲意识太强,难得雍容自适的心态,写起散文来自然浮躁了些。
二
周作人在《谈鬼论》中曾经说过,他对于鬼故事有两种立场不同的爱好,一是文艺的,一是历史的(民俗学上的)。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还应加上第三种立场的爱好:现实政治斗争的。从艺术欣赏角度谈鬼、从民俗学角度谈鬼,与从现实斗争角度谈鬼,当然有很大不同。不应该单纯因其角度不同而非此即彼或者扬此抑彼,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对其有所褒贬。只是必须记得,这种褒贬仍然有社会学的、民俗学的和文艺学的差别。
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来说,生活实在太紧张太严肃了,难得有余暇如周作人所吟咏的街头终日听谈鬼。这就难怪周氏《五十自寿诗》一出来,就引起那么多激进青年的愤怒。现实中的神鬼为害正烈,实在没有心思把玩鉴赏。于是,作家们拿起笔来,逢神打神,遇鬼赶鬼。虽说鬼神不可能因此斩尽杀绝,毕竟尽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
后人或许不理解这个时代的作家为什么热衷于把散文写成科普读物,甚至提出了了解鬼是为了消灭鬼这样煞风景的口号,比起苏东坡的姑妄听之,比起周作人的谈狐说鬼寻常事,未免显得太少雅趣。陈独秀的话部分解答了这个问题:吾国鬼神之说素盛,支配全国人心者,当以此种无意识之宗教观念最为有力。(《有鬼论质疑》)致力于社会进步的现代中国作家,不能不请科学来驱鬼即使明知这样做没有多少诗意。是的,推远来看,鬼神之说挺有诗意,有了鬼,宇宙才神秘而富有意义(许钦文《美丽的吊死鬼》)。可当鬼神观念纠缠民心,成为中国发展的巨大障碍时,打鬼势在必行,作家也就无权袖手旁观,更不要说为之袒护了。清末民初的破除迷信、八十年代的清算现代造神运动,都是为了解放人的灵魂。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从人类发展史来看,不也挺有诗意吗当然,落实到每篇文章又是另一回事。
文人天性爱谈鬼,这点毋庸讳言。中国古代文人留下那么多鬼笔记、鬼诗文、鬼小说和鬼戏曲,以至让人一想就手痒。虽说有以鬼自晦、以鬼为戏、以鬼设教之别(刘青园《常谈》),但谈鬼可自娱也可娱人,我想,这一点谁也不否认。李金发慨叹:那儿童时代听起鬼故事来,又惊又爱的心情!已不可复得了,何等可惜啊!(《鬼话连篇》)之所以不可复得,因为接受了现代科学,不再相信神鬼。倘若摒弃鬼神有利于社会进步,那么少点又惊又爱的刺激,也不该有多大抱怨。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世纪的文人尽管不乏喜欢谈鬼说神的,可大都有所克制,或者甚至自愿放弃这一爱好的原因。
三十年代中期,《论语》杂志拟出版鬼故事专号,从征文启事发出到专号正式发排才十五天时间,来稿居然足够编两期,可见文人对鬼的兴趣之大。除周作人此前此后均曾著文论鬼外,像老舍、丰子恺、梁实秋、李金发、施蛰存、曹聚仁、老向、陈铨、林庚、许钦文等,都不是研究鬼的专家,却也都披挂上阵。好多人此后不再谈鬼,很可能不是不再对鬼感兴趣,而是因为鬼神问题在二十世纪中国,基本上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文化问题。要不打鬼,要不闭口,难得有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小品心态。也就三十年代有过这么一次比较潇洒而且富有文化意味的关于鬼的讨论,余者多从政治角度立论。不说各种名目的真真假假的打鬼运动,即使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或讨论一出鬼戏,都可能是一场政治斗争的讯号或标志。这么一来,谈神说鬼成了治国安邦的大事,区区散文家也就毋庸置喙了。勉强要说也可以,可板起面孔布道,笔下未免滞涩了些。
三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的《贾生》诗,曾令多少怀才不遇的文人感慨唏嘘。时至二十世纪,再自命贾生才调更无伦者,也不敢奢望宣室求贤访逐臣了。即便如此,不谈苍生谈鬼神,还是让人胆怯乃至本能地反感。古代文人固然甚多喜欢说鬼者,知名的如苏轼、蒲松龄、纪昀、袁枚等,可据说或者别有怀抱、或者寄托幽愤。今人呢?今人实际上也不例外,都是兼问苍生与鬼神。正当鬼故事专号出版之际,就有人著文捅破这层窗户纸,诉说不谈国事谈鬼事的悲哀,结论是客中无赖姑谈鬼,不觉阴森天地昏(陈子展《谈鬼者的悲哀》)。
茶棚里高悬莫谈国事的告示,可并不禁止白日说鬼;报刊中要求舆论一律,可也不妨偶尔来个鬼话连篇。无权问苍生,只好有闲谈鬼神,这是一种解释;无权直接问苍生,只好有闲假装谈鬼神,这又是一种解释。中国现代作家中无意于苍生者实在太少,故不免常常借鬼神谈苍生。鲁迅笔下发一声反狱的绝叫的地狱里的鬼魂(《失掉的好地狱》),老舍笔下无处无时不令人讨厌的不知死的鬼(《鬼与狐》),周作人笔下附在许多活人身上的野兽与死鬼(《我们的敌人》),还有李伯元笔下的色鬼、赌鬼、酒鬼、鸦片烟鬼(《说鬼》),何尝不是都指向这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清人吴照《题〈鬼趣图〉》早就说过:请君试说阎浮界,到底人多是鬼多?
不管作家意向如何,读者本来就趋向于把鬼话当人话听,把鬼故事当人故事读,故不难品味出文中隐含的影射、讽喻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暗示与引申。即使把一篇纯属娱乐的鬼故事误读成意味深长的政治寓言也不奇怪,因为鬼世界本就是人世间的摹写与讽喻。正如曹聚仁说的:为鬼幻设十殿阎罗,幻设天堂地狱,幻设鬼市鬼城,也是很可哀的;因为这又是以人间作底稿的蜃楼(《鬼的箭垛》)。一般地说,牵涉到人的事情总不大好谈,说鬼还比较稳当(黄苗子《〈鬼趣图〉和它的题跋》)。但也有例外,说鬼可能最安全也可能最危险,因为鬼故事天生语意含糊而且隐含讽刺意味。当社会盛行政治索隐和大众裁决,而作者又没有任何诠释权时,鬼故事便可能绝迹。谁能证明你的创作不是影射现实发泄不满?鬼能证明吗?
还有另外一种说鬼,不能说无关苍生,但确实离现实政治远些,那就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出发,借助鬼神的考察来窥探一个民族的心灵。不同于借鬼神谈苍生,而是谈鬼神中的苍生,或者说研究鬼中的人。这就要求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同情,多一点文化意味和学识修养,而不只是意气用事。周作人说得好: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我不懂什么是二气之良能,但鬼为生人喜惧愿望之投影则当不谬也。(《鬼的生长》)虽说早在公元一世纪,哲学家王充就说过鬼由人心所生之类的话: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论衡》)。但是,王充着眼于破有鬼论,周作人则注重鬼产生的文化心理背景,两者仍有很大差别。在理论上,周作人谈不上什么建树,他所再三引述的西方人类学家茀来则等对此有更为精细的辨析。不过,作为一个学识颇为渊博的散文家,认准鬼后有人,听人说鬼实即等于听其谈心(《鬼的生长》),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钩稽出许多有关鬼的描述,由此也就从一个特定角度了解了中国民族的真心实意。经过周氏整理、分析的诸多鬼故事,以及这些谈论鬼故事的散文小品,确实如其自称的,是极有趣味也极有意义的东西。至于这项工作的目的与途径,周作人有过明确的表述:我们喜欢知道鬼的情状与生活,从文献从风俗上各方面去搜求,为的可以了解一点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鬼里边的人。(《说鬼》)代代相传的辉煌经典,固然蕴藏着一个民族的灵魂;可活跃于民间、不登大雅之堂的鬼神观念及其相关仪式,何尝不也代表一个民族心灵深处的隐秘世界?前者历来为学者所重视,后者在思想史研究上的意义尚未得到普遍的承认。当然,不能指望散文家作出多大的学术贡献,可此类谈神说鬼的散文确实引起人们对鬼神的文化兴趣。借用汪曾祺的话,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民族(《水母》),因此,我们不能撇下鬼神不管。在这方面,散文家似乎仍然大有可为。
四
本世纪初,正当新学之士力主驱神斩鬼之时,林纾翻译了立义遣词,往往托象于神怪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哈葛德的小说。为了说明专言鬼神的文学作品仍有其存在价值,林纾列出两条理由,一为鬼神之说虽野蛮,可野蛮之反面,即为文明。知野蛮流弊之所及,即知文明程度之所及(《〈埃及金塔剖尸记〉译余剩语》);一为政教与文章分开,富国强兵之余,始以余闲用文章家娱悦其心目,虽哈氏、莎氏,思想之旧,神怪之托,而文明之士,坦然不以为病也(《〈吟边燕语〉序》)。用老话说,前者是认识意义,后者为文学价值。
三十年后,梁实秋再说莎士比亚作品里的鬼,可就只肯定鬼是莎氏戏剧中很有用的技巧,而且称莎士比亚若生于现代,他就许不写这些鬼事了(《略谈莎士比亚作品里的鬼》)。或许一般读者还没有真正摆脱鬼神观念的束缚,还很难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客观考察鬼神的产生与发展,故文学作品不宜有太多鬼神。说起古代的鬼诗、鬼画、鬼戏、鬼小说来,作家们大致持赞赏的态度,可一涉及当代创作,则都谨慎得多,不敢随便表态。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有什么妨害呢?这话说得很通达。可别忘了,那是有前提的:前人的戏曲有鬼神,这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没有办法可想。(《有鬼无害论》)也就是说,廖沫沙肯定的也只是改编的旧戏里的鬼神,至于描写现代生活的戏里能否出现鬼神,仍然不敢正面回答。
这里确实不能不考虑中国读者的接受水平。理论上现代戏也不妨出现神鬼,因那只是一种可供选择的艺术技巧,并不代表作家的思想认识水平,更无所谓宣传迷信。可实际上作家很少这么做,因尺度实在不好把握。周作人在谈到中外文学中的僵尸时称,此类精灵信仰,在事实上于文化发展颇有障害,但从艺术上平心静气的看去,我们能够于怪异的传说的里面瞥见人类共通的悲哀或恐怖,不是无意义的事情(《文艺上的异物》)。反过来说,倘若不是用艺术的眼光,不是平心静气地欣赏,鬼神传说仍然可能于文化发展颇有障害。了解二十世纪中国读者的整体文化水平以及中国作家普遍具有的启蒙意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家们对当代创作中的鬼神问题举棋不定、态度暧昧。直到八十年代中期,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至于为什么鬼神并称,而在这个世纪的散文中,却明显地重鬼轻神,想来起码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原因:一是鬼的人情味,一是散文要求的潇洒心态。不再是敬鬼神而远之,民间实际上早就是敬神而驱鬼。现代人对于神,可能崇拜,也可能批判,共同点是走极端,或将其绝对美化,或将其绝对丑化,故神的形象甚少人情味,作家落笔也不免过于严肃。对鬼则不然,可能畏惧,也可能嘲讽,不过因其较多非俗非圣亦俗亦圣的人间味道,故不妨对其调笑戏谑。据说,人死即为鬼,是自然转正,不用申请评选;而死后为神者,则百年未必一遇。可见鬼比神更接近凡世,更多人味。传说里鬼中有人,人中有鬼,有时甚至人鬼不分;作家讲起此类鬼而人、理而情的鬼故事来,虽也有一点超人间的神秘色彩,可毕竟轻松多了。而这种无拘无束的宽松心境,无疑更适合于散文小品的制作。
对于鬼神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作家们虽一再提及,其实并没有认真的研究。老舍也不过说说鬼神可以造成一种恐怖,故意的供给一种人为的哆嗦,好使心中空洞的人有些一想就颤抖的东西神经的冷水浴(《鬼与狐》);而邵洵美分析文学作品中使用鬼故事的五易,则明显带有嘲讽的意味(《鬼故事》)。如果说这个世纪的散文家在研究文艺中的鬼方面有什么值得注意之处的话,一是诸多作家对罗两峰《鬼趣图》的评论,一是鲁迅对目连戏中无常、女吊形象的描述。这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无常》),这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锭,准备作厉鬼以复仇的女吊(《女吊》),借助于鲁迅独特的感受和传神的文笔,强烈地撼动了千百万现代读者的心。这种鬼戏中的人情,很容易为下等人领悟;而罗两峰的《鬼趣图》和诸家题跋,则更多为文人所赏识。现代作家未能在理论上说清鬼诗、鬼画、鬼戏的艺术特色,可对若干以鬼为表现对象的文艺作品的介绍评析,仍值得人们玩味这里有一代文人对鬼神及鬼神文艺潜在而浓厚的兴趣。
一九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