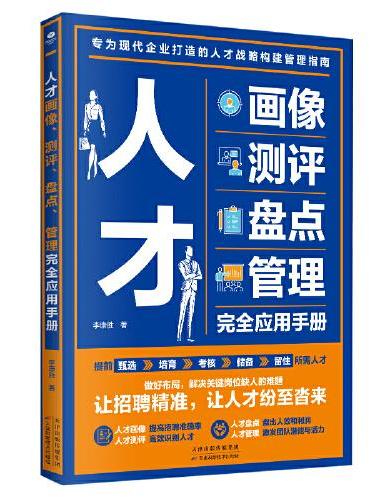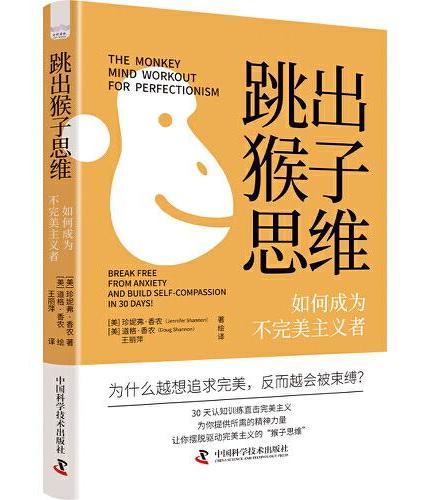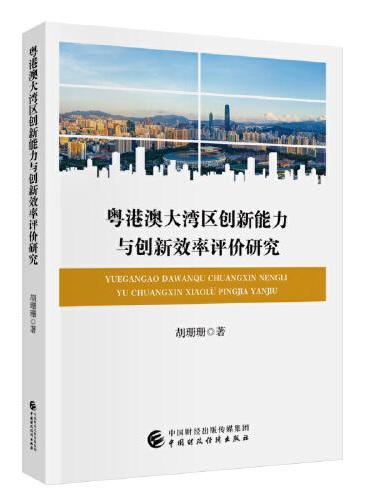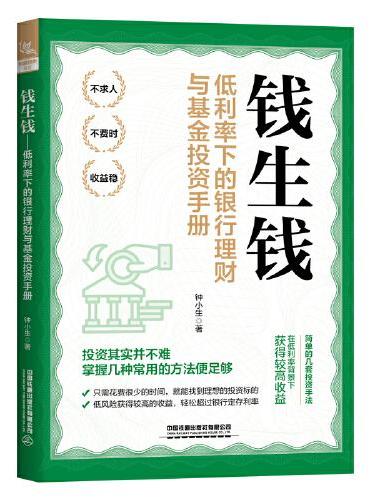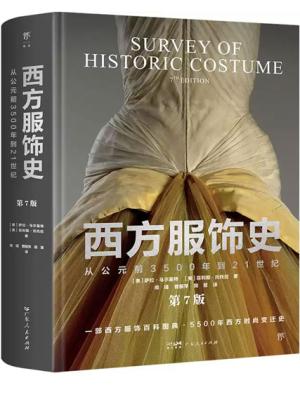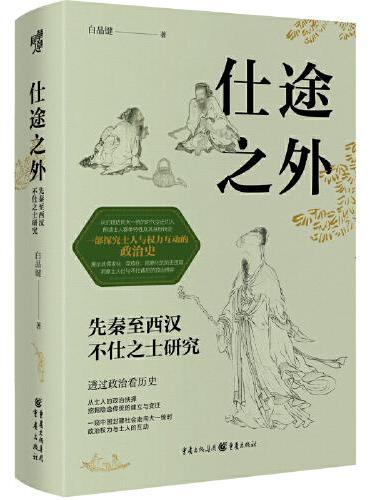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影神图 精装版
》
售價:NT$
653.0

《
不止于判断:判断与决策学的发展史、方法学及判断理论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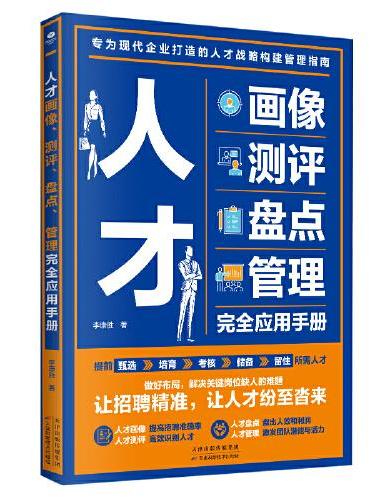
《
人才画像、测评、盘点、管理完全应用手册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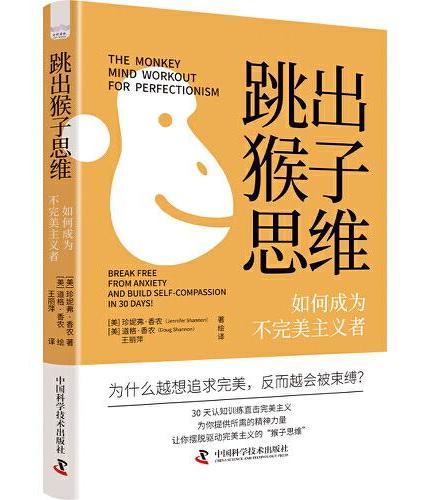
《
跳出猴子思维:如何成为不完美主义者(30天认知训练打破完美主义的困扰!实现从思维到行为的全面改变!)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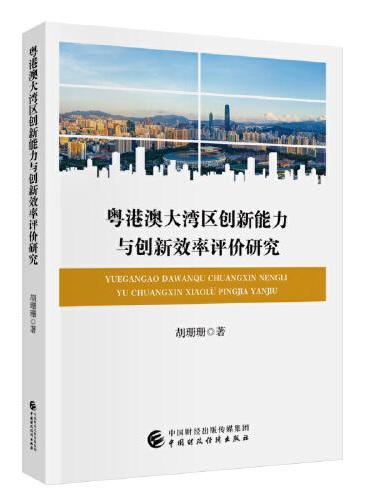
《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能力与创新效率评价研究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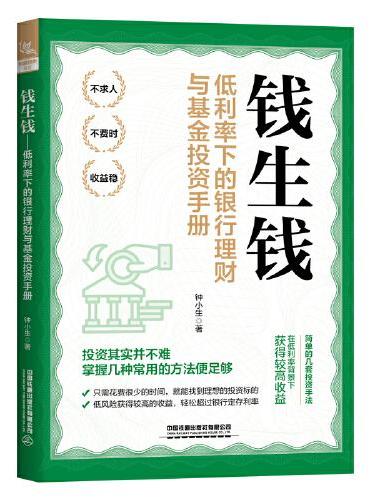
《
钱生钱:低利率下的银行理财与基金投资手册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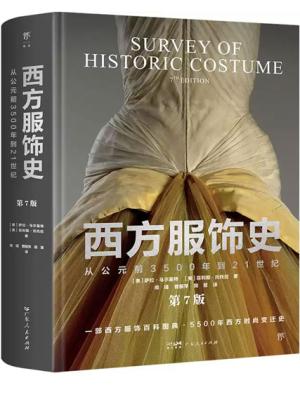
《
西方服饰史:从公元前3500年到21世纪(第7版,一部西方服饰百科图典。5500年时尚变迁史,装帧典雅,收藏珍品)
》
售價:NT$
20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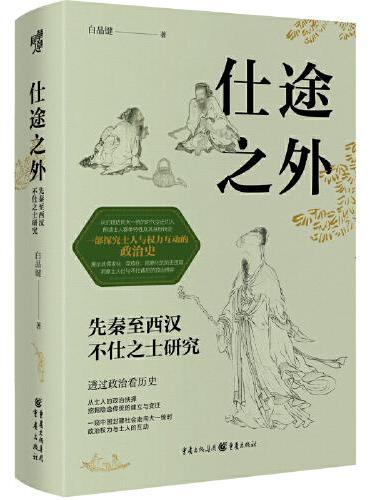
《
仕途之外:先秦至西汉不仕之士研究
》
售價:NT$
305.0
|
| 編輯推薦: |
◎拉丁美洲330年殖民地时期艺术史全景呈现
1492年至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期间的艺术创造是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非洲人、亚洲人、克里奥尔人和欧洲人共同参与、相互适应、不断妥协的成果,这段时期经历了不同文明相遇后的互相审视、帝国的暴政,传教站和教堂等艺术诞生地的辉煌,以及西、葡两国在海外实现了文艺复兴等景象。期间产生的艺术在很多面向上体现了不同种族的文化信仰和审美倾向。对异质又冲突的拉美殖民地时期文化遗产的了解,有助于形成客观审视拉美当下现实的批判性眼光。
◎视角du特、细节丰富,还原拉丁美洲艺术的发生与发展过程
摒除传统上认为欧洲文化塑造了拉美艺术风格的观点,以相遇的视角看待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不同种族艺术家汇聚起来创造艺术的事件。艺术并没有因为创造者的被殖民和改宗而wanquan抹去或覆盖掉其本身的文化信仰,而在很多层面上以一种悄无声息又无孔不入的方式宣告着自我的身份。还原艺术产生的过程,仿佛忽略了惊心动魄、残暴血腥的殖民和奴役过程,但艺术品却始终诚实地诉说着每个参与者的故事,有强势入侵、迂回抵抗、含蓄认同或曲意迎合,甚至是血泪控诉,于是成为不同艺术风格杂糅的复合体,这种文化遗产成
|
| 內容簡介: |
高文亚历山大贝利在本书中采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对殖民地时期的拉丁美洲艺术展开论述,即这是源于一场相遇,而非一次发现,这种视角首先超越了通常的刻板印象,尽可能地给予这段历史不同的参与者以相对平等的话语权,并以此为前提真实地还原殖民地约330 年历史中艺术的发生与发展,因此,殖民地文化的复杂多样性及其中不同角色的各种纠缠博弈在作者笔下得到了相对客观的呈现。
殖民地时期的艺术不仅是被欧洲强势的宗教文化影响和塑造的他者,还是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黑人、亚洲人、克里奥尔人和欧洲人相互适应、共同参与的一个动态过程的呈现,更是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不断坚持又zui终妥协而形成的不拘一格的艺术形式。拉丁美洲du特的地理环境和多样的种族文化丰富了殖民地时期的艺术表达,期间形成的意识形态和艺术风格也作为艺术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继续影响着拉丁美洲jin天的文化生活。
本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层次分明,作者在梳理殖民地时期拉丁美洲艺术发展脉络的同时,也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巨细无遗的拉丁美洲艺术全景图。
|
| 關於作者: |
|
[加] 高文亚历山大贝利(Gauvin Alexander Bailey)|美裔加拿大著名作家、艺术史专家,毕业于多伦多大学,1996 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皇后大学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研究员。
|
| 目錄:
|
引 言
第一章 初次相遇
殖民前的世界与殖民地景象
第二章 审视另一方
土著的反应
第三章 帝国的图像
宣示王权的艺术
第四章 创作艺术
行会和学院
第五章 偶像和祭坛
传教站和乡村教堂
第六章 神圣的辉煌
都市教堂
第七章 城镇和乡村
殖民地贵族的艺术
第八章 海外的文艺复兴
亚洲和非洲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
结 语
附 录
术语表
人物简传
关键日期
延伸阅读
索 引
致 谢
|
| 內容試閱:
|
引 言
今天,拉丁美洲艺术与世界的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紧密。公众关于这一主题的新认知催生了无数的展览、研究与电视纪录片,使得拉丁美洲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比以往更加容易接近。在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本身因为移民和媒体而变得越来越西裔化的国家,人们愈发认为拉丁美洲艺术是自身国族文化的一部分。许多博物馆赶着为这一领域策划和举办展览,比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就于2004 年3 月在曼哈顿的巴里奥博物馆举办了首次拉丁美洲艺术藏品的回顾展。在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法国、荷兰和意大利,书籍与展览反映出人们对于自己国家与美洲过去和现在的艺术联结的新兴趣。这一主题也在英国激起了热情,泰特现代艺术馆在2002 年委任了第一个拉丁美洲艺术策展人,而在日本,秘鲁与巴西的移民遗产引起了公众对于那些地区的好奇心。不过几乎所有这些新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殖民前和现当代的拉丁美洲艺术上。学者和热爱艺术的公众很晚才正视其间更被忽略的时期:即14921820 年前后330 年的殖民地时期。学界之所以不关注殖民地时期,部分原因在于这是一个公认的敏感话题。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抵达美洲(1492 年)至独立抗争时期之间的殖民地艺术背负着帝国与暴政的包袱,以及被占领、流离失所和被迫改宗的耻辱。如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仍旧
将殖民地时期视作屈辱史,以及一种对于他们被殖民前的历史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压迫和专制的陪衬,而全世界的人都不情愿去接受一段与欧洲的集体罪恶相关联的时期。
如果对殖民地时期的拉丁美洲艺术视而不见,我们就会错过一段至少与同时代西欧艺术同样丰富多彩的艺术传统,我们会对一整个半球有着上千万的人口在3 个世纪里富有创造力的艺术产出闭上双眼。创造并使用这些艺术和建筑的人民社会背景极其多样化。他们中有非洲人、亚洲人和梅斯蒂索人(混血民族),以及来自西班牙、意大利和波希米亚等地的欧洲人。他们中还有生活在美洲的土著人不止有阿兹特克人、印加人和玛雅人的后代,还有普韦布洛人、艾马拉人、瓜拉尼人和维利切人等组成的各种部落。他们当中有农民和总督、司铎和士兵、修女和侯爵。殖民地时期的拉丁美洲是当时世界上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与今天的全球共同体惊人地相似。
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关注殖民地时期的拉丁美洲文化,我们还会忽略一段为现代拉丁美洲奠定基础的历史。正如阿尔韦托希纳斯特拉或曼努埃尔庞塞这些20 世纪的作曲家借鉴殖民地时期的民谣旋律为现代阿根廷和墨西哥创作出了乐音一样,从弗里达卡罗(19071954年)到费尔南多博特罗(Fernando Botero,1932)的艺术家们根据殖民地时期的文化对现代拉丁美洲的视觉特性进行了各种探索。也许殖民地时期艺术连续性的最佳例证就是16 世纪的墨西哥画作《瓜达卢佩圣母》(Virgin of Guadalupe,图1),在这幅文艺复兴后期风格的精美画像中,圣母(Virgin of the Apocalypse)有着神秘的灰紫色皮肤,因此世代的墨西哥人将她视为自己种族的一员,无论是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还是克里奥尔人(生于美洲的欧洲人)。这幅画从中世纪对《启示录》中一个段落的阐释派生而来,玛利亚是耶路撒冷和巴比伦之间永恒战争的主要人物,她出现的时候身披阳光,脚踩半月,头戴星冠。这件今天最为著名的殖民地时期的拉丁美洲艺术品,受到过奇卡诺(Chicano)劳工活动分子、女权主义艺术家、超自然爱好者以及保守的天主教徒群体各色人等的拥戴。在洛杉矶它以壁画形式出现(图242),在利马和波哥大它被嵌入树脂钥匙链,它也是互联网上的热议话题。2002 年,由于教皇若望保禄二世(1978 年)将胡安迭戈夸特拉托阿特钦(JuanDiego Cuauhtlatoatzin,据说是他于1531 年在自己的斗篷里发现了这幅画)封圣,这幅画才重见天日。胡安迭戈,持圣母像者,由此成为天主教会的首个印第安圣人尽管有许多人论辩说他其实从未存在过。瓜达卢佩圣母是拉丁美洲身份认同的核心,她体现了殖民地时期异质又冲突的遗产。这一遗产是今日拉丁美洲政治、宗教、文化和民族主义的核心,忽略殖民地时期的历史就意味着失去洞察当下的批判性眼光。
过去一直没有什么适合的时机去重新评估殖民地时期的拉丁美洲艺术。直到最近,任何关于西班牙与葡萄牙探索发现、征服与殖民的讨论都还强烈地偏向欧洲的殖民者,并赞美他们借由习俗、宗教和建筑为土著人带来了文明。传统历史强调个人崇拜,将探险者和征服者们描述为超级英雄尽管有着贪婪和虚荣的缺点并且将他们的探索视作欧洲显而易见的天命。其中最著名的英雄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被南北美洲、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人民当作民族主义的捍卫者崇敬了一个多世纪,并得到地名、雕像和节日等各种形式的纪念。埃尔南科尔特斯,墨西哥的征服者(1521 年,图86),也受到那些为欧洲文化传播到全世界而欢呼的人们的崇敬。这一关于探索和征服的大英雄概念有着古老的传承。早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就沉浸于骑士与国王冒险的幻想之中反骑士小说《堂吉诃德》的作者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在玻利维亚谋求职位就显得恰如其分了而来自虚张声势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者们的报告也给人以同样引人入胜的阅读体验,以至于在看待美洲其他居民的时候,我们的双眼都被蒙蔽了。通过屏蔽印第安人的声音,他们将一大部分人口他们在殖民地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占多数转变为欧洲文化的被动接受者。结果就是我们倾向于将殖民地时期与殖民前完全割裂,同时用欧洲文化擦净了写字板。这一史学思想构建出一种倾向,即将相遇过分简单化,仿佛欧洲人和印第安人代表着团结而同质的两部分比起史实倒更像是中世纪的寓言故事。传统上就欧洲对美洲贡献的关注同样不利于拉丁美洲殖民地时期的艺术史研究。直到现在,大多数人还认为殖民地文化纯粹起源于伊比利亚,那里的艺术仅仅是西葡模板恶劣的地方变体。
1992年的哥伦布首航美洲500 周年纪念活动给了人们重新审视哥伦布遗产的机会,哪怕不否认它的重要性,他们如今也能够讨论一场相遇而非一次发现了,即能够把非欧洲人对于殖民地时期拉丁美洲文化的贡献放到一个更为客观的位置上,并将其与欧洲殖民者相提并论。尽管活动突出了这一历史时刻为美洲土著人带来的惊人的艰难险阻与变革,但它也同样揭示了征服后的历史中繁荣发展的土著文明的存在以及它们自己的艺术传统,活动也展示了这些文明对殖民地文化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成为对白板论(Clean Slate)的有力挑战。2000年的葡萄牙人登陆巴西500 周年纪念和20012002 年在纽约与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及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所举办的巴西展,给予全世界一个相似的机会去反思欧洲与拉丁美洲最大国家的相遇。巴西纪念活动的一个特别贡献,就是重新唤醒人们去关注殖民地时期被运往巴西的数百万黑奴所遭遇的困境,并将他们在巴西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留下的大量文化遗产视作一个整体。多亏这一对于巴西黑人文化的新认识,学者和公众如今都更偏向于将拉丁美洲殖民地时期的文化视作一条三向马路(印第安人、非洲人、欧洲人)。这些纪念活动启发我们以新的角度去看待殖民地时期拉丁美洲的艺术。通过承认印第安人、非洲人和其他非欧洲人对殖民地时期拉丁美洲艺术的贡献无论是符号还是装饰细节,风格还是技艺,抑或是他们与非欧洲信仰和世界观的联系我们才得以更好地认清它的财富。
殖民地时期拉丁美洲的独特不只因为文化多样性,自然景观和地理状况的复杂多样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地方能提供与拉丁美洲同样多的地理类型。这一个半大洲,从火地岛延伸到加利福尼亚,包含着荒无人烟的山地高原和繁茂的低地雨林,包含着贫瘠、阳光炙热的沿海荒漠和肥沃起伏的草原,以及冰川峡湾和奔腾的热带河流。这种气候上的极端导致了无数风格与结构上的变体。危地马拉和秘鲁沿岸的抗震教堂使用厚墙和轻质材料制成的拱顶来防范地震(图167);在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低地的雨林里,传教团的住所有着宽宽的遮檐以保护居住者不受热带暴雨的伤害(图122);在智利南方的奇洛埃群岛上,质朴的木教堂以小窗抵挡寒冷的天气,它们与新英格兰的礼拜堂相似,又与北欧式的环境(图143)相契合。材料的供应情况在巴西北部的热带地区和新墨西哥的荒漠区十分不同,这也决定了教堂或雕像是用石头、黏土还是木头做成,以及画家们会在画布上用什么颜色,乃至他们到底能不能用画布等艺术品或建筑载体的选择与确立。在墨西哥,建筑师利用大量的青铜和一种名为特松特雷(tezontle)的粉色多孔火山岩为教堂立面赋予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微妙质感和丰富色彩(图158);在巴西,蓝花楹这种本地出产的硬木为殖民地时期的雕塑赋予了深邃的光泽与弹性,比葡萄牙使用的松木和雪松木更富有美感,并奢华得多(图181);在秘鲁,土著织工采用本地出产的天然染料来制作鲜艳美丽的挂毯和披肩(图49)。通过将本地景观或动植物在装饰中呈现出来,殖民地时期拉丁美洲的艺术也更加直接地反映了当地的自然风光,因此玻利维亚高地建筑门窗周围的雕塑装饰中会有玉米或木瓜植株的头,巴拉圭的祭坛画会把西番莲的形态融入装饰卷轴中,而秘鲁库斯科和厄瓜多尔基多的圣经场景画里则有美洲狮和豚鼠点缀风景(图48)。
最重要的是,殖民地时期拉丁美洲的艺术是人类创造力的明证,无关种族、民族或是出生地。不可否认,在殖民地时期拉丁美洲艺术的一些装饰图形、符号和技巧中可以找到印第安、非洲或欧洲的形式,但对于将这些形式特征联系到艺术家所属的特定民族或种族背景上,人们已经投入了太多的精力,以至于艺术家的作品被降格成了人类学工艺品。这种用种族或文化来定义的艺术文化始于19 世纪的信仰,即一个民族的人都有着同样的艺术意志,而不同的种族有着与生俱来的不同能力,随着20 世纪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些理论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殖民地时期拉丁美洲艺术的历史与这种信仰相矛盾其中尽是由克里奥尔艺术家采用土著图形创作的绘画、巴西教堂里由来自里斯本的雕塑家创作的黑人圣徒像,或是由印第安石匠设计并建造的粉刷完美的晚期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教堂立面。我们还能看到许多有着印第安、非洲和欧洲特征的作品,而我们知道它们的作者是梅斯蒂索人。正是这种风格、技巧与意象(代表了一个文明或宗教十分重要的思想的图形)的融合令拉丁美洲艺术独特而迷人,而它应该被用来警示那些过分根据种族或是祖籍来进行艺术分类的人。
美洲培养了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和建筑师,他们为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式的艺术品类型创造了独特的变体,这些变体有着空前的构思与惊人的美感。18 世纪的非裔巴西雕塑家和建筑师阿莱雅迪尼奥(约
173017381814 年,又名安东尼奥弗朗西斯科利斯博阿)就是如此,作为国际化的洛可可风格的最后一位伟大雕塑家,他作品中粗暴的痛苦表达出一种发自肺腑又有人情味的哀婉之美(图182、183)。在17世纪早期的秘鲁,安第斯印第安画家迭戈基斯佩蒂托(16111681年)将超自然的辉光与偶尔闪现的印加意象相结合,创作出了缥缈的风景画(图176)。普雷佩查印第安人胡安巴普蒂斯塔奎里斯(JuanBaptista Cuiris,活跃于15501580 年)的羽毛画高明地融合阿兹特克的技巧与欧洲题材,创作出了精致而明快的圣人像,在文艺复兴堂皇的宫殿里广受赞誉。这些艺术家都没有欧洲血统,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天赋来自他们的他性。你也可以列举出许多具有欧洲背景的天才艺术家,比如16 世纪的意大利裔秘鲁画家马泰奥达莱乔(15471616 年,图174),他是最后一位给因米开朗琪罗而著名的西斯廷教堂创作湿壁画的艺术家。莱乔在利马幸运地创建了一所兴旺的本地壁画学校。这也同样适用于克里奥尔晚期巴洛克风格画家克里斯托瓦尔德比利亚尔潘
多(约16491714 年),他是18 世纪新西班牙(如今的墨西哥)奢华世界最活跃的人物之一。比利亚尔潘多在普埃布拉(图178)和墨西哥城的主教座堂内创作的巨大的油画与壁画采用了一种受威尼斯绘画启发的微光技法,早于戈雅(17461828 年)和透纳(17751851 年)的技法革命,后两者由于松散而心血来潮的技巧实验受到称颂。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甚至无法奢求了解艺术家的种族或民族。殖民地时期拉丁美洲艺术家中的大多数,无论是欧洲人、印第安人还是非洲人,都会永远保持逸名的状态。大多数在巴塔哥尼亚至加利福尼亚之间土地上工作的雕刻师、画师和建筑者将他们的任务视作集体任务,并且习惯于从不署名。
图像和建筑自从美洲被征服以来便一直是殖民地时期拉丁美洲的核心艺术形式,即便是最基础的教堂也需要宗教画。它们对于改宗大业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15121513 年的《布尔戈斯法》(Laws ofBurgos;又名《印第安人处置法》译者注)规定,殖民地地主不仅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为土著社群提供一座教堂和一座钟,而且一定要配备圣母的画像。传教士与殖民者都相信图像会行使神迹,无论是转变印第安人的信仰还是保护殖民者。这一对于图画的热忱与文艺复兴时期和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关系不大,而与中世纪欧洲认为神像代表了所指主体存在的信念有关。一幅受到敬拜的圣母像不只是圣人的画像,还是她存在的延伸。当图像被复制以后,复制品就无限地延伸了她的存在。
事实上,圣母成了西班牙征服者的一种胜利象征。埃尔南科尔特斯航行到墨西哥的时候带着一箱子的圣母像。他进入陷落的阿兹特克城市的时候带着一个别名征服者(La Conquistadora)的圣母横幅,这一传统后来被征服者和传教士从阿根廷带到了新墨西哥。他们的印第安对手对于带有圣像的征服者的力量实在太过敏感,他们经常把袭击和亵渎圣像当作击败传教士或诅咒殖民者的方式。有些做法甚至更加激进。在巴拉圭的偏远地区,17 世纪的宗教领袖圭拉维拉甚至建起假教堂和反传教堂,他在那些地方用祭坛和木薯糕圣饼(用一种热带植物的果肉制成)施行假弥撒,还利用瓜拉尼宗教的技巧,即通过装扮成对方的样子来俘获敌人。
从另一方面来说,印第安人与非裔美洲人依靠他们自己对于画像力量的传统信念,从他们为教堂与房屋雕刻和绘制的圣人那里得到了安慰、力量与认同感,尽管他们使用的图像来源于欧洲的宗教。巴拉圭的瓜拉尼雕塑师称自己为圣徒制造者,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天生看得见神迹的人才能制作圣人的雕像,图像之后会成为神明的延伸,无论是基督教的神明还是土著的神明(图113)。非欧洲裔常常按自己的长相来处理圣人的脸部特征和肤色,比如维利切雕刻师制作的奇洛埃的圣人像有着高高的颧骨和强健的上半身。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相信,许多印第安人之所以专注于基督受难的图像是将其作为自身在殖民枷锁下所受苦难的隐喻。土著人加入前基督教时代他们信仰的装饰图形与符号,为作品在视觉上提供了一抹与他们自身精神世界相关的色彩(见第二章)。然而,其中一些土著特征,是欧洲传教士为了让基督教的形象更易于被教堂会众接受才加进来的。
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艺术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渗透得有多深远。在博物馆整洁的环境里或书中的配图上见到这些雕塑、画作及其他物品时,我们通常会忘记它们的社会与宗教背景。它们最初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无论是作为教堂或房屋的装饰,还是男人女人的私人饰品,它们被固定在祭坛画上并悬挂于墙面上,或是在游行或旅途中被带着到处走。人们在圣人的雕像或画像前礼拜与冥想,抚摸它们或给它们涂膏,抑或给它们穿上服饰,配上金冠或银色边框。人们把绣花布料穿上身或者用绣花布料装点家或祭坛;他们用陶瓷容器吃饭,用银具装扮圣体,给晚餐客人留下好印象或者为他们在矿井里照路。一个圣人像通常被作为社群认同的有力象征,就像现代旗帜或纹章一般,当雕像或画像脱离了背景,它与一个地方的基本联结就不可避免地丧失了。脑中没有这些最初的联系,我们就永远也无法完整地理解一件殖民地时期拉丁美洲的艺术品。
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最早的建筑和艺术品反映了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艺术风格。它们非常不同,因为各个国家的艺术风格并不单一,其中还包括哥特风格。在这种国际化的中世纪风格里,建筑有着典型的肋拱顶、尖拱和精美的花窗,雕塑和绘画带有少许显著的现实主义色彩和明亮丰富的着色。佛兰德曾是晚期哥特文化的中心之一,而且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影响尤其深远。另一种可以在殖民地时期拉丁美洲早期建筑中见到的风格被称作银匠风格,是一种平坦的建筑装饰风格,16世纪上半叶在西班牙得到发展,通常由繁杂精细的花形装饰组成。在美洲最早的教堂圣多明各的主教座堂(图2)里,哥特风格和银匠风格结伴出现。
主教座堂由一队西班牙建筑师和石匠建于1512 年,里边有哥特式肋拱顶,而立面的装饰细节则是典型的银匠风格这一对比源于参与建造工作的两代石匠的不同风格。拉丁美洲殖民地时期的艺术受到1492 年之前西班牙的伊斯兰艺术流派的深刻影响。7111492 年,西班牙的很多地方都被来自叙利亚和北非的穆斯林征服者统治,他们在科尔多瓦与格拉纳达的南部建立了强大的王朝,从此便将他们的文化传遍伊比利亚半岛。这种所谓的穆德哈尔风格以镶嵌的木头和珍珠母上极其复杂的几何图形为特征。尤卡坦、基多和利马的木匠都很擅长穆德哈尔风格的天花板,我们在16 和17 世纪早期的教堂里仍能见到(图165)。两个大洲的木匠都将穆德哈尔风格的技巧用在了箱子、书桌和圣经架上(图19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