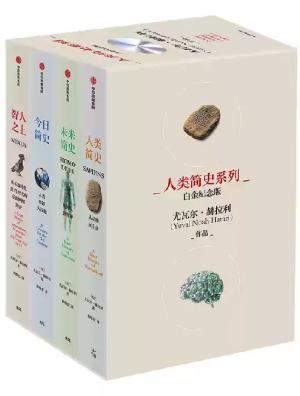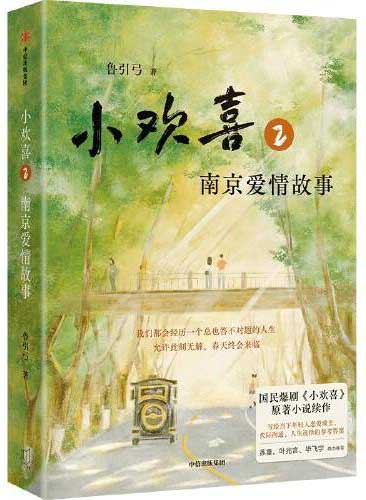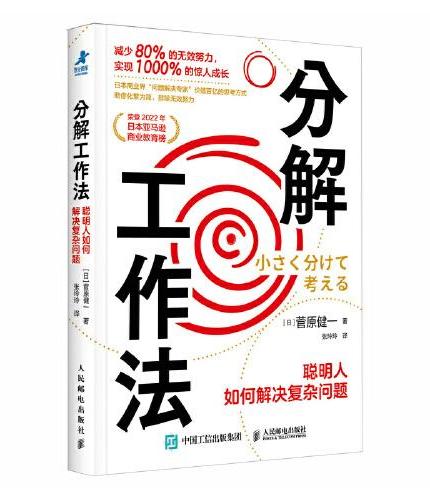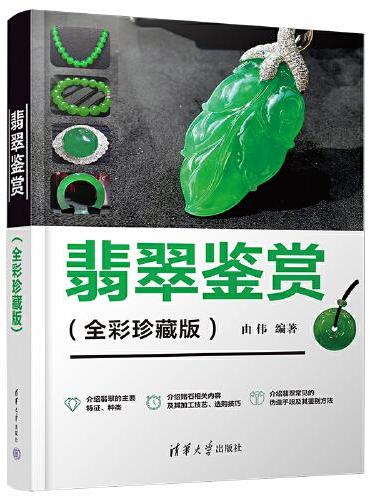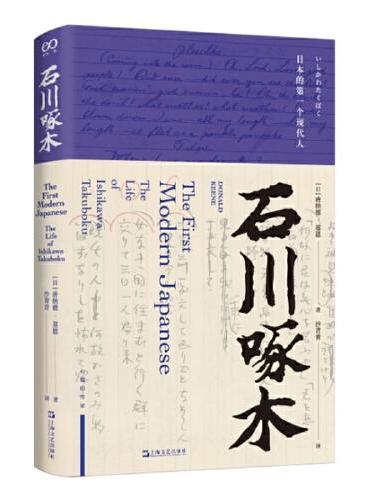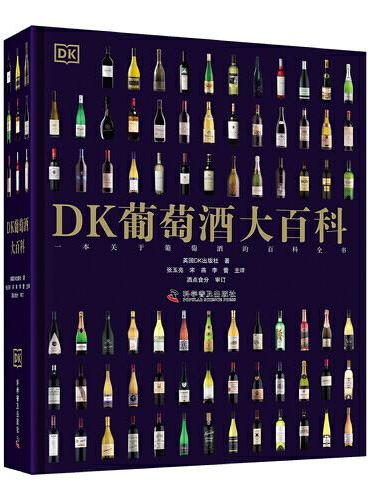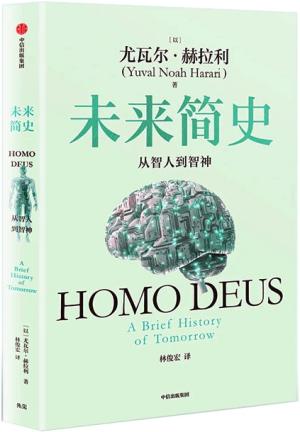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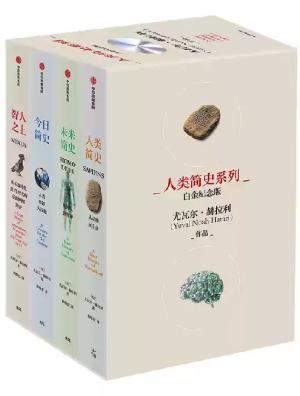
《
人类简史系列(白金纪念版)(套装共4册)
》
售價:NT$
1612.0

《
深度学习推荐系统2.0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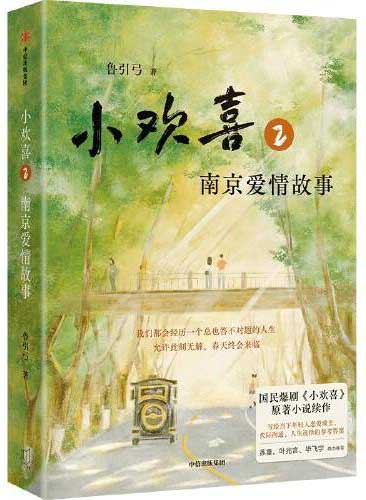
《
小欢喜2:南京爱情故事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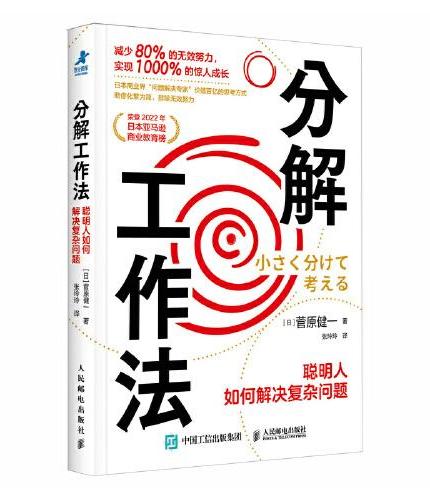
《
分解工作法:聪明人如何解决复杂问题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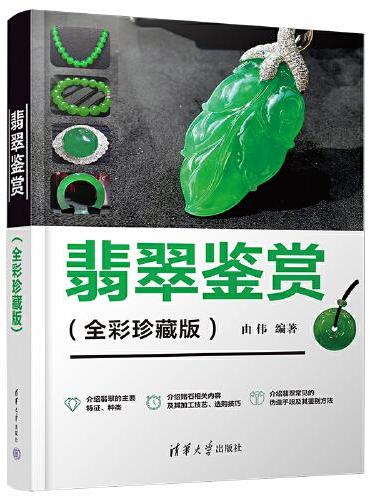
《
翡翠鉴赏(全彩珍藏版)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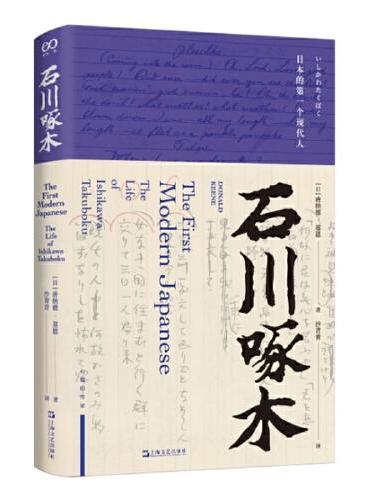
《
艺文志·石川啄木:日本的第一个现代人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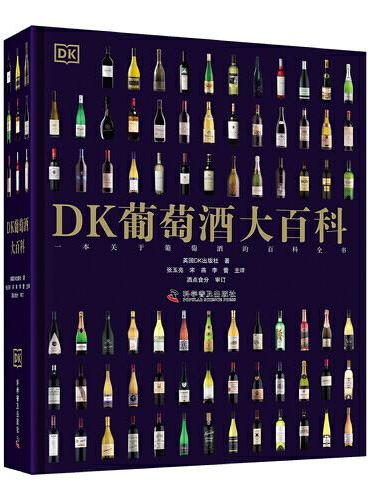
《
DK葡萄酒大百科:一本关于葡萄酒的百科全书
》
售價:NT$
25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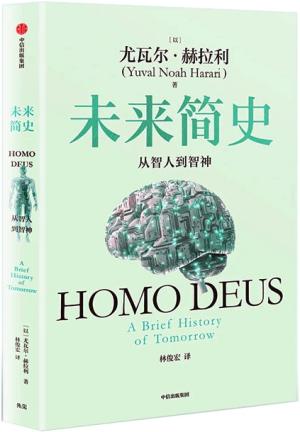
《
未来简史 从智人到智神(2025白金纪念版)
》
售價:NT$
403.0
|
| 編輯推薦: |
|
《弱者的武器》是一部卓越的农民运动研究著作,斯科特以其出色的工作展示了农民反抗外来侵犯的全貌,是对反抗霸权的日常形式的精彩理论和经验阐释。任何想要了解东南亚农民社会的人都不能错过此书。
|
| 內容簡介: |
|
《弱者的武器》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
| 關於作者: |
|
詹姆斯C.斯科特(1936 ),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和人类学斯特林教授、农业研究计划主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其研究兴趣包括政治经济学、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农民政治学、革命、东南亚和阶级关系等。主要著作包括《马来西亚的政治意识形态》(1968)、《比较政治腐败》(1972)、《农民的道义经济学》(1976)、《弱者的武器》(1986)、《统治与抵抗的艺术》(1992)等。
|
| 目錄:
|
前言
第一章 阶级战争中的短兵相接
拉扎克
哈吉布鲁姆
权力的象征性平衡
第二章 常规的剥削,常规的反抗
未被书写的反抗史
作为思想和象征的反抗
人类行动者的经验与意识
第三章 反抗的景观
背景:马来西亚和水稻主产区
中层背景:吉打州和穆达地区的灌溉系统
第四章 塞达卡:从1967年到1979年
村庄
富与穷
村庄构成
土地占有与使用
租佃的变化
水稻生产的变化和工资的变化
地方机构和经济权力
第五章 胜利者和失败者眼中的历史
分类
夜行船
绿色革命的阶级史
双耕与双重看法
从活租到死租
联合收割机
失去的地盘:土地的获得
慈善的仪式与社会控制
记忆中的村庄
第六章 延展事实:意识形态的运作
特定情境中的意识形态运作
剥削的词汇表
歪曲事实:分层与收入
合理化的剥削
意识形态冲突:村庄大门
意识形态冲突:村庄改进计划
作为反抗的争论
第七章 超越口舌之战:谨慎反抗与适度遵从
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障碍
抵制联合收割机的努力
常规的反抗
常规的镇压
常规的顺从与不留痕迹的反抗
服从以及部分的文本
何谓反抗?
第八章 霸权与意识:
意识形态斗争的日常形式
塞达卡的物质基础和规范性上层建筑
重新思考霸权概念
附录
附录A 村庄人口记录,19671979
附录B 不同土地使用类型/农场规模的农场收入比较(穆达地区,1966、1974和1979年)
附录C 关于土地使用情况变更、净利润及政治事务的数据
附录D 飞翔信的译文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阶级战争中的短兵相接
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主张道德是人类选择和意志的某种自治领域,独立地出现在历史过程之中。这样一种关于道德的观点从来就不够唯物主义,它通常将强大的惯性有时是强大的革命性力量简化为一个充满希望的理想主义的虚构。这就是说,与之相反,每一种矛盾都既是价值的冲突,也是利益的冲突;每一种需求在它成为应然的过程中,都含有情感和要求(反之亦然);每一种阶级斗争同时也是关于价值观的斗争。
E.P.汤普森:《理论的贫困》
拉扎克
这是一个种植水稻的小村庄,作为村庄通道的那条狭窄的小路在那个早晨显得比平时繁忙。成群的妇女正赶着去插秧,男人们则骑自行车载着他们的孩子去邻近的凯帕拉巴斯塔镇上的学校上早课。我的孩子们像往常一样围在窗边观望,而每一个路过的人也同样注视着我们,从我住的房子进入他们的视野直到从其视野中消失。这一情景在几个星期内成为每日的仪式。塞达卡的村民正在满足对生活在他们当中的陌生家庭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我的孩子们也在满足一种更为不怀好意的好奇心。他们开始温和地抱怨自己如同缸里的金鱼一样的处境,而且确信迟早有人会因探头观望而不留神走进或骑进路旁的沟渠。这种喜剧般的可能性引起了他们的想象,当它不可避免地发生时,他们希望亲眼目睹。
但事情似乎有点不对头。一小群人静静地站在隔壁的房子前面,一些过路的人停下来和他们交谈。哈姆扎、他的哥哥拉扎克和嫂子阿齐扎,还有村里的产婆托沙赫比丹都来了。他们说话的语调压抑而低沉,时断时续。往常这个时候,阿齐扎已经和其他贫穷人家的妇女与她的插秧组一起出发去工作了。在我准备离开前,和我同住这栋房屋的富有地主哈吉卡迪尔走进来告诉我所发生的一切,拉扎克两个季前出生的小孩死了,这是她的命,她运气不好。
情况简单明了:两天前,小孩发烧病倒了。在吉打州,发烧在旱季的末期是常见的,但是这一次看起来要比通常的发烧严重,有人认为也许是麻疹。昨天她被送到勒拜萨卜拉尼那里,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布道者和传统的治病术士,住在邻近的双溪通港村。他为孩子诵读《古兰经》中的诗篇,并在她的额头上敷了膏药。拉扎克后来告诉我,我才知道自己也牵涉其中。如果我不去访问另一个村庄,他就会请我开车把孩子送到州府亚罗士打的诊所或医院。因为我不在,他才去求沙姆苏尔,沙姆苏尔是村里除我之外唯一有车的人,沙姆苏尔告诉他需要15马元的油钱。拉扎克身无分文,我猜想,他对医院也没有足够的信任。而他的女儿在第二天的黎明前就夭折了。
我本能地走向拉扎克的住处,它位于哈姆扎家房屋的后面,尸体通常要在那停放。拉扎克叫住了我:她不在这儿,我们把她放在哈姆扎家,那里比这好。他的尴尬可以从他避开我的目光中显现出来。
拉扎克是村里的贫困户,他的房子不仅仅对他而言是一种尴尬,对大多数塞达卡人来说也是一种集体的耻辱。我到达村庄的时候,拉扎克和他的家人可以说是住在房子下面,而不是房子里面。两面竹木墙已经倾斜,大部分的屋顶也已经坍塌。村里人嘲笑说:他们像小鸡住在鸡窝里一样,房子是单坡屋顶,和马来人的不一样。不久以后,执政党的当地领导人巴塞尔了解到拉扎克加入了他所在的党派,而且对他来说,村里任何马来人像畜牲一样露宿是非常尴尬的,于是他让村长从他可支配的资金中拿出适当的钱购买木材来修复这房子。一小群全部来自执政党的志愿工作者修好了房子的三面墙,留下最后一面墙和屋顶让拉扎克来完成。毕竟,拉扎克和阿齐扎得在那屋顶下生活。然而,屋顶依然如故,而且用来修最后一面墙的木板也不见了,拉扎克把它们卖了两次一次是卖给罗吉娅,另一次卖给了卡米勒,但只有卡米勒得到了木材;罗吉娅把拉扎克称做老骗子,还说他连自己的孩子也会卖掉。她发誓说她再也不会从他那买任何东西,除非她先拿到货。
当我爬上梯子进入哈姆扎家时,我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进入他家人生活起居的房间。此前我从未进过拉扎克的家或村里其他最贫穷的6户人家。他们总是在屋外接待我,我们要么蹲着,要么坐在简陋的长凳上。我们之所以留在外面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房屋的状况感到尴尬,而且实际上进屋意味着有一定的款待(如咖啡和小点心),那将使他们原本匮乏的生活更为紧张。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尽量在公共场合去见他们,比如,在稻田里、路上、村里两个小店中的某一个或者每周两次在市场旁边相见。在这些地方,我可以合理地扮演主人的角色。对村里的富人来说,这从来不是问题;他们从来不进穷人的家。拜访总是沿着地位阶梯向上进行的,只有地位相等的除外,尤其是在穆斯林斋月结束后的仪式性访问中。事实上,访问模式服务于确定村庄的地位等级。这种模式只有在穷人家发生严重疾病和死亡的情况时才会破例,这时,待客的通常规则暂时停止,以表达对更普遍的人生礼仪的尊重。
这就是玛兹娜(拉扎克的女儿)的夭折使得哈姆扎的家门得以向我和其他人开放的原因。女孩躺在小床垫上,被从房椽上垂下的蚊帐包围着。她的身体裹在一块新白布里,她的小脸由于被那种妇女祈祷时所戴的花边头巾覆盖,几乎看不见了。在蚊帐旁边燃着一炷香,放着一个锡盘。每一个新来的访问者在掀开蚊帐看一眼女孩后,都会在盘子里放点钱,少则5角,多则2马元。这笔捐款将用做葬礼的开支,称为救急款或紧急捐助,由于拉扎克和其他许多非常贫穷的村民都未参加能够支付丧葬费用的死亡抚恤金会,这些捐助就尤为必要。一天下来,盘子里的钱至少可以支付最小的礼仪费用。
大约25个村民,大部分是女人,坐在这间破屋的地板上轻声地相互交谈着。几个男人自己聚在一起交谈,但大多数迅速离开加入到屋外的其他男人中。坐在地板上的拉扎克被忽视了,但是他被孤立并非表达对他个人悲痛的一种集体尊重。在筵席上,在其他葬礼上,在村庄的店铺中,甚至在市场的货摊上,其他男人总是与拉扎克保持一定距离。他无法使自己加入其中,即使他女儿的死亡也不例外;那些起身离开的男人们从他身边不慌不忙地走过,好像他只是一件家具。当他被提起的时候,人们的语调是明白无误的。有时,一群男人坐在村子的一家店铺中边喝冷饮边抽烟,看见他来了,人们会以敦拉扎克来了作为招呼,随之而来的是周围心照不宣的笑声。敦拉扎克是马来西亚第二总理的贵族头衔,这一称谓用在这个贫贱的、虚弱的、谄媚的最下等村民身上是要说明他的地位。那天如果谁做东谁就会付他的饮料钱,而拉扎克则吸着自己用烟草和切碎的聂柏榈叶做成的农民式香烟。他被给予了最低程度的礼遇,但在其他方面被忽略了,就像今天村民在埋葬他的女儿,而他本人最好还是被视而不见。
直接穿过村中的小路,在集中了村庄会所、伊斯兰学校和祈祷场所的建筑外面,几个年轻人开始丈量他们收集来的不多的木板,准备做一具棺材。雅各布觉得木板太长了,于是村长的儿子达乌德被派回哈姆扎家拿绳子去丈量。这时,巴塞尔带来了热茶和用来垫在棺材下面的特制帆布。如同经常发生在咖啡店里的一样,话题变成了有关拉扎克的许多可笑的故事的交流,这当中大部分构成了村里流言蜚语的来源。阿明讲了最近的与政府资助的房屋改造和建设永久性室外厕所有关的分期付款的事情。拉扎克连同其他执政党的成员(只有他们)是一种瓷制抽水马桶的受益者。尽管已经被明确告知这一物资不许买卖,拉扎克还是拿它和阿明的塑料马桶进行了交换,并换回一些现金,而后又将塑料马桶以15马元的价钱卖给了诺尔。雅各布开玩笑地问道,拉扎克甚至连房子都没有,为什么要建一个厕所呢?
雅各布接着问有没有其他人看见拉扎克两天前在罗吉娅女儿的婚宴上大口猛吃咖哩饭,而这场筵席并没有邀请他。沙赫侬补充道,就在昨天,当拉扎克来到集市的咖啡店时,他请拉扎克喝咖啡,这意味着由沙赫侬买单。接下来他注意到拉扎克不但喝了咖啡,还带走了三块蛋糕和两支香烟。部分由于我的提醒,其他一些人回忆起拉扎克是如何从卡米勒那里拿到买屋顶木材的钱而不交货,以及卡米勒是如何把买特种稻种的现金付给他,因为拉扎克说他可以从邻村的一个朋友那儿拿到这些种子。可一个星期以后,他说他朋友和种子都不在家里。又过了一个星期,他说他朋友已经把种子卖了。而这笔钱却从未退还。在不同的场合,人们还说到拉扎克经常以播种的名义讨要稻种,以养家糊口为由要饭,而每一次村民的施舍都被他换成了现金,既没有耕种也没有吃掉。加扎利指责他未经允许私自使用他房屋后面的聂柏树做房顶,而且甚至在收割季之前,他就开始讨要伊斯兰教每年一次的稻谷施舍(扎卡特)。在许多人不停地摇头时,他补充道,我发脾气了。
当富人们不断地抱怨他们所雇用的田间劳力变得越来越懒惰和独立的时候,拉扎克总是现成的例子。尽管他们也有其他的例证,但拉扎克到目前为止是最适用的。他们说有许多次,拉扎克提前拿了工资(现金或稻米的形式)却不出来工作。对于他的贫穷他们心存怀疑,毕竟他有半里郎(0.35英亩)地,但他却像地主一样租了出去,而不是自己耕种。对拉扎克的普遍看法是他简直不成器。当村长阿布杜尔马吉德向我谈及穷人不再愿意工作并要求不切实际的工钱时,他援引了拉扎克的例子,他使自己陷入困境,那是他自作自受。
现在简易棺材差不多做成了,村里最好的木匠阿明开始做一些小装饰添加上去。阿里芬提出,没有必要添加装饰,于是阿明停了下来。当他们把棺材运到停放玛兹娜的哈姆扎家中时,有人察看了棺木的做工后说,太破了。
在回住所的路上,我碰到一群帕克哈吉卡迪尔妻子的朋友在议论孩子的亡故。她们似乎都觉得这很大程度上是拉扎克和阿齐扎的过错。毕竟,前天他们把生病的女儿带到了罗吉娅的筵席上,喂她不该吃的东西,而且让她一直待到深夜。他们吃得很差,托卡西姆的妻子说,他们只能吃些其他人筵席的剩饭。在我的追问下,她们向我透露了这个家庭饮食匮乏的细节。比如早餐,如果家里有点钱,就是咖啡和木薯或者是前一天剩下的一点冷饭。如果没有钱,就只有水。有人补充说拉扎克家里的饮用水和洗浴用水来自同一个沟渠。早餐很少有粥,从没有牛奶,而且几乎没有糖,除非从阿齐扎在杜兰村的亲戚那儿拿来一点。同他们相比,村长哈吉加法尔则经常在镇上的咖啡店吃早餐,在那里他喝粥或者吃加糖或咖哩的油炸面包片,还有各种蛋糕、用糯米做的甜点和加甜浓缩牛奶的咖啡。中餐在村里是正餐,拉扎克一家人经常吃的是米饭和从村里免费采集到的蔬菜,如果经济状况允许,会有一些从市场上买回来的干鱼或最便宜的小鱼。没有人见过拉扎克买过蔬菜。当他们吃新鲜鱼的时候,通常是直接放在明火上烧烤,因为他们几乎买不起最少卖3角钱的最便宜的烹调油。而在另一方面,哈吉加法尔的中餐则表现出他的富有和更是奢侈的偏好:用市场里买来的蔬菜和最贵的鱼做成的美味的咖哩饭,每周至少吃两次肉,这是拉扎克从未有过的奢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