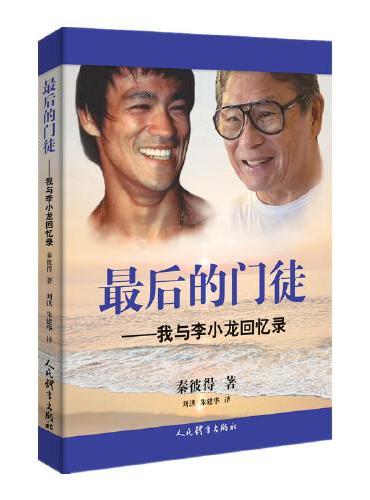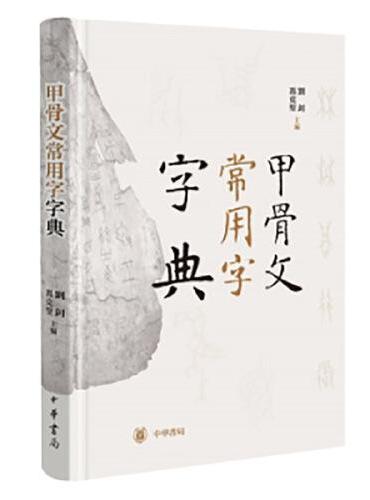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害马之群:失控的群体如何助长个体的不当行为
》
售價:NT$
449.0

《
性别:女(随机图书馆01)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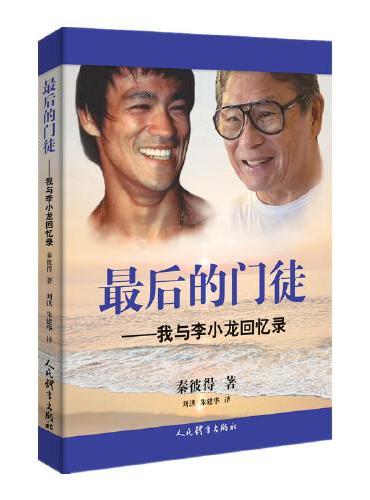
《
最后的门徒——我与李小龙回忆录
》
售價:NT$
347.0

《
没有明天的我们,在昨天相恋
》
售價:NT$
218.0

《
流动的白银(一部由白银打开的人类文明发展史)
》
售價:NT$
296.0

《
饮食的谬误:别让那些流行饮食法害了你
》
售價:NT$
296.0

《
三千年系列:文治三千年+武治三千年+兵器三千年
》
售價:NT$
9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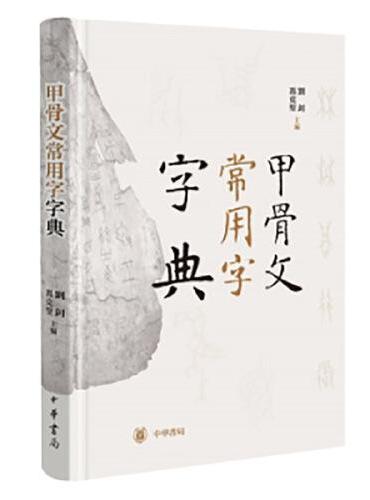
《
甲骨文常用字字典(精) 新版
》
售價:NT$
347.0
|
| 編輯推薦: |
1.深入剖析和解读博尔赫斯、布鲁诺舒尔茨、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等当下热门大师杰作。
2. 触及时代*鲜活的话题和标签,如女权意识和女性主义等,契合时代的节奏和观念变化。
3. 阎连科、骆以军倾情作序,当代著名作家余华、苏童、迟子建、梁鸿以及著名批评家李欧梵、王德威推荐。
4. 喜马拉雅课程。本书上市前后,将在喜马拉雅平台开发线上课程《世界文学大师的梦幻与越界》,与纸质书实现联动。
|
| 內容簡介: |
《小说的越界》是刘剑梅老师的文学评论集,本书分为女性的水上书写文学的变幻之旅文学的各种维度文学随笔四部分。
女性的水上书写:刘剑梅阐释了玛丽莲.罗宾逊、韩江、阿兰达蒂洛伊等四位女性作家,如何通过作品大胆地跨越了男权社会规定的家的边界,表达女性的独立意识;
文学的变幻之旅深入地剖析了博尔赫斯、布鲁诺舒尔茨、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及其他中外作家,如何以梦、幻想和变形跨越现实的各种疆域和束缚,完成越界式的飞翔;
文学的各种维度:分析波多尼奥、萨曼鲁西迪、格雷厄姆格林等人的作品,讨论了文学的各种维度,比如现实维度、历史维度、宗教维度和思想维度。
文学随笔:透彻地剖析了杰出的文学大师们的作品中所蕴含的深邃秘密和神奇魅力,而且也引导当代读者摆脱来自现实的种种压力、苦恼和束缚,安抚焦虑、不安的灵魂。
|
| 關於作者: |
刘剑梅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现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终身教授,曾任美国马里兰大学亚洲与东欧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曾出版中文专著《狂欢的女神》《共悟红楼》(与刘再复合著)《革命与情爱》《彷徨的娜拉》《庄子的现代命运》,英文专著《革命与情爱:文学史女性身体和主题重复》《庄子与中国现代文学》《金庸现象:中国武侠小说与现代中国文学史》(与何素楠合编)。在文学批评领域有极大的影响。
|
| 目錄:
|
被现代情怀滋养的经典析说
阎连科 001
作为鲁迅之后一百年的小说小读者
骆以军 012
第一辑 女性的水上书写
家的忧伤女性的写作 003
灵动婉转的散文体小说 029
第二辑 文学的变幻之旅
博尔赫斯的梦 057
色彩缤纷的舒尔茨 083
变形的文学变奏曲 107
第三辑 文学的各种维度
文学如何面对暴力 145
互绑的个人与历史 173
关于灵魂的书写 198
思想小说的另一条路 219
第四辑 文学随笔
拒绝遗忘的书写 249
关于书的挽歌 257
书写疾病和历史 267
后记 281
|
| 內容試閱:
|
被现代情怀滋养的经典析说
读刘剑梅《小说的越界》
阎连科
理论与小说写作的隔膜,一如北方的老榆和一棵南方棚大的榕树,几无可谈的相似之处,使得我们经常在左耳听到作家信誓旦旦地说,我从来不读文学理论书;又几乎是同时,在右耳听到理论家面带讥笑道,当代文学实在难有可读之小说。这种两相对立、互不心往的状况,不仅宛若北方的榆树和南方之榕树,怕也是同一片土地上的野草和菊花、荆棵与野槐,你开你花,我生我叶,并无实质之交错,只是在外人眼里,榆树和榕树都是世间树木吧;野草、菊花、荆棵和野槐,都是人世的绿中之植吧。这样久常的疏离和隔膜,每每使人读一篇或一本能够如渴之饮的文本批评或理论,便会觉得比读了十本、二十本每天都在出版、每日都在书店的货架上摆上或撤下的小说要胜好着许多或太多。
作家等待和寻找如渴之饮的文学批评,如同批评家朝日求找一部可读可言、言而不烦的小说。此间两相的抱怨和根恨,在双方的胸腔之深处,已经怼埋了太久、太深远,只是中国的文化和人情,让彼此笑而不谈并彼此心知肚明地饰而不言着。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冷笑、隔膜和彼此难有正眼相视的奇情与异状,读到刘剑梅教授这一系列对现代经典的析阅论说时,先是感到有一种隔膜消除的亲近感,后是那种两相根恨如柏林墙样被推翻的豁然和开朗。及至她将这一系列的文章汇编为《小说的越界》后,再一次地集中阅读,便突然有了那种等到了找到了的喜悦和兴奋。
实实在在地说,很久没有读到过对自己和诸多读者都共同心仪的作家和作品有个人见地或观点相似的理论著作了。《小说的越界》,是一个批评家的私人阅读史,也是这个批评家与作家和读者的共同阅读史。而这其中谈到的伟大作家和作品,是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几乎都读、却又少有成文的理论去梳理和言说的。《小说的越界》就在这时如期而至了。它既不东拉西扯地去卖弄和装点,也不仰视、膜拜地将那些伟大的作家和作品,当作耶稣和《圣经》,摆在文学的圣桌上供奉和恭敬。每一篇的阅读和剖析,只是要告诉你我喜欢和我为什么会喜欢。亲近、随和,并发自内心去分享,而非因为我要理论才去说,才去读,才去引经据典地写出来。原来在文学理论中,我喜欢和我要写,是这么不同的两件事。前者因为喜欢才去读和写;后者因为要写才去读。当二者都成为理论文字呈现在读者面前时,前者的文字中,呈出一种自然亲切的欣悦感,后者呈出一种肃严、正经的呆板感。前者的轻松、欣喜一如坐在茶馆、咖啡馆里相遇和聊天,无非彼此见面聊的不是吃饭、穿衣和住房,而是我最近读了什么书,为什么会喜欢这些书;而后者,则如教室中的老师和学生、讲台与课桌样的距离及隔阂。因为后者一上来,老师就对学生说,现在上课了,请大家都拿出笔和本。
再次读完《小说的越界》而收合尾章时,我沉落在这本给我带来喜悦的理论书册里,于是想到这喜悦的渊源出处了12篇文章,谈到了百来个作家和上百部的书,并不是每个作家和每本书都使我喜爱并欣悦,那么为什么一本理论著作中的文章和通篇之析作,又篇篇会让人感到不间断的喜悦和亲近?如同阅读一部你并不完全喜欢、却又让你一字不落地去品味的作品一样。如波拉尼奥的《2666》这部巨制,到底有多少人真正读完了它?到底有多少人真心喜爱它?到底那些喜爱它的作家和读者,有几个能说出因之喜爱的一二三?大凡一站到人前就谈论波拉尼奥和《2666》的人,我常用惊异的目光看着他们的脸,试图从那脸上读到一层人云亦云的盲从和虚伪。然而在读刘剑梅的《文学如何面对暴力》这篇对《2666》抽丝剥茧的作品分析时,她和她的文章让我那种怀疑的目光变得温和了、释然了,随性并也包容了。直到今天,我都以为《2666》因为作家写作前是为了五部小说而起笔,并非为了一部巨制的面世与出版,所以,当将五部组合为一部时,结构上是有着明显隔离和生涩的(当然也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游离而又联系的新结构),然由于我们对波拉尼奥的写作与离世,深怀着敬重而不去挑剔这一些。所以在几乎所有人都盲目盛赞《2666》时,我总是盯着那盛赞者的眼也就这时候,恰到好处地读到了刘剑梅的《文学如何面对暴力》这来去有据的文本分析了,也是这时我对刘剑梅教授开始怀有了顿为愕然的敬重感。这种敬重不仅是她率先打破了《2666》的伟大连续多年都凝结停留在中文读者和作家嘴边的喧闹上,以一个女性的独有之目光,写出了《2666》对世界、暴力和女人与人的强力、强大的关注和投入,而更在于《文学如何面对暴力》这篇论文,使人感受到了批评家的文学情怀是何等重要和关键。一如一个作家没有情怀空写出的小说一样,倘若一个批评家,没有情怀而去析说理论时,哪怕你的才华、聪智大如山脉与海洋,写出来的文章、著作怕也是没有血脉的积木建筑吧。
我想应该是这样当我们说没有情怀的小说就是没有灵魂的篇章文字,也可以说,没有情怀的理论,同样是没有灵魂的篇章文字。从面对波拉尼奥到面对舒尔茨,从面对舒尔茨到面对托卡尔丘克,再到她面对奥维德和他的《变形记》,这一路的解读和析说,在刘剑梅的文本分析与纵论横比中,我们始终在她的理论述说里,可以真切、清晰地读到她对人与人世的爱,读到她对文学天然的情感与纠缠,对语言创造发自内心的敬重和对孤独写作者无条件的拥抱和同暖。一如她在《文学如何面对暴力》中说的一样:
波拉尼奥的《2666》对全人类范围的暴力的书写,就是一把可以敲碎我们内心冰海的冰镐,非常有力度。他不仅质疑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以及精神出路的问题,而且通过小说的形式继续探讨斯坦纳提出的大哉问,那就是面对人性的野蛮和邪恶,文学和语言是否已经失去了其本来应该具有的人文精神,还是仍然有力量去表现和批评现实中的暴力和谎言,发出呐喊,让麻木的人们为之震颤?那些知识的承载者,是否已经全军覆没,对黑暗的世界无能为力?
这样一段深具现代意义的盘诘叩问的胸腔文字,刘剑梅说的是《2666》,但也同时是她诘问着整个的世界和文学,是她面对文学的一种现代情怀,也是一位女性面对自己的阅读和写作的现代情愫。而整部《小说的越界》,也正是她面对人性的野蛮和邪恶,文学和语言是否已经失去了其本来应该具有的人文精神的分析与对答。
正是在这个最基本的现代情怀基调上,刘剑梅和她的《文学如何面对暴力》,让我们理解了波拉尼奥和他的《2666》,也让我们深明了《小说的越界》这部批评家、作家和普通读者所共有的阅读史和经典文本分析史。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批评家建立在对文学灼情挚爱基础上的宽广和无际。在时间的线轴上,她根系中国古典的老子、庄子乃至百家和西方文明的古希腊。一篇《变形的文学变奏曲》,宛若一碗水中盛装了大海、山脉和世界,从希腊神话到古罗马,从奥维德的《变形记》,再到卡夫卡的《变形记》和舒尔茨的《肉桂色铺子及其他故事》《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从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到果戈理的《鼻子》乃至20世纪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鲁西迪的《撒旦诗篇》和《摩尔人的最后叹息》,乃至当今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乳房》,日本作家安部公房的《墙》、《砂女》和《箱男》,法国作家达里厄塞克的《母猪女郎》等;然后是中国古典《庄子》中的庄周梦蝶,《山海经》和《聊斋志异》乃至当下中国作家贾平凹、莫言、余华、迟子建等人作品中的鬼神变化和怪诞,一线珠串,洒洒洋洋;通过变形这一文学的意象、方法和镜照,在时间上自古至今,在空间里由西到东,拿来时如开箱取物,放下时如闭门离去,信手拈来,自由自然。这不由得不使人感叹写作者的阅读和记忆,在这变形的一绳珠串的牵引下,文章中的每一书、每一例、每一故事和章节,都贴切到如落叶在秋,晨珠黎明,恰到好处地拿来,又恰到好处地放下。还有这册批评集中的《灵动婉转的散文体小说》《关于灵魂的书写》《思想小说的另一条路》《关于书的挽歌》等,但凡有纵论性质的书写,批评家都可上古下今、左西右东地论述和分析,其阅读之宽广,论说之自由,使人惊异和愕然,惊异她的阅读量之大,愕然她的记忆力之好。而且在这如同随笔一样的随性论述中,她又总能以纲带网地始终不离其主轴和主道,让人随步她的言说和分析,遍翻书页,览尽阅读,一如一个图书馆的馆长领带读者到图书海洋的某一区域或某一架柜前的寻找和检索,直到你终于找到你要找的那本书,找到打开某一书架柜门的那把钥匙为止。
以不甚恰当的方式说,面对20世纪的现代文学,我以为世界上最好的读者,是那些可以拆解小说的人,一如最好的锁匠,是那些可以配钥匙的人。这群锁匠就是批评家和会拆解小说的一些作家们。批评家的宽广,奠定着他们的视野和深度;作家的宽广,奠定着他们写作的坐标和方位。没有阅读量的批评家是不可思议的,没有阅读量的作家持续写作也是不可思议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刘剑梅是上帝经常去看望的那个人。因为上帝让她出生在了一个特殊的时代和特殊的家庭里,父亲的博学与慈爱,以世为家的宽广和超越,所有的人都有人的博大与情怀,这些来自其父天然的言传和身教,如同家庭接力棒般的交接与续跑,加之特殊年代的命运安排她西去留学与求读,苦难恰恰成了她阅读的方舟和摆渡。当历史更迭,朝夕时移,回望岁月给她的艰辛和酸楚时,又哪里不是命运所赐给她的大天下的宽广和幸运,哪里不是成就情怀与胸襟之爱的神谕和安排。
当然,并不是说人有了情怀和宽广,成功与成就便可以春种秋收般在时间和季节里等着你的到来和收获。对于好的文学和批评,世界上没有无天赋的写作和创造,也没有单一地从阅读中就可以孕生、成长起来的批评家。刘剑梅,这位充满着对人和文学现代情怀的批评家,她对文学的敏锐,一如一个作家对故事和细节的敏感一样,如一个农人对天气和未来季节变化的敏感一样。有人能从别人的一句闲谈中触摸到一部不同凡响的长篇小说来,有人却只能从巨大的历史动荡中提炼出一声叹息来。这也就是所谓的兑现天赋要透过敏锐的呈现与表达。换言之,文学的天赋或天才,相当程度上就是文学的敏锐性和敏感度。在托卡尔丘克于中文世界还相当冷寒的两年前,《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和《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在中国出版,宛若一场倒春的寒流对新生杨柳的卷袭,剑梅总是和我谈起托卡尔丘克的写作与超越,并将她最早从英文读到《云游》的感受如喂食一样告诉我。而当我的迟钝如门板一样还横在她的敏锐面前时,关于托卡尔丘克文本分析的论文她已经写将出来了。
我很喜欢托卡尔丘克的散文体小说,因为这种文体轻盈、灵动、疏离,如同加了会飞起来的羽翅,带我们飞越各种固定的沉重的边界,飞离各种重复单调的表述形式,像淘气的孩子一样总是故意偏离轨道,在俏皮的逃离主流话语和传统书写方式的旅途中找到一种快感,一种释放,在虚无里看到生命,在生命里看到虚无。
从她的《灵动婉转的散文体小说》中,读到她对托卡尔丘克写作的这段精准论述时,我吃惊地在房间里默站着。这种默然的站立,一方面是为那时自己对托卡尔丘克写作的无知而惊讶;另一方面,是对刘剑梅敏锐的阅读、感悟而愕然。尽管我自己并不完全认为托卡尔丘克的写作是一种散文体小说,也不认为她一定就是碎片化的写作,而觉得她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对已有故事有意的重组和再塑,甚至觉察到了她在这种重组、再塑中的艰难和锲而不舍的叹息与努力,但当批评家敏锐地意识到托卡尔丘克带我们飞越各种固定的沉重的边界,飞离各种重复单调的表述形式的意义时,她那种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把握和敏锐,又一次横亘在了我面前。她总是能从中国文学最顽固、板结、封闭的土地上,敏锐注意到世界文学中最为鲜活的探索和冲击,并能从中文以外的写作中阅读、回望、医证出中国作家写作在面对世界文学不可逆的潮进间原地踏步的脚音和无奈退倒的歌唱声。正是因为这一些从中国文学中走出去,又从世界文学中走回来,这种往复来去的每一次环行、观望、医证和比较,使得她的这些对现代经典的拆解、条理和析文,都怀着一种对世界文学的敏锐和对中国文学固封的焦虑。也正是她反复地从这块土地、故文的出发和对这块土地、故文的再回,使她率先去理析了《2666》对中国文学真正的价值在哪儿;托卡尔丘克的写作,对中国文学写作的意义在何方。乃至于面对没有那么知名的法国作家菲利普福雷斯特的小说《永恒的孩子》和《然而》,她也敏锐地写出来了《拒绝遗忘的书写》;面对舒尔茨的《肉桂色铺子及其他故事》和《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这些作家们痴爱而读者寥冷的小说,她又写出了《色彩缤纷的舒尔茨》。还有面对鲁西迪那难啃的骨头《午夜之子》等,她都能直系纲领地拆解和论述。《互绑的个人与历史》将《午夜之子》这栋复杂的建筑拆解还原为原材料;《文学如何面对暴力》将《2666》还原为一栋建筑的骨架和地基;《灵动婉转的散文体小说》将托卡尔丘克小说中始终氤氲弥漫的韵云与气息、时间与历史,化解为云、雨和日出,这种拆解和还原力,对于批评家正是敏锐和天赋,一如天才的作家总能把一滴水衍生为大海。且她的这种能力又总是和中国文学联系在一起但凡在世界文学的书写里,有小说对中国文学有弥缺补憾之意义,她都能从缺憾的文学中走出去,透过敏锐的阅读和感悟,到更广阔的文学之林里徜徉后,带着敏锐分析、比较的一桥一梁走回来。这些从文本出发的比较与论说,一方面是为了改变中国作家的写作而写作;而另一方面,乃至于她更多是为了我看到和说出来的自由而着笔。因此间,敏锐的发现,就成了她阅读和论述的起点乃至为一个终点了,宛若一个敏于自己身有术疤的人,仅仅是为了对天气的感应而持续存在着。
情怀、宽广、敏锐对《小说的越界》这本如此蕴含文学前沿意义的论文集,不能不说的是批评家最具个人意味的现代性。她的现代性不是我们日常说的小说写作的现代性,而是一个批评家对20世纪文学现代性始终如一的倾情与关注,是批评家以一个女性或女性主义者的独有目光对文学的投射、分析和研讨。这在中国诸多批评家中是鹤立鸡群或独一无二的,尤其以女性和女性主义者的目光去瞻望或析说这里说的并不单纯是指那篇她在这本书中对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优美论述《家的忧伤女性的写作》如同散文一样,娓娓道来地对美国女作家玛丽莲罗宾逊的《管家》、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罗伊的《微物之神》和韩国女作家韩江的《素食主义者》进行条理分析,发出对家这个如此烟火、世俗和温暖的房居,被女性、现代的目光戳穿而成为女人笼窝的批评和批判。还有她在这本书中关注的所有作家和作品,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立场到格雷厄姆格林和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的《沉默》和《深河》,当中文批评家多都对此沉默而三缄其言时,她却是始终并反复地提及和讨论,始终将宗教、信仰作为现代文明和当下文学更应该关注的现代性的问题去读、去说、去论述,如同她从来都不搁置、疏远暴力、女性和女性主义的文学一样。还有文学中的时间、梦幻、结构、第三空间和现代生活与文学的碎片化等,这些在20世纪文学中万花筒般被反复旋转、变幻到使人眼花缭乱,而不得不使许多写作者乃至整个中国文学都返回传统和现实主义以喘息、歇栖、逃离和守成的姿态写作与阅读。而她却从来都以一个女性温润而执着的姿态,始终如一地相信时代无论如何是要向前的,文学可以回归,但最终还是要向前的。她以这种理解退守、却又称颂执着前行的现代性,几乎目不转睛地盯在那些更有现代创造意义的作家和作品上。在她看来,博尔赫斯的梦和梦中梦,图书馆和图书馆中的书,迷宫和迷宫中的路,时间和时间中的空间及空间中的新时间为文学加了起飞的翅膀。因为只有在梦中,作家才有虚构时间的能力,打破直线式的进步的时间观(《博尔赫斯的梦》)。在《色彩缤纷的舒尔茨》中,她不光精密、究细地去论述舒尔茨小说中的变形、时间和梦幻,还独有洞见地发现舒尔茨小说中的自然精神,看到了舒尔茨在他不多的小说中无处不在的物质的深处,隐藏着无限的可能性。植物、动物、家具、窗户、大门、墙壁、季节和我们生活周围的点点滴滴的物质和环境,全部都等待着他来赋予其生命的呼吸和灵魂。这种对舒尔茨自然精神的洞明,除了阅读与写作的敏感,更需要的则是对小说现代性的高度认知。没有这种更具现代意义的个人认知,我们则无法从根本上理解舒尔茨。在《思想小说的另一条路》中,她从索尔贝娄和他的《赫索格》《晃来晃去的人》《洪堡的礼物》等小说中以思考对人物、故事和风格的取代说开去,并以此延宕开来,讨论一种独有写作的回心向内转内心世界内在经验及托马斯曼的《魔山》,库切的《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但批评家最终要阐明的,却是文学要摆脱单一模式的重要性和现代性。
我们当然不能说刘剑梅是现代小说的铁定拥戴者,但在《小说的越界》一书里,她让我们通常被人道固有拥抱的人文情怀,几乎毫无保留地转移至了对文学,尤其是更具独创意义的现代主义文学的拥抱和颂扬上。她以一个女性批评家的独立、洞见、绸柔、温润的笔墨,随情随性、自由无束地去讨论几乎所有在传统的目光下,都显得突兀、横亘的现代性问题,使得并不厚重的《小说的越界》,成为当下几乎所有大陆论集中最为鲜明的一册;也成为从今天这个文学时代的上空,清晰划过的一道越界的光,为今天的读者、作家和论家,留下了超越中文的更为宽广、独特、自由论说和飞翔的身影。
2020年1月18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