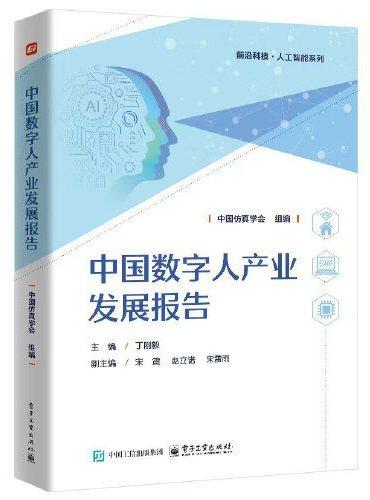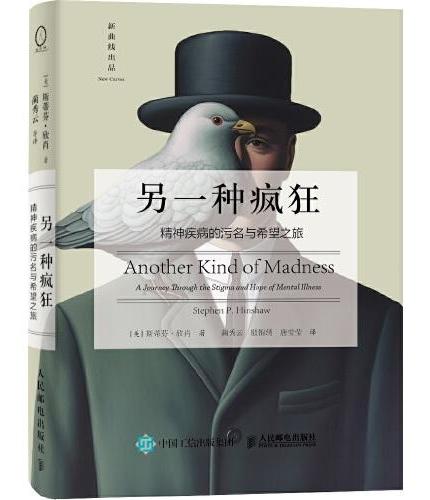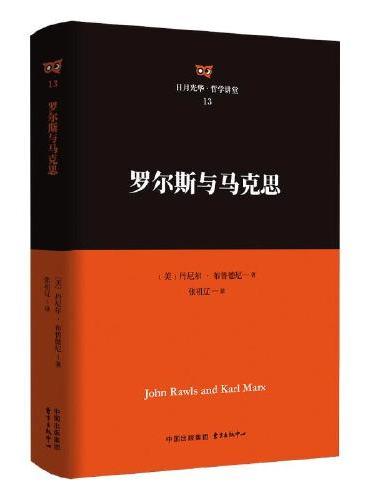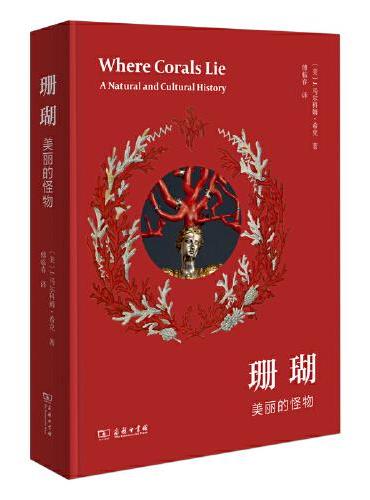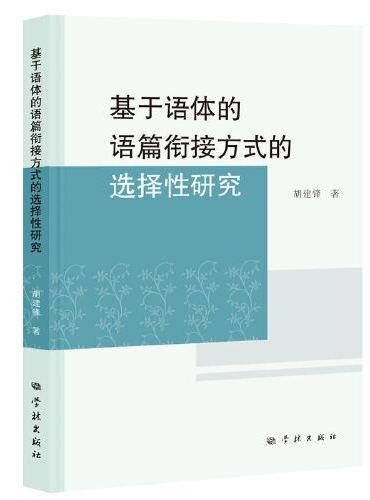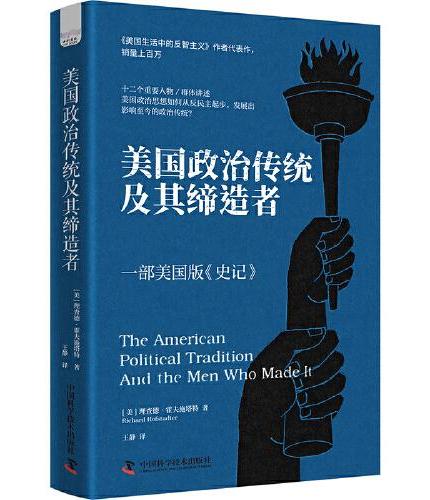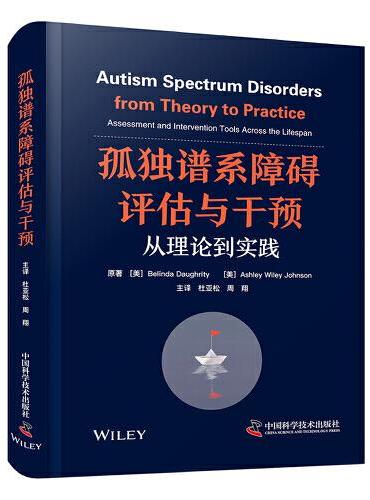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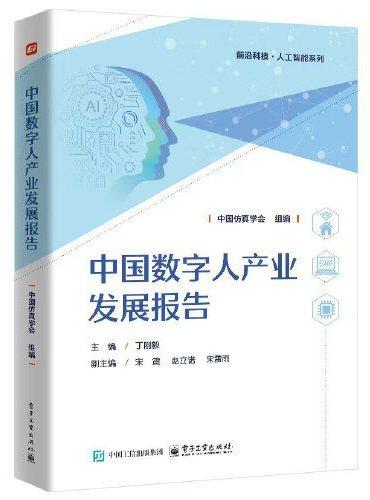
《
中国数字人产业发展报告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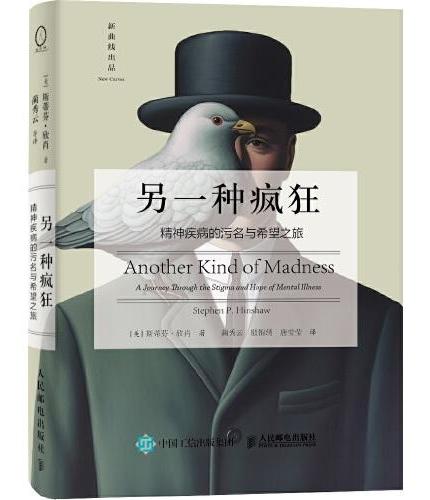
《
另一种疯狂:精神疾病的污名与希望之旅(APS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斯蒂芬·欣肖教授倾其一生撰写;2018年美国图书节最佳图书奖)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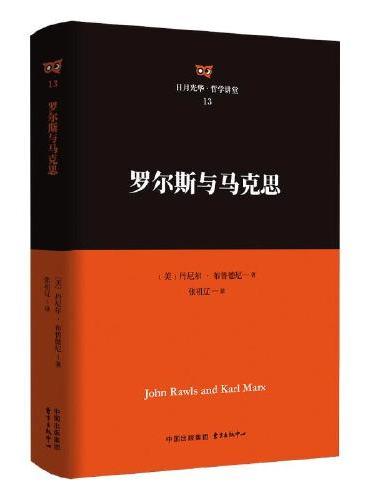
《
罗尔斯与马克思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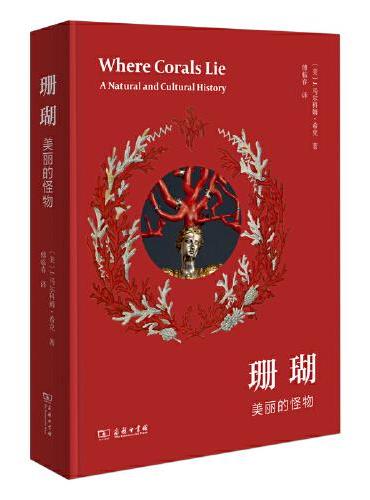
《
珊瑚:美丽的怪物
》
售價:NT$
58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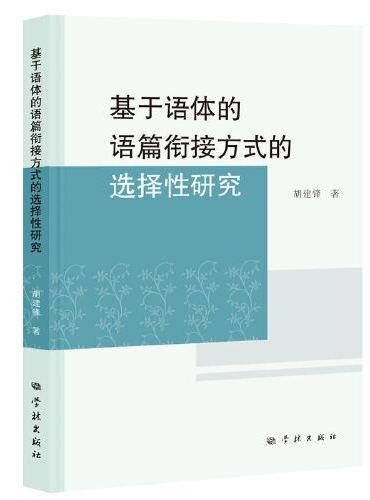
《
基于语体的语篇衔接方式的选择性研究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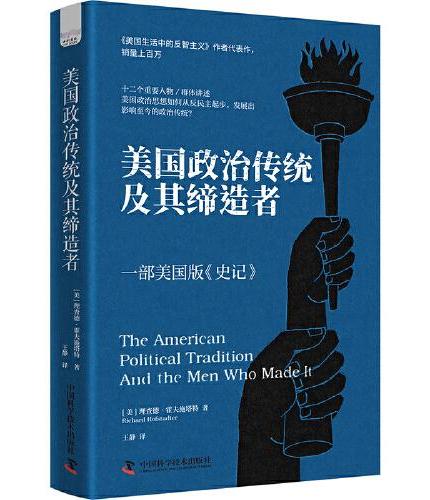
《
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一部美国版《史记》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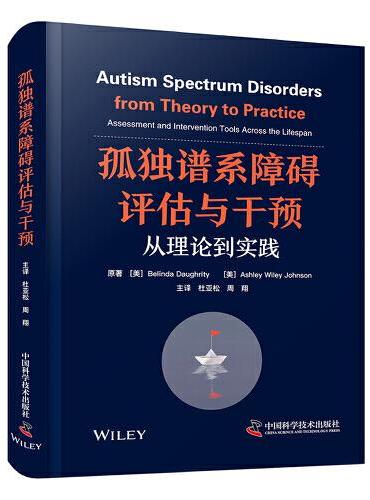
《
孤独谱系障碍评估与干预:从理论到实践 国际经典医学心理学译著
》
售價:NT$
1061.0

《
大数据导论(第2版)
》
售價:NT$
352.0
|
| 編輯推薦: |
1.中文世界首次引进译介
2.阿尔帕西诺主演同名电影原著
|
| 內容簡介: |
|
《低入尘埃》的主人公阿克斯勒是知名的舞台剧演员,有一天他的才华顿失,再也无法上台表演,深受困扰并想自杀的他主动住进精神病院,但出院后仍旧无法重拾演艺事业。同时,他离了婚,与好友的女儿培琴陷入热恋,这对年龄相差二十岁的伴侣为彼此的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改变,然而女方却在他情浓之时转身离去。阿克斯勒又冒出了自杀的念头,实践这出演员在现实中只许演一次的戏。
|
| 關於作者: |
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33-2018)
美国代表性作家。
1960年、1996年,罗斯分别凭借处女作《再见,哥伦布》和《萨巴斯剧院》两度将美国国家图书奖揽入囊中。1997年,罗斯凭借《美国牧歌》摘得普利策文学奖。1998年,罗斯在白宫受颁美国国家艺术勋章。2002年,他又获得美国艺术文学院颁发的最高荣誉虚构类作品金奖,该奖的往届获奖者有约翰多斯帕索斯、威廉福克纳、索尔贝娄等著名作家。罗斯的《反美阴谋》被誉为2003-2004年度以美国为主题的优秀历史小说,这部小说于2005年荣获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奖和W.H.史密斯文学奖年度最佳图书。罗斯也因此成为W.H.史密斯文学奖设立四十六年以来首位两度获奖的作家。此外,他还获得美国书评人协会奖两次,笔会福克纳奖三次。
2005年,罗斯成为第三位由美国文库为其出版权威版作品全集的在世作家。此后,罗斯接连获得笔会纳博科夫奖(2006)和笔会贝娄奖(2007)。2011年,他在白宫被授予美国国家人文奖章;同年,他又成为第四位布克国际文学奖的获得者。2012年,罗斯赢得西班牙最高荣誉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2013年,他又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最高荣誉法国荣誉高等骑士勋章。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33-2018)
美国代表性作家。
1960年、1996年,罗斯分别凭借处女作《再见,哥伦布》和《萨巴斯剧院》两度将美国国家图书奖揽入囊中。1997年,罗斯凭借《美国牧歌》摘得普利策文学奖。1998年,罗斯在白宫受颁美国国家艺术勋章。2002年,他又获得美国艺术文学院颁发的最高荣誉虚构类作品金奖,该奖的往届获奖者有约翰多斯帕索斯、威廉福克纳、索尔贝娄等著名作家。罗斯的《反美阴谋》被誉为2003-2004年度以美国为主题的优秀历史小说,这部小说于2005年荣获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奖和W.H.史密斯文学奖年度最佳图书。罗斯也因此成为W.H.史密斯文学奖设立四十六年以来首位两度获奖的作家。此外,他还获得美国书评人协会奖两次,笔会福克纳奖三次。
2005年,罗斯成为第三位由美国文库为其出版权威版作品全集的在世作家。此后,罗斯接连获得笔会纳博科夫奖(2006)和笔会贝娄奖(2007)。2011年,他在白宫被授予美国国家人文奖章;同年,他又成为第四位布克国际文学奖的获得者。2012年,罗斯赢得西班牙最高荣誉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2013年,他又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最高荣誉法国荣誉高等骑士勋章。
|
| 目錄:
|
一、 窘迫 1
二、 蜕变 41
三、 最后的表演 85
媒体评论
他的作品包含一种透彻乃至无情,阅读体验紧张、狂野他是*后一位巨人。
《时代周刊》
与他同时代的文坛巨匠一一淡去,唯有罗斯的写作仍旧精神奕奕,为叶芝之后所罕有。
《文学评论》
在线试读一、窘迫
他魅力顿失,激情枯竭。在舞台上他从来不曾失过手,他所作的一切都那么铿锵有力和成功,接着可怕的事情来了: 他不能表演了。登台已成为痛苦不堪的折磨。他不再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会创造奇迹,相反心里清楚会必败无疑。这种感觉接连出现了三次,最后一次出现时已经没有任何人感兴趣,没有任何人来看了。他已经招不来观众。他的才华消陨殆尽。
当然,如果你拥有这份才华,肯定也会有异于常人之处。我生来就跟常人不同,阿克斯勒对自己说,因为我就是我。那种特质跟我形影不离这点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可是,曾经环绕他的光环,以及所有那些做派、怪僻和个人特立独行之处,那些曾为出演福斯塔夫和培尔金特以及万尼亚服务的气质作为古典戏剧演员中最后的高人,那种给西蒙阿克斯勒带来显赫声名的东西如今没有一丁点儿可以给他的任何角色派上用场了。曾让阿克斯勒显得卓尔不群的一切,现在反而把他弄得像个疯子似的。他每时每刻都惦记着自己在舞台上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过去,只要表演,他脑子里就什么杂念都没有。他表现得最出色的东西全都出自本能的发挥。现在他脑子里可谓无所不想,而且各种东西同时纷至沓来,生命力惨遭扼杀他试图借助思考来控制它,到头来却消灭掉了它。认了吧,阿克斯勒告诉自己,看来他是碰上倒霉期了。虽然已经年过六十,没准这个霉头终会过去,因为他仍然承认自己还是不错的。何况他不是第一个经历这种倒霉期的经验老到的演员了。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经历。我以前就碰到过,他心想,所以我终究会找到解决的出路。这次我虽然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出路,但我定会找到定会挺过去。
到头来还是没挺过去。他不能表演了。从前在舞台上专心致志的本事没了。现在每一场演出他都害怕,而且提心吊胆的感觉会长达一天之久。他经常花整天的时间思索这辈子在上场表演前从不思索的问题: 我可能会失败,我演不好,我在扮演不当的角色,我的表演太过火,我的表演虚情假意,我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第一句台词。其间,他巴不得干上一百件貌似不做不行的事儿来佯做准备以消磨时间: 我得再看眼对白,我得休息,我得练习,我得再看眼对白,到该登台演出时,他早已精疲力竭。这时他又害怕上台了。听到提醒演出的时间越来越迫近,他心想自己这回可能要演砸了。他等着快点开始,早点解脱好了,等着变成现实的刹那快点到来,等着忘记自己是谁,变成扮演这个角色的人,可是他却站在那儿,头脑完全茫然,做着人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时才会做的那种动作。他既不能表现什么又无法收回去;他的表演既不流畅,也不内敛。表演成为一种夜复一夜、试图解脱某种东西的操练。一、窘迫
他魅力顿失,激情枯竭。在舞台上他从来不曾失过手,他所作的一切都那么铿锵有力和成功,接着可怕的事情来了: 他不能表演了。登台已成为痛苦不堪的折磨。他不再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会创造奇迹,相反心里清楚会必败无疑。这种感觉接连出现了三次,最后一次出现时已经没有任何人感兴趣,没有任何人来看了。他已经招不来观众。他的才华消陨殆尽。
当然,如果你拥有这份才华,肯定也会有异于常人之处。我生来就跟常人不同,阿克斯勒对自己说,因为我就是我。那种特质跟我形影不离这点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可是,曾经环绕他的光环,以及所有那些做派、怪僻和个人特立独行之处,那些曾为出演福斯塔夫和培尔金特以及万尼亚服务的气质作为古典戏剧演员中最后的高人,那种给西蒙阿克斯勒带来显赫声名的东西如今没有一丁点儿可以给他的任何角色派上用场了。曾让阿克斯勒显得卓尔不群的一切,现在反而把他弄得像个疯子似的。他每时每刻都惦记着自己在舞台上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过去,只要表演,他脑子里就什么杂念都没有。他表现得最出色的东西全都出自本能的发挥。现在他脑子里可谓无所不想,而且各种东西同时纷至沓来,生命力惨遭扼杀他试图借助思考来控制它,到头来却消灭掉了它。认了吧,阿克斯勒告诉自己,看来他是碰上倒霉期了。虽然已经年过六十,没准这个霉头终会过去,因为他仍然承认自己还是不错的。何况他不是第一个经历这种倒霉期的经验老到的演员了。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经历。我以前就碰到过,他心想,所以我终究会找到解决的出路。这次我虽然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出路,但我定会找到定会挺过去。
到头来还是没挺过去。他不能表演了。从前在舞台上专心致志的本事没了。现在每一场演出他都害怕,而且提心吊胆的感觉会长达一天之久。他经常花整天的时间思索这辈子在上场表演前从不思索的问题: 我可能会失败,我演不好,我在扮演不当的角色,我的表演太过火,我的表演虚情假意,我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第一句台词。其间,他巴不得干上一百件貌似不做不行的事儿来佯做准备以消磨时间: 我得再看眼对白,我得休息,我得练习,我得再看眼对白,到该登台演出时,他早已精疲力竭。这时他又害怕上台了。听到提醒演出的时间越来越迫近,他心想自己这回可能要演砸了。他等着快点开始,早点解脱好了,等着变成现实的刹那快点到来,等着忘记自己是谁,变成扮演这个角色的人,可是他却站在那儿,头脑完全茫然,做着人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时才会做的那种动作。他既不能表现什么又无法收回去;他的表演既不流畅,也不内敛。表演成为一种夜复一夜、试图解脱某种东西的操练。
那种感觉最初是从人们跟他讲话开始的。三四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对自己讲话和听人讲话陶醉不已。从一开始他就感觉自己在入戏。他驾驭聆听的那股专注和全神投入劲儿,堪比个别演员对激情释放的驾驭。当然,在舞台之外,他同样具有那种力量,特别是还比较年轻的时候,跟那些女人在一起的时候: 她们意识不到自己还有故事,最后他揭示出她们不仅有故事,还有自己独特的声音,以及谁也不具备的气质。她们后来都成了跟阿克斯勒搭档的女演员,成为自己生活中的女主人公。舞台演员鲜有能像他那样讲话和善于聆听的人,但是如今这二者他都不行了。感觉那些仿佛灌入耳朵的声音像在慢慢地渗出去,他说出的每句话似乎都是在表演而不是讲话。他表演的最初源泉都在自己听到的东西中,他的表演的核心就是对自己听到的东西的反应,如果不能听了,听不到什么了,他就没有任何往前走下去的资本了。
有人让他在肯尼迪中心扮演普洛斯佩罗和麦克白雄心勃勃的连场演出想来都严峻糟糕的是这两个角色都演砸了,但麦克白演得要更糟些。莎士比亚塑造的低强度和高强度角色,他都演不好了可他演了一辈子的莎剧。他演的麦克白油腔滑调,看过的人个个都这样说,连许多没看过的人也瞎起哄。不,他们甚至都没去过现场,他说,就来侮辱你。许多演员借着酒劲来摆脱尴尬。有则流传甚广的玩笑讲的就是这种情形: 有个演员上台之前总要喝酒,当被警告说你不能喝了,他就回答:什么,难道独自从这儿出去?可是阿克斯勒从不喝酒,所以他崩溃了。他的崩溃来得非同小可。
最糟糕的是,他对自己精神崩溃的洞察跟演戏如出一辙。这是一种剧痛,但他仍然怀疑这不是真的,事情因此变得雪上加霜。他甚至不知道如何从这一分钟混到下一分钟,他的思维感觉像在融化,对自个儿独处恐惧得要命,一个晚上睡不了两三个小时。他不思饮食,每天都考虑着用藏在阁楼上的那杆枪结束性命那是一杆雷明顿牌870型压动式射击步枪,他保存在那幢离群索居的农舍里,用来防身自卫可是整个这件事儿好像也是一场表演,一场拙劣的表演。当你表演某个崩溃的人物角色时,它是有组织有规矩的;当你观察自己分崩离析,扮演自己死亡的角色时,那又是另一码事,那可是浸透恐怖和恐惧的事情。
阿克斯勒都无法信服自己已经疯了,更不要说让自己或者别人信服他就是普洛斯佩罗或者麦克白。同时他又成了一个矫揉造作的疯子。他能表演的唯一角色就是在表演某个角色的人。一个表演神志不清者的神志清醒者。一个表演支离破碎者的健全者。一个表演失控者的控制裕如的人。一个成就卓著的人,一个戏剧界的传奇人物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结实的演员,站在那里身高足有6.4英尺,长着一个巨大的秃脑袋,一副打手般结实和乱毛丛生的体格,脸上传达的内容如此之丰富,下巴坚毅果断,阔大的嘴巴可以扭成各种形状,从喉咙深处发出居高临下、低沉浑厚的声音,那里好像经常含着轻微的咆哮声,一个大气正派的男人,好像一切考验都能经受得住,而且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赋予一个男人的所有角色,他是坚忍不拔的化身,极力想往自己身上注入某种令人信赖的巨人的利己主义扮演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半夜醒来,他有时会惊声尖叫,发现自己还囚禁在一个被夺去了自我、才华,在这个世界丧失了地位的男人的角色中,依然是一个可恶之人,除了那份失败的记录外一无所有。好几个早晨,他在被窝里一躲就是几个钟头,可仍然躲不掉自己还在表演的那个角色。最后他不得不起床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自杀,而且还不是对这种念头的模拟。一个人想通过表演一个想去死的人来活着。
其间,普洛斯佩罗最著名的台词无法让他放松,也许是因为他最近把这些语言全都粉碎成细末了。这些语言经常在他的脑子里定时重现,很快就变成了一片意义晦涩空洞的叫嚣之声,没有实际意义但却携带着充满个人意味的魔咒。我们的狂欢现在已经结束。我们的这些演员,我早就告诉过你,全都是精灵全都化作空气,融入窘迫的空气。对窘迫的空气这几个字他无计可施,无论如何都清除不掉。早晨,他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时,这几个字的音节乱嚷嚷地重复个不休,而且即便这些音节变得越来越莫名其妙的时候,都还笼罩着一圈模模糊糊控诉的光晕。他全部复杂的人格完全处于窘迫的空气的操纵中。
阿克斯勒的妻子维多利亚也不再关怀他了,而且如今她自个儿还需要关怀。只要在厨房的餐桌上看到丈夫,她就会哭泣。他双手捂住脑袋,吃不下妻子准备好的饭菜。试着吃点吧。维多利亚都恳求了,可他什么都不吃,什么也不说,很快维多利亚就开始惊慌了。她从来没有见过阿克斯勒这样萎靡不振,连八年前他父亲开车跟别人相撞,年迈的父母在车祸中丧生,他都不曾如此沮丧过。当时他只是痛哭了一场,然后挺了过来。他从来都能挺过来。他吃了不少亏,可是自己的表演从来没有踉踉跄跄过。维多利亚一团糟的时候,是他让维多利亚保持坚强,最后渡过了难关。她老要面对居无定所的儿子的吸毒纠葛。随之而来的是衰老的永恒之痛和职业生涯的终结。失望如此巨大,但是有阿克斯勒在,所以她还是能够忍受。只要有阿克斯勒在就好,可是那个她曾经依赖的男人如今不复存在了!
一九五〇年代,维多利亚鲍尔斯曾经是巴兰钦[1]最年轻的宠儿。后来她膝盖受伤,动了一次手术,然后又能跳舞了,然后又受伤,又动了一次手术,她第二次恢复时,别人已经取代了巴兰钦最年轻宠儿的位置。她再也没有恢复过自己的地位。她结婚、生子、离婚,然后是第二次结婚,第二次离婚,然后跟西蒙阿克斯勒相遇、相恋。早在二十年前,阿克斯勒刚走出大学不久便在纽约的舞台上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那时他经常去城市中心剧场看她跳舞。倒不是他多么喜爱芭蕾,而是面对维多利亚通过最温柔的感情方式撩拨得他情欲勃发的本事,年纪轻轻的他难抵诱惑: 打那以后,多年来在他的记忆中,维多利亚仍然是情欲悲怅的化身。七十年代后期,他们以四十岁高龄相遇时,已经很久没有人请她去表演了,但是她每天坚毅地去本地一家舞蹈工作室参加训练。为了保持体型的健美和显得年轻,她无所不用其极。可是,那时自己的痛苦已经凌驾于她人为控制的能力之上。
经历了丈夫在肯尼迪中心的那场败落、他的意外崩溃之后,维多利亚也崩溃了,于是逃到加利福尼亚去找儿子会合了。
顷刻间,住在乡下那幢大房子里的阿克斯勒变成了孤家寡人,他害怕自己会自杀。现在什么都拦不住他了。现在他可以向前进,完成维多利亚在家的时候自己深感办不到的事情: 爬上楼梯走进阁楼间,给那杆枪装上子弹,把枪杆塞进嘴里,长长的手臂向下伸过去扣动扳机。妻子走后,他选择了这把枪。然而一旦她走了,阿克斯勒独自在家,几乎连最初的一个小时都很难熬过去甚至都难以爬上通向阁楼梯子的第一级台阶。当天,阿克斯勒就给自己的精神科医生打去电话,请他安排入住一家精神病院。几分钟之内,医生就在哈默顿医院给他找到一张床位,这是一家声誉不错的小医院,向北行程不到几个小时。
他在那里住了二十六天。被一个护士问过话、打开行李、交出自己的尖锐物之后,他的各种值钱的东西都被带到商务办公室妥善保管起来。一旦又变成独自一人,待在分配给自己的房间里,他便坐在床上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回忆自己从二十岁出头成为职业演员后以绝对把握表演过的那些角色现在到底是什么摧毁了他的自信?他来这个病房究竟要干什么?一幅自我戏仿画像已然成形,此人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是一幅毫无所本的自我戏仿画,为什么就成这样了呢?这纯属时间流逝带来的衰落和崩溃吗?这是渐入老境的征兆吗?他的容貌依然令人赞叹。他的演员目标没有改变,为了表演好一个角色不辞辛苦进行准备的态度也没有改变。没有人比他更加殚精竭虑、勤勉辛苦、严肃认真,没有人比他更加惜乎自己的才华,或者更加善于调整自己以适应戏剧这个行当几十年来瞬息万变的形势。骤然间停顿了演艺生涯此事颇难解释,好像自己在沉睡之际一夜间卸除了身为职业演员的重负和实质。在舞台上讲话和聆听别人讲话的能力归根结底就是这个,但它又消失了。
他去找的精神科医生法尔博士询问,他遭遇的这一切是否果真没有明显原因,而且在他们每周两次的讨论中,请他仔细反省下这位医生所谓的一种常见噩梦突如其来之前自己的生活状况。他的意思是说,这位演员在戏剧舞台上的不幸遭遇登上舞台后却发现自己根本就演不了,这种不知所措的打击这种内容在人们做的跟自己有关的纷扰梦境中很常见。这里所谓的人们不是指像西蒙阿克斯勒这样的职业演员。上了舞台却不会演戏是很多病人在不同场合诉说的常见梦境。此外,有人梦见自己赤身裸体行走在熙熙攘攘的城市大街上,有人梦见自己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参加一场事关重大的考试,有人梦见自己从一道悬崖上坠落下来,有人梦见自己在高速公路上发现车闸失灵了。法尔医生要阿克斯勒谈谈他的婚姻、父母的死亡、跟毒瘾缠身的继子之间的关系、童年时代、青春期、步入演员职业的开端、他二十岁时死于红斑狼疮的姐姐等情况。医生想听听他最近几个星期和几个月来在肯尼迪中心出场的具体细节,想了解他是否还能想得起发生在这段时间的大大小小的事件。阿克斯勒努力做到陈述时忠实原貌,以便让自己的病根暴露出来而且借此可以恢复自己的能力可是他所能告诉的这一切,坐在这位充满同情心和凝视聆听的心理医生对面诉说的任何东西,都不是引起这个常见噩梦的原因。相反,这样倒变本加厉地催生出新的噩梦。可是他仍然没有放弃向医生倾诉,每次他都照来不误。干吗不试试呢?痛苦到某个份儿上,你就会不惜一切来解释自己出了什么问题,纵然知道什么都解释不了,而且接二连三的解释均告失败。
在医院住了二十多天之后,某天晚上,阿克斯勒没有像平时那样,在夜里两三点钟醒来后在恐惧中毫无睡意地躺到天亮,而是一觉睡到早晨八点钟。按照医院的标准,这个时候已经晚到需要护士上房间来叫醒他跟别的病人去餐厅吃七点三刻开张的早点,然后开始当天的活动,包括小组治疗、艺术治疗、一场跟法尔医生的咨询、一场跟理疗师的讨论,这位女医师正竭尽全力医治他的慢性脊椎疼痛。清醒的每个小时,各种活动和会见安排得满满的,目的是为了不要让患者回到房间忧郁沮丧,痛苦不堪地躺在自己的床上,不要像某些人那样,晚上围拢在一起探讨曾经尝试过的自杀手法。
有好几次,阿克斯勒跟那伙要自杀的病人坐在娱乐室的角落,听他们回忆策划一死了之的那股热忱劲儿,然后又哀叹没有如愿以偿。每个人依然沉浸在自杀企图的崇高的幻觉中,为最终活了下来而感到羞耻难当。有人真的下得了手、真的能控制自己的死亡,这种境界让他们所有的人迷恋不已这是他们天经地义的话题,就像男孩子谈论体育运动一样。有些人把那种感觉描述得非常像一个精神变态者杀害别人时产生的冲动,当他们打算自杀时会铺天盖地涌过来。一个年轻女人说:你好像对自己、对周围的每个人都麻木不仁而且完全无动于衷,可是你却能做出最困难的行为的决定。这令人欣喜,令人鼓舞,令人痛快。没错,某人会说,这里有某种残忍的快感。你的生命在瓦解,已经失去了核心,而自杀是一种你能控制的行为。一个年迈的老人,一个曾想在车库吊死自己的退休中学教师,向他们发表过一场关于外行如何看待自杀的演讲。人们总想解释自杀是怎么回事,解释它,评判它。对那些事后幸存者来说,需要找个方式来思索它,这想来简直令人惊心。有人觉得自杀是懦弱的行为,有人觉得自杀是犯罪,是针对活人的犯罪。另有一派思想认为自杀是英雄壮举,是勇敢的行为。于是就有了纯粹主义者的主张。对他们来说这个问题就变成了: 自杀是正当的吗,有充分的根据吗?心理医生的观点更具临床色彩,既没有惩罚的意味,也不予理想化,只是想描述自杀的精神状态: 他自杀时处于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此人每晚都不厌其烦地沿着这条思路苦思冥想,似乎他不跟别人一样是个备受煎熬的患者,而是一个客座讲师,请来阐述这个让大伙昼夜寝食不安的话题。一天晚上,阿克斯勒忽然开始夸夸其谈他意识到这是在表演,是放弃表演以来当着最多一群观众的表演。自杀是你们替自己写的一出戏,他告诉大家,你们依附于这出戏而存在,表演这出戏。全都是精心的舞台设计人们在什么地方找到你们,以及如何找到你们,都做过精心设计。他又补充了一句,只许演一次的戏。
在他们的谈话中,丁点儿隐私都痛快地昭然若揭,而且暴露得寡廉鲜耻。好像自杀是多么崇高的目标,而活着是多么可恶的状态。因为演过好几部电影,阿克斯勒碰到的某些患者立刻认出他来,可是这些人完全沉溺在自己的苦苦挣扎中,对他的关注程度绝对不会超过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普通人。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阿克斯勒在戏剧界的赫赫声名根本不可能让他们分神太久。在这家医院,他不仅完全不获得别人的认可,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
从他再次发现睡了个通宵的奇迹的刹那,不得已被护士叫醒吃早饭之后,他就开始感觉到那种可怕的昏沉了。他们在未经本人许可的情况下给他服了一种治疗精神忧郁的药物,然后又服了一次。最后,服完第三次后并没有引发什么难以忍受的副作用,但是至于有什么好作用,他自己都说不上。他绝不相信自己的好转跟药物、心理咨询、集体治疗、艺术治疗,所有这些感觉恍若空洞无物的训练有任何关系。随着出院时间逐渐临近,继续让他感到恐惧的是,自己身上发生的这一切好像查不出别的原因。当他告诉法尔医生此人也在竭尽所能,试图在他们会面探讨时找出个原因来让自己更感心安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他却丧失了作为演员的魅力,而且好像不由分说那种结束自己生命的欲望开始退潮,至少暂时如此吧。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没有什么理由好说的。那天晚些时候他对医生说,得之失之世事从来无常。无常的威力无限巨大。颠倒翻转大有可能。没错,随时有不可预料的逆转,力量格外强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