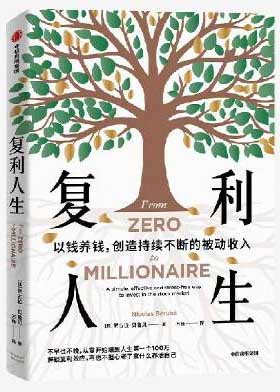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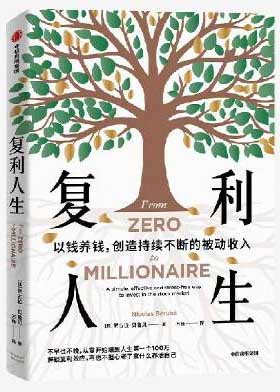
《
复利人生
》
售價:NT$
352.0

《
中国绘画:元至清(巫鸿“中国绘画”系列收官之作,重新理解中国绘画史)
》
售價:NT$
857.0

《
这里,群星闪耀:乒坛典藏·绽放巴黎(全套7册)
》
售價:NT$
1204.0

《
想通了:清醒的人先享受自由
》
售價:NT$
281.0

《
功能训练处方:肌骨损伤与疼痛的全周期管理
》
售價:NT$
653.0

《
软体机器人技术
》
售價:NT$
454.0

《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
》
售價:NT$
347.0

《
奴隶船:海上奴隶贸易400年
》
售價:NT$
352.0
|
| 編輯推薦: |
|
从三联版24种钱穆作品系列中精选8种,涵括作者一生对经学、史学和哲学的精研和深思。如对孔子和《论语》的典范研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不同领域、不同专题的会通博识、深入浅出;而作者分别在青年和耄耋之年对宇宙自然、政治社会和德性修为的观照和感悟,无论是闲思还是盲言,都洞彻天地,启悟来者。
|
| 內容簡介: |
|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钱穆先生的专题演讲合集,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
| 關於作者: |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 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 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 。他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大陆、香港、台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 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
| 目錄:
|
序
前言
第一讲汉代
一、汉代政府组织
甲、皇室与政府
乙、中央政府的组织
丙、汉代地方政府
丁、中央与地方之关系
二、汉代选举制度
三、汉代经济制度
四、汉代兵役制度
五、汉制得失检讨
第二讲唐代
一、唐代政府组织
甲、汉唐相权之比较
乙、唐代中央政府三省职权之分配
丙、中央最高机构政事堂
丁、尚书省与六部
戊、唐代地方政府
己、观察使与节度使
二、唐代考试制度
甲、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九品中正制
乙、唐代之科举
三、唐代经济制度
甲、唐代的租府调制
乙、唐代账籍制度
丙、唐代的两税制
丁、汉唐经济财政之比较
四、唐代兵役制度
五、唐代制度综述
第三讲宋代
一、宋代政府组织
甲、宋代中央政府
乙、相权之分割
丙、君权之侵揽
丁、谏垣与政府之水火
戊、宋代地方政府
二、宋代考试制度
三、宋代赋税制度
四、宋代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
第四讲明代
一、明代的政府组织
甲、明代之中央政府
乙、明代内阁制度
丙、明代地方政府
丁、元明以下之省区制度
戊、明代地方之监司官与督抚
己、明清两代之胥史
二、明代考试制度
甲、进士与翰林院
乙、八股文
三、明代赋税制度
四、明代兵制
第五讲清代
一、制度与法术
二、清代的部族政权
三、清代部族政权下的政府
甲、清代中央政府
子、清代的军机处
丑、清代的六部尚书
乙、清代地方政府
丙、清代的各禁区
四、部族政权下之考试制度
五、清代的统制政策
六、民众的反抗运动
七、变法与革命
总论[1]
|
| 內容試閱:
|
犹记风吹水上鳞
敬悼钱宾四师
余英时
海滨回首隔前尘,犹记风吹水上鳞。
避地难求三户楚,占天曾说十年秦。
河间格义心如故,伏壁藏经世已新。
愧负当时传法意,唯余短发报长春。
八月三十一日深夜一时,入睡以后突得台北长途电话,惊悉钱宾四师逝世。悲痛之余,心潮汹涌,我立刻打电话到钱府,但钱师母不在家中,电话没有人接、所以我至今还不十分清楚钱先生(我一直是这样称呼他的,现在仍然只有用这三个字才能表达我对他的真实情感)逝世的详情,不过我先后得到台北记者的电话已不下四五起,都说他是在很安详的状态下突然去的,这正是中国人一向所说的无疾而终。这一点至少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今年七月,我回到台北参加中央研究院的会议,会后曾第一次到钱先生的新居去向他老人家问安。想不到这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了,走笔至此禁不住眼泪落在纸上。
最近十几年,我大概每年都有机会去台北一两次,多数是专程,但有时是路过。而每次到台北,无论行程怎么匆促,钱先生是我一定要去拜谒的。这并不是出于世俗的礼貌,而是为一种特殊的情感所驱使。我们师生之间的情感是特别的,因为它是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四十年来,这种情感已很难再用师生两个字说明它的内容了。但最近两三年来,我确实感到钱先生的精神一次比一次差。今年七月初的一次,我已经不敢说他是否还认识我了。但是他的身体状态至少表面上还没大变化。所以他的突然逝世对我还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
我对于钱先生的怀念,绝不是短短一两篇,甚至三五篇逝世纪念那种形式化的文字所能表达得出来的,而且我也绝不能写那样的文字来亵渎我对他老人家的敬爱之情。所以我现在姑且回想我最初认识他的几个片断,为我们之间四十年的师生情谊留下一点最真实的见证,同时也稍稍发抒一下我此时的哀痛。以后我希望有机会写一系列文字来介绍他的思想和生平,但那必须在我的情绪完全平复以后才能下笔。
我在前面所引的诗是我五年以前祝贺钱先生九十岁生日的四首律诗的最后一首,说的正是我们在香港的那一段岁月。我第一次见到钱先生是一九五零年的春天,我刚刚从北京到香港,那时我正在北京的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我最初从北京到香港,自以为只是短期探亲,很快就会回去的。但是到了香港以后,父亲告诉我钱先生刚刚在这里创办了新亚书院,要我去跟钱先生念书。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带我去新亚的情形。钱先生虽然在中国是望重一时的学者,而且我早就读过他的《国史大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曾在燕大图书馆中参考过《先秦诸子系年》,但是他在香港却没有很大的号召力。当时新亚书院初创,学生一共不超过二十人,而且绝大多数是从大陆来的难民子弟,九龙桂林街时代的新亚更谈不上是大学的规模,校舍简陋得不成样子,图书馆则根本不存在:整个学校的办公室只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一张长桌已占满了全部空间。我们在长桌的一边坐定不久,钱先生便出来了。我父亲和他已见过面。他们开始寒暄了几句。钱先生知道我愿意从燕京转来新亚,便问问我以前的读书情况。他说新亚初创,只有一年级。我转学便算从二年级的下学期开始,但必须经过一次考试,要我第二天来考。我去考试时,钱先生亲自出来主持,但并没有给我考题,只叫我用中英文各写一篇读书的经历和志愿之类的文字:交卷以后,钱先生不但当场看了我的中文试卷,而且接着又看我的英文试卷。这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知道钱先生是完全靠自修成功的,并没有受到完整的现代教育、他怎么也会看英文呢?我心中不免在问。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在写完《国史大纲》以后,曾自修过一年多的英文,但当时我是不知道的。阅卷之后,钱先生面带微笑,这样我便被录取了,成为新亚书院文史系二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了。这是我成为他的学生的全部过程。现在回想起,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引以自傲的事。因为钱先生的弟子尽管遍天下,但是从口试、出题、笔试、阅卷到录取,都由他一手包办的学生,也许我是唯一的一个。
钱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虽小,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同时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他是一个十分严肃、不苟言笑的人。但是这个感觉是完全错误的,不过等到我发现这个错误,那已是一两年以后的事了。
当时新亚学生很少,而程度则参差不齐。在国学修养方面更是没有根基,比我还差的也大有人在。因此钱先生教起课来是很吃力的,因为他必须尽量迁就学生的程度。我相信他在新亚教课绝不能与当年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时相提并论。我个人受到他的教益主要是在课堂之外。他给我的严肃印象,最初使我有点敬而远之。后来由于新亚师生人数很少,常常有同乐集会,像个大家庭一样,慢慢地师生之间便熟起来了。熟了以后,我偶尔也到他的房间里面去请教他一些问题,这样我才发现他真是即之也温的典型。而后来我父亲也在新亚兼任一门西洋史,他常常和我们一家人或去太平山顶或去石澳海边坐茶馆,而且往往一坐便是一整天,这便是上面所引诗中的犹记风吹水上鳞了。钱先生那时偶尔还有下围棋的兴趣,陈伯庄先生是他的老对手,因为两人棋力相等。我偶尔也被他让几个子指导一盘,好像我从来没有赢过。
这样打成一片以后,我对钱先生的认识便完全不同了。他原本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而又深厚的人。但是他毕竟有儒学的素养,在多数情况下,都能够以理驭情,恰到好处。我只记得有一次他的情感没有完全控制好,那是我们一家人请他同去看一场电影,是关于亲子之情的片子。散场以后,我们都注意到他的眼睛是湿润的。不用说,他不但受了剧情的感染,而且又和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他在怀念着留在大陆的子女。但这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敬爱。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他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