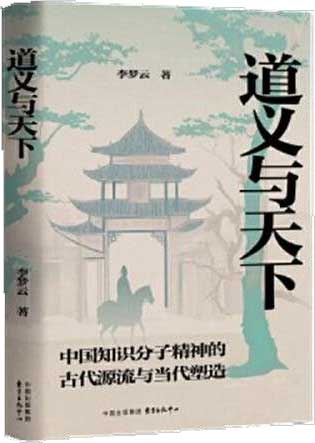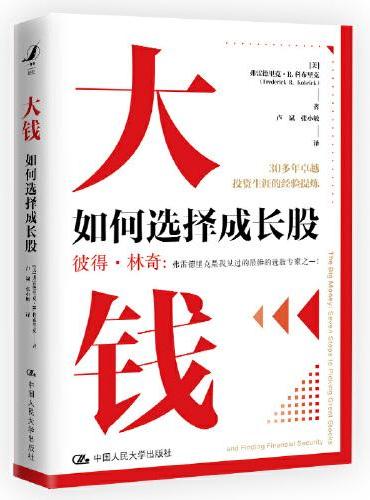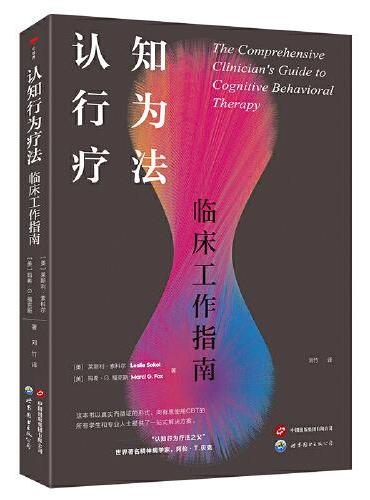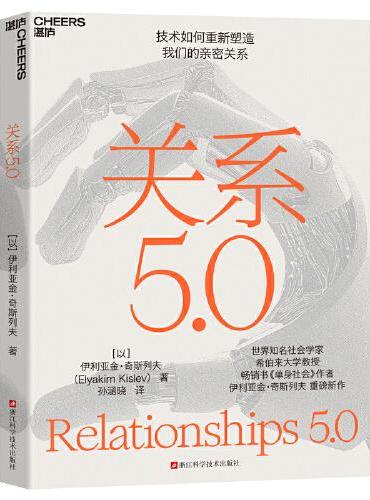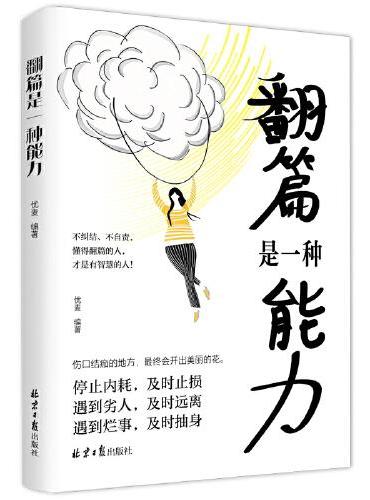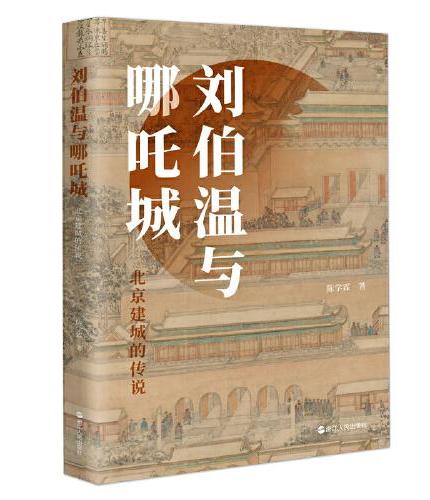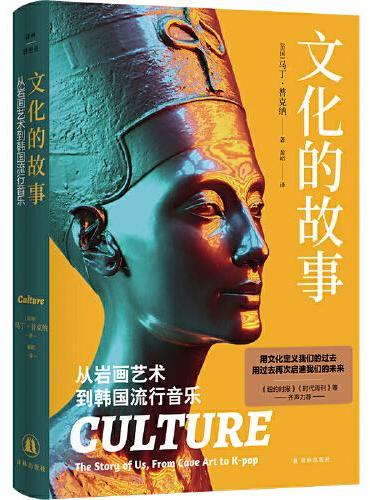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诗经》全注全译全本彩图 全书系列50万册焕新升级典藏纪念版
》
售價:NT$
25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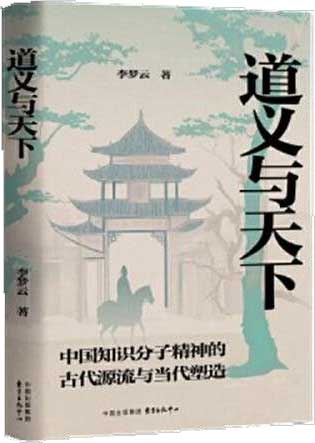
《
道义与天下: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古代源流与当代塑造
》
售價:NT$
4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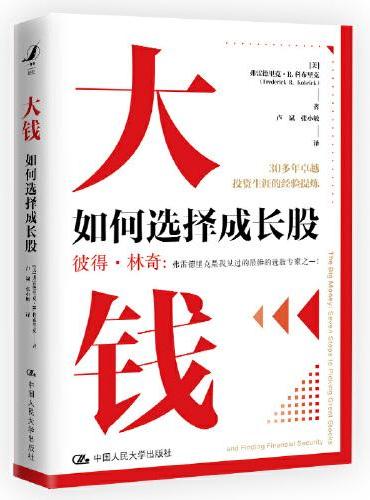
《
大钱:如何选择成长股
》
售價:NT$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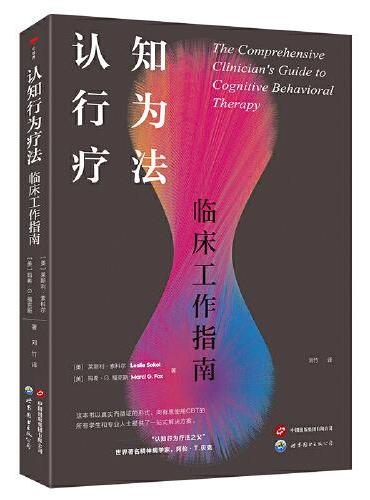
《
认知行为疗法:临床工作指南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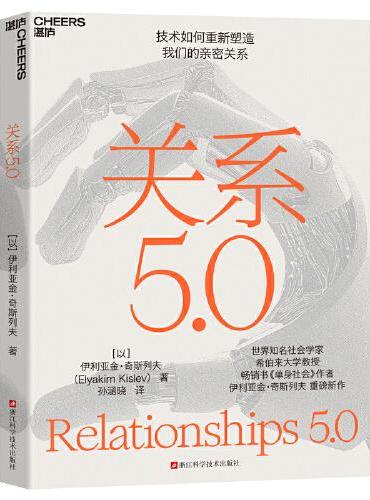
《
关系5.0
》
售價:NT$
6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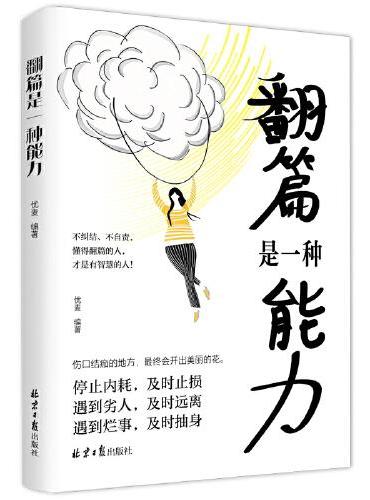
《
翻篇是一种能力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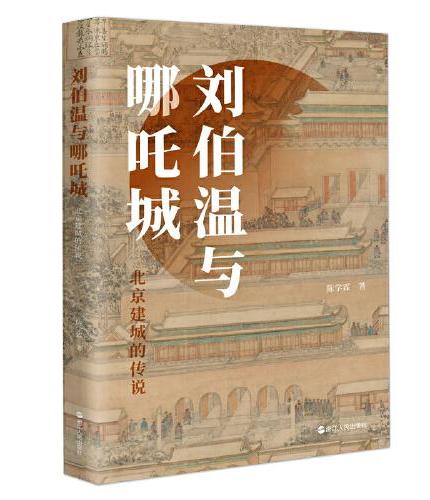
《
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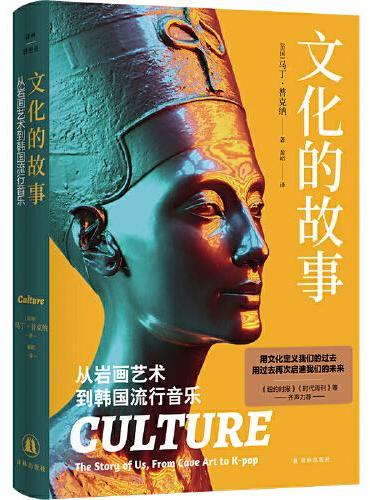
《
文化的故事:从岩画艺术到韩国流行音乐(译林思想史)哈佛大学教授沉淀之作 获奖不断 全球热销 亲历文化史上的15个关键点 从史前艺术到当代韩流的人类文化全景
》
售價:NT$
398.0
|
| 編輯推薦: |
★季羡林、郑振铎盛赞的作家。胡也频的一生是短暂而又辉煌的。英年早逝,与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并称为左联五烈士。季羡林曾评:胡也频,这个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和文学史上宛如夏夜流星一闪即逝但又留下永恒光芒的人物。
★再现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优秀品质。本书作为一部作品集,收录了胡也频的多篇小说作品,尤以《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为主,故事主人公刘希坚为了革命信仰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崇高精神,甚为感人动情。和平年代里,我们需要一种主心骨的精神来感召时代青年,唤醒爱国意识。
★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为献礼百年荣耀时刻专门设计,收入作品皆为名家名作,旨在重温红色经典,缅怀先烈,传承革命精神,弘扬爱国主义。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一部作品集,主要集合了左翼作家胡也频的多篇小说作品,包括《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中秋节》《北风里》《不能忘的影》《珍珠耳坠子》《初恋的自白》《小小的旅途》。其中,《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为一部中篇小说,剩余篇章均为短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是作家胡也频的代表作。作品以五卅运动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女青年白华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故事。白华的男友刘希坚是一名共产党员,刚开始他们两个人经常因为各自的政治信仰而产生争辩。五卅运动爆发后,大批的青年被枪杀,血的教训终于使白华认清了现实,抛弃了自己之前坚持的无政府主义,进而转向共产主义。小说表现力强,情节精练紧凑,扣人心弦,是胡也频创作思想转变的智慧结晶。
|
| 關於作者: |
|
胡也频,别名胡崇轩,作家,福建福州人。192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当选为左联执行委员,并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193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选为出席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与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并称为左联五烈士。著有小说《光明在我们前面》《到莫斯科去》等。
|
| 目錄:
|
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中秋节
北风里
不能忘的影
珍珠耳坠子
初恋的自白
小小的旅途
媒体评论胡也频,这个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和文学史上宛如夏夜流星一闪即逝但又留下永恒光芒的人物。
季羡林(文学家)
在白色恐怖压制密不透风时,这个文弱青年,敢于举起一面斗争的旗帜,写出《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这种警笛似的作品。
《文艺报》
在线试读干什么?她笑得仰起来摇了两下头,那黑丝一般的头发便披散到脸上,从其中隐现着脸颊的颜色,就象是一些水红色牡丹花的花瓣。
我不会为那样的人白费我的时间,她充满着得意的,又带着天真的快乐的声音继续说:我现在说他就因为他使我觉得太可笑了。那样的人,斜眼睛,蠢猪!你想他居然做了些什么蠢事?你不知道?当然!谁都想不出。他,瞧那蠢样子,他简直见鬼了,忽然找到我当我昨天从学校里出来的时候他开头就说:我在这里等了两点多钟呢。便伸过手来想同我握。谁喜欢和他握手?我只问:你等着你的朋友么?再见。他忽然蠢蠢的摇一下头,把眼睛瞧着我斜的,大约是瞧着我吧,一面说:我只等你呵!见你的鬼呢!我这样想,一面给他一个很尊严的脸色,使他知道他的话是错的,不应该和冒昧的,一面冷淡的说:等我?我们没有什么事情要说呀。好,再见!说完我就快步的走了。可是他又蠢里蠢气的跟了来。我装做不看见,走了好远,我以为他走开了,回头一看,又看见了那双斜眼睛。我真的冒火了:密司特陈,你这样跟着我,是不应该的,你知道么?他却现出一副哭丧的脸,吱吱的回答说:知道。并且又蠢蠢的走拢来,接着说:知道。但是但是但是什么呢?我被他的哭声觉得可笑了。我有几句话想同你说,他又吱吱的接下说:我们到中央公园去说好不好?谁愿意同你逛公园!我气愤了。不是逛公园。只是只是因为这里不大不大方便。他的样子简直蠢极了。我只好冷冷的说:有什么事,请说吧。于是他就做出一种特别的蠢气,用斜眼睛呆看着我又象是呆看着别的地方,开始说他简直沾污了这一句话说他爱我!我在他的脸上看一下那样蠢得可怜我反乐了。我忍不住笑的说:你爱我,真的么?真的真的他仿佛就要跪下来发誓了。你不爱你的妻子么?我又笑着问。不爱,一点也不爱,他惶恐的说:真的一点也不爱。我那里会爱她!哼!你倒把你自己看得满不凡呢!我一面想着一面又问:你的小孩子呢?也不爱。把他们怎么办呢?他以为满有希望似的伸过手来说:如果如果你我都不爱他们。好极了,于是我忍不住的便给他一个教训:你把爱情留着吧,不是前门外有许多窑子么?说完我跳上一辆洋车了
她说完这故事又天真地狂笑起来,同时她的眼睛又流盼着对面的男子,仿佛是在示意:你瞧,他那配爱我?
希坚却不觉得那个蠢人的可笑,只觉得可怜。并且为了她的生动的叙述而沈思着,觉得她很富饶文学的天才
忽然象一种海边的浪似的声音从他的耳边飞过去了:干什么?她笑得仰起来摇了两下头,那黑丝一般的头发便披散到脸上,从其中隐现着脸颊的颜色,就象是一些水红色牡丹花的花瓣。
我不会为那样的人白费我的时间,她充满着得意的,又带着天真的快乐的声音继续说:我现在说他就因为他使我觉得太可笑了。那样的人,斜眼睛,蠢猪!你想他居然做了些什么蠢事?你不知道?当然!谁都想不出。他,瞧那蠢样子,他简直见鬼了,忽然找到我当我昨天从学校里出来的时候他开头就说:我在这里等了两点多钟呢。便伸过手来想同我握。谁喜欢和他握手?我只问:你等着你的朋友么?再见。他忽然蠢蠢的摇一下头,把眼睛瞧着我斜的,大约是瞧着我吧,一面说:我只等你呵!见你的鬼呢!我这样想,一面给他一个很尊严的脸色,使他知道他的话是错的,不应该和冒昧的,一面冷淡的说:等我?我们没有什么事情要说呀。好,再见!说完我就快步的走了。可是他又蠢里蠢气的跟了来。我装做不看见,走了好远,我以为他走开了,回头一看,又看见了那双斜眼睛。我真的冒火了:密司特陈,你这样跟着我,是不应该的,你知道么?他却现出一副哭丧的脸,吱吱的回答说:知道。并且又蠢蠢的走拢来,接着说:知道。但是但是但是什么呢?我被他的哭声觉得可笑了。我有几句话想同你说,他又吱吱的接下说:我们到中央公园去说好不好?谁愿意同你逛公园!我气愤了。不是逛公园。只是只是因为这里不大不大方便。他的样子简直蠢极了。我只好冷冷的说:有什么事,请说吧。于是他就做出一种特别的蠢气,用斜眼睛呆看着我又象是呆看着别的地方,开始说他简直沾污了这一句话说他爱我!我在他的脸上看一下那样蠢得可怜我反乐了。我忍不住笑的说:你爱我,真的么?真的真的他仿佛就要跪下来发誓了。你不爱你的妻子么?我又笑着问。不爱,一点也不爱,他惶恐的说:真的一点也不爱。我那里会爱她!哼!你倒把你自己看得满不凡呢!我一面想着一面又问:你的小孩子呢?也不爱。把他们怎么办呢?他以为满有希望似的伸过手来说:如果如果你我都不爱他们。好极了,于是我忍不住的便给他一个教训:你把爱情留着吧,不是前门外有许多窑子么?说完我跳上一辆洋车了
她说完这故事又天真地狂笑起来,同时她的眼睛又流盼着对面的男子,仿佛是在示意:你瞧,他那配爱我?
希坚却不觉得那个蠢人的可笑,只觉得可怜。并且为了她的生动的叙述而沈思着,觉得她很富饶文学的天才
忽然象一种海边的浪似的声音从他的耳边飞过去了:
你在想什么呀?
他立刻注视到她的脸:
想你你写小说一定写得很好的。
女人的天性总喜欢男子的恭维。而他的这一句话,更象她在睡觉以前吃着橘子水,甜汁汁的非常受用,便不自禁的向他望了一眼,那是又聪明,又含蓄,又柔媚的眼光啊。
他的心又开始动摇了惶惑地,而且迷路了,但不象什么迷路的鸟儿,却是象一只轮子似的在爱情的火焰里打圈。所以他的眼睛虽然看着白华的脸,而暗中却在想:假使我向你表示呢?于是把她的一句那我学音乐呢?的问话也忽略了。
你觉得怎样?她接着又问。
他的脑筋才突然警醒地振作一下,便找出很优雅的答话了:
我在想,他的态度很从容地,微笑地。究竟你学文学对于音乐有没有损失呢?结果是: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两方面同时用功于是他等着这些话的回响。
自然,她又给他更迷惑的眼光。但是这意中的报酬却使他难受透了。他想着考虑着又决不定在这种氛围里,在这种情调中,在这个房间内,究竟是不是一个向她表示爱情的最适宜的时机。他觉得有点苦闷了。但他仍然忍着听她的话。
可是别人都不相信我呢,她带点骄傲的声音说:你是第一接着又向他柔媚地笑一笑。
他乘机进一步说:是的,那些人只会在纸上看文章。
她完全接受了他的话,并且向他吐出心腹来了:
我曾经写过好几篇散文她真心的说。
在那里?发表过么?他热情地看住她。
都扯了。她低了声音说。
唉他惋惜之后又问:为什么把它扯了呢?这简直是一个损失。
我不相信自己
以后可不要扯不的确不应该扯!
她没有说什么,只现着满意的笑。于是他又极力怂恿她,给了她许多鼓励。
但当他还赞美她的性格可以在舞台上装沙乐美[沙乐美:原文如此,今通译为莎乐美,英国作家王尔德所作同名戏剧中女主角的名字。]的时候,也就是在他们的情感更融洽的时候,房门上却响起叩门的声音,他和她都现着讨厌的神气把眼睛望到门上去。
谁?她更是不高兴的问。
自由人无我!门外的人一面报名一面进来了,是一个有心不修边幅的长头发的瘦子,可以在浪漫派的小说中作为颓废又潇洒的代表人物。他很冷淡地向刘希坚点一点头,便故意表示亲热地走过去和白华握了手,又说:
我把新村的图案画好了,拿来给你看一看。便把一个纸卷摊开了。
显然,白华是不喜欢这位同志(看她只懒懒的和他握手便明白),但她却为那新村的图案而迷惑了,聚精会神地站着看。她也忘了这房子里还有另一个人
希坚便一个人孤独地坐在一边,他慢慢的感到被人冷视的气愤了,但他又用天真的字眼去原谅她的确她是天真的,她还一点也不懂得世故呢。于是他等着,吸上香烟,却终于想走,但正要动身,又被那位中国的安那其同志的言论而留住了。他静静的听着:
这就是整个新村,那位自由人无我很傲然地,一面又狂热地在纸上划来指去的说:我们可以名做无政府新村,这里分为东西两区域你不看见么?东边是男区,全住着男子;西边是女区,全住着女人;东西两区之间是大公园我们可以名做恋爱的天堂让男女在那里结合,而完成安那其的理想:恋爱自由!
放屁!希坚只想从中叫出来了。
这时那位理想家又发出妙论:
住在村里的人都不行吃饭自然吃面包也不行,只行吃水果。接着他说出他的理由吃水果可以把身体弄成纯洁的。
希坚简直耐不住了,他一下跳起来,朝着白华的背影说:
我走了!
她忽然跑过来了(大约有点抱歉的缘故),便亲切的捉住他的手,把脸颊几乎贴在他肩臂上,眼睛翻着望他,完全用温柔的声音说:
就走么?好的。吃过晚饭我到你那里来并且多情得象一个小孩子。
好吧。
希坚短削的回答,便什么都不看,昂然地走了。
三
马路上的阳光已经不见了,只在老柳树的尖梢上还散着金黄的闪烁。北京大学是刚刚下课,路上正现着许多学生,他们的臂膀下都挟着讲义和书本,大踏步的走,露着轻松的神情。刘希坚从这些活泼的人群中很悒郁的走出了马神庙。
先生,洋车!
他不坐车,只用他自己的脚步。他差不多是完全沈默的,微微的低着头,傍着古旧的皇城根,在景山西街走着,走得非常之慢。
这一条马路是非常僻静的。宽的马路的两旁排列着柳树,绿荫荫地,背后衬着黄瓦和红色的墙,显出一种帝都的特色,也显出一种衰落的气象。路上的行人少极了,树荫中的鸟语却非常繁碎。这地方是适宜于散步的,更适宜于古典诗人的寻思
但他对于这景色是完全忽略的美的或者丑的景物都与他无关,一点也不能跑进他的意识。他是因刚才的经过而扰乱着他的全部思想了。
他一面走着一面想起许多很坏的印象那个自由人无我,便是这印象之一。滚你的吧!他想起那新村的胡说便低声的骂了。但接着这是非常可惋惜的他又看见了白华站在那里看图的影子,他不禁的在心里叹息着:
唉,白华
而且,他带点痛苦的意味而想到她的笑态了。这笑态却使他联想到他自己在第三者面前受到她的冷视,心头便突突的飘上火焰。但他立刻又把这气愤压制着,并且把许多浮动的感情都制止了,因为他觉得,他是一切只应该用科学的头脑,不应该由心
于是,第一,他分析了他和她的关系,他冷静地把它分析起来:他认定自己是爱她的(这个爱在最近更显著),并且她也很爱他她有许多爱他的证据,但是他和她的爱情之中有一个很大的阻碍,那就是他们的思想他认为只是她的那些乌托邦的迷梦把他们的结合弄远了。
不,这是他分析的结果:她不会永远这样的,她总有一天会觉醒。
然而这信仰却使他忧郁起来了,因为他料不出她觉醒的时期。
我应该帮助她他想,于是又想起他和她已经经过的那许多纠纷。当他退出安那其而加入共产党的时候,他和她的冲突便开始了那是第一个。但是这冲突是接连着第二,第三,一直到现在。他是常常为这冲突而苦恼着的。他也常常都在作着扑灭这冲突的努力。他又常常为这努力而忍耐。为的他不能丢开她以及责备她。因为他是很了解她的:惟一,她只是太天真了。否则,他认为她不会为实际的社会运动反沉溺于乌托邦的迷梦。并且他相信:只要她再进一步去观察现实的社会,或者只要她能冷静一点把那安那其主义和二十世纪的世界作一个对照,那她一定会立刻把幻想丢弃了,把刚毅的信仰从克鲁泡特金的身上而移到马克思和列宁来。虽说她这时还受那许多糊涂同志的眩惑,也把她原谅了。他的职志只是乘机去帮助她,去把她从歧路的思想中救出来。可是,无论在什么时候,当他一说出抵触安那其的言论,她就不管事实,只凭着矜夸的意志,用狂热的感情来和他对抗,于是变成不是理论的辩证,而是无意识的争驳了。这样的结果很使他感到懊恼和痛苦,但没有失望。他是仍然继续进行着这努力去进行的。一有机会,他就用种种方法去唤醒她
她呢,每次都是很固执地红着脸的。当他把一切都用唯物论来解释的时候,她总是动着感情说:
各人信仰各人的。我只信仰我的唯心论。便什么都弄僵了。
让步的其实只是压制的又是他。因为他不愿他的行动也超出理性的支配,并且他不愿因这样的争执而损伤到他们尚在生长的爱情。所以他们每次的相见,都成为三个转变:开头是欢喜的握手,中间经过争论,随后用喜剧的煞尾。
但今天的情形却不同了。他离开她,完全是被迫的。那时,假使不是突然跑来了那位神经病的理想家,说不定在那种如同被花香所熏着的情调中,他和她的爱情的火花就会爆发起来,更说不定他还可以借着爱情的力量使她牺牲执见,使她用客观的眼光来观察这现实的社会,而成为他的共产主义的同志
的确,他带点惘然的回想,今天算是失掉了一个好机会。因此便想到那个自由人无我划来指去的样子,他几乎要出声了:
简直是糊涂蛋!
接着他在心里很沈重地轻蔑了那些中国的无政府党人,他觉得他们是戴着安那其主义的面幕,而躲在时代的后头,躺在幻想的摇篮里,做着个人享乐的迷梦,无聊之极。
然而白华,唉!他重新又惋惜到她了。她的影子便又浮到眼前来。但他所看见的却是那天真的,任性的,骄纵的,但又很迷人的,妩媚的,温柔的,她的完全的性格和她的一切风姿。随后是那双圆圆的,大的黑的,特别充满着女性魅力的眼睛,又使他感到爽然的一种愉快了。
|
| 內容試閱:
|
“;干什么?”;她笑得仰起来摇了两下头,那黑丝一般的头发便披散到脸上,从其中隐现着脸颊的颜色,就象是一些水红色牡丹花的花瓣。
“;我不会为那样的人白费我的时间,”;她充满着得意的,又带着天真的快乐的声音继续说:“;我现在说他就因为他使我觉得太可笑了。那样的人,斜眼睛,蠢猪!你想他居然做了些什么蠢事?你不知道?当然!谁都想不出。他,瞧那蠢样子,他简直见鬼了,忽然找到我—;—;当我昨天从学校里出来的时候—;—;他开头就说:‘;我在这里等了两点多钟呢。’;便伸过手来想同我握。谁喜欢和他握手?我只问:‘;你等着你的朋友么?再见。’;他忽然蠢蠢的摇一下头,把眼睛瞧着我—;—;斜的,大约是瞧着我吧,一面说:‘;我只等你呵!’;‘;见你的鬼呢!’;我这样想,一面给他一个很尊严的脸色,使他知道他的话是错的,不应该和冒昧的,一面冷淡的说:‘;等我?我们没有什么事情要说呀。好,再见!’;说完我就快步的走了。可是他又蠢里蠢气的跟了来。我装做不看见,走了好远,我以为他走开了,回头一看,又看见了那双斜眼睛。我真的冒火了:‘;密司特陈,你这样跟着我,是不应该的,你知道么?’;他却现出一副哭丧的脸,吱吱的回答说:‘;知道。’;并且又蠢蠢的走拢来,接着说:‘;知道。但是—;—;但是—;—;’;‘;但是什么呢?’;我被他的哭声觉得可笑了。‘;我有几句话想同你说,’;他又吱吱的接下说:‘;我们到中央公园去说好不好?’;‘;谁愿意同你逛公园!’;我气愤了。‘;不是逛公园。只是—;—;只是因为这里不大—;—;不大方便。’;他的样子简直蠢极了。我只好冷冷的说:‘;有什么事,请说吧。’;于是他就做出一种特别的蠢气,用斜眼睛呆看着我—;—;又象是呆看着别的地方,开始说—;—;他简直沾污了这一句话—;—;说他爱我!我在他的脸上看一下—;—;那样蠢得可怜—;—;我反乐了。我忍不住笑的说:‘;你爱我,真的么?’;‘;真的—;—;真的—;—;’;他仿佛就要跪下来发誓了。‘;你不爱你的妻子么?’;我又笑着问。‘;不爱,一点也不爱,’;他惶恐的说:‘;真的一点也不爱。我那里会爱她!’;‘;哼!你倒把你自己看得满不凡呢!’;我一面想着一面又问:‘;你的小孩子呢?’;‘;也不爱。’;‘;把他们怎么办呢?’;他以为满有希望似的伸过手来说:‘;如果—;—;如果你—;—;我都不爱他们。’;‘;好极了,’;于是我忍不住的便给他一个教训:‘;你把爱情留着吧,不是前门外有许多窑子么?’;说完我跳上一辆洋车了…;…;”;
她说完这故事又天真地狂笑起来,同时她的眼睛又流盼着对面的男子,仿佛是在示意:“;你瞧,他那配爱我?”;
希坚却不觉得那个蠢人的可笑,只觉得可怜。并且为了她的生动的叙述而沈思着,觉得她很富饶文学的天才…;…;
忽然象一种海边的浪似的声音从他的耳边飞过去了:
“;你在想什么呀?”;
他立刻注视到她的脸:
“;想你—;—;你写小说一定写得很好的。”;
女人的天性总喜欢男子的恭维。而他的这一句话,更象她在睡觉以前吃着橘子水,甜汁汁的非常受用,便不自禁的向他望了一眼,那是又聪明,又含蓄,又柔媚的眼光啊。
他的心又开始动摇了—;—;惶惑地,而且迷路了,但不象什么迷路的鸟儿,却是象一只轮子似的在爱情的火焰里打圈。所以他的眼睛虽然看着白华的脸,而暗中却在想:“;假使我向你表示呢?…;…;”;于是把她的一句“;那我学音乐呢?”;的问话也忽略了。
“;你觉得怎样?”;她接着又问。
他的脑筋才突然警醒地振作一下,便找出很优雅的答话了:
“;我在想,”;他的态度很从容地,微笑地。“;究竟你学文学对于音乐有没有损失呢?结果是: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两方面同时用功…;…;”;于是他等着这些话的回响。
自然,她又给他更迷惑的眼光。但是这意中的报酬却使他难受透了。他想着—;—;考虑着—;—;又决不定—;—;在这种氛围里,在这种情调中,在这个房间内,究竟是不是一个向她表示爱情的适宜的时机。他觉得有点苦闷了。但他仍然忍着听她的话。
“;可是别人都不相信我呢,”;她带点骄傲的声音说:“;你是…;…;”;接着又向他柔媚地笑一笑。
他乘机进一步说:“;是的,那些人只会在纸上看文章。”;
她完全接受了他的话,并且向他吐出心腹来了:
“;我曾经写过好几篇散文…;…;”;她真心的说。
“;在那里?发表过么?”;他热情地看住她。
“;都扯了。”;她低了声音说。
“;唉…;…;”;他惋惜之后又问:“;为什么把它扯了呢?这简直是一个损失。”;
“;我不相信自己…;…;”;
“;以后可不要扯—;—;不—;—;的确不应该扯!”;
她没有说什么,只现着满意的笑。于是他又极力怂恿她,给了她许多鼓励。
但当他还赞美她的性格可以在舞台上装沙乐美[沙乐美:原文如此,今通译为莎乐美,英国作家王尔德所作同名戏剧中女主角的名字。]的时候,也就是在他们的情感更融洽的时候,房门上却响起叩门的声音,他和她都现着讨厌的神气把眼睛望到门上去。
“;谁?”;她更是不高兴的问。
“;自由人无我!”;门外的人一面报名一面进来了,是一个有心不修边幅的长头发的瘦子,可以在浪漫派的小说中作为“;颓废又潇洒”;的代表人物。他很冷淡地向刘希坚点一点头,便故意表示亲热地走过去和白华握了手,又说:
“;我把新村的图案画好了,拿来给你看一看。”;便把一个纸卷摊开了。
显然,白华是不喜欢这位同志(看她只懒懒的和他握手便明白),但她却为那新村的图案而迷惑了,聚精会神地站着看。她也忘了这房子里还有另一个人…;…;
希坚便一个人孤独地坐在一边,他慢慢的感到被人冷视的气愤了,但他又用“;天真”;的字眼去原谅她—;—;的确她是天真的,她还一点也不懂得世故呢。于是他等着,吸上香烟,却终于想走,但正要动身,又被那位中国的安那其同志的言论而留住了。他静静的听着:
“;这就是整个新村,”;那位“;自由人无我”;很傲然地,一面又狂热地在纸上划来指去的说:“;我们可以名做‘;无政府新村’;,这里分为东西两区域—;—;你不看见么?—;—;东边是男区,全住着男子;西边是女区,全住着女人;东西两区之间是大公园—;—;我们可以名做‘;恋爱的天堂’;—;—;让男女在那里结合,而完成安那其的理想:恋爱自由!”;
“;放屁!”;希坚只想从中叫出来了。
这时那位理想家又发出妙论:
“;住在村里的人都不行吃饭—;—;自然吃面包也不行,只行吃水果。”;接着他说出他的理由—;—;“;吃水果可以把身体弄成纯洁的。”;
希坚简直耐不住了,他一下跳起来,朝着白华的背影说:
“;我走了!”;
她忽然跑过来了(大约有点抱歉的缘故),便亲切的捉住他的手,把脸颊几乎贴在他肩臂上,眼睛翻着望他,完全用温柔的声音说:
“;就走么?好的。吃过晚饭我到你那里来…;…;”;并且多情得象一个小孩子。
“;好吧。”;
希坚短削的回答,便什么都不看,昂然地走了。
三
马路上的阳光已经不见了,只在老柳树的尖梢上还散着金黄的闪烁。北京大学是刚刚下课,路上正现着许多学生,他们的臂膀下都挟着讲义和书本,大踏步的走,露着轻松的神情。刘希坚从这些活泼的人群中很悒郁的走出了马神庙。
“;先生,洋车!”;
他不坐车,只用他自己的脚步。他差不多是完全沈默的,微微的低着头,傍着古旧的皇城根,在景山西街走着,走得非常之慢。
这一条马路是非常僻静的。宽的马路的两旁排列着柳树,绿荫荫地,背后衬着黄瓦和红色的墙,显出一种帝都的特色,也显出一种衰落的气象。路上的行人少极了,树荫中的鸟语却非常繁碎。这地方是适宜于散步的,更适宜于古典诗人的寻思…;…;
但他对于这景色是完全忽略的—;—;美的或者丑的景物都与他无关,一点也不能跑进他的意识。他是因刚才的经过而扰乱着他的全部思想了。
他一面走着一面想起许多很坏的印象—;—;那个“;自由人无我”;,便是这印象之一。“;滚你的吧!”;他想起那新村的胡说便低声的骂了。但接着—;—;这是非常可惋惜的—;—;他又看见了白华站在那里看图的影子,他不禁的在心里叹息着:
“;唉,白华…;…;”;
而且,他带点痛苦的意味而想到她的笑态了。这笑态却使他联想到他自己在第三者面前受到她的冷视,心头便突突的飘上火焰。但他立刻又把这气愤压制着,并且把许多浮动的感情都制止了,因为他觉得,他是一切只应该用科学的头脑,不应该由心…;…;
于是,,他分析了他和她的关系,他冷静地把它分析起来:他认定自己是爱她的(这个爱在近更显著),并且她也很爱他—;—;她有许多爱他的证据,但是他和她的爱情之中有一个很大的阻碍,那就是他们的思想—;—;他认为只是她的那些乌托邦的迷梦把他们的结合弄远了。
“;不,”;这是他分析的结果:“;她不会永远这样的,她总有一天会觉醒。”;
然而这信仰却使他忧郁起来了,因为他料不出她觉醒的时期。
“;我应该帮助她…;…;”;他想,于是又想起他和她已经经过的那许多纠纷。当他退出安那其而加入共产党的时候,他和她的冲突便开始了—;—;那是个。但是这冲突是接连着第二,第三,一直到现在。他是常常为这冲突而苦恼着的。他也常常都在作着扑灭这冲突的努力。他又常常为这努力而忍耐。为的他不能丢开她以及责备她。因为他是很了解她的:惟一,她只是太天真了。否则,他认为她不会为实际的社会运动反沉溺于乌托邦的迷梦。并且他相信:只要她再进一步去观察现实的社会,或者只要她能冷静一点把那安那其主义和二十世纪的世界作一个对照,那她一定会立刻把幻想丢弃了,把刚毅的信仰从克鲁泡特金的身上而移到马克思和列宁来。虽说她这时还受那许多糊涂同志的眩惑,也把她原谅了。他的职志只是乘机去帮助她,去把她从歧路的思想中救出来。可是,无论在什么时候,当他一说出抵触安那其的言论,她就不管事实,只凭着矜夸的意志,用狂热的感情来和他对抗,于是变成不是理论的辩证,而是无意识的争驳了。这样的结果很使他感到懊恼和痛苦,但没有失望。他是仍然继续进行着这努力去进行的。一有机会,他就用种种方法去唤醒她…;…;
她呢,每次都是很固执地红着脸的。当他把一切都用唯物论来解释的时候,她总是动着感情说:
“;各人信仰各人的。我只信仰我的唯心论。”;便什么都弄僵了。
让步的—;—;其实只是压制的—;—;又是他。因为他不愿他的行动也超出理性的支配,并且他不愿因这样的争执而损伤到他们尚在生长的爱情。所以他们每次的相见,都成为三个转变:开头是欢喜的握手,中间经过争论,随后用喜剧的煞尾。
但今天的情形却不同了。他离开她,完全是被迫的。那时,假使不是突然跑来了那位神经病的理想家,说不定在那种如同被花香所熏着的情调中,他和她的爱情的火花就会爆发起来,更说不定他还可以借着爱情的力量使她牺牲执见,使她用客观的眼光来观察这现实的社会,而成为他的—;—;共产主义的同志…;…;
“;的确,”;他带点惘然的回想,“;今天算是失掉了一个好机会。”;因此便想到那个“;自由人无我”;划来指去的样子,他几乎要出声了:
“;简直是糊涂蛋!”;
接着他在心里很沈重地轻蔑了那些中国的无政府党人,他觉得他们是戴着安那其主义的面幕,而躲在时代的后头,躺在幻想的摇篮里,做着个人享乐的迷梦,无聊之极。
“;然而—;—;白华,唉!”;他重新又惋惜到她了。她的影子便又浮到眼前来。但他所看见的却是那天真的,任性的,骄纵的,但又很迷人的,妩媚的,温柔的,她的完全的性格和她的一切风姿。随后是那双圆圆的,大的黑的,特别充满着女性魅力的眼睛,又使他感到爽然的一种愉快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