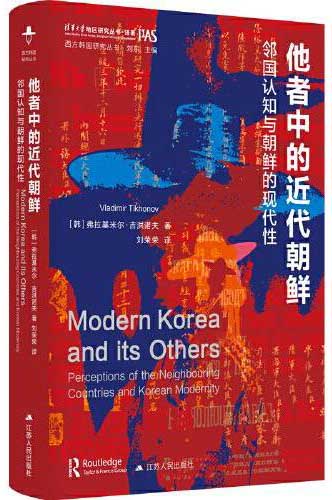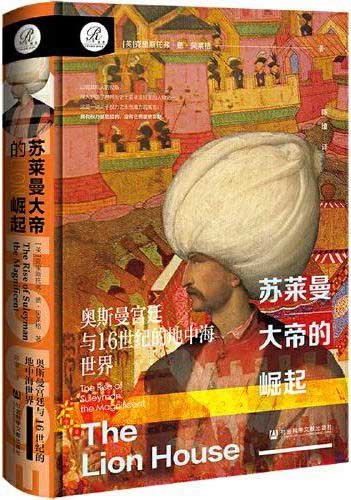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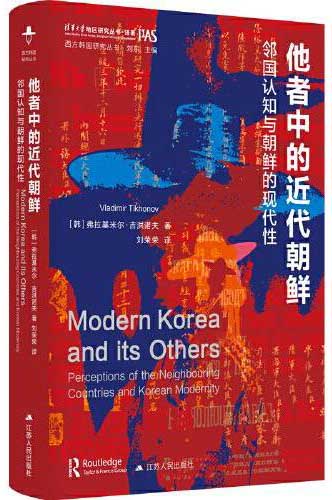
《
他者中的近代朝鲜(西方韩国研究丛书)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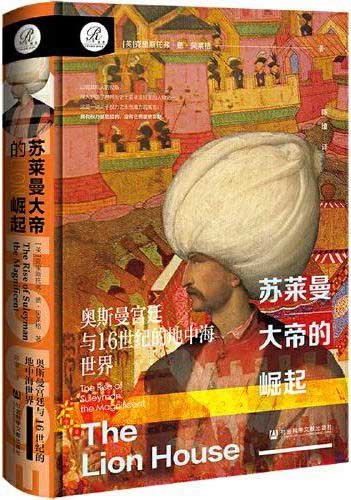
《
索恩丛书·苏莱曼大帝的崛起:奥斯曼宫廷与16世纪的地中海世界
》
售價:NT$
403.0

《
攀龙附凤: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增订本)宋代将门百年兴衰史
》
售價:NT$
454.0

《
金钱的力量:财富流动、债务、与经济繁荣
》
售價:NT$
454.0

《
超越想象的ChatGPT教育:人工智能将如何彻底改变教育 (土耳其)卡罗琳·费尔·库班 穆罕默德·萨欣
》
售價:NT$
352.0

《
应对百年变局Ⅲ:全球治理视野下的新发展格局
》
售價:NT$
398.0

《
前端工程化——体系架构与基础建设(微课视频版)
》
售價:NT$
454.0

《
《诗经》全注全译全本彩图 全书系列50万册焕新升级典藏纪念版
》
售價:NT$
2545.0
|
| 編輯推薦: |
※ 年近六十才开始文学创作,朱利安·巴恩斯、乔纳森·弗兰岑、A.S拜厄特的文学偶像,“简·奥斯汀继承人”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再次打破历史小说的桎梏,将目光投向人心的深处。
※“一战”前的剑桥校园里,一切都在动摇,原子和鬼魂一样不可观测掌控,爱情和信仰一般无法诉诸实在。
※ 特邀作家顾湘为本书创作封面,与《无辜》《离岸》《书店》《蓝花》《早春》构成作者系列,让读者全方位体会到佩奶奶的经典魅力。
|
| 內容簡介: |
看不见的灵魂,存在吗?看不见的原子,又存在吗?“一战”前的剑桥校园,物理研究员弗雷德的生活被诸如此类的问题所占据。
伦敦下层社会,母亲逝世后的黛西孤苦伶仃,打工接连遇到骚扰和解雇。在那个连女性选举权都需要争取的年代,坚强独立的她几乎走投无路。一场意外让她与弗雷德相遇,这会是一个奇迹吗?
在这里,真理以各种方式脱离了确定性:原子和鬼魂一样不可观测,爱情和信仰一般无法诉诸实在。1912年的世界站在一个门槛上,跨过去,一切将永远改变。
|
| 關於作者: |
|
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Penelope Fitzgerald, 1916-2000),2000年被《卫报》誉为英国文学优雅、独特的声音。她年近六十才开始文学创作,一生共创作了九部长篇小说,1979年凭借《离岸》获得布克奖。《蓝花》曾十九次被媒体评为“年度图书”,并获得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2008年,她被《泰晤士报》评选为“二战后伟大的五十位英国作家”之一。
|
| 目錄:
|
部分
1.弗雷德的三封信
2.圣安吉里克斯学院
3.弗雷德当初是如何得到这个职位的4.圣安吉里克斯学院的晚餐
5.在教区长住宅
6.在抗议者辩论社团
7.谁是黛茜?
第二部分
8.黛茜
9.黑修士医院
10.男病区
11.病人詹姆斯·埃尔德
12.凯利
13.黛茜离开伦敦
第三部分
14.黛茜的行踪并不神秘
15.乡间漫步
16.费尔里家人的到访第四部分
17.马修斯博士的鬼故事
18.不寻常的开庭
19.罪有应得的凯利
20.弗雷德给他学生的忠告
21.在萨杰医生的医院
22.天使之门
|
| 內容試閱:
|
第八章 黛西
黛西住在伦敦南部,斯托克韦尔和布里克斯顿的交接地带。这里的人太多,她倒是一直都习惯。人行道太窄了,容纳不下这里的住户,他们就蔓延到下水道盖子上,站在那里摆摊卖货——火柴、几个钱就能买到的铅玩具或锡玩具、年鉴、专利药品、笼鸟等等。待到夜幕降临,再也没了卖东西的指望,房子前门打开,仿佛把这些人收了进去,一同收进去的还有下班回来的工人,站在街口煤气灯下的传教士,孩子,醉汉,都进去了,后上了门闩。一旦离开了河边,离开了河边的仓库,伦敦南部的建筑低矮,但凡雾气退去,就可以看到大片的天空,天空按照自己的速度在移动,穿过太阳,穿过云朵,穿过点点繁星。
空气中混合着酸醋、杜松子酒、煤烟、煤油、硫磺,后院的马粪,后街工厂的漂白粉气味,还有每天清晨烤面包的香味,呼吸着这样的空气,黛西长大了。她很小的时候,家里很穷。这不好,但另一方面,这大城市应对自如,穷的人,富的人,都能在这里自得其所。市场上的摊位划分严格,便宜的东西聚集在一头。顾客没有半点装模做样,直接就去他们所属的区域。在便宜的一头,你可以买到牛蹄。不同于其他大多数的肉,牛蹄很不容易烹饪。煮牛蹄的锅子放在炉灶后面,一炖就是大半天,用桑德斯太太的话来说,到了后,要等它自己变得汤浓色白。长时间炖煮之后,抽出牛骨,用盘子盖住灰色的胶质牛筋,上面再压上扁平的铁块。下游有个胶水厂来收牛骨,但炖过的牛蹄真是卖不出什么钱来。
到了季度结算日,每家每户的邮箱里就多了一张传单:提前交房租。否则开夜车走人。那些人来搬你东西,都用手推车,动静比马车小。桑德斯一家,也就是母亲和女儿两个人,从来没有在同一条街上租过两次房子,但她们也不离开主战场。黛西的母亲在猎鹰啤酒厂工作,她只想在工作附近租房。黛西照顾婴儿。黛西没有自己的兄弟姐妹,但桑德斯太太说,这也是好事,否则从小就照顾弟弟妹妹,早就腻歪了。
黛西自然是有父亲的,但关于父亲的事情,她也说不出所以然。在黛西的出生证明上,他的职业是包装搬运工。他包装过什么,或是搬运过什么,现在又在哪儿搬运东西呢?这对母女并不想知道。后来,完全是意料之外,不可思议的好运落在了她们头上,桑德斯太太得知,自己从未提及过的姐姐,给她留了一栋房子,一栋小排屋,位于哈斯丁。律师写信来,说“奉命”告知,“衷心想要”给她细节信息。“但我一直以为她早死了,”桑德斯太太说了一遍又一遍。
“嗯,她现在是死了,”黛西说,“你也就不必认为自己错了。”
“我一直以为,若是活着,她是在新南威尔士州 。”
“别伤心,”黛西说。“你没有那么难过。”
“如果不是消息来得太突然,我会难过的,”桑德斯太太说道。
这消息也没有那么不可思议。律师又写信来澄清,害怕她们误会(可就是他让人误会的),说这栋房子并不属于桑德斯太太,也不会属于桑德斯太太。她得到的只是一纸租约,转租。接下来五年的时间,她们每个季度可以得到五英镑的租金。律师告诉她们,这笔租金将极大地改善她们的生活。
桑德斯太太继续在猎鹰啤酒厂拧瓶盖,有了这份工作,她就有权送女儿去拉奇米尔路的持证售酒者免费学校上学。黛西长大了,高挑苗条,但很结实。她有了生活的根基,这辈子,要活着,她就得做很多事情,一直做到头发花白。现在她满头奔放的卷发,很引人注目,总是没法判定到底是棕色多一点,还是红色多一点。到底什么颜色,完全取决于光线。
到了十五岁,她盘起头发,用粗钢夹固定,开始了办事员的生涯。干这份差事,就要与十五万伦敦南部的人一起,每天两次过河。当时,社会学观察家把过河比作逃难,邻近的土地上发生了大战或是大灾,逃难者绝不敢回头,争先恐后,用尽各种方式,快步过桥,如若没有落水的危险,绝不会停下脚步。到了有轨电车站,那是没人排队的,人们只有在免费医疗诊所外面才有人排队。电车摇摇晃晃,从拐角转出来,猛然停住,人就像是黑压压的蜂群,一拥而上,把电车围个水泄不通。一定要冲锋陷阵,争当批次。但也要精心做好防卫工作。黛西和她的朋友们出去工作,衣服都扣得严严实实的,帽子别在头发上,严防死守,不准有人前来靠近。她在无名指上戴上了一枚宽宽的金戒,那是哈斯丁长期杳无音信姨妈的遗物。埃利姨妈结过婚吗?戒指上刻有铭文——终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电车上气闷拥挤,那些前来靠近的人,并不承认婚戒的存在。他们如同黛西本人,完全清楚她还穿了什么。这是一场没有规矩的战斗,电车开始朝前滚动,一车的人,散发着浓郁的体味,跟着前仰后合,东倒西歪,男人们用手护着车票和钱袋,上学的男童护着自己的生殖器,而女人们则要前防后守,杜绝所有的接触。
黛西在富勒姆的兰伯特玻璃窗供货处上班。仓库虽然是灰暗萧条的样子,入口处却有一块很大的彩色玻璃,上面画的是《寻找迷失的羊》。天空是一整块混色玻璃,白色和蓝色随意交融,产生一种盛夏浮云的效果。在1909年的英格兰,大概没有人可以调出这样的玻璃;兰伯货处的人肯定调不出来。在巴特西 、克拉珀姆 、斯特里特姆和斯托克韦尔,虽然每栋小房子的前门都有镶嵌有一点彩色玻璃,但黛西从未见过兰伯应处门口的这种玻璃,在教堂里也没见过。
兰伯货处的工作时间是八点到八点。年轻的黛西报到的那天,她心甘情愿,按捺不住地要取悦于人,就仿佛那是创世纪的天清晨,这个世界上耗心费力蔚然壮观的场面之一。她领到了一个凳子和一个钩子,来到玻璃店后面一个基本上不透光,不透气的箱房中。在她眼中,一排排的数字赏心悦目,如果有数字摆放歪了,那就更是如此。8073英尺的玻璃,每英尺1先令6便士,再配上四分之一英寸的铅条,后来铅条的尺寸变成了十六分之五,整个估计也就上涨了13.5%,她觉得心满意足,仿佛是她本人迎接了挑战,征服了困难。
她每周的薪水是十二先令。桑德斯太太丢了啤酒厂的工作。她身体出了问题,疼痛,但每次疼痛的位置都不一样。她有了充足的时间来思考疼痛的问题。她们搬到一栋房子顶楼两间通风透气的房间里。这栋房子,除了她俩的房间,每个窗户上都贴有手写的卡片,提供有用服务。提供普通洗衣(这是在一楼,锅炉所在地),地道音乐教学,草本疗法。“你不要去试那些东西,”黛西说。但桑德斯太太已经和草药师寒暄过一番。她得以汇报说,草药师什么都没有,以千里光 为治疗的开始,再以装在普通信封里的薄荷草为结束。对她这个年龄的女人,什么都没有。
不到一年的时间,黛西在兰伯特公司递交了辞职,开始了新工作,这次是在塞德利纸箱厂,还是办事人员。这一次持续的月份也不长。是她干活不得力?不是的,黛西镇定地说道,她干活无可指摘。桑德斯太太叹了一口气。“嗯,你对我说,兰伯特先生总是动手动脚。难道他没有注意到可怜的埃利留下的婚戒?”“上帝呀,母亲,那枚戒指只是在电车上用的,”黛西说道。“只是在路上用。工作的时候,我就摘下来。兰伯特知道我十五岁,他知道我没有结婚。我们不要再谈兰伯特了。”
“那塞德利先生呢?”
“他更糟糕,”黛西说道。“他甜言蜜语。”
“甜言蜜语”这个词,在伦敦南部,就不是轻描淡写的意味。也不会有人觉得黛西难相处,或是难满足,甚至没人觉得她挑剔。正好相反,她慷慨大度,正是那种心都可以掏出来给你的女孩。只是她不喜欢兰伯特老先生为她做决定,更不喜欢年轻的塞德利给她做决定。
很多人没有了工作,她记得以前可没有这么多人。她证明自己是上过学的,还从圣詹姆斯英国国教高派教传教教堂的哈格特神父得到了一份推荐书。神父同情自己的教区居民,只要在情理之中,能帮他们挣钱,他都愿意签字。有了推荐书,黛西找到一份洗盘子的工作,但一周只有七个先令,还要交三便士的押金,以赔偿打破的餐具。
黛西爱自己的母亲,母亲是她惟一的亲人。但黛西觉得,也可以说是自己害死了母亲。1909年的春天,塞尔弗里奇百货公司在牛津街开了一家店。印了好多传单,贴在橱窗上,到处都是,大家都看见了。在教堂大厅后面的女性阅读室,黛西看到了这张传单。“塞尔弗里奇百货公司开张大吉,我们诚邀所有英国公众以及海外游客光临,无需入店凭证,在开张之际,你将享受到购物和观光的双重喜悦。崭新的购物环境,历经时间考验的经营原则——真诚的交易,竭诚的服务。”
传单上说,在这沮丧的萧条时期,公司雇佣了一千五百人,一年之内,宏伟的大楼平地而起,柱廊的前门,自成一景。大楼有电梯。“如果你想去,我就带你去看看,”黛西对母亲说。“那天我只有半天班。”桑德斯太太经常去伦敦西区,但从未进过大商店。想着高挑漂亮的女儿要护着自己去大商场,她几乎要高兴得发狂,但还是设防地说道:“我不在意,如果你正好去那个方向,就行。”
她们坐电车去维多利亚,然后搭乘敞顶的公交车,两个人就像是云雀一样,一点点地爬上楼梯,坐到了左手边的前两个座位,这样视野为宽广,只是天空中云层灰黑,像要下雨。牛津街上全是马匹和汽车,几乎就是水泄不通。她们在424号寒酸的拉斯科布料店下车。为了致敬塞尔弗里奇百货公司的顾客,人行道上铺上了红地毯。甚至去拉斯科布料店的寒酸顾客也可以蹭上地毯边。进了大门,灯火通明,戈登·塞尔弗里奇身着长礼服,亲自巡视,等到夜幕降临,他则换上晚礼服。桑德斯太太女王般地朝他点点头。有黛西挽着她的胳膊,桑德斯太太觉得并不屈尊于任何人。她很高兴,并不是这里商店多达一百个,在广告中被比作遥远的东方集市,也不是这里有一千两百名售货员,而是她有机会向他们展示,对于她这样的女人,并没有把这些放在眼里。
她们大概看了百个商店中的二十个之后,黛西提出建议,说坐电梯上楼,到露天茶苑。茶苑在大楼的楼顶,她们可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黛西说这话的样子,就像是母女二人刚从遥远的乡村而来,从绿色树林中而来,或是从土豆田地而来。
“空气!”桑德斯太太说道。“他们不可能空气也要我们付钱吧。”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付过钱,”黛西说道。
这些天,每天清晨,塞尔弗里奇百货公司开门营业,要吹响号角,晚上关门,再次吹响号角,仿佛每天在购物中度过,都是载入史册的大事。之前,桑德斯太太虽然说了好多关于号角的事情,现在有了机会,似乎不再关心是否听到号角。
“我想回去了,”她说道。“也就是这些东西。”
“母亲,你累了。”
“不,我不累,”桑德斯太太说道。“我什么时候累过?”
“觉得累了,又不是什么罪恶。”
“但承认累了,就是大过错。”
这之后,她就没怎么说话,她们再次转车去搭乘电车,穿过河,回到了自己的地盘。市场上的街道黑黢黢的,摊位都推到了旁边的小巷里,用油布裹得严严实实的。你可以闻到马厩那种不透风的气味,马被关进马厩过夜,不时地换脚踱步。街道路口的煤气灯下,传教士、政治演讲家、马克思主义者,妇女参政论者,眼见没有了听众,无论有什么样的家,也都回去了。
“黛西,你觉得商店怎么样?”桑德斯太太问道。“你觉得可以开多久呢?一层楼又一层楼,全是东西,我都没怎么看他们的要价。全放在那里,任凭大家盯着看,不怎么体面的样子。”
“我知道,”黛西说道。“他们几乎就是求着人进来,请人随便拿东西了。”
她从裙子口袋里掏出前门的钥匙。
“嗯,我真拿了一件东西,就一件,”桑德斯太太说道。
黛西心想,上帝呀,她没有吧。但应该不是什么大东西。她问道:“你怎么拿回来的呢?”
“还是老办法。”那就是放在伞里面了。黛西伸出胳膊搂住她骨瘦如柴的小个子母亲。
“黛西,我为你拿的,给你的礼物。”
“不,你没有拿,”黛西说道。
“嗯,也许没有。”
等她们到了楼上,一看,原来拿的是发卷,一团假发,别在头发上,增加发量,好做流行的造型。但这种发卷的颜色总是不太匹配,总是看得出来是假发。而这个发卷是金黄色的。
“你真喜欢这个?”黛西疑惑地问道。
“不,算不上。现在再看,不太喜欢了。跟我的头发不配,跟你的头发也不配。当时看到,就想起了我在你这个年龄的头发颜色。下次再去,我们就送回去吧。”
“有一千两百个售货员盯着顾客,本不该担心,但我想每天打烊的时候,他们都会发现丢了好些东西吧。你应该拿你真正想要的东西。”
三天后,桑德斯太太死了,当时黛西在上班。母亲的死,她痛彻心扉;当时不在场,更让她难以释怀。她并没有询问医生,去伦敦西区会不会是心脏病突发的诱因,她知道医生也没办法给出明确的答复。因此,她就只字不提。
草药师,地道音乐教学的老师,还有洗衣人,都找来了,进了黛西的房间,房间里有盥洗架,有煤油炉,两样东西都放在帘子后面。她深知这些人的来意,他们是来看看有没有东西可拿的。黛西对他们说,等她把一切安排妥当后,他们再来看看有什么吧。母亲的东西,除了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其余的,她都不要了。从照片看来,桑德斯太太并没有金色的头发,但那个时候是靠摄影师染色,也许把颜色搞错了。
“桑德斯小姐,家具不要了?”草药师问道。
“我不住这儿了。”黛西说道。
“盥洗架呢?”
“我不会带走的。”他肯定猜出盥洗架在帘子后面,或者他打探了一番,知道架子是大理石台面。
黛西通知律师,对方真心想要表示遗憾。等到黛西前去拜访,询问埃利姨妈房子的事情,他指出,因为桑德斯太太去世,每个季度5英镑的款项也就自动终结了。
“那这钱归谁了呢?”黛西问道。那律师说,她好好考虑自己的将来,应该会过得很好。黛西告诉他,她之前想成为医院护士,现在仍然想,而且也不需要考虑母亲了。
“要进入护理行业,有两种方式,”他说道,“一种是成为普通的实习护士,我知道大多数实习护士都来自家政服务行业。另一种就是支付附加费,接受培训成为护士小姐,当然了制服会很不一样,也不需要去做那些倒胃口的工作。我猜,你应该没有接触过护士小姐。”
他给了建议,没有收费,可能是作为一种赔偿,毕竟黛西没了哈斯丁房子的租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