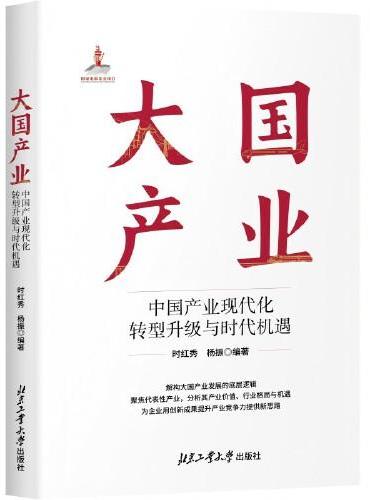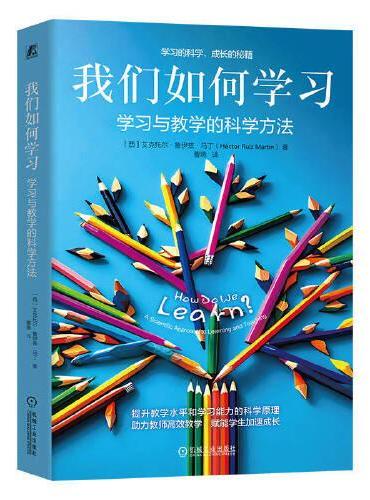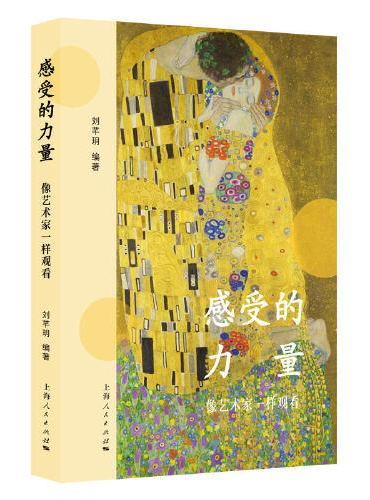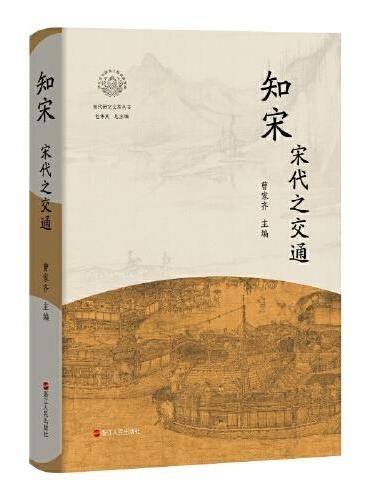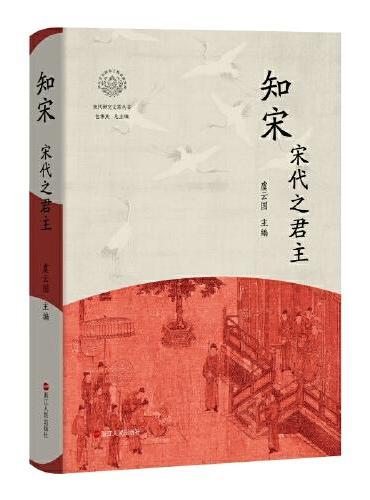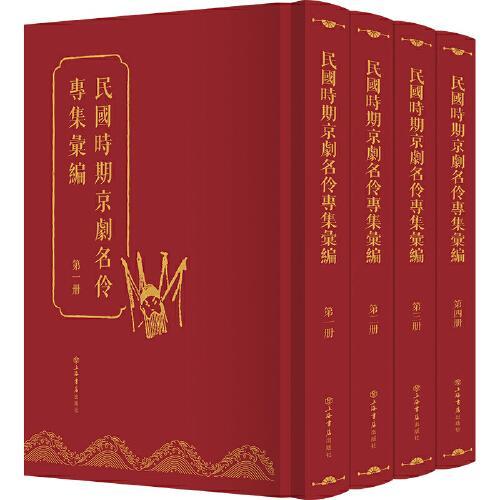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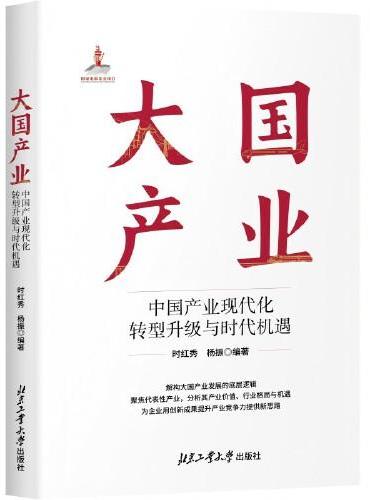
《
大国产业—中国产业现代化转型升级与时代机遇
》
售價:NT$
403.0

《
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咨询
》
售價:NT$
70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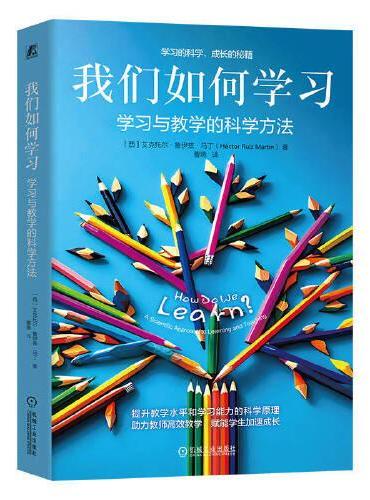
《
我们如何学习:学习与教学的科学方法 (西班牙)艾克托尔·鲁伊兹·马丁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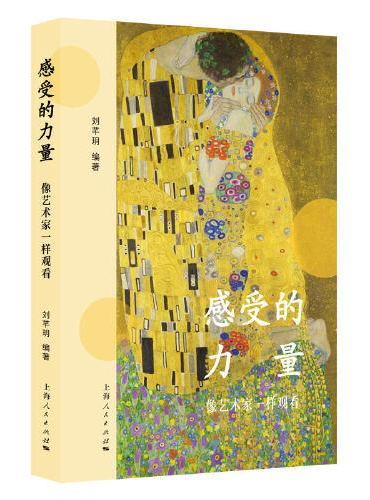
《
感受的力量--像艺术家一样观看
》
售價:NT$
265.0

《
诗词串起中国史:按照朝代顺序用诗词串起一部中国通史。
》
售價:NT$
122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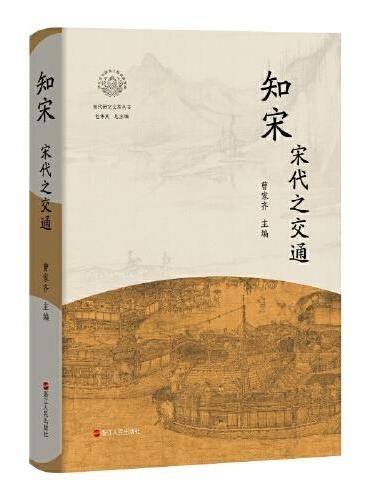
《
知宋·宋代之交通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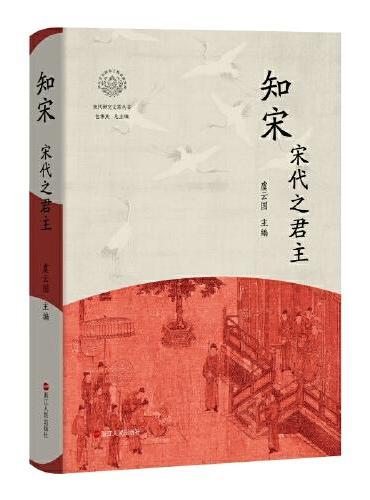
《
知宋·宋代之君主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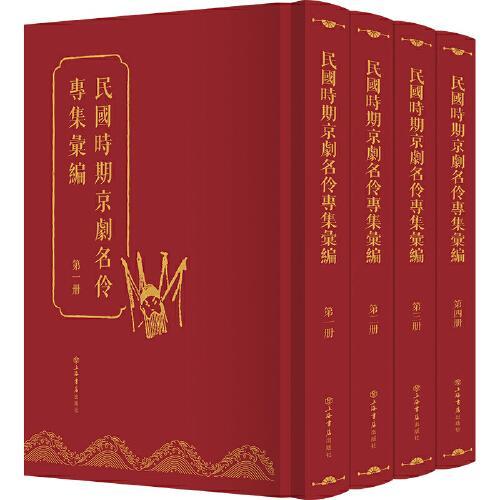
《
民国时期京剧名伶专集汇编(全4册)
》
售價:NT$
20298.0
|
| 編輯推薦: |
★在木心逝世十周年,纪念他求学、生活、顿挫、创作、载誉的一生
★木心首部年谱著作;谢泳、陈丹青作序推荐;张天杰诚挚推荐
★自2013年以来,积八年之功,全面搜集了木心的生平资料
★涵盖家世、求学、任职、交游、创作、际遇诸端,今后的木心研究无法绕开的奠基之作
★辑录了8张木心珍贵照片、木心自制年表两份及日文简历
|
| 內容簡介: |
本书是近年十分热门的诗人、文学家、画家木心的部年谱性质的著作,致力于将木心的生平行迹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分“卷首”“家世”“编年”“附录”四部分。“卷首”为木心的姓名、字号;“家世”汇集其家世背景及家庭成员情况;“编年”则为其一生之经历,涉及求学、任职、交游、创作、际遇诸端;“附录”收录木心自制的两份汉语年表和一份日语简历。
本书尽力做到两点:一是尽编者所能,程度地搜集目前所能见到的木心先生的生平资料,可确定时间者不论巨细,悉加选录;二是对资料进行必要的考辨,尽可能地确保内容的准确性。
本书征引的资料主要来自木心业已出版的个人著述、研究木心及其作品的著述、与之相关人物的著述、地方文献、公私馆藏资料、木心与师友间的来往书简、媒体访谈等。凡有出处,均一一注释。除编年对象本事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人和事,以按语的形式略加介绍,以为本事之助。
|
| 關於作者: |
夏春锦
青年学者,阅读推广人,现供职于桐乡市图书馆,系浙江外国语学院浙江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杭州师范大学木心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著有《悦读散记》《木心考索》《文学的鲁滨逊:木心的前半生》《木心先生编年事辑》等,主编和策划有“知新文丛”“蠹鱼文丛”《谷林锺叔河通信》等。
|
| 目錄:
|
目 录
序 一(谢 泳)
序 二(陈丹青)
几点说明
卷 首/ 001
家 世/ 005
编 年/ 015
附 录/ 293
自制年表一/ 295
自制年表二/ 297
日文简历/ 298
代 跋 追寻那个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张天杰)/ 299
自 跋/ 306
|
| 內容試閱:
|
序 二
现代中国作家的简历,以我所知,恐怕是木心的自撰为最简扼,仅三十六字:名字、生年、籍贯、学历、客居地。他去世后的再版本,添上他归来到逝世的年份,也才够五十字吧。
现代中国作家出书最迟者,就我所知,恐怕也是木心:五十六岁抵纽约之前,他从未在大陆发表过一个字。首册简体版文集在大陆面世,他已七十九岁。
木心是谁?但凡初闻其名,初读其书的人,都会有此一问。当今市面,这几十字会是何种效应,木心当然知道,怎么办呢,他一再引福楼拜的话,叫做:
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
中国作家而特意称引这句话,木心之前,似乎没有。这是他的立场,他的游戏,他的公然的骄傲,也是他的经历所含藏的苦衷。而在晚年访谈中再次说起同样的意思,他忽而笑道:
艺术家真的要隐退吗,他是要你找他呀。
这是真的。木心的每句话周边必会站着别的意思——“他要你去找他呀”——梁文道说起过有趣的观察,他说:“五四及今,读者读罢书还想趋前面见的作家,除了鲁迅和张爱玲,第三位,便是木心。”
鲁迅与好些晚辈作家的行谊,不消说了。张爱玲却不肯见人,至少,很难见,木心与她同调。二〇〇九年我亲见晚晴小筑门外站着一位愣小伙子,从广西来,苦候终日,天黑了,老人就是不见。其时秋凉,这孩子穿着T恤,木心唯嘱咐给他买件单衣。纽约期间,我也亲见不少访客被木心婉拒。二〇〇三年,耶鲁美术馆为他办了体面的个展,他居然不去开幕式,记者找他,他也推阻。
一个毕生不为人知的作家,迟迟面世,却刻意回避读者,国中文界殊少这样的个案。西方倒是不罕见,最近的例,是备受瞩目的意大利女作家埃莱娜·弗兰特,她不进入宣发出书的任何环节,从不露面,以至她的整本访谈录不断被问及为何如此。
木心非但不露面,回归后几乎不接受当面的采访。直到他的葬礼,各地赶来的上百位青年才见到他,而生前介绍自己,这个人只肯给几十个字。
其实他越是这样子,读者越想见他。
他不写回忆录。他说,回忆录很难诚实。但有谁到了中年晚岁而不回想自己的往昔吗?遗稿中,我发现他在世界文学史讲稿最后一页,写着平实而简单的记述——那年他大约六十六岁——某年在哪里,某年到哪里……这是他唯一的“年表”,自己看看,没有发表的意思。近时木心遗稿拟将出版。在数十册小小的本子里,不下十次,他零碎写到某段往事,同样简洁,譬如抗战期间避难嘉兴的一段:
小学四年级
租住燕贻堂
出入天后宫弄
秋季运动会
一百米短跑冠军
看上女生了
她叫盖静娴
她是不知道的
结伴拔草的男生姓周
头发黑得发乌 香
级任老师特别好
钱之江,现在还记得
忆写往事,木心鲜少渲染,直陈年份、地名、街名、人名。遗稿的好几处页面写满名字,譬如:
方圆、老熊、六十、兆丁、陈妈、春香、莲香、顺英、秋英、海伯伯、管账先生、教师、阿祥、祖母、母亲、姊姊、我、姊夫、剑芬溶溶 十九人
这是他历数幼年的故家——也就是乌镇东栅财神湾一八六号——总共多少人,其中大半是仆佣:
这样一个家,我只经历了五年,之后,在杭州、上海过了四十多年,美国二十五年。
显然,他在自言自语,毫无示人的企图。他曾说,老了,记性差,忘了某事某人、某书某词,硬想,保持想,直到想起,能锻炼记忆力。那些年我俩交谈,话到嘴边,想不起,下一回见,他会喜滋滋说:呶,想起来了呀!于是一字字说出,有时到家就来电话,报告他豁然寻回的记忆,哪怕几个字。
遗稿中另有两组更“庞大”的名单,一份应是上海艺专的同学姓名,另一份,是他寄身近三十年的工艺美术工厂员工。锻炼记性吗?我想,晚年木心是在不断反刍行将过完的一生,而当转头面对外界,就那么几十个字。
读者不会放过他。学者更不会放过——定居桐乡的夏春锦,可能是试图追索木心生平行状和家族谱系的第一人。为读者,也为文学研究,他苦寻资料,试图拼接木心简历之外的一生。我如何看待这份工作呢?以下的意思,自知不能说服人。
我不认为读了文学家的生平,果然能认知“那个人”,甚或有助于理解他的文学。生平、文学,不是核对的关系。一份处处求真的传记,可能布满——也许是——善意的错讹,即便再详实,也不可能破解卓越的小说、神奇的诗,何以卓越,何以神奇。
西人云:作品有时比作者更聪明。艺术家最为隐秘而珍贵的一切,全然凝在作品里、字面上。倘若好到不可思议,这不可思议的种种,分明裸露着,却未必见于他的生平。
真的。倘若我是木心的侄甥,仍无法获知为什么他能写出“你再不来,我要下雪了”。交往二十九年,有时,我巨细无遗介入他的日常,他开口,我便知道会说什么,但我还是不明白何以他在赠我的诗中写出“仁智异见鬼见鬼,长短相吃蛇吃蛇”。
木心逐字解释了——还特意说,“蛇”的读音应作“啥”——但于我而言,仍是谜。我喜欢谜,为什么要破解它?
为人立传,很难很难,甚或难于文学。作传者的功力,品性,大诚恳,简直等同创作。恕我直说,我不记得看过可读的中文传记,并非作传者不良,而是,恕我妄说,自引入西洋人“传记”体写作迄今,现代白话文水准尚未准备好书写体贴入微而知守分寸的传记。
我并非是为木心专来说这番话。我也不曾与他深谈过:为什么不写回忆录,为什么不要相信传记。我是以自己的经验,或曰“痛感”:艺术家之为艺术家,是苦心交付给作品的另一个自己,为什么读者总想离开书页,掉头找“那个人”?
我不认为谁能写谁的传记。人,人的一生,何其复杂,而况木心。早年我曾热心读过一二册《鲁迅传》,丝毫不令我豁然明白鲁迅,那是另一人的想象,另一人的手笔,读过即忘,而每次读鲁迅的随便哪篇短文,我好似和他面对而坐。
这一层,木心说得痛快,近乎板着脸:“不要写我,你们写不好的。”但我知道,木心身后必有人要来写他,琢磨他。这是令我无奈而近乎痛苦的事:我目击他如何守身如玉般,维护私己。他渴望尊敬、荣耀、文名,但绝不是希求一份传记。除了他留下的作品,我不指望世人了解他,认真说,我也并不自以为了解他——那才是木心之所以是木心。
以上的话,我愿如实说给春锦听,也说给读者听。我爱敬木心的理由之一,是不愿看到他成为身后有传记的人。我不得不坦言,春锦发来的书稿,我不曾读,在我的恒定的记忆中,那个长年与我倾谈言笑的人,才是木心。
没见过木心的读者,怎么办呢?好在眼下这本书是“木心先生编年事辑”,不是传记。尤使我宽心者,是谢泳先生为此书写的序言,他以中国“年谱”这样一种传统体例,肯定了春锦的工作,他说:年谱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独特体例,和方志一样,均是西方历史著述体例中不曾出现的文体……年谱的学术生命力要高于专著,专著如非名著,很难打败年谱……这是第一部关于木心先生的年谱,虽然春锦谦虚,只用了“编年事辑”的书名,其实这就是一部合格的年谱……以后再出新谱一定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今后的木心研究也绕不开这部年谱,如果木心研究可以持久,这部年谱也就不会过时。
这是平实剀切的话。我不是学者,我该从自己与木心的漫长交谊中,退开几步,放下己见,顾及众多爱木心的人,而春锦所做的一切,正是念在日渐增多的木心读者——三十多年前,木心毫无声名,我俩在曼哈顿人流中且走且聊,或在各自的厨房煎炒烹煮,相对抽烟,万想不到桐乡有个孩子,名叫夏春锦。
今木心逝世十年了,春锦做这件事怕也快有十年了吧。身为同乡晚辈,春锦的工作,允为美谈。
陈丹青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写在北京
追寻那个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代跋)
张天杰
木心是谁?木心有小诗《我》: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哪!木心还有俳句:你再不来,我要下雪了!木心,就是那个生前、死后,似乎都在一片迷离的大雪之中的人。
当年美国电影人拍摄的纪录片,木心行走在大雪之中的孙家花园的画面,想必留给许多人深刻的印象。是的,木心与雪,就是那么切合,所谓纷纷飘下,更静,更大……后来偶遇主人离去的孙家花园,也曾细细思量,那一场乌镇的雪,呈现了什么?退隐了什么?
事到如今,想要追寻木心其人,也只有到那遗存下来的文字符号当中了。木心的遗稿,再三论说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分明隔着代沟,却又是忘年交,相隔百年千年,可以一见如故。确实如此,想要从那么多的文字符号之中,再来拼成一个近似完整的故人木心,有这么一份痴心痴情的人,想必也有不少了吧?其中的痴,引一句古人的话:今夜故人来不来?教人立尽梧桐影!
木心再三说过,他坚信福楼拜的信条:呈现艺术,退隐艺术家。关于艺术家与艺术的关系,木心最欣赏的哲学家尼采曾在《艺术的背后》一文中说道:“无论艺术家幕后、背后的工作是如何艰辛,但他呈现的艺术作品应当给人这种印象,这是优秀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一个标志,当人们通过艺术品来设想艺术家时,一定要使人们把艺术家想象成一个在艺术上充满力感的人,由于这种力感,他从容不迫、举重若轻。”是的,艺术家在艺术中所呈现出来的,有时候与其人惊人的一致,有时候却会绝然相反,仿写一句木心似的话:举重若轻,轻也就是轻给人家看看而已。
再说木心,也不是一个绝口不谈自己的人,《木心谈木心》则是与友人谈自己,以及自己的作品,其中就说:写写虚的,写实了;写写实的,弄虚了。艺术就是在虚与实、真与幻之中存在。木心不写回忆录,或者说只有一部曾经想写终于没有写出来的回忆录,在《海峡传声》一文里回忆当初想写的《瓷国回忆录》,传记性,应归小说类。其实已经写成的诸如《此岸的克里斯多夫》《战后嘉年华》之类,也应如是观。
其实,木心本人也是极其喜欢读艺术家的回忆录、传记之类的,比如尼采,喜欢读其自传《瞧!这个人》,也喜欢丹尼尔·哈列维的《尼采传》。据《战后嘉年华》中的回忆:“杭州旧书店多多,多到每天只要我出去逛街,总可以选一捆,坐黄包车回来,最嗜读的是‘欧洲艺术家轶事’之类的闲书,没有料到许多故事是好事家捏造出来逗弄读者的,我却件件信以为真,如诵家谱,尤其是十九世纪英、法、德、俄的文学家音乐家画家的传记,特别使我入迷着魔。”当年的木心,就是在这些亦真亦幻的“轶事”当中学习做那种知易行难的艺术家,作油画,学钢琴……多年以后的某一天,木心靠在窗栏上凝望慢流的河水,还想起那些轶事、传记中的艺术家:“他们的不幸,也还是幸。”不知后来的木心,是否也是如此看待自己?
木心与童明《关于〈狱中手稿〉的对话》之中就说:“艺术家最初是选择家,他选择了艺术,却不等于艺术选择了他,所以必得具备殉难的精神。浩劫中多的是死殉者,那是可同情可尊敬的,而我选择的是‘生殉’——在绝望中求永生。”木心在与李宗陶对话时也说:“我如此克制悲伤,我有多悲伤。历史在向前进,个人的悲喜祸福都化掉了。我对自己有一个约束:从前有信仰的人最后以死殉道,我以‘不死’殉道。”这里提及一种精神,以及精神的伟大力量,也是木心在与许多人的对话之中再三提及的,平常还在思想死,到了危难之中则偏偏不想死了,一死了之,还是容易,向死的机会多,却要去挺过来,也只有挺了过来,方才不辜负艺术的教养。
所以说,木心,就是这么一位以不死殉道的艺术家,对于艺术的追求,最终在他自己的身上汇聚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成就了一个全方位的人。木心八十四岁时,给乌镇的周乾康先生的一份简历中提及,罗森科兰兹先生曾引用布克哈特描述“文艺复兴式人物”的话,借以称赞木心:“当这种高度自我实现的意愿与强健而丰沛的天赋结合,并精通一个时代的文化的各种要素,一个‘全方位的人’,一个通达世界精神的人应运而生……”是的,木心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世界精神的艺术家,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这种定位,也将会越来越清晰起来。
二〇〇一年,内地的《上海文学》连载了木心的《上海赋》,陈子善先生在当年五月号的《上海文学》上介绍:“木心者,何许人也?即便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专家,恐怕也感到很陌生吧。其实,他是享誉台港和美国华文文坛的著名散文家,只不过他一贯低调,专心绘画和作文,以至长期以来此间对他以艺术家的慧眼和心智,观察环境思索生命驰聘想像的隽永散文,几乎一无所知。”这也就是所谓的“文学的鲁滨逊”,直到读书界所谓木心年的二〇〇六年,内地的许多报刊都在争论这一形象,争论似乎还在持续下去。
同样也是二〇〇一年,“木心的艺术:风景画与狱中杂记”大型博物馆级全美巡回展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耶鲁大学美术馆隆重开幕,预告手册上是这么介绍木心的:“木心是二十世纪最不寻常的艺术家之一。一九二七年生于中国,见证了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中的起起伏伏……《狱中杂记》写于稍早文革期间他的单独禁闭。二者都展现了木心以理性生活战胜牢狱生涯的意志,他因此可以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的伟大历史人物的自如交流。”这里呈现的是一个以艺术以及理性生活战胜牢狱生涯的斗士形象,这也许是西方人更愿意接受的。
木心逝世之后,为木心录制纪录片的两位美国导演在乌镇的追思会上回忆木心:“他在我们心中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有幸见过木心的人都曾被他感染,而对于大多数没有见过他的人来说,他的作品传达的感染力是同样强烈的。事实上他养成了的那种低调,给他带来了一种令他舒服的距离,……木心的脸几乎没有皱纹,他的眼神明亮又开阔,并没有表现出他的年龄或他的那些遭遇给他刻下的东西。是的,他会同我们讲起他的过去,但他真正想同我们说的是他依然在创作。对木心来说,最重要的是,他这样告诉我们,是对得起少年时他对艺术所做的承诺。在历经了六七十年代的牢狱和之后远走美国初期的拮据,他千万里回到中国,依然怀着热情继续写、继续画,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个美妙的人,他上了一堂课:他告诉我们如何在阴影和逆境中对待生活,他向我们展示了使用你的自由去做些什么比空谈更重要。”同样是西方人,在这两位曾经与木心朝夕相处十多天的导演看来,无论其人、其作品,都有着强烈的感染力,无论过去、现在,都在继续写、继续画,所以方才成就真正的艺术家,一个美妙的人。
诚如一千个读者眼里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人看木心,都会有不同的认识。此处且摘录几则木心故乡人的记述。孔明珠《去乌镇见木心先生》:“木心先生美丽阴柔,像一个老派的大家闺秀——不是老克勒,是大家闺秀,我等的祖母一类。看到这样的人,再想到其作品中对美近乎病态的热爱,想到的比喻是王尔德。这些是人间美的化身,美的儿子,存在先于本质,存在的本身就是目的,相比之下,那些作品有也好,没有也好,好也好,不好也好,都不重要。”戴卫中《“欢迎你再来!”》:“他穿着很普通的灰黑的衣服,但很整洁,初看如常见的在家老人一样,但他坐下时和坐下后架势显示了他的儒雅风范。”徐树民《我第一次见木心先生》:“他面容清癯,但精神很好,这时我脑际不觉浮现出王世贞形容李时珍的那几句话:晬然貌也,癯然身也,津津然谭议也,真北斗以南一人。”后来徐树民先生还说,从内在来说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些回忆,也许都是管窥锥指,各有一得,然而他们最为关切的不是木心其文其画,而是其人,有时候甚至认为只要有其人的存在,就是好了;至于其文其画,有或没有,并不是那么重要,或者说其人其画就是因为其人的存在,而获得了存在的意义。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艺术家需要适度的隐藏,从而呈现其艺术。然后真正要去懂得其艺术,还是要去懂得艺术家其人本身。在木心生前,就有木心的朋友介绍其人,如陈英德《也是画家木心》、巫鸿《读木心:一个没有乡愿的流亡者》;还有媒体人的访谈,如李宗陶《木心:我是绍兴希腊人》、陈晖《木心:难舍乌镇的倒影》、曾进《我不是什么国学大师》。在木心死后,回忆木心的文字也就更多的了,如王韦《为文学艺术而生的舅舅》与《在天国再相聚言欢:追忆舅舅木心与姐夫郑儒鍼的交往》、曹立伟《木心片断追记》与《回忆木心》,以及沈罗凡《怀念孙木心》、夏葆元《木心的远行与归来》、秦维宪《木心的人生境界》,等等。木心曾与台湾的读者林慧宜通信说:“二十年后,你写《木心评传》。”可见,木心还是希望他的读者、观众,能够知晓其人,懂得其人的。
或许曾经有过为木心写上一部传记的木心的读者、观众也是极多,只是光有一份冲动,还是不够的。以文字符号拼出那个远去的故人,实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呢。然而还是会有人,一直在坚持。比如这部《木心先生编年事辑》的编撰者夏春锦兄,他曾经说:“随着读者对木心作品逐渐深入的探究,对其传奇的一生自然也会发生深度了解的欲望。这既是出于同情心与好奇心,也是理所固然,因为,理解的深度与广度,离不开对作者生平的了解,准确详实的资料,于是成为首要的条件。事实上,木心一生际遇与他的作品、尤其是与他内心历程的关系,比一般文学家来的更其紧密、幽邃、深沉。”是的,探寻木心传奇的一生,不只是因为好奇,更是因为同情。同情之了解,正带着温情与敬意。
春锦兄追寻那个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读木心、写木心,都是在木心去世以后,而编撰这部书,也是近几年里的坚持。我佩服春锦兄的坚持,知晓这部看似举重若轻的小书背后的艰辛,每一片文字符号的得来都不容易,至于考证其中的虚实则更不容易,焊接得恰到好处,“那焊疤尤美”则更是难上加难。作为这部书的最早读者,我看着他从几千字到几万字,再到十几万字,由衷地感到高兴。高兴的是,一册在手,或可弥补作为木心的老乡,却不能与之成为忘年交的遗憾,透过纷飞如雪的文字符号,亦可与这位可亲可敬的故乡老人,一见如故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