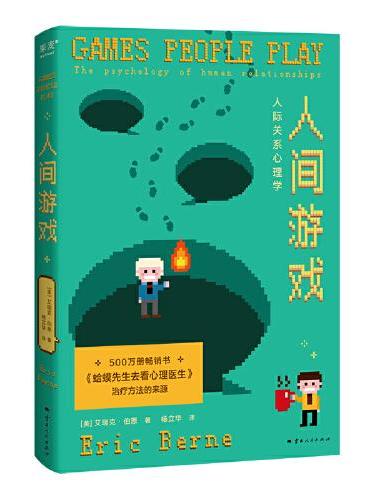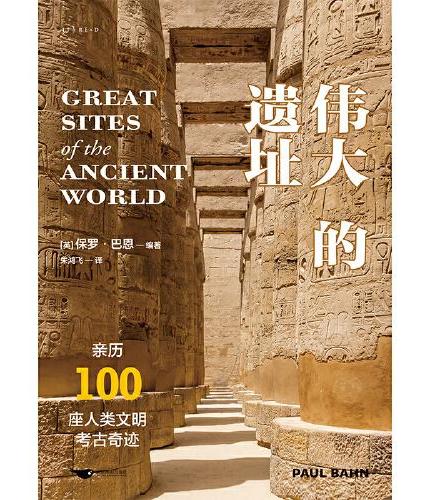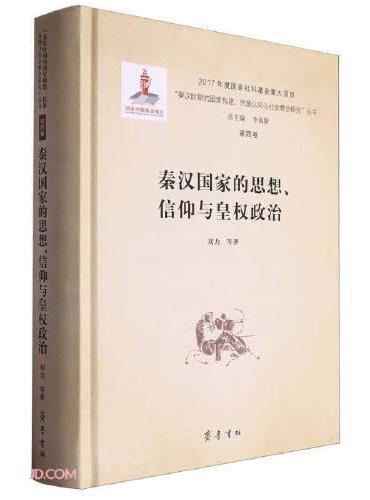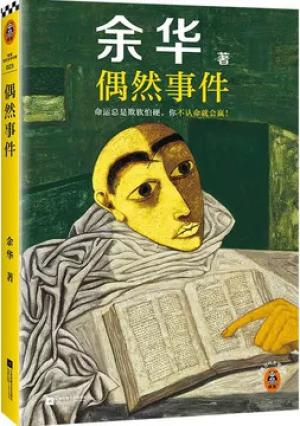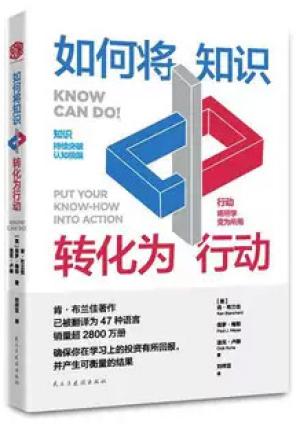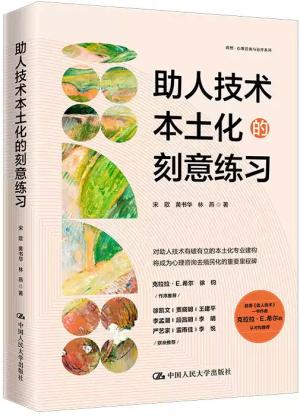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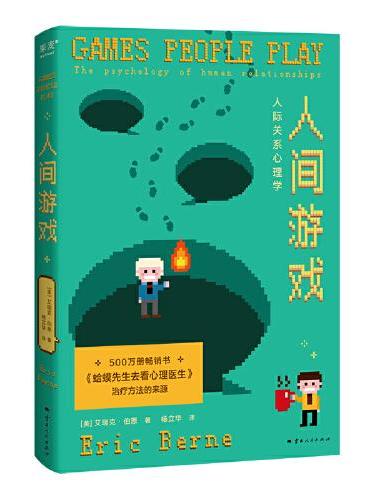
《
人间游戏:人际关系心理学(500万册畅销书《蛤蟆先生》理论原典,帮你读懂人际关系中那些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
售價:NT$
2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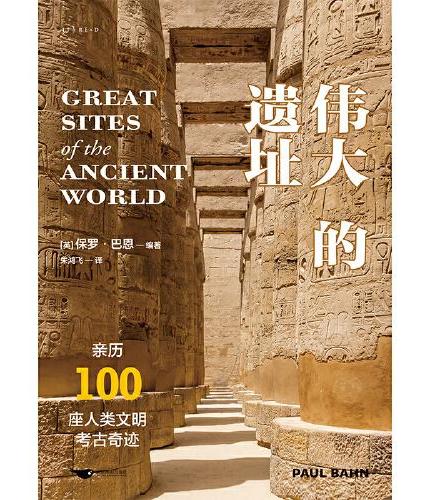
《
伟大的遗址(亲历100座人类文明考古奇迹)
》
售價:NT$
95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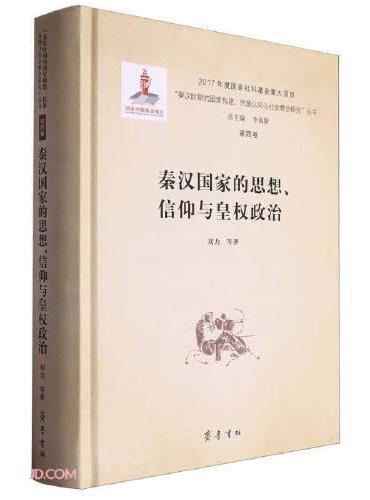
《
秦汉国家的思想、信仰与皇权政治
》
售價:NT$
1000.0

《
反卷社会:打破优绩主义神话(一本直面焦虑与困境的生活哲学书!)
》
售價:NT$
38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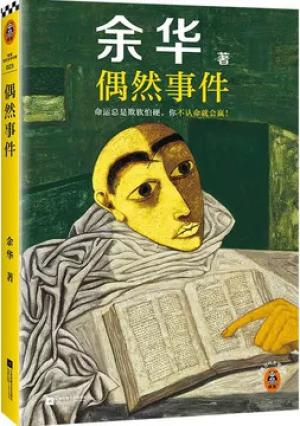
《
偶然事件(命运总是欺软怕硬,你不认命就会赢!)
》
售價:NT$
255.0

《
余下只有噪音:聆听20世纪(2025)
》
售價:NT$
95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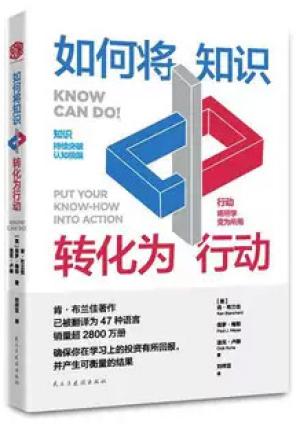
《
如何将知识转化为行动
》
售價:NT$
3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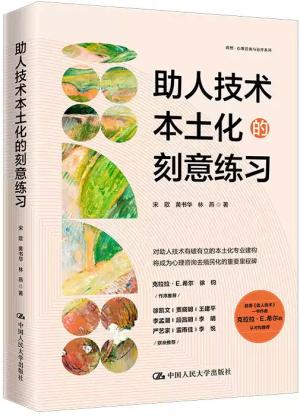
《
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
》
售價:NT$
408.0
|
| 編輯推薦: |
明代文学家汤显祖有诗云:“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当代著名作家赵焰从徽州那片水墨画长卷中走出,携其《千年徽州梦-老徽州》《行走新安江-徽之味》《思想徽州-徽商六讲》,讲述徽州的历史,带我们走近徽州,找寻剪不断的乡愁……
《赵焰文集卷一:徽州文化散文精编》是一套徽州文化散文,文字富有现代感和穿透力,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将一个多维度的徽州,活色生香地展示出来, “坐”中国文化的“天”,来“观”徽州文化的“井”,充分体现出徽州文化的精髓。
徽州就是一个人、一幅图、一物件、一本书、一杯茶、一朵花……当安静地看,用心地品,用思想去解剖,用体温去摩挲,用禅意去赏玩,当所有的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商业化,带着他们的人、事以及心思时,一个人,如果能独守空灵,借助于某种神明,用内在的纽带试图去连接那一片安谧的气场,就该是一种幸事吧?这样的感觉,与其说是思念的流露,不如说是乡愁的排遣。一种坠落于时空变幻中复杂情感的宣泄。
|
| 內容簡介: |
《赵焰文集卷一:徽州文化散文精编》该卷从不同的角度,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徽州的历史、文化、人物、风情等,充分描摹出徽风皖韵之代表徽州文化的独特魅力。《行走新安江-徽之味》着重介绍徽州予人的文化印象,以新安江的流向为线索,从其源头六股尖写起,一路逶迤而来,描写了沿途的山水人情、风俗典故、历史遗迹、人物事迹,用细腻的文笔,刻画了徽州的自然、文化与历史面貌,牵引着读者踏上一条文化和精神之旅。同时,介绍了沿途的经典徽州美味及其发展传承,不仅有传统的徽菜代表,更有街头巷尾的小吃,将舌尖上的徽州细细道来,由此折射出徽文化的博大精深。《思想徽州-徽商六讲》重在从精神层面解读徽州。从徽商的起源、发展、特点、代表人物、经典事迹六个方面讲述了徽商精神与徽文化的关系,并且通过徽州文化、徽商状况和精神这个窗口,了解徽州、思考徽州。沉积静谧的徽州具有优秀的文化,孕育出“徽骆驼”,却也因自身的局限性,导致徽商在外致富,回乡后并没有反哺故土。本书即阐述了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千年徽州梦-老徽州》则带领读者穿越回历史上的徽州。通过一幅幅珍贵的老照片,还原真实的徽州,发掘出徽州积淀千年的文化。
《千年徽州梦-老徽州》赵焰徽州文化散文集萃。赵焰生长于徽州,又走出了徽州,这决定了他对于徽州的回望。既有情感的渗透,又有理性的思考,赵焰的徽州文化散文,不同于一般性游记随笔,是在阅尽徽州山水风光的同时,以一个文化行走者的姿态,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从不同的角度,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徽州的历史、文化、人物、风情等。各分册之间,既有整体概貌,又各有侧重。作者思想深刻而敏锐,文字富有现代感和穿透力。有人评价赵焰的黴州散文,是“坐”中国文化的“天”,来“观”徽州文化的“井”。可谓一语中的,形象地概括了赵焰徽州文化散文的精髓和特点。
|
| 關於作者: |
|
赵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以文笔畅达、思想通透见长,多种作品在全国有较大影响,深受读者喜爱。出版有长篇小说《异瞳》《无常》,中短篇小说集《与眼镜蛇同行》,历史传记《晚清三部曲》《晚清之后是民国》,文化散文《思想徽州》《行走新安江》《千年徽州梦》《在淮河边上讲中国历史》,电影随笔《巴黎的忧伤》《蝶影抄》,散文《野狐禅》等书籍30多种。
|
| 目錄:
|
总序
本卷序 苍白的乡愁
千年徽州梦
代序
壹如梦:春花秋月
山印象
水印象
民居印象
贰如幻:阴睛圓缺
历史就是记忆
虚幻的影像
家族的背影
叁如泡:阴历阳历
桃花源梦
风水宝地
金鳌山下
肆如影:八千里路
渔梁送別
徽商的故事
山外的世界
千年一觉扬州梦
伍如露:遍地风流
高人即仙
文房四宝的宿命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
孤傲的渐江
天生一个黄宾虹
大爱陶行知
陆如电:镜花水月
徽州旧事
徽州出了个“老愤青”
风情茶馆
外婆的天井
尾 声
跋 语
老徽州
前言 那时花开
第一章 那些山川
叶挺的照片
旧时的黄山
立马空东海,登高望太平
黄山与名人
第二章 那些城镇
郁达夫笔下的屯溪
屯溪老街
徽帅 府歙县
最佳之处是水口
旺川村史
江 村
第三章 那些事儿
抗战时的徽州
营救美国飞行员
雄村中美合作所
婺源“回皖运动”
第四章 那些徽商
扬州的汪氏家族
无徽不成镇
祁红屯绿走天下
汪裕泰与汪惕予
传奇徽商胡雪岩
小上海的繁荣
黄山旅社
第五章 那些桃李
陶行知
徽州师范
第六章 那些人物
吕碧城
胡 适
汪孟邹
最后的翰林许承尧
第七章 那些志异
赛金花
李苹香
第一长人詹世钗
第八章 那些徽菜
我的徽菜
徽 菜
徽菜走天下
后记
|
| 內容試閱:
|
总序
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性情浮躁之人,定力较弱,喜新厌旧。自己的写作也是,虽然笔耕不辍,不过文字却五花八门、难成系统,既涉及徽州,也涉及晚清、民国历史;有散文、传记,也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中国文化随笔什么的。文字全是信马由缰,兴趣所致,写得快活和欢乐,却没想到如何深入,更不考虑流芳人间什么的。回头看自己的写作之路,就像一只笨手笨脚的狗熊一路掰着玉米,掰了就咬,咬了就扔,散了一地。
写作幸运之事,是难逃时代的烙印:文明古国数十年,相当于西方历史数百年——我们的少年,尚在农耕时代;青年时代,千年未遇的社会转型光怪陆离;中年之后,电子信息时代五光十色……童年时,我们只有小人书相伴;中年后,手机在手,应有尽有。少年时,我们赤着脚在田埂上滚着铁环;中年后,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起了汽车。少年时,喜爱的姑娘浓眉大眼大圆脸;中年后,美人变成了小脸尖下巴……世界变化如此之快,除了惊奇、欣喜,就是无所适从。
人生一世,各种酸甜苦辣麻缠身。写作呢,就是一个人挤出来的茶歇,泡上一杯好茶,呷上一口,放空自己,不去想一些烦心事。现在看来,这样的活法,使我的内心丰富而坚强,虽然不能“治国、平天下”,却可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我经常戏言:哪里是勤奋,只是做不了大事,也是把别人打牌喝酒的时间,拿去在纸上胡涂乱抹罢了。这话一半是戏谑,一半也是大实话。世界如此精彩,风光各有人在,有得就有失,有失就有得。不是谁都有机会成为弄潮儿的,做不了传奇,做一个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或者做一个历史深海的潜水员,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一路前行中,也有好心人给我掌声,也为我喝彩——写徽州,有人说我是“坐天观井”:坐中国文化的井,去观徽州文化的天;写晚清,有人说我将历史写作和新闻写作结合得恰到好处;写小说,有人说我是虚实结合,以人性的视角去觉察历史人物的内心……这都是高看我了。对这些话,我都听在耳里,记在心里,视为鼓励。我也不知道哪对哪,只是兴之所至,耽于梦幻罢了。写作人都是蜘蛛,吐了一辈子丝,网住的,只是自己;也是蚕,吐出的丝,是为自己筑一厢情愿的化蝶之梦。对于写作,常识告诉我,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内心,不是发财,也不是成名,而是写出真正的好文字;要说真话,必须说实话——花言巧语不是写作,自欺欺人不是写作,装腔作势不是写作。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不过假话一定不是真理。在这个世界上,说真话和说实话并不容易,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真话,很多人不敢说真话。怎么办?借助于文字,直达心灵。灵魂深处的声音,肯定是真话。
自青年时代开始写作,写写停停,停停写写,不知不觉地,就到了知天命之年,不知不觉,也写了三十多本书了。庆幸的是,我的书一直有人在读,即使是十几年前写的书,还有不少人在读在转。想起张潮的一句话: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其实写作也一样:少年写作,充满期望;中年写作,惯性使然;老年写作,不得不写,因为已无事可做。的确是这样,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可以对话的人会越来越少。写作,是对自己的低语,也是对世界的呓语。
写作没有让我升官发财,却让我学到了很多,得到了很多,也明白了很多。我明白最基本的道理是“我思故我在”,明白最高妙的境界是“无”。通过写作,我不再惧怕无聊,也不再惧怕“无”。我这样说,并不玄虚,是大实话,也是心里话。
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将我一路掰下的“玉米棒子”收集起来,出成文集。文集如家,能让流浪的文字和书籍,像游子般回归。不管它们是流浪狗、流浪猫也好,还是不记得路的鸽子、断了线的风筝也好,家都会善待它们,让它们排排坐、分果果,靠在大院的墙上晒太阳。晒着晒着,就成了葳蕤蓬勃的太阳花了。改一句张爱玲的话:人生,其实是一袭华美的锦袍,绣满太阳花,也爬了一些虱子。当人生的秋天来临的时候,晒着太阳,展示锦袍,也捉着虱子,应有一种阿Q般的美好。人活一世,本质上都得敝帚自珍,充满自怜和自恋的乐观主义精神,否则哪里活得下去呢?虽然文字和所有东西一样,终究是落花流水,不过能心存想念、心存安慰,又何尝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呢?
文集又如大门关上的声音,让人心存忐忑,仿佛身后有追兵,一路嗷嗷叫着举着刀剑砍来。面对此状,我更得如狗熊一样奔跑,得拼命向前,拼命跑到自己的最高点,然后像西西弗斯一样摔下来。
感谢缘分,感谢相关助缘之人,为我半生的写作,作一个总结和了断。这是一部秋天奏鸣曲,畅达之中,有平静的惬意和欢喜。
是为序。
本卷序
苍白的乡愁
|一幅图|
在我的印象里,外公和外婆一直端坐在老屋堂前八仙桌的两旁,静穆无声,就像是一幅巨大立体的古代容像。
他们似乎一直是老人:外公长得白白净净的,有着稀稀拉拉的胡须,说话慢条斯理,永远是慈眉善目的;而外婆呢,似乎总是有倾诉不完的怨气,只要一开口,便用一口难懂的歙县话大声地数落。平日里,很少看到他们走出那个黑漆漆的大门,一有空闲,他们总是喜欢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像土地庙里的一对菩萨。
老了,也许只剩下沉默和思想了。外婆的心思是好揣摩的,无非家庭,无非生计;而外公呢,这个十来岁就开始“下新安”,后来又壮志未酬的“老徽商”,对于自己的人生,会不会有着失意的懊恼?或者,有着对宿命的怀疑?——总而言之,他们应该是在反刍吧,人与牛一样,在很多时候,是需要反刍的。当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做完,无须再做的时候,他必定会选择沉默和端坐,反刍岁月,内心忧伤。
|一物件|
20世纪70年代,外公、外婆的家已近一贫如洗了。我小时候只见过几枚老银圆,很漂亮,沿着边猛一吹气,侧耳聆听,便能听到风铃似的清脆响声。后来,银圆不见了,拿去换钱了,一枚银圆,当时能换八元人民币。我能得到的,只是一些铜板。铜板很漂亮,上面有一些字,“光绪”“咸丰”什么的。铜板是我们用来“打币”的:把一分、两分的人民币硬币放在青砖上,用铜板去打,打下来的,就归自己了。铜板是无孔的,铜钱则是有孔的。铜钱我们都瞧不上眼,在一些角落和路边,经常会看到一些生锈的铜钱。铜钱,就像历史的弃儿。
那一年夏天,我忽然迷上了斗蟋蟀。有一天,在老宅的旮旯里逮到了一只蟋蟀,顺手就放进了一只玻璃瓶子。泥菩萨似的外公忽然开口,他对舅舅说:你找几只蟋蟀罐给他,让他放蛐蛐。于是,舅舅不知从哪个角落拖来一个脏兮兮的大木橱子,里面竟然有数十个蟋蟀罐子!有的是陶砂制的,有的是青石刻的,看得出,是有些岁月的了。我挑了一个最漂亮的:似乎是用龙尾石雕刻的,比一般的蟋蟀罐要小,因为小,根本就不能放蟋蟀,一放进去,就跳出来了。但我喜欢这只罐子,它小巧、精致、漂亮,盖子上刻有一个人物,身着明代官袍,线条流畅;罐底下,有着篆刻印,大约是制作者的图章。
这个蟋蟀罐至今还留在我的身边,放在我的柜子里。前些年有一次拿出来赏玩,盖子落在地上,打碎了,随后又用胶水粘上,算是破相了。有时候偶然瞥到这个物件,我会突然想:当年这个蟋蟀罐到底是谁的呢?它比外公的年纪大,甚至要比外公的外公年纪都大。这个罐子那样精致,那样漂亮,当年的主人一定对它爱不释手吧?但爱不释手又能怎么样呢?物还在,人已去。两厢渺渺,物我两忘。
人真苦,童年如白纸,命终复空旷。我们生而支离破碎,只能依靠各种各样的物件来修修补补。
|一本书|
如果说“心想事成”的确有的话,那么我与《歙事闲谭》这本书的结缘,还真是心想事成。
2004年左右,正是我对徽州有着浓厚兴趣的时候,我阅读了很多有关徽州的资料,发现很多资料都出自许承尧所编撰的《歙事闲谭》,但我一直没找到这本书。那一天,我们去了徽州,把车停在屯溪老街边的延安路上买东西,顺便就进了旁边一个小书店,就在书架上看到了上下两本《歙事闲谭》——这样的感觉,不是“心想事成”,又是什么?
《歙事闲谭》其实就是怀旧。怀旧的心思,除了追溯尘封的人物和事件,还得触摸一些过去的品质:清洁、专注、端庄、认真、静美、自然和真实。那些不怀旧的人,总是显得肆无忌惮、无所畏惧。他们都是没有故乡的游子,是漂泊在这个世界上的萤火虫。在《歙事闲谭?自序》中,许承尧这样阐述他编撰的初衷:“垂老观书,苦难记忆,因消闲披吾县载籍,偶事副墨,以备遗忘。”他所说的“以备遗忘”,不是针对个人,更像是对未来。也因此,这本书更像是回忆,是一个老人对前世徽州的回忆和总结。眼中有大美者,内心必有敬畏和惜缘。
许承尧是老徽州最后的“三昧真火”。当老徽州注定逝去,新的世界携着锋利、快速和浮躁扑面而来的时候,也许,最佳的选择,就是躲进书斋,用一种温润的回忆来消解这个世界的寒冷。
回忆,是怀念,是留存,更是确立一种根基。许承尧的用意,我想就在于此。
|一段话|
现在回忆某些久远的事件和场景,我会不由自主地眩晕,像跌入空蒙,飘荡于云雾之中——从2000年开始,我陆续写了一些有关徽州的书,比如2004年的《思想徽州》、2006年的《千年徽州梦》、2007年的《行走新安江》以及穿插其间所写的《发现徽州建筑》(与张扬合作);然后,又因为喜欢徽州老照片的缘故,在2010年写作了《老徽州》。写这些书的初衷,是想以自己自以为是的思想,撞击一下徽州,然后去触摸徽州文化的内里。这样的感觉,就像一个妄自尊大的年轻人,以吃奶的气力,试图晃动千年古寺边上硕大古老的银杏树——然后喘着粗气,听头顶上叶子窸窣的响声——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书出版之后,大约是切合现代人的阅读口味和思维方式吧,不时地会听到一些肯定,引发一些共鸣。有点小得意的同时,也会让我诚惶诚恐、羞赧生怯。
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是他们给这一套书穿上了新装。 沉静的包装风格,对于文字和思想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尤其是对于我淡淡的乡愁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小团圆”。
徽州就是一个人、一幅图、一物件、一本书、一杯茶、一朵花……当安静地看,用心地品,用思想去解剖,用体温去摩挲,用禅意去赏玩,当所有的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商业化,带着他们的人、事以及心思时,一个人,如果能独守空灵,借助于某种神明,用内在的纽带试图去连接那一片安谧的气场,就该是一种幸事吧?这样的感觉,与其说是思念的流露,不如说是乡愁的排遣。一种坠落于时空变幻中复杂情感的宣泄。
徽州从未消逝,它只是和流逝的时光在一起。
在更大的程度上,徽州就如一个婉约的梦。
梦是奇特的。如果站在高空看徽州,就会明白这个地方梦一般的意境。这里峰峦叠翠,绿水如带。北面是“天下第一奇山”黄山,云蒸霞蔚,如梦如幻;东面是天目山,古木参天,连绵千里;境内还有称为“五大道教名山”之一的齐云山,奇谲秀丽,峰峦叠嶂。除此之外,所在之地几乎全都是大大小小、知名不知名的山。群山相拱之中,新安江顺流而下,山水环峙,轻帆斜影。青山绿水之中,古村落星罗棋布,粉墙、黛瓦、马头墙,恬然自得,清淡文雅。
雄伟的黄山当然是群山之首。黄山最大的特点是鬼斧神工、匪夷所思,在黄山面前,人类只有惊叹。黄山无处不石,无石不松,无松不奇;云来时,波涛滚滚,群峰忽隐忽现;云去时,稍纵即逝,瞬息万变。黄山是名副其实的仙境。仙境是什么呢?人消受不起的东西,就只有神仙来消受了。说黄山是仙境就是这个意思。曾有人这样形容黄山,说很多山都是在山外看起来美,而进山之后发现不过如此,而黄山却不是这样,黄山是在山外看着美,进山之后,人在山中,会发现黄山更美。的确是这样,黄山的美,不仅仅是静止的,而且是运动的、奇妙的,它可以瞬息万变,随着春夏秋冬的交替、晴雨天气的变化、阳光月色的晕染,变幻无穷,翻陈出新。纵使你一千次来黄山,你也会有一千次新的感受和发现——初春,云里花开,香漫幽谷;盛夏,层峦叠翠,飞瀑鸣泉;金秋,枫叶似火,层林尽染;严冬,银装素裹,玉砌冰峰。
对于黄山,所有的文字都是一种累赘。黄山就是一个坐标,它是上天用来检测人的创造力,也是用来警示人的创造力的。有谁敢在黄山面前自满又自得呢?只有徒叹自己渺小的分量,也徒叹自己创造力的薄弱。黄山当然是属于徽州的,它代表着徽州的钟灵毓秀,同时又将徽州的美推向了一个极致,它是无法被超越的。在黄山面前,所有的山都自甘寂寞,但却不甘渺小——在徽州,每座山都有每座山的奇特,每座山都有每座山的风景,比如说齐云山的奇谲,清凉峰的神秘,牯牛降的繁杂。甚至,一些微不足道的山也都有着它的诱人之处,也都有着各自的性格和魅力。
从总体上来说,徽州的山是妩媚的,也是灵秀的。它们不是咄咄逼人的美丽,美丽是外相的,是一种虚假的东西,它没有用处,它不会看人,而只能被别人看。徽州的山是会看人的,它们看尽了沧桑,所以归于平淡。它们不属于雄奇的、艰险的和叛逆的,它们是属于小家碧玉型的,懂情、懂理而又无欲则刚,是那种看似寻常巷陌而又深藏着智慧的风格。当然,黄山和齐云山是徽州山峦的两极,它们可以说是徽州山峦的一种参照、一种反观,似乎是所有山的平凡才能孕育着它们的离奇和神异。不是说它们是高人一筹的,是出类拔萃的,它们同样是山。黄山是属于文学和诗的,是美和秀的,但黄山是太美了,是美丽到极限的那种,它容易让人们惊叹于它的美丽而忘却了其他所有的东西,容易因为美丽而丢失内容,比如文化、宗教等。我们可以把黄山和九华山相比。黄山天生的钟灵毓秀和精美绝伦似乎天生就是让人来观看的、来惊叹的,这样的美丽和脱俗使得它天生地与人世有一种距离感,它散着美的光辉,高高地耸立云端,如一轮理念的太阳。黄山的美丽绝伦,使得它在这个世界上一直保持着居高临下的姿势,它是俯瞰众生一览众山小的;与此同时,因为美丽至极,它也是简单的,它只是美的,它的美让所有赋予的意义都显得牵强附会。九华山则不同,九华山的大气、智慧、无欲则刚的整体感觉,更接近于佛的宗旨,所以凡是懂佛的人,只要看一眼九华山,必然认定这是佛的最好栖身地了。因为两者的精神是契合的,是合而为一的、是密不可分的,也因此,九华山承担了更多的文化、宗教意义。在这一点上,齐云山也不同,与众多徽州的山相比,齐云山的特点在于其奇谲和幽微。这是一种更接近于道教真谛的东西。不仅是齐云山,其他的道教名山,诸如四川的青城山、江西的龙虎山、湖北的武当山等,其实都是一种风格,是一种暗合道教精神剑走偏锋的感觉。所以从这一点上说,齐云山是“道”的,而且应该是“道”的。
让我们撇开美到极致的黄山以及奇谲的齐云山,来感觉一下单纯而普通的徽州之山。白天的山是普通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特色的,它们不高也不险,不奇也不谲。它们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一点也不引人注目,是彼此之间没有特色也很难辨认的。我们很容易把一座山误认为是另一座山,把一个山坳误认为是另一个山坳,甚至把一个地方误认为是另一个地方。它们叠叠层层,错落散布,就如同迷宫一样。迷宫之所以“迷”,那是因为彼此没有可以区别的地方,相似和重复,这就是迷宫的真谛。但这最朴素自然的山是最有生命的,它就像一个最平凡的妇人一样,从不引人注目、从不招摇过市,但它极具生命力地孕育着自然的生机、人类的生长和文化的延续。
山是缄默的,也是永恒的。缄默是指它从不对世人表示什么,永恒则在于它比人类的历史更加漫长。当徽州还不叫徽州,或者也不叫其他什么称谓的时候,甚至这一片地方还是蛮荒之地时,它们就已经存在了。它们才不理会人类呢,在它们看来,人类的历史都是过眼烟云,它们早就预知了这块土地的结局,周而复始,一切都归于零。它们的沉静,是因为它们目睹了过多的重复。对于时间,它们是不敏感的,因为时间对于它们没有意义,能让它们燥热难耐的是四季。在四季的更替中,它们往往倾注着热情和愿望——春天,整个山峦是一片水洗过的新绿,纯净而透明,所有的植物都将喜悦挂在脸上。布谷鸟在灌木丛里抑制不住激动,它们上蹿下跳很是欢欣,云雀总是不甘寂寞,在蓝天里划出一道道弧线。夏天,则是一种浓绿,仿佛从天上倒下来无数绿色的颜料,淹没了山野里其他的颜色,即使有一点杂色,也像是水中的一片浪花。秋天呢,那是色彩的盛宴,仿佛所有的颜色都盛装打扮,来参加一个节日的舞会。然后,便是色彩的狂喜,在狂喜中,主色调变成了金黄,变成了一点零星的红。红是山野的枫叶以及乌桕树叶,那样的红灿若云霞,似乎每株树与每株树都不一样,每株树都有着不同的风姿,甚至每片叶子与叶子之间,那样的红色都不一样,都在尽自己的个性进行招摇。秋天是色彩最后的节日了,也许它们是想在最后的生命中,尽情地展示华丽的篇章。很快,冬天来了,寒冷淹没了所有的颜色,这时的主色调变成了最本色的白色。冬天如果下起雪来,便是原驰蜡象般的一片白。这时候的徽州仿佛是一个放大了的盆景,它静止而沉寂,又仿佛动物一样,在寒冷中冬眠了,静心了,但实际上在它的骨子里,却欢喜而热闹,在它的心里头,正孕育着下一季轮回的温暖。
颜色就是四季的表情,也是从内心当中溢出的情感,它富有主观的意义。但山是有本质的,也有本质的颜色。这一点,山与所有有生命的东西一样。它本质的颜色,应是黑色的或者白色的。掀去地表的层土,它的里面是黑色的石头,或者是白色的石头。这样的颜色,不仅仅是山的本质颜色,同时也是世界最本质的颜色。梦境似乎可以拿来说明一点问题——在人们的梦境中,是从没有斑斓色彩的,也不会出现其他颜色,只有白色或者黑色。这就是本质。由梦境可以得出结论,所有其他的颜色,都是颜色的延伸,那是一种附会或者迷幻。山如果会做梦,它的梦必定也是黑色或白色,黑色是过去,白色是将来,与黑色、与白色相连的地方,就是现在。所以,现在是虚假的、是不确切的。山的梦一做就是很多年,很难说它一直是梦着或者说是醒着,但它总是在假寐中等待,这样的等待无所谓欢欣,也无所谓悲痛——人们总在它们身上攫取粮食、树木、水果、布谷鸟、叫天子、黄莺,甚至蚂蚱、蛇蝎等,也在它的身上欢唱或者哀啼,但它总是隐忍着,什么也不表现,就像情感无法穿透它似的。人总是受时间捆绑的,时间从不放过人,它们把人当作自己的奴隶。但对动物,时间却异常宽容,因为它们既不想创造什么,也不想留住什么,它们从不自以为是,它们只是观望,无动于衷地观望,什么都不会往它们心里去。对于动物,包括植物,时间给它们的优待就是,尽量宽容地对待它们,让它们像四季一样反复轮回。动物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它只有空间,所以它可以轮回。植物也是。但人类不行。在动物的眼睛里,是可以找到轮回迹象的,你只要正视动物的眼睛,就可以从它的瞳孔里看到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影子,那是一片纯净,是过去或者未来的通明。
夜色来临之后,徽州的山总是显得很苍老,冷月无声,清风呜咽,所有的一切空旷和寂寥,黑黢黢的,有点接近虚化,只有轮廓,没有立体感和细节。这时候山与山之间是彼此相连的,不仅仅在空间上相连,连内心都合而为一。它们融合在一起,彼此之间交换着感觉,也交换着对于时空的印象。夜晚的山峦似乎更神秘,更具有一种神性,就像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具有那种缥缈的感觉,也更接近于这个世界的本质。而山风总是不知所来,又不知所踪,这山风很容易让人想起时间、历史、幻想,也容易让人谈起传说或者故事等具体一点的东西。从人们嘴里说得生龙活虎、惟妙惟肖的东西往往是虚假的,而说不清、道不明无从说起或者压根儿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山就是这样,你无法说清道明它,但你可以感觉得到,它的灵魂是确切存在的。彼此面对,如果静静地放下心来,进入一种物我两忘的境地,你便会感到一种轻若游丝的音乐缥缈,感觉到山、头顶上的星空、夜风飘忽中的萤火虫与自己的心灵,其实都是一个东西。水印象
“天地恒昌”是徽州人从山地中领略到的,而水,则让他们感悟到人生的无常。山的哲学是不知日月,水的哲学则是不舍昼夜。徽州人离不开山水,他们的民居都是依山面水而建,在这样的接触中,人们寻找着与山水的亲近,也得到了内心的安宁。
徽州的水是这块土地上最具灵性的内容。它们是由土地的灵气幻变而生的,也暗藏着这片土地的情感和欲望。曾经有一阶段,它们是天上的云,在天空中飘浮游荡,因为距离,它们有着清醒,可以冷静地感受和观望土地的美丽和沧桑,揣摩着巨大内容背后的细节。但这样的清醒状态让它们惶恐而慌乱,它们急切地想重新回归。在天宇之上,它们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孕育着,然后在某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它们倾泻而下,哗,哗,哗……重新皈依土地的温暖和踏实。当它们的双脚一接触到地面,便立即变得心安理得、欢呼雀跃。它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条条溪水或河流了。
徽州的水总是绿的。是一种沁人的绿,也是一种有着内容的绿。水是宁静的,但这是表面的,宁静只是它的表面特征,它的内在仍是不安分的,是躁动的。它需要交流,需要运动,仅仅有爱是不满足的。它渴望升天,也渴望走出山外。水的躁动与山的敦实构成了截然不一样的性格。但这种截然不同不是矛盾的,而是和谐的。山总是容忍,总是包容,所以它负载历史,凝固时间。而水的躁动总是对现实加以冲击,它不满足现状,渴望改变历史,改变观念。水的流淌就是活力在流淌,整个徽州就是因为水的流淌而变得丰盈起来。
徽州的水负载了很多的经济和文化意义,但它又毫不把这种负载放在心上,它依然自在,依然轻松。水是清的,也是深的。每一条河流都有无数条由涓涓小溪组成的分支。真是多亏了这些水系,它串起了整个徽州。它给徽州带来了生命、希望和不断更新的内容。在水边,总是湿漉漉的青石码头和石拱桥,宅基地浸在吃水线以下的老房子探出个身子;弥漫诗意的雨巷,青灰色的瓦檐永远有一种惆怅的意味。当然,下雨天的时候,总有人撑着油纸伞在等待着什么;也有人挎着精致的竹篮,在桥边沟边摘着马兰头、荠菜以及地衣什么的。徽州人的出行也是从小码头顺流而下的,那往往是黎明或者傍晚,小舟缓缓地撑离了码头,天际上有一弯不甚明澈的月亮。几乎没有声音,偶然只是水面小鸟的叫声,再就是桨橹击水的声音了。在船尾摇橹的艄公蓑衣竹笠,有一搭无一搭地跟船舱里的那个人说话。潺潺的水声有时会夹着雨点的杂乱,而那个船舱里的人有一声无一声地回答着,此时此刻,即将离家远行的他已变得失魂落魄了。这时候整个河流乍一听是静寂的,但只要用心去听,你会听到一首绵延的、有着巨大感染力的交响曲。河流是赋予人和土地灵魂的。这时候船里的人会感到茫茫的水面是一种巨大的生命存在,人在其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音符。
在这片土地之上,最著名的、给徽州影响最大的,就要数新安江了。新安江是从徽州西北方向流过来的,它清澈见底,富有生机,像少女一样天真烂漫。水面上有鱼鹰昂首游弋着,有时候会突然扎入水中,叨出一条鳜鱼来;江中还有水獭,在拐弯处的沼泽地里偷偷溜出,从岸边噙走一只青蛙;那种精灵似的水鸟飞来飞去,像线一样滑过水面……而在更多的时候,它又显得娴静、温顺、包容、智慧,像一个恬静的少妇;开阔处,它水天一色,烟波浩渺,宛若梦中情人;两山相夹中,它更如仙女下凡,一条长长窄窄的飘带,很随和地飘散在起伏绵延的山峦之中。
新安江是徽州的母亲河,也是徽州文明的“月亮河”。说“月亮河”的意思在于,这一条河流能够给徽州一种潜质,并且能给徽州很多观照。它所具有的,是那种月光所具有的潜在的神性。新安江水不仅对徽州文化有巨大的影响,同时在灵魂上也赋予徽州以灵秀的意义。它蜿蜒静谧,就像这片土地内在的魂魄一样,悄无声息地游走。近山滴翠,远山如黛。而更远一点,则是一派清新美丽的自然风光,随意地散淡在那儿。在山坳密密的树林边,掩映着白墙黛瓦,传来了阵阵鸡鸣犬吠声。
新安江看起来还是忧郁的。这反映在它的颜色上,那是深深浅浅的绿中带一点蓝的颜色,那样的蓝是一般人很难察觉出来的。这样的蓝色,就是新安江的忧郁,也是它内在的情绪。实际上不只是新安江,任何一条河流,从本质上都是忧郁的。那是因为它承载的东西太多,心思也太绵密。一个东西,如果责任太多、心思太多,那它就不可能不忧郁了。这一点就像时间,实际上时间也是无形的河流,我们全是在这样的河流中沉沉浮浮。时间也是忧郁的,虽然它看起来那样理智,充满着冷酷和无情。但时间在骨子里还是忧郁的,它充满了慈悲心,它总是悲悯地看待河流中的任何一个人。看他们无助,也看他们自以为是、得意忘形。这时候,时间总想善意地提醒人们,不过很少有人觉察到,一直到时间放下面孔,冷若冰霜地对待他们时,人们才恍过神来——这些鼠目寸光的人啊!
在大多数时候,新安江总携有一团浓浓淡淡的雾气,即使是在阳光灿烂的时候,看起来也是如此。这使得河流上的木排、船以及船的帆影,常常有一种梦幻般的感觉,仿佛它们不是漂浮在水面上,而是飘浮在云彩之上,并且将要去的是一个神秘的天堂之国。船也是不甘心一直寂静的,有时候岸边会传来隐约的箫声。徽州的高人隐士总是很多,他们喜欢独自一人的时候吹起竹箫。那箫声凄清幽静,这样的声音,似乎骨子里就有悲天悯人的成分,它就是用来警醒忙碌而贪婪的世人的。有时候江边还会传来笛声,那笛声在宁静的背景中,更显孤单而悠长,具有撕心裂肺的味道。在江边,一直有很多古树葳蕤,从很多年前开始,它们就一直伫立在这里,观看着这样的情景。这些老树都是成了精的,它们似乎从一开始就知道事情的结果了,知道世情冷暖、人力无奈。但它们一直保持着缄默、保持着木讷。它们从不对人情冷暖说些什么,最多是在夜深人静时,悄然发出几声重重的喟叹。
很少有人问,要是徽州的水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会怎么样?徽州呈现的面目会改变吗?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很难想象徽州没有水会怎么样,徽州没有新安江又会怎么样。没有流动的水,敦厚而木讷的山会占据主导地位,那将是一个全封闭的、没有生机的世界。时间可能会是缓慢的,一切观照没有了流动感。没有河流,徽州所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历史和文化,影响最大的将是心理上的。人们将失去温柔,失去细腻,失去敏感、体贴、才思以及诗情。
徽州的山水就是这样富有魅力和诗性。也因为这样的山水,潜移默化着徽州人的审美和人生走向。曾有人说,如果你要真正地认识一个地方人们的性格,你必须到那个地方走一走,看看那里的山水,你就会知道那里的人文走向,也就会真正地了解那个地方人们的喜怒哀乐。的确是这样,山水的灵性总是在不经意中潜入人的血液。受这样一等美丽的山水影响,必然会产生一流的人物,因为在这样山水之中所成长的人,他的灵魂中必然有着山川之灵气、山川之心胸。当然,这样的灵秀山水也是可以消磨人们志向的,在徽州的过去和今天,已有相当一部分历史与人整日沉湎于山水之中,消解了,也湮没了。当然,这一切太正常不过,历史与世界观一样,都是很难辨别对错,也很难辨别黑白的。所有行为都源于理解,源于认识。而人的思想,往往就是因为一张纸的隔膜,相差十万八千里。
新安江,就是在这样的不怨与不嗔中,缓慢而优雅地流动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徽州的历史也是这样,它一直沿着新安江顺流而下,飞溅起万朵浪花。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徽州的河流永远有着起点的意义,它既是空间上的起点、时间上的起点,同时也是思想的起点以及才情的起点。
与这些老树紧密相依的,还有村口溪水边的风车。那些风车总有一种破落贵族的气质,一副孤芳自赏的神情,看起来无动于衷,自负、冷漠、桀骜不驯。风车的感觉总像是村庄的叛逆者,也像是村庄边游荡的野鬼孤魂。当年破落贵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引得全世界都开心一笑。其实,堂吉诃德跟风车应该是同一个东西,在他和它们之间,具有同样的意义。当然,风车的倨傲是有理由的,因为它们给村庄带来了太多,也目睹了很多,而自己从不索取什么。风车屹立在村边,在它们的身上,隐藏着这个地方的一些元素,也暗藏着一种隐秘,这些元素可能在将来的某一个时间会出现,并凝聚、降解、分化,成为某种力量。当然,在更多的时候,风车不是风车本身,它还是乡村孩子们的游玩工具。那些村里的顽劣孩童在黄昏来临时会集中来此,骚扰一番,嬉戏一阵,然后,大笑着离开。每当寂静重新来临,风车便会郁郁寡欢,会在蔓延的夜色中躲藏起来,像遗失的旧梦一般。
与孤傲的风车相比,村边的耕牛以及独轮车似乎更符合村庄的口味。田里耕作的是水牛,山地里犁田的是黄牛。耕牛的历史有上万年了吧,上万年来,它们一直是人类的好朋友,忠心耿耿,绝不背弃。牛眼看天下,是无所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也无所谓好与坏、是与非。所有的时间,在它们看来,都是同一个东西,所有的行为也是这样。世界在它们的眼中,也是那样的简单和单纯,没有分别。至于独轮车,它们一直以一种缓慢的节奏连接起各个山村,在这个山村与那个山村之间的石板路上,它们执着的轮子轧出了深深的痕印。这样的车辙让村庄变得踏实,也感到心安。在独轮车面前,村庄会觉得自己还年轻,因为车的岁月更长、年轮更密集,并且它们永不厌倦。那些如活化石般的东西虽然不富有激情,但它坚韧而含蓄,充满了人间烟火,也充满了人间真谛。这样的状态,也如同人生——其实人生也一样,最根本的,就是不能厌倦,要能相守,能保持常态。一厌倦,问题也随之而来了。老山村深知这一点。所以它一直努力着,不让自己厌倦,它一直保持着一种节奏,缓慢而悠长,如歌的行板,这节奏千年万年地延续着,一成不变,伴随着植物的气息,还有牛粪的味道,飘荡在乡野里,也飘荡在时光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