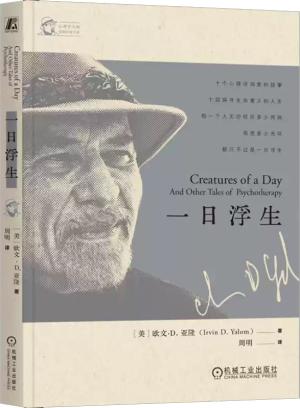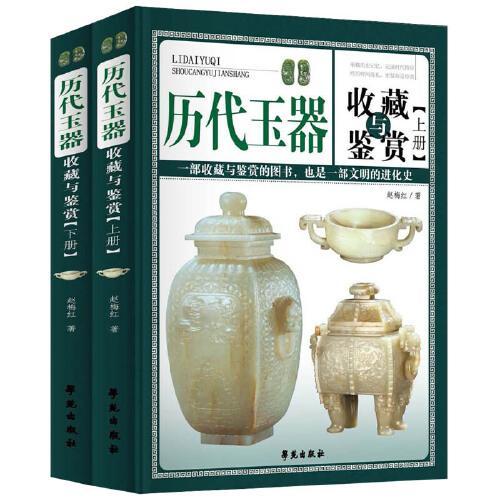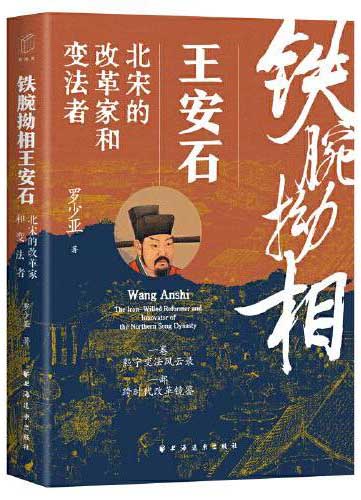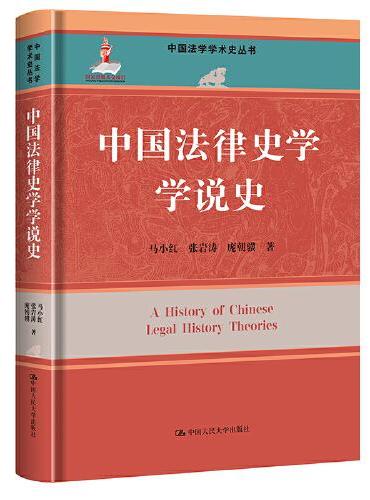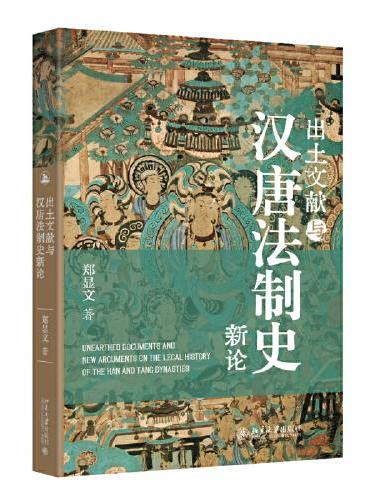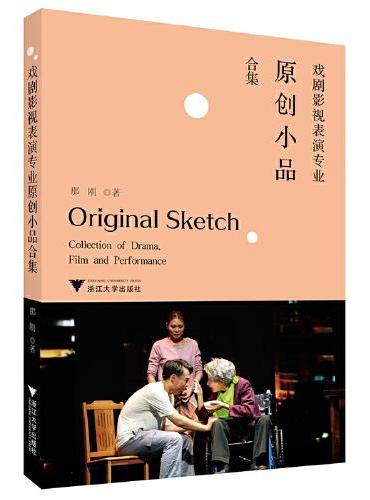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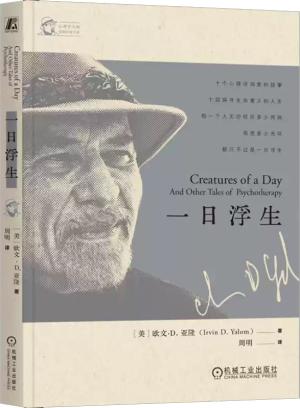
《
一日浮生
》
售價:NT$
3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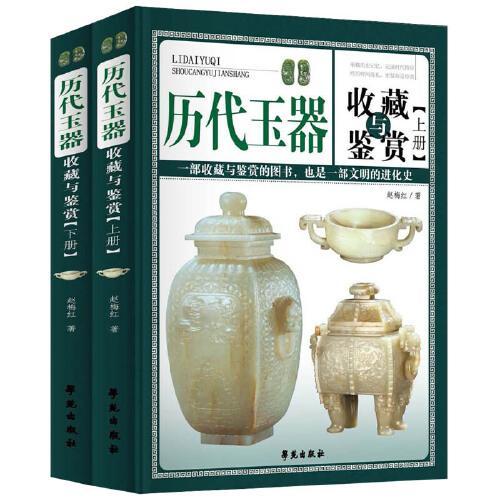
《
历代玉器收藏与鉴赏
》
售價:NT$
183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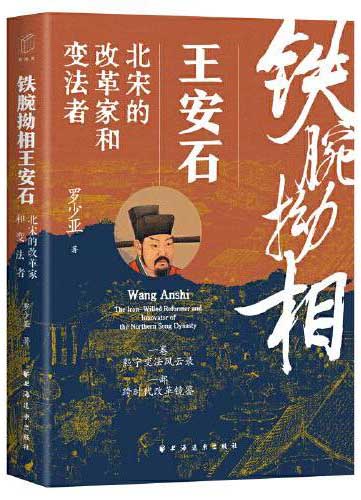
《
铁腕拗相王安石:北宋的改革家和变法者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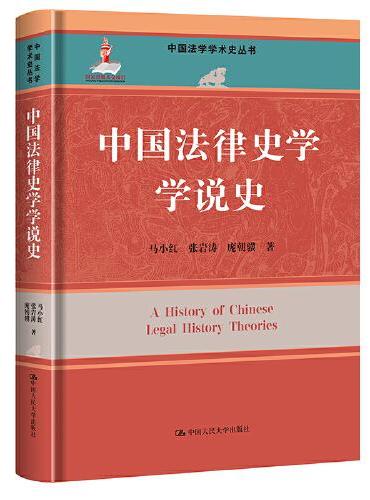
《
中国法律史学学说史(中国法学学术史丛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
售價:NT$
857.0

《
方尖碑(全2册)
》
售價:NT$
4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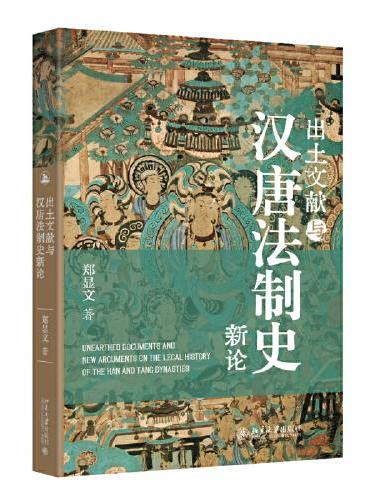
《
出土文献与汉唐法制史新论
》
售價:NT$
398.0

《
最美最美的博物书(全5册)
》
售價:NT$
7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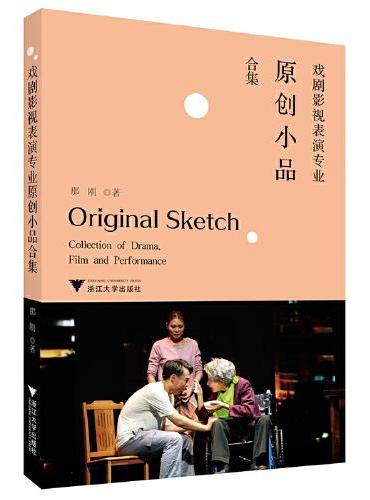
《
戏剧影视表演专业原创小品合集
》
售價:NT$
449.0
|
| 編輯推薦: |
★“红色牧师”声名远扬。在那个军阀混战的黑暗时期,余心清利用在冯玉祥军队担任“随军牧师”的机会,大讲世界革命之潮流,中国贫弱之根源,以及革命军人应肩负的救国救民的重任,从而推动了西北军的革命化。惊世骇俗的“红色牧师”,风传一时。此外,他还是一位热心育才的教育家、坚持抗战的爱国者、坚强不屈的民主战士、勇于负责的领导干部,在党的建设和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业绩。
★真实感人的纪实作品。本书真实感人地记述了作者余心清被捕前的政治活动以及被捕后在北平、南京两地的狱中生活,从侧面揭示了革命的胜利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广泛团结全国各阶层、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勠力同心、并肩战斗得来的。
★“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为献礼百年荣耀时刻专门设计,收入作品皆为名家名作,旨在重温红色经典,缅怀先烈,传承革命精神,弘扬爱国主义。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一部纪实类文学作品,文中真实感人地记述了作者余心清被捕前的政治活动以及被捕后在北平、南京两地的狱中生活,书中多处提到他与冯玉祥将军共同策划反对蒋介石独裁打内战的密切交往。作者从青年时起与冯将军多年相随,他们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上互有影响。他们之间不完全是长官与部属关系,同时也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因此所述更是翔实真切。全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革命的胜利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广泛团结全国各阶层、各民主学派爱国人士戮力同心,并肩战斗得来的。
|
| 關於作者: |
|
余心清,爱国民主人士,安徽合肥人。1920年毕业于南京神学院。1927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行政系。曾任冯玉祥部开封训政学院院长、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务处处长。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经济委员会代主席。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训政处处长、第十一战区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4年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1947年9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49年获释。同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典礼局局长、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国家民委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等职务。著有《在蒋牢中》。
|
| 目錄:
|
一、由山城到古城 // 001
二、被捕的清晨 // 021
三、初的两个月 // 036
四、宁海路十九号 // 071
五、羊皮大学 // 094
六、不朽的死 // 129
七、特刑庭 // 150
八、从牢门的狭缝中挤出来// 188
|
| 內容試閱:
|
黑夜虽然快消逝,但黎明前还有更昏暗的一刹那,象产妇生产前的阵痛,这一刹那难熬,也难度过。
那一只魔掌,虽然是已经缩到幔子后面,但还在远远地伸着。
每一颗心都浮动起来,一天的时间,觉得更长了,好象太阳永远不会落到西边去。
每一个人的脸上,不再看到愁容,老董的前额上,少了一些绉纹,陈斌的嘴更俏皮了。梁蔼然不时从嗓子里哼出了几口二簧。
今天,他们——蒋介石一帮的悲哀,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欢乐。
腐烂的加速腐烂,好叫崩溃的赶快崩溃,一个已经臭了的尸体,让它毁灭在它自己生前掘的坟墓中吧!
我们的屋子里,长日挤满了人,一批出去,另一批走进来。谈到高兴的时候,大家举起杯来互相碰着:“让我们用一杯清茶,代替一杯烈酒,来畅饮,来庆祝。”
一月二十六,是梁蔼然四十岁的生日,我们清早一爬起来,就和他握手道贺,听说在军法局看守所里的时候,有位会算命的朋友给他排过八字,说他“要脱牢狱之灾,非过了四十岁生日不可。”我对梁笑着:“看情势,这回算命的猜着了。”我们在中午弄到一包糖果和一些花生米,就给他大张盛筵,庆起寿来。这一天我们喝的水特别多,把两只马桶都尿满了。
二十七日的上午十点钟左右,一个看守跑进来对我们说:“命令就要到这里,你们今天下午准可以出去。”这一消息,引起了一阵骚动和欢呼。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把行李捆好,坐在铺盖卷上等待释放。我漠然地躺在铺上,有点不相信事情会这么干脆地解决。自然,捆不捆铺盖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我没有理由去反对别人捆铺盖。等到夕阳斜照在铁窗上,大家等得不耐烦的时候,依然“杳无消息到人间”。这时候重新打开铺盖的人,有点不是滋味了。
第二天清晨,大家爬起来特别早,这是一月二十八日,阴历年的除夕。有的朋友在屋里嚷:“他妈的!昨天不放,今天还不放吗?硬要叫老子们蹲在牢里守岁吗?”昨天报信的看守又来了:“今天准放,我敢保险,不放‘惟我是问’。”大家听了,又兴奋地跳跃起来,好象昨夜的失望,被这一两句话早已吹到九霄云外。每个屋子里,又忙着收东西,捆行李。我的被褥仍然原样地放在床上,陈斌问我:“昨天不收拾,今天还不收拾吗?大概今天有希望出去的。”走进我的屋子的人,都奇怪我的态度,为什么反倒更沉着起来了?
“毒蛇把人们的指头咬上的时候,怎么肯轻易松口。”我常常想起这一句话。
我们永远是他们的敌人,他们也永远是我们的革命对象。
过分的希望,有时会招致过分的失望。
自从在北平被捕、走出我住的卧室那一刹那开始,相反地无时无刻,我不在准备着死。这并不是矫情,因为我的问题,我自己清楚。
有一次兰华告诉我,她找过张知本(立法院院长),请他帮忙。张说:“已经托过特刑庭的庭长,据这位庭长说,现在又发现了我在牢中写给我兄弟的一封信,要他赶紧到苏北去活动,这封信现在留在检察官手里,如果是事实的话,事情就难办了。”很明显的,这是他们的一个阴谋。
因此,除了谢士炎之外,我对一般难友,都为他们抱着希望,并且不断地鼓励他们,只是对自己,却断绝了这个希望。
这几天来,朋友们不断地和我讨论着一个问题,就是许多难友出去的安置,因为他们有的离家太远,有的一文不名,并且问我,是不是能在我出去以后,和李宗仁商量一下,解决他们的困难。这件事倒引起我注意到另外的一个问题。
李宗仁上台以后,为了进行他的“和平”,可能想起我来,拉拢一番。“我还能替这般家伙作‘冯妇’吗?”我这样问着自己。“决不和他见面!”后我决心下定。
我告诉朋友:“因为我们不够了解外面的情势,政治上的行动就不能不慎重。朋友们中间的困难还是我们自己来解决。能走开的一出去就迅速地走开,能隐藏的就赶紧地在外面隐藏起来,我们有经济能力的,应当尽力帮助手上没有钱的。”
从以后的事实上证明,我的想法,完全正确,所谓“和平”,原是阴谋,李宗仁走上了更反动的路子。
后来听说在我出去以前的一星期,李宗仁派人到我的家里,探望了一次,并赠送金元券两万元,还说要帮助通知特刑庭早日释放我,等到我出来的第二天一清早(阴历的新年),邱昌渭衔着李的命令去看我,代表李邀我出来“斡旋和平”。兰华对他说:“心清因为心脏病很厉害,一出牢,就乘昨天的夜车去上海就医了。”
“斡旋和平”,多么好听的一个名词,一年前我策动和平的时候,你下令抓我,你咒骂我,今天,你上台了,你要和平了。看我这颗脑袋还长在脖子上没有分开,又想来借重一番,你未免太自命聪明了吧!别打如意算盘吧!从今我们不是朋友了!让我们永远敌对着吧!
因此,出狱之后,不敢住在家里,躲了几天,情势渐渐不妙,就溜到上海,正碰到上海抓人,我就溜到香港,因为如果我再度地被捉起,单是李宗仁的态度就可想象了。
中大的几位同学,走到我的面前,和我握着手,告诉我:“他们这几天作着牢狱生活自我检讨的总结,希望我给他们每人一个批评。”这个问题倒难住了我。我对他们说:“你们的态度,我从心里敬佩,批评的话我是一句也没有。”他们总以为我和他们客气,不肯直率地说出,就一再地勉强我开口,其实,我说什么呢?他们和我同住的日子,从来没有私生活的接触,因此无从知道每个人的短长。我只见到他们学习那样的努力、有恒,态度那样的沉着、英勇、有生气。我为他们前途抱着希望,我为新中国前途深致庆幸。我相信十年后的领导阶层,就是他们这一类的人。“不要脱离群众,不要间断学习,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你们将来的成就,一定是不可限量的。”后我对他们这样说。
伟大的时代,创造了这一代伟大的青年,这些伟大的青年又去创造未来的伟大时代。社会是不停止地向前推进着,现在中国革命的胜利,已在加速的发展中,那些栏横在进步程途上的障碍物,很快地就要被清除干净。未来的监牢,将要成为教育坏人、强迫坏人参加生产的场所。蒋介石匪帮丢失了一个“王朝”,我们丢失的却是一付锁链。
当天的下午,一个看守手里拿张名单,还没有打开铁门,有的人就嚷起来:“开释了!”这时候大家都拥到甬道上,好象要争先出去的样子。等到念完了名字,出去的是十位苏北籍的难友。有的人等得不耐烦了:“还有没有人放出去呢?”“等第二批吧!”看守忙乱地回答着。
过了约莫两小时,第二批名单到了,站在铁门里的朋友们,一看到就嚷起来:“又来了!”点完了苏州“群社”十几位青年的名字,接着喊到我的名字,这时我还躺在床上,翻着一本《唐诗》,陈斌跑进来说:“现在你该捆行李了吧!”好几位朋友,帮我捆好了铺盖,并且给我搬到铁门边,我们紧紧地握了手,然后走出来。
这一批名单,除了十七位苏州朋友,就是我们一案的七个人。法警领我们走到大门里的院子中停下来。这时,院子里挤满了各形各色的人,除了我们,还有另一批普通监犯,也在等着出去,许多来迎接的家属,站在一边焦灼地用眼睛寻找着他们所等待的人。
兰华和华心跑过来和我及梁握了一回手,我们相对望了一望,没有说什么,李文卿(照顾梁的)走过来说:“你们还得到特刑庭去开庭。门外已经预备好了一辆大汽车。”陈斌问他:“我们还要上特刑庭吗?”“是的。”李说。
等到特刑庭法警把我们查点清楚,那扇象老虎嘴的铁门微微地开了一条缝,我们和我们的行李就在这缝里挤着出去。
老虎桥边站着的人就更多了,一半是家属东张西望地打听他们家中的人,一半是看热闹的过路行人。陈斌的太太穿着一件绛红色的短袄,围着一条大红围巾正在人群中窜来窜去,在斜照的阳光下,红的象一朵五月的石榴花,等到看见了她的丈夫,就跳着跑过来。梁笑着对她说:“回家等着吧!我们还有未了的手续呢!”
华心雇了一辆三轮车,拉着我的行李,兰华去找梁的一位朋友金先生(他在审计部的一个机关里服务,我们要他到特刑庭来招呼我们。)我们爬上了汽车,一个法警和我坐在司机的旁边,车子一开动,有的朋友就唱起来。我回头看那张老虎嘴,已在我们的后面紧紧地合上了。
特刑庭的门口,已经没有了警卫,汽车一直开到院子里。那间候审室,不再被炊烟熏着,横七竖八的凳子杂乱地倒在遍地扔着的字纸上。有一位苏北的难友坐在一个墙角落上叹气,我问他:“你不是在批名单里出来的吗?为什么还留在这里呢!”他抬起了失望的眼睛看着我:“他们叫我找保,我是江北人,此地没有亲友,找不到保,他们就不放,要把我押在这里。”我安慰他说:“放心吧!他们不会再把你送回监狱去,此地又不是关人的地方。等到晚间,他们看到你真的没有保,也要放你出去的。”随即我找到一个法警,拉他到一旁,问他对这个朋友怎么办?“这就是衙门的一套,别人放完了,还得让他走。”
我们七个人一同被喊进去,还是那个姓廖的坐在上面,他的一边,坐着对于我们有好感的年青书记官。他把我们的名字点了一遍,接着就向我们说:“现在政府诚意地谋求和平,要把你们开释出去。你们应当体念这种苦心,大家出去以后,应当为着和平和建设共同努力。”他停顿了一会儿,脸上带着不自然的神色,用两只贼般的小眼向我扫射一下,然后继续着说:“本庭奉命开释你们,各人到外面取保。”老顾和小耿问他:“我们实在找不到保,能不能通融一下呢!”“不行,没有保就还要押。”他不耐烦地说着。
回到候审室,我和梁商量:“我们两个人的保不成问题,他们五个人呢!我们不能不管。”李文卿立在我们一旁,梁问他:“你能保我们七个人吗?”他迟疑了一下说:“如果我作了保,我就得跟你们走,否则你们走了,他们要人,我怎么办呢!反正我早已下了决心要离开这里,以后你们到那里,我也到那里。”梁望一望我,我们都点了头。
这时法警开口了:“今天是阴历年,我们要不是为了你们诸位先生们,我们早已回家过年了,现在忙了一天,还要陪着出去对保,唉!没有法子,替先生们效劳吧!”我把梁和李文卿拉到外面:“这小子要价了。”我对李说:“你和金去商量打发他们吧!”李和法警去了好久才回来,李看见我和梁的时候,把右手五个手指伸出来翻了三次,同时告诉:“保单上的印盖过了。”我们知道“后赎身费花了一万五千元”。
夕阳已消逝在黄昏里,灯光把人影照在地上,这时候,等待后释放的通知,谁也坐不定,焦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因为保单对过以后,还得送去让那姓廖的看一下,他签了字,我们才能走开。这个关节,也是他和法警权威的所在。
消息终于的来到了,那个和我打交道的法警笑着来了。“廖法官对于一颗图章担保七个人,还有一点挑眼,我给诸位先生竭力承担下来,告诉他‘决没有错’,现在恭喜先生们,你们回去过年吧!”华心听到了,就拉着我的手说:“爸爸!自由了,回去吧!”
梁和他的朋友金同李一道走了,陈斌一直地去找太太,老顾、小耿四位各自投奔亲友,我和华心正走出门口的时候,碰上和我一道关在笼子里的那位汽车行老板,开着一部汽车来接,我们上了他的汽车,华心问我:“回家吗?”“不,先到照相馆。”我一手捋着长须,一手摸着白了的头发。
今天整整是十六个月零一天。
我没死,蒋介石终于垮了。
我微笑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