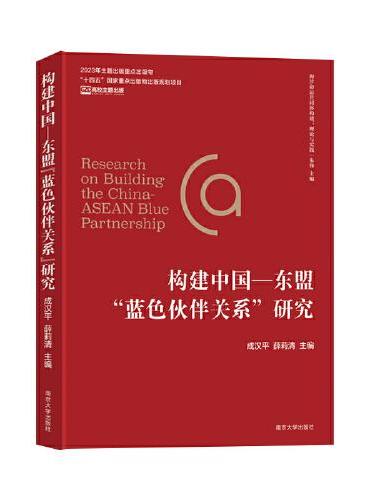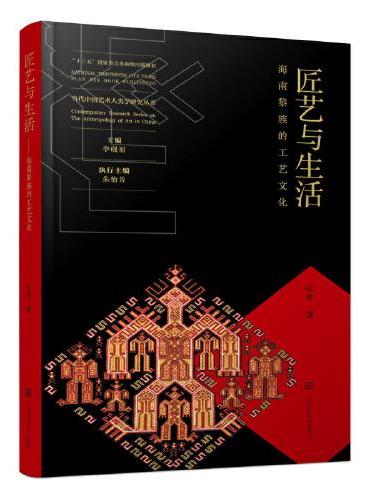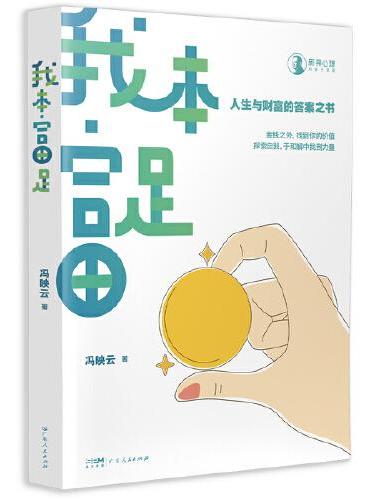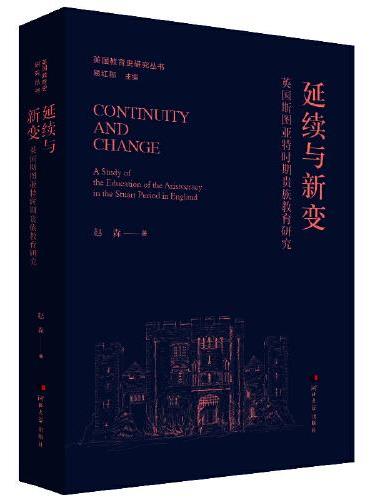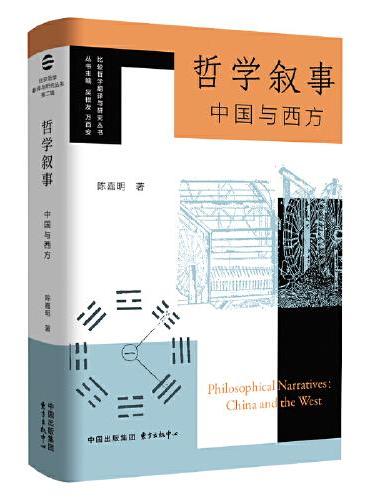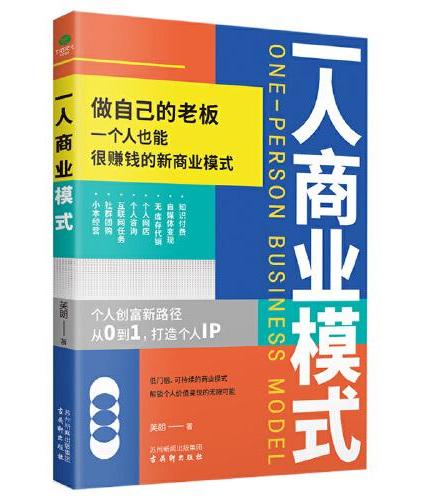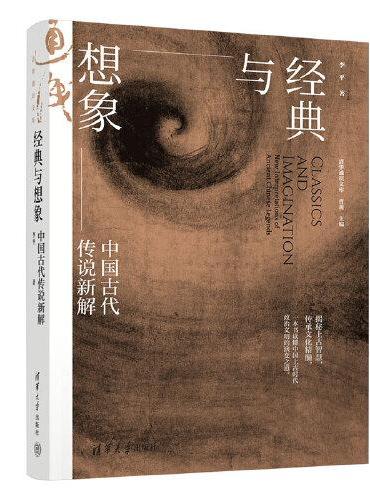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 理论与实践)构建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研究
》 售價:NT$
500.0
《
匠艺与生活:海南黎族的工艺文化
》 售價:NT$
500.0
《
我本富足
》 售價:NT$
347.0
《
英国教育史研究丛书——延续与新变:英国斯图亚特时期贵族教育研究
》 售價:NT$
505.0
《
更易上手!钢琴弹唱经典老歌(五线谱版)
》 售價:NT$
254.0
《
哲学叙事:中国与西方
》 售價:NT$
500.0
《
一人商业模式 创富新路径个人经济自由创业变现方法书
》 售價:NT$
254.0
《
经典与想象:中国古代传说新解
》 售價:NT$
398.0
編輯推薦:
◎风行三百余年的文学经典,再版次数多的英文图书之一。
內容簡介:
英语中关于垂钓的书,是汗牛充栋的,著名的,则推这一本《钓客清话》。此书初版于1653年,风行至今,已成“垂钓圣经”,是再版次数多的英文图书之一。《钓客清话》写的是垂钓,但不是钓鱼人的技术指南,而是垂钓的哲学,垂钓中体现的做人的理想、生活的理想,即简单、忍耐、厚道、知足等。
關於作者:
艾萨克·沃尔顿 (Izaak Walton,1593—1683)
目錄
钓客清话 001
內容試閱
译者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