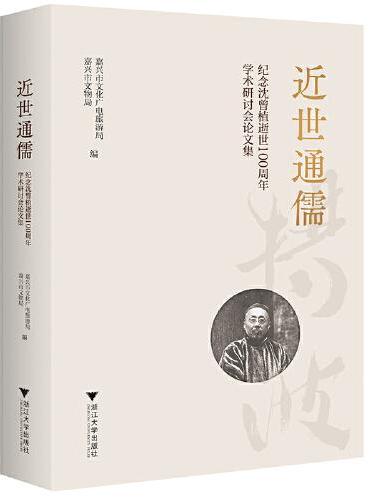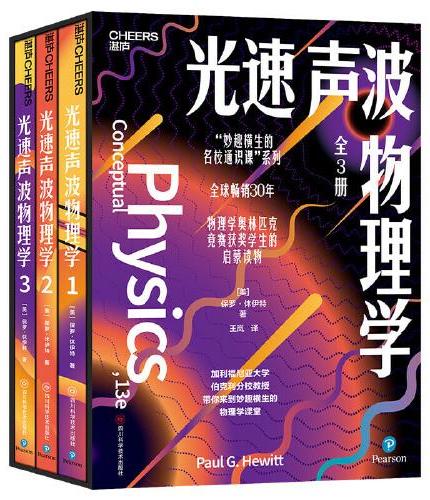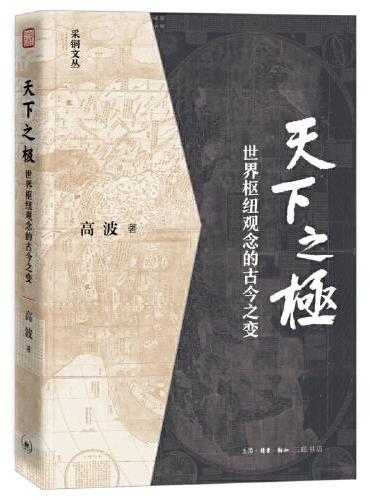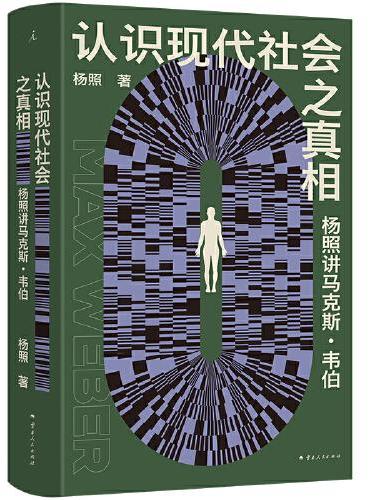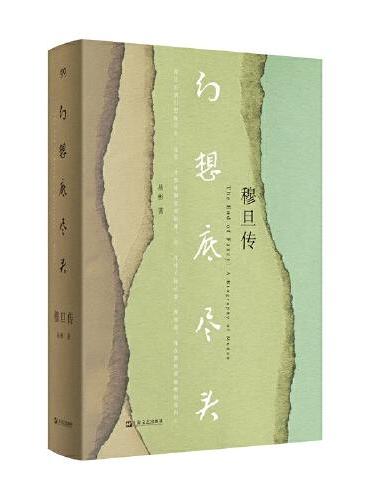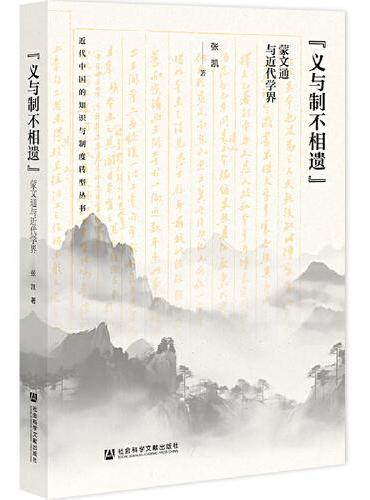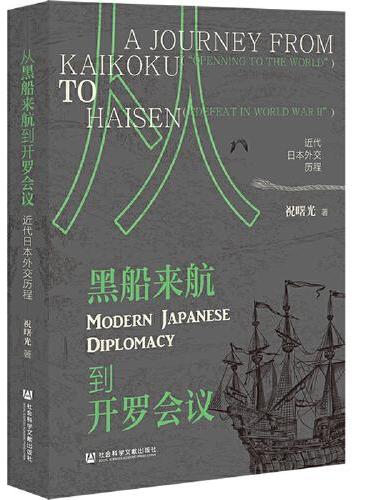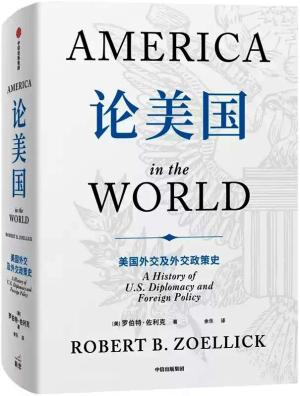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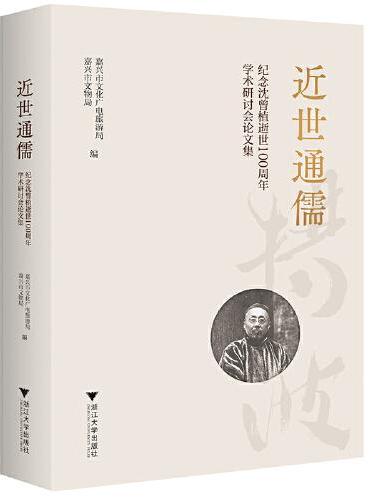
《
近世通儒——纪念沈曾植逝世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售價:NT$
85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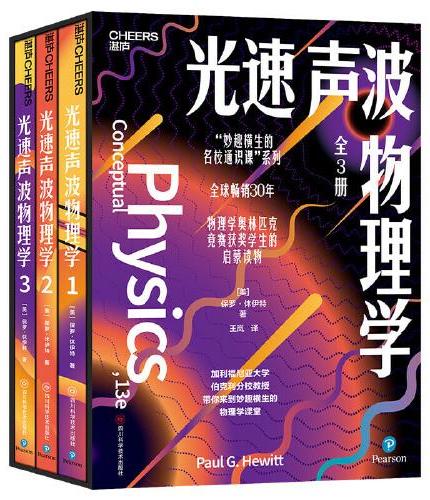
《
光速声波物理学. 1、2、3
》
售價:NT$
22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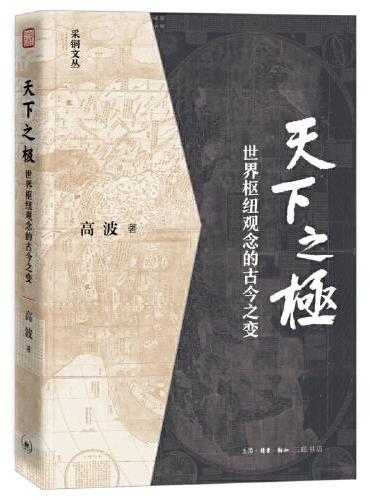
《
天下之极:世界枢纽观念的古今之变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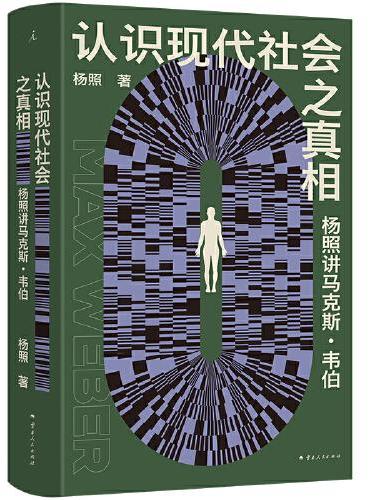
《
认识现代社会之真相:杨照讲马克斯·韦伯
》
售價:NT$
43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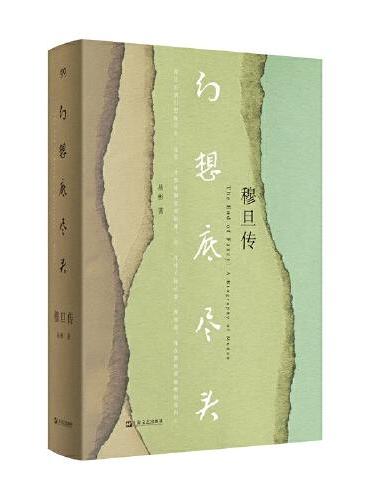
《
幻想底尽头:穆旦传(《穆旦年谱》编撰者历时二十余年心血之作,基于《穆旦评传》精心修订,文献翔实可靠,完整讲述了一位中国诗人与翻译家并不平顺的一生。)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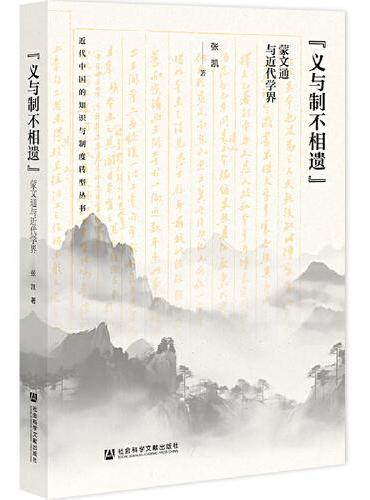
《
“义与制不相遗”:蒙文通与近代学界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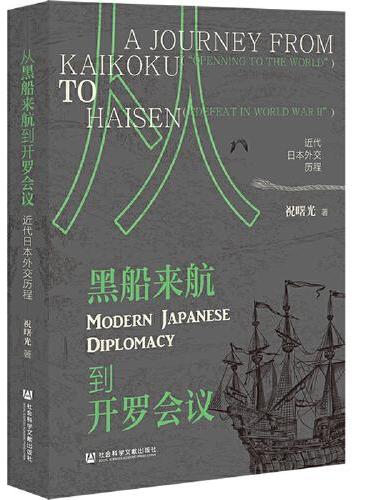
《
从黑船来航到开罗会议:近代日本外交历程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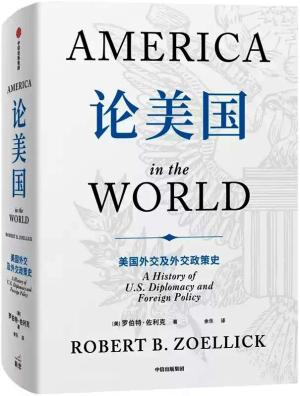
《
论美国(附赠解读手册)
》
售價:NT$
653.0
|
| 編輯推薦: |
|
《语文》五年级课本篇目,琦君经典散文大陆完整授权!近二十篇文章被选作中考现代文阅读试题
|
| 內容簡介: |
《桂花雨》是琦君的散文代表作,这本书也是琦君自己满意的一本书。本书收录有琦君散文代表作《桂花雨》《两条辫子》《一对金手镯》《看戏》等共三十余篇,内容关于童年、母亲、亲情、友情等。琦君的文笔细腻,情感充沛,文字间洋溢着少年般的纯真气质。
与性情豪爽的朋友通电话,如游山玩水;与性情温和、学养深厚的朋友通电话,如读名著。偶然一两句话,常使你获益无穷。
——《话友》
这个世界,无论是绚烂如锦,或雨歇歌沉,一颗心总是闲闲的,也清清寂寞的。生涯中的点点滴滴,记忆都十分清晰。
——《人鼠之间》
每个人或多或少藏有一份不愿向人全部吐露的心情,这并不是不坦诚,而是生活上一点含蓄的情趣。一个人如果可被透视得跟玻璃球似的,还有什么意味可言。
——《秘密》
|
| 關於作者: |
琦君(1917—2006)
原名潘希真,女,中国著名作家。从小在温州、杭州两地学习生活,曾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散文集、小说集及儿童文学作品四十余种,主要著作有《桂花雨》《青灯有味似儿时》《烟愁》《橘子红了》等。
|
| 目錄:
|
序 / 1
父?亲 / 1
母?亲 / 15
相逢是别筵 / 26
《我的另一半》补述 / 35
遥寄楠儿 / 43
妈妈,给你快乐! / 50
一对金手镯 / 54
两条辫子 / 64
童仙伯伯 / 72
话?友 / 82
遥?念 / 87
遥远的友情 / 94
千古艰难死 / 100
难忘龙子 / 105
人鼠之间 / 110
秘?密 / 116
十?三 / 124
桂花雨 / 130
乡音不改 / 134
迟来的青春 / 139
我没有绿拇指 / 144
你丢我捡 / 150
因病得闲 / 153
求医杂感 / 158
如此星辰非昨夜 / 163
读书记趣 / 166
春水船如天上坐 / 171
犹有枝 / 179
看?戏 / 187
|
| 內容試閱:
|
我幼年时,有一段短短的时日,和哥哥随母亲离开故乡,做客似的,住在父亲的任所杭州,在我们的小脑筋中,父亲是一位好大好大的官,比外祖父说的“状元”还要大得多的官。每回听到马弁们一声吆喝:“师长回府啦!”哥哥就拉着我的手,躲到大厅红木嵌大理石屏风后面,从镂花缝隙中向外偷看。每扇门都左右洞开,一直可以望见大门外停下来巍峨的马车,四个马弁拥着父亲咔嚓咔嚓地走进来。笔挺的军装,胸前的流苏和肩徽都是金光闪闪的,帽顶上矗立着一朵雪白的缨。哥哥每回都要轻轻地喊一声:“噢!爸爸好神气!”我呢,看到他腰间的长长指挥刀就有点害怕。一个叫胡云皋的马弁把帽子和指挥刀接过去,等父亲坐下来,为他脱下长靴,换上便鞋,父亲就一声不响地进书房去了。跟进书房的一定是那个叫陈胜德的马弁。书房的钥匙都由他管,那是我们的禁地。哥哥说书房里有各种司的克(手杖),里面都藏着细细长长的钢刀,有的是督军赠的,有的是部下送的。还有长长短短的手枪呢。听得我汗毛凛凛的,就算开着门我都不敢进去,因此见到父亲也怕得直躲。父亲也从来没有摸过我们的头。倒是那两个贴身马弁,胡云皋和陈胜德,非常地疼我们。只要他们一有空,我们兄妹就像牛皮糖似的黏着他们,要他们讲故事。陈胜德小矮个子斯斯文文的,会写一手好小楷。母亲有时还让他记菜账。为父亲炖好的参汤、燕窝也都由他端进书房。他专照顾父亲在司令部和在家的茶烟、点心、水果。他不抽烟,父亲办公桌上抽剩的加里克、三炮台等等香烟,都拿给胡云皋。吃剩的雪梨、水蜜桃、蜜枣就拿给我们。他说他管文的,胡云皋管武的,都是父亲忠实的仆人。这话一点不错,在我记忆中,父亲退休以后,陈胜德一直替父亲擦水烟筒、打扫书房,胡云皋专管擦指挥刀、勋章等等,擦得亮晶晶的,再收起来,嘴里直嘀咕:“这些都不用,真可惜。”父亲出外散步,他就左右不离地跟着,叫他别跟都不肯。对父亲讲话总是喊“报告师长”。陈胜德就改称“老爷”了。
陈胜德常常讲父亲接见宾客时的神气给我们听,还学着父亲的蓝青官话拍桌子骂部下。我说:“爸爸这么凶呀?”他说:“不是凶,是威严。当军官要有威严,但他不是乱发脾气的,部下做错了事他才骂,而且再怎么生气,从来不骂粗话,顶多说‘你给我滚蛋’。过一会儿也就没事了。这是因为他本来是个有学问的读书人,当初老太爷一定教导得很好,又是陆军大学期毕业,又是日本留学生,所以他跟其他的军长、师长,都不一样。”哥哥听了好得意,摇头晃脑地说:“将来我也要当爸爸一样的军官。”胡云皋跷起大拇指说:“行,一定行。不过你得先学骑马、打枪。”他说父亲枪法好准,骑马功夫高人一等,能够不用马鞍,还能站在马背上跑。我从来没看见过父亲骑马的英姿,只看见那匹牵在胡云皋手里驯良的浅灰色大马。胡云皋把哥哥抱在马背上骑着过瘾,又把我的小手拉去放在马嘴里让它啃,它用舌头拌着、舔着,舔得湿漉漉、痒酥酥的,却一点也不疼。胡云皋说:“好马一定要好主人才能骑。别看你爸爸威风八面,心非常仁慈,对人好,对马也好,所以这匹马被他骑得服服帖帖的,连鞭子都不用一下,因为你爸爸是信佛的。”哥哥却问:“爸爸到了战场上,是不是也要开枪杀人呢?”胡云皋说:“在战场上打仗,杀的是敌人,你不杀他,他就杀你。”哥哥伸伸舌头,我呢,不喜欢听打仗的事了。
幸亏父亲很快就退休下来,退休以后,不再穿硬邦邦的军服、戴亮晶晶的肩徽。在家都穿一袭蓝灰色的长袍。手里还时常套一串十八罗汉念佛珠。剪一个平顶头,鼻子下面留了短短八字胡,看去非常和气,跟从前穿长筒靴、佩指挥刀的神气完全不一样了。看见我们在做游戏,他就会喊:“长春、小春过来,爸爸有美国糖给你们吃。”一听说“美国糖”,我们就像苍蝇似的飞到他身边。哥哥曾经仰着头问:“爸爸,你为什么不再当军官、不再打仗、杀敌人了呢?”父亲慢慢儿拨着念佛珠说:“这种军官当得没有意思,打的是内仗,杀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的同胞,这是十分不对的,所以爸爸不再当军官了。”檀香木念佛珠的芬芳扑鼻而来,和母亲经堂里香炉中点的香一个味道,我就问:“那么爸爸以后也念经啰。”父亲点点头说:“哦,还有读书、写字。”后来父亲买了好多好多的书和字画,都归陈胜德管理,他要哥哥和我把这些书统统读完,做一个有学问的人。
可是,读书对于幼年的哥哥和我来说,实在是件很不快乐的事。老师教完一课书,只放我们出去玩一下,时间一到,就要回书房。我很怕老师,不时地望着看不大懂的自鸣钟催哥哥快回去,哥哥总是说:“再玩一下,时间还没到。”有一次,我自怨自艾地说:“我好笨啊,连钟都不会看。”父亲刚巧走过,笑着把我牵进书房,取下桌上小台钟,一圈圈地转着长短针,一个个钟头教我认,一下子就教会了。他说:“你哥哥比你懒惰,你要催他,遵守时刻是很重要的。”打那以后,哥哥再也骗不了我说时间没到了。只要老师限定的休息时间一过,我就尖起嗓门喊:“哥哥,上课去啦。”神气活现的样子。哥哥只好噘着嘴走回书桌前坐下来,书房里也有一口钟,哥哥命令我说:“看好钟,一到下课时间就喊‘老师,下课啦’!”所以老师对父亲说我们兄妹俩都很守时。
没多久,父亲不知为什么决定要去北平,就把哥哥带走了,让我跟着母亲回故乡。那时我才六岁,哥哥八岁。活生生地拆开了我们兄妹,我们心里都很难过,后悔以前不应该时常吵架。哥哥能去北平,还是有点兴奋,劝我不要伤心,他会说服父亲接母亲和我也去的。母亲虽舍不得哥哥远离身边,却是很坚定地带我回到故乡。她对我说:“你爸爸是对的,男孩子应当在父亲身边,好多学点做人的道理,也当见见更大的世面,将来才好做大事业。”我却有点不服气,同时也实在思念哥哥。
老师和我们一起回到故乡,专门盯住我一个人教,教得我更苦了。壁上的老挂钟又不准确,走着走着,长针就跳一下,掉下一大截,休息时间明明到了,老师还是说:“长针走得太快,不能下课。”我好气,写信告诉父亲和哥哥。父亲来信说,等回来时一定买只金手表,戴在我手腕上,让我一天二十四个钟头都看着长短针走。于是我天天盼着父亲和哥哥回来,天天盼着那只金手表。哥哥告诉我,北平天气冷,早晨上学总起不了床,父亲给他买了个闹钟放在床头几上,可是闹过了还是起不来,时常挨父亲的骂,父亲说懒惰就是没有志气的表现。他又时常伤风要吃药,吃药也得按时间,钟一闹非吞药粉不可,药粉好苦,他好讨厌闹钟的声音。也好盼望我去和他做伴,做他的小闹钟。我看了信,心里实在难过,觉得父亲不带母亲和我去北平是不公平的。可是老师说,大人有大人的决定,是不容孩子多问的。我写信对哥哥说,如果我也在北平的话,早晨一定会轻轻地喊:“哥哥,我们上学啦。”一点也不会吵醒爸爸。吃药时间一到,我也会喊:“哥哥,吃药啰。”声音就不致像闹钟那么讨人嫌了。
哥哥的身体愈来愈弱,到父亲决心接我们北上时,已经为时太晚。电报突然到来,哥哥竟因急性肾脏炎不治去世,我们不必北上,父亲就要南归故里了。兄妹分别才两年,也就成了永别。我那时才八岁,我牢牢记得,父亲到的那天,母亲要我走到轿子边上,伸双手牵出父亲。要面带笑容。我好怕,也好伤心,连一声“爸爸”都喊不响。父亲还是穿的蓝灰色长袍,牵着我的手走到大厅里坐下来,叫我靠在他怀里,摸摸我的脸、我的辫子,把我的双手紧紧捏在他手掌心里说:“怎么这样瘦?饭吃得下吗?”这是他到家后,对我说的句话,声音是那般的低沉,我呆呆地说:“吃得下。”父亲又抬头看看站在边上的老师说:“读书不要逼得太紧,还是身体重要。”不知怎的,我忽然忍不住哭了起来,不完全是哭哥哥,好像自己也有无限的委屈,父亲也掩面而泣。好久好久,他问:“你妈妈呢?”我才发现母亲不在旁边,原来她一个人躲在房中悄悄地落泪。这一幕伤怀的情景,我毕生不会忘记。尤其是他捏着我的手问的句话,包含了多少爱怜和歉疚。他不能抚育哥哥长大成人,内心该有多么沉痛。我那时究竟还幼小,不会说安慰他的话,长大懂事以后,又但愿他忘掉哥哥,不忍再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