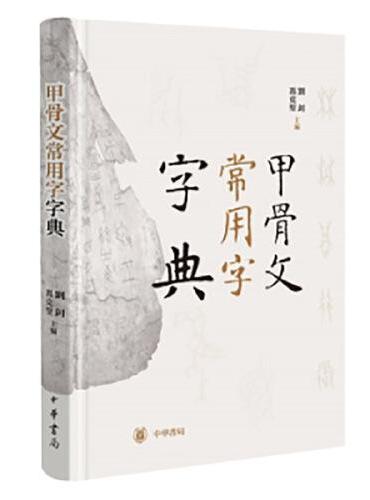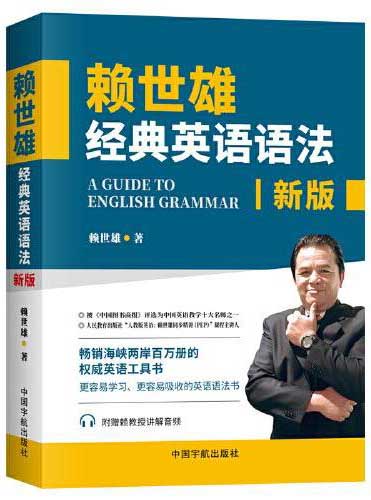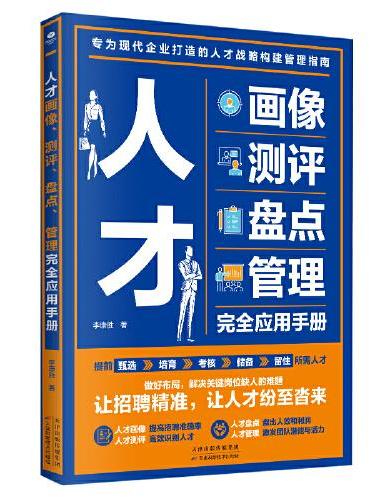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流动的白银(一部由白银打开的人类文明发展史)
》
售價:NT$
296.0

《
饮食的谬误:别让那些流行饮食法害了你
》
售價:NT$
296.0

《
三千年系列:文治三千年+武治三千年+兵器三千年
》
售價:NT$
9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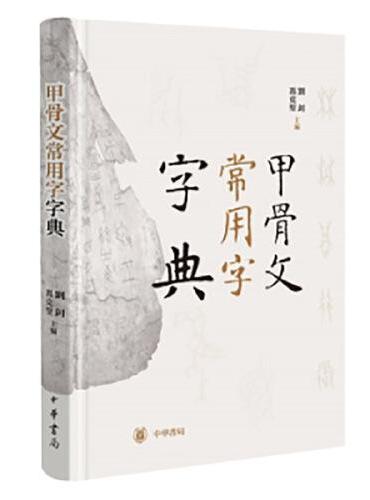
《
甲骨文常用字字典(精) 新版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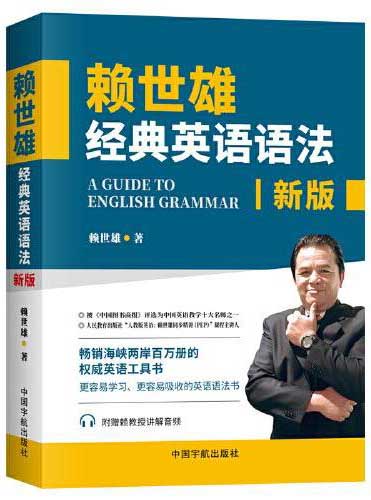
《
赖世雄经典英语语法:2025全新修订版(赖老师经典外语教材,老版《赖氏经典英语语法》超32000条读者好评!)
》
售價:NT$
305.0

《
影神图 精装版
》
售價:NT$
653.0

《
不止于判断:判断与决策学的发展史、方法学及判断理论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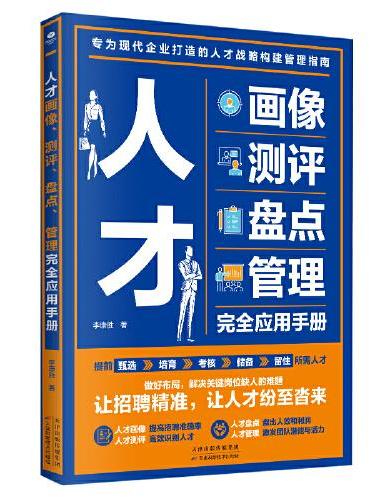
《
人才画像、测评、盘点、管理完全应用手册
》
售價:NT$
254.0
|
| 編輯推薦: |
回望70年代至80年代艰难岁月的长篇力作,比《活着》和《平凡的世界》更真实,也更励志。阿来给予厚望的作家,国内重要文学阵地——期刊《十月》封面推荐
从大山中走出的杜阳林,作品根植于丰富充实的现实生活,行文间充满真情与质朴。兼之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敏锐,视角独特、充满力量。
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故事,个人的奋斗史与“大时代”融合,写出乡村十年的转变。人物对话中使用川北方言,字里行间可品味浓厚的四川地域特色。真实的地方,虚构的人物,一个村庄折射出整个人类社会的善恶美丑。“也许人年轻时,都会面对他自己的迷惘和困惑,如今年轻人的苦恼,和我们年轻时代也许有所迥异和区别,但那种“如同行走在黑暗隧道”的感觉是共通的。我们用自己的岁月经过摸索、试探与实践,走出了一条道路,并不是说这条路适合于当下的年轻人,但这种面对困惑不退却的精神,在暗中苦苦护住一点光亮的执着,也许会为年轻读者带来一些启迪,一点鼓舞。”
——杜阳林
|
| 內容簡介: |
《惊蛰》是四川作家杜阳林撰写的半自传体的长篇小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四川北部阆南县观龙村,少年凌云青聪慧早熟,坚强好学,但苦难却如影随形:寒冷和饥饿的折磨,乡邻旁亲的刁难与欺辱……十年岁月,几番生死劫难与惊蛰之醒,凌云青完成了野蛮的生长。时代的列车载着这个倔强少年和他沉重的过去,无可阻挡地奔向未来。
小说风格质朴,叙事语言融入川北方言,独具特色。整部作品通过一个农村少年与生活抗争的成长史,彰显了个体生命向善、向上的昂扬精神,同时也呈现了中国乡村大地上的人物群像和时代的惊蛰之变。
|
| 關於作者: |
杜阳林
四川省社科院城市文化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中国作协会员、四川省作协小说专委会副主任、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曾任《华西都市报》首席记者、部门主任,《成都女报》总编辑;作品散见《十月》《收获》《中国作家》《美文》《海燕》《湖南文学》《四川文学》《青年作家》等文学期刊;著有《惊蛰》《步步为营》《长风破浪渡沧海》等小说和散文集;四川南部县人,长居成都。
|
| 目錄:
|
上
章...............................................................................003
第二章...............................................................................020
第三章...............................................................................035
第四章...............................................................................054
第五章...............................................................................065
中
第六章...............................................................................079
第七章...............................................................................098
第八章...............................................................................117
第九章...............................................................................134
第十章...............................................................................150
第十一章..........................................................................160
第十二章...........................................................................170
第十三章...........................................................................185
下
第十四章...........................................................................201
第十五章...........................................................................220
第十六章...........................................................................233
第十七章...........................................................................243
第十八章...........................................................................257
第十九章...........................................................................278
第二十章...........................................................................294
第二十一章.......................................................................308
|
| 內容試閱:
|
上
凌云青坐上了绿皮火车,但他并不知道,这趟远方求学旅程的尽头,命运会画出怎样的曲线。他的脸上尚未褪尽青涩,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分明有着一份热切的期盼。
车轮轰隆向前,家乡风物一帧帧地消失于脑后。车身摇晃轻颤,父亲去世后的艰辛时光,犹如此刻车窗玻璃折射的微微反光,在这位十四岁少年的脑海中一幕幕闪过。
凌云青沉浸在过往的回忆中,像是和从前的自己,做一次郑重告别。
章
一
一阵撕心裂肺的号哭,打破了阆南县观龙村的宁静。那座四面漏风的茅屋传出的悲啼之声,瞬间揪住了人们的心。
在家午饭的一些村民小声嘀咕:凌永彬这样高高大大的一个汉子,咋个说走就走了呢?他这一撒手,苦了徐秀英和五个娃娃呀!
那一年的一月份,敬爱的周总理去世,村民们聚在晒场哭了一场。大人小孩的悲伤,让天上的月亮不复皎洁,拉了一朵厚云遮住半张脸。凌永彬又哭又喘、又抖又咳,旁边的人拼命捶拍他的后背,劝他莫要难过。哪晓得才几个月时间,他把自己也哭到了“那边”呢?
村民丢下碗筷拥出房门,相继前往凌家,帮忙料理一些后事。
岳红花冲在前头,跨进凌家门槛。徐秀英软瘫瘫地坐在地上,身体倚着床架那堵黑乎乎的墙。上官云萼正托起秀英下巴,含了口茶水,喷向她的脸。
上官云萼走哪儿都像清朝老爷们一样,右手托个小小的陶瓷茶壶,左手夹着烟卷。她这种派头,观龙村的女人们看了大为诧异,背后议论纷纷,当面却不敢冒句杂音。
上官云萼连喷了三口水,徐秀英悠悠地醒转,又扑向床沿,却扑了个空。上官云萼对她努努嘴:“老周把门板拆了,让你家老凌换过老衣,躺到那上头。”徐秀英“嗯”一声,忍住泪水,想掏出两句感谢的话,舌头却打了结,干干地吞了两口唾沫,软软地搭着上官云萼一条胳膊,站起身来,呆涩地望向她的孩子们。
凌家老大采萍刚满十三岁,套的褂子皱巴巴地箍在身上,粗布背带在她身后紧紧绕扎几圈,趴伏着头发稀黄的五弟云白。采萍承接着母亲悲痛欲绝的目光,不敢哭出声来。比她小六岁的采芹,像被忽降的变故压得年龄后缩了一截,六神无主的眼睛被手揉得通红。云白闭着眼睛,偶尔冒出两声啼哭,犹如小猫的呜咽,受到感染的采芹狠狠地打了个哆嗦。
云鸿和云青兄弟俩不知道去了哪里。秀英的眼珠木木的,仿佛要靠这一眼又一眼的“看”,才能将缥缈辽远的灵魂拉回来。
岳红花凑近徐秀英的额头,额头有一块鸡蛋大的青肿。她关心地询问:“你脑门顶个青包干啥子?痛不痛,要不我回去拿点清油,给你擦来消肿?”
岳红花说得体贴,却听上官声音板板地对她道:“那你还不赶紧回去端些清油。”
岳红花说不清为何会惧怕上官,觉得自己对徐秀英的关心过了头,她平时都舍不得吃的清油,咋能真的让给她使用呢?要怪就怪自个儿这张插不上门闩的嘴巴。她极不情愿地往家走,见刘翠芳沉着一张脸孔走向凌家,赶紧堆起一脸笑褶子招呼:“你这个嫂子,这么快就赶来帮忙了。”刘翠芳却往地上啐了一口:“哪个舅子想来帮忙!”岳红花亲亲热热地靠过去,不管刘翠芳狐臭不狐臭,指头点了点茅草屋,又飞快地指了指自己额头:“刚刚撞得晕死过去了!”
“真撞死才好!”刘翠芳似乎吃了炮仗,开口便有火药味。岳红花呲着一口黄牙,咯吱咯吱笑:“要是里面那个真的撞死了,你还不得帮着人家养娃儿?”
刘翠芳吐出一句气鼓鼓的话:“哪个背时的才带他凌家的娃儿!”岳红花“嘿”一声,脸上露出了然的笑意。
刘翠芳原本不想来凌家。陈金柱那个欺软怕硬的货,只敢在老婆面前挥舞拳头。他不想到凌家,却逼着自己女人去,免得村里人戳他脊梁骨。刘翠芳到底害怕男人火气一上来,打打杀杀的吓死个人,这才绷着一张脸,来踏凌家的门槛。
凌家屋里乱哄哄的,徐秀英的泪珠子打湿了前襟,几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粗针大线地帮忙缝制孝帽孝衣。她们间或劝上两句,被新寡妇的遭遇勾起了自己一腔伤心事,倒呜呜哭将起来。
云白原本半睡半醒,忽然放开喉咙哭叫。他挣扎着向后翻仰,挣得眉毛发红,尖厉的哭声如同一枚枚刀子,插进屋里每个人的耳膜。
采萍面红耳赤,微微屈膝抖颤,发出“哦哦”的声音,用这种节奏的晃动安慰云白。但她惯用的做法失去了作用,云白每一声哭叫都用尽全力,小小的身体发出如此大的声量,真是让人奇怪的事。
屋里屋外几个女人凑过来,七手八脚地帮助采萍解开背上的背带,将云白抱起。五六双手轮了个遍,嘴里发出各种软糯黏稠哐哄娃儿的话,却没有让云白止住哭声。
“给我。”上官云萼开了口,连小茶壶都没搁,弯着手臂,将云白塞到了徐秀英怀里。
“娃娃饿了。”上官云萼的话说得威严而又不能抗拒。
秀英一转动身体,关节就“吱嘎”响,像是一架年老失修的机器。她好不容易才弄明白上官的意思,苍白的脸庞泛起一丝愧意:“前两个月,奶水就回了。”
秀英没有奶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永彬的肺结核延宕了几年,虽说身子虚得像被虫子蛀过的柱子,但也“稳定”着。谁晓得就在这个暑热天,病情忽然恶化,永彬开始大口吐血。秀英照顾丈夫、操持农活,家里大人娃儿,哪个都要操心。那段时间,她就没睡一个囫囵觉。
家里的事不让人安生,外面的消息更令人心惊肉跳。广播里有个声音,沉痛地说唐山闹了大地震,不晓得死了多少人。虽然阆南地处西南地区,离唐山上千公里,消息传来,还是让所有人忐忑难安。村里流传着各种传闻,说是“地乌龟”抖上几抖,便让唐山地裂山崩,倘若“地乌龟”再发脾气,动弹得更厉害一点,不晓得阆南县会不会也跟着翻过来。村民睡到半夜,不时有人尖叫着:“地震啦!”人一吼,狗就吠,整个村庄不得安宁。凌家几个孩子坐起来抽泣哭嚷,当妈的少不得一通安慰。秀英有时通宵不敢闭眼,生怕一家人病的病小的小,被檩子墙头埋到地下。
生下老五云白,秀英身子闹了虚空,彻底唱起反调来,无论云白怎样努力吮吸也没用,她的乳房变成了一对空荡荡的摆设。哺育了四个孩子的胸脯,如今竟挤不出一滴奶水来。
采萍懂得替妈脸红了,她跨前半步建议:“我去调点糊糊给云白吃吧。”上官云萼充耳不闻,两道利剑一般的目光看向秀英,那眼神,能将秀英脸上灼出两个小洞来。
秀英下意识地避开上官的视线,右手机械地解开了衣襟。云白已经闭着眼睛耍了好久的横,糊了满脸的眼泪鼻涕,却未消减他的敏感。人间的婴儿是靠直觉行事的小神通,云白准确无误地一口噙住了秀英的乳头,小小的腮帮子,一鼓一瘪,一张一息。令秀英吃惊的事发生了,仿佛有一股热流,从她手板、脚板开始发烫,急急匆匆跌跌撞撞,抢着挤着往乳房奔跑。香甜的乳汁,已经欢快顺畅地滑下了云白的喉咙。
上官云萼意味深长地看了秀英一眼,漫不经心地说道:“你是当妈的呀。”
秀英抱着云白柔软的身子,眼泪滑到鼻梁,聚成亮晶晶的一颗。她顾不上擦掉,现在终于明白上官的用意了,她还有五个儿女尚未成人,旁人都死得,就她死不得。
二
在凌家帮了一天忙,上官云萼有些疲累,临走前嘱咐采萍:“有事就到家里喊我。”采萍嗯嗯地点头,眼里迅速包起了碎银一样的眼泪。
刚来观龙村时,上官云萼不愿出门,将自己关在漏风的小屋里整整一个月。这里离省城远,没那么多“革命群众”,揪着扯着要看你的热闹,不允许谁“缩进乌龟壳里”,逼你站在街头示众。上官经过一个月与世隔绝的躲避休憩,才算在鬼门关转过身还了阳。如今,一晃多年过去,她心中早就藏了一幅“地图”,就算闭着眼睛,在观龙村也不会失了方向。
上官云萼抬起头,视线扫过高高的野棉花山,重重呼出一口气。
家住山脚下,上官刚搬来那段时间,夜里总做噩梦,梦见山塌了,将她压在下面,甚至能感受骨头深处慢慢攀上来的疼痛。待的时间久了,很久没做这种怪梦,不过今日体力有些透支,倒像是那时被梦深深魇住的难受感觉了:脑袋眩晕,双眼发花,脚底虚浮。上官转了转脖子,拍了拍后颈,轻咳两声,拐向左边大路。凌家兄弟从右边的一条小路走了过来。
右边本没有路,杂草中生长着苍耳和火棘,观龙村的人不懂火棘学名,管它叫“红军粮”。传说以前红军路过观龙村,饿得要命,却不肯吃老百姓一粒粮食,采摘这红而小的果实饱腹。火棘虽能救命,此刻却让凌云鸿和凌云青吃尽苦头。
“你没长手是不是?没长手你长了脚啊,没长脚还长了嘴,未必你比云白还不如,云白好歹还长出四颗门牙,你连门牙都没长?”八岁的云鸿责骂四岁的弟弟云青,不管不顾地拉着他,走上右边这条不算路的小路。云青被火棘枝条上的小刺刮伤了脖子和手背,留下一道道血痕,亦步亦趋地跟在云鸿后面。云鸿也刮伤了手脚,可他正在气头上,感受不到身体的疼痛,一心一意地“讨伐”云青。
云青刚才被陈富贵推到水沟里,也是这个模样,一声不吭,不愿还手。云鸿气得直骂:“打死你都不晓得回句嘴!”
云青越是闷不作声,云鸿越是怒气难平。弟弟的“迟钝”反应,让他感到心头像揣了一只乱跳的兔子,不听管束。就云青这怂样,以后还不晓得要受外人多少欺负。
父亲两腿一蹬,“走”了,这让云鸿心生害怕。大人们只晓得慌慌张张地叠元宝、印纸钱、找孝布,再来几个婶婶和大嫂,拉着秀英的手一通嘤嘤地抽泣。她们就算哭破天,或者流一碗眼泪,能把爹哭回来吗?爹再也睁不开眼了,云鸿是家里的长子,他想不通:自己咋就成了家里的那个男人了呢?
云鸿撞见大伯家的陈富贵欺负云青。陈富贵脸盘子的肉,比玉米饼子还厚,仗着高出同龄伙伴半个头,在村里使蛮占强。富贵始终对云青看不顺眼,在碾子旁边,二话不说,将云青一把推到水沟里。水沟一点浅水,淹不死人,却弄得云青成了个脏兮兮的泥猴儿。云青不哭不闹,从淤泥里爬上来,既不报复陈富贵,也没咬他一口。
云鸿是在不远的菜园边看到的。他怒不可抑,握紧拳头向陈富贵冲去,陈富贵拉起吮吸大拇指的妹妹吉祥,跑得没了踪影。云鸿的火气索性发泄到云青身上。
云鸿喋喋不休地骂了云青一路,云青默默忍受被尖刺刮出血痕的疼痛。他们跌跌撞撞,走出了遍布火棘的小路。兄弟俩居高临下,所站的土坡位置与茅屋烟囱一样高,云青没头没脑地告诉云鸿:“富贵说,他妈因为我们妈,差点挨了他爸的打。”云鸿口干舌燥,弟弟并未“认真反思”,还在想陈富贵那些不着调的屁话。
云鸿推了云青一把:“那个瓜娃子说的话,你也要当真?他妈那么泼,咋会因为我们妈挨打?”
云青低下视线,两只脚板糊满泥污,又划拉了血道子。他抬起右脚,在左脚背上蹭了蹭,郑重其事抛给云鸿一个问题:“哥,啥叫死?”
云鸿蓬起了一股邪火,仿佛从父亲真正离开他们的那个清晨开始,这股邪火就再也没有消退过。在他完全没有做好准备之时,一股不由分说的蛮横力量逼云鸿硬着头皮当了“凌家年长的男人”。他可以拒绝吗?可以逃避吗?天大地大,好像找不到一个地方申诉。
云鸿找不到人说话,心里有些窝火。当然,即使能找到像周爷那么有见识的人,云鸿照样不晓得怎么开口。大人懂个屁,只会拿哀伤的眼神剜云鸿一记,语重心长叮嘱他:“你以后要懂事,你妈你弟妹全都靠你了。”云鸿委屈迷惘,他被这火苗炙烤着、折磨着、追赶着,只好瞪着云青发脾气:“死死死!你晓得个啥!白吃了几年饭,咋个啥都不懂!”
云鸿恨唧唧地离开了云青。云青呆呆地看着哥哥的身影,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被富贵一把推下水沟都没哭,两脚被刺丛勾拉受伤也没哭,哥哥丢下他,他望着自家熟悉的茅草屋顶,竟然有一种陌生的潮湿情绪袭上来。云青眨了两下眼,试图眨走眼前那一层蒙蒙的泪雾。
泪雾中走来了姐姐采芹。
云青本能地和三姐采芹亲近些。二哥云鸿平时不爱和云青玩耍,觉得他呆头呆脑的,碍手碍脚。采芹长云青三岁,却是兄弟姊妹中为瘦小胆怯的,她总爱缩着肩膀耷拉脑袋,说话声音像蚊子,两句话不对付就落下泪蛋蛋。采芹老是害怕云鸿凶她,平日喜欢和云青待在一起。此刻,她拉住云青的手,一边打噎一边抽泣。
“大姐骂我。”采芹向弟弟云青诉说委屈。云青忘记了自己的伤痛,急忙问:“大姐为啥骂你?”“大姐说我在家里打噎,吵着爹升不了天,她一生气,就把我赶出来了。”
云青仿佛在黑暗中,感受到是谁擦亮了一根火柴,瞥到一丝微光,模模糊糊通晓了一些事。死是什么呢?死是到哪里去呢?就是升天!
云青看向烟囱,他不无困惑地想:妈烧饭腾起的烟子,原来每天都要死上一次。
采芹不是故意打噎的,但就是一直止不住,就连秀英也比她好不到哪里。村里的福喜婆婆,一边颤巍巍地蘸着清油,擦抹秀英额头上的青包,一边毫不客气地责怪:“莫出息,男人死了你就要死要活的,永彬晓得你这么莫出息,要怨自己莫得眼力劲,后悔当年娶了你!”
秀英指头绕着一条洗得透光的手绢,沉沉地吸饱了泪水。福喜婆婆平日笑眯眯善么么的,说起话来这么重,一句一句,像石头密密匝匝地砸向秀英:“到底有啥子好哭的,三十好几的人了,连这个都不明白吗?你多流一滴泪,你男人身上就多一分湿,到时你把他弄得湿嗒嗒重乎乎的,看他咋个莫牵莫挂地离开你们!”
这话将采芹也镇住了,却没止住她的泪水。她一边对云青转述,一边用手背擦拭脸面孔,眼睛肿成了两只桃子。她们听了福喜婆婆的劝,吓得一个劲儿地回憋眼中的泪水。采芹打噎流泪,烦得采萍说她待在家里现世添堵。她伤伤心心走出来,看到弟弟云青,此刻成为她温暖的依靠。
姐弟俩紧紧拉着手,云青脑瓜里还没转明白:爹的死,和炊烟又有啥关系?母亲每天都让炊烟升起两次,那爹是不是很快又能回来?
天黑了,远处传来老鸹阴恻恻的叫声,钻进了人的耳朵里。
|
|